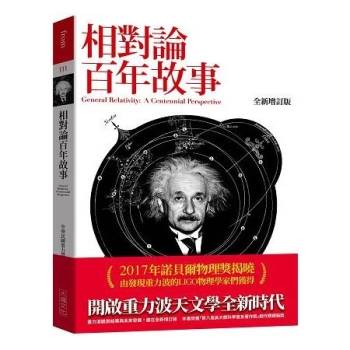廣義相對論與重力波
愛因斯坦於 1915 年發表廣義相對論,寫下愛因斯坦場方程式,描述時空與質量(也就是能量)的交互作用。在這個目前被視為「重力的標準模型」的愛因斯坦理論下,牛頓的重力場其實是能量所造成的彎曲空間表象。可以想像在一個軟的彈簧床中央放一粒鉛球,鉛球彎曲了床面的二維空間並微微下陷一般。這時如果扔幾顆乒乓球在這個彎曲的二維床面上,且想像沒有任何滾動摩擦力或空氣阻力,這些乒乓球將不會走直線路徑,而會偏向中央,有些直接往鉛球撞去,有些繞著鉛球轉,有些則因為速度太快或距離太遠而直接滾到外面去。每一個時刻、每一點床面的下陷程度,也就是曲率,都有些許不同。如果將這些不同時刻的二維面堆砌起來,就形成三維空間。這個概念再延伸下去,將三維空間沿第四個維度堆砌,就對應到所熟悉的四維時空。如果類比到我們的太陽系運動,太陽(如同鉛球)造成一個近乎靜態的時空曲率,影響周遭行星(乒乓球)運動,這些行星的運動同樣也會對鄰近的時空曲率有一些小小的影響,但與太陽相比,相當微弱。
在愛因斯坦的解釋下,牛頓重力中的運動軌跡,如掉下的蘋果、星球的軌道,僅僅是那些物體順著彎曲時空所走的最短路徑。這一路徑僅與物體的質量有關,而和內部結構及其他性質(如電荷,自旋等)無關。並且這個全新的的重力理論,符合十年前愛因斯坦自己所提出的狹義相對論框架,不但精確地解釋觀測現象並通過精密實驗的檢驗,也解決了牛頓重力中存在瞬時力的窘境。愛因斯坦理論的數學細節及計算過程也許較複雜,但他將四個基本作用力之一的重力,以幾何的語言描述,使人類對「時空」本質的理解向前邁了一大步。誠如他的名言: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萬物應盡可能地使其簡化,直至不過簡為止)。要強調這裡所說的簡化,並不是指計算操作上的簡化,而是這個描述足夠精煉,並且放諸四海皆準。幾何,正是目前描述重力最恰當的方式。在廣義相對論發表的隔年,德國卡爾.史瓦西就在一戰的蘇俄前線服役中,得出愛因斯坦方程在真空中的球對稱解,描述任意球對稱天體所造成的時空。這就是史瓦西黑洞,一個物質集中在足夠小的區域後,經重力塌縮所形成的緻密物體,所造成的曲率連光也無法脫離。黑洞的概念在十八世紀後期就出現了,但直到 1967 年,約翰.惠勒才靈光一閃提出黑洞一詞。由於黑洞的概念太過不可思議,而且在黑洞中心的奇異點暗示著所有物理定律在那失效,因此黑洞的真實性一直備受討論。不過物理學家仍然很快地將廣義相對論的純數學結果應用在天文與宇宙的尺度上,並以新的時空概念來討論宇宙演化。
愛因斯坦方程式中的宇宙常數,就是愛因斯坦自己所加入的擴張項,以抵銷宇宙物質自己的重力吸引而維持他認為的靜態的宇宙。史瓦西黑洞也推廣到帶有自旋(1963年)甚至帶電荷(1965 年)的系統,後來都對應到實際上可能的天文實體。1964 年後來自天鵝座強大的 X 射線訊號的觀測,與最近對銀河系中心人馬座鄰近星體運動軌跡的分析,更加支持了黑洞的存在,並推測大部分的星系中心都可能存在百萬倍太陽質量的黑洞。以現代的恆星演化模型看來,那些密度與原子核相當的緻密星體,如黑洞、中子星及白矮星等,是大質量恆星燃燒殆盡死亡後的結果,但對於 20 世紀初的科學家簡直難以想像,特別是當時原子核的概念才剛被拉塞福(Ernest Rutherfood, 1871-1937)提出。
再回到剛剛的彈簧床例子中,假設這時的鉛球重重地摔在床面中央,床面會開始震動,每一點的曲率發生週期性變化,並且如漣漪般向外傳遞,這種時空曲率的波動即是重力波。但請注意這僅是幫助理解的圖像,並不十分準確。因為鉛球墜到床面上產生的震盪,對一個只有三維時空概念的生物而言,就好像是由一團反覆憑空出現又消失的質量所造成,直接推廣到我們的四維時空是違反能量守恆的。嚴格來說,重力波主要是由質量的「四極矩」(quadruple)加速變化所產生,例如非柱狀對稱物體的轉動,或是雙星互繞。張開雙臂原地旋轉也會產生重力波,不過遠遠小於天文上恆星尺度運動所造成的重力輻射。在廣義相對論發表的隔年,愛因斯坦發現,他的重力場方程式在弱重力場近似下具有波動特性,正如電荷的加速會輻射出電磁波一樣,質量的加速(確切的說,是質量四極矩的加速變化)也會輻射出重力波(在大陸地區稱之為引力波,以區分流體力學中因重力或浮力所造成的波動)。這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波,它們的傳播都需要時間,同樣以光速傳遞能量、動量、與角動量,符合狹義相對論中的因果概念,並非像牛頓重力理論下的即時傳遞。想像太陽突然從世界消失(雖然這違反能量守恆),生活在地球上的我們也需要相隔約八分鐘才會感受到太陽消失後引力的變化。
新型態的輻射意味著新的觀測媒介。讓我們回顧歷史,天文觀測除了讓我們能看得愈遠、看到更古老的宇宙,全新的觀測方式總是帶來令人驚奇的結果及革命性的影響。伽利略在 1609 年以自製望遠鏡開啟天文光學觀測新頁,1930 年代的央斯基(Karl Jansky, 1905-1950)所做的銀河系無線電觀測,及 1950 年代 X 射線與 1960 年代後的伽瑪射線觀測,每一次的技術突破都帶來意外的發現,呈現出的宇宙圖像遠比肉眼下的更加活躍激烈,而且還給出各種不同面向的資訊,如無線電波帶來類星體、脈衝星與宇宙微波輻射,提供黑洞、中子星及大爆炸的餘暉等觀測上的證據,或是伽瑪射線反應出恆星內部以及超新星爆炸的資訊等。這些發現的累積讓人們拼湊出更豐富的宇宙樣貌與演化史,並且描繪出其背後形成的神祕機制。這些高能天文物理現象,往往伴隨著高質量高密度的物質與極端強大重力場的相互作用,因此隨著觀測技術的突破,廣義相對論的精確時空描述也變得更為重要,扮演探索未知宇宙的嚮導。而另一方面,遠處的星空也成為檢驗廣義相對論或其他基本理論的絕佳場所,測試我們對基本物理學的認識。幸運的,目前我們正處在另一次突破的關鍵時刻;除了電磁波觀測,以及最近宇宙射線或微中子偵測,重力波測量即將開啟探索宇宙的另一扇窗,讓我們得以一窺宇宙深處的各種驚奇現象。人們從懷疑黑洞這樣的奇特物體的存在開始,到終於獲得間接的觀測證據;從生怕黑洞奇異點的存在,讓所有物理定律失效,到嘗試提出各種解釋來彌補這理論上的矛盾――一代代的科學家們不斷努力突破未知的邊界,提升了人類文明的高度。中子星的概念,最早也是為了解釋恆星能量如何產生的問題開始,而在 1930 年代所做的大膽假設,現在也早已成為恆星演化的標準模型。在那一段各種新現象新理論交錯混雜、晦澀不明的時代,相對論與核物理各自在極大與極小的尺度下摸索時空與物質的本質,並逐漸歸納出愈來愈宏觀的圖像。而將近一個世紀重力波理論的發展,在經歷近半個世紀的觀測研究,也將在日後的大型觀測與模擬計算中獲得直接證實與天文應用。
愛因斯坦於 1915 年發表廣義相對論,寫下愛因斯坦場方程式,描述時空與質量(也就是能量)的交互作用。在這個目前被視為「重力的標準模型」的愛因斯坦理論下,牛頓的重力場其實是能量所造成的彎曲空間表象。可以想像在一個軟的彈簧床中央放一粒鉛球,鉛球彎曲了床面的二維空間並微微下陷一般。這時如果扔幾顆乒乓球在這個彎曲的二維床面上,且想像沒有任何滾動摩擦力或空氣阻力,這些乒乓球將不會走直線路徑,而會偏向中央,有些直接往鉛球撞去,有些繞著鉛球轉,有些則因為速度太快或距離太遠而直接滾到外面去。每一個時刻、每一點床面的下陷程度,也就是曲率,都有些許不同。如果將這些不同時刻的二維面堆砌起來,就形成三維空間。這個概念再延伸下去,將三維空間沿第四個維度堆砌,就對應到所熟悉的四維時空。如果類比到我們的太陽系運動,太陽(如同鉛球)造成一個近乎靜態的時空曲率,影響周遭行星(乒乓球)運動,這些行星的運動同樣也會對鄰近的時空曲率有一些小小的影響,但與太陽相比,相當微弱。
在愛因斯坦的解釋下,牛頓重力中的運動軌跡,如掉下的蘋果、星球的軌道,僅僅是那些物體順著彎曲時空所走的最短路徑。這一路徑僅與物體的質量有關,而和內部結構及其他性質(如電荷,自旋等)無關。並且這個全新的的重力理論,符合十年前愛因斯坦自己所提出的狹義相對論框架,不但精確地解釋觀測現象並通過精密實驗的檢驗,也解決了牛頓重力中存在瞬時力的窘境。愛因斯坦理論的數學細節及計算過程也許較複雜,但他將四個基本作用力之一的重力,以幾何的語言描述,使人類對「時空」本質的理解向前邁了一大步。誠如他的名言:Everything should be made as simple as possible, but not simpler(萬物應盡可能地使其簡化,直至不過簡為止)。要強調這裡所說的簡化,並不是指計算操作上的簡化,而是這個描述足夠精煉,並且放諸四海皆準。幾何,正是目前描述重力最恰當的方式。在廣義相對論發表的隔年,德國卡爾.史瓦西就在一戰的蘇俄前線服役中,得出愛因斯坦方程在真空中的球對稱解,描述任意球對稱天體所造成的時空。這就是史瓦西黑洞,一個物質集中在足夠小的區域後,經重力塌縮所形成的緻密物體,所造成的曲率連光也無法脫離。黑洞的概念在十八世紀後期就出現了,但直到 1967 年,約翰.惠勒才靈光一閃提出黑洞一詞。由於黑洞的概念太過不可思議,而且在黑洞中心的奇異點暗示著所有物理定律在那失效,因此黑洞的真實性一直備受討論。不過物理學家仍然很快地將廣義相對論的純數學結果應用在天文與宇宙的尺度上,並以新的時空概念來討論宇宙演化。
愛因斯坦方程式中的宇宙常數,就是愛因斯坦自己所加入的擴張項,以抵銷宇宙物質自己的重力吸引而維持他認為的靜態的宇宙。史瓦西黑洞也推廣到帶有自旋(1963年)甚至帶電荷(1965 年)的系統,後來都對應到實際上可能的天文實體。1964 年後來自天鵝座強大的 X 射線訊號的觀測,與最近對銀河系中心人馬座鄰近星體運動軌跡的分析,更加支持了黑洞的存在,並推測大部分的星系中心都可能存在百萬倍太陽質量的黑洞。以現代的恆星演化模型看來,那些密度與原子核相當的緻密星體,如黑洞、中子星及白矮星等,是大質量恆星燃燒殆盡死亡後的結果,但對於 20 世紀初的科學家簡直難以想像,特別是當時原子核的概念才剛被拉塞福(Ernest Rutherfood, 1871-1937)提出。
再回到剛剛的彈簧床例子中,假設這時的鉛球重重地摔在床面中央,床面會開始震動,每一點的曲率發生週期性變化,並且如漣漪般向外傳遞,這種時空曲率的波動即是重力波。但請注意這僅是幫助理解的圖像,並不十分準確。因為鉛球墜到床面上產生的震盪,對一個只有三維時空概念的生物而言,就好像是由一團反覆憑空出現又消失的質量所造成,直接推廣到我們的四維時空是違反能量守恆的。嚴格來說,重力波主要是由質量的「四極矩」(quadruple)加速變化所產生,例如非柱狀對稱物體的轉動,或是雙星互繞。張開雙臂原地旋轉也會產生重力波,不過遠遠小於天文上恆星尺度運動所造成的重力輻射。在廣義相對論發表的隔年,愛因斯坦發現,他的重力場方程式在弱重力場近似下具有波動特性,正如電荷的加速會輻射出電磁波一樣,質量的加速(確切的說,是質量四極矩的加速變化)也會輻射出重力波(在大陸地區稱之為引力波,以區分流體力學中因重力或浮力所造成的波動)。這兩種截然不同類型的波,它們的傳播都需要時間,同樣以光速傳遞能量、動量、與角動量,符合狹義相對論中的因果概念,並非像牛頓重力理論下的即時傳遞。想像太陽突然從世界消失(雖然這違反能量守恆),生活在地球上的我們也需要相隔約八分鐘才會感受到太陽消失後引力的變化。
新型態的輻射意味著新的觀測媒介。讓我們回顧歷史,天文觀測除了讓我們能看得愈遠、看到更古老的宇宙,全新的觀測方式總是帶來令人驚奇的結果及革命性的影響。伽利略在 1609 年以自製望遠鏡開啟天文光學觀測新頁,1930 年代的央斯基(Karl Jansky, 1905-1950)所做的銀河系無線電觀測,及 1950 年代 X 射線與 1960 年代後的伽瑪射線觀測,每一次的技術突破都帶來意外的發現,呈現出的宇宙圖像遠比肉眼下的更加活躍激烈,而且還給出各種不同面向的資訊,如無線電波帶來類星體、脈衝星與宇宙微波輻射,提供黑洞、中子星及大爆炸的餘暉等觀測上的證據,或是伽瑪射線反應出恆星內部以及超新星爆炸的資訊等。這些發現的累積讓人們拼湊出更豐富的宇宙樣貌與演化史,並且描繪出其背後形成的神祕機制。這些高能天文物理現象,往往伴隨著高質量高密度的物質與極端強大重力場的相互作用,因此隨著觀測技術的突破,廣義相對論的精確時空描述也變得更為重要,扮演探索未知宇宙的嚮導。而另一方面,遠處的星空也成為檢驗廣義相對論或其他基本理論的絕佳場所,測試我們對基本物理學的認識。幸運的,目前我們正處在另一次突破的關鍵時刻;除了電磁波觀測,以及最近宇宙射線或微中子偵測,重力波測量即將開啟探索宇宙的另一扇窗,讓我們得以一窺宇宙深處的各種驚奇現象。人們從懷疑黑洞這樣的奇特物體的存在開始,到終於獲得間接的觀測證據;從生怕黑洞奇異點的存在,讓所有物理定律失效,到嘗試提出各種解釋來彌補這理論上的矛盾――一代代的科學家們不斷努力突破未知的邊界,提升了人類文明的高度。中子星的概念,最早也是為了解釋恆星能量如何產生的問題開始,而在 1930 年代所做的大膽假設,現在也早已成為恆星演化的標準模型。在那一段各種新現象新理論交錯混雜、晦澀不明的時代,相對論與核物理各自在極大與極小的尺度下摸索時空與物質的本質,並逐漸歸納出愈來愈宏觀的圖像。而將近一個世紀重力波理論的發展,在經歷近半個世紀的觀測研究,也將在日後的大型觀測與模擬計算中獲得直接證實與天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