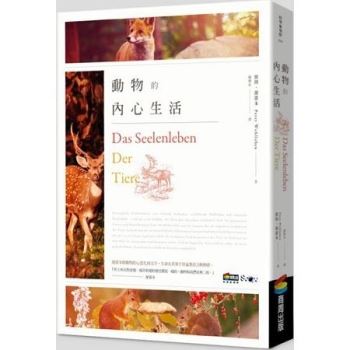陌生的世界
大自然的景致通常是如此寧靜和諧,就像一首田園牧歌,令人輕鬆自在、悠然神往。那翩翩飛舞於草地繁花之間的蝴蝶,被蔥綠灌木襯托得清新亮眼的白樺樹幹,樹梢上在風中輕搖款擺的枝椏……對我們來說,這些景象確實充滿了療癒的效果,然而這純粹是因為在這片開闊的田野間,對人類幾乎不存在任何危險。對於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動物居民來說,情況並非如此,因此牠們看待這「田園風光」的方式,自然也與我們大相徑庭。
只要觀察一下不同的蝶類與蛾類,就會發現兩個關鍵性的差異:首先,主要活動於白天的蝶類,多半美麗繽紛,譬如像孔雀蛺蝶。這種蝴蝶彩色的翅膀上有著逼真的大型眼斑圖案,目的是要嚇阻鳥類及其他天敵;再者,牠們的身體與翅膀表面的細毛也較少,這樣上面的圖案才能足夠清晰讓攻擊者留心。主要活動於夜晚的蛾類,色彩則很是單調,因為牠們在白天時,通常是在樹幹或枝椏上休憩等待暮色降臨,灰和棕是牠們最常見的顏色。在白晝裡,棲息中的蛾類由於動作遲鈍,很容易淪為鳥類手到擒來的獵物。許多鳥有著無比銳利的眼睛,即使是些微的顏色差異也能察覺;所以要是有隻飛蛾不慎選錯了樹,棲息在與自己翅膀顏色不搭的樹皮上,接下來可就要自求多福了,牠很有可能再也見不著明日的太陽與月亮。
為求生存,動物甚至會讓自己適應這個處處被人類文明改造過的世界。就像樺尺蠖,這種蛾類的白色翅膀上有著黑色的斑點圖案,這正好與白樺樹皮的顏色一樣;平展著寬幅約為五公分的雙翼,牠特別喜歡棲息在這種樹木的樹幹上。不過在英格蘭,白樺樹的「白色」樹皮大約只維持到一八四五年左右,在那之後由於興盛的工業活動與煤的燃燒,大量的煤灰被排放至空氣中,四處飄散沉降,連樹皮上都累積出一層又黑又髒的汙垢。於是這種原本有著最佳偽裝的動物,現在卻變得異常醒目,有數十萬隻都成了鳥兒的嘴下亡魂,直到剩下一群「非我族類」。其實這些「非我族類」一直都存在,就像一群白羊裡的黑羊一樣,牠們是長著深色翅膀的黑色樺尺蠖,在此之前這個特徵根本等同唯一死罪,然而現在這些體色深暗的物種卻搖身一變成為贏家。牠們不僅生存了下來,還在不到幾年之內,讓自己成為當地的絕對優勢種。一直要到一九六○年代末期,空氣汙染防制的法規通過後,隨著白樺樹恢復本色,情勢才又再度逆轉。一九七○年的《時代週報》(die Zeit)上也才會有此報導:白色物種再度榮膺最常見的樺尺蠖。
不過,所有東西在夜色中,看起來都會不太一樣。顏色此時並不重要,因為昆蟲的終結者「鳥類」正棲息在樹梢枝椏上,這時候會登場的獵人是蝙蝠,牠很少用眼睛來幫忙獵食,而是用牠的超音波絕技。蝙蝠會先發出高頻率的聲波,接著傾聽從周遭物體或可能的獵物身上反射的回音;所以視覺上的偽裝在此時此刻毫無用武之地,因為這隻會飛行的哺乳類動物,是用耳朵來「看」東西。除非你有辦法讓自己不被牠的耳朵「看見」,而這又該怎麼做呢?
一個可能的作法是不讓聲音反射回去,而是將其吸收。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在夜晚活動的蛾類全身覆滿細密的毛,因為這些細毛會捕捉蝙蝠發出的聲音,或者更精準地說,是讓聲音混亂地向所有可能的方向反射。如此一來,蝙蝠在接收到回音訊息後腦中所浮現的,並不是一幅清晰的蛾類影像,而只是某種模糊不清、可能就跟塊樹皮一樣的東西。
鴿子眼中的世界也跟我們完全不同,牠們雖然與人類一樣都是視覺動物,都強烈地依賴視覺感官,且因此很需要白晝的光,但是除了人類生活空間裡所有可見的細節,牠們顯然還能從空中察覺到其他的東西:鴿子飛行時可以見到偏振光(也就是光波的振動方向)所呈現出來的圖案,而這種偏振光則對準了北方。這意味著鴿子在白天時,根本隨處都有無形的羅盤可供參考,也難怪信鴿即使在遠距離的飛行中,都能明確地掌握方向,並且總有辦法找到回家的路。
如果在蝙蝠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接受聽力是一種額外附加的「視覺」,那就應該也可以將這種觀點擴及其他動物,試著了解牠們的感受,以及牠們是生活在一個怎麼樣的主觀世界中。例如狗兒,牠們的視覺天生就發展得比人類差,然而這種缺陷,是否可完全由嗅覺與聽覺來彌補?如果只有透過眼睛得到的整體印象,才能把周遭環境完整地描繪出來,那我們在評估過狗的視力之後,應該會對牠眼中的世界完全摸不著頭緒,牠絕對迫切需要戴眼鏡!狗眼睛裡的水晶體並不擅長調整遠近,所以物體必須在近到在牠眼前約六公尺時,牠才能夠看清楚;然而只要物體與牠的距離小於五十公分,影像就又會開始模糊。所有的影像,都是透過牠大約十萬條的視覺神經纖維來展現的;而人類的眼睛,相對地則大約有一百三十萬條在運作。
不過即使是對我們這種視覺動物來說,只靠眼睛仍然是遠遠不夠的,你可以做個小實驗:假若你正置身於充斥著各種談話或車輛噪音的環境中,那麼就試著把耳朵緊緊地「關」起來一下;重要的不是你現在會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重要的是你對整個環境的空間感會瞬間改變—因為它的景深不見了。所以對於十分仰賴耳朵,聽力比我們敏銳十五倍的狗來說,牠所看到的影像又會是什麼樣的呢?
試想每一種動物,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觀看與感覺這個世界,如此一來,我們周遭就存在著無數個萬千世界……這種想法總令我深深入迷。而在我們的緯度帶裡,還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世界在等待著被發現;僅僅在中歐地區,除了那些已經被介紹過的物種之外,還有好幾千種不同的動物,只因為太過渺小而入不了人類的眼,牠們的存在尚未被系統化地研究過。也因此很令人遺憾地,對於牠們的感受我們一無所知,因為要是一種動物對人類沒有明顯的重要性,幾乎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資金補助來研究牠。假若沒有人知道這些小生物的內心世界,不知道牠們是否有任何需求,是否在商業性林業經營的環境中吃盡苦頭,也就不會有人替牠們發聲與爭取保留地。譬如我就極其渴望知道,那些象鼻蟲的小小腦袋裡到底在想些什麼。有些種類的象鼻蟲已經失去了飛行的能力,但牠們卻令我一見鍾情:想像一個超級迷你、身長只有兩毫米的小傢伙,外表看起來卻像一頭大象!牠們在頭部及背部長著整齊的條紋狀毛髮,看起來像極了梳著一頭莫霍克髮型。牠們完全適應了在原始森林腐爛落葉裡的生活,此處的特點是幾乎不曾發生過任何改變。到處生長的山毛櫸樹,構成了極為穩定的社會共同體,其中的樹木會透過彼此根系的結合生長,活躍地傳輸著養分或甚至是訊息,因此不管是暴風雨、昆蟲或甚至是氣候變遷,幾乎都無法對它們造成危害。這種環境讓象鼻蟲得以過著寧靜詳和的生活,安心地慢慢咀嚼牠最愛的枯葉大餐。
這類甲蟲被稱為原始森林的遺留物種,也就是說,牠們原生於我們最初始的自然環境中,在今日被視為是一種指標:只要找得到牠們的地方,必定也存在著至少有上百年歷史的闊葉森林。身為一隻這樣的象鼻蟲,誰會想要遊走他方呢?而且在這裡又何需翅膀?費力遷移至他處太過多餘,牠們可以世世代代都待在同一個地方,安安靜靜地老去。萬分慶幸,在我們林區的保留地裡也可以讓牠在這裡養老,因為這裡曾發現過一種象鼻蟲的蹤跡。不過此處所謂的「變老」,必須按照象鼻蟲的標準來衡量,因為這些小傢伙只要能活到一歲,就算是步入高齡了。
然而,沒有翅膀就很難逃出生天,而像鳥類和蜘蛛這些嗜吃象鼻蟲的天敵可從來都不少。如果跑不了又躲不掉,但內心又充滿恐懼,那就必須要另謀求生的招數,而象鼻蟲在遇到狀況時的絕招,就是一翻兩瞪眼地裝死。藉由身上的圖案且與落葉顏色接近的保護色,這會讓敵人難以發現牠們,可惜對於森林的訪客也一樣,因為以牠們只有二到五毫米長的迷你尺寸,想看象鼻蟲的人大概要帶把放大鏡才行。至於這些小傢伙除了恐懼之外,還能感受到什麼,受限於缺乏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也只能猜測。不過即使是如此,向大家介紹象鼻蟲還是十分重要,因為牠代表著許多雖然不是我們的關注焦點,但至少已經贏得某些注意的物種。環繞在我們身邊的生命多樣性是如此美好,羽翼繽紛的鳥類、毛絨絨的哺乳類,奇妙有趣的兩棲類,甚至是好處多多的蚯蚓……引人入勝的生命形式隨處可見,但這正是我們的弱點,因為我們只會欣賞、讚嘆那些眼睛「看得見」的東西;而在動物的世界裡,絕大部分的生命是如此微小,只有借助放大鏡或是顯微鏡,牠們才會讓我們揭開面紗。
那麼至今已被發現超過了一千種的水熊蟲,又是怎麼樣的一種生命呢?有著八隻腳和可愛柔軟的身軀,使牠們看起來真的就像是多長了幾隻小腳的超級迷你熊。這種大小只有一毫米左右的真後生動物(牠們在科學上被歸類於這個動物亞界),喜歡很潮濕的環境,因此德國水熊蟲最喜愛的生活空間,就是同樣也性喜濕潤且保水能力又特別好的蘚苔。在一片蘚苔中,這些小小熊會忙得不可開交,依據種類不同牠們有些吃的是植物,有些則會捕食比自己更小的生物,譬如線蟲。
不過如果牠的家在炎炎夏日中缺水枯萎了,那該如何是好?我林區裡的那些美麗的蘚苔綠墊,就長在粗壯山毛櫸樹樹幹的底層,夏天時就經常因為缺水,而乾得摸起來簌蔌作響;可想而知,水熊蟲在此時也得不到一絲水分,於是接下來牠會採行一種極端的休眠形式:讓自己完全脫水變乾。只有營養充足的水熊蟲,才能夠在這個過程中生存下來,因為牠身上的脂肪在這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假若失水的過程發生得太快,牠的下場就唯有一死;而水分若散失得夠慢,這隻迷你動物就可以讓自己循序漸進地適應狀況,牠會逐漸地脫水,同時把所有的小腳縮進體內,整個身體的新陳代謝作用就會歸零。在這種狀態之下的小水熊蟲,幾乎可以撐過一切絕境:因為身上所有的生物活動都已停頓,因此不管是炙人的高溫或刺骨的嚴寒,都無法對牠造成絲毫損害。此時的牠當然也不再做夢,因為腦中劇場的活動也會消耗能量。到頭來,這其實是某種型態的死亡,因此牠自然也就不可能繼續「老化」;於是原本就壽命不長的水熊蟲在極端情況下,可以「活」上好幾十年,直到某天牠的救命甘霖終於降下。
那片蘚苔會再度飽吸水分,而那小小的僵硬身軀亦然;直到牠再度伸展出所有的小腳,體內所有的機能構造也再度全效運作,整個過程只需要區區二十分鐘。然後,這個小傢伙便會重新投身於牠的尋常生活之中。
大自然的景致通常是如此寧靜和諧,就像一首田園牧歌,令人輕鬆自在、悠然神往。那翩翩飛舞於草地繁花之間的蝴蝶,被蔥綠灌木襯托得清新亮眼的白樺樹幹,樹梢上在風中輕搖款擺的枝椏……對我們來說,這些景象確實充滿了療癒的效果,然而這純粹是因為在這片開闊的田野間,對人類幾乎不存在任何危險。對於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動物居民來說,情況並非如此,因此牠們看待這「田園風光」的方式,自然也與我們大相徑庭。
只要觀察一下不同的蝶類與蛾類,就會發現兩個關鍵性的差異:首先,主要活動於白天的蝶類,多半美麗繽紛,譬如像孔雀蛺蝶。這種蝴蝶彩色的翅膀上有著逼真的大型眼斑圖案,目的是要嚇阻鳥類及其他天敵;再者,牠們的身體與翅膀表面的細毛也較少,這樣上面的圖案才能足夠清晰讓攻擊者留心。主要活動於夜晚的蛾類,色彩則很是單調,因為牠們在白天時,通常是在樹幹或枝椏上休憩等待暮色降臨,灰和棕是牠們最常見的顏色。在白晝裡,棲息中的蛾類由於動作遲鈍,很容易淪為鳥類手到擒來的獵物。許多鳥有著無比銳利的眼睛,即使是些微的顏色差異也能察覺;所以要是有隻飛蛾不慎選錯了樹,棲息在與自己翅膀顏色不搭的樹皮上,接下來可就要自求多福了,牠很有可能再也見不著明日的太陽與月亮。
為求生存,動物甚至會讓自己適應這個處處被人類文明改造過的世界。就像樺尺蠖,這種蛾類的白色翅膀上有著黑色的斑點圖案,這正好與白樺樹皮的顏色一樣;平展著寬幅約為五公分的雙翼,牠特別喜歡棲息在這種樹木的樹幹上。不過在英格蘭,白樺樹的「白色」樹皮大約只維持到一八四五年左右,在那之後由於興盛的工業活動與煤的燃燒,大量的煤灰被排放至空氣中,四處飄散沉降,連樹皮上都累積出一層又黑又髒的汙垢。於是這種原本有著最佳偽裝的動物,現在卻變得異常醒目,有數十萬隻都成了鳥兒的嘴下亡魂,直到剩下一群「非我族類」。其實這些「非我族類」一直都存在,就像一群白羊裡的黑羊一樣,牠們是長著深色翅膀的黑色樺尺蠖,在此之前這個特徵根本等同唯一死罪,然而現在這些體色深暗的物種卻搖身一變成為贏家。牠們不僅生存了下來,還在不到幾年之內,讓自己成為當地的絕對優勢種。一直要到一九六○年代末期,空氣汙染防制的法規通過後,隨著白樺樹恢復本色,情勢才又再度逆轉。一九七○年的《時代週報》(die Zeit)上也才會有此報導:白色物種再度榮膺最常見的樺尺蠖。
不過,所有東西在夜色中,看起來都會不太一樣。顏色此時並不重要,因為昆蟲的終結者「鳥類」正棲息在樹梢枝椏上,這時候會登場的獵人是蝙蝠,牠很少用眼睛來幫忙獵食,而是用牠的超音波絕技。蝙蝠會先發出高頻率的聲波,接著傾聽從周遭物體或可能的獵物身上反射的回音;所以視覺上的偽裝在此時此刻毫無用武之地,因為這隻會飛行的哺乳類動物,是用耳朵來「看」東西。除非你有辦法讓自己不被牠的耳朵「看見」,而這又該怎麼做呢?
一個可能的作法是不讓聲音反射回去,而是將其吸收。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在夜晚活動的蛾類全身覆滿細密的毛,因為這些細毛會捕捉蝙蝠發出的聲音,或者更精準地說,是讓聲音混亂地向所有可能的方向反射。如此一來,蝙蝠在接收到回音訊息後腦中所浮現的,並不是一幅清晰的蛾類影像,而只是某種模糊不清、可能就跟塊樹皮一樣的東西。
鴿子眼中的世界也跟我們完全不同,牠們雖然與人類一樣都是視覺動物,都強烈地依賴視覺感官,且因此很需要白晝的光,但是除了人類生活空間裡所有可見的細節,牠們顯然還能從空中察覺到其他的東西:鴿子飛行時可以見到偏振光(也就是光波的振動方向)所呈現出來的圖案,而這種偏振光則對準了北方。這意味著鴿子在白天時,根本隨處都有無形的羅盤可供參考,也難怪信鴿即使在遠距離的飛行中,都能明確地掌握方向,並且總有辦法找到回家的路。
如果在蝙蝠的例子中,我們可以接受聽力是一種額外附加的「視覺」,那就應該也可以將這種觀點擴及其他動物,試著了解牠們的感受,以及牠們是生活在一個怎麼樣的主觀世界中。例如狗兒,牠們的視覺天生就發展得比人類差,然而這種缺陷,是否可完全由嗅覺與聽覺來彌補?如果只有透過眼睛得到的整體印象,才能把周遭環境完整地描繪出來,那我們在評估過狗的視力之後,應該會對牠眼中的世界完全摸不著頭緒,牠絕對迫切需要戴眼鏡!狗眼睛裡的水晶體並不擅長調整遠近,所以物體必須在近到在牠眼前約六公尺時,牠才能夠看清楚;然而只要物體與牠的距離小於五十公分,影像就又會開始模糊。所有的影像,都是透過牠大約十萬條的視覺神經纖維來展現的;而人類的眼睛,相對地則大約有一百三十萬條在運作。
不過即使是對我們這種視覺動物來說,只靠眼睛仍然是遠遠不夠的,你可以做個小實驗:假若你正置身於充斥著各種談話或車輛噪音的環境中,那麼就試著把耳朵緊緊地「關」起來一下;重要的不是你現在會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重要的是你對整個環境的空間感會瞬間改變—因為它的景深不見了。所以對於十分仰賴耳朵,聽力比我們敏銳十五倍的狗來說,牠所看到的影像又會是什麼樣的呢?
試想每一種動物,都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來觀看與感覺這個世界,如此一來,我們周遭就存在著無數個萬千世界……這種想法總令我深深入迷。而在我們的緯度帶裡,還有許許多多這樣的世界在等待著被發現;僅僅在中歐地區,除了那些已經被介紹過的物種之外,還有好幾千種不同的動物,只因為太過渺小而入不了人類的眼,牠們的存在尚未被系統化地研究過。也因此很令人遺憾地,對於牠們的感受我們一無所知,因為要是一種動物對人類沒有明顯的重要性,幾乎就不可能得到任何資金補助來研究牠。假若沒有人知道這些小生物的內心世界,不知道牠們是否有任何需求,是否在商業性林業經營的環境中吃盡苦頭,也就不會有人替牠們發聲與爭取保留地。譬如我就極其渴望知道,那些象鼻蟲的小小腦袋裡到底在想些什麼。有些種類的象鼻蟲已經失去了飛行的能力,但牠們卻令我一見鍾情:想像一個超級迷你、身長只有兩毫米的小傢伙,外表看起來卻像一頭大象!牠們在頭部及背部長著整齊的條紋狀毛髮,看起來像極了梳著一頭莫霍克髮型。牠們完全適應了在原始森林腐爛落葉裡的生活,此處的特點是幾乎不曾發生過任何改變。到處生長的山毛櫸樹,構成了極為穩定的社會共同體,其中的樹木會透過彼此根系的結合生長,活躍地傳輸著養分或甚至是訊息,因此不管是暴風雨、昆蟲或甚至是氣候變遷,幾乎都無法對它們造成危害。這種環境讓象鼻蟲得以過著寧靜詳和的生活,安心地慢慢咀嚼牠最愛的枯葉大餐。
這類甲蟲被稱為原始森林的遺留物種,也就是說,牠們原生於我們最初始的自然環境中,在今日被視為是一種指標:只要找得到牠們的地方,必定也存在著至少有上百年歷史的闊葉森林。身為一隻這樣的象鼻蟲,誰會想要遊走他方呢?而且在這裡又何需翅膀?費力遷移至他處太過多餘,牠們可以世世代代都待在同一個地方,安安靜靜地老去。萬分慶幸,在我們林區的保留地裡也可以讓牠在這裡養老,因為這裡曾發現過一種象鼻蟲的蹤跡。不過此處所謂的「變老」,必須按照象鼻蟲的標準來衡量,因為這些小傢伙只要能活到一歲,就算是步入高齡了。
然而,沒有翅膀就很難逃出生天,而像鳥類和蜘蛛這些嗜吃象鼻蟲的天敵可從來都不少。如果跑不了又躲不掉,但內心又充滿恐懼,那就必須要另謀求生的招數,而象鼻蟲在遇到狀況時的絕招,就是一翻兩瞪眼地裝死。藉由身上的圖案且與落葉顏色接近的保護色,這會讓敵人難以發現牠們,可惜對於森林的訪客也一樣,因為以牠們只有二到五毫米長的迷你尺寸,想看象鼻蟲的人大概要帶把放大鏡才行。至於這些小傢伙除了恐懼之外,還能感受到什麼,受限於缺乏進一步的研究,我們也只能猜測。不過即使是如此,向大家介紹象鼻蟲還是十分重要,因為牠代表著許多雖然不是我們的關注焦點,但至少已經贏得某些注意的物種。環繞在我們身邊的生命多樣性是如此美好,羽翼繽紛的鳥類、毛絨絨的哺乳類,奇妙有趣的兩棲類,甚至是好處多多的蚯蚓……引人入勝的生命形式隨處可見,但這正是我們的弱點,因為我們只會欣賞、讚嘆那些眼睛「看得見」的東西;而在動物的世界裡,絕大部分的生命是如此微小,只有借助放大鏡或是顯微鏡,牠們才會讓我們揭開面紗。
那麼至今已被發現超過了一千種的水熊蟲,又是怎麼樣的一種生命呢?有著八隻腳和可愛柔軟的身軀,使牠們看起來真的就像是多長了幾隻小腳的超級迷你熊。這種大小只有一毫米左右的真後生動物(牠們在科學上被歸類於這個動物亞界),喜歡很潮濕的環境,因此德國水熊蟲最喜愛的生活空間,就是同樣也性喜濕潤且保水能力又特別好的蘚苔。在一片蘚苔中,這些小小熊會忙得不可開交,依據種類不同牠們有些吃的是植物,有些則會捕食比自己更小的生物,譬如線蟲。
不過如果牠的家在炎炎夏日中缺水枯萎了,那該如何是好?我林區裡的那些美麗的蘚苔綠墊,就長在粗壯山毛櫸樹樹幹的底層,夏天時就經常因為缺水,而乾得摸起來簌蔌作響;可想而知,水熊蟲在此時也得不到一絲水分,於是接下來牠會採行一種極端的休眠形式:讓自己完全脫水變乾。只有營養充足的水熊蟲,才能夠在這個過程中生存下來,因為牠身上的脂肪在這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假若失水的過程發生得太快,牠的下場就唯有一死;而水分若散失得夠慢,這隻迷你動物就可以讓自己循序漸進地適應狀況,牠會逐漸地脫水,同時把所有的小腳縮進體內,整個身體的新陳代謝作用就會歸零。在這種狀態之下的小水熊蟲,幾乎可以撐過一切絕境:因為身上所有的生物活動都已停頓,因此不管是炙人的高溫或刺骨的嚴寒,都無法對牠造成絲毫損害。此時的牠當然也不再做夢,因為腦中劇場的活動也會消耗能量。到頭來,這其實是某種型態的死亡,因此牠自然也就不可能繼續「老化」;於是原本就壽命不長的水熊蟲在極端情況下,可以「活」上好幾十年,直到某天牠的救命甘霖終於降下。
那片蘚苔會再度飽吸水分,而那小小的僵硬身軀亦然;直到牠再度伸展出所有的小腳,體內所有的機能構造也再度全效運作,整個過程只需要區區二十分鐘。然後,這個小傢伙便會重新投身於牠的尋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