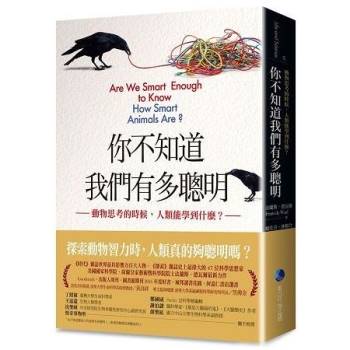前言
「在心智上,人類和其他高等動物之間的差異,至多僅是程度,而非本質。」──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71)
十一月某天清晨,天氣轉冷之際,我注意到一隻母黑猩猩(chimpanzee)法蘭潔(Franje)正忙著收集牠臥房裡所有的草稈。居住在荷蘭安亨市(Arnhem)伯格斯動物園(Burger’s Zoo)的牠把草稈夾在腋下,搬到一座大島上。法蘭潔的行為令我感到相當訝異,不只是牠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舉動,我在其他黑猩猩身上也從未見過類似的行為。一開始,我們假設牠的目的是為了保暖,但是在收集草稈前,法蘭潔都一直待在溫暖舒適的室內建築裡,理應無法感受到戶外溫度,最合理的解釋是牠根據以往的經驗,推算出今天的氣溫偏低。無論如何,法蘭潔和牠的兒子馮斯(Fons)那天在親手堆築的草稈窩裡,度過了一段美好又溫暖的時光。
每當看到這類案例,即使心裡明白單一事件並不足以得出什麼具體結論,我卻總是忍不住對動物「計畫性」的舉動所展現的心智能力感到不可思議。這類故事為科學家的觀察和實驗帶來啟發,並且幫助我們釐清事實。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曾於訪談中說過:「在科學領域中,最讓人興奮不已、表示有了新發現的一句話,並不是『啊!我想到了!』(Eureka),而是『這實在太有趣了!』(That’s funny)。」這種想法或許真的過於美好,畢竟科學家得先經過漫長的觀察,在發現引人好奇或令人驚嘆的動物行為時,進行系統化的檢驗,再試著與先前的假設相互參照、比對,有時還免不了和研究夥伴爭辯資料背後的意義。因此,我們常需要更多時間接受新的觀點,並在各式各樣的論點間產生歧見。即使最初的「現象觀察」並不困難(例如一隻黑猩猩收集一堆草稈),但要進一步獲得研究結果,就需要耗費相對龐大的資源了。正如法蘭潔的行為所暗示的:「動物是否真的會規畫未來?」這正是科學目前關注的問題。在本書中,我會避免使用像心理時間旅行(mental time travel,又稱chronesthesia)、自我覺知(autonoesis)等學者常用的艱澀專有名詞,試著以淺顯易懂的詞彙解釋科學研究進展。本書將以一個個動物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智力的真實故事,連結相對應的實驗證據—前者可以告訴我們其認知的功能,對照組的實驗結果則能進一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之所以如此撰寫,是因為儘管我能理解「看故事」對讀者來說輕鬆易懂,但我認為事件和實驗兩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試想一下動物的道別與打招呼之間的關聯。「打招呼」不難理解,就像你踏進家門,家裡的狗狗會撲向你一樣,打招呼是對離開一陣子的熟悉個體重新出現在眼前的自然反應。寵物看到人在外地的軍人飼主的視訊影像時,打招呼的強度與分離的時間長短有關,這同樣適用於我們人類。關於打招呼,其實不需要什麼了不起的認知理論就能解釋了,但道別呢?
我們人類懼怕向所愛的人道別。在我要搬到大西洋另一端之前,母親忍不住哭了起來,雖然我們雙方都心知肚明我不會永遠消失不見。「說再見」意味著預設了即將到來的別離,這也是為什麼「道別」在其他動物中較為罕見。我一樣有個關於道別的故事要說:一隻名叫庫芙(Kuif)的母黑猩猩,在我的訓練下學會使用奶瓶哺育一隻領養的黑猩猩寶寶。庫芙除了母乳不足之外,她的行為與親生母親沒有任何差別。庫芙會用我們給她的溫牛奶瓶,小心翼翼地餵食那隻黑猩猩寶寶,她甚至懂得在寶寶需要打嗝時及時抽出奶瓶。這項計畫進行的方式是讓庫芙全天候照顧寶寶,白天某段時間她會被喚到室內餵寶寶喝奶,因此得留下仍在戶外的同伴。沒過多久,我們開始注意到庫芙在哺乳時間來臨時不會直接進入室內,而是先親吻過島上每隻雄性首領(alpha male)、雌性首領(alpha female)與幾位好友後才離開。如果對方正在打盹,她會喚醒牠們,給了一個道別之吻後才走入室內。和法蘭潔相仿,這個行為本身看似簡單,但如此具體的情境一再上演,令我們對這種行為背後的認知機制感到好奇:庫芙與法蘭潔似乎具備「事先考慮」能力。
然而,對此抱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相信,只有人類才會考慮未來,動物關注的事物僅局限在當下。他們的假設是否合理?或者這些科學家只是矇蔽了雙眼,不願深究動物的能力?我們人類又為什麼傾向輕視動物的智力?將自身智力視為理所當然的我們卻習於否定動物的智力,這背後代表了什麼意義?在發掘其他物種心智層面運作機制的過程中,真正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動物本身,更包括人類內心的抗拒。這個故事有絕大部分和人類對待事物的態度、創造力與想像力有關。當我們試圖了解動物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智能之前,我們首先必須克服那深埋的心理障礙:人類格外珍視的自身能力,其他物種也可能同樣具備。因此,本書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探索動物智力時,人類真的夠聰明嗎?」簡短版本的答案是:「夠,但絕對和你猜想的不一樣。」就在不久前的上個世紀末,主流科學對動物的智力仍抱持著極度謹慎和懷疑的態度,絕大多數的學者將動物的意圖與情緒表現歸類在不值得相信的民間謠言或道聽塗說。因為「我們科學家懂得比較多!」,科學家才不會深入研究「我家的狗會嫉妒」,或是「我養的貓知道她要什麼」之類的問題,更別提什麼追憶過去、感同身受這種複雜的情感了。研究動物行為學的學生要不是不在意動物的認知能力,就是積極反對所有相關的見解;大部分的人根本不願意碰觸這個主題。幸好凡事都有特例,而我會盡力細讀這些資料。畢竟這是我的研究領域,再加上我熱愛與這個領域相關的科學史。我發現,當時兩個主流的學派,無非將動物視為「追求獎勵、避免懲罰」的刺激反應式機制,或僅是由遺傳本能操控的機械行為。即使學派間相互撻伐並鄙視對方視野狹窄,但它們的觀點基本上非常雷同:動物的機械觀。因此,擔憂動物內在世界的人不過是多餘的關心,這些人只是把動物擬人化、一廂情願或不科學罷了。
難道,我們註定要經歷這段遲滯的研究時期?其實在更早以前,有關動物智能的想法反而比較開放。達爾文便曾廣泛論述過人類和動物的情緒,許多十九世紀的科學家也渴望在動物身上尋找更高等智力的證據。為什麼學界的這些努力一度中止?為什麼我們自願在生物學的進程畫地自限?至今這依舊是個謎。偉大的演化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就曾把笛卡兒的動物觀形容為「愚蠢的機械論」。隨著時代改變,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感受到了,在過去短短的數十年內,新知不斷湧現,並透過網路迅速傳播。幾乎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有關動物複雜認知能力的新發現,同時多半包含有力的錄影紀錄加以支持佐證,其中包括老鼠對自身做出的決定感到後悔、烏鴉製造工具、章魚辨識人臉、特定的神經元協助猴子從其他個體的錯誤中學到教訓等。時至今日,我們公開討論動物的文化、同理心、友誼,甚至一度被視為我們得天獨厚的「理性」也不再是人類的專利。界線已然消融。人類總是喜歡將自身當作衡量智力的標準,比較自己和動物之間的差異。然而,現在我們應該可以開始理解到,這個方式顯然已經過時。智力的比較不應著眼在「人」與「動物」有何不同,而是包含我們在內的各式各樣物種間有何不同。雖然我也會在用字遣詞時,貪圖一時之便使用「動物」一詞,但無可否認的,人類亦是動物的一分子。比較智力的前提不該是把人與動物視為「不同種類」,而是相較「同一種類」的程度之差。我不但將人類的認知能力看作是動物認知能力的形式之一,甚至在面對身懷八隻獨立腕足、各自擁有認知網絡分布及神經系統的物種,或相較能夠用自行發出尖叫聲的回音判斷距離、在飛行中捕捉獵物的物種來說,我實在難以確認人類的智力究竟算不算獨一無二。
的確,人類非常仰賴抽象思考及語言(正在寫書的我在此絕無嘲諷之意),即使如此,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不過是尋求生存的一種策略。以群體緊密合作關係取代個體思考為生存策略的螞蟻和白蟻,無論在族群數量和生物量(biomass)方面都更勝人類一籌。每個社會的運作彷彿是自我組織的單一心智—雖然是由成千上萬喧鬧的腳步聲組成。近年來,科學家對動物界各種不可思議的訊息處理、組織及散播方式,才逐漸由原先否定或抗拒的態度轉為坦然接受。
因此,沒錯,人類是夠聰明去理解其他物種,但我們這顆冥頑不靈的腦袋,還需要做好不斷接受衝撞的心理準備,畢竟過去學界已經忽略了數以千計的事實,甚至棄之如敝屣。同時,該如何減少偏見、人類本位的想法,以及產生如此觀念的背後原由,永遠值得我們好好反思。在回顧相關研究進展的過程中,我不免會融入自己的見解:強調演化的連續性,並檢討傳統二元論的嚴重缺陷。無論是身體之於心靈、人類之於動物或理性之於感性的二元論,乍看似乎有所幫助,卻非常容易導致我們見樹不見林。身為一個專業的生物學家和動物行為學家,我不想浪費篇幅討論過時的懷疑主義論。這並不值得我們(包括我在內)為其耗費無盡筆墨。
撰寫本書時,我一開始就不打算提供演化認知學系統化的綜論。讀者如果對綜論感興趣,可以在其他學術性的著作覓得。我希望能從林林總總的科學發現、動物物種以及科學家的研究過程裡,挑選出一則則故事,用以傳達過去二十年間的研究成果是何等令人振奮。我本身的研究領域為靈長類的行為和認知能力,這個領域向來扮演開路先鋒,對其他物種的相關研究影響深遠。我從一九七○年代便投入這個領域,一路上結識了許多「夥伴」(包括人類和動物),因此我在書中也將放入一些個人感觸。其中豐富的歷史值得我們駐足凝視,此領域的成長正是一場冒險旅程(或許有人會形容如同坐上雲霄飛車),但這場引人入勝的冒險永無止盡。正如奧地利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所言,「行為」就是生物最生氣蓬勃的模樣了。
第一章 神奇的井
「我們觀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按照我們提問的方式所展現的樣貌。」──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58)
變成一隻蟲
睜開雙眼,葛列戈.薩姆沙從一隻不明動物的體內醒過來。外殼堅硬的他,成了「恐怖的害蟲」,藏身於沙發底下。葛列戈沿著牆壁和天花板來回爬行,喜愛腐爛的食物。可憐的葛列戈終於變成家人的負累與厭惡的對象。現在,他的死亡對家人而言是種解脫。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變形記》(Metamorphosis)中,以詭異的開場為人類本位主義逐漸式微的世紀揭開序幕。卡夫卡用隱喻的手法刻意選了一個令人反感的生物,強迫讀者想像自己變成一隻蟲之後有什麼感受。約莫在同一時期,德國的生物學家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提出一個觀看動物的嶄新視角—「環境界」(Umwelt,德文「周遭世界」之意)。借用環境界一詞,他帶領我們進入形形色色的周遭世界。魏克斯庫爾進一步解釋,每個生命都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周遭環境。例如,無眼壁蝨爬上草稈,屏息等待哺乳動物表皮散發出的丁酸氣味。實驗結果顯示,母壁蝨這種蛛形類生物即使十八年沒有進食也能存活,因此有充分的時間等待與哺乳動物相遇的那一刻。只要等到那一刻,就可以投入「被害者」的懷裡,用溫暖的血液餵飽自己,接著牠將產卵,並迎接死亡的到來。我們真的能夠理解壁蝨的「環境界」嗎?與人類相比,壁蝨顯然活在養分來源匱乏的生存環境,但魏克斯庫爾認為,壁蝨環境界的簡單是種優勢:牠的目標明確,能分心的事物不多。此外,魏克斯庫爾還檢視了其他例子。這些例子顯示,即使是單一環境也能提供每一個物種上百個特有的現實世界。環境界和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的概念大相逕庭。生態棲位指的是生物生存所需的棲地,環境界強調的是生物以自我為中心感知到的主體世界。因此,對單一物種而言,環境界只展現出整座世界的一小部分。根據魏克斯庫爾所言,對每一個物種來說,他們「永遠無法充分理解與察覺」構築所有物種的各式環境界。舉例來說,有些動物看得見紫外光,有些則活在利用嗅覺感知的地底世界,星鼻鼴鼠(star-nosed mole)就是一例。另外,以同一棵樹為例,不同物種對自己所感知到「片面的世界」也截然不同:有些生活在橡樹的樹幹上,有些在橡樹的樹皮層下,狐科動物則在橡樹根部挖鑿自己的巢穴—牠們各自擁有屬於自己的環境界。
人類可以試著想像其他物種的環境界。我們屬於高度視覺化的動物,能使用買來的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模擬出色盲人士眼中的世界。藉由科技,觀看到視障者的環境界,同時增強了同理心。對於其他個體的環境界想像,我自身印象最為深刻的經驗來自於飼養寒鴉(jackdaw,一種小型的鴉科)。那時,我住在學生宿舍四樓的房間,其中兩隻寒鴉從我的窗戶飛進飛出,我則在一旁觀察牠們在忙些什麼。懷抱著與許多雙親一樣的心情,我憂心忡忡地看著兩隻年幼、缺乏經驗的小傢伙。鳥類飛翔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事實上,這是一項需要後天學習的技能,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安全著陸」了。我邊看邊忍不住擔心牠們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撞上行駛中的汽車。此時,我開始想像自己就是一隻鳥,四處搜尋完美的著陸點,並且判斷心中的著陸點(可能是樹枝,也可能是陽臺)與我相距多遠。接著,我發現寒鴉在完成安全著陸的那一刻,會發出快樂的「呱呱聲」。我會再把牠們叫喚回來,重複剛才整個過程。當年幼的寒鴉終於成為飛行專家後,看著牠們隨風翻滾的姿態,我也跟著高興起來,彷彿享受飛翔的就是我自己。那時,我進入了鳥類的環境界—雖然稱不上完美無缺。當魏克斯庫爾企圖進一步探索和比對各個物種環境界的同時,這個概念更深深啟發了動物行為學的後輩。動物行為學從此不再只是上個世紀悲觀主義的美學及哲學。一九七四年,托馬斯.納格爾(Thomas Nagel)提出:「變成蝙蝠是什麼感受?」他藉此得出一個結論:身為人類的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我們無法進入另一個物種的主觀生活。納格爾尋求的並非人類變成蝙蝠後有什麼感受,而是身為一隻蝙蝠的感受為何。這的確遠超出我們的理解範圍。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曾為那堵橫亙在不同物種間的厚牆,提出一段著名的論述:「即使獅子可以說話,我們依舊無法聽懂。」當時部分學者對此番言論頗有微詞,他們認為維根斯坦根本不懂動物溝通的領域。然而,維根斯坦這段話的精髓在於,我們的生命經歷和獅子完全不同,因此即使獅子會說人話,我們仍然無法理解。維根斯坦的想法確實可以擴及到當我們面對陌生文化時,就算能理解其他國家的語言,仍不能立刻熟悉異地環境。維根斯坦要強調的是,進入其他個體的內在生活,我們本來就有能力限制,無論對象是不同物種或外國人。
我不打算在這本書解決這項棘手的問題,而是將焦點放在動物生活的世界,以及牠們如何探索自身環境界的複雜性。即使無法理解牠們的感受,我們依舊可以嘗試踏出人類狹隘的環境界,發揮我們的想像力。納格爾如果沒有聽過蝙蝠的回聲,他不可能寫出敏銳的反思。正由於科學家試圖想像身為一隻蝙蝠是什麼感受,他們才能發現蝙蝠的各種行為,並取得研究成果。跳脫感知框架去想像思考,正是人類這個物種的優勢。當我還是學生時,曾從烏特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的系主任史文.迪吉葛拉夫(Sven Dijkgraaf)聽到一則令我十分驚訝的故事。迪吉葛拉夫述說他在與我年紀相仿時,如何發現自己是世上少數幾個聽力特異的人,他能聽到蝙蝠發出超音波時伴隨的微弱卡㗳聲。科學家在超過一個世紀以前便知道目盲的蝙蝠仍能得知身在何處,並且安全地在牆壁或洞穴頂壁著陸,但是一旦失去聽力,蝙蝠就無法做到了。換句話說,失去聽力的蝙蝠就如同盲人。當時沒人知曉牠們飛行背後的機制,所以蝙蝠的能力被視為一種「第六感」。然而,科學家不甘願就此接受這種超感知理論,於是迪吉葛拉夫提出另一項解釋。由於他可以感受蝙蝠的聲音,便進一步注意到當蝙蝠前方出現障礙物時,發聲的頻率會隨之增加,因此他認為蝙蝠發出的聲音有助於在環境中通行無阻。不過,每當迪吉葛拉夫聊起這個故事,聲音中總不免流露一絲遺憾—身為蝙蝠回聲定位的發現者,他的成就至今尚未獲得認可。
「在心智上,人類和其他高等動物之間的差異,至多僅是程度,而非本質。」──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71)
十一月某天清晨,天氣轉冷之際,我注意到一隻母黑猩猩(chimpanzee)法蘭潔(Franje)正忙著收集牠臥房裡所有的草稈。居住在荷蘭安亨市(Arnhem)伯格斯動物園(Burger’s Zoo)的牠把草稈夾在腋下,搬到一座大島上。法蘭潔的行為令我感到相當訝異,不只是牠過去從來沒有這樣的舉動,我在其他黑猩猩身上也從未見過類似的行為。一開始,我們假設牠的目的是為了保暖,但是在收集草稈前,法蘭潔都一直待在溫暖舒適的室內建築裡,理應無法感受到戶外溫度,最合理的解釋是牠根據以往的經驗,推算出今天的氣溫偏低。無論如何,法蘭潔和牠的兒子馮斯(Fons)那天在親手堆築的草稈窩裡,度過了一段美好又溫暖的時光。
每當看到這類案例,即使心裡明白單一事件並不足以得出什麼具體結論,我卻總是忍不住對動物「計畫性」的舉動所展現的心智能力感到不可思議。這類故事為科學家的觀察和實驗帶來啟發,並且幫助我們釐清事實。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Isaac Asimov)曾於訪談中說過:「在科學領域中,最讓人興奮不已、表示有了新發現的一句話,並不是『啊!我想到了!』(Eureka),而是『這實在太有趣了!』(That’s funny)。」這種想法或許真的過於美好,畢竟科學家得先經過漫長的觀察,在發現引人好奇或令人驚嘆的動物行為時,進行系統化的檢驗,再試著與先前的假設相互參照、比對,有時還免不了和研究夥伴爭辯資料背後的意義。因此,我們常需要更多時間接受新的觀點,並在各式各樣的論點間產生歧見。即使最初的「現象觀察」並不困難(例如一隻黑猩猩收集一堆草稈),但要進一步獲得研究結果,就需要耗費相對龐大的資源了。正如法蘭潔的行為所暗示的:「動物是否真的會規畫未來?」這正是科學目前關注的問題。在本書中,我會避免使用像心理時間旅行(mental time travel,又稱chronesthesia)、自我覺知(autonoesis)等學者常用的艱澀專有名詞,試著以淺顯易懂的詞彙解釋科學研究進展。本書將以一個個動物在日常生活中運用智力的真實故事,連結相對應的實驗證據—前者可以告訴我們其認知的功能,對照組的實驗結果則能進一步排除其他可能的解釋。之所以如此撰寫,是因為儘管我能理解「看故事」對讀者來說輕鬆易懂,但我認為事件和實驗兩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試想一下動物的道別與打招呼之間的關聯。「打招呼」不難理解,就像你踏進家門,家裡的狗狗會撲向你一樣,打招呼是對離開一陣子的熟悉個體重新出現在眼前的自然反應。寵物看到人在外地的軍人飼主的視訊影像時,打招呼的強度與分離的時間長短有關,這同樣適用於我們人類。關於打招呼,其實不需要什麼了不起的認知理論就能解釋了,但道別呢?
我們人類懼怕向所愛的人道別。在我要搬到大西洋另一端之前,母親忍不住哭了起來,雖然我們雙方都心知肚明我不會永遠消失不見。「說再見」意味著預設了即將到來的別離,這也是為什麼「道別」在其他動物中較為罕見。我一樣有個關於道別的故事要說:一隻名叫庫芙(Kuif)的母黑猩猩,在我的訓練下學會使用奶瓶哺育一隻領養的黑猩猩寶寶。庫芙除了母乳不足之外,她的行為與親生母親沒有任何差別。庫芙會用我們給她的溫牛奶瓶,小心翼翼地餵食那隻黑猩猩寶寶,她甚至懂得在寶寶需要打嗝時及時抽出奶瓶。這項計畫進行的方式是讓庫芙全天候照顧寶寶,白天某段時間她會被喚到室內餵寶寶喝奶,因此得留下仍在戶外的同伴。沒過多久,我們開始注意到庫芙在哺乳時間來臨時不會直接進入室內,而是先親吻過島上每隻雄性首領(alpha male)、雌性首領(alpha female)與幾位好友後才離開。如果對方正在打盹,她會喚醒牠們,給了一個道別之吻後才走入室內。和法蘭潔相仿,這個行為本身看似簡單,但如此具體的情境一再上演,令我們對這種行為背後的認知機制感到好奇:庫芙與法蘭潔似乎具備「事先考慮」能力。
然而,對此抱持懷疑態度的科學家相信,只有人類才會考慮未來,動物關注的事物僅局限在當下。他們的假設是否合理?或者這些科學家只是矇蔽了雙眼,不願深究動物的能力?我們人類又為什麼傾向輕視動物的智力?將自身智力視為理所當然的我們卻習於否定動物的智力,這背後代表了什麼意義?在發掘其他物種心智層面運作機制的過程中,真正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動物本身,更包括人類內心的抗拒。這個故事有絕大部分和人類對待事物的態度、創造力與想像力有關。當我們試圖了解動物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智能之前,我們首先必須克服那深埋的心理障礙:人類格外珍視的自身能力,其他物種也可能同樣具備。因此,本書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探索動物智力時,人類真的夠聰明嗎?」簡短版本的答案是:「夠,但絕對和你猜想的不一樣。」就在不久前的上個世紀末,主流科學對動物的智力仍抱持著極度謹慎和懷疑的態度,絕大多數的學者將動物的意圖與情緒表現歸類在不值得相信的民間謠言或道聽塗說。因為「我們科學家懂得比較多!」,科學家才不會深入研究「我家的狗會嫉妒」,或是「我養的貓知道她要什麼」之類的問題,更別提什麼追憶過去、感同身受這種複雜的情感了。研究動物行為學的學生要不是不在意動物的認知能力,就是積極反對所有相關的見解;大部分的人根本不願意碰觸這個主題。幸好凡事都有特例,而我會盡力細讀這些資料。畢竟這是我的研究領域,再加上我熱愛與這個領域相關的科學史。我發現,當時兩個主流的學派,無非將動物視為「追求獎勵、避免懲罰」的刺激反應式機制,或僅是由遺傳本能操控的機械行為。即使學派間相互撻伐並鄙視對方視野狹窄,但它們的觀點基本上非常雷同:動物的機械觀。因此,擔憂動物內在世界的人不過是多餘的關心,這些人只是把動物擬人化、一廂情願或不科學罷了。
難道,我們註定要經歷這段遲滯的研究時期?其實在更早以前,有關動物智能的想法反而比較開放。達爾文便曾廣泛論述過人類和動物的情緒,許多十九世紀的科學家也渴望在動物身上尋找更高等智力的證據。為什麼學界的這些努力一度中止?為什麼我們自願在生物學的進程畫地自限?至今這依舊是個謎。偉大的演化學家恩斯特.邁爾(Ernst Mayr)就曾把笛卡兒的動物觀形容為「愚蠢的機械論」。隨著時代改變,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感受到了,在過去短短的數十年內,新知不斷湧現,並透過網路迅速傳播。幾乎每個星期都可以看到有關動物複雜認知能力的新發現,同時多半包含有力的錄影紀錄加以支持佐證,其中包括老鼠對自身做出的決定感到後悔、烏鴉製造工具、章魚辨識人臉、特定的神經元協助猴子從其他個體的錯誤中學到教訓等。時至今日,我們公開討論動物的文化、同理心、友誼,甚至一度被視為我們得天獨厚的「理性」也不再是人類的專利。界線已然消融。人類總是喜歡將自身當作衡量智力的標準,比較自己和動物之間的差異。然而,現在我們應該可以開始理解到,這個方式顯然已經過時。智力的比較不應著眼在「人」與「動物」有何不同,而是包含我們在內的各式各樣物種間有何不同。雖然我也會在用字遣詞時,貪圖一時之便使用「動物」一詞,但無可否認的,人類亦是動物的一分子。比較智力的前提不該是把人與動物視為「不同種類」,而是相較「同一種類」的程度之差。我不但將人類的認知能力看作是動物認知能力的形式之一,甚至在面對身懷八隻獨立腕足、各自擁有認知網絡分布及神經系統的物種,或相較能夠用自行發出尖叫聲的回音判斷距離、在飛行中捕捉獵物的物種來說,我實在難以確認人類的智力究竟算不算獨一無二。
的確,人類非常仰賴抽象思考及語言(正在寫書的我在此絕無嘲諷之意),即使如此,從更加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不過是尋求生存的一種策略。以群體緊密合作關係取代個體思考為生存策略的螞蟻和白蟻,無論在族群數量和生物量(biomass)方面都更勝人類一籌。每個社會的運作彷彿是自我組織的單一心智—雖然是由成千上萬喧鬧的腳步聲組成。近年來,科學家對動物界各種不可思議的訊息處理、組織及散播方式,才逐漸由原先否定或抗拒的態度轉為坦然接受。
因此,沒錯,人類是夠聰明去理解其他物種,但我們這顆冥頑不靈的腦袋,還需要做好不斷接受衝撞的心理準備,畢竟過去學界已經忽略了數以千計的事實,甚至棄之如敝屣。同時,該如何減少偏見、人類本位的想法,以及產生如此觀念的背後原由,永遠值得我們好好反思。在回顧相關研究進展的過程中,我不免會融入自己的見解:強調演化的連續性,並檢討傳統二元論的嚴重缺陷。無論是身體之於心靈、人類之於動物或理性之於感性的二元論,乍看似乎有所幫助,卻非常容易導致我們見樹不見林。身為一個專業的生物學家和動物行為學家,我不想浪費篇幅討論過時的懷疑主義論。這並不值得我們(包括我在內)為其耗費無盡筆墨。
撰寫本書時,我一開始就不打算提供演化認知學系統化的綜論。讀者如果對綜論感興趣,可以在其他學術性的著作覓得。我希望能從林林總總的科學發現、動物物種以及科學家的研究過程裡,挑選出一則則故事,用以傳達過去二十年間的研究成果是何等令人振奮。我本身的研究領域為靈長類的行為和認知能力,這個領域向來扮演開路先鋒,對其他物種的相關研究影響深遠。我從一九七○年代便投入這個領域,一路上結識了許多「夥伴」(包括人類和動物),因此我在書中也將放入一些個人感觸。其中豐富的歷史值得我們駐足凝視,此領域的成長正是一場冒險旅程(或許有人會形容如同坐上雲霄飛車),但這場引人入勝的冒險永無止盡。正如奧地利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所言,「行為」就是生物最生氣蓬勃的模樣了。
第一章 神奇的井
「我們觀察到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自然按照我們提問的方式所展現的樣貌。」──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 1958)
變成一隻蟲
睜開雙眼,葛列戈.薩姆沙從一隻不明動物的體內醒過來。外殼堅硬的他,成了「恐怖的害蟲」,藏身於沙發底下。葛列戈沿著牆壁和天花板來回爬行,喜愛腐爛的食物。可憐的葛列戈終於變成家人的負累與厭惡的對象。現在,他的死亡對家人而言是種解脫。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一九一五年出版的《變形記》(Metamorphosis)中,以詭異的開場為人類本位主義逐漸式微的世紀揭開序幕。卡夫卡用隱喻的手法刻意選了一個令人反感的生物,強迫讀者想像自己變成一隻蟲之後有什麼感受。約莫在同一時期,德國的生物學家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提出一個觀看動物的嶄新視角—「環境界」(Umwelt,德文「周遭世界」之意)。借用環境界一詞,他帶領我們進入形形色色的周遭世界。魏克斯庫爾進一步解釋,每個生命都各自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周遭環境。例如,無眼壁蝨爬上草稈,屏息等待哺乳動物表皮散發出的丁酸氣味。實驗結果顯示,母壁蝨這種蛛形類生物即使十八年沒有進食也能存活,因此有充分的時間等待與哺乳動物相遇的那一刻。只要等到那一刻,就可以投入「被害者」的懷裡,用溫暖的血液餵飽自己,接著牠將產卵,並迎接死亡的到來。我們真的能夠理解壁蝨的「環境界」嗎?與人類相比,壁蝨顯然活在養分來源匱乏的生存環境,但魏克斯庫爾認為,壁蝨環境界的簡單是種優勢:牠的目標明確,能分心的事物不多。此外,魏克斯庫爾還檢視了其他例子。這些例子顯示,即使是單一環境也能提供每一個物種上百個特有的現實世界。環境界和生態棲位(ecological niche)的概念大相逕庭。生態棲位指的是生物生存所需的棲地,環境界強調的是生物以自我為中心感知到的主體世界。因此,對單一物種而言,環境界只展現出整座世界的一小部分。根據魏克斯庫爾所言,對每一個物種來說,他們「永遠無法充分理解與察覺」構築所有物種的各式環境界。舉例來說,有些動物看得見紫外光,有些則活在利用嗅覺感知的地底世界,星鼻鼴鼠(star-nosed mole)就是一例。另外,以同一棵樹為例,不同物種對自己所感知到「片面的世界」也截然不同:有些生活在橡樹的樹幹上,有些在橡樹的樹皮層下,狐科動物則在橡樹根部挖鑿自己的巢穴—牠們各自擁有屬於自己的環境界。
人類可以試著想像其他物種的環境界。我們屬於高度視覺化的動物,能使用買來的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模擬出色盲人士眼中的世界。藉由科技,觀看到視障者的環境界,同時增強了同理心。對於其他個體的環境界想像,我自身印象最為深刻的經驗來自於飼養寒鴉(jackdaw,一種小型的鴉科)。那時,我住在學生宿舍四樓的房間,其中兩隻寒鴉從我的窗戶飛進飛出,我則在一旁觀察牠們在忙些什麼。懷抱著與許多雙親一樣的心情,我憂心忡忡地看著兩隻年幼、缺乏經驗的小傢伙。鳥類飛翔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事實上,這是一項需要後天學習的技能,最困難的部分就是「安全著陸」了。我邊看邊忍不住擔心牠們會不會一不小心就撞上行駛中的汽車。此時,我開始想像自己就是一隻鳥,四處搜尋完美的著陸點,並且判斷心中的著陸點(可能是樹枝,也可能是陽臺)與我相距多遠。接著,我發現寒鴉在完成安全著陸的那一刻,會發出快樂的「呱呱聲」。我會再把牠們叫喚回來,重複剛才整個過程。當年幼的寒鴉終於成為飛行專家後,看著牠們隨風翻滾的姿態,我也跟著高興起來,彷彿享受飛翔的就是我自己。那時,我進入了鳥類的環境界—雖然稱不上完美無缺。當魏克斯庫爾企圖進一步探索和比對各個物種環境界的同時,這個概念更深深啟發了動物行為學的後輩。動物行為學從此不再只是上個世紀悲觀主義的美學及哲學。一九七四年,托馬斯.納格爾(Thomas Nagel)提出:「變成蝙蝠是什麼感受?」他藉此得出一個結論:身為人類的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我們無法進入另一個物種的主觀生活。納格爾尋求的並非人類變成蝙蝠後有什麼感受,而是身為一隻蝙蝠的感受為何。這的確遠超出我們的理解範圍。奧地利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也曾為那堵橫亙在不同物種間的厚牆,提出一段著名的論述:「即使獅子可以說話,我們依舊無法聽懂。」當時部分學者對此番言論頗有微詞,他們認為維根斯坦根本不懂動物溝通的領域。然而,維根斯坦這段話的精髓在於,我們的生命經歷和獅子完全不同,因此即使獅子會說人話,我們仍然無法理解。維根斯坦的想法確實可以擴及到當我們面對陌生文化時,就算能理解其他國家的語言,仍不能立刻熟悉異地環境。維根斯坦要強調的是,進入其他個體的內在生活,我們本來就有能力限制,無論對象是不同物種或外國人。
我不打算在這本書解決這項棘手的問題,而是將焦點放在動物生活的世界,以及牠們如何探索自身環境界的複雜性。即使無法理解牠們的感受,我們依舊可以嘗試踏出人類狹隘的環境界,發揮我們的想像力。納格爾如果沒有聽過蝙蝠的回聲,他不可能寫出敏銳的反思。正由於科學家試圖想像身為一隻蝙蝠是什麼感受,他們才能發現蝙蝠的各種行為,並取得研究成果。跳脫感知框架去想像思考,正是人類這個物種的優勢。當我還是學生時,曾從烏特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的系主任史文.迪吉葛拉夫(Sven Dijkgraaf)聽到一則令我十分驚訝的故事。迪吉葛拉夫述說他在與我年紀相仿時,如何發現自己是世上少數幾個聽力特異的人,他能聽到蝙蝠發出超音波時伴隨的微弱卡㗳聲。科學家在超過一個世紀以前便知道目盲的蝙蝠仍能得知身在何處,並且安全地在牆壁或洞穴頂壁著陸,但是一旦失去聽力,蝙蝠就無法做到了。換句話說,失去聽力的蝙蝠就如同盲人。當時沒人知曉牠們飛行背後的機制,所以蝙蝠的能力被視為一種「第六感」。然而,科學家不甘願就此接受這種超感知理論,於是迪吉葛拉夫提出另一項解釋。由於他可以感受蝙蝠的聲音,便進一步注意到當蝙蝠前方出現障礙物時,發聲的頻率會隨之增加,因此他認為蝙蝠發出的聲音有助於在環境中通行無阻。不過,每當迪吉葛拉夫聊起這個故事,聲音中總不免流露一絲遺憾—身為蝙蝠回聲定位的發現者,他的成就至今尚未獲得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