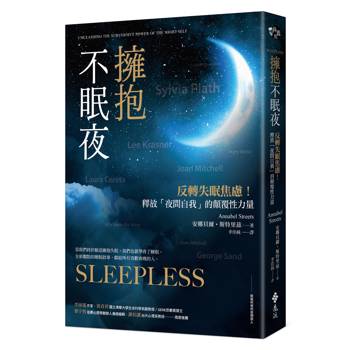第一章 夜之自我
十二月的一個週日,我在狹窄的鄉村小徑慢跑,這是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跑步。平常我偏好緩慢的步行,但在注定永遠改變我人生平衡點的這一天,我正在跑步。當天的空氣稀薄而閃閃發光,我的肺冷得陣陣刺痛。我感受到晨跑者都有的振奮心情,當下決定我的新年新希望,就是要多多跑步。我沒想過我可能再也不會有什麼新希望,或者,我可能還要過好長一段時間,才能再次體會這種振奮感。
當我快接近小屋時,手機響了。我很驚訝,因為現在才早上八點多,我以為會在手機螢幕看見丈夫馬修的名字,沒想到來電的是我父親的妻子,我稱她L。「喂,」我喘著粗氣,心想她是不是打電話來討論聖誕節計畫。我邀了她和我父親共進聖誕晚餐,一直以來我們都一起慶祝耶誕。自從我父母離婚後,聖誕節就是個需要花心思的節日。
二十二年來,我和手足分別成家立業,爸媽也上了年紀,家族成員中有離婚不合的,眾人四散各地,飲食習慣也不同,這些都需要協調。也就是說,少不了籌劃家族聖誕節會碰上的各種麻煩。今年由於疫情影響,只有一部分的家人能夠團聚。由於死亡人數還在不斷增加,也尚無疫苗(第一批疫苗在未來兩週內會出現),今年的慶祝活動勢必籠罩在焦慮之中。我父親特別謹慎,為了避免聚眾感染而採取了極端措施。我預期他可能會取消這個聚餐。
這些想法在我腦海中一一飄過,我在風中大聲喊,「喂?」
「你爸爸……,」L說。「急救人員在這裡。」
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為什麼急救人員會在那裡?
「他死了。」她說。
她聽起來冷靜而無動於衷,我以為我聽錯了。而且她的話完全沒有道理。首先,我爸不可能死了,我前兩天才和他通過電話,當時他好好的。第二,如果他死了,急救人員在那邊做什麼?
「心臟病發作。」她補充。
「我現在開車過去,」我說。「我馬上到!」我聽到背景有聲音,好像L正與某人商量。他們為什麼不對他進行急救?
「他們說讓你開車小心一點。」她的聲音依然平靜從容,「我是指警察說。」
警察?為什麼L會跟警察在一起?
我掛上電話開始尖叫。我一路狂奔哭泣著回到家,腦海不斷重複著一句話:我還沒準備好,我還沒準備好,我還沒準備好。
一切就從這裡開始。過了很久之後,我才覺得很奇怪,一個如此明確的結束,竟然也是如此明顯的開始。
丈夫馬修開車時,我打電話給我妹,又打給我弟。我妹妹失手把手機砸在地上,我聽到她不停尖叫。我弟很冷靜,後來我才意識到,我對妹妹的轉述太直白,而對弟弟講的則太模糊。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弟在一小時後打回來問我急救的進展,我只好跟他說,父親已經去世了近十二個小時,當場沒有救活的可能。然後,我弟說了和我一樣的話:「他不可能死了,我昨晚才和他通話。」他想得跟我一樣,這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了。我們需要更多時間。我們還沒來得及說再見,說我愛你。
公寓裡充斥著穿制服的人,他們正寫報告、講電話、喝茶,他們的存在暗示了秩序和確定,讓人迅速平靜下來。L問我是否想看看爸爸,我無法回答,只能點頭。我既想又不想,我努力調節情緒,保持冷靜;就跟L一樣,此刻的她比我見過的任何時候都要冷靜。
爸坐在他的紅椅上,看來像睡著了。接下來幾個月,我們一直反覆提起這個畫面,他看起來是多麼安詳。我碰碰他的手,冰冷如玻璃,那種冰冷感在接下來幾個月縈繞著我,但我最記得的卻是他的沉默。一開始不容易發現,因為周圍擠滿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我隱約察覺,沒有絲毫的氣息從他的唇間洩出,沒有骨頭或關節的輕微聲響,沒有牙齒磨擦聲,也沒有衣物颤動聲,沒有言語。體內沒有生命的時候,我們就悄然無聲了。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死亡,我發現是那麼寧靜。我想,這是否就是我們會害怕沉默的原因。因為在沉默的縫隙,承載著我們無法忽視的事:人終有一死。
父親去世前一週,我剛協助母親安葬了與她相伴二十年的伴侶。道格拉斯和我母親沒有結婚,但我還是稱他「繼父」,我一直是這麼看待他的。母親為他哀悼,我們都為他哀悼,他在一個令他痛恨的養老院受盡病痛折磨才解脫。由於疫情,我們甚至無法探望他,更別說握著他的手,這讓我們留下滿腹的酸楚和壓抑。他就像成千上萬的其他人,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時沒有得到安慰和尊嚴。我胸口的緊繃感,也許就是我在父親去世當天去慢跑的原因,也許我希望能擺脫鐵鉗般的束縛,大口呼吸,以徹底甩掉憤怒和悲傷的痕跡。
然而,束縛卻更緊了。
當晚我待在父親家,睡在書房裡的行軍床,鋪蓋是橘色床單和橙色羽絨被,我的頭緊貼著書桌。我身邊都是他的藏書,他的筆跡停在筆記本中半句話的地方,他的開襟毛衣隨意披在椅背上。我父親總是為特定的物品賦予意義—石頭、羽毛、貝殼、小雕塑,這些物件都圍繞在我身邊,精心擺放在桌面和層架,以便他在寫作時可以看見。房裡充滿了他的氣息,他的存在感,他的希望。
第一晚,我根本沒奢望能夠睡著。我不想睡。我挑了幾本父親的書來看,準備流著淚度過一個情感豐沛但清醒的夜晚。我沒想到的是,當晚我沉沈睡去,一夜無夢!我醒來時感到震驚和羞愧:我沒有哭上一整夜,反而度過了記憶中最棒的一夜好眠。
在經歷了人生中的重大打擊,我怎能睡得那麼好?我後來在科學研究中讀到,像我這樣的反應並不罕見,因為大腦在必要時會關機,這是確保生存而設計的機制。
然而好景不常。接下來的十幾天,我在父親家忙著安排葬禮:處理驗屍和死亡證明,通知親友、撰寫訃告,裝飾(紙板)棺材,為L採買和做飯,處理種種伴隨著猝逝而來的雜務差事。L像行屍走肉般維持著日常作息,有時我會想,她的心神到哪裡去了?後來我才知道她一直處於震驚之中,這種麻木的表現,也是保護人免受極端痛苦的心理狀態。我把「震驚」視為一個所在,介於醫院和旅館之間。L悄然且不由自主地撤退到了那裡。
我把她的缺席視為理由,讓自己變得忙碌和「能幹」。但當夜幕降臨,我蓋上橘色被單,凝視著周遭書本的輪廓,我無法繼續偽裝。每晚,鐵爪堅定地緊繃在胸口,我差點以為我也要心臟病發了!我哭泣、喘息、吞嚥著並努力放緩呼吸。然後我起床,展開另一個忙碌的日子。
很顯然,那個不受干擾的第一晚只是個異常現象。我開始在安眠藥櫃翻找,對抗越來越長的不眠之夜。我吞了很多奈妥(Nytol)、褪黑激素和鎂,把枕頭灑滿洋甘菊和薰衣草精油;我戒掉藍光、咖啡因和酒精,翻出處方藥。當然,沒有任何效果。
然後我讓自己變得更忙碌。我深信知曉如何排解悲傷:我在網路上領養了一隻小狗,安排在父親葬禮第二天去接牠,還買好了玩具和食物。還有什麼比迎接新生命更能療癒這突如其來的失落?有誰會比小狗更適合承接我們無家可歸的愛?
然而,我們的小狗從被帶回家的那一刻就開始生病。牠病懨懨地躺著,偶爾喝口水。我看著牠軟弱無力的身軀,心裡充滿不祥的預感。聖誕節那天,我帶牠去看獸醫急診,獸醫懷疑牠感染了犬小病毒。他解釋說會有冗長的檢測,高昂的診療費,以及微乎其微的生存機會。由於疫情肆虐及無數規定,還有正值聖誕節,這個過程會比平常耗時。
「牠應該來自繁殖場吧。」他聳聳肩,「可能同胎的都會死。」
我們的小狗在獸醫院住了五個晚上。我們無法看望牠,因為犬小病毒不僅致命而且傳染性很高,牠被放在隔離病房。我們不斷打電話關切,每次獸醫都詢問我們是否願意讓小狗安樂死。醫療費日漸高昂,而牠一直沒有進食。但在測試結果出來之前,無法得到診斷。
「還有希望嗎?一點點也好?」我流著淚問。每天獸醫都說,「也許有一線希望……總會有希望。」到了第五個晚上,獸醫打電話來:「牠的情況惡化,我認為沒希望了。」我們的小狗在獸醫護士的懷裡被安樂死。我們再也沒有見過牠。
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想著牠小小的身軀,牠這麼年幼就死掉令我無比傷痛。我把牠從母親的身邊帶走,放任牠死去,我沒有好好保護牠。一隻跟我們相處不到三天的動物,竟能帶給我如此痛苦,我很吃驚。即使我們沒有建立真正的關係,也沒有共同的經歷,但我現在一想到牠,眼淚還是流個不停。因為牠瘦小的肩膀也肩負著希望的重擔,某種難以言喻的方式讓牠成為一個熔爐,一個讓我懷念父親和繼父的方式。突然間,那負擔彷彿太沉重了,於是一切再次回到了牠的微小。
我不希望這巨大狂烈的悲痛驚嚇到我的孩子,我還有悲傷的家人要照料,如果我崩潰了,對身邊的人毫無益處。於是,白天我忙於為小狗伸張正義,晚上則忙於處理我父親的遺產——保持忙碌,保持忙碌,保持忙碌。
但我還是無法入睡。
然後在一個灰濛濛的黎明,我忽然發現,總在夜晚哀悼成了我的常態。因此,我把安眠藥收了起來,慢慢接受這麼多個無法入眠的夜晚。此時我意識到,這並非我平常習慣性的失眠,曾幾何時,我的不眠之夜已經變為我未曾預料的樣子,它們成了重要的避風港。雖然我的白天塞滿事務安排和照顧責任,但我的不眠夜卻成為內心的綠洲。
在這個黑暗而令人舒適的地方,我開始明白在夜裡清醒的必要性。
這些漫長而無法成眠的時光,是我從未經歷過的。不像過往的失眠,那種習慣性的恐懼和焦慮並不存在。這次不一樣,黑暗似乎在移動並軟化了,而且有著重量和密度,彷彿將我包圍在棉花糖或甜美的蛋白霜裡。有時,黑暗給人的感覺是一層柔軟的保護膜,一張可以讓我迷失其中的輕柔皮毛。
我清楚記得被黑暗扶持的感覺。它從未對我施壓,只是支撐著我;不提問,也不要求。黑暗給了我空間、隱秘、安靜和匿名性,然而它似乎在我身旁呼吸脈動,就像一個沉睡的同伴,因此我從不孤單。
這位同伴並非完全緘默,我的夜晚會伴隨著自己的聲音景觀:飛機聲、車流聲、無法解釋的刮擦聲、摩擦聲和碰撞聲。我這才了解到,還有另一個世界與我同時清醒著,我第一次聽到了我後來稱之為「夜間自我」的微小聲音—心跳聲、唾液流動聲、腳跟摩擦床單的聲音。
每晚當我忽然睜開眼,腦中浮現父親的身影,接著是小狗和道格拉斯,我想到那些已然失去且永遠無法尋回的事物。我的胃底出現一個空洞,巨石壓在胸口,然後黑暗迅速湧入,彷彿在說「但還有我在啊,我屬於你。」這就像一種緩衝,介於我和身體的疼痛之間。
這時,有一種鬆口氣的感覺湧上心頭:我不需要起床,不需故作堅強,也不需要急著安排什麼,我可以與我的悲傷靜靜躺著,挖掘那害怕失去的記憶,尋找問題的答案:我父親在哪?道格拉斯和小狗在哪?死去的人會去哪?
作為一個未知論者,我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白天,我沒有時間思考這件事。而且在白天思考這種問題似乎很荒謬,不可能有答案。然而到了夜裡,思考這個問題再合理不過。
我們都曾在黑暗中搜尋,這個尋找的過程(從摸索門把到找尋車鑰匙)讓人覺得很有意義,我們可以耐心優雅的翻找。試想,如果是在明亮的光線下搜尋東西,往往會顯得很無能,我們會譴責自己愚蠢,最後變得匆忙又沮喪。所以我感覺,探索亡者行蹤這類事情根本就是個夜間任務,應該在黑夜的掩護下進行。
夜色漸逝,從綢緞般的漆黑轉變為帶著銀灰的不透明,天色變得稀薄且顆粒感十足。黎明的光透進房間,車流聲持續響起,鳥兒鳴唱。黑暗已經隱沒,不再支撐著我,而我的眼睛酸痛,空洞無物,渴望入眠。然而,那些黑暗時刻給予了我比睡眠更深刻的東西,它給了我純粹的時間和空間,同時讓我擺脫了我後來稱為「白日思考」的束縛。
在一個不眠夜,我聽到走廊地板發出了嘎吱聲。我突然想到,也許此時孩子們都還醒著,他們敞開的心靈正思考著那些令我困擾的問題。我腦海不斷轉動:數十萬人才因為新冠肺炎而過世,這無疑意味著數十萬人正清醒地處在同一個邊界、痛苦和無眠之地。我的想像力被這個影像絆住了:好多失親同胞孤獨卻微妙地相連,佔據著同一個半成形的世界。我開始好奇,那些跟我一樣不成眠的哀悼者是誰,他們在做什麼?想什麼?又感受到什麼?
失眠往往是由失落所引發。根據《睡眠醫學評論》的研究,「失去親友常與入睡困難、無法維持睡眠,以及睡眠時數減少密切相關。」簡單來說,喪親者很少能夠一夜好眠。研究指出,悲傷越強烈,睡眠就越破碎、零碎且中斷。
生理性別在其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喪親的女性比男性更常出現睡眠障礙。年齡也加劇了失眠問題,越年輕的人,越不會因喪親而影響睡眠。另外,死亡性質也有影響,意外死亡比預期的死亡更容易打亂喪親者的睡眠節奏。我是個剛經歷了數起非預期死亡的中年女性,難怪,現在遭遇了我人生中最嚴重的失眠。
但是,哀悼的人不僅睡得少,睡眠方式也不一樣。研究人員測量喪親者的睡眠波長,發現他們的睡眠呈現更多的快速眼動(充滿夢境的)模式,較少深層而具有修復作用的睡眠。悲傷越強烈,睡眠變化就越大。
當然了,失眠的時間也越長。
我父親去世前,我的失眠持續了二十多年。我完全預期自己無法入睡,也預期失眠會更嚴重,所以我習慣先靠安眠藥,接著憤怒地在床上翻來覆去,最後聽著有聲書斷斷續續睡著。過去幾次失眠,我經常乾脆放棄睡覺,結果到天亮時整個人疲憊不堪,滿臉憔悴,詛咒著夜晚,痛罵自己無法入睡。
然而現在,因為心中充滿了悲傷,我發現我的夜晚正在改變。我開始期待夜裡的清醒時光,那如墨的安慰、柔和的寧靜,以及平靜。夜裡,我可以放下堅強形象,我不再是那個負責張羅一切的女兒,我可以盡情悲傷,也不會影響到任何人——我可以做我自己。
黑暗有一種簡化的能力,這正是我喜歡並且需要的。我看不到滿地必須清掃的蜘蛛網,看不到堆積如山的待洗衣物,我什麼也看不見。於是,我的目光轉向內心。從前這意味著我要冥想幾個小時,然後把夜半還醒著當成一場災難,擔心睡眠不足隔天會犯錯。或者,我會血壓飆升,腦袋昏沉,讓負面情緒糾纏個沒完。但因為此刻我陷於喪親之痛,正在跟更大的問題搏鬥,所以這些擔憂悄然消散了。我不在乎不眠夜帶來的威脅,如果我隔天看起來很疲憊或者脾氣暴躁,那又怎麼樣?
聖誕假期結束,我的家人陸續返回倫敦,而我決定留在位於城外的小屋,離L與母親近一點。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日常的喧囂。倫敦忽然變得比往常更吵雜,我耳裡的隔音層好像被剝掉了,噪音令我痛苦。飛機、汽車警報、救護車警笛、摩托車轟鳴,一切聲音都被放大得刺耳,在我聽來有如驚恐的死亡之聲。
但鄉村夜晚的聲景就柔和得多。我喜歡聽著風聲,田野羊群的咩叫,門前柳樹的嘆息和吱嘎。我喜歡化作音樂的夜雨宛如音符,雨水拍打玻璃落在屋頂上的滴答,那是黑暗中零星而綿密的毛毛雨。雨聲交錯著絕對的寂靜時刻,那寂靜同時映照我內心的空虛,卻也暗示了其他的可能。
然而除了寂靜,我還渴望黑暗——濃密而純粹的黑。我花了幾個小時用膠帶遮擋住藍色的網路信號燈,在窗戶上安裝紙板。每一絲人造光都是一種冒犯。這突如其來對黑暗的渴望讓我倍感困惑,因為過去我總是害怕它,也怕隨之而來的遺忘、壓抑,以及黑暗誘發的可怕幻想。然而此時,黑暗似乎帶來了解放,予人安慰。黑暗的神秘感給了我希望與救贖。
我也學會辨識黑暗的色調和質地,它可能輕如羽毛,柔軟如肌膚,或如毯子般漆黑厚重。我感到意外:當黑暗改變,我也跟著改變了,有如一種巫術。
我依然無法入睡,但這無關緊要。在一個沒有光和聲音的環境,我感受到另一個自我的覺醒。在清醒的夜晚,我第一次遇見了我的「夜間自我」。沉寂中,我聽到了她柔和哀婉的聲音。在朦朧意識狀態的靜謐中,我傾聽並學習。
起初,我在微小的事物中注意到「她」,我發現我的思考、感受、感知、記憶和存在狀態都起了微妙的變化。在夜裡,我無法條理分明地邏輯思考,也少了白日的樂觀開朗,我惆悵而若有所思,我常常反覆回味我的想法、對話和記憶。時間似乎被延展了,感知以慢動作移動,我更傾向於質疑和反思,我對世界的掌控感沒那麼到位了。
這一切看來都是好事,無論是反思、不慌亂、放鬆,都是好事,只要我還能維持些許的控制。然而,控制變得沒那麼輕鬆了,我很容易瞬間爆怒,憤怒如閃電來得快去得也急,我也會在彈指間就陷入後悔和悲傷。我的夜間自我是如此的易怒,有時讓我非常不安,但我喜歡這種不同的思維:放鬆,缺乏結構,輕薄而透明。思想、感知和記憶似乎如水般漫無邊界,大腦不再企圖去定義、整理、構建或評斷。
一開始,我把這些特質認為是人因為過度悲傷而引發的瘋狂,卻發現這樣的不眠夜並沒有伴隨著討人厭的焦慮。於是我意識到,我對「夜間自我」會如斯熟悉,是因為她一直陪伴著我,只是我從未注意過她罷了。因為我習慣在夜晚盡可能地爭取睡眠,加上對人造光的執著,我把她給徹底忽略了。
這一次,我決定歡迎她進入我的生活,跟她交朋友。
十二月的一個週日,我在狹窄的鄉村小徑慢跑,這是幾個月以來我第一次跑步。平常我偏好緩慢的步行,但在注定永遠改變我人生平衡點的這一天,我正在跑步。當天的空氣稀薄而閃閃發光,我的肺冷得陣陣刺痛。我感受到晨跑者都有的振奮心情,當下決定我的新年新希望,就是要多多跑步。我沒想過我可能再也不會有什麼新希望,或者,我可能還要過好長一段時間,才能再次體會這種振奮感。
當我快接近小屋時,手機響了。我很驚訝,因為現在才早上八點多,我以為會在手機螢幕看見丈夫馬修的名字,沒想到來電的是我父親的妻子,我稱她L。「喂,」我喘著粗氣,心想她是不是打電話來討論聖誕節計畫。我邀了她和我父親共進聖誕晚餐,一直以來我們都一起慶祝耶誕。自從我父母離婚後,聖誕節就是個需要花心思的節日。
二十二年來,我和手足分別成家立業,爸媽也上了年紀,家族成員中有離婚不合的,眾人四散各地,飲食習慣也不同,這些都需要協調。也就是說,少不了籌劃家族聖誕節會碰上的各種麻煩。今年由於疫情影響,只有一部分的家人能夠團聚。由於死亡人數還在不斷增加,也尚無疫苗(第一批疫苗在未來兩週內會出現),今年的慶祝活動勢必籠罩在焦慮之中。我父親特別謹慎,為了避免聚眾感染而採取了極端措施。我預期他可能會取消這個聚餐。
這些想法在我腦海中一一飄過,我在風中大聲喊,「喂?」
「你爸爸……,」L說。「急救人員在這裡。」
我不明白她在說什麼。為什麼急救人員會在那裡?
「他死了。」她說。
她聽起來冷靜而無動於衷,我以為我聽錯了。而且她的話完全沒有道理。首先,我爸不可能死了,我前兩天才和他通過電話,當時他好好的。第二,如果他死了,急救人員在那邊做什麼?
「心臟病發作。」她補充。
「我現在開車過去,」我說。「我馬上到!」我聽到背景有聲音,好像L正與某人商量。他們為什麼不對他進行急救?
「他們說讓你開車小心一點。」她的聲音依然平靜從容,「我是指警察說。」
警察?為什麼L會跟警察在一起?
我掛上電話開始尖叫。我一路狂奔哭泣著回到家,腦海不斷重複著一句話:我還沒準備好,我還沒準備好,我還沒準備好。
一切就從這裡開始。過了很久之後,我才覺得很奇怪,一個如此明確的結束,竟然也是如此明顯的開始。
丈夫馬修開車時,我打電話給我妹,又打給我弟。我妹妹失手把手機砸在地上,我聽到她不停尖叫。我弟很冷靜,後來我才意識到,我對妹妹的轉述太直白,而對弟弟講的則太模糊。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弟在一小時後打回來問我急救的進展,我只好跟他說,父親已經去世了近十二個小時,當場沒有救活的可能。然後,我弟說了和我一樣的話:「他不可能死了,我昨晚才和他通話。」他想得跟我一樣,這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了。我們需要更多時間。我們還沒來得及說再見,說我愛你。
公寓裡充斥著穿制服的人,他們正寫報告、講電話、喝茶,他們的存在暗示了秩序和確定,讓人迅速平靜下來。L問我是否想看看爸爸,我無法回答,只能點頭。我既想又不想,我努力調節情緒,保持冷靜;就跟L一樣,此刻的她比我見過的任何時候都要冷靜。
爸坐在他的紅椅上,看來像睡著了。接下來幾個月,我們一直反覆提起這個畫面,他看起來是多麼安詳。我碰碰他的手,冰冷如玻璃,那種冰冷感在接下來幾個月縈繞著我,但我最記得的卻是他的沉默。一開始不容易發現,因為周圍擠滿熙熙攘攘的人群,直到我隱約察覺,沒有絲毫的氣息從他的唇間洩出,沒有骨頭或關節的輕微聲響,沒有牙齒磨擦聲,也沒有衣物颤動聲,沒有言語。體內沒有生命的時候,我們就悄然無聲了。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死亡,我發現是那麼寧靜。我想,這是否就是我們會害怕沉默的原因。因為在沉默的縫隙,承載著我們無法忽視的事:人終有一死。
父親去世前一週,我剛協助母親安葬了與她相伴二十年的伴侶。道格拉斯和我母親沒有結婚,但我還是稱他「繼父」,我一直是這麼看待他的。母親為他哀悼,我們都為他哀悼,他在一個令他痛恨的養老院受盡病痛折磨才解脫。由於疫情,我們甚至無法探望他,更別說握著他的手,這讓我們留下滿腹的酸楚和壓抑。他就像成千上萬的其他人,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時沒有得到安慰和尊嚴。我胸口的緊繃感,也許就是我在父親去世當天去慢跑的原因,也許我希望能擺脫鐵鉗般的束縛,大口呼吸,以徹底甩掉憤怒和悲傷的痕跡。
然而,束縛卻更緊了。
當晚我待在父親家,睡在書房裡的行軍床,鋪蓋是橘色床單和橙色羽絨被,我的頭緊貼著書桌。我身邊都是他的藏書,他的筆跡停在筆記本中半句話的地方,他的開襟毛衣隨意披在椅背上。我父親總是為特定的物品賦予意義—石頭、羽毛、貝殼、小雕塑,這些物件都圍繞在我身邊,精心擺放在桌面和層架,以便他在寫作時可以看見。房裡充滿了他的氣息,他的存在感,他的希望。
第一晚,我根本沒奢望能夠睡著。我不想睡。我挑了幾本父親的書來看,準備流著淚度過一個情感豐沛但清醒的夜晚。我沒想到的是,當晚我沉沈睡去,一夜無夢!我醒來時感到震驚和羞愧:我沒有哭上一整夜,反而度過了記憶中最棒的一夜好眠。
在經歷了人生中的重大打擊,我怎能睡得那麼好?我後來在科學研究中讀到,像我這樣的反應並不罕見,因為大腦在必要時會關機,這是確保生存而設計的機制。
然而好景不常。接下來的十幾天,我在父親家忙著安排葬禮:處理驗屍和死亡證明,通知親友、撰寫訃告,裝飾(紙板)棺材,為L採買和做飯,處理種種伴隨著猝逝而來的雜務差事。L像行屍走肉般維持著日常作息,有時我會想,她的心神到哪裡去了?後來我才知道她一直處於震驚之中,這種麻木的表現,也是保護人免受極端痛苦的心理狀態。我把「震驚」視為一個所在,介於醫院和旅館之間。L悄然且不由自主地撤退到了那裡。
我把她的缺席視為理由,讓自己變得忙碌和「能幹」。但當夜幕降臨,我蓋上橘色被單,凝視著周遭書本的輪廓,我無法繼續偽裝。每晚,鐵爪堅定地緊繃在胸口,我差點以為我也要心臟病發了!我哭泣、喘息、吞嚥著並努力放緩呼吸。然後我起床,展開另一個忙碌的日子。
很顯然,那個不受干擾的第一晚只是個異常現象。我開始在安眠藥櫃翻找,對抗越來越長的不眠之夜。我吞了很多奈妥(Nytol)、褪黑激素和鎂,把枕頭灑滿洋甘菊和薰衣草精油;我戒掉藍光、咖啡因和酒精,翻出處方藥。當然,沒有任何效果。
然後我讓自己變得更忙碌。我深信知曉如何排解悲傷:我在網路上領養了一隻小狗,安排在父親葬禮第二天去接牠,還買好了玩具和食物。還有什麼比迎接新生命更能療癒這突如其來的失落?有誰會比小狗更適合承接我們無家可歸的愛?
然而,我們的小狗從被帶回家的那一刻就開始生病。牠病懨懨地躺著,偶爾喝口水。我看著牠軟弱無力的身軀,心裡充滿不祥的預感。聖誕節那天,我帶牠去看獸醫急診,獸醫懷疑牠感染了犬小病毒。他解釋說會有冗長的檢測,高昂的診療費,以及微乎其微的生存機會。由於疫情肆虐及無數規定,還有正值聖誕節,這個過程會比平常耗時。
「牠應該來自繁殖場吧。」他聳聳肩,「可能同胎的都會死。」
我們的小狗在獸醫院住了五個晚上。我們無法看望牠,因為犬小病毒不僅致命而且傳染性很高,牠被放在隔離病房。我們不斷打電話關切,每次獸醫都詢問我們是否願意讓小狗安樂死。醫療費日漸高昂,而牠一直沒有進食。但在測試結果出來之前,無法得到診斷。
「還有希望嗎?一點點也好?」我流著淚問。每天獸醫都說,「也許有一線希望……總會有希望。」到了第五個晚上,獸醫打電話來:「牠的情況惡化,我認為沒希望了。」我們的小狗在獸醫護士的懷裡被安樂死。我們再也沒有見過牠。
幾個星期以來,我一直想著牠小小的身軀,牠這麼年幼就死掉令我無比傷痛。我把牠從母親的身邊帶走,放任牠死去,我沒有好好保護牠。一隻跟我們相處不到三天的動物,竟能帶給我如此痛苦,我很吃驚。即使我們沒有建立真正的關係,也沒有共同的經歷,但我現在一想到牠,眼淚還是流個不停。因為牠瘦小的肩膀也肩負著希望的重擔,某種難以言喻的方式讓牠成為一個熔爐,一個讓我懷念父親和繼父的方式。突然間,那負擔彷彿太沉重了,於是一切再次回到了牠的微小。
我不希望這巨大狂烈的悲痛驚嚇到我的孩子,我還有悲傷的家人要照料,如果我崩潰了,對身邊的人毫無益處。於是,白天我忙於為小狗伸張正義,晚上則忙於處理我父親的遺產——保持忙碌,保持忙碌,保持忙碌。
但我還是無法入睡。
然後在一個灰濛濛的黎明,我忽然發現,總在夜晚哀悼成了我的常態。因此,我把安眠藥收了起來,慢慢接受這麼多個無法入眠的夜晚。此時我意識到,這並非我平常習慣性的失眠,曾幾何時,我的不眠之夜已經變為我未曾預料的樣子,它們成了重要的避風港。雖然我的白天塞滿事務安排和照顧責任,但我的不眠夜卻成為內心的綠洲。
在這個黑暗而令人舒適的地方,我開始明白在夜裡清醒的必要性。
這些漫長而無法成眠的時光,是我從未經歷過的。不像過往的失眠,那種習慣性的恐懼和焦慮並不存在。這次不一樣,黑暗似乎在移動並軟化了,而且有著重量和密度,彷彿將我包圍在棉花糖或甜美的蛋白霜裡。有時,黑暗給人的感覺是一層柔軟的保護膜,一張可以讓我迷失其中的輕柔皮毛。
我清楚記得被黑暗扶持的感覺。它從未對我施壓,只是支撐著我;不提問,也不要求。黑暗給了我空間、隱秘、安靜和匿名性,然而它似乎在我身旁呼吸脈動,就像一個沉睡的同伴,因此我從不孤單。
這位同伴並非完全緘默,我的夜晚會伴隨著自己的聲音景觀:飛機聲、車流聲、無法解釋的刮擦聲、摩擦聲和碰撞聲。我這才了解到,還有另一個世界與我同時清醒著,我第一次聽到了我後來稱之為「夜間自我」的微小聲音—心跳聲、唾液流動聲、腳跟摩擦床單的聲音。
每晚當我忽然睜開眼,腦中浮現父親的身影,接著是小狗和道格拉斯,我想到那些已然失去且永遠無法尋回的事物。我的胃底出現一個空洞,巨石壓在胸口,然後黑暗迅速湧入,彷彿在說「但還有我在啊,我屬於你。」這就像一種緩衝,介於我和身體的疼痛之間。
這時,有一種鬆口氣的感覺湧上心頭:我不需要起床,不需故作堅強,也不需要急著安排什麼,我可以與我的悲傷靜靜躺著,挖掘那害怕失去的記憶,尋找問題的答案:我父親在哪?道格拉斯和小狗在哪?死去的人會去哪?
作為一個未知論者,我一直被這個問題困擾。白天,我沒有時間思考這件事。而且在白天思考這種問題似乎很荒謬,不可能有答案。然而到了夜裡,思考這個問題再合理不過。
我們都曾在黑暗中搜尋,這個尋找的過程(從摸索門把到找尋車鑰匙)讓人覺得很有意義,我們可以耐心優雅的翻找。試想,如果是在明亮的光線下搜尋東西,往往會顯得很無能,我們會譴責自己愚蠢,最後變得匆忙又沮喪。所以我感覺,探索亡者行蹤這類事情根本就是個夜間任務,應該在黑夜的掩護下進行。
夜色漸逝,從綢緞般的漆黑轉變為帶著銀灰的不透明,天色變得稀薄且顆粒感十足。黎明的光透進房間,車流聲持續響起,鳥兒鳴唱。黑暗已經隱沒,不再支撐著我,而我的眼睛酸痛,空洞無物,渴望入眠。然而,那些黑暗時刻給予了我比睡眠更深刻的東西,它給了我純粹的時間和空間,同時讓我擺脫了我後來稱為「白日思考」的束縛。
在一個不眠夜,我聽到走廊地板發出了嘎吱聲。我突然想到,也許此時孩子們都還醒著,他們敞開的心靈正思考著那些令我困擾的問題。我腦海不斷轉動:數十萬人才因為新冠肺炎而過世,這無疑意味著數十萬人正清醒地處在同一個邊界、痛苦和無眠之地。我的想像力被這個影像絆住了:好多失親同胞孤獨卻微妙地相連,佔據著同一個半成形的世界。我開始好奇,那些跟我一樣不成眠的哀悼者是誰,他們在做什麼?想什麼?又感受到什麼?
失眠往往是由失落所引發。根據《睡眠醫學評論》的研究,「失去親友常與入睡困難、無法維持睡眠,以及睡眠時數減少密切相關。」簡單來說,喪親者很少能夠一夜好眠。研究指出,悲傷越強烈,睡眠就越破碎、零碎且中斷。
生理性別在其中扮演著一定的角色:喪親的女性比男性更常出現睡眠障礙。年齡也加劇了失眠問題,越年輕的人,越不會因喪親而影響睡眠。另外,死亡性質也有影響,意外死亡比預期的死亡更容易打亂喪親者的睡眠節奏。我是個剛經歷了數起非預期死亡的中年女性,難怪,現在遭遇了我人生中最嚴重的失眠。
但是,哀悼的人不僅睡得少,睡眠方式也不一樣。研究人員測量喪親者的睡眠波長,發現他們的睡眠呈現更多的快速眼動(充滿夢境的)模式,較少深層而具有修復作用的睡眠。悲傷越強烈,睡眠變化就越大。
當然了,失眠的時間也越長。
我父親去世前,我的失眠持續了二十多年。我完全預期自己無法入睡,也預期失眠會更嚴重,所以我習慣先靠安眠藥,接著憤怒地在床上翻來覆去,最後聽著有聲書斷斷續續睡著。過去幾次失眠,我經常乾脆放棄睡覺,結果到天亮時整個人疲憊不堪,滿臉憔悴,詛咒著夜晚,痛罵自己無法入睡。
然而現在,因為心中充滿了悲傷,我發現我的夜晚正在改變。我開始期待夜裡的清醒時光,那如墨的安慰、柔和的寧靜,以及平靜。夜裡,我可以放下堅強形象,我不再是那個負責張羅一切的女兒,我可以盡情悲傷,也不會影響到任何人——我可以做我自己。
黑暗有一種簡化的能力,這正是我喜歡並且需要的。我看不到滿地必須清掃的蜘蛛網,看不到堆積如山的待洗衣物,我什麼也看不見。於是,我的目光轉向內心。從前這意味著我要冥想幾個小時,然後把夜半還醒著當成一場災難,擔心睡眠不足隔天會犯錯。或者,我會血壓飆升,腦袋昏沉,讓負面情緒糾纏個沒完。但因為此刻我陷於喪親之痛,正在跟更大的問題搏鬥,所以這些擔憂悄然消散了。我不在乎不眠夜帶來的威脅,如果我隔天看起來很疲憊或者脾氣暴躁,那又怎麼樣?
聖誕假期結束,我的家人陸續返回倫敦,而我決定留在位於城外的小屋,離L與母親近一點。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日常的喧囂。倫敦忽然變得比往常更吵雜,我耳裡的隔音層好像被剝掉了,噪音令我痛苦。飛機、汽車警報、救護車警笛、摩托車轟鳴,一切聲音都被放大得刺耳,在我聽來有如驚恐的死亡之聲。
但鄉村夜晚的聲景就柔和得多。我喜歡聽著風聲,田野羊群的咩叫,門前柳樹的嘆息和吱嘎。我喜歡化作音樂的夜雨宛如音符,雨水拍打玻璃落在屋頂上的滴答,那是黑暗中零星而綿密的毛毛雨。雨聲交錯著絕對的寂靜時刻,那寂靜同時映照我內心的空虛,卻也暗示了其他的可能。
然而除了寂靜,我還渴望黑暗——濃密而純粹的黑。我花了幾個小時用膠帶遮擋住藍色的網路信號燈,在窗戶上安裝紙板。每一絲人造光都是一種冒犯。這突如其來對黑暗的渴望讓我倍感困惑,因為過去我總是害怕它,也怕隨之而來的遺忘、壓抑,以及黑暗誘發的可怕幻想。然而此時,黑暗似乎帶來了解放,予人安慰。黑暗的神秘感給了我希望與救贖。
我也學會辨識黑暗的色調和質地,它可能輕如羽毛,柔軟如肌膚,或如毯子般漆黑厚重。我感到意外:當黑暗改變,我也跟著改變了,有如一種巫術。
我依然無法入睡,但這無關緊要。在一個沒有光和聲音的環境,我感受到另一個自我的覺醒。在清醒的夜晚,我第一次遇見了我的「夜間自我」。沉寂中,我聽到了她柔和哀婉的聲音。在朦朧意識狀態的靜謐中,我傾聽並學習。
起初,我在微小的事物中注意到「她」,我發現我的思考、感受、感知、記憶和存在狀態都起了微妙的變化。在夜裡,我無法條理分明地邏輯思考,也少了白日的樂觀開朗,我惆悵而若有所思,我常常反覆回味我的想法、對話和記憶。時間似乎被延展了,感知以慢動作移動,我更傾向於質疑和反思,我對世界的掌控感沒那麼到位了。
這一切看來都是好事,無論是反思、不慌亂、放鬆,都是好事,只要我還能維持些許的控制。然而,控制變得沒那麼輕鬆了,我很容易瞬間爆怒,憤怒如閃電來得快去得也急,我也會在彈指間就陷入後悔和悲傷。我的夜間自我是如此的易怒,有時讓我非常不安,但我喜歡這種不同的思維:放鬆,缺乏結構,輕薄而透明。思想、感知和記憶似乎如水般漫無邊界,大腦不再企圖去定義、整理、構建或評斷。
一開始,我把這些特質認為是人因為過度悲傷而引發的瘋狂,卻發現這樣的不眠夜並沒有伴隨著討人厭的焦慮。於是我意識到,我對「夜間自我」會如斯熟悉,是因為她一直陪伴著我,只是我從未注意過她罷了。因為我習慣在夜晚盡可能地爭取睡眠,加上對人造光的執著,我把她給徹底忽略了。
這一次,我決定歡迎她進入我的生活,跟她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