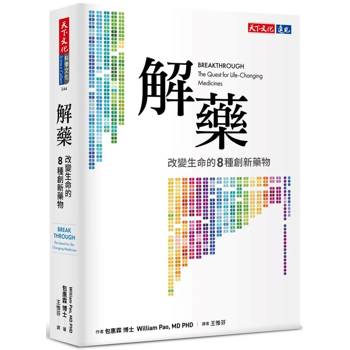前言 為了父親、也為了下一代
巴西蝮蛇是致命的掠食動物。長久以來,在巴西東南部從業的農民,一直遭受巴西蝮蛇的危害,因為此處是牠們的自然棲地。幾世紀以來,許多人親眼目睹過這種蛇類毒液的可怕威力,任何人只要被咬上一口,就會當場倒下。由於毒性強大,當地原住民會把巴西蝮蛇的毒液塗在箭頭上,獵物只要中箭,便會失去行動力。
巴西藥理學家羅沙席爾瓦(Maurício Rocha e Silva)其實早在1940 年代,就對響尾蛇屬的蝮蛇產生興趣。當時正值二戰期間,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陷入戰火之際,羅沙席爾瓦則在聖保羅的生物研究所研究循環休克(circulatory shock)。他的團隊試圖了解蛇毒的毒理學,解釋毒液對人體的作用。
1948 年,羅沙席爾瓦團隊發現一種未知的胜肽(為短鏈胺基酸,是蛋白質的組成成分),對動物施加蝮蛇的毒液後,血漿中這種胜肽的濃度會跟著升高。這種神祕的分子會導致血管擴張,一旦受害者遭蝮蛇咬傷,血壓就會下降,有時甚至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當血壓不足以驅動血流,重要的肌肉、神經和腦細胞就會缺氧。羅沙席爾瓦團隊將這種造成嚴重破壞的奇怪胜肽稱為緩激肽(bradykinin)。
這一年,傑出的巴西醫師費雷拉(Sérgio Ferreira)還只有14 歲。費雷拉在聖保羅州長大,原本的志向是成為精神科醫師,因此申請就讀醫學院。但考慮到這份夢想工作將面對的現實,他改變了主意:「在巴西,精神病的公共照護條件相當差,所以我決定當個科學家。」於是他後來加入了羅沙席爾瓦的實驗室,開始研究蝮蛇毒液和緩激肽。
1964 年,正在進行博士研究的費雷拉,發現蝮蛇毒液中含有一種物質,可讓緩激肽的活性變得更強,稱之為緩激肽增強因子。蝮蛇之所以致命,是因為牠的毒液會破壞人體內負責調節血壓的重要分子系統。不過真正的醫學突破,要等到費雷拉搬到倫敦後才出現。他那時加入另一位傑出藥理學家范恩(John Vane)的實驗室,並且帶了一瓶蝮蛇的緩激肽增強因子前往英國。
范恩是俄羅斯移民第三代,自稱信奉「實驗主義」。「12歲那年,」他寫道:「我父母在聖誕節送我一套化學試劑組,很快的,我對做實驗著迷不已。」他的第一次實驗使用了本生燈,瓦斯來自他母親的瓦斯爐,最後引發「一場涉及硫化氫(有毒的腐蝕性氣體)的小爆炸」,毀了廚房新粉刷的牆壁。於是這位早熟的年輕科學家,被趕到一間棚屋。
范恩對高血壓很感興趣,這是世界各地的重大死因。高血壓是造成中風、心臟病、心臟衰竭和腎衰竭的主要因素,當時有數百萬人,因為無法可靠的控制血壓而面臨過早死亡的風險。人體必須能夠根據身體的活動調升或調降血壓,我們有一套複雜的生理機制和備援控制系統,可將血壓保持在適當範圍。當費雷拉加入實驗室時,范恩團隊正忙著尋找血壓控制系統的關鍵。其中一種關鍵成分是血管收縮素II,這是一種會導致血管壓力上升的胜肽。製造這種胜肽,得使用一種稱為血管收縮素轉化酶的酵素。
「費雷拉帶來這個……棕色黏液,」巴赫勒(Mick Bakhle)在2016 年接受採訪時笑著回憶。當時,巴赫勒也是范恩研究團隊的一員,那時的任務正是研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得知蝮蛇毒液對血壓的影響後,范恩在1970 年,讓巴赫勒測試費雷拉的緩激肽增強因子對血管收縮素轉化酶的影響。「這種棕色黏液不是很好操作,但我們確實做了測試,結果大吃一驚……」
范恩實驗室證實費雷拉的棕色黏液,可以抑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在當時,這是備受矚目的大發現,證實南美洲的蛇毒萃取物,可以讓血壓上升胜肽的生成酶關閉。少了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就無法生成血管收縮素II;沒有血管收縮素II,可能就沒有高血壓的問題。
當時還有一個發現: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會使緩激肽失去活性,這意味著如果沒有這種酵素,緩激肽會繼續作用,使血壓降得更低。這項發現可說是毒蛇之謎的最後一塊拼圖。范恩立即意識到,蝮蛇毒液抑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在醫學上的意義。但他也明白,儘管費雷拉的蛇毒胜肽很有效,卻是糟糕的降血壓藥。因為高血壓是慢性病,需要長期、有時甚至是長達一生的定期治療。除非透過口服,否則大多數人很難重複用藥。
偏偏緩激肽增強因子無法製成口服錠,因為這種分子的結構相當脆弱,會在胃中直接分解,無法送達血液。想使用它,只能仿效毒蛇使用毒液的方式,也就是直接注射。但世界需要的,是一種能夠通過人體的消化系統、經由腸道完全吸收到血液的藥丸,可用來抑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以治療高血壓。
這種如珍珠般寶貴的藥物,超出了學術實驗室的能力。不過范恩當時也擔任美國施貴寶(Squibb)製藥公司的顧問,他向公司提案製作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認為是相當有潛力的研發方向。施貴寶藥廠的兩位化學家庫許曼(Dave Cushman)和翁德蒂(Miguel Ondetti)接下范恩遞出的棒子,為費雷拉的蝮蛇胜肽繪製了分子結構圖,並開始設計結構類似、但更強韌的化學分子。經過長年研究,經歷多次挫折後,他們最終成功了,發明的藥物命名為卡托普利(captopril),於1981 年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成為第一種可靠且安全的高血壓藥物。
乍看之下,卡托普利似乎相當普通,由常見的成分組成,有9 個碳原子、15 個氫、3 個氧、1 個硫和1 個氮,僅此而已。然而,卡托普利堪稱20 世紀的一大創新,絕對能與科學界的其他發現媲美。飛機打開世界的大門;半導體和網路迎來數位時代;但卡托普利和隨後出現的其他血管收縮素轉換酶抑制劑,讓數百萬人延長了壽命。
家族使命
身為一名腫瘤學家,也是癌症醫師,我曾治療重症患者長達14 個年頭。在這段期間,我協助過許多患者延長生命,但也看過許多病人死亡,或長期痛苦、處於失能狀態。我看診過的每位病患都成為一股動力,激勵我改善現狀。不過促使我走上癌醫這個職涯的人,是我的父親,他於1981 年因為結腸癌而早逝。
我父親於1922 年出生於中國,在1948 年5 月搭乘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梅格斯將軍號」來到美國。甫到新國度的他舉目無親,但因為擁有上海國立醫學院的學位,所以有機會在猶他州的奧格登接受住院實習醫師的培訓,領取每個月100 美元的津貼。之後,他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接受進一步的訓練,並在該州洛克維一家名為栗子館(Chestnut Lodge)的私人精神療養院找到工作,最終成為心理治療部主任。
關於父親,我記得最清楚的回憶,是跟他一起打牌或玩拼字遊戲,還有聽他唱百老匯歌曲或演一段中國京戲。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我們每四個星期會相約去理髮,然後一起吃午餐。
父親第一次入院是在1979 年,當時我11 歲。我不記得有人告訴我他罹患了癌症,還以為他是因為糞便中有血才住院。回想過去,我想他那時應當是結腸癌第三期,並做了切除手術。之後,他肯定接受了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藥物化療,所以頭髮脫落,還出現噁心和嘔吐的症狀。我們共享理髮和午餐的日子就那樣暫停了。不過化療完成後,父親康復了,生活似乎恢復正常。
大約又過了兩年,父親回到醫院進行探查手術,因為癌症復發,醫師想確定擴散的程度(當時放射線影像的技術還不是很成熟)。結果父親死在手術臺上,醫師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大部分的肝臟,於是對病變處進行活體採檢,卻血流不止。
也許對父親來說,這是上天賜予的小小仁慈,讓他逃過緩慢的抗癌折磨。但對我家來說,父親過世卻是一大災難打擊。我們的遭遇絕非少數,癌症每天奪走大量患者的生命,其中有很多人都還很年輕,有很多人徒留悲傷的家人和朋友。全世界每年約有1000 萬人死於癌症,幾乎占總死亡人數的六分之一。我的母親也是醫師,父母一向希望我和姊姊能夠從醫,父親的過世更是強化我們兩人走上醫學道路的決心。父親走後,我誓言奉獻一輩子,為他這樣的病患帶來改變。
大約20 年後,經過大學、醫學院、實習醫師、住院醫師、研究員和博士後的訓練,我成為腫瘤內科醫師和轉譯科學研究人員,兼具癌症醫師和科學家的身分。在治療患者的同時,我也帶領一間學術轉譯研究† 實驗室,試圖從分子層級尋找癌症生長的原因,最終希望找到消除癌症的方法。
在那段時間,我與製藥公司合作開發新藥,包括一種重要的新型肺癌藥物,現在已有許多患者使用這種藥物延長生命(見第二章)。2014 年,我離開學術醫學界,轉而擔任製藥業的研發主管。我想直接投身開發新的治療選項,更廣泛的造福全球數百萬名病患。
藥物研發最前線
多年來我體會到,新藥的製造需要豐沛的創造力,但過程中大部分的付出,只有少數人有機會見證並因而珍惜。在大半的製藥業、生技公司、政府實驗室及整個學術界,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和專家每天都在努力創造各種分子,期望能夠拯救生命,或幫助病人復原,改善不適或功能。他們正在開拓新的生物學領域,發明新工具和新技術以攻擊藥物針對的靶點,並增進我們對疾病的理解。這個社群由創新所推動,其中的藥物獵人每天都在重繪新的科學疆界。然而,社會大眾對這些過程幾乎完全不理解。
對我來說,創新是想出沒人做過的事,然後證明可行,並有勇氣說服別人這些事值得做。這是各行各業中許多人都在追求的目標。我們勢必會尋找更好的方法──透過創新來創造價值。
身為癌症醫師、研究科學家和藥物開發者,我看見一個龐大的創新領域如何為大眾所不解,甚至不在意。致力研發下一代藥物的男女科學家們,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非凡的創新工作。我想藉由這本書,揭開其中一些創新的面紗,分享藥物研發最前線的故事。
要實現這份野心,並沒有那麼直截了當。矽谷創新故事中的產品,通常是廣為人知的設備或應用程式,幾乎無所不在,單憑直覺便可使用。相較之下,在藥學領域中,創新故事裡的產品非常小,通常是肉眼看不見的分子,即使是具有科學背景的人,也常常難以理解這些產品的名字和作用方式。這些分子可能拯救成千上萬的生命,但要是連它的名稱讀起來都是一場噩夢,又有誰會來談它呢?
而且讓我們面對現實:如果可能,大多數人寧願不吃藥。只有在本人或親人遭受疾病侵襲時,才會勉為其難認識一下藥物。此外,每個人的健康狀況不同,所以只有少數藥物會廣為人知或廣受服用。
這正是我們在降血壓藥物卡托普利的故事中所看到的,要開發出一種新藥,背後很少只靠一位英雄或一個團隊。創新過程通常會涉及多個組織,以及數百名科學家數十年的努力。即使是開藥的醫師,也很可能不知道他開的藥是誰發明的。相對於其他創新,藥物研發的故事顯得既抽象又隱晦。
不過最嚴峻的挑戰,可能還是科學本身。火箭科學是出了名的困難,但太空探索的基本問題很容易溝通:如何確保太空人有足夠的氧氣;如何抵禦太空中的寒冷或重返大氣層時的高熱;如何在無重力狀態下移動。然而談到癌症治療時,說故事的人必須先從細胞層級開始解釋什麼是癌症,這種病症如何受分子訊息傳導路徑所驅動,以及路徑是由致癌基因編碼的酵素所組成──你能理解這段話在講什麼嗎?
儘管看起來很複雜,但我將在本書中,試著分享自己對世界各地藥物開發實驗室的創新所油然興起的敬畏之心。這些故事將打開一扇大門,讓讀者得以更詳盡、深入的知道,要創造出這些可在我們身上或身體裡作用的新產品,要付出什麼樣的心血。醫學是一般人從小就會接觸的科技;吃個藥,身體就能變好,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其實這件事非常了不起!正如後面章節一位科學家所讚嘆的:「哇,天哪!只要化學家建構出正確的分子,就可以讓一種重症就此消失。」
想製造新藥,必須先解碼自然,也就是生命經過數百萬年演化得出的生物學祕密。我們必須先確定疾病,對它加以描述,並以科學方法理解疾病發生的原因,然後尋找方法改變病程,也就是提供患者特定的化學分子,以影響疾病,但同時不帶來明顯的副作用。這整個過程是群策群力的成果,集結人類的聰明才智、毅力、協作和韌性所得來的勝利。讀這些故事會讓你對人類的潛力充滿希望,相信我們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開發新藥牽涉的科學確實很具挑戰,但並非深不可測。事實上,我認為它很迷人,有時令人感到興奮不已,有時深具啟發。一旦理解,就會對自己身體的運作方式有更好的認識。讀這些故事,你不需要有任何科學背景,只需要一顆願意探究的好奇心。
我希望本書能成為一座明亮的燈塔,讓考慮以生命科學為職志的年輕人,得到一些指引。在人生中,我們的心態及重大的決定,都會因為我們所聽到的故事而受到左右,但關於藥物研發的故事實在太少了。
如果想鼓勵下一代加入對抗癌症及老年失智症的行列,或準備好應對下一次的流行性疾病,就需要挖掘並分享經典的科學創新過程中那些無名英雄的故事。所以接下來請跟我著,一起深入探索八種藥物的研發冒險之旅。我們將明白,為什麼目前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藥物乙醯胺酚(paracetamol,普拿疼的主成分),在最初發現後的數十年間,一直被束之高閣;從一位病童毅力非凡的母親身上,看到少數人如何憑藉決心和動力,推動創新;巧妙修改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如何促成突破,將血友病患者解放出來,不再需要過著幾乎每天輸血的痛苦生活;子宮內胎兒才擁有的血液,如何在成人體內被喚醒,用以治療鐮狀細胞貧血症;對錐體幾何的熱情,如何通往治療愛滋病的新方法;肆虐全球的大流行,如何促使研究者在破紀錄的短時間內,研發出抗病毒藥物;還有,針對特定基因標靶的新療法,又是如何延長了癌症患者的生命。
在這一段段的旅程中,我們將探索各種偉大的想法是從何而來;傑出科學家如何克服一個又一個障礙;不同團隊如何攜手努力,追求共同目標;創新者如何充分掌握偶然機運;最新突破如何從看似毫不相關的深層基礎知識中得出;科學家又如何從試誤學習中求取進步,即使他們非常聰明;最後,個人的好奇心和專注投入,如何驅使研究人員前行。
新藥的發現意味著,只要投入時間、毅力、技能,彼此合作再加上一點運氣,就可以達成看似不可能的突破。我希望書中藥物開發人員所展現的堅定決心和非凡創造力,能激勵你在自己所選的領域中創新,甚至改變人們的生活,就像書中人物一樣。
巴西蝮蛇是致命的掠食動物。長久以來,在巴西東南部從業的農民,一直遭受巴西蝮蛇的危害,因為此處是牠們的自然棲地。幾世紀以來,許多人親眼目睹過這種蛇類毒液的可怕威力,任何人只要被咬上一口,就會當場倒下。由於毒性強大,當地原住民會把巴西蝮蛇的毒液塗在箭頭上,獵物只要中箭,便會失去行動力。
巴西藥理學家羅沙席爾瓦(Maurício Rocha e Silva)其實早在1940 年代,就對響尾蛇屬的蝮蛇產生興趣。當時正值二戰期間,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陷入戰火之際,羅沙席爾瓦則在聖保羅的生物研究所研究循環休克(circulatory shock)。他的團隊試圖了解蛇毒的毒理學,解釋毒液對人體的作用。
1948 年,羅沙席爾瓦團隊發現一種未知的胜肽(為短鏈胺基酸,是蛋白質的組成成分),對動物施加蝮蛇的毒液後,血漿中這種胜肽的濃度會跟著升高。這種神祕的分子會導致血管擴張,一旦受害者遭蝮蛇咬傷,血壓就會下降,有時甚至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當血壓不足以驅動血流,重要的肌肉、神經和腦細胞就會缺氧。羅沙席爾瓦團隊將這種造成嚴重破壞的奇怪胜肽稱為緩激肽(bradykinin)。
這一年,傑出的巴西醫師費雷拉(Sérgio Ferreira)還只有14 歲。費雷拉在聖保羅州長大,原本的志向是成為精神科醫師,因此申請就讀醫學院。但考慮到這份夢想工作將面對的現實,他改變了主意:「在巴西,精神病的公共照護條件相當差,所以我決定當個科學家。」於是他後來加入了羅沙席爾瓦的實驗室,開始研究蝮蛇毒液和緩激肽。
1964 年,正在進行博士研究的費雷拉,發現蝮蛇毒液中含有一種物質,可讓緩激肽的活性變得更強,稱之為緩激肽增強因子。蝮蛇之所以致命,是因為牠的毒液會破壞人體內負責調節血壓的重要分子系統。不過真正的醫學突破,要等到費雷拉搬到倫敦後才出現。他那時加入另一位傑出藥理學家范恩(John Vane)的實驗室,並且帶了一瓶蝮蛇的緩激肽增強因子前往英國。
范恩是俄羅斯移民第三代,自稱信奉「實驗主義」。「12歲那年,」他寫道:「我父母在聖誕節送我一套化學試劑組,很快的,我對做實驗著迷不已。」他的第一次實驗使用了本生燈,瓦斯來自他母親的瓦斯爐,最後引發「一場涉及硫化氫(有毒的腐蝕性氣體)的小爆炸」,毀了廚房新粉刷的牆壁。於是這位早熟的年輕科學家,被趕到一間棚屋。
范恩對高血壓很感興趣,這是世界各地的重大死因。高血壓是造成中風、心臟病、心臟衰竭和腎衰竭的主要因素,當時有數百萬人,因為無法可靠的控制血壓而面臨過早死亡的風險。人體必須能夠根據身體的活動調升或調降血壓,我們有一套複雜的生理機制和備援控制系統,可將血壓保持在適當範圍。當費雷拉加入實驗室時,范恩團隊正忙著尋找血壓控制系統的關鍵。其中一種關鍵成分是血管收縮素II,這是一種會導致血管壓力上升的胜肽。製造這種胜肽,得使用一種稱為血管收縮素轉化酶的酵素。
「費雷拉帶來這個……棕色黏液,」巴赫勒(Mick Bakhle)在2016 年接受採訪時笑著回憶。當時,巴赫勒也是范恩研究團隊的一員,那時的任務正是研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得知蝮蛇毒液對血壓的影響後,范恩在1970 年,讓巴赫勒測試費雷拉的緩激肽增強因子對血管收縮素轉化酶的影響。「這種棕色黏液不是很好操作,但我們確實做了測試,結果大吃一驚……」
范恩實驗室證實費雷拉的棕色黏液,可以抑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在當時,這是備受矚目的大發現,證實南美洲的蛇毒萃取物,可以讓血壓上升胜肽的生成酶關閉。少了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就無法生成血管收縮素II;沒有血管收縮素II,可能就沒有高血壓的問題。
當時還有一個發現: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會使緩激肽失去活性,這意味著如果沒有這種酵素,緩激肽會繼續作用,使血壓降得更低。這項發現可說是毒蛇之謎的最後一塊拼圖。范恩立即意識到,蝮蛇毒液抑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在醫學上的意義。但他也明白,儘管費雷拉的蛇毒胜肽很有效,卻是糟糕的降血壓藥。因為高血壓是慢性病,需要長期、有時甚至是長達一生的定期治療。除非透過口服,否則大多數人很難重複用藥。
偏偏緩激肽增強因子無法製成口服錠,因為這種分子的結構相當脆弱,會在胃中直接分解,無法送達血液。想使用它,只能仿效毒蛇使用毒液的方式,也就是直接注射。但世界需要的,是一種能夠通過人體的消化系統、經由腸道完全吸收到血液的藥丸,可用來抑制血管收縮素轉化酶,以治療高血壓。
這種如珍珠般寶貴的藥物,超出了學術實驗室的能力。不過范恩當時也擔任美國施貴寶(Squibb)製藥公司的顧問,他向公司提案製作血管收縮素轉化酶抑制劑,認為是相當有潛力的研發方向。施貴寶藥廠的兩位化學家庫許曼(Dave Cushman)和翁德蒂(Miguel Ondetti)接下范恩遞出的棒子,為費雷拉的蝮蛇胜肽繪製了分子結構圖,並開始設計結構類似、但更強韌的化學分子。經過長年研究,經歷多次挫折後,他們最終成功了,發明的藥物命名為卡托普利(captopril),於1981 年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核准,成為第一種可靠且安全的高血壓藥物。
乍看之下,卡托普利似乎相當普通,由常見的成分組成,有9 個碳原子、15 個氫、3 個氧、1 個硫和1 個氮,僅此而已。然而,卡托普利堪稱20 世紀的一大創新,絕對能與科學界的其他發現媲美。飛機打開世界的大門;半導體和網路迎來數位時代;但卡托普利和隨後出現的其他血管收縮素轉換酶抑制劑,讓數百萬人延長了壽命。
家族使命
身為一名腫瘤學家,也是癌症醫師,我曾治療重症患者長達14 個年頭。在這段期間,我協助過許多患者延長生命,但也看過許多病人死亡,或長期痛苦、處於失能狀態。我看診過的每位病患都成為一股動力,激勵我改善現狀。不過促使我走上癌醫這個職涯的人,是我的父親,他於1981 年因為結腸癌而早逝。
我父親於1922 年出生於中國,在1948 年5 月搭乘美國總統輪船公司的「梅格斯將軍號」來到美國。甫到新國度的他舉目無親,但因為擁有上海國立醫學院的學位,所以有機會在猶他州的奧格登接受住院實習醫師的培訓,領取每個月100 美元的津貼。之後,他在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接受進一步的訓練,並在該州洛克維一家名為栗子館(Chestnut Lodge)的私人精神療養院找到工作,最終成為心理治療部主任。
關於父親,我記得最清楚的回憶,是跟他一起打牌或玩拼字遊戲,還有聽他唱百老匯歌曲或演一段中國京戲。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我們每四個星期會相約去理髮,然後一起吃午餐。
父親第一次入院是在1979 年,當時我11 歲。我不記得有人告訴我他罹患了癌症,還以為他是因為糞便中有血才住院。回想過去,我想他那時應當是結腸癌第三期,並做了切除手術。之後,他肯定接受了5-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藥物化療,所以頭髮脫落,還出現噁心和嘔吐的症狀。我們共享理髮和午餐的日子就那樣暫停了。不過化療完成後,父親康復了,生活似乎恢復正常。
大約又過了兩年,父親回到醫院進行探查手術,因為癌症復發,醫師想確定擴散的程度(當時放射線影像的技術還不是很成熟)。結果父親死在手術臺上,醫師發現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大部分的肝臟,於是對病變處進行活體採檢,卻血流不止。
也許對父親來說,這是上天賜予的小小仁慈,讓他逃過緩慢的抗癌折磨。但對我家來說,父親過世卻是一大災難打擊。我們的遭遇絕非少數,癌症每天奪走大量患者的生命,其中有很多人都還很年輕,有很多人徒留悲傷的家人和朋友。全世界每年約有1000 萬人死於癌症,幾乎占總死亡人數的六分之一。我的母親也是醫師,父母一向希望我和姊姊能夠從醫,父親的過世更是強化我們兩人走上醫學道路的決心。父親走後,我誓言奉獻一輩子,為他這樣的病患帶來改變。
大約20 年後,經過大學、醫學院、實習醫師、住院醫師、研究員和博士後的訓練,我成為腫瘤內科醫師和轉譯科學研究人員,兼具癌症醫師和科學家的身分。在治療患者的同時,我也帶領一間學術轉譯研究† 實驗室,試圖從分子層級尋找癌症生長的原因,最終希望找到消除癌症的方法。
在那段時間,我與製藥公司合作開發新藥,包括一種重要的新型肺癌藥物,現在已有許多患者使用這種藥物延長生命(見第二章)。2014 年,我離開學術醫學界,轉而擔任製藥業的研發主管。我想直接投身開發新的治療選項,更廣泛的造福全球數百萬名病患。
藥物研發最前線
多年來我體會到,新藥的製造需要豐沛的創造力,但過程中大部分的付出,只有少數人有機會見證並因而珍惜。在大半的製藥業、生技公司、政府實驗室及整個學術界,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和專家每天都在努力創造各種分子,期望能夠拯救生命,或幫助病人復原,改善不適或功能。他們正在開拓新的生物學領域,發明新工具和新技術以攻擊藥物針對的靶點,並增進我們對疾病的理解。這個社群由創新所推動,其中的藥物獵人每天都在重繪新的科學疆界。然而,社會大眾對這些過程幾乎完全不理解。
對我來說,創新是想出沒人做過的事,然後證明可行,並有勇氣說服別人這些事值得做。這是各行各業中許多人都在追求的目標。我們勢必會尋找更好的方法──透過創新來創造價值。
身為癌症醫師、研究科學家和藥物開發者,我看見一個龐大的創新領域如何為大眾所不解,甚至不在意。致力研發下一代藥物的男女科學家們,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非凡的創新工作。我想藉由這本書,揭開其中一些創新的面紗,分享藥物研發最前線的故事。
要實現這份野心,並沒有那麼直截了當。矽谷創新故事中的產品,通常是廣為人知的設備或應用程式,幾乎無所不在,單憑直覺便可使用。相較之下,在藥學領域中,創新故事裡的產品非常小,通常是肉眼看不見的分子,即使是具有科學背景的人,也常常難以理解這些產品的名字和作用方式。這些分子可能拯救成千上萬的生命,但要是連它的名稱讀起來都是一場噩夢,又有誰會來談它呢?
而且讓我們面對現實:如果可能,大多數人寧願不吃藥。只有在本人或親人遭受疾病侵襲時,才會勉為其難認識一下藥物。此外,每個人的健康狀況不同,所以只有少數藥物會廣為人知或廣受服用。
這正是我們在降血壓藥物卡托普利的故事中所看到的,要開發出一種新藥,背後很少只靠一位英雄或一個團隊。創新過程通常會涉及多個組織,以及數百名科學家數十年的努力。即使是開藥的醫師,也很可能不知道他開的藥是誰發明的。相對於其他創新,藥物研發的故事顯得既抽象又隱晦。
不過最嚴峻的挑戰,可能還是科學本身。火箭科學是出了名的困難,但太空探索的基本問題很容易溝通:如何確保太空人有足夠的氧氣;如何抵禦太空中的寒冷或重返大氣層時的高熱;如何在無重力狀態下移動。然而談到癌症治療時,說故事的人必須先從細胞層級開始解釋什麼是癌症,這種病症如何受分子訊息傳導路徑所驅動,以及路徑是由致癌基因編碼的酵素所組成──你能理解這段話在講什麼嗎?
儘管看起來很複雜,但我將在本書中,試著分享自己對世界各地藥物開發實驗室的創新所油然興起的敬畏之心。這些故事將打開一扇大門,讓讀者得以更詳盡、深入的知道,要創造出這些可在我們身上或身體裡作用的新產品,要付出什麼樣的心血。醫學是一般人從小就會接觸的科技;吃個藥,身體就能變好,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其實這件事非常了不起!正如後面章節一位科學家所讚嘆的:「哇,天哪!只要化學家建構出正確的分子,就可以讓一種重症就此消失。」
想製造新藥,必須先解碼自然,也就是生命經過數百萬年演化得出的生物學祕密。我們必須先確定疾病,對它加以描述,並以科學方法理解疾病發生的原因,然後尋找方法改變病程,也就是提供患者特定的化學分子,以影響疾病,但同時不帶來明顯的副作用。這整個過程是群策群力的成果,集結人類的聰明才智、毅力、協作和韌性所得來的勝利。讀這些故事會讓你對人類的潛力充滿希望,相信我們可以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開發新藥牽涉的科學確實很具挑戰,但並非深不可測。事實上,我認為它很迷人,有時令人感到興奮不已,有時深具啟發。一旦理解,就會對自己身體的運作方式有更好的認識。讀這些故事,你不需要有任何科學背景,只需要一顆願意探究的好奇心。
我希望本書能成為一座明亮的燈塔,讓考慮以生命科學為職志的年輕人,得到一些指引。在人生中,我們的心態及重大的決定,都會因為我們所聽到的故事而受到左右,但關於藥物研發的故事實在太少了。
如果想鼓勵下一代加入對抗癌症及老年失智症的行列,或準備好應對下一次的流行性疾病,就需要挖掘並分享經典的科學創新過程中那些無名英雄的故事。所以接下來請跟我著,一起深入探索八種藥物的研發冒險之旅。我們將明白,為什麼目前世界上最多人使用的藥物乙醯胺酚(paracetamol,普拿疼的主成分),在最初發現後的數十年間,一直被束之高閣;從一位病童毅力非凡的母親身上,看到少數人如何憑藉決心和動力,推動創新;巧妙修改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如何促成突破,將血友病患者解放出來,不再需要過著幾乎每天輸血的痛苦生活;子宮內胎兒才擁有的血液,如何在成人體內被喚醒,用以治療鐮狀細胞貧血症;對錐體幾何的熱情,如何通往治療愛滋病的新方法;肆虐全球的大流行,如何促使研究者在破紀錄的短時間內,研發出抗病毒藥物;還有,針對特定基因標靶的新療法,又是如何延長了癌症患者的生命。
在這一段段的旅程中,我們將探索各種偉大的想法是從何而來;傑出科學家如何克服一個又一個障礙;不同團隊如何攜手努力,追求共同目標;創新者如何充分掌握偶然機運;最新突破如何從看似毫不相關的深層基礎知識中得出;科學家又如何從試誤學習中求取進步,即使他們非常聰明;最後,個人的好奇心和專注投入,如何驅使研究人員前行。
新藥的發現意味著,只要投入時間、毅力、技能,彼此合作再加上一點運氣,就可以達成看似不可能的突破。我希望書中藥物開發人員所展現的堅定決心和非凡創造力,能激勵你在自己所選的領域中創新,甚至改變人們的生活,就像書中人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