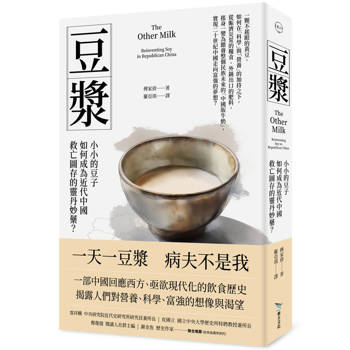4 哪一種奶?促進發育和發展的豆奶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在思考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時,乳類變成很重要的依據。儘管從早期的歷史時代開始,乳製品及相關製程已不斷傳入,乳類仍然象徵「他者」,令人聯想到中亞和帝國北疆的那些遊牧與半遊牧族群。乳類主要被視為老人(有時則是孩童)的藥物或補藥,而在烹飪著作中提到乳類時,往往會納入烹調過程,進行發酵、凝固或加熱,不會在新鮮狀態下食用。儘管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乳業於上海、哈爾濱、北京等數個中國通商口岸興起,乳類大體上依然位於中國人世界觀的邊陲。然而,歐美國家對乳類的觀念在十九世紀產生轉變,愈來愈多西方人開始喝牛奶,視為不可或缺的食物,於是中國人也漸漸認識到乳類的優良特質、在現代營養這個科學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打造健康強壯身體的作用。乳類變成西方富強的象徵,先前的他者概念並沒有淡化,只是重新被定位。
認為乳類對追求富強的現代中國十分重要的這個概念,催生乳類替代品的論述和物質實驗。中國人幾乎一發現牛奶被當作現代膳食的根基,為現代國家成功的關鍵,便開始探索更適合中國與中國人的其他可能。由於廣為流傳的營養觀念將乳製品視為人類膳食當中必要食物類別,其中又特別認為牛奶是關鍵的保護型食物,可確保個人和國家的健全,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的中國企業家和科學家便展開實驗,找尋改造豆漿這種常見食品(可以單獨飲用,但是更常用來作為豆腐的必要原料)的方法。在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和兒科醫生祝慎之等人的努力下,豆漿獲得新的詮釋,在論述上被建構成一種健康、更加衛生且蘊含尖端生產技術的牛奶替代品。豆奶跟牛奶顏色相近、營養豐富,在全球都在追求更好的營養健康時,可以成為中國對此做出的本地貢獻。
牛奶愈來愈被認為是標準膳食的核心要素,因此不喝牛奶就變成一個問題,而孕育現代中國的第一步就是要好好解決它。到了一九三○年代,牛奶變得跟兒童的生長和發育有關。發展主義的思維認為,孩童是乘載發展抱負的容器,並且孩童發育成為大人的過程就如同中國自身發展之路的生理展現,因此中國的營養科學家和其他營養社運人士便援引這些思想, 把孩子變成改革的主要接受者。尋找改正中國膳食的實際解方,變得跟拯救中國孩童的健康與活力──從瘦小的身材就能看出他們營養不良──畫上等號。營養和醫療科學家將跟嬰幼兒哺育有關的習慣做法視為需要改革的地方,重新評估哪些食物適合生長發育。
對許多人而言,富含蛋白質、源自本土的黃豆可以被改造來滿足發育中的孩童需求, 為中國的營養困境帶來一絲希望。經濟實惠、容易進行科學改造又比較容易消化的黃豆──尤其是豆奶這個形式,替中國開闢了一條發展道路,也符合現代國家的營養需求。許多推廣豆奶的宣傳用語都會說到,這是一種獨特的中國食物,在中國膳食中發揮的作用就跟牛奶一樣。事實不管是否真的如此,其實沒有那麼重要,重點在於這無形中挑戰了生物文化主義認為全世界都應該頌揚牛奶的假定。
牛奶之道
十九世紀時,科學界對牛奶及其化學性質產生興趣。當時,德國、法國和英國的科學家運用實驗室新研發出來的分析化學技術,開始調查食物、體液和人體組織的化學組成。一八二七年,英國醫生威廉.普洛特(William Prout,一七八五到一八五○年)找出維持人類生命的三個元素單位──「糖、油和蛋白」,稱這些是血肉、骨頭和人類能量的基石。後來的化學家修改了這種食物分類的用語,分別有:卡爾.施密(Carl Schmidt)在一八四四年提出的詞彙「碳水化合物」,用以表示糖類和澱粉類;「脂肪」;以及跟蛋白一樣遇熱會凝固的「蛋白質」。人和牛的乳汁是這三種元素都有包含在內的食物。普洛特稱讚牛奶是天意使然才會存在的普世營養物質。他說:「在所有能證明整個自然秩序都是事先設計好的證據中,牛奶提供了最為確鑿的例證。」他還說:「這是大自然特意設計和製作成食物的唯一營養物,也是所有有機體當中唯一如此製造的物質。因此,牛奶為營養物質應該要是什麼樣子的模範──可以說是一種原型,是所有營養物質的標竿。」
普洛特對牛奶強大力量的讚許傳播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令羅伯特.米勒姆.哈特利(Robert Milham Hartley,一七九六到一八八一年)印象深刻;他是紐約的社會改革家,因受到宗教啟發而參與禁酒運動,同時也是紐約改善窮人狀況協會的第一任會長。哈特利積極改善窮人嬰孩的牛奶供應情況。美國城市的發展導致哺乳情形減少,因此為人母者──特別是富有人家──改以牛奶取代奶娘。但,最容易取得的牛奶是廉價的「餿水牛奶」,也就是被餵食都市釀酒廠副產物的牛所分泌的乳汁。哈特利批評「餿水牛奶」是一種危險的產品,花費很多心力證明攝取這種乳品會帶來的道德與生理危害。他發起行動要廢止紐約餿水牛奶體制,使用藉由鐵路運到城市的「純淨」鄉村牛奶取而代之。這是因為他強烈相信牛奶是一種本質美好、上帝賜予的人類食物,也是「所有營養食物當中最完美之物」。哈特利憎惡的是餿水牛奶體制,不是牛奶本身。他的目標是要「讓市民恢復聖經的鮮乳飲用傳統」。
哈特利讚不絕口地稱讚牛奶是適合每個人的完美食物,儘管很符合他的牛奶改革家身分,卻過分誇大了牛奶在一九一○年代美國膳食中的地位。起初,牛奶改革家動員起來是為了增加特定族群,也就是嬰兒(後來還有身體衰弱者)的牛奶攝取量。雖然牛奶廣泛被當作一種烹飪食材,但是將牛奶當作飲品攝取的情況卻很少見,特別是在美國城市。牛奶被認為是適合每個人的優良食物,得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至少在美國和英國是如此)。會有這樣的轉變,有一部分是因為維生素和其他微量營養素的發現,大大改變了西方科學家對膳食與營養的理解。在試圖理解維生素功用的過程中,麥科勒姆和霍普金斯等科學家發現,把牛奶加在不恰當的純化物質中,似乎可以為實驗動物帶來奇蹟般的生長效果。美國農夫將牛奶補充品加進牲畜的飼料中,也曾經發現類似的效果。普洛特先前展現了牛奶的獨特性(同時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這三大膳食元素),這下被證實是對的,只不過理由不太一樣,這次是因為發現牛奶裡含有維生素。麥科勒姆說:「牛奶的組成非常特別,因此無論是搭配動物或植物來源的食物,都能修正其膳食缺陷。」
牛奶的營養地位獲得提升,連兒科這個新興領域的美國從業人員都很看好,主張牛奶可以預防兒童營養缺乏症。嬰兒照護的醫療化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前便已經展開,當時愈來愈多美國醫生投身尋找嬰兒死亡率根本原因的行列。針對高嬰兒死亡率,許多醫學作家和研究型醫生都認為原因出在不適當的哺育方式和食物,儘管母乳普遍被認為是最好的嬰兒食品,大部分的醫生卻認為「理想的母乳」並不存在,因此鼓勵女性使用替代品。牛奶被捧為最好也最容易取得的替代品。一名卓越的美國兒科醫生曾說:「若要避免兩歲以下的孩童生病死亡,並確保即將來臨的世代能夠存活下來、維持國家水準,除了使用母乳哺乳,牛奶是絕對必要的─這件事無庸置疑。」
牛奶被譽為是大自然最完美的食物,甚至還被認為是現代文明能夠崛起最重要的營養因子。麥科勒姆在全脂牛奶的脂肪中找到促進動物與人類生長的關鍵物質(維生素A), 堅稱牛奶及其相關製品是必要、甚至最好的保護型食物,根據某地的膳食當中有沒有這種食物,便能預測當地的社會、文化與科學成就。麥科勒姆在一九一八年寫到,世界上分兩種人,一種是膳食中包含牛奶的人,另一種就是膳食中不含牛奶的人。一方面,「由中國人、日本人和大部分熱帶地區的人為代表」的那些人,「幾乎完全以植物的葉子當作唯一的保護型食物。他們也吃蛋,這補救了他們的膳食。」另一方面,北美和歐洲的族群「同樣也會運用植物的葉子,但程度較低。此外,他們的食物來源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牛奶及其製品。」這些膳食方面的差異造成截然不同的社會文化結果:「以植物葉子作為唯一保護型食物的人們,其特徵包括體型矮小、壽命相對較短、嬰兒死亡率高、堅持使用祖先發明的簡單機械。反之,大量運用牛奶這種食物的族群體型比較高大、壽命較長,也更能夠成功養育下一代。他們比不使用牛奶的人們還要積極進取,自然在文學、科學和藝術方面取得大上許多的成就。」
麥科勒姆如此稱讚牛奶,還主張西方在政經方面的成功及身材體型和乳業文化是互有因果關係的,這或許可以駁斥為他個人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然而事實卻是,科學界普遍接受這樣的論點。麥科勒姆以自己一九一八年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發表的演說為基礎,出版了《營養學的最新知識》(The Newer Knowledge of Nutrition)一書,這本書被譽為「牛奶聖經」,出版三年內便賣出一萬四千本,在一九三九年之前就已經達到五刷。《營養學的最新知識》很受歡迎且被廣泛閱讀,要讓世界各地的民眾知道含有大量牛奶的美國/北歐膳食有多崇高。如社會學家E.梅蘭妮.迪普伊(E. Melanie Dupuis)所說的,這本書表揚了一種純淨政治,認為只有一種膳食是完美健康的,其他全部(無論是不同人種、民族或地區的飲食方式)都被貶為令人難以消化的食物,是退化的證據。
麥科勒姆是國際聯盟營養委員會的資深成員,這樣的身分讓他可以透過各種方式發揮影響力。國際聯盟於一九三六年的《最終報告》(Final Report)將「正確的營養」定義為擁有「好」的蛋白質(也就是動物性蛋白質)和保護型食物,可以看出他堅定地認為牛奶是優良膳食的必要成分。牛奶在保護型食物中名列前茅,因為它有「好」的蛋白質、礦物質和維生素(A、B、C和D)。國際聯盟的專家曾進行有關營養恰當性的跨國研究,發現「優越的健康」往往可以歸因於牛奶的攝取,例如:非洲的馬賽人和印度的錫克教教徒就是很好的代表。
這種牛奶在現代健康膳食中的重要性所出現的轉變,同樣也受到中國人的注意。牛奶廣告開始出現在一九一○年代的期刊雜誌上,如《婦女雜誌》和《申報》。到了一九三○年代,牛奶已經很常被描述為是現代的、科學的。一九二七和一九三七年之間,《申報》平均每天都找得到一篇牛奶廣告。人們將牛奶跟地緣政治的富強聯想在一起,把它定位成某種超級營養食物,可以預防疾病、促進生長,這相當吸引那些希望摧毀傳統模式、根據西方模範重建中國的改革家。上海乳業企業家尤懷皋(一八八九到?)等家庭改革家闡述了對現代核心家庭的願景,重新想像這類家庭在創造中國時所扮演的角色。尤懷皋的小家庭概念特別強調家庭的經濟生產力,並將消費物質商品跟陶冶知識及性靈交織在一起。他主張,國家可以透過家庭的理性消費來獲得強化,而在他鼓勵讀者購買的各式各樣商品中,其中一樣便是牛奶,因為他認為牛奶的營養特性可確保中國寶寶獲得適當發育,變得健康強壯。
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在思考中國在世界上的定位時,乳類變成很重要的依據。儘管從早期的歷史時代開始,乳製品及相關製程已不斷傳入,乳類仍然象徵「他者」,令人聯想到中亞和帝國北疆的那些遊牧與半遊牧族群。乳類主要被視為老人(有時則是孩童)的藥物或補藥,而在烹飪著作中提到乳類時,往往會納入烹調過程,進行發酵、凝固或加熱,不會在新鮮狀態下食用。儘管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乳業於上海、哈爾濱、北京等數個中國通商口岸興起,乳類大體上依然位於中國人世界觀的邊陲。然而,歐美國家對乳類的觀念在十九世紀產生轉變,愈來愈多西方人開始喝牛奶,視為不可或缺的食物,於是中國人也漸漸認識到乳類的優良特質、在現代營養這個科學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打造健康強壯身體的作用。乳類變成西方富強的象徵,先前的他者概念並沒有淡化,只是重新被定位。
認為乳類對追求富強的現代中國十分重要的這個概念,催生乳類替代品的論述和物質實驗。中國人幾乎一發現牛奶被當作現代膳食的根基,為現代國家成功的關鍵,便開始探索更適合中國與中國人的其他可能。由於廣為流傳的營養觀念將乳製品視為人類膳食當中必要食物類別,其中又特別認為牛奶是關鍵的保護型食物,可確保個人和國家的健全,一九一○和一九二○年代的中國企業家和科學家便展開實驗,找尋改造豆漿這種常見食品(可以單獨飲用,但是更常用來作為豆腐的必要原料)的方法。在無政府主義者李石曾和兒科醫生祝慎之等人的努力下,豆漿獲得新的詮釋,在論述上被建構成一種健康、更加衛生且蘊含尖端生產技術的牛奶替代品。豆奶跟牛奶顏色相近、營養豐富,在全球都在追求更好的營養健康時,可以成為中國對此做出的本地貢獻。
牛奶愈來愈被認為是標準膳食的核心要素,因此不喝牛奶就變成一個問題,而孕育現代中國的第一步就是要好好解決它。到了一九三○年代,牛奶變得跟兒童的生長和發育有關。發展主義的思維認為,孩童是乘載發展抱負的容器,並且孩童發育成為大人的過程就如同中國自身發展之路的生理展現,因此中國的營養科學家和其他營養社運人士便援引這些思想, 把孩子變成改革的主要接受者。尋找改正中國膳食的實際解方,變得跟拯救中國孩童的健康與活力──從瘦小的身材就能看出他們營養不良──畫上等號。營養和醫療科學家將跟嬰幼兒哺育有關的習慣做法視為需要改革的地方,重新評估哪些食物適合生長發育。
對許多人而言,富含蛋白質、源自本土的黃豆可以被改造來滿足發育中的孩童需求, 為中國的營養困境帶來一絲希望。經濟實惠、容易進行科學改造又比較容易消化的黃豆──尤其是豆奶這個形式,替中國開闢了一條發展道路,也符合現代國家的營養需求。許多推廣豆奶的宣傳用語都會說到,這是一種獨特的中國食物,在中國膳食中發揮的作用就跟牛奶一樣。事實不管是否真的如此,其實沒有那麼重要,重點在於這無形中挑戰了生物文化主義認為全世界都應該頌揚牛奶的假定。
牛奶之道
十九世紀時,科學界對牛奶及其化學性質產生興趣。當時,德國、法國和英國的科學家運用實驗室新研發出來的分析化學技術,開始調查食物、體液和人體組織的化學組成。一八二七年,英國醫生威廉.普洛特(William Prout,一七八五到一八五○年)找出維持人類生命的三個元素單位──「糖、油和蛋白」,稱這些是血肉、骨頭和人類能量的基石。後來的化學家修改了這種食物分類的用語,分別有:卡爾.施密(Carl Schmidt)在一八四四年提出的詞彙「碳水化合物」,用以表示糖類和澱粉類;「脂肪」;以及跟蛋白一樣遇熱會凝固的「蛋白質」。人和牛的乳汁是這三種元素都有包含在內的食物。普洛特稱讚牛奶是天意使然才會存在的普世營養物質。他說:「在所有能證明整個自然秩序都是事先設計好的證據中,牛奶提供了最為確鑿的例證。」他還說:「這是大自然特意設計和製作成食物的唯一營養物,也是所有有機體當中唯一如此製造的物質。因此,牛奶為營養物質應該要是什麼樣子的模範──可以說是一種原型,是所有營養物質的標竿。」
普洛特對牛奶強大力量的讚許傳播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令羅伯特.米勒姆.哈特利(Robert Milham Hartley,一七九六到一八八一年)印象深刻;他是紐約的社會改革家,因受到宗教啟發而參與禁酒運動,同時也是紐約改善窮人狀況協會的第一任會長。哈特利積極改善窮人嬰孩的牛奶供應情況。美國城市的發展導致哺乳情形減少,因此為人母者──特別是富有人家──改以牛奶取代奶娘。但,最容易取得的牛奶是廉價的「餿水牛奶」,也就是被餵食都市釀酒廠副產物的牛所分泌的乳汁。哈特利批評「餿水牛奶」是一種危險的產品,花費很多心力證明攝取這種乳品會帶來的道德與生理危害。他發起行動要廢止紐約餿水牛奶體制,使用藉由鐵路運到城市的「純淨」鄉村牛奶取而代之。這是因為他強烈相信牛奶是一種本質美好、上帝賜予的人類食物,也是「所有營養食物當中最完美之物」。哈特利憎惡的是餿水牛奶體制,不是牛奶本身。他的目標是要「讓市民恢復聖經的鮮乳飲用傳統」。
哈特利讚不絕口地稱讚牛奶是適合每個人的完美食物,儘管很符合他的牛奶改革家身分,卻過分誇大了牛奶在一九一○年代美國膳食中的地位。起初,牛奶改革家動員起來是為了增加特定族群,也就是嬰兒(後來還有身體衰弱者)的牛奶攝取量。雖然牛奶廣泛被當作一種烹飪食材,但是將牛奶當作飲品攝取的情況卻很少見,特別是在美國城市。牛奶被認為是適合每個人的優良食物,得要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至少在美國和英國是如此)。會有這樣的轉變,有一部分是因為維生素和其他微量營養素的發現,大大改變了西方科學家對膳食與營養的理解。在試圖理解維生素功用的過程中,麥科勒姆和霍普金斯等科學家發現,把牛奶加在不恰當的純化物質中,似乎可以為實驗動物帶來奇蹟般的生長效果。美國農夫將牛奶補充品加進牲畜的飼料中,也曾經發現類似的效果。普洛特先前展現了牛奶的獨特性(同時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這三大膳食元素),這下被證實是對的,只不過理由不太一樣,這次是因為發現牛奶裡含有維生素。麥科勒姆說:「牛奶的組成非常特別,因此無論是搭配動物或植物來源的食物,都能修正其膳食缺陷。」
牛奶的營養地位獲得提升,連兒科這個新興領域的美國從業人員都很看好,主張牛奶可以預防兒童營養缺乏症。嬰兒照護的醫療化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前便已經展開,當時愈來愈多美國醫生投身尋找嬰兒死亡率根本原因的行列。針對高嬰兒死亡率,許多醫學作家和研究型醫生都認為原因出在不適當的哺育方式和食物,儘管母乳普遍被認為是最好的嬰兒食品,大部分的醫生卻認為「理想的母乳」並不存在,因此鼓勵女性使用替代品。牛奶被捧為最好也最容易取得的替代品。一名卓越的美國兒科醫生曾說:「若要避免兩歲以下的孩童生病死亡,並確保即將來臨的世代能夠存活下來、維持國家水準,除了使用母乳哺乳,牛奶是絕對必要的─這件事無庸置疑。」
牛奶被譽為是大自然最完美的食物,甚至還被認為是現代文明能夠崛起最重要的營養因子。麥科勒姆在全脂牛奶的脂肪中找到促進動物與人類生長的關鍵物質(維生素A), 堅稱牛奶及其相關製品是必要、甚至最好的保護型食物,根據某地的膳食當中有沒有這種食物,便能預測當地的社會、文化與科學成就。麥科勒姆在一九一八年寫到,世界上分兩種人,一種是膳食中包含牛奶的人,另一種就是膳食中不含牛奶的人。一方面,「由中國人、日本人和大部分熱帶地區的人為代表」的那些人,「幾乎完全以植物的葉子當作唯一的保護型食物。他們也吃蛋,這補救了他們的膳食。」另一方面,北美和歐洲的族群「同樣也會運用植物的葉子,但程度較低。此外,他們的食物來源有很大一部分來自牛奶及其製品。」這些膳食方面的差異造成截然不同的社會文化結果:「以植物葉子作為唯一保護型食物的人們,其特徵包括體型矮小、壽命相對較短、嬰兒死亡率高、堅持使用祖先發明的簡單機械。反之,大量運用牛奶這種食物的族群體型比較高大、壽命較長,也更能夠成功養育下一代。他們比不使用牛奶的人們還要積極進取,自然在文學、科學和藝術方面取得大上許多的成就。」
麥科勒姆如此稱讚牛奶,還主張西方在政經方面的成功及身材體型和乳業文化是互有因果關係的,這或許可以駁斥為他個人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然而事實卻是,科學界普遍接受這樣的論點。麥科勒姆以自己一九一八年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發表的演說為基礎,出版了《營養學的最新知識》(The Newer Knowledge of Nutrition)一書,這本書被譽為「牛奶聖經」,出版三年內便賣出一萬四千本,在一九三九年之前就已經達到五刷。《營養學的最新知識》很受歡迎且被廣泛閱讀,要讓世界各地的民眾知道含有大量牛奶的美國/北歐膳食有多崇高。如社會學家E.梅蘭妮.迪普伊(E. Melanie Dupuis)所說的,這本書表揚了一種純淨政治,認為只有一種膳食是完美健康的,其他全部(無論是不同人種、民族或地區的飲食方式)都被貶為令人難以消化的食物,是退化的證據。
麥科勒姆是國際聯盟營養委員會的資深成員,這樣的身分讓他可以透過各種方式發揮影響力。國際聯盟於一九三六年的《最終報告》(Final Report)將「正確的營養」定義為擁有「好」的蛋白質(也就是動物性蛋白質)和保護型食物,可以看出他堅定地認為牛奶是優良膳食的必要成分。牛奶在保護型食物中名列前茅,因為它有「好」的蛋白質、礦物質和維生素(A、B、C和D)。國際聯盟的專家曾進行有關營養恰當性的跨國研究,發現「優越的健康」往往可以歸因於牛奶的攝取,例如:非洲的馬賽人和印度的錫克教教徒就是很好的代表。
這種牛奶在現代健康膳食中的重要性所出現的轉變,同樣也受到中國人的注意。牛奶廣告開始出現在一九一○年代的期刊雜誌上,如《婦女雜誌》和《申報》。到了一九三○年代,牛奶已經很常被描述為是現代的、科學的。一九二七和一九三七年之間,《申報》平均每天都找得到一篇牛奶廣告。人們將牛奶跟地緣政治的富強聯想在一起,把它定位成某種超級營養食物,可以預防疾病、促進生長,這相當吸引那些希望摧毀傳統模式、根據西方模範重建中國的改革家。上海乳業企業家尤懷皋(一八八九到?)等家庭改革家闡述了對現代核心家庭的願景,重新想像這類家庭在創造中國時所扮演的角色。尤懷皋的小家庭概念特別強調家庭的經濟生產力,並將消費物質商品跟陶冶知識及性靈交織在一起。他主張,國家可以透過家庭的理性消費來獲得強化,而在他鼓勵讀者購買的各式各樣商品中,其中一樣便是牛奶,因為他認為牛奶的營養特性可確保中國寶寶獲得適當發育,變得健康強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