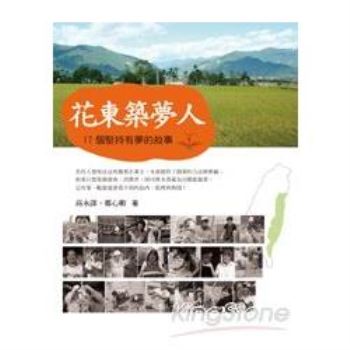點蜆成金
立川休閒漁場
蔡有進、蔡志峰
在電影《阿甘正傳》中,每當別人懷疑他是否是個笨蛋、還是瘋子時,阿甘總是說:「媽媽說過笨人才做笨事。」儘管曾歷經一段捕不到蝦的窘日子,但傻人有傻福的阿甘,始終相信:「不放棄的精神,終究會帶來成功。」
同樣也面對旁人質疑的眼光,立川休閒漁場總經理蔡志峰從小跟著父親蔡有進,每天泡在蜆仔的水產養殖世界中。當面臨家中養殖場搖搖欲墜、負債累累時,蔡志峰以異於常人的堅持,不僅為養蜆仔這個古老行業找出一條新生路,更帶領立川從絕境中翻身,成為全台規模最大的黃金蜆專業養殖場,甚至一手打造出蜆加工製品的藍海商機。
自行摸索蜆精的煉製
事實上,養蜆業曾經風光一時,一九九○年代啤酒屋盛行,炒蜆仔是最好的下酒菜。不過,受到飲食習慣改變,啤酒屋式微,立川的養蜆場一度搖搖欲墜,促使蔡志峰決定為養蜆仔這個古老行業找條生路,以民間喝蜆仔湯補肝的食補習慣,結合雞精製作技術,嘗試生產蜆精。
一瓶僅六十公克的蜆精,需要用上二百顆生蜆,經過浸泡、吐沙、洗淨、蒸煮、急冷、濃縮與去腥等多道加工製程才完成。然而,當時國內卻沒有一家食品加工廠有煉製蜆精的經驗,一切只能靠蔡志峰自行摸索。
蜆湯原汁的營養成分極高,常溫下卻容易引發微生物及細菌繁殖,所以熬出的高溫蜆湯必須在三分鐘內急速冷卻到攝氏六度以下。剛開始,蔡志峰為解決溫度的問題,竟很天真地買來一大桶冰塊,想用隔水降溫的方式,結果等了半個小時,溫度才降到十度左右,上百公斤肥美的生蜆熬煮半天的蜆湯,頓時變成惹來滿室蒼蠅的餿水。
於是,蔡志峰拋開土法煉鋼的方法,投入龐大資金添購設備,並建立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自動化生產製程,但提升設備標準後,卻只能解決一半的問題。
原因是蜆一年四季的肥滿度(指蜆肉占整顆蜆的重量比例)不同,而且養殖戶技術參差不齊,加上收購來的生蜆送到工廠等待加工的時間不一,導致熬煮出來的蜆湯,每一批鮮度、甜度及濁度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若是夏天盛產期,肥美的生蜆煮出來的原汁極鮮甜,但冬天的蜆因生長較慢,肥滿度較差,就必須拉長蜆湯原汁的提煉時間。
一開始,蔡志峰缺乏經驗,曾經發生客戶喝起來覺得口感和上一批貨不同,整卡車上百萬原料遭退貨的慘況。為了維持口感和品質的一致性,蔡志峰從七個小時的熬煮過程中,不斷反覆實驗,找出對應到不同肥滿度生蜆的煉製溫度和熬煮時間。
終於,產品好不容易通過品管標準,但卻是蔡志峰另一個惡夢的開始。
天天跑三點半的夢魘
由於當時消費者只喝過雞精,根本沒聽過瓶裝蜆精,立川又缺乏大品牌背書,致使市場對蜆精功效沒信心,產品乏人問津。蔡志峰常搭夜車從花蓮到台北,親自到通路鋪貨,可是第一批貨一萬瓶蜆精,花了半年時間還銷不完,滿屋子的庫存,讓蔡家兄弟逆中求勝的信心面臨嚴苛的考驗。
蔡志峰回憶,當時家族已因養殖事業擴充過速而負債累累,投入大筆資金及人力,費盡辛勞,研發出全世界第一瓶蜆精,沒想到市場反應卻不佳。整整十年、四千多個日子中,父親蔡有進天天都得跑三點半,與銀行往來的退換票紀錄累計高達八千多筆,欠員工的薪水更是以年為單位。當時,蔡氏父子最害怕要過農曆新年,別人家歡喜慶團圓,他們卻是怕面對上門的債主,以及一同勒緊褲帶的員工們。
眼見財務缺口愈來愈大,在毫無退路下,反倒激起蔡有進、蔡志峰父子奮力一搏的勇氣。每天一早,蔡志峰穿起漁褲裝,巡視養殖池水位變化,他不斷對自己信心喊話:「窮則變,變不一定通,但不變一定不通。做蜆精,一定有出路,只是還沒找到路標而已。」
正值蔡家人為了資金周轉,猶如熱鍋上的螞蟻時,已遭欠薪兩年的老員工卻不離不棄,四處幫忙籌錢,甚至蔡有進的朋友還拿出退休金,大力相挺立川度過難關。對於員工及朋友的信任,蔡有進感念在心,也告誡兒子們:「別人願意把錢交給我們,我們絕對不能辜負人家!」
歷經十年債台高築的艱辛日子,如今立川年營收早已超過上億元,並擁有一百五十位員工,擔負起一百五十個家庭的生計。這就是蔡氏父子的能耐,不僅能跳脫養殖戶的生產者思維,更靠著成功突破養殖技術,摸索出一條蜆加工製品市場活路的本領。
打造黃金蜆文化園區
台糖蜆精一炮而紅後,蔡志峰向父親提出休閒體驗的計畫,希望將原本養殖的五分魚塭地回填,開創讓遊客親身體驗「摸蜆仔兼洗褲」的樂趣,左鄰右舍都認為蔡志峰瘋了,就連父親都質疑:「誰會來這裡摸蜆仔啊?」
直到風靡而來的遊客人數愈來愈多,立川休閒漁場內處處可見大人與孩子一同體驗古早溪畔摸蜆仔的趣味,或三五好友點盤炒黃金蜆仔,啜飲啤酒的沁涼滋味,這項轉型計畫才受到父親的肯定。
不過,大量的廢棄蜆殼,卻成了蔡志峰另一頭痛問題。在石資中心輔導下,立川向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辦公室申請「資源化蜆殼作添加物之研發先期研究計畫」,結果發現,經?燒後的蜆殼粉末,具有抗菌效果,可做成蔬果清潔劑、農業殺菌劑、抗菌紡織品等。
懷著夢想的蔡志峰,一直希望能成立黃金蜆形象館,卻苦無經費,石資中心獲悉後,再度協助立川向經濟部技術處申請「黃金蜆文化創意產業加值開發計畫」,協助打造出具3D虛擬實境效果的黃金蜆文創園區。
回顧過去一路走來的起起伏伏,蔡家父子從危機中淬煉出蜆產業的千萬倍商機,其境遇如同蜆生存受到威脅時,生命力就愈旺盛,也正好印證了危機與機會並存的「蜆」學精神!
(節錄)
咖啡、黑豆、麴菌的醬油三結義
阿貴天然手工坊
陳阿貴、盧美英
台灣生機飲食愛好者、信徒日眾,無論其動機是出自於對病痛、死亡的恐懼,或基於愛護地球的堅持,或將其視為潮流、時尚,抑或讓身心更為和諧的生命態度、生活方式;他們對食材總是千挑百選,深怕有一絲絲農藥殘留,面對標榜全程有機種植的蔬果時,即使價格再高昂,從腰包掏錢時也絕不猶豫。
然而,大多數生機飲食愛好者、信徒卻常百密一疏,將所有心力放在檢視有機食材是否名實相符,忽略查核餐桌、鍋碗中的配角——醬油、醬料、醋,到底算是可食的調味料,還是化學工業產品。設址於花蓮縣花蓮市的阿貴天然手工坊,便著眼於天然調味料的潛在需求,遵循傳統手工釀製流程,並在原料中加入自產的咖啡調味、調色,研發出愈陳愈香的咖啡醬油。
遵循古法 滴滴皆辛苦
聯手創立阿貴天然手工坊的陳阿貴、盧美英,為一對情同母女的婆媳。兩人昔日在做菜時,也以一般家庭慣用的化學醬油調味;但約三年前,在南投縣醬油廠任職多年的陳阿貴弟弟來訪,卻堅決不願食用以化學醬油烹飪的食物,理由是其含有人工甘味劑、色澤改良劑與防腐劑,將造成身體沉重負擔。
雖早已知化學醬油加進眾多化學添加物,但身為醬油專家的弟弟嚴詞拒吃,才讓陳阿貴猶如醍醐灌頂,決心以行動捍衛食的安全,拉著原是家庭主婦的盧美英,一起投身研發、釀製天然醬油。在弟弟無私的技術指導下,陳阿貴從頭學習傳統手工釀製天然醬油流程的每個步驟,按部就班、絕不速成,最後更堅持將成熟醬醪露天發酵半年,堪稱滴滴皆辛苦。
一瓶化學醬油售價不過數十元,但為了釀製天然醬油,單是購買原料、相關設備,就花了陳阿貴超過七十萬元的養老金;雖有盧美英的鼎力協助,但仍遭遇數不清的失敗、挫折,歷經兩年的勤奮鑽研,終於從生手晉升為達人,並有能力穩定量產高品質的天然醬油。
然而,雖然陳阿貴、盧美英所釀製的天然醬油,可口甘甜、氣味清香,但由於未添增色澤改良劑,顏色較一般醬油淡了許多;考量大多數消費者根深柢固的習性,陳阿貴嘗試在釀製過程中加入咖啡,讓色澤更接近一般醬油,研發出別具風味的咖啡醬油。在咖啡醬油廣受親友好評後,激勵陳阿貴成立阿貴天然手工坊,讓更多消費者可享其心血的結晶,並著手開發天然醋品與其他產品。
婆媳同心 其香勝於蘭
原本,陳阿貴只將釀製天然醬油當成退休生活的娛樂兼運動,兒子自是樂觀其成。沒想到,她愈釀製愈有興趣、心得,投入的時間、精力、資源愈來愈多,連媳婦也成為助手,令兒子不禁擔憂,並屢次溫言勸阻,希望她安享清福、遊山玩水,無須如此操勞,更認為縱使追求吃得健康,也無須如此大費周章。
陳阿貴笑著說,兒子的擔憂與疑慮,在見證天然醬油的優點後,隨即轉為認可與支持;因為天然醬油是烹煮、滷漬食材的最佳調味料,愈煮、愈滷便愈香甜,食材也更加美味、爽口。而在獲得家人肯定後,陳阿貴開始將成果分享給親友,釀製技術也快速精進,產能也逐漸擴大,遂興起成立工作坊的念想!
「剛開始學習釀製天然醬油時,總得失敗約三次,才能成功一次。」陳阿貴靦腆地說。在熟稔釀製流程的每一個步驟之後,產品良率已大幅提升,而在苦心研發出天然咖啡醬油後,更確信其深備市場潛力,值得推廣給廣大消費者。於是,陳阿貴徵得盧美英首肯,決定以自己的名字為商號,創立了阿貴天然手工坊。
《周易》有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嗅如蘭。」而陳阿貴、盧美英同心所釀製的天然咖啡醬油,有著濃郁「婆婆、媽媽的味道」,其香也勝於蘭,即使單價較化學醬油來得高,開封後還得放入冰箱內冷藏,但在消費者聞化學添加物色變的今日,仍有機會再度成為調味料的主流。
糙米釀醋 傳統兼創新
而在咖啡醬油普獲好評後,陳阿貴、盧美英決定挑戰釀製天然醋品;難度雖更高,但有了釀製天然醬油的經驗為基礎,過程反倒較為順利;目前,阿貴天然手工坊已推出咖啡糙米醋、諾麗果糙米醋兩種醋品,既可當料理醋,且開封後無須冷藏。特別的是,為了保存米的營養,陳阿貴選用糙米為釀醋的原料,日後還將嘗試添加不同的當季水果,開發更多新口味的醋品。
而在工研院的輔導下,陳阿貴、盧美英習得:如何以最低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在醬油裝瓶、隔水加熱時,如何才能徹底殺菌,並如何進行商品整體設計、規劃,方能貼近當今調味料商品的主流。終於,阿貴天然手工坊各項產品,都已通過國際公信力、標準最嚴格的SGS檢驗,相信也能獲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
展望未來,陳阿貴透露,當阿貴天然手工坊在市場站穩腳步後,她希望進一步運用花蓮縣當地的特色食材,研發健康且具高經濟價值的加工品,包括精油,與蜂蜜、梅子相關產品,創造洄瀾農業的新商機。
(節錄)
魯凱黑金魅力
金峰鄉咖啡產銷班第三班
羅忠輝
咖啡,西方人稱之為「上帝的禮物」,而且所含的咖啡因能刺激腦部的中樞神經系統,幫助振奮精神,增加幸福感。
有關發現咖啡豆的傳說,各家說法不一。其中,較為人知的是,相傳西元六世紀,衣索比亞牧羊人發覺他飼養的羊群無意間吃了一種紅色果實後,充滿活力,甚至晚上常亢奮到睡不著覺。他將果實分送給修道院僧侶們品嚐,結果大夥兒試喝了這種果實煮後的汁液,都感到精神奕奕,晚上做禮拜也不再打瞌睡。
十三世紀,衣索比亞軍隊入侵葉門,將咖啡引進阿拉伯世界,成為當時伊斯蘭教徒生活中很重要的社交飲品。十六、十七世紀,咖啡透過威尼斯商人與荷蘭人交易而傳入歐洲,這種香濃甘醇的黑色飲料,很快就風靡了歐洲上流貴族社會,身價也節節上漲,甚至被稱為「黑色金子」。
爾後,隨著歐洲大航海時代來臨,咖啡逐漸流傳到世界各地。「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咖啡館;如果不是在咖啡館,就是在往咖啡館的路上。」這句名言道盡了許多咖啡愛好者對生活氛圍的堅持。
如今,「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歷坵咖啡園;如果不是在歷坵咖啡園,就是在往歷坵咖啡園的路上。」這句話最能形容台東縣金峰鄉咖啡產銷班第三班班長羅忠輝每天的生活,以及對歷坵村未來的期許。
終於,在工研院鼎力相助下,魯凱族羅忠輝和他的班員們,正一步一腳印,努力用夢想和行動,訴說著這個隱身在雲霧縹緲間的美麗原鄉故事。
退伍返鄉學習種咖啡
高中畢業後,苦於部落裡少有工作機會的羅忠輝,選擇當職業軍人,駐紮在高雄。離鄉背井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羅忠輝,因有感於家族耆老心中總是掛念著白白浪費一塊寶地,十分可惜,二○一○年,他毅然決定從職業軍人的身分退休,返回歷坵村,從頭開始學習種植咖啡、選豆、烘焙,到煮咖啡。
「老人家一直叮嚀我們,不要浪費了這塊土地啊!為了不辜負老人家的心意,又想要同時保護上帝賜予的這塊土地,才決定要種植咖啡。」羅忠輝靦腆地笑說,他希望在發展咖啡事業之餘,也能照顧年邁的父母,更期待未來的下一代可以回家延續家業,「否則離開自己的家鄉那麼久的時間,突然要返鄉務農、下田,其實也是很辛苦的。」
事實上,羅忠輝的祖父母、父親,原本是屏東縣霧台鄉阿里村的西魯凱族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間,隨著族人遷居到現今的歷坵部落,當時只有七戶人家。落地生根後,族人胼手胝足,努力打拚,終於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
然而,萬事起頭難。從咖啡門外漢到略懂咖啡,甚至成為咖啡達人,羅忠輝可說是吃盡不少苦頭、歷經許多困難。起先,他只聽聞有族人曾在歷坵村種植咖啡,卻不知從何著手,在偶然機遇下,剛好看到由工研院、東部產業計畫服務中心共同策劃的《八十萬公里的熱情——釣竿科學家與花東農民的故事》中,專文介紹台東縣卑南鄉第五咖啡產銷班班長阮勇光生產「果子狸咖啡」的傳奇。
受到該則故事啟發後,羅忠輝跑去參加台東縣咖啡產業發展協會舉辦的相關課程,到處找人學習,並探詢、汲取田間管理、咖啡豆採收、日曬、脫殼、發酵、挑豆、烘焙及泡煮等技術,再將自己所學無償傳授給有興趣的族人。
成立產銷班展現領導力
為了推展歷坵咖啡,羅忠輝體會到團隊合作力量勝過單憑一己之力。二○一○年,他開始籌備、申請成立產銷班;二○一一年四月十一日,金峰鄉咖啡產銷班第三班正式成立,目前全班種植面積有十二公頃,約一萬株咖啡樹。
由於咖啡和洛神花皆屬特用作物,而金峰鄉已有洛神花產銷班第一班、第二班,所以雖取名為咖啡產銷班第三班,事實上卻是金峰鄉目前唯一的咖啡產銷班。成立產銷班的好處,在於可以申請辦公室、生產設備,爭取更多資源,並達到整合咖啡農友的目的。
目前產銷班班員有十人,現年四十三歲的羅忠輝,年紀最小,卻被推舉為班長。在軍中服役長達二十年的羅忠輝,很快就展現領導統御能力,要求班員開會遲到十分鐘要罰錢、會議中不能喝酒。
「他的年紀最小,但大家都很推崇他的領導能力,每次來開會,都會開玩笑說:『班長,今天不要太兇喔!』」羅忠輝的大姊羅英惠笑說。為了支持弟弟的夢想,羅英惠不僅加入產銷班,更將她的英惠原藝工作坊當作臨時開會場所。
過去一年來,羅忠輝特別安排專家到歷坵村開設咖啡種植、管理、烘焙、沖泡等課程。第一天上課時,每個班員竟然都穿雨靴、戴斗笠,一副準備下田的模樣,令羅忠輝又好氣又好笑,直呼:「我們班員真的很可愛!」
有趣的是,產銷班班員雖然種植咖啡,平時卻根本不喝咖啡。為了增加說服力,羅忠輝要求班員試喝咖啡,結果狀況百出,有人皺起眉頭:「咦,這是什麼鬼味道?」有人則是喝了一小口後,馬上問:「班長,檳榔咧?」
羅忠輝嘗試給了三杯不同品種的咖啡,要求他們再試喝,有人捏著鼻子,在三十秒內一口氣喝光,有人還一臉無辜地說:「班長,這三杯咖啡喝起來味道都一樣耶。」
經過多次努力,這群咖啡農終於學會親手泡煮咖啡、品嚐各種味道的咖啡。當看著自己親手栽種的咖啡豆,在熱騰騰的蒸氣中,化成黑色的液體,並伴隨著香氣汨汨流出時,每個人的臉上都有說不出的驕傲與成就感。
(節錄)
立川休閒漁場
蔡有進、蔡志峰
在電影《阿甘正傳》中,每當別人懷疑他是否是個笨蛋、還是瘋子時,阿甘總是說:「媽媽說過笨人才做笨事。」儘管曾歷經一段捕不到蝦的窘日子,但傻人有傻福的阿甘,始終相信:「不放棄的精神,終究會帶來成功。」
同樣也面對旁人質疑的眼光,立川休閒漁場總經理蔡志峰從小跟著父親蔡有進,每天泡在蜆仔的水產養殖世界中。當面臨家中養殖場搖搖欲墜、負債累累時,蔡志峰以異於常人的堅持,不僅為養蜆仔這個古老行業找出一條新生路,更帶領立川從絕境中翻身,成為全台規模最大的黃金蜆專業養殖場,甚至一手打造出蜆加工製品的藍海商機。
自行摸索蜆精的煉製
事實上,養蜆業曾經風光一時,一九九○年代啤酒屋盛行,炒蜆仔是最好的下酒菜。不過,受到飲食習慣改變,啤酒屋式微,立川的養蜆場一度搖搖欲墜,促使蔡志峰決定為養蜆仔這個古老行業找條生路,以民間喝蜆仔湯補肝的食補習慣,結合雞精製作技術,嘗試生產蜆精。
一瓶僅六十公克的蜆精,需要用上二百顆生蜆,經過浸泡、吐沙、洗淨、蒸煮、急冷、濃縮與去腥等多道加工製程才完成。然而,當時國內卻沒有一家食品加工廠有煉製蜆精的經驗,一切只能靠蔡志峰自行摸索。
蜆湯原汁的營養成分極高,常溫下卻容易引發微生物及細菌繁殖,所以熬出的高溫蜆湯必須在三分鐘內急速冷卻到攝氏六度以下。剛開始,蔡志峰為解決溫度的問題,竟很天真地買來一大桶冰塊,想用隔水降溫的方式,結果等了半個小時,溫度才降到十度左右,上百公斤肥美的生蜆熬煮半天的蜆湯,頓時變成惹來滿室蒼蠅的餿水。
於是,蔡志峰拋開土法煉鋼的方法,投入龐大資金添購設備,並建立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自動化生產製程,但提升設備標準後,卻只能解決一半的問題。
原因是蜆一年四季的肥滿度(指蜆肉占整顆蜆的重量比例)不同,而且養殖戶技術參差不齊,加上收購來的生蜆送到工廠等待加工的時間不一,導致熬煮出來的蜆湯,每一批鮮度、甜度及濁度都不盡相同。舉例來說,若是夏天盛產期,肥美的生蜆煮出來的原汁極鮮甜,但冬天的蜆因生長較慢,肥滿度較差,就必須拉長蜆湯原汁的提煉時間。
一開始,蔡志峰缺乏經驗,曾經發生客戶喝起來覺得口感和上一批貨不同,整卡車上百萬原料遭退貨的慘況。為了維持口感和品質的一致性,蔡志峰從七個小時的熬煮過程中,不斷反覆實驗,找出對應到不同肥滿度生蜆的煉製溫度和熬煮時間。
終於,產品好不容易通過品管標準,但卻是蔡志峰另一個惡夢的開始。
天天跑三點半的夢魘
由於當時消費者只喝過雞精,根本沒聽過瓶裝蜆精,立川又缺乏大品牌背書,致使市場對蜆精功效沒信心,產品乏人問津。蔡志峰常搭夜車從花蓮到台北,親自到通路鋪貨,可是第一批貨一萬瓶蜆精,花了半年時間還銷不完,滿屋子的庫存,讓蔡家兄弟逆中求勝的信心面臨嚴苛的考驗。
蔡志峰回憶,當時家族已因養殖事業擴充過速而負債累累,投入大筆資金及人力,費盡辛勞,研發出全世界第一瓶蜆精,沒想到市場反應卻不佳。整整十年、四千多個日子中,父親蔡有進天天都得跑三點半,與銀行往來的退換票紀錄累計高達八千多筆,欠員工的薪水更是以年為單位。當時,蔡氏父子最害怕要過農曆新年,別人家歡喜慶團圓,他們卻是怕面對上門的債主,以及一同勒緊褲帶的員工們。
眼見財務缺口愈來愈大,在毫無退路下,反倒激起蔡有進、蔡志峰父子奮力一搏的勇氣。每天一早,蔡志峰穿起漁褲裝,巡視養殖池水位變化,他不斷對自己信心喊話:「窮則變,變不一定通,但不變一定不通。做蜆精,一定有出路,只是還沒找到路標而已。」
正值蔡家人為了資金周轉,猶如熱鍋上的螞蟻時,已遭欠薪兩年的老員工卻不離不棄,四處幫忙籌錢,甚至蔡有進的朋友還拿出退休金,大力相挺立川度過難關。對於員工及朋友的信任,蔡有進感念在心,也告誡兒子們:「別人願意把錢交給我們,我們絕對不能辜負人家!」
歷經十年債台高築的艱辛日子,如今立川年營收早已超過上億元,並擁有一百五十位員工,擔負起一百五十個家庭的生計。這就是蔡氏父子的能耐,不僅能跳脫養殖戶的生產者思維,更靠著成功突破養殖技術,摸索出一條蜆加工製品市場活路的本領。
打造黃金蜆文化園區
台糖蜆精一炮而紅後,蔡志峰向父親提出休閒體驗的計畫,希望將原本養殖的五分魚塭地回填,開創讓遊客親身體驗「摸蜆仔兼洗褲」的樂趣,左鄰右舍都認為蔡志峰瘋了,就連父親都質疑:「誰會來這裡摸蜆仔啊?」
直到風靡而來的遊客人數愈來愈多,立川休閒漁場內處處可見大人與孩子一同體驗古早溪畔摸蜆仔的趣味,或三五好友點盤炒黃金蜆仔,啜飲啤酒的沁涼滋味,這項轉型計畫才受到父親的肯定。
不過,大量的廢棄蜆殼,卻成了蔡志峰另一頭痛問題。在石資中心輔導下,立川向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辦公室申請「資源化蜆殼作添加物之研發先期研究計畫」,結果發現,經?燒後的蜆殼粉末,具有抗菌效果,可做成蔬果清潔劑、農業殺菌劑、抗菌紡織品等。
懷著夢想的蔡志峰,一直希望能成立黃金蜆形象館,卻苦無經費,石資中心獲悉後,再度協助立川向經濟部技術處申請「黃金蜆文化創意產業加值開發計畫」,協助打造出具3D虛擬實境效果的黃金蜆文創園區。
回顧過去一路走來的起起伏伏,蔡家父子從危機中淬煉出蜆產業的千萬倍商機,其境遇如同蜆生存受到威脅時,生命力就愈旺盛,也正好印證了危機與機會並存的「蜆」學精神!
(節錄)
咖啡、黑豆、麴菌的醬油三結義
阿貴天然手工坊
陳阿貴、盧美英
台灣生機飲食愛好者、信徒日眾,無論其動機是出自於對病痛、死亡的恐懼,或基於愛護地球的堅持,或將其視為潮流、時尚,抑或讓身心更為和諧的生命態度、生活方式;他們對食材總是千挑百選,深怕有一絲絲農藥殘留,面對標榜全程有機種植的蔬果時,即使價格再高昂,從腰包掏錢時也絕不猶豫。
然而,大多數生機飲食愛好者、信徒卻常百密一疏,將所有心力放在檢視有機食材是否名實相符,忽略查核餐桌、鍋碗中的配角——醬油、醬料、醋,到底算是可食的調味料,還是化學工業產品。設址於花蓮縣花蓮市的阿貴天然手工坊,便著眼於天然調味料的潛在需求,遵循傳統手工釀製流程,並在原料中加入自產的咖啡調味、調色,研發出愈陳愈香的咖啡醬油。
遵循古法 滴滴皆辛苦
聯手創立阿貴天然手工坊的陳阿貴、盧美英,為一對情同母女的婆媳。兩人昔日在做菜時,也以一般家庭慣用的化學醬油調味;但約三年前,在南投縣醬油廠任職多年的陳阿貴弟弟來訪,卻堅決不願食用以化學醬油烹飪的食物,理由是其含有人工甘味劑、色澤改良劑與防腐劑,將造成身體沉重負擔。
雖早已知化學醬油加進眾多化學添加物,但身為醬油專家的弟弟嚴詞拒吃,才讓陳阿貴猶如醍醐灌頂,決心以行動捍衛食的安全,拉著原是家庭主婦的盧美英,一起投身研發、釀製天然醬油。在弟弟無私的技術指導下,陳阿貴從頭學習傳統手工釀製天然醬油流程的每個步驟,按部就班、絕不速成,最後更堅持將成熟醬醪露天發酵半年,堪稱滴滴皆辛苦。
一瓶化學醬油售價不過數十元,但為了釀製天然醬油,單是購買原料、相關設備,就花了陳阿貴超過七十萬元的養老金;雖有盧美英的鼎力協助,但仍遭遇數不清的失敗、挫折,歷經兩年的勤奮鑽研,終於從生手晉升為達人,並有能力穩定量產高品質的天然醬油。
然而,雖然陳阿貴、盧美英所釀製的天然醬油,可口甘甜、氣味清香,但由於未添增色澤改良劑,顏色較一般醬油淡了許多;考量大多數消費者根深柢固的習性,陳阿貴嘗試在釀製過程中加入咖啡,讓色澤更接近一般醬油,研發出別具風味的咖啡醬油。在咖啡醬油廣受親友好評後,激勵陳阿貴成立阿貴天然手工坊,讓更多消費者可享其心血的結晶,並著手開發天然醋品與其他產品。
婆媳同心 其香勝於蘭
原本,陳阿貴只將釀製天然醬油當成退休生活的娛樂兼運動,兒子自是樂觀其成。沒想到,她愈釀製愈有興趣、心得,投入的時間、精力、資源愈來愈多,連媳婦也成為助手,令兒子不禁擔憂,並屢次溫言勸阻,希望她安享清福、遊山玩水,無須如此操勞,更認為縱使追求吃得健康,也無須如此大費周章。
陳阿貴笑著說,兒子的擔憂與疑慮,在見證天然醬油的優點後,隨即轉為認可與支持;因為天然醬油是烹煮、滷漬食材的最佳調味料,愈煮、愈滷便愈香甜,食材也更加美味、爽口。而在獲得家人肯定後,陳阿貴開始將成果分享給親友,釀製技術也快速精進,產能也逐漸擴大,遂興起成立工作坊的念想!
「剛開始學習釀製天然醬油時,總得失敗約三次,才能成功一次。」陳阿貴靦腆地說。在熟稔釀製流程的每一個步驟之後,產品良率已大幅提升,而在苦心研發出天然咖啡醬油後,更確信其深備市場潛力,值得推廣給廣大消費者。於是,陳阿貴徵得盧美英首肯,決定以自己的名字為商號,創立了阿貴天然手工坊。
《周易》有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嗅如蘭。」而陳阿貴、盧美英同心所釀製的天然咖啡醬油,有著濃郁「婆婆、媽媽的味道」,其香也勝於蘭,即使單價較化學醬油來得高,開封後還得放入冰箱內冷藏,但在消費者聞化學添加物色變的今日,仍有機會再度成為調味料的主流。
糙米釀醋 傳統兼創新
而在咖啡醬油普獲好評後,陳阿貴、盧美英決定挑戰釀製天然醋品;難度雖更高,但有了釀製天然醬油的經驗為基礎,過程反倒較為順利;目前,阿貴天然手工坊已推出咖啡糙米醋、諾麗果糙米醋兩種醋品,既可當料理醋,且開封後無須冷藏。特別的是,為了保存米的營養,陳阿貴選用糙米為釀醋的原料,日後還將嘗試添加不同的當季水果,開發更多新口味的醋品。
而在工研院的輔導下,陳阿貴、盧美英習得:如何以最低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在醬油裝瓶、隔水加熱時,如何才能徹底殺菌,並如何進行商品整體設計、規劃,方能貼近當今調味料商品的主流。終於,阿貴天然手工坊各項產品,都已通過國際公信力、標準最嚴格的SGS檢驗,相信也能獲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
展望未來,陳阿貴透露,當阿貴天然手工坊在市場站穩腳步後,她希望進一步運用花蓮縣當地的特色食材,研發健康且具高經濟價值的加工品,包括精油,與蜂蜜、梅子相關產品,創造洄瀾農業的新商機。
(節錄)
魯凱黑金魅力
金峰鄉咖啡產銷班第三班
羅忠輝
咖啡,西方人稱之為「上帝的禮物」,而且所含的咖啡因能刺激腦部的中樞神經系統,幫助振奮精神,增加幸福感。
有關發現咖啡豆的傳說,各家說法不一。其中,較為人知的是,相傳西元六世紀,衣索比亞牧羊人發覺他飼養的羊群無意間吃了一種紅色果實後,充滿活力,甚至晚上常亢奮到睡不著覺。他將果實分送給修道院僧侶們品嚐,結果大夥兒試喝了這種果實煮後的汁液,都感到精神奕奕,晚上做禮拜也不再打瞌睡。
十三世紀,衣索比亞軍隊入侵葉門,將咖啡引進阿拉伯世界,成為當時伊斯蘭教徒生活中很重要的社交飲品。十六、十七世紀,咖啡透過威尼斯商人與荷蘭人交易而傳入歐洲,這種香濃甘醇的黑色飲料,很快就風靡了歐洲上流貴族社會,身價也節節上漲,甚至被稱為「黑色金子」。
爾後,隨著歐洲大航海時代來臨,咖啡逐漸流傳到世界各地。「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咖啡館;如果不是在咖啡館,就是在往咖啡館的路上。」這句名言道盡了許多咖啡愛好者對生活氛圍的堅持。
如今,「如果我不在家,就是在歷坵咖啡園;如果不是在歷坵咖啡園,就是在往歷坵咖啡園的路上。」這句話最能形容台東縣金峰鄉咖啡產銷班第三班班長羅忠輝每天的生活,以及對歷坵村未來的期許。
終於,在工研院鼎力相助下,魯凱族羅忠輝和他的班員們,正一步一腳印,努力用夢想和行動,訴說著這個隱身在雲霧縹緲間的美麗原鄉故事。
退伍返鄉學習種咖啡
高中畢業後,苦於部落裡少有工作機會的羅忠輝,選擇當職業軍人,駐紮在高雄。離鄉背井長達二十年之久的羅忠輝,因有感於家族耆老心中總是掛念著白白浪費一塊寶地,十分可惜,二○一○年,他毅然決定從職業軍人的身分退休,返回歷坵村,從頭開始學習種植咖啡、選豆、烘焙,到煮咖啡。
「老人家一直叮嚀我們,不要浪費了這塊土地啊!為了不辜負老人家的心意,又想要同時保護上帝賜予的這塊土地,才決定要種植咖啡。」羅忠輝靦腆地笑說,他希望在發展咖啡事業之餘,也能照顧年邁的父母,更期待未來的下一代可以回家延續家業,「否則離開自己的家鄉那麼久的時間,突然要返鄉務農、下田,其實也是很辛苦的。」
事實上,羅忠輝的祖父母、父親,原本是屏東縣霧台鄉阿里村的西魯凱族人,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間,隨著族人遷居到現今的歷坵部落,當時只有七戶人家。落地生根後,族人胼手胝足,努力打拚,終於能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
然而,萬事起頭難。從咖啡門外漢到略懂咖啡,甚至成為咖啡達人,羅忠輝可說是吃盡不少苦頭、歷經許多困難。起先,他只聽聞有族人曾在歷坵村種植咖啡,卻不知從何著手,在偶然機遇下,剛好看到由工研院、東部產業計畫服務中心共同策劃的《八十萬公里的熱情——釣竿科學家與花東農民的故事》中,專文介紹台東縣卑南鄉第五咖啡產銷班班長阮勇光生產「果子狸咖啡」的傳奇。
受到該則故事啟發後,羅忠輝跑去參加台東縣咖啡產業發展協會舉辦的相關課程,到處找人學習,並探詢、汲取田間管理、咖啡豆採收、日曬、脫殼、發酵、挑豆、烘焙及泡煮等技術,再將自己所學無償傳授給有興趣的族人。
成立產銷班展現領導力
為了推展歷坵咖啡,羅忠輝體會到團隊合作力量勝過單憑一己之力。二○一○年,他開始籌備、申請成立產銷班;二○一一年四月十一日,金峰鄉咖啡產銷班第三班正式成立,目前全班種植面積有十二公頃,約一萬株咖啡樹。
由於咖啡和洛神花皆屬特用作物,而金峰鄉已有洛神花產銷班第一班、第二班,所以雖取名為咖啡產銷班第三班,事實上卻是金峰鄉目前唯一的咖啡產銷班。成立產銷班的好處,在於可以申請辦公室、生產設備,爭取更多資源,並達到整合咖啡農友的目的。
目前產銷班班員有十人,現年四十三歲的羅忠輝,年紀最小,卻被推舉為班長。在軍中服役長達二十年的羅忠輝,很快就展現領導統御能力,要求班員開會遲到十分鐘要罰錢、會議中不能喝酒。
「他的年紀最小,但大家都很推崇他的領導能力,每次來開會,都會開玩笑說:『班長,今天不要太兇喔!』」羅忠輝的大姊羅英惠笑說。為了支持弟弟的夢想,羅英惠不僅加入產銷班,更將她的英惠原藝工作坊當作臨時開會場所。
過去一年來,羅忠輝特別安排專家到歷坵村開設咖啡種植、管理、烘焙、沖泡等課程。第一天上課時,每個班員竟然都穿雨靴、戴斗笠,一副準備下田的模樣,令羅忠輝又好氣又好笑,直呼:「我們班員真的很可愛!」
有趣的是,產銷班班員雖然種植咖啡,平時卻根本不喝咖啡。為了增加說服力,羅忠輝要求班員試喝咖啡,結果狀況百出,有人皺起眉頭:「咦,這是什麼鬼味道?」有人則是喝了一小口後,馬上問:「班長,檳榔咧?」
羅忠輝嘗試給了三杯不同品種的咖啡,要求他們再試喝,有人捏著鼻子,在三十秒內一口氣喝光,有人還一臉無辜地說:「班長,這三杯咖啡喝起來味道都一樣耶。」
經過多次努力,這群咖啡農終於學會親手泡煮咖啡、品嚐各種味道的咖啡。當看著自己親手栽種的咖啡豆,在熱騰騰的蒸氣中,化成黑色的液體,並伴隨著香氣汨汨流出時,每個人的臉上都有說不出的驕傲與成就感。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