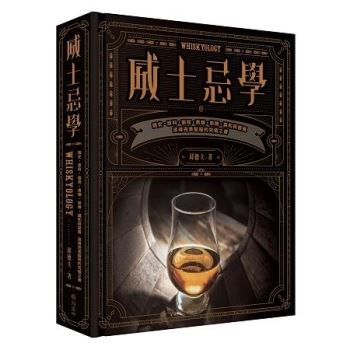【推薦序】
台灣威士忌的「知識狂熱者」
葉怡蘭
飲食生活作家、蘇格蘭雙耳小酒杯執持者(Keeper of the Quaich)
毫無疑問,在世界威士忌版圖上,台灣絕對佔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威士忌在台灣,從發端到興盛才短短不過十數年,卻明顯成就斐然。不僅銷售量在全球市場上名列前茅、且半數集中於進階級酒款;在專業領域也備受敬重:新品限定品常在台灣首發或獨賣,各品牌與酒廠總製酒師調酒師年年來訪,在地蒸餾廠與選桶裝瓶更在各種國際競賽中屢創佳績……
細究其中原因,我認為,和威士忌從一開始,便成功在台建立起博大精深品味形象大有關係。
其時,由先驅飲者(業內慣稱為「達人」)們領頭,積極擁抱、深入威士忌的知識面,從類型、產地、原料、釀造與蒸餾工藝以至熟陳、調和、裝瓶,每一環節學問講究都深入挖掘鑽研;並紛紛成立專門社團,開辦品酒會、課程,熱烈交流討論。究極之深,每讓遠渡重洋來台之專家大師驚嘆咋舌刮目相看。
讓威士忌得以擺脫其餘酒類習見的乾杯豪飲文化、或是虛無縹渺的浮面尊榮表象,在這品味顯學、智識故事為王的時代裡,先一步吸引菁英族群的關注與興趣,繼而一年年風行草偃,朝廣大消費群眾間擴散普及,蔚成龐大勢力。
而一眾達人間,本書作者邱德夫──我習慣敬稱他為邱大哥,可說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
相識相契十多年,在無數酒聚酒會中同座飲酒論酒、兩度同行拜訪國外酒廠酒鄉,邱大哥對於威士忌的旺盛求知慾和追根究柢毅力,總是讓我備受激勵。
一如邱大哥多年來屢次行文提及,專業工程師出身,使他對於原理、技術、圖表、數據,以至他所謂的「真相」、「證據」有著超乎尋常的執迷。
他不僅博覽群籍、找足資料,每回品酒會、每一次酒旅,更從現場發問到事後email往還,無不以著非把原廠榨乾淘盡的氣勢,每一製程細節都必得徹底通曉分明不可。
因此,出乎私心,我一直盼著邱大哥快快出書。畢竟,比起部落格與專欄上零星散落閱讀加上偶而當面切磋,我更想能有一整本內容俱全著作,將他十數年來於威士忌學海裡的修習研究、統整歸納,悉數有理有序通通貢獻出來,好讓我一次讀個明白痛快。
鞭策多年,此刻終見成書。展讀書稿,果然一點不負所望,這本書,非常邱大哥。一點不是他老愛自謙(雖然在我看來更像是誇耀)的詰屈聱牙艱澀板硬冗長難懂──事實上,我家另一半向來戲稱邱大哥為「文老」,所謂文老者,資深文青也;蓋因威士忌之外,他對文學也頗有雅好,日常言行和文字都流露濃濃文人氣文人樣。
遂而此書,當然全不見任何邱大哥平素最鄙視的「風花雪月」,卻是敘述析理活潑生動流暢,偶而穿插一己之感觸感發裡,還隱隱然透著些許任情和浪漫。
但章章篇篇,都是積累醞釀龐然深厚而發、擲地有聲的大塊文章。
大不同於此刻中文書市裡的國內外威士忌著作之通常大半本篇幅都由酒廠介紹占掉,一如書名,此書貨真價實正正就是一本「威士忌學」。
開篇娓娓談過歷史之後,接下來五章,便全然結結實實聚焦於完整製程的「鉅細靡遺」呈現。
說它「鉅細靡遺」可絕非客套或玩笑話。近十九萬字數裡,汪洋浩瀚涵蓋包羅遼廣深入:比方自古至今法令稅制的變遷,大麥、水源、酵母的組成構造及成分分析,歷來大麥品種出酒率與產量的比較,泥煤所含不同酚類化合物的詳述,各酒廠麥芽與新酒的泥煤含量對照,蒸餾器本體以至各部位零件材質為銅或不鏽鋼所形成的個別差異,蒸餾時水酒混合液在不同溫度下所產生之乙醇液態與氣態變化,2次、3次、2.5次、2.81次蒸餾流程的完整運作說明,各類橡木桶材加熱後所產生之纖維素、木質素、橡木單寧、橡木內酯高低所帶來的個別風味影響……等等等等,百分百來自一名知識控、原理控、技術控、數據控、圖表控的狂熱「工程師」的「表」圖文並茂威士忌書寫。
尤其在徹底實事求是抽絲剝繭同時,還據理針對種種時下迷思、潮流甚至既有傳統之存在必要性奮勇提出質疑與詰問,並對正初初萌芽的新實驗新嘗試細細說解評介後,進一步寄予鼓勵和展望……
讀來一點不枯燥,反覺加倍興味盎然。只因這種種,都非單單就是資料數字的堆砌,而是一一清楚指向酒液裡,每一細微色、香、味與韻之究竟由何處來,以及,將往何方去。
「原來如此啊!」──對飲食向來求知若渴的我,太清楚這感官覺知與門道智識講究學問的能夠連結、有源有本,是何等踏實暢快,咀嚼回味不盡,愛悅繫戀綿長。
且不獨我如此,相信眾多台灣威士忌飲者們也都一樣,長年樂在這連結中,耽溺沈醉、流連忘返。所以我認為,《威士忌學》此書不只非常邱大哥,還非常台灣。
鮮明具現了台灣威士忌界獨樹一幟的「知識狂熱」特質;也為這明明非為歷史悠久之產威士忌飲威士忌國度,卻能在短時間內風起雲湧豐收傲人碩果,留下絕佳印證與註腳。
────────────────────────────────────────────────
【自序】
白髮戴花君莫笑,人生何處似樽前
唐朝詩人杜甫,少時豪放自負,中年以後漂泊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寫下《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詩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當今世人皆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大鳴大放,卻鮮有人知詩人「為人性僻耽佳句」而捻斷數莖鬚的辛苦執著,不過杜老歷經滄桑浮沉後,終究放下偏執的性情,不再一字一句的耽持推敲,卻也難免寂寥,渴盼有陶謝諸文老作伴漫遊。
杜老此詩寫於50歲上下,若以今日人類健康長壽的角度觀之,仍屬壯年,更與我年紀相當。不過生為現代人的我,個性就算孤僻,就「交遊」一事上擁有比杜老更多的可能,尤其是網路興盛之後,懷四十年不遇之才有了出口,所以書寫部落格,潛心練酒,更進而跨出電腦螢幕外,認識了一批酒徒同好,除了加入台灣第一個專業威士忌的品飲團體「台灣單一麥芽威士忌品飲研究社」(TSMWTA)之外,也盡力參加各類品酒盛會,藉由各式各樣的酒款以及往來大師的講解開釋,努力吸收前輩高人的酒知酒識,用以彌補起步過晚的不足。這一段時間極長,自2004年開始,馬步蹲了約莫10年,重心放在大量品飲以建立自我的感官資料庫。如今回想這段時期,每日案牘勞形的疲累工作後,最大的幸福莫過夜裡的品飲時間,我將蒐集而來的酒款樣品有系統的一一試過,寫下品飲紀錄,再放在部落格讓眾酒友回饋討論,猶如睡前儀式般神聖又甜蜜,逐漸累積了超過2000個酒款資料,也築就充分、但從來不敢稱完備的認知。據此在外走闖,「達人」稱呼每每讓我心驚肉跳,因為所學功夫並不紮實,多來自道聽塗說或網路資料,且疑惑越學越多,何達之有?2014年底有了最重要的契機,姚和成(K大)、陳正穎(老鼠)及李宏仁(瘋狂喵喵)於臉書號召讀書會,以分章方式讀完硬底子的基本科學書Whisky: Technology,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這本書是蘇格蘭Heriot-Watt大學釀造及蒸餾研究所使用的教科書,不僅深入製程細節,涵蓋面又廣及裝瓶行銷,只是對於非生化科學背景的我而言,讀來痛苦莫名,但從2015年1月的第一次聚會,到2016年11月的最後一次,一字一淚、血汗交織的讀下來,心底越來越踏實,書寫的文字也從感官分析,逐漸偏向-工程?
沒錯,我是受過長期專業訓練的工程師,過去所有的學習和工作經歷都教我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數據是王,頂多加上可容許的安全係數,幾十年的制約,多說一分都會逾越我的心理紅線。另一方面,威士忌是一種非民生必須品,客層有限,販售時需要包裝,而包裝是一種藝術,必須說得巧又夠讓人信服,絕非死板板的數字,也因此與我的訓練存在先天上的差異橫溝。由於習慣性的解構話術,又是個不折不扣的懷疑論者,對於所有看得到、讀得到的行銷包裝都存有一定的懷疑,以致追根究底,最愛提問,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咦?) 總之,這兩三年間,我的文章風格愈發遠離風花雪月,愈發去追究一般愛酒人士感官讚嘆之餘,不怎麼在意的微末細節,一心以為浪漫不足以製酒,回到製作的初始,方是所有包裝的基礎,而用圖表去解釋威士忌,不正是工程師的重責大任嗎?(一笑)寫部落格是很私人的,也相當寂寞,因為除非留言回饋,否則永遠不知道讀者是誰。到了資訊快速流動的今天,這種寂寞感更是排山倒海,某個話題或許可能吸引他人目光片刻,但立即被其他議題覆蓋,以致部落格經營13年,累積的點閱總數僅66萬人次,雖說差強人意,卻萬萬不及隨便哪個網紅正妹一天的點閱率,所以未曾有過集結出書的打算。不過隨著字數的累積增加,以及從2014年起於《財訊雙週刊》書寫專欄,越來越多出書的聲音在耳邊營營作響,初時無感,惟幾位重量級人物如姚和成、王學信(班長)開始推坑後,自小懷抱的作家夢想逐漸甦醒,但依舊自忖,現代人能耐著性子讀多少文字?尤其是詰屈聱牙的技術類,出書豈不等同害了出版社?反反覆覆的猶豫,真正臨門一腳是好朋友怡蘭踢出,她不僅直接找來出版社,還在安排見面中說了一句「這本書你不寫誰寫?」我虎目含淚,只能點頭稱是。
寫部落格是寂寞的,寫書則是痛苦,原以為將過去的文字湊合湊合也是十來萬字,足夠撐出一本2、3百頁的書,但過去的邏輯訓練不這麼輕鬆放過我。擬定的大綱其實單純,只是從原料、原料的處理、蒸餾、熟陳到調和裝瓶等大家耳熟能詳的製程主項,加上一篇簡史,我稱之為「威士忌六講」(這是我最早構思的書名,卻因為太過老掉牙而被老婆、兒子打槍),實際寫起來,以前累積的文字幾乎不管用,砍掉重鍊之外,單單「簡史」便叫我寫到地老天荒。從此手邊擺著一本又一本的參考書,網路資料往來對照(多言一句,網路資料謬誤甚多,絕不可盡信),蘇格蘭的幾位大師也被我追著煩,逮到機會就問,問不出答案寫信去追,我能想及的疑惑,非得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挖出根底不可。就這麼緩慢的,約一個半月一篇的進度完成架構並堆砌骨肉,而後再不斷的、似乎永無止盡的根據詢問得來的資訊去修改,折磨到自己尚可接受,總字數也遠遠超出預期。徒文不足以成書,缺少圖片,讀者可能無法從文字理解我拙劣的說明。為了蒐集想要的圖片,幾乎威士忌界所能尋得的資源都被我煩了好幾番,無論是酒公司如愛丁頓寰盛、格蘭父子、台灣保樂力加、人頭馬君度、酩悅軒尼詩、帝亞吉歐、台灣三得利、金車噶瑪蘭、南投酒廠、隼昌、尚格、廷漢、豪邁和橡木桶洋酒,或是個人如Max、Paul、Kelly、Afra、Kingfisher、Winnie、Alex、Thomas、Cathy、威利,或甚至網路上鼎鼎大名的法國老Serge以及遠在加拿大的Davin de Kergommeaux,都被我糾纏了好久。可由於我的需求異於常人,著重在細部解說,以致忍痛捨棄許多華美的沙龍照,反倒是幾位好友於參觀酒廠行程中,一些不經意透露製程細節的照片讓我如獲至寶,同時也驗證了書本上的知識。但無論如何,眾多朋友提供了近13G的照片,或有用或未用,全都讓我衷心感謝也永銘五內。
───────────────────────────────────────
【第一篇、 細說從頭】
──從生命之水到蘇格蘭威士忌
■蘇格蘭威士忌簡史(1823~1853):連續式蒸餾器、穀物威士忌
高登公爵的承租人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因應「貨物稅法」的實施於1824年率先輸誠,而蒸餾廠名稱則是我們熟知的格蘭利威(Glenlivet)。他原來也是一位私釀者,不過產量極低,每星期僅製作約1個重組桶(Hogshead,約250公升)的烈酒。多年之後他向報社講述合法化的心路歷程:「當新法案公布後,高地區的私釀業者都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有人願意相信政府?不過地主們十分焦急,盡其一切可能鼓勵承租人向政府投誠,只是我們依舊處在走私者的暴力威脅下。1824年的時候我年輕氣盛,同時也受到高登公爵的鼓勵,所以決定把握這個機會。不過鄰居們卻揚言要焚毀我的蒸餾廠,幸好亞伯樂(Aberlour)領主給我2把手槍自衛,這2把槍在10年內從來沒離開過我的腰帶」。如今這2把手槍展示在格蘭利威的旅客中心。
接下來世人耳熟能詳的高地蒸餾廠紛紛出列:皇家藍勛(Lochnargar)、麥卡倫(Macallan)、卡杜(Cardhu)、慕赫(Mortlach)、亞伯樂等等,波特艾倫(Port Ellen)也在同年成立,並且引進了剛剛發明、用以管控蒸餾酒量的烈酒保險箱(spirit safe),至於投誠的低地蒸餾廠更多,超過50間。根據統計,1823年的合法蒸餾廠共計203間,隔年便增加到337間,其中79間屬於大型(蒸餾器大於500加侖),其餘則是小型(蒸餾器小於250加侖),而新成立的134間蒸餾廠中,29間都屬於大型。一窩蜂的投產下,合法威士忌的產量到1828年已高達1000萬加侖,遠超過蘇格蘭的需求,供需逐漸失衡,此時連續式蒸餾器的發明讓問題更形擴大。
▲淘汰壺式蒸餾器,不間斷的連續蒸餾器成為主流
至今為止所謂的蒸餾都使用壺式蒸餾器,以批次的方式進行,一個批次做完後必須清洗蒸餾器及管線,而後再進行下一個批次,工續多而流程慢,雖然低地蒸餾業者使用投機加速方法,產製的威士忌品質卻不被認同。這種情況在羅勃特史丹(Robert Stein)—— 一位在低地區Kilbagie蒸餾廠工作的蒸餾者,於1826年發明連續式蒸餾器之後有了革命性的改變,只要持續輸入酒汁,便能不間斷地蒸餾。
可惜羅勃史丹生不逢時,蘇格蘭威士忌的供需比例開始反轉,費一番心力後,這套劃時代的設備仍於1828年獲准試做,1829年5月取得專利並裝置在至今仍在運作中的克爾門布里基(Cameronbridge)蒸餾廠,到了年底,總共生產15萬加侖的麥芽威士忌。這個產量與當時的大型蒸餾廠比較,如麥卡倫的年產量5000加侖,不論量或純淨度都遠遠超過,且因口感溫和、酒精度高,適合摻料飲用。
就在相近的時間點,愛爾蘭都柏林一位稅務官埃尼斯科菲(Aeneas Coffey)也設計了類似的裝置,同樣是高聳的柱狀,但包含2座蒸餾器,而內部則採用銅製多孔蒸餾板,與羅勃特史丹使用的毛織布(haircloth)比較,不僅較為堅固,且因為銅質的化學交換作用,可產製出更純淨的新酒。
這套設備於1830年取得專利,而後於都柏林興建Dock蒸餾廠,並在倫敦成立蒸餾器製造廠。蘇格蘭第1座科菲蒸餾器,則是在1834年於早已消失的Grange蒸餾廠裝設,投資並未成功,但蒸餾方式終於大躍進,且相同的設計原理一直沿用至今,一般稱之為「科菲蒸餾器」、專利蒸餾器、柱式或連續式蒸餾器。▲高低地區採用不同配方,釀製穀物混雜的威士忌
科菲蒸餾器裝置大、價格昂貴,但易於操作及維護保養,除了每小時可製作出驚人的3000加侖新酒之外,其酒精度高(94~96%)也更為純淨,有利於穀物威士忌的登場。過去由於地形、地質、土壤及氣候等關係交互影響,高地區的主要作物為大麥,而低地區則遍產大麥、裸麥及小麥,導致長久以來,高地區單純使用麥芽生產威士忌,而低地區則採用不同的穀物配方。
《國富論》的作者亞當史密斯也注意到此種情況,在書中提到:「所謂的麥芽威士忌只有1/3的麥芽,其他使用的穀物要不是未發芽的大麥,便是1/3的大麥和1/3的小麥」,由此可知當時的麥芽威士忌很可能混用不同穀物,並不像今天界定清楚。
只不過科菲蒸餾器雖然在愛爾蘭取得專利,但愛爾蘭的蒸餾業者並不買單,反倒在蘇格蘭更受歡迎,這種情況持續數十年並未改變,都柏林的蒸餾業者在1878年出版的一本《威士忌真理》(Truths About Whisky)小冊子中,便提到:「專利蒸餾器業者剝除了烈酒該有的一切。對人來說,就算剝掉衣物還是人,雖然不符禮法,所以這種「沉默的烈酒」(silent spirit)依舊是威士忌,但已經失去烈酒該有的飲用價值了」。
另一方面,英國於1815年開始實行的「穀物法」(Corn Laws)有了變化。這個法令原本是以徵收超高額的進口穀物關稅來保護國內農民,但就在1845~1852年間,愛爾蘭因馬鈴薯枯萎症導致大饑荒,史稱Great Famine或Great Hunger,超過100萬人死亡、100萬人移居他地,總人口減少20~25%。
首相Robert Peel眼見情況不對,1846年在國會倡議下廢除穀物法,大量進口廉價的美國玉米以消減機荒,但很快的,這種廉價穀物在蘇格蘭有了新的用途,科菲蒸餾器業者進口玉米取代價格較為昂貴的麥芽來製作烈酒,成本及售價大幅滑落,為接下來調和式威士忌的登場打下充足的基礎。
從原料的角度來看,不同穀物所含的澱粉、蛋白值比例不同,產製的威士忌風味自然也不同。一般而言,非大麥穀物的蛋白質含量較大麥為高,經發酵後產生的化合物較多也較雜。採用壺式蒸餾器作麥芽威士忌,即使經2次或3次蒸餾,仍無法將所有雜質濾除,導致新酒較「髒」,且由於麥芽是大麥發芽後,以泥煤烘烤燻乾製成,無法避免的飽含大量泥煤味,風味當然獨特,除了蘇格蘭高地區,其實並不受歡迎。連續式蒸餾器如同進行10、20次的蒸餾,絕大部份分子較大、較重或沸點較高的化合物都會被濾除,因此得到的新酒較為純淨,若以廉價的玉米為主要原料,則毫無泥煤味的新酒酒質更是乾淨,就算口味較為平淡,卻可滿足廉價烈酒的消費需求,因此越來越受到歡迎。
不過這都是後話,這段時期只是稱是威士忌產業的搖籃期。
▲威士忌產業的搖籃期,多加工、少純飲
在威士忌產業搖籃期(約1825年以前),無論是產自英格蘭、蘇格蘭或愛爾蘭的威士忌,極少人拿來純飲,絕大部分的烈酒商都會加工精製以去除粗獷、刺激的風味,讓威士忌更能入口。加工的方法不外乎添加一些草藥或杜松子、莓果或松節油,而後再行蒸餾做出琴酒(British Gin),或仿製成白蘭地等外國酒,所以加工調製的烈酒商等同於掌握獲控制了大眾的口味。
以科菲蒸餾器產製的穀物烈酒,無論是來自愛爾蘭或蘇格蘭,送到英格蘭之後將重新再製成琴酒,小部分不加工而以「英國烈酒」(British spirit)的名稱便宜出售,其餘則調入少許麥芽威士忌在蘇格蘭銷售,到了19世紀中期,則輸往大英帝國所屬的澳洲、南非、加拿大及獨立後的美國。
不過在1840年前後,由於氣候不穩、農民收成差加上銀行破產,蘇格蘭威士忌的需求量從1836年的660萬加侖下降到1843年的560萬加侖,即使英格蘭對穀物威士忌的需求量依舊維持穩定,但大部分來自愛爾蘭,以致於蘇格蘭威士忌的整體產量減少1/4,蒸餾廠數量從230間減少到169間,不過格蘭花格(Glenfarclas)、格蘭歐德(Ord)、大摩(Dalmore)、格蘭傑(Glenmorangie)這幾座現在世人耳熟能詳的酒廠卻也在這段時間內誕生。對後世影響更大的是,調和威士忌的商業模式逐漸興起、漸成主流。
【第六篇、調和與裝瓶──製酒師一生懸命所追求的工藝】
■ 焦糖著色及冷凝過濾
台灣是個威士忌非常成熟的市場,但也非常偏執,譬如SWA歷年來公布的統計資料,台灣自蘇格蘭進口的威士忌「總量」排名大多在十幾名,但「價值」時時在前3名;又或者是《麥芽威士忌年鑑》公布的資料中,台灣的麥芽威士忌進口量連年排名第3,但調和威士忌擠不進前10名,顯然台灣人總愛購買平均單價較高的單一麥芽威士忌,而非總量占9成左右的調和式威士忌。
台灣威士忌的「知識狂熱者」
葉怡蘭
飲食生活作家、蘇格蘭雙耳小酒杯執持者(Keeper of the Quaich)
毫無疑問,在世界威士忌版圖上,台灣絕對佔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威士忌在台灣,從發端到興盛才短短不過十數年,卻明顯成就斐然。不僅銷售量在全球市場上名列前茅、且半數集中於進階級酒款;在專業領域也備受敬重:新品限定品常在台灣首發或獨賣,各品牌與酒廠總製酒師調酒師年年來訪,在地蒸餾廠與選桶裝瓶更在各種國際競賽中屢創佳績……
細究其中原因,我認為,和威士忌從一開始,便成功在台建立起博大精深品味形象大有關係。
其時,由先驅飲者(業內慣稱為「達人」)們領頭,積極擁抱、深入威士忌的知識面,從類型、產地、原料、釀造與蒸餾工藝以至熟陳、調和、裝瓶,每一環節學問講究都深入挖掘鑽研;並紛紛成立專門社團,開辦品酒會、課程,熱烈交流討論。究極之深,每讓遠渡重洋來台之專家大師驚嘆咋舌刮目相看。
讓威士忌得以擺脫其餘酒類習見的乾杯豪飲文化、或是虛無縹渺的浮面尊榮表象,在這品味顯學、智識故事為王的時代裡,先一步吸引菁英族群的關注與興趣,繼而一年年風行草偃,朝廣大消費群眾間擴散普及,蔚成龐大勢力。
而一眾達人間,本書作者邱德夫──我習慣敬稱他為邱大哥,可說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
相識相契十多年,在無數酒聚酒會中同座飲酒論酒、兩度同行拜訪國外酒廠酒鄉,邱大哥對於威士忌的旺盛求知慾和追根究柢毅力,總是讓我備受激勵。
一如邱大哥多年來屢次行文提及,專業工程師出身,使他對於原理、技術、圖表、數據,以至他所謂的「真相」、「證據」有著超乎尋常的執迷。
他不僅博覽群籍、找足資料,每回品酒會、每一次酒旅,更從現場發問到事後email往還,無不以著非把原廠榨乾淘盡的氣勢,每一製程細節都必得徹底通曉分明不可。
因此,出乎私心,我一直盼著邱大哥快快出書。畢竟,比起部落格與專欄上零星散落閱讀加上偶而當面切磋,我更想能有一整本內容俱全著作,將他十數年來於威士忌學海裡的修習研究、統整歸納,悉數有理有序通通貢獻出來,好讓我一次讀個明白痛快。
鞭策多年,此刻終見成書。展讀書稿,果然一點不負所望,這本書,非常邱大哥。一點不是他老愛自謙(雖然在我看來更像是誇耀)的詰屈聱牙艱澀板硬冗長難懂──事實上,我家另一半向來戲稱邱大哥為「文老」,所謂文老者,資深文青也;蓋因威士忌之外,他對文學也頗有雅好,日常言行和文字都流露濃濃文人氣文人樣。
遂而此書,當然全不見任何邱大哥平素最鄙視的「風花雪月」,卻是敘述析理活潑生動流暢,偶而穿插一己之感觸感發裡,還隱隱然透著些許任情和浪漫。
但章章篇篇,都是積累醞釀龐然深厚而發、擲地有聲的大塊文章。
大不同於此刻中文書市裡的國內外威士忌著作之通常大半本篇幅都由酒廠介紹占掉,一如書名,此書貨真價實正正就是一本「威士忌學」。
開篇娓娓談過歷史之後,接下來五章,便全然結結實實聚焦於完整製程的「鉅細靡遺」呈現。
說它「鉅細靡遺」可絕非客套或玩笑話。近十九萬字數裡,汪洋浩瀚涵蓋包羅遼廣深入:比方自古至今法令稅制的變遷,大麥、水源、酵母的組成構造及成分分析,歷來大麥品種出酒率與產量的比較,泥煤所含不同酚類化合物的詳述,各酒廠麥芽與新酒的泥煤含量對照,蒸餾器本體以至各部位零件材質為銅或不鏽鋼所形成的個別差異,蒸餾時水酒混合液在不同溫度下所產生之乙醇液態與氣態變化,2次、3次、2.5次、2.81次蒸餾流程的完整運作說明,各類橡木桶材加熱後所產生之纖維素、木質素、橡木單寧、橡木內酯高低所帶來的個別風味影響……等等等等,百分百來自一名知識控、原理控、技術控、數據控、圖表控的狂熱「工程師」的「表」圖文並茂威士忌書寫。
尤其在徹底實事求是抽絲剝繭同時,還據理針對種種時下迷思、潮流甚至既有傳統之存在必要性奮勇提出質疑與詰問,並對正初初萌芽的新實驗新嘗試細細說解評介後,進一步寄予鼓勵和展望……
讀來一點不枯燥,反覺加倍興味盎然。只因這種種,都非單單就是資料數字的堆砌,而是一一清楚指向酒液裡,每一細微色、香、味與韻之究竟由何處來,以及,將往何方去。
「原來如此啊!」──對飲食向來求知若渴的我,太清楚這感官覺知與門道智識講究學問的能夠連結、有源有本,是何等踏實暢快,咀嚼回味不盡,愛悅繫戀綿長。
且不獨我如此,相信眾多台灣威士忌飲者們也都一樣,長年樂在這連結中,耽溺沈醉、流連忘返。所以我認為,《威士忌學》此書不只非常邱大哥,還非常台灣。
鮮明具現了台灣威士忌界獨樹一幟的「知識狂熱」特質;也為這明明非為歷史悠久之產威士忌飲威士忌國度,卻能在短時間內風起雲湧豐收傲人碩果,留下絕佳印證與註腳。
────────────────────────────────────────────────
【自序】
白髮戴花君莫笑,人生何處似樽前
唐朝詩人杜甫,少時豪放自負,中年以後漂泊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寫下《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詩云「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當今世人皆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大鳴大放,卻鮮有人知詩人「為人性僻耽佳句」而捻斷數莖鬚的辛苦執著,不過杜老歷經滄桑浮沉後,終究放下偏執的性情,不再一字一句的耽持推敲,卻也難免寂寥,渴盼有陶謝諸文老作伴漫遊。
杜老此詩寫於50歲上下,若以今日人類健康長壽的角度觀之,仍屬壯年,更與我年紀相當。不過生為現代人的我,個性就算孤僻,就「交遊」一事上擁有比杜老更多的可能,尤其是網路興盛之後,懷四十年不遇之才有了出口,所以書寫部落格,潛心練酒,更進而跨出電腦螢幕外,認識了一批酒徒同好,除了加入台灣第一個專業威士忌的品飲團體「台灣單一麥芽威士忌品飲研究社」(TSMWTA)之外,也盡力參加各類品酒盛會,藉由各式各樣的酒款以及往來大師的講解開釋,努力吸收前輩高人的酒知酒識,用以彌補起步過晚的不足。這一段時間極長,自2004年開始,馬步蹲了約莫10年,重心放在大量品飲以建立自我的感官資料庫。如今回想這段時期,每日案牘勞形的疲累工作後,最大的幸福莫過夜裡的品飲時間,我將蒐集而來的酒款樣品有系統的一一試過,寫下品飲紀錄,再放在部落格讓眾酒友回饋討論,猶如睡前儀式般神聖又甜蜜,逐漸累積了超過2000個酒款資料,也築就充分、但從來不敢稱完備的認知。據此在外走闖,「達人」稱呼每每讓我心驚肉跳,因為所學功夫並不紮實,多來自道聽塗說或網路資料,且疑惑越學越多,何達之有?2014年底有了最重要的契機,姚和成(K大)、陳正穎(老鼠)及李宏仁(瘋狂喵喵)於臉書號召讀書會,以分章方式讀完硬底子的基本科學書Whisky: Technology,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這本書是蘇格蘭Heriot-Watt大學釀造及蒸餾研究所使用的教科書,不僅深入製程細節,涵蓋面又廣及裝瓶行銷,只是對於非生化科學背景的我而言,讀來痛苦莫名,但從2015年1月的第一次聚會,到2016年11月的最後一次,一字一淚、血汗交織的讀下來,心底越來越踏實,書寫的文字也從感官分析,逐漸偏向-工程?
沒錯,我是受過長期專業訓練的工程師,過去所有的學習和工作經歷都教我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數據是王,頂多加上可容許的安全係數,幾十年的制約,多說一分都會逾越我的心理紅線。另一方面,威士忌是一種非民生必須品,客層有限,販售時需要包裝,而包裝是一種藝術,必須說得巧又夠讓人信服,絕非死板板的數字,也因此與我的訓練存在先天上的差異橫溝。由於習慣性的解構話術,又是個不折不扣的懷疑論者,對於所有看得到、讀得到的行銷包裝都存有一定的懷疑,以致追根究底,最愛提問,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咦?) 總之,這兩三年間,我的文章風格愈發遠離風花雪月,愈發去追究一般愛酒人士感官讚嘆之餘,不怎麼在意的微末細節,一心以為浪漫不足以製酒,回到製作的初始,方是所有包裝的基礎,而用圖表去解釋威士忌,不正是工程師的重責大任嗎?(一笑)寫部落格是很私人的,也相當寂寞,因為除非留言回饋,否則永遠不知道讀者是誰。到了資訊快速流動的今天,這種寂寞感更是排山倒海,某個話題或許可能吸引他人目光片刻,但立即被其他議題覆蓋,以致部落格經營13年,累積的點閱總數僅66萬人次,雖說差強人意,卻萬萬不及隨便哪個網紅正妹一天的點閱率,所以未曾有過集結出書的打算。不過隨著字數的累積增加,以及從2014年起於《財訊雙週刊》書寫專欄,越來越多出書的聲音在耳邊營營作響,初時無感,惟幾位重量級人物如姚和成、王學信(班長)開始推坑後,自小懷抱的作家夢想逐漸甦醒,但依舊自忖,現代人能耐著性子讀多少文字?尤其是詰屈聱牙的技術類,出書豈不等同害了出版社?反反覆覆的猶豫,真正臨門一腳是好朋友怡蘭踢出,她不僅直接找來出版社,還在安排見面中說了一句「這本書你不寫誰寫?」我虎目含淚,只能點頭稱是。
寫部落格是寂寞的,寫書則是痛苦,原以為將過去的文字湊合湊合也是十來萬字,足夠撐出一本2、3百頁的書,但過去的邏輯訓練不這麼輕鬆放過我。擬定的大綱其實單純,只是從原料、原料的處理、蒸餾、熟陳到調和裝瓶等大家耳熟能詳的製程主項,加上一篇簡史,我稱之為「威士忌六講」(這是我最早構思的書名,卻因為太過老掉牙而被老婆、兒子打槍),實際寫起來,以前累積的文字幾乎不管用,砍掉重鍊之外,單單「簡史」便叫我寫到地老天荒。從此手邊擺著一本又一本的參考書,網路資料往來對照(多言一句,網路資料謬誤甚多,絕不可盡信),蘇格蘭的幾位大師也被我追著煩,逮到機會就問,問不出答案寫信去追,我能想及的疑惑,非得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挖出根底不可。就這麼緩慢的,約一個半月一篇的進度完成架構並堆砌骨肉,而後再不斷的、似乎永無止盡的根據詢問得來的資訊去修改,折磨到自己尚可接受,總字數也遠遠超出預期。徒文不足以成書,缺少圖片,讀者可能無法從文字理解我拙劣的說明。為了蒐集想要的圖片,幾乎威士忌界所能尋得的資源都被我煩了好幾番,無論是酒公司如愛丁頓寰盛、格蘭父子、台灣保樂力加、人頭馬君度、酩悅軒尼詩、帝亞吉歐、台灣三得利、金車噶瑪蘭、南投酒廠、隼昌、尚格、廷漢、豪邁和橡木桶洋酒,或是個人如Max、Paul、Kelly、Afra、Kingfisher、Winnie、Alex、Thomas、Cathy、威利,或甚至網路上鼎鼎大名的法國老Serge以及遠在加拿大的Davin de Kergommeaux,都被我糾纏了好久。可由於我的需求異於常人,著重在細部解說,以致忍痛捨棄許多華美的沙龍照,反倒是幾位好友於參觀酒廠行程中,一些不經意透露製程細節的照片讓我如獲至寶,同時也驗證了書本上的知識。但無論如何,眾多朋友提供了近13G的照片,或有用或未用,全都讓我衷心感謝也永銘五內。
───────────────────────────────────────
【第一篇、 細說從頭】
──從生命之水到蘇格蘭威士忌
■蘇格蘭威士忌簡史(1823~1853):連續式蒸餾器、穀物威士忌
高登公爵的承租人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因應「貨物稅法」的實施於1824年率先輸誠,而蒸餾廠名稱則是我們熟知的格蘭利威(Glenlivet)。他原來也是一位私釀者,不過產量極低,每星期僅製作約1個重組桶(Hogshead,約250公升)的烈酒。多年之後他向報社講述合法化的心路歷程:「當新法案公布後,高地區的私釀業者都覺得不可思議,怎麼會有人願意相信政府?不過地主們十分焦急,盡其一切可能鼓勵承租人向政府投誠,只是我們依舊處在走私者的暴力威脅下。1824年的時候我年輕氣盛,同時也受到高登公爵的鼓勵,所以決定把握這個機會。不過鄰居們卻揚言要焚毀我的蒸餾廠,幸好亞伯樂(Aberlour)領主給我2把手槍自衛,這2把槍在10年內從來沒離開過我的腰帶」。如今這2把手槍展示在格蘭利威的旅客中心。
接下來世人耳熟能詳的高地蒸餾廠紛紛出列:皇家藍勛(Lochnargar)、麥卡倫(Macallan)、卡杜(Cardhu)、慕赫(Mortlach)、亞伯樂等等,波特艾倫(Port Ellen)也在同年成立,並且引進了剛剛發明、用以管控蒸餾酒量的烈酒保險箱(spirit safe),至於投誠的低地蒸餾廠更多,超過50間。根據統計,1823年的合法蒸餾廠共計203間,隔年便增加到337間,其中79間屬於大型(蒸餾器大於500加侖),其餘則是小型(蒸餾器小於250加侖),而新成立的134間蒸餾廠中,29間都屬於大型。一窩蜂的投產下,合法威士忌的產量到1828年已高達1000萬加侖,遠超過蘇格蘭的需求,供需逐漸失衡,此時連續式蒸餾器的發明讓問題更形擴大。
▲淘汰壺式蒸餾器,不間斷的連續蒸餾器成為主流
至今為止所謂的蒸餾都使用壺式蒸餾器,以批次的方式進行,一個批次做完後必須清洗蒸餾器及管線,而後再進行下一個批次,工續多而流程慢,雖然低地蒸餾業者使用投機加速方法,產製的威士忌品質卻不被認同。這種情況在羅勃特史丹(Robert Stein)—— 一位在低地區Kilbagie蒸餾廠工作的蒸餾者,於1826年發明連續式蒸餾器之後有了革命性的改變,只要持續輸入酒汁,便能不間斷地蒸餾。
可惜羅勃史丹生不逢時,蘇格蘭威士忌的供需比例開始反轉,費一番心力後,這套劃時代的設備仍於1828年獲准試做,1829年5月取得專利並裝置在至今仍在運作中的克爾門布里基(Cameronbridge)蒸餾廠,到了年底,總共生產15萬加侖的麥芽威士忌。這個產量與當時的大型蒸餾廠比較,如麥卡倫的年產量5000加侖,不論量或純淨度都遠遠超過,且因口感溫和、酒精度高,適合摻料飲用。
就在相近的時間點,愛爾蘭都柏林一位稅務官埃尼斯科菲(Aeneas Coffey)也設計了類似的裝置,同樣是高聳的柱狀,但包含2座蒸餾器,而內部則採用銅製多孔蒸餾板,與羅勃特史丹使用的毛織布(haircloth)比較,不僅較為堅固,且因為銅質的化學交換作用,可產製出更純淨的新酒。
這套設備於1830年取得專利,而後於都柏林興建Dock蒸餾廠,並在倫敦成立蒸餾器製造廠。蘇格蘭第1座科菲蒸餾器,則是在1834年於早已消失的Grange蒸餾廠裝設,投資並未成功,但蒸餾方式終於大躍進,且相同的設計原理一直沿用至今,一般稱之為「科菲蒸餾器」、專利蒸餾器、柱式或連續式蒸餾器。▲高低地區採用不同配方,釀製穀物混雜的威士忌
科菲蒸餾器裝置大、價格昂貴,但易於操作及維護保養,除了每小時可製作出驚人的3000加侖新酒之外,其酒精度高(94~96%)也更為純淨,有利於穀物威士忌的登場。過去由於地形、地質、土壤及氣候等關係交互影響,高地區的主要作物為大麥,而低地區則遍產大麥、裸麥及小麥,導致長久以來,高地區單純使用麥芽生產威士忌,而低地區則採用不同的穀物配方。
《國富論》的作者亞當史密斯也注意到此種情況,在書中提到:「所謂的麥芽威士忌只有1/3的麥芽,其他使用的穀物要不是未發芽的大麥,便是1/3的大麥和1/3的小麥」,由此可知當時的麥芽威士忌很可能混用不同穀物,並不像今天界定清楚。
只不過科菲蒸餾器雖然在愛爾蘭取得專利,但愛爾蘭的蒸餾業者並不買單,反倒在蘇格蘭更受歡迎,這種情況持續數十年並未改變,都柏林的蒸餾業者在1878年出版的一本《威士忌真理》(Truths About Whisky)小冊子中,便提到:「專利蒸餾器業者剝除了烈酒該有的一切。對人來說,就算剝掉衣物還是人,雖然不符禮法,所以這種「沉默的烈酒」(silent spirit)依舊是威士忌,但已經失去烈酒該有的飲用價值了」。
另一方面,英國於1815年開始實行的「穀物法」(Corn Laws)有了變化。這個法令原本是以徵收超高額的進口穀物關稅來保護國內農民,但就在1845~1852年間,愛爾蘭因馬鈴薯枯萎症導致大饑荒,史稱Great Famine或Great Hunger,超過100萬人死亡、100萬人移居他地,總人口減少20~25%。
首相Robert Peel眼見情況不對,1846年在國會倡議下廢除穀物法,大量進口廉價的美國玉米以消減機荒,但很快的,這種廉價穀物在蘇格蘭有了新的用途,科菲蒸餾器業者進口玉米取代價格較為昂貴的麥芽來製作烈酒,成本及售價大幅滑落,為接下來調和式威士忌的登場打下充足的基礎。
從原料的角度來看,不同穀物所含的澱粉、蛋白值比例不同,產製的威士忌風味自然也不同。一般而言,非大麥穀物的蛋白質含量較大麥為高,經發酵後產生的化合物較多也較雜。採用壺式蒸餾器作麥芽威士忌,即使經2次或3次蒸餾,仍無法將所有雜質濾除,導致新酒較「髒」,且由於麥芽是大麥發芽後,以泥煤烘烤燻乾製成,無法避免的飽含大量泥煤味,風味當然獨特,除了蘇格蘭高地區,其實並不受歡迎。連續式蒸餾器如同進行10、20次的蒸餾,絕大部份分子較大、較重或沸點較高的化合物都會被濾除,因此得到的新酒較為純淨,若以廉價的玉米為主要原料,則毫無泥煤味的新酒酒質更是乾淨,就算口味較為平淡,卻可滿足廉價烈酒的消費需求,因此越來越受到歡迎。
不過這都是後話,這段時期只是稱是威士忌產業的搖籃期。
▲威士忌產業的搖籃期,多加工、少純飲
在威士忌產業搖籃期(約1825年以前),無論是產自英格蘭、蘇格蘭或愛爾蘭的威士忌,極少人拿來純飲,絕大部分的烈酒商都會加工精製以去除粗獷、刺激的風味,讓威士忌更能入口。加工的方法不外乎添加一些草藥或杜松子、莓果或松節油,而後再行蒸餾做出琴酒(British Gin),或仿製成白蘭地等外國酒,所以加工調製的烈酒商等同於掌握獲控制了大眾的口味。
以科菲蒸餾器產製的穀物烈酒,無論是來自愛爾蘭或蘇格蘭,送到英格蘭之後將重新再製成琴酒,小部分不加工而以「英國烈酒」(British spirit)的名稱便宜出售,其餘則調入少許麥芽威士忌在蘇格蘭銷售,到了19世紀中期,則輸往大英帝國所屬的澳洲、南非、加拿大及獨立後的美國。
不過在1840年前後,由於氣候不穩、農民收成差加上銀行破產,蘇格蘭威士忌的需求量從1836年的660萬加侖下降到1843年的560萬加侖,即使英格蘭對穀物威士忌的需求量依舊維持穩定,但大部分來自愛爾蘭,以致於蘇格蘭威士忌的整體產量減少1/4,蒸餾廠數量從230間減少到169間,不過格蘭花格(Glenfarclas)、格蘭歐德(Ord)、大摩(Dalmore)、格蘭傑(Glenmorangie)這幾座現在世人耳熟能詳的酒廠卻也在這段時間內誕生。對後世影響更大的是,調和威士忌的商業模式逐漸興起、漸成主流。
【第六篇、調和與裝瓶──製酒師一生懸命所追求的工藝】
■ 焦糖著色及冷凝過濾
台灣是個威士忌非常成熟的市場,但也非常偏執,譬如SWA歷年來公布的統計資料,台灣自蘇格蘭進口的威士忌「總量」排名大多在十幾名,但「價值」時時在前3名;又或者是《麥芽威士忌年鑑》公布的資料中,台灣的麥芽威士忌進口量連年排名第3,但調和威士忌擠不進前10名,顯然台灣人總愛購買平均單價較高的單一麥芽威士忌,而非總量占9成左右的調和式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