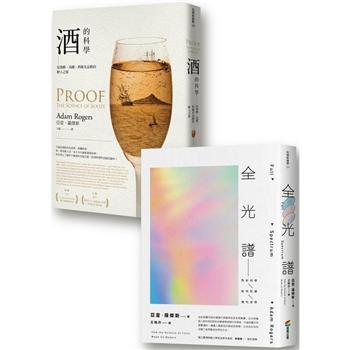《酒的科學》
──摘自〈序曲〉
兩個奇蹟
我點了杯啤酒;雖然已不記得是哪個牌子。只見吧台侍者向我點了點頭,時間開始慢了下來。他先為我鋪好一紙方巾,隨手取出一只啤酒杯,走向供酒閥。眼見他推開拉桿,啤酒從桶中流出。不久後啤酒送達,只見杯子外緣長滿一層薄霜。我緊緊握住杯子,用心感受滿手沁涼,舉起杯子,仔細覺察它的重量,我啜飲了一口。
時光瞬間停止。世界為之翻轉。看似如此微不足道的舉動──不就是某人走進一間酒吧這麼簡單嗎?──然而,正是這看似簡單的行為構築了本書的核心基石,敘述一件人類有史以來無與倫比的盛事。在世界各地,每天都發生成千,甚至數百萬次的這件事,看似尋常,卻是人類成就、科技文明達到極致的表徵,反映出人類在自然環境與工藝技術間領悟的奧義。曾有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的論述主張,啤酒的出現使得人類願意安家落戶,開始以務農為生──認真的定居下來,栽植穀物,從而停止了四處遷徙游牧的生活方式。
另外,當「智人」(Homo Sapiens)創造了酒精飲料,毋庸置疑的也對社會與經濟帶來了革命,促使其自身演進成為更具文明的人種。地球上人類的生活方式於焉達到頂峰。這著實是不折不扣的奇蹟。
其實總共有兩個奇蹟。第一個奇蹟是經過二億年的演進才發生的。發酵,這是個極其複雜而又驚人的奈米技術之作,過程中,一種我們稱為酵母的真菌,讓單純的糖類轉化成二氧化碳及乙醇。早在人類出現之前,發酵和乙醇就已存在。微生物與人類共生共存於地球;然而,微生物的世界裡不斷進行著我們看不見、永無休止的戰爭,戰爭中使用乙醇做為武器,對人類大腦造成的愉悅效應,則僅為其副作用。
發酵的生化作用在各種化工產業中都相當受到倚重,但它至今仍是寶貴的研究題材。畢竟就在不久之前,世上一些了不起的化學家和生物學家還不曉得它是什麼,並為此爭論不休。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證明了釀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啤酒酵母)具有生命,並會引起發酵作用,因此功成名就,也順勢帶動了細胞生物學的發展。從遺傳學的角度看今天的改良菌種,則仍存在不少待解謎團:它是在何時發展出製造乙醇的能力,以及人類是基於什麼原因,又是在何時才將它馴化為己所用?
人類直到大約一萬年前才開始擁有控制發酵的能力,隨即便與真菌建立起合作關係,而等到認清這位合作伙伴的真實身分時,又已經是許久之後的事了。我們的先人使用了與馴養狗與牛一樣的方法來馴化這種微生物,只為了一件事,就是製作發酵飲料。
據信,在距今二千年前左右,我們人類自己創造了第二個奇蹟:蒸餾法,混沌之初的科學家所使用最古老的設備之一。當時的煉金術士亟欲採集天地萬物菁華(靈魂,spirits)做為煉丹靈藥;然而,在冶煉過程中收集起來的蒸汽,卻意外提供了濃縮味道與香氣於液體(烈酒,spirits)的絕佳途徑,產生的液體也發展成為人類日常耗用的各種飲品。現代化學的起步就是從蒸餾法衍生而出,為人類奠定了石油經濟的基礎。
多虧了這些奇蹟,才能造就出酒吧裡的美妙時刻;從屏氣凝神輕啜的第一口,每時每秒都感受無比快樂,在享用第二杯雞尾酒當下,歡欣之情依然無可挑剔。乙醇的口感絕無僅有,當它放送出其他風味時更是別具特色。製酒是一門工藝──然而製酒師們,無論是在野火雞波本威士忌(Wild Turkey)、阿比塔啤酒(Abita)或是嘉露(E. & J. Gallo)的酒廠工作,都不需要了解分子生物學、酵母酶運動學、冶金學,或是多環芳香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屬有機化學。(不過他們往往具備這些名詞背後的知識。)他們知道,蒸餾器的造型及金屬材質,與產出的酒品口感息息相關;他們也相當清楚,揀選不同木材所製的陳年用酒桶,對最後的成品風味具有關鍵影響。(比起用美國橡木桶陳年的波本酒及蘇格蘭威士忌,日本橡木桶陳年的威士忌在口感上要來得更為辛辣。很有意思,對吧?)
眾人多半以為,所謂科學就是發現新的事物。其實,科學饒富趣味之處並不在於最後的答案,而是在探討諸多仍然存疑的問題、親身參與(或閱讀)解答的過程中。在製作發酵飲品、接著加以蒸餾成為烈酒的過程裡,每一個環節背後都藏有高深的科學知識,讓許許多多的研究者想方設法努力探究。
這便是本書的主題。酒吧裡的歡樂時光,代表了人類與身處環境之間至高無上的共鳴、科技的登峰造極,以及我們對自己身體、心靈與行為進行反思的重大時刻。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應該說過:「人類文明始於蒸餾。」我認為尤有甚者──還要納入蒸餾酒、葡萄酒、啤酒、蜂蜜酒、清酒……無所不包。這是屬於杯中之物的文明。
從酵母到宿醉
接下來的章節,將是對啜飲下肚的酒精飲料做的一場由生至死的編年記述。首先我們要探討酵母菌,這是種會產生酒精的微生物,隨之而來的是分子生物學與有機化學的研究領域。然後我們討論一下糖,也就是酵母菌的食物──並且,我會說它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分子。所以在聊到糖的時候,我們會思索農作法以及人類與植物的聯繫,回顧一下人類是如何從野生植物裡揀擇,將某些植物特別育種成農作物。再來,在糖的話題上,我還會回頭提到一個不太討喜、不太知名的微生物種,然而這物種的重要性比起酵母菌來毫不遜色。我個人特別偏愛、稱為清酒麴(koji)的真菌,若非遭逢命運反覆捉弄,很可能會是更重要的菌種。
明瞭酵母與糖的關係後,我們就可以討論發酵了,這是一堂關於酵母菌吃了糖之後排放酒精的基礎生物課。但話說回來,這裡也訴說了一個人類最早開始利用自然現象,加以操控後為己所用的例子。
接下來會談到蒸餾,人類別具匠心的創意巧思在此顯露無遺。蒸餾過程對發酵後的產物施以技術與工藝的魔法去蕪存菁,以致其搖身一變成為精煉的佳釀。發明蒸餾法之際,恰好時值人類利用技術改善生活條件的時代開啟,因此絕非偶然。這項始於古埃及煉金術士的新技術持續發光發熱、開枝散葉,廣泛應用在製藥、物理與冶金。
酒精飲料製造出來後,到達你準備享用的那一刻前,它的生命通常是在一個木桶中度過──行家稱之為「熟成」(maturation)。其間又隱藏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化學,酒桶木質中各種基本元素引起的化學反應,與桶中盛裝的液體同樣驚人。對於製酒人來說,酒品的熟成過程會影響經濟效益──因此,他們也嘗試運用科技手段來加速熟成以利銷售,其中有些作法還不錯,有些則讓人不敢領教。
接著我們會言歸正傳,繼續談我剛才說個不停的酒吧時刻,只是討論的話題從外在環境,來到了人體內部。首先,我們會提到人類感官如何面對酒精飲料的這門神奇科學,這個主題引發了神經學家與心理學家之間的終極論戰。蒸餾而來的烈酒裡有數百種氣味分子構成它的風味,然而至今還無人能夠將它們全部歸納清楚。泥煤(peat),是經由部分腐化分解的泥煤苔蘚夾雜其他植物的不完全碳化而形成,為蘇格蘭威士忌帶來煙燻和泥土的味道,但會因為開採地點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化合物──法國葡萄酒商按照生物分子學觀點,稱其為酒的風土(terroir)。在二○一○年,美國辛辛那提州立大學的化學家(當然也是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物理學家協助下)對幾種純度最高、成分只有乙醇及水的伏特加進行口感差異研究,結果發現乙醇與水分子間的氫鍵(hydrogen bonds)強度是造成不同口感的主因。所以,當我們從鐵錨牌荷蘭琴酒中聞到、嘗到杜松子酒的味道(就舉個令人驚訝的例子),其實背後藏有極其深奧的生物學與遺傳學玄機,而發現者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再來,要想弄清楚酒精飲料對身體與大腦產生的影響,則需要面對更加複雜的神經生物學,而在抽絲剝繭之際,還要為這杯雞尾酒加上一、兩份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輔料。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人會喝醉,還有人會成癮;然而,一個世紀以來的研究一直顯示,誰也不知道原因。就此而言,沒人真的明白為什麼喝醉後會有那樣的感覺。
本書最後(你不妨當成餐後酒)會談到宿醉,是指當你不是小酌,而是喝了很多、很多,非常大量的酒後,會發生的事情。宿醉背後的科學其實不痛不癢,遠非你想像中那種會殃及許多人、感覺很惡劣的事情。事實上,直到過去這幾年才有研究人員勉強同意對宿醉做個正式的定義,所以別指望有人會真心替它尋找原因(及解方)。終於,好不容易有幾位勇氣十足的研究人員(研究主題更是英勇得令人感動)對宿醉做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你在大學時對於宿醉的所見所聞都不正確。
《全光譜》
簡單來說,本書大致上會來來回回談到色彩在物理與心智之間的發展。人會製造具有色彩的事物,以及能夠為人事物賦予色彩的材料,後者指的就是顏料、染料、油漆、化妝品等物品。接著,人會瞭解色彩的運作原理,以及物理、化學、神經科學方面的特性。具備上述知識後,人會製造出更多色彩。光波長會改變,但在瞭解與製造之間來回擺盪的情形永遠不會變。不過,我承認,我們在接下來數百頁的篇幅中將踏上的路途,比起筆直前進,更像是迂迴前行,甚至可說是特立獨行。
我將從人類開始實驗如何製造色彩談起,這些透露出當時世界線索的色彩,誕生於十萬年前中石器時代可遮風避雨的洞窟內。目前找到最古老的顏料製作工坊便是屬於這個時代,就位在南非布隆伯斯(Blombos)洞窟之中。我會說這是一個約略的起始點,因為人類這時開始把周遭世界的自然物質轉換成製造色彩的原料——以便應用於工藝、工具、藝術。
接下來會稍微離題,探討一下生物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何會)看見色彩。分辨各種不同的光一定具有某種演化優勢,否則如此的能力就不會遺傳至今了。這種能力大概源自於某個古老的微生物,它與地球上任何生物都有所不同,跟我們人類之間的差異則大到彼此其實可以把對方視為外星生物。透過某種方式,這些小生物把以光為食的能力,例如光合作用,轉換成靠光的顏色就能判斷海下某處是否適合覓食。以色彩具體呈現出來的光,從動力來源轉變為知識。
不過,色彩直到人類開始出現貿易行為,才成為商業的一環。最早的人類文明擁有多種顏料,懂得創作五顏六色的藝術品,探討色彩代表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的貿易在西元早期數世紀如火如荼展開時,物品上的顏色可以大幅提高其價值。中國與阿拔斯帝國之間(以及絲路沿途各處)此消彼長的貿易興衰,背後推動的力量就是色彩。絲綢當然要染色,而染料基本上是一種由材料吸收的顏料,不光只是塗在表層而已。但本書要聚焦在另一種收益來源:陶瓷,具體來說是堅薄的瓷器,以及鑽研製瓷上釉的技術是如何推動數個文明的整體發展。
事實上,這些色彩本身以及色彩從何而來是如此重要,早期科學家不得不去瞭解色彩是由什麼所構成。這個故事經常始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接著有如穿越時空般,跳至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但在希臘人與啟蒙時代之間為其中的哲學與技術斷層搭起橋梁的,得歸功於數世紀阿拉伯學者、各國譯者與創新家所做的努力,這些人讀了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後表示:「嗯,這樣不對。」有像波斯科學家法利西(Al-Farisi)這樣的人,讓光穿過裝滿水的球形玻璃,好把光與物理化為實際數值,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才得以展開。
少了啟蒙運動以及從科學角度瞭解世界的意識崛起,色彩學在十八、十九世紀就不會有活絡興盛的光景。正是在這個時期,眾人開始研發新顏料,製造出世上前所未見的色彩,並發明新方法,複製圖像,加以利用。同一個時代的人也終於明白眼睛感知色彩的原理,進而為現代物理學揭開序幕。
即便人類開始創造出愈來愈多的合成色彩,白色依然獨樹一格,不論是在化學性質上,還是象徵意義上皆然。其中鉛白這種顏料,從古埃及與羅馬帝國興盛時期開始便舉足輕重,毒性也可怕至極。
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無色全白與下個世紀鮮明多彩的不和諧混雜,兩者間千年來的來回擺盪,到達了衝突最高潮。人們口中所謂的「白城」(White City),由當時的頂尖建築師與規劃師設計打造,仰賴的全是無趣的圓柱、殿堂、白色——不只是外觀,還包括種族。但其中一座建築物,也就是多色的運輸建築館(Transportation Building),鶴立雞群。這棟建築是由其中一位摩天大樓之父路易斯.蘇利文(Louis Sullivan)所打造,也是一項色彩理論的成果,其概念源自人腦是如何整合所見資訊的新科學。
一切都各就各位了。科學理論有了,需求也出現了。在工業革命的鼎盛時期,名為奧古斯特.羅西(Auguste Rossi)的工程師將會努力研究該如何利用由尼加拉瀑布發電的電爐,用鈦製造出更好的鋼合金——這真是十足的美國作風。這一切將徒勞無功,但在鑽研期間,他會發覺其中一種副產物可以當成白色顏料,也就是白得透亮的二氧化鈦粉末。不出數十年,這種白色粉末將主宰整個顏料製造業;如今,它依然獨占鰲頭。
二次大戰後,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生產的顏色與色彩繽紛的物品開始激增,但一個難解之謎也隨之浮上檯面:每個人眼中所見的色彩都各有不同。不是每個人都以相同的字眼來表達相同的色彩,這個差異不只出現在人與人之間,也體現在文化與文化之間。不過,隨著色彩學和新顏料更普及,大家開始清楚瞭解到,一般人如何看見與感知色彩的這個謎團,一部分跟人使用什麼詞彙來形容色彩有關。於是,在一九七○年代,語言學家保羅.凱伊(Paul Kay)與人類學家布倫特.柏林(Brent Berlin)派調查人員前往世界各地,想瞭解大家是如何談論色彩,兩人的成果至今依然是瞭解人類環境界(譯註: Umwelt,德文「周遭世界」之意)的關鍵。我們已經證實,色彩這項工具不只改變了靠技術革新而帶來進步的世界,也能用來瞭解語言和認知的內在世界。
這方面的研究甚至深入擴及至大腦與心智:神經生理學家在二十世紀中葉便展開研究,想釐清人類腦袋中的那團黏糊糊肉塊是如何把光轉換成色彩的概念,相關研究目前仍在進行。這個科學領域依然相當振奮人心,我這麼說的意思其實是,目前尚未有人徹底瞭解背後的原理。而證明這個科學領域尚待研究的最佳證據之一,出現在二○一五年,當時,單單一張藍色連衣裙(是藍的,不是白的,好嗎?)的彩圖就讓全世界分成兩派。由於網路已經深入每個口袋與包包,隨處可見的高畫質螢幕讓人人都有辦法重新創造出色彩近乎無限的調色盤。但這種創造色彩的全能能力,受到一張在傍晚時分拍下,並導致眾人意見兩極的藍色連衣裙照考驗後,顯示出每個人對這種無限色彩都各有看法。解構分析這件事,或許也能讓科學家瞭解眼睛和大腦究竟是如何運作,才得以在周遭環境的色彩改變時,為我們打造出一個色彩恆常的世界。
這也將為色彩科技帶來未來發展的契機。多虧數位投影機與先進3D列印機的協助,調色師正在讓各種既有色彩煥然一新,並使得新舊色彩難以區別。瞭解眼睛是如何解讀色彩,又是如何維持對各種色彩的概念,得以讓藝術品修復師挽救抽象派畫家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即將毀損的油畫作品,也可以讓人印出幾可亂真的藝術仿作——即便只有如黑箱作業般的人工智慧曉得其中的運作原理。
現今,所有螢幕、所有眼睛、所有大腦全都合力要創造出不可能出現的色彩,以及一種不單純是光譜,還能羅列情緒的頻譜。祕訣可能就在於亮度,也就是光影間的差距,其中一個極端仿自亮到不行的甲蟲,另一個則是所謂的超級黑顏料,導致現代藝術界四分五裂。皮克斯(Pixar)動畫工作室的色彩高手動畫師則橫跨在光影間的那條線上,透過目前所能打造的最先端科技,創造出只見於特殊銀幕上的色彩……也許有一天,他們運用雷射與編碼,就能喚起只存在於觀眾腦中,卻完全不屬於銀幕上的色彩。
──摘自〈序曲〉
兩個奇蹟
我點了杯啤酒;雖然已不記得是哪個牌子。只見吧台侍者向我點了點頭,時間開始慢了下來。他先為我鋪好一紙方巾,隨手取出一只啤酒杯,走向供酒閥。眼見他推開拉桿,啤酒從桶中流出。不久後啤酒送達,只見杯子外緣長滿一層薄霜。我緊緊握住杯子,用心感受滿手沁涼,舉起杯子,仔細覺察它的重量,我啜飲了一口。
時光瞬間停止。世界為之翻轉。看似如此微不足道的舉動──不就是某人走進一間酒吧這麼簡單嗎?──然而,正是這看似簡單的行為構築了本書的核心基石,敘述一件人類有史以來無與倫比的盛事。在世界各地,每天都發生成千,甚至數百萬次的這件事,看似尋常,卻是人類成就、科技文明達到極致的表徵,反映出人類在自然環境與工藝技術間領悟的奧義。曾有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的論述主張,啤酒的出現使得人類願意安家落戶,開始以務農為生──認真的定居下來,栽植穀物,從而停止了四處遷徙游牧的生活方式。
另外,當「智人」(Homo Sapiens)創造了酒精飲料,毋庸置疑的也對社會與經濟帶來了革命,促使其自身演進成為更具文明的人種。地球上人類的生活方式於焉達到頂峰。這著實是不折不扣的奇蹟。
其實總共有兩個奇蹟。第一個奇蹟是經過二億年的演進才發生的。發酵,這是個極其複雜而又驚人的奈米技術之作,過程中,一種我們稱為酵母的真菌,讓單純的糖類轉化成二氧化碳及乙醇。早在人類出現之前,發酵和乙醇就已存在。微生物與人類共生共存於地球;然而,微生物的世界裡不斷進行著我們看不見、永無休止的戰爭,戰爭中使用乙醇做為武器,對人類大腦造成的愉悅效應,則僅為其副作用。
發酵的生化作用在各種化工產業中都相當受到倚重,但它至今仍是寶貴的研究題材。畢竟就在不久之前,世上一些了不起的化學家和生物學家還不曉得它是什麼,並為此爭論不休。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證明了釀酒酵母(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啤酒酵母)具有生命,並會引起發酵作用,因此功成名就,也順勢帶動了細胞生物學的發展。從遺傳學的角度看今天的改良菌種,則仍存在不少待解謎團:它是在何時發展出製造乙醇的能力,以及人類是基於什麼原因,又是在何時才將它馴化為己所用?
人類直到大約一萬年前才開始擁有控制發酵的能力,隨即便與真菌建立起合作關係,而等到認清這位合作伙伴的真實身分時,又已經是許久之後的事了。我們的先人使用了與馴養狗與牛一樣的方法來馴化這種微生物,只為了一件事,就是製作發酵飲料。
據信,在距今二千年前左右,我們人類自己創造了第二個奇蹟:蒸餾法,混沌之初的科學家所使用最古老的設備之一。當時的煉金術士亟欲採集天地萬物菁華(靈魂,spirits)做為煉丹靈藥;然而,在冶煉過程中收集起來的蒸汽,卻意外提供了濃縮味道與香氣於液體(烈酒,spirits)的絕佳途徑,產生的液體也發展成為人類日常耗用的各種飲品。現代化學的起步就是從蒸餾法衍生而出,為人類奠定了石油經濟的基礎。
多虧了這些奇蹟,才能造就出酒吧裡的美妙時刻;從屏氣凝神輕啜的第一口,每時每秒都感受無比快樂,在享用第二杯雞尾酒當下,歡欣之情依然無可挑剔。乙醇的口感絕無僅有,當它放送出其他風味時更是別具特色。製酒是一門工藝──然而製酒師們,無論是在野火雞波本威士忌(Wild Turkey)、阿比塔啤酒(Abita)或是嘉露(E. & J. Gallo)的酒廠工作,都不需要了解分子生物學、酵母酶運動學、冶金學,或是多環芳香烴(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屬有機化學。(不過他們往往具備這些名詞背後的知識。)他們知道,蒸餾器的造型及金屬材質,與產出的酒品口感息息相關;他們也相當清楚,揀選不同木材所製的陳年用酒桶,對最後的成品風味具有關鍵影響。(比起用美國橡木桶陳年的波本酒及蘇格蘭威士忌,日本橡木桶陳年的威士忌在口感上要來得更為辛辣。很有意思,對吧?)
眾人多半以為,所謂科學就是發現新的事物。其實,科學饒富趣味之處並不在於最後的答案,而是在探討諸多仍然存疑的問題、親身參與(或閱讀)解答的過程中。在製作發酵飲品、接著加以蒸餾成為烈酒的過程裡,每一個環節背後都藏有高深的科學知識,讓許許多多的研究者想方設法努力探究。
這便是本書的主題。酒吧裡的歡樂時光,代表了人類與身處環境之間至高無上的共鳴、科技的登峰造極,以及我們對自己身體、心靈與行為進行反思的重大時刻。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應該說過:「人類文明始於蒸餾。」我認為尤有甚者──還要納入蒸餾酒、葡萄酒、啤酒、蜂蜜酒、清酒……無所不包。這是屬於杯中之物的文明。
從酵母到宿醉
接下來的章節,將是對啜飲下肚的酒精飲料做的一場由生至死的編年記述。首先我們要探討酵母菌,這是種會產生酒精的微生物,隨之而來的是分子生物學與有機化學的研究領域。然後我們討論一下糖,也就是酵母菌的食物──並且,我會說它是全宇宙最重要的分子。所以在聊到糖的時候,我們會思索農作法以及人類與植物的聯繫,回顧一下人類是如何從野生植物裡揀擇,將某些植物特別育種成農作物。再來,在糖的話題上,我還會回頭提到一個不太討喜、不太知名的微生物種,然而這物種的重要性比起酵母菌來毫不遜色。我個人特別偏愛、稱為清酒麴(koji)的真菌,若非遭逢命運反覆捉弄,很可能會是更重要的菌種。
明瞭酵母與糖的關係後,我們就可以討論發酵了,這是一堂關於酵母菌吃了糖之後排放酒精的基礎生物課。但話說回來,這裡也訴說了一個人類最早開始利用自然現象,加以操控後為己所用的例子。
接下來會談到蒸餾,人類別具匠心的創意巧思在此顯露無遺。蒸餾過程對發酵後的產物施以技術與工藝的魔法去蕪存菁,以致其搖身一變成為精煉的佳釀。發明蒸餾法之際,恰好時值人類利用技術改善生活條件的時代開啟,因此絕非偶然。這項始於古埃及煉金術士的新技術持續發光發熱、開枝散葉,廣泛應用在製藥、物理與冶金。
酒精飲料製造出來後,到達你準備享用的那一刻前,它的生命通常是在一個木桶中度過──行家稱之為「熟成」(maturation)。其間又隱藏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化學,酒桶木質中各種基本元素引起的化學反應,與桶中盛裝的液體同樣驚人。對於製酒人來說,酒品的熟成過程會影響經濟效益──因此,他們也嘗試運用科技手段來加速熟成以利銷售,其中有些作法還不錯,有些則讓人不敢領教。
接著我們會言歸正傳,繼續談我剛才說個不停的酒吧時刻,只是討論的話題從外在環境,來到了人體內部。首先,我們會提到人類感官如何面對酒精飲料的這門神奇科學,這個主題引發了神經學家與心理學家之間的終極論戰。蒸餾而來的烈酒裡有數百種氣味分子構成它的風味,然而至今還無人能夠將它們全部歸納清楚。泥煤(peat),是經由部分腐化分解的泥煤苔蘚夾雜其他植物的不完全碳化而形成,為蘇格蘭威士忌帶來煙燻和泥土的味道,但會因為開採地點的不同,而生成不同的化合物──法國葡萄酒商按照生物分子學觀點,稱其為酒的風土(terroir)。在二○一○年,美國辛辛那提州立大學的化學家(當然也是在莫斯科國立大學物理學家協助下)對幾種純度最高、成分只有乙醇及水的伏特加進行口感差異研究,結果發現乙醇與水分子間的氫鍵(hydrogen bonds)強度是造成不同口感的主因。所以,當我們從鐵錨牌荷蘭琴酒中聞到、嘗到杜松子酒的味道(就舉個令人驚訝的例子),其實背後藏有極其深奧的生物學與遺傳學玄機,而發現者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再來,要想弄清楚酒精飲料對身體與大腦產生的影響,則需要面對更加複雜的神經生物學,而在抽絲剝繭之際,還要為這杯雞尾酒加上一、兩份社會學與人類學的輔料。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人會喝醉,還有人會成癮;然而,一個世紀以來的研究一直顯示,誰也不知道原因。就此而言,沒人真的明白為什麼喝醉後會有那樣的感覺。
本書最後(你不妨當成餐後酒)會談到宿醉,是指當你不是小酌,而是喝了很多、很多,非常大量的酒後,會發生的事情。宿醉背後的科學其實不痛不癢,遠非你想像中那種會殃及許多人、感覺很惡劣的事情。事實上,直到過去這幾年才有研究人員勉強同意對宿醉做個正式的定義,所以別指望有人會真心替它尋找原因(及解方)。終於,好不容易有幾位勇氣十足的研究人員(研究主題更是英勇得令人感動)對宿醉做了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你在大學時對於宿醉的所見所聞都不正確。
《全光譜》
簡單來說,本書大致上會來來回回談到色彩在物理與心智之間的發展。人會製造具有色彩的事物,以及能夠為人事物賦予色彩的材料,後者指的就是顏料、染料、油漆、化妝品等物品。接著,人會瞭解色彩的運作原理,以及物理、化學、神經科學方面的特性。具備上述知識後,人會製造出更多色彩。光波長會改變,但在瞭解與製造之間來回擺盪的情形永遠不會變。不過,我承認,我們在接下來數百頁的篇幅中將踏上的路途,比起筆直前進,更像是迂迴前行,甚至可說是特立獨行。
我將從人類開始實驗如何製造色彩談起,這些透露出當時世界線索的色彩,誕生於十萬年前中石器時代可遮風避雨的洞窟內。目前找到最古老的顏料製作工坊便是屬於這個時代,就位在南非布隆伯斯(Blombos)洞窟之中。我會說這是一個約略的起始點,因為人類這時開始把周遭世界的自然物質轉換成製造色彩的原料——以便應用於工藝、工具、藝術。
接下來會稍微離題,探討一下生物究竟是如何(以及為何會)看見色彩。分辨各種不同的光一定具有某種演化優勢,否則如此的能力就不會遺傳至今了。這種能力大概源自於某個古老的微生物,它與地球上任何生物都有所不同,跟我們人類之間的差異則大到彼此其實可以把對方視為外星生物。透過某種方式,這些小生物把以光為食的能力,例如光合作用,轉換成靠光的顏色就能判斷海下某處是否適合覓食。以色彩具體呈現出來的光,從動力來源轉變為知識。
不過,色彩直到人類開始出現貿易行為,才成為商業的一環。最早的人類文明擁有多種顏料,懂得創作五顏六色的藝術品,探討色彩代表的意義。人與人之間的貿易在西元早期數世紀如火如荼展開時,物品上的顏色可以大幅提高其價值。中國與阿拔斯帝國之間(以及絲路沿途各處)此消彼長的貿易興衰,背後推動的力量就是色彩。絲綢當然要染色,而染料基本上是一種由材料吸收的顏料,不光只是塗在表層而已。但本書要聚焦在另一種收益來源:陶瓷,具體來說是堅薄的瓷器,以及鑽研製瓷上釉的技術是如何推動數個文明的整體發展。
事實上,這些色彩本身以及色彩從何而來是如此重要,早期科學家不得不去瞭解色彩是由什麼所構成。這個故事經常始於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接著有如穿越時空般,跳至艾薩克.牛頓(Isaac Newton)。但在希臘人與啟蒙時代之間為其中的哲學與技術斷層搭起橋梁的,得歸功於數世紀阿拉伯學者、各國譯者與創新家所做的努力,這些人讀了亞里斯多德等人的著作後表示:「嗯,這樣不對。」有像波斯科學家法利西(Al-Farisi)這樣的人,讓光穿過裝滿水的球形玻璃,好把光與物理化為實際數值,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才得以展開。
少了啟蒙運動以及從科學角度瞭解世界的意識崛起,色彩學在十八、十九世紀就不會有活絡興盛的光景。正是在這個時期,眾人開始研發新顏料,製造出世上前所未見的色彩,並發明新方法,複製圖像,加以利用。同一個時代的人也終於明白眼睛感知色彩的原理,進而為現代物理學揭開序幕。
即便人類開始創造出愈來愈多的合成色彩,白色依然獨樹一格,不論是在化學性質上,還是象徵意義上皆然。其中鉛白這種顏料,從古埃及與羅馬帝國興盛時期開始便舉足輕重,毒性也可怕至極。
一八九三年,在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無色全白與下個世紀鮮明多彩的不和諧混雜,兩者間千年來的來回擺盪,到達了衝突最高潮。人們口中所謂的「白城」(White City),由當時的頂尖建築師與規劃師設計打造,仰賴的全是無趣的圓柱、殿堂、白色——不只是外觀,還包括種族。但其中一座建築物,也就是多色的運輸建築館(Transportation Building),鶴立雞群。這棟建築是由其中一位摩天大樓之父路易斯.蘇利文(Louis Sullivan)所打造,也是一項色彩理論的成果,其概念源自人腦是如何整合所見資訊的新科學。
一切都各就各位了。科學理論有了,需求也出現了。在工業革命的鼎盛時期,名為奧古斯特.羅西(Auguste Rossi)的工程師將會努力研究該如何利用由尼加拉瀑布發電的電爐,用鈦製造出更好的鋼合金——這真是十足的美國作風。這一切將徒勞無功,但在鑽研期間,他會發覺其中一種副產物可以當成白色顏料,也就是白得透亮的二氧化鈦粉末。不出數十年,這種白色粉末將主宰整個顏料製造業;如今,它依然獨占鰲頭。
二次大戰後,在世界各地大規模生產的顏色與色彩繽紛的物品開始激增,但一個難解之謎也隨之浮上檯面:每個人眼中所見的色彩都各有不同。不是每個人都以相同的字眼來表達相同的色彩,這個差異不只出現在人與人之間,也體現在文化與文化之間。不過,隨著色彩學和新顏料更普及,大家開始清楚瞭解到,一般人如何看見與感知色彩的這個謎團,一部分跟人使用什麼詞彙來形容色彩有關。於是,在一九七○年代,語言學家保羅.凱伊(Paul Kay)與人類學家布倫特.柏林(Brent Berlin)派調查人員前往世界各地,想瞭解大家是如何談論色彩,兩人的成果至今依然是瞭解人類環境界(譯註: Umwelt,德文「周遭世界」之意)的關鍵。我們已經證實,色彩這項工具不只改變了靠技術革新而帶來進步的世界,也能用來瞭解語言和認知的內在世界。
這方面的研究甚至深入擴及至大腦與心智:神經生理學家在二十世紀中葉便展開研究,想釐清人類腦袋中的那團黏糊糊肉塊是如何把光轉換成色彩的概念,相關研究目前仍在進行。這個科學領域依然相當振奮人心,我這麼說的意思其實是,目前尚未有人徹底瞭解背後的原理。而證明這個科學領域尚待研究的最佳證據之一,出現在二○一五年,當時,單單一張藍色連衣裙(是藍的,不是白的,好嗎?)的彩圖就讓全世界分成兩派。由於網路已經深入每個口袋與包包,隨處可見的高畫質螢幕讓人人都有辦法重新創造出色彩近乎無限的調色盤。但這種創造色彩的全能能力,受到一張在傍晚時分拍下,並導致眾人意見兩極的藍色連衣裙照考驗後,顯示出每個人對這種無限色彩都各有看法。解構分析這件事,或許也能讓科學家瞭解眼睛和大腦究竟是如何運作,才得以在周遭環境的色彩改變時,為我們打造出一個色彩恆常的世界。
這也將為色彩科技帶來未來發展的契機。多虧數位投影機與先進3D列印機的協助,調色師正在讓各種既有色彩煥然一新,並使得新舊色彩難以區別。瞭解眼睛是如何解讀色彩,又是如何維持對各種色彩的概念,得以讓藝術品修復師挽救抽象派畫家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即將毀損的油畫作品,也可以讓人印出幾可亂真的藝術仿作——即便只有如黑箱作業般的人工智慧曉得其中的運作原理。
現今,所有螢幕、所有眼睛、所有大腦全都合力要創造出不可能出現的色彩,以及一種不單純是光譜,還能羅列情緒的頻譜。祕訣可能就在於亮度,也就是光影間的差距,其中一個極端仿自亮到不行的甲蟲,另一個則是所謂的超級黑顏料,導致現代藝術界四分五裂。皮克斯(Pixar)動畫工作室的色彩高手動畫師則橫跨在光影間的那條線上,透過目前所能打造的最先端科技,創造出只見於特殊銀幕上的色彩……也許有一天,他們運用雷射與編碼,就能喚起只存在於觀眾腦中,卻完全不屬於銀幕上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