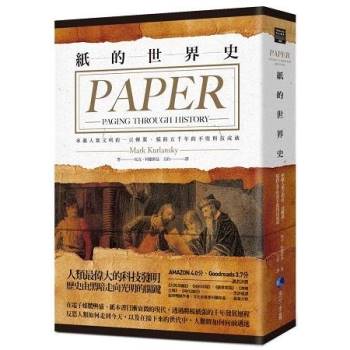前言 科技的謬論
十二世紀時,法國克呂尼修道院(Cluny monastery)正直又虔誠的僧侶彼得尊者(Peter the Venerable)造訪西班牙,看到當地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不在獸皮上書寫,而是連宗教經文都寫在以舊衣製成的頁面上,其品質在今日文具商口中不啻「不折不扣的破紙頭」。他視之為不言可喻的落後社會象徵。
綜觀歷史,科技的任務和人們對科技的反應一直都格外一致,因此憂心科技與其對社會的影響的那些人,不妨對紙的歷史好好反省一番。
我們習以為常,認為「科技」僅指物質器具、十九世紀時期的機械,乃至於現在電子的發展。殊不知,根據《韋氏詞典》(Merriam-Webster’s dictionary),這個字眼也能指稱任何「實用的知識應用」。
需求永遠是科技發明之母。在紙張之前,有無數的發明產物;首先是口說語言 ,接著是繪畫,爾後圖形文字,再來字母,然後拼音,之後寫字,接下來紙張。有紙之後方有刻版打印、活字版、打字機、機械式印刷機,然後電子的文書處理機和電子印刷機應運而生。需求一現,立見解決之道。每一個想法又引發另一個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最初的那些發明(口語而後文字)皆非物質產物、非人造物,因此按照傳統的認知,也非「科技」。然而,它們在社會和歷史上的運作和影響卻無異於科技──是創始的科技。口語是車輪,最終通往紙大車。
研究紙的歷史暴露出一些歷史上的錯誤觀念,其中最嚴重的就是這個科技謬論:以為是科技改變社會。實則恰恰相反。社會發展科技是為了表述它正在發生的變化。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西元前二五○年,中國的蒙恬發明了以駱駝毛 製成的毛筆。他的發明並未突然激發中國人開始寫字、畫畫,或是發展出書法。相反地,中國的社會早已建立一套書寫系統,只不過也已經對更多書寫的文件和寫出更精緻的書法,需求愈來愈迫切。中國人之前使用的用具,用小樹枝沾墨汁,無法滿足這項日益增長的需要。蒙恬發現了一種能夠既加快寫字和書法,又大幅提高品質的用具。
歷史上,研究紙的編年史家們總愛為紙的角色發出這樣的豪語:沒有紙就沒有建築;沒有紙,就沒有文藝復興。假如世上沒有紙,也不可能會有工業革命。
這類聲明沒有一個是真的。這些發展之所以能誕生,是因為社會已經進展到一個它們被需要的時間點。對於所有的科技,都是如此,但是在紙這個例子上又特別明顯。
依學者之見,中國人曾是唯一懂得製造紙的民族;雖然中部美洲民族 也可能會,但由於它的文化遭受西班牙人破壞,我們無法確知。在不同時期裡的不同文化當中,當社會演變發展出對它的需求時,而環境也需要一種實惠又便於書寫的材料時,紙就會派上用場。
中國官方開始廣泛用紙後五百年,高麗佛僧們也開始對紙產生需求。他們採用了中國的工法,並把它帶到日本以便傳教。數個世紀之後,早已非常擅長算數、天文學、會計和建築的阿拉伯人正視到紙的需求,便開始造紙,並在中東地區、北非和西班牙廣泛加以使用。
歐洲人最初用不著紙,直到中國人發明紙之後一千多年才改觀。不過,並非只是因為他們發現了紙的存在。阿拉伯人多年來一直想賣紙給他們,但要等到歐洲人開始學習阿拉伯人的算數和科學並普遍識字時,發現原先使用的書寫材料,獸皮製造的羊皮紙變得太慢又太貴,不敷快速成長的需求,情況才有了轉變。
腦力工作與政府官員的增長,加上思想傳播與商業蓬勃,都促進了紙的製造。然而它在全球的成長卻是個非常緩慢的過程。印刷機、蒸汽機、汽車和電腦傳遍全世界的時間,都遠比紙更短。
紙不太像是個發明──把木頭或布料弄碎取得「纖維素纖維」(cellulose fibers),用水加以稀釋,然後將溶液用篩網過濾,使之任意編排形成一大片,這不是邏輯就能想得到的主意,尤其是在無人知道何謂纖維素纖維的年代裡。它也不像印刷是顯而易見的下一個步驟,各個社會都能各自獨立發展出來。要是沒有人想到紙呢?也會有其他材料被找出來;因為社會的需要要求它,所以必須要找到優化的書寫材料。
科技史還教導了我們其他的重要課題,以及其他常見的謬論。其一是,新科技會淘汰舊的。這幾乎沒有發生過。紙張問世後數百年,莎草紙仍存在於地中海一帶。羊皮紙現在還在使用中。瓦斯和電熱器的問世從不曾意味著壁爐的末日,印刷術並未消滅書法,電視機沒有消滅廣播,電影沒有消滅舞台劇,家用錄影帶沒有消滅電影院,雖然這一切都曾遭到錯誤的預測。電子計算機未曾終結算盤,而且,當愛迪生在一八七九年因為成功推出商品化電燈泡而榮獲專利之後一百多年,今天單單在美國仍有四百家蠟燭製造商,大約七千名員工,每年創造超過二十億美元的銷售量。事實上,二○一○年代的蠟燭銷售量還是成長的,雖然使用蠟燭的方式當然大大改變了。類似情況也發生在羊皮紙的生產與使用方式上。新科技,非但沒有淘汰舊科技,還反而增加了選擇性。電腦無疑地將會改變紙的角色,但是紙絕無可能被淘汰。
科技史同時也證明,反新科技的盧德主義人士 穩輸不贏。原先的盧德主義人士是十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的手藝工匠,他們起而抗爭是因為,熟練的差事被毋須經驗、工資較低的操作機器活兒所取代。最初,抗爭運動在各行各業獲得熱烈響應,包括印刷業在內。但是到了一八一○年代,這個運動大部分只集中在紡織業。支持者被稱為「盧德」原因不明,只知道十八世紀時有一名叫盧德的反機器叛亂分子,像羅賓漢,住在雪伍德森林 。盧德主義人士反對織布機這類科技產物,他們攻擊磨坊、砸爛機器並向英國軍隊開戰。有一位磨坊主人甚至遭到刺殺,該事件催生了一八一二年制訂了「限制破壞法」(Frame Breaking Act),破壞機器將判以死罪。最後這項法令也帶來砸壞機器所衍生出的大量審判。
如今,盧德這個詞被用來形容反對新科技的人。那些抵抗使用電腦的人可謂得了盧德之輩的真傳,因為當初盧德們反對的紡織機,只要透過打孔卡片 ,就能設定機器織出各式各樣圖案,正是電腦的早期機械式先驅。
在影響深遠的《資本論》書中,馬克思說盧德主義者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們反對的是機器而非社會。他觀察到:「盧德派的錯誤是他們難以分辨機器和資本受雇者的不同,所以無法直接去攻擊他們被對待的模式,只能攻擊生產的物質性工具。」
換言之,聲討科技本身是毫無意義的。相反地,你必須去改變的,是創造出科技的社會運作方式。每一項新科技產物都會有人不以為然,那些人認為新發明會毀掉舊產物的一切好處。這樣的詆毀也發生在文字開始要取代口語時,在紙張開始要取代羊皮紙時,在印刷開始奪走手抄時──至今仍屢見不鮮,譬如電子書威脅紙本書。在所有這些案例當中,非議新科技的論點都很相似:將危害到人類大腦的運作,我們會失去記憶力,人的接觸會減少,人的交流溫暖會喪失。
這些強烈反對科技的早期聲浪大多無人理會,一如現在對電腦的警告被置若罔聞。說真的,給記憶力愈多輔助,我們會愈少依賴我們的大腦。但那不表示我們的心智就會遭到破壞。文盲人士比識字之輩擁有更好的記憶力,但幾乎沒有人會用這個理論來支持文盲的存在。文字世界的到來,證明了這些輔助雖然會使我們更依賴,卻也同時讓我們能力更強。
你無法發出警告,說某個新科技將會對某個社會做什麼,因為那個社會早已有了改變。這是馬克思對盧德派所持的論點。科技只不過是催化劑。社會有了變革,而那個變革創造了新的需求。那也是科技應運而生的原因。阻止新科技的唯一方法,只有逆轉社會的變遷。印刷術並未促成宗教改革,而是傳播宗教的想法和意願創造出印刷機。中國官方和佛教僧侶並不是紙所創造出來的。紙是為他們而創造的。
爭辯某個科技以某種方式改變了社會,無疑是說某個科技會徹底改變社會的趨勢。但這件事情根本從沒發生過。意圖改變社會趨勢的科技產物通常都會一敗塗地。事實上,大多數科技公司並沒有推出新科技,而是對已存在的概念提出新用法。它們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做市場調查,也就是,確定社會已經想要發展的去向。一旦確定了這個趨勢,它們只不過是量身打造出一項新產品去滿足那個需求。
並不是所有科技都有前途。有些科技在變化中的社會能立足,有些卻狼狽不堪。即使想法是對的,問世的機器卻未必行得通。蔡倫並沒有發明紙,古騰堡並沒有發明印刷機,富爾頓 並沒有發明汽船,愛迪生並沒有發明燈泡。相反地,這些都是人們把不符合社會需求的現成概念或機器,重新改造成能滿足需求的科技產物。這說明了我們的世界鮮少會記得想到某個點子的人,卻會將把它商業化的實用主義家奉為典範。我們都忘了創造大多數關鍵電腦概念的人,卻把光環戴在靠它們致富的人頭上。
另一個重大教訓是,經年累月之後科技產物通常變得比較便宜,同時也更易取得但品質較差。如今紙遠比以前便宜很多,但是,十八世紀的紙卻比十九世紀的品質好,而十九世紀的紙又比現在的品質更好。
有超過一千年之久,造紙術被視為文明的象徵:所謂先進的文明就是必須懂得造紙。一五○四年當西班牙征服者科提茲(Hernán Cortés)抵達新世界時,他對阿茲特克人感到驚異萬分。阿茲特克人建造了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城市,而且數學和天文學十分進步,不過最讓科提茲印象深刻的是造紙的能力。對西班牙人來說,一個能造紙的社會就是先進文明。
把紙視同文明象徵,會得出令人驚訝其迥異但頗正確的歷史畫面。在這個歷史版本裡,文明始於西元前二五○年的亞洲,然後傳播到阿拉伯世界。有數百年之久,阿拉伯人曾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而歐洲人則是地球上最落後的民族之一。歐洲人不識字、沒有科學,連簡單的算數都一竅不通;甚至在買賣記帳時都不用紙。這群「蠻族」在西元五世紀時消滅了羅馬帝國,到了十一世紀卻依然還是「蠻族」。
如今大部分歷史學家都強調「黑暗時期」並不真如史載所說那般黑暗。但不容辯駁的是,歐洲人在很多方面遠遠落後亞洲人與阿拉伯人。基督徒的智識水準不及穆斯林和猶太人。當基督徒占領穆斯林所統治的西班牙時,這點尤其明顯;他們破壞穆斯林安達魯斯(al-Andalus)的文化,而且,在墨西哥有計畫地破壞世界上最進步的文化之一時,他們查禁當地語言、宗教和文化,還焚毀書籍。
等到歐洲終於開始發展時,並沒有如當今許多人臆測那樣按照地理順序。義大利從南部往上發展,始於西西里。愛爾蘭的發展早於英格蘭。同時,歐洲大多藉助於採用阿拉伯的想法獲得進步,特別是在數學、科學和會計等領域。稍晚之後,歐洲在歷史上能跨步躍進超越了競爭對手阿拉伯和亞洲,全拜中國人發明的活字版所賜。不像亞洲人和阿拉伯人,歐洲人之所以能好好利用那項發明,是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拼音文字特別適合活字版。這也表示,歐洲人得以想要歷史怎麼發聲就怎麼寫歷史。
★
從有大量宗教擁有神聖經文,而且多數宣稱經文出自神的親筆,也可窺見文字的重要性。埃及人相信,是䴉首人身、眾神的抄寫員托特(Thoth)給了人類書寫的天賦。對於亞述人而言,則是書寫神拿布(Nabu)的恩賜。馬雅人相信,是造物主的兒子伊茲沙瑪(Itsama)發明了寫字和書籍。紙未發明之前,神聖經文寫在各種材料上廣為流傳,有一些至今仍維持手寫在獸皮上的形式,例如猶太律法書 。
不過值得銘記在心的是,儘管在宗教與文化、科學與數學上很重要,但不論過去或現在,科技發明最大的推手之一,都是對金錢的追求。文字、紙、電腦全都是為了促進商業蓬勃而開發出來的。
在大名鼎鼎的《技術的追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書中,作者海德格 斷言科技是「一種為達目的的手段」,並進一步聲稱「科技是一種解蔽的方式」。
根據海德格的說法,想了解這個,我們就必須探問促使科技發展的原因是什麼。所有的科技都始於一個原創的聰明想法。從這樣的意義來看,那麼輪子是原創的偉大點子,汽車是進一步的探索。而紙,同樣是從一個偉大的原創發明──文字──發展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