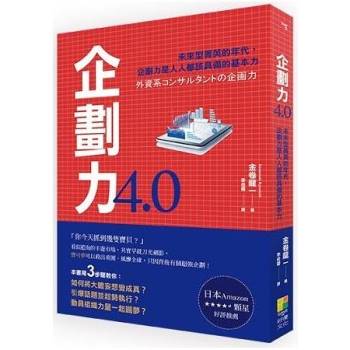◇營運策略要制定在「現今的前提」下
自古就存在的企業,一定是制定了正確營運策略並確實執行的企業,所以才能傳承至今。而且,制定營運策略必須先分析當時面臨的狀況,並且依據某種前提(圖4-1)。換句話說,當經營環境發生變化,勝利方程式失去效用時,企業就必須制定新的營運策略。可惜的是,多數企業遇到策略需要調整的時候,大都忘不了過去的成功經驗,無法痛下決心著手改變。
例如:經常被視為營業改革指標的「面對面時間」。它的意思是,在每天的工作時間中,有多少時間面對顧客。一般認為面對面的時間愈長,營業額愈高,但我認為這種面對面時間至上的營業改革已經不適用。
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之間,日本做到了令人驚異的經濟成長。一個全世界資源最為匱乏的國家,竟然創造出世界屈指可數的繁華景況。每年的GDP都有兩位數的成長。就像是今年原本只有一百位顧客,到了明年會自動增加成一百一十位顧客似的,於是為了攻城掠地,爭取新增加的那十位顧客,必須不眠不休地拜訪顧客。那是一個需要多於供給、「加班會變成金錢」的時代。在業務部門,坐守辦公室被視為懶惰的行為,所以從早到晚都得在外面跑客戶。
當時前來日本拜訪的外國人,在丸之內看到每個人在路上都用跑的,還為此驚訝不已。當年的業務勝利方程式,確實是增加與顧客接觸的時間。然而,現在的勝利方程式還和過去一樣嗎?日本的高度成長期早已結束,顧客已經成熟且懂得利用情報了。網際網路的誕生與普及,讓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進行交易,或是利用電子郵件或SNS瞬間傳遞情報。於是無論如何頻繁地拜訪顧客,一般的情報已吸引不了顧客的注意,若再缺乏精闢的洞察力和新發想,更難讓顧客買帳。更何況沒什麼事還每天前來拜訪,只會造成顧客極大的困擾。
換句話說,執著或盲目信仰過去的勝利方程式,很可能造就今日的問題。
•現在的常識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時代的哪種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當時的「前提」是什麼?
•現在是否有足以動搖該前提的驅動改變因素?如果有,新的前提又是什麼?值得注意的是,就新的前提來「修正」建立在舊有前提下的策略,並無多大意義(圖4-2)。例如:汽車的引擎。以前的馬力和扭力大小是決定引擎好壞的最大因素,但現在出現了「環境問題」這個驅動改變的因素,使得衡量尺度變成燃料費或是低汙染了。這時是否要針對既有的引擎,調查燃料費及CO2的排放量問題,然後徹底修正設計呢?這麼做只會受限於前一個時代的設計思維,最後製造出不理想的產品而已。
一般的做法一定是針對新的時代,以這個例子來說,就是把燃料費和低汙染作為第一考量,用全新的概念重新設計引擎。然後,如果自家公司尚未完全精通該項新技術,就調查看看有沒有哪家公司已經迎合新時代,設計出全新的引擎,再研究該引擎的結構。在經營的世界裡,這種做法叫做最佳實務。然而近年來,實例和最佳實務已變成了同義詞,實在是件可惜的事。在意識到時代的潮流,也就是驅動改變的因素後,能最快順應新時代的遊戲規則,並向外揭示成功結果,才真正配得上最佳實務的稱號。
討論解決對策是有趣的過程。但是,未討論前提就直接討論解決對策,是非常危險的事。首先要把時代變化當作「前提的變化」來思考。
◇比起創造雙贏,讓敵對方理解、認同更重要
身處在商業世界,最讓人頭痛的就是,單靠自己一個人什麼都做不成,只能利用周遭專家和組織的資源來達到目的。所謂利用周遭的人,就是讓不同立場的人和不認識的人(有時甚至是敵對關係的人)都來幫助自己。為此,必須先讓對方「願意理解」、「願意贊成」自己的想法。不時有人把「創造雙贏(Win-Win)局面」掛在嘴上,但實際上,要在組織裡實現這件事並不容易,多數時候都必須考慮交織在組織內部的種種情感,彼此互相協調。
「協調」兩字總給人一種消極的感覺,它讓人聯想到擷取眾人意見中的相同部分,予以彙整,以求取意見的最大公約數。想要求得前所未有的新發想,卻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認同,根本是糟蹋了企劃。所以要做的並不是協調,而是說服,營造出對方的認同感。世上根本沒有哪個點子是所有人都贊成的,就算有,那也是任何人都覺得「理所當然要做的事」。假設贊成和反對的人數各佔一半,這對自然科學來講是平等局面,但是在人文科學的世界就不是這樣了。因為贊成的人裡面,有些人是不表示意見的「同意」,但反對的人卻幾乎都是有「意見」的。其中,有些人覺得用以前的那種做法還不是成功了,根本不需要改,因為對反對的人來說,光是做出改變這件事,就會叫人產生極大的抗拒。所以反對勢力會比預期還要強烈。
當我在全球性的外資企業裡工作時,曾經上過一堂讓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研修課程,叫做「領導能力研修課」。當年的我既年輕又傲慢,覺得光聽課堂名稱就知道內容大概是什麼,對那堂課沒有半點興趣。勉為其難去上了課之後,我的世界觀從此變得完全不一樣。那堂課的主題是介紹經理人和領導人的不同,這兩種人雖然完全不同,卻都是組織需要的人才。
結論就是:經理人是組織賦予「權限」,可以用「指示或命令」驅使人去做事;領導人則是獲得了身邊人的「認同」,用「理解和感動」驅使人去做事。過去不管面對什麼事,我都覺得「自己沒有權限去做」,現在我明白了這是錯誤的想法。
等待被賦予權限只會虛擲光陰,何況等得再久,也不保證可以獲得權限。從此以後,我不再考慮自己有無權限,而是去思考要怎麼做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同並付諸執行。與此同時,我也才明白,混合了各種人種、語言、文化與宗教的全球性企業,為了能不斷地改進與成長,內部也和日本企業一樣,都存在一個組織圖上所沒有的改善機制。
當然,企業裡的高層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產生認同與感動,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讓他們「認識」自己的發想。這時不能只是單純地讓他們知道而已,同時也要有條理地表達出發想帶來的利益,然後再整理一份最後能帶來利益的流程圖及評價指標。如果能妥善考慮最適合整體利益的內容,且所有相關人員都能正確了解該內容,個別問題就會變小,就連龐大的山也可以緩緩移動起來了。這一連串的設想安排,正是構想的樂趣所在。
自古就存在的企業,一定是制定了正確營運策略並確實執行的企業,所以才能傳承至今。而且,制定營運策略必須先分析當時面臨的狀況,並且依據某種前提(圖4-1)。換句話說,當經營環境發生變化,勝利方程式失去效用時,企業就必須制定新的營運策略。可惜的是,多數企業遇到策略需要調整的時候,大都忘不了過去的成功經驗,無法痛下決心著手改變。
例如:經常被視為營業改革指標的「面對面時間」。它的意思是,在每天的工作時間中,有多少時間面對顧客。一般認為面對面的時間愈長,營業額愈高,但我認為這種面對面時間至上的營業改革已經不適用。
一九六○年到一九七○年代之間,日本做到了令人驚異的經濟成長。一個全世界資源最為匱乏的國家,竟然創造出世界屈指可數的繁華景況。每年的GDP都有兩位數的成長。就像是今年原本只有一百位顧客,到了明年會自動增加成一百一十位顧客似的,於是為了攻城掠地,爭取新增加的那十位顧客,必須不眠不休地拜訪顧客。那是一個需要多於供給、「加班會變成金錢」的時代。在業務部門,坐守辦公室被視為懶惰的行為,所以從早到晚都得在外面跑客戶。
當時前來日本拜訪的外國人,在丸之內看到每個人在路上都用跑的,還為此驚訝不已。當年的業務勝利方程式,確實是增加與顧客接觸的時間。然而,現在的勝利方程式還和過去一樣嗎?日本的高度成長期早已結束,顧客已經成熟且懂得利用情報了。網際網路的誕生與普及,讓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進行交易,或是利用電子郵件或SNS瞬間傳遞情報。於是無論如何頻繁地拜訪顧客,一般的情報已吸引不了顧客的注意,若再缺乏精闢的洞察力和新發想,更難讓顧客買帳。更何況沒什麼事還每天前來拜訪,只會造成顧客極大的困擾。
換句話說,執著或盲目信仰過去的勝利方程式,很可能造就今日的問題。
•現在的常識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時代的哪種背景下建立起來的?
•當時的「前提」是什麼?
•現在是否有足以動搖該前提的驅動改變因素?如果有,新的前提又是什麼?值得注意的是,就新的前提來「修正」建立在舊有前提下的策略,並無多大意義(圖4-2)。例如:汽車的引擎。以前的馬力和扭力大小是決定引擎好壞的最大因素,但現在出現了「環境問題」這個驅動改變的因素,使得衡量尺度變成燃料費或是低汙染了。這時是否要針對既有的引擎,調查燃料費及CO2的排放量問題,然後徹底修正設計呢?這麼做只會受限於前一個時代的設計思維,最後製造出不理想的產品而已。
一般的做法一定是針對新的時代,以這個例子來說,就是把燃料費和低汙染作為第一考量,用全新的概念重新設計引擎。然後,如果自家公司尚未完全精通該項新技術,就調查看看有沒有哪家公司已經迎合新時代,設計出全新的引擎,再研究該引擎的結構。在經營的世界裡,這種做法叫做最佳實務。然而近年來,實例和最佳實務已變成了同義詞,實在是件可惜的事。在意識到時代的潮流,也就是驅動改變的因素後,能最快順應新時代的遊戲規則,並向外揭示成功結果,才真正配得上最佳實務的稱號。
討論解決對策是有趣的過程。但是,未討論前提就直接討論解決對策,是非常危險的事。首先要把時代變化當作「前提的變化」來思考。
◇比起創造雙贏,讓敵對方理解、認同更重要
身處在商業世界,最讓人頭痛的就是,單靠自己一個人什麼都做不成,只能利用周遭專家和組織的資源來達到目的。所謂利用周遭的人,就是讓不同立場的人和不認識的人(有時甚至是敵對關係的人)都來幫助自己。為此,必須先讓對方「願意理解」、「願意贊成」自己的想法。不時有人把「創造雙贏(Win-Win)局面」掛在嘴上,但實際上,要在組織裡實現這件事並不容易,多數時候都必須考慮交織在組織內部的種種情感,彼此互相協調。
「協調」兩字總給人一種消極的感覺,它讓人聯想到擷取眾人意見中的相同部分,予以彙整,以求取意見的最大公約數。想要求得前所未有的新發想,卻又希望得到所有人的認同,根本是糟蹋了企劃。所以要做的並不是協調,而是說服,營造出對方的認同感。世上根本沒有哪個點子是所有人都贊成的,就算有,那也是任何人都覺得「理所當然要做的事」。假設贊成和反對的人數各佔一半,這對自然科學來講是平等局面,但是在人文科學的世界就不是這樣了。因為贊成的人裡面,有些人是不表示意見的「同意」,但反對的人卻幾乎都是有「意見」的。其中,有些人覺得用以前的那種做法還不是成功了,根本不需要改,因為對反對的人來說,光是做出改變這件事,就會叫人產生極大的抗拒。所以反對勢力會比預期還要強烈。
當我在全球性的外資企業裡工作時,曾經上過一堂讓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研修課程,叫做「領導能力研修課」。當年的我既年輕又傲慢,覺得光聽課堂名稱就知道內容大概是什麼,對那堂課沒有半點興趣。勉為其難去上了課之後,我的世界觀從此變得完全不一樣。那堂課的主題是介紹經理人和領導人的不同,這兩種人雖然完全不同,卻都是組織需要的人才。
結論就是:經理人是組織賦予「權限」,可以用「指示或命令」驅使人去做事;領導人則是獲得了身邊人的「認同」,用「理解和感動」驅使人去做事。過去不管面對什麼事,我都覺得「自己沒有權限去做」,現在我明白了這是錯誤的想法。
等待被賦予權限只會虛擲光陰,何況等得再久,也不保證可以獲得權限。從此以後,我不再考慮自己有無權限,而是去思考要怎麼做才能得到別人的認同並付諸執行。與此同時,我也才明白,混合了各種人種、語言、文化與宗教的全球性企業,為了能不斷地改進與成長,內部也和日本企業一樣,都存在一個組織圖上所沒有的改善機制。
當然,企業裡的高層不是那麼容易就能產生認同與感動,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讓他們「認識」自己的發想。這時不能只是單純地讓他們知道而已,同時也要有條理地表達出發想帶來的利益,然後再整理一份最後能帶來利益的流程圖及評價指標。如果能妥善考慮最適合整體利益的內容,且所有相關人員都能正確了解該內容,個別問題就會變小,就連龐大的山也可以緩緩移動起來了。這一連串的設想安排,正是構想的樂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