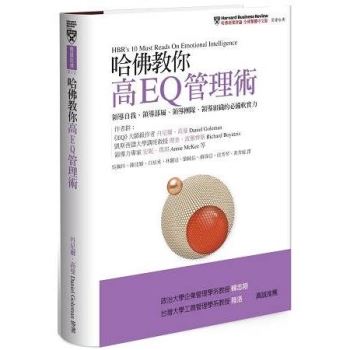公平為什麼這麼難
Why It’s So Hard to Be Fair
每個人都知道,維持公平是成本最小、但成效卓著的做法,那麼,為什麼即使大多數人都希望得到公平待遇,高階主管在行事作為上,還是極少表現出公平的一面?
喬爾.布羅克納 Joel Brockner
當A公司決定裁員後,便支出大筆費用,為被解雇的員工提供安全保障,遣散方案包括好幾個星期的工資、大量的就業諮詢,以及最多長達一年的健康保險。然而,高階主管從不解釋為什麼裁員是不可避免的,也沒說明他們如何決定裁撤哪些工作。除此之外,許多負責傳遞裁員訊息給被解雇員工的中階主管,也處理得相當笨拙,只是敷衍地丟出一句「並不想這麼做」,就把燙手山芋扔給人力資源部門。即使是留任的員工,也無法認同這樣的處理方式。許多人在星期五開車回家的路上聽到這個消息,卻必須等到星期一,才能確定自己是否保住飯碗。直到九個月後,該公司仍必須不斷解釋這件事。公司不僅花費大筆法律費用,來處理不當解雇的訴訟,還必須進行另一波裁員,這主要是因為沒有妥善處理第一波裁員,導致員工生產力與士氣低落。
相反的,B公司裁員時,並沒有提供跟A公司一樣優渥的遣散方案,但B公司的資深經理人在實際裁員之前,就曾多次解釋這麼做的策略目的,而且高階與中階主管都隨時願意回答員工提出的問題,並對離職與留任員工表達他們的遺憾。部門主管與人力資源部門一起通知員工,他們的工作要被裁撤,在傳達這個訊息時,真誠地表達擔心。結果,沒有任何員工提起不當解雇訴訟。留任員工花了一些時間,來適應失去部分同事的事實,但都了解為何要裁員。在不到九個月之後,B公司的績效超越裁員之前的表現。雖然A公司在重整期間花費較多金錢,但B公司的流程公平性(process fairness)較高。換句話說,B公司員工相信自己受到公平對待。在面對與組織或人員有關的許多不同類型挑戰時,流程公平性都能帶來巨大的額外好處,從盡量降低成本到強化績效都包括在內。根據研究,當經理人執行流程公平性,員工回應的方式會直接或間接提升組織獲利。舉例來說,流程公平性讓新策略較容易獲得支持,也可以孕育出鼓勵創新的文化,而且,執行時不需要耗費太多成本。簡單來說,公平的流程極符合商業利益。既然如此,為何不見更多企業持續執行流程公平性?本文將檢視這個矛盾現象,並提出建議,讓你的組織提高流程公平性。
公平流程背後的邏輯
某個決定是否公平,最終還是要由每位員工自己決定。但一般來說,流程公平性有三大驅動因素。第一,員工認為自己參與了多少決策過程:是否有人徵詢並認真考量他的意見?第二,員工認為決策是如何制定與執行的:決策是否一致?決策是否基於正確資訊?錯誤是否可以修正?決策者是否盡量減少個人偏誤?事前是否充分告知?決策過程是否透明?第三,經理人如何執行:他們有沒有解釋為什麼做這樣的決策?他們是否尊重員工,主動聽取員工的考量,並理解員工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流程公平與結果公平(outcome fairness)不同,所謂的結果公平,是指員工對他們與公司交易後的最終結果作何判斷。流程公平並不保證員工能得到想要的結果,而是表示員工的意見有機會被聽見。舉一位與升遷擦身而過的員工為例。若他相信,獲得升遷的那位員工很適任,而主管也曾與他坦誠討論要如何做更好的準備,以爭取下次的升遷機會,那麼,這位員工的生產力與投入程度,可能會高過若是他認定升遷的那位是上司愛將,或是主管沒有給他任何努力方向的情況。當員工覺得被公司傷害,往往會展開報復,這麼一來,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1990年代中期,由杜克大學(Duke)的亞倫.林德(Allan Lind)和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的傑拉德.格林伯格(Jerald Greenberg)領導的一項針對近一千人的研究發現,員工是否會對不當解雇提出告訴,有一項主要決定因素,那就是員工對於解聘過程是否公平執行的觀感。認為自己受到高度公平對待的離職員工,只有1%會提起不當解雇的訴訟,相形之下,那些認為過程中未獲高度公平對待的前員工中,有17%會提起訴訟。如果把這些數據換算成金錢,以公平流程對待解聘員工,預期每裁員一百名員工就可省下128萬美元的成本。這個數字是根據1988年法律辯護成本是八萬美元來計算的,這是保守的估計,因為光是考慮到通貨膨脹,現在成本就已上漲到12萬美元。因此,縱然無法精確計算執行公平流程的財務成本,但至少可以說,對離職員工表達真誠的關懷,並以有尊嚴的方式對待他們,付出的代價將遠低於不這麼做。
同樣地,如果顧客認為自己在過程中獲得公平對待,也較不會對服務提供者提出訴訟。1997年,醫學研究人員溫蒂.萊文森(Wendy Levinson)與同事進行的研究發現,病患通常不會只因為醫療照顧不良,就告醫生醫療疏失,更重要的因素,在於醫生是否有花時間解釋治療做法,並耐心回答病人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以公平的流程來對待病人。至於那些沒這麼做的醫生,較可能在發生問題時,面臨醫療疏失的訴訟。
除了降低法律成本,流程公平也會降低偷竊率與流動率。管理與人力資源教授格林伯格的研究,檢視了兩家製造商如何處理減薪問題。其中一家製造商的副總裁,在一週工作結束時召開會議,並宣布所有員工將全面減薪15%,為期十週。他很簡潔地解釋原因、感謝員工,並回答幾個問題;整個過程在15分鐘內結束。另一家製造商實施一模一樣的減薪,不同的是由總裁對員工宣布。他告訴員工,他們已考慮過裁員等其他降低成本的選項,但減薪似乎是最不痛苦的選擇。總裁花了一個半鐘頭來回應員工的問題與擔憂,而他也一再表達遺憾不得不走上這一步。格林伯格發現,在減薪的十週期間,第二家公司的員工偷竊率較第一家低80%,而第二家員工辭職的可能性,也只有第一家的15分之1。許多高階主管喜歡先用錢來解決問題,但我的研究顯示,企業若是常態性實施流程公平,就可以降低費用。試想:問員工對某項新計畫的意見,或是向員工解釋你為什麼把某項工作交給他的同事,這樣做其實沒有什麼成本。當然,公司也應持續對員工提供具體的協助,但實施公平的流程,可讓公司在節省支出之餘,仍維持高度的員工滿意度。
想像一下外派人員若提早放棄他們的海外任務,會造成何種財務後果。一般認為,外派人員或他們的家人若無法適應新環境,就可能提早離開,因此,企業通常選擇付出高額成本,來協助外派人員度過調整期,像是支付房租、小孩的學費等。人力資源顧問榮恩.蓋隆茲克(Ron Garonzik)、羅格斯商學院(Rutgers Business School)教授菲莉斯.希格(Phyllis Siegel)和我,在2000年針對128位外派人員所作的研究發現,外派人員只要認為上司對待自己大致公平,那麼,對工作之外各種生活面向的適應程度,並不會影響他們是否提早離職的意願。換句話說,外派人員即使對住在國外並不特別感興趣,流程高度公平仍會吸引他們持續執行海外任務。
同樣地,有些企業設計昂貴的解決方案,來幫助員工應付現代工作壓力。他們在公司設置托兒所,也舉辦壓力管理工作坊,來降低缺席率與工作倦怠。這些努力都是值得讚許的,但流程公平也是有效的策略。當我和菲莉斯.希格針對數十個組織的近三百位員工進行調查時,發現只要員工覺得高階主管清楚說明自己的決定,並以有尊嚴與尊重的方式相待,工作/生活的衝突,對員工的投入程度並沒有那麼具體的影響。
當然,高階主管不該只強調流程公平,卻未提供具體支援。若想決定究竟該提供多少具體支援,最好的方式或許是運用報酬率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除了中度的財務協助之外,實施公平流程已證實更具成本效益,因為金錢雖然有效,但並非萬能。
以公平流程提升績效
流程公平性不僅可大幅降低成本,也有助於提升價值,激勵營運經理積極執行嚴謹的策略計畫,或是接受組織變革,而不是破壞它。這類價值雖不像直接降低成本那樣顯而易見,卻同樣影響企業獲利。其實,大部分的策略或組織變革計畫都敗在執行,而不是概念。幾年前,我曾與一家需要組織再造的金融服務公司執行長合作,而該銀行的營運經理表現得很抗拒,很快就中斷了整個執行過程。我建議執行長與資深管理團隊召開幾次全員參與的大會,並與營運經理進行非正式的焦點團體訪談。經過這些對談之後,情況逐漸明朗,經理覺得執行長與高階主管並未體認到他們要求的改變幅度有多大。有趣的是,這些經理並未要求更多資源,只希望高層了解他們面臨的困境。高階經理表現出真心想要了解營運經理的想法,因而創造了一個信任的環境,讓營運主管覺得可以安心表達抗拒變革的真正理由,這麼一來,高階主管經理人就能處理抗拒變革的根本原因。此外,營運主管覺得受到尊重,因此在實際執行組織再造期間,也以類似的公平流程對待直屬部屬,讓整個變革過程進行得更順利。
哈佛商學院的麥可.比爾(Michael Beer)、組織契合度中心(Center for Organizational Fitness)董事長羅素.艾森史泰特(Russell Eisenstat)近期提供證據顯示,許多組織有系統地實施流程公平,爭取到員工支持公司的策略,因而能夠獲取價值(這種系統性做法屬於一個稱為「策略契合度流程」〔strategic fitness process,簡稱SFP〕的行動學習方法)。策略契合度流程的關鍵因素,是指定一個任務小組,成員包括八位層級低於資深主管一到二級、廣受敬重的經理人。他們的任務,是與公司各部門約一百名員工面談,以了解組織有哪些長處有助於策略執行,以及有哪些弱點可能阻礙策略執行。任務小組成員把他們從訪談中得到的資訊,消化整理成幾個主要議題,再傳達給資深管理階層,接著,他們會討論如何更有效地推展策略。策略契合度是公平流程的一個典型例子:超過25家企業,包括BD醫療(Becton, Dickinson)、漢威聯合(Honeywell)、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惠普(HP)和默克藥廠(Merck),已成功運用這項工具,來強化策略行動方案的內容,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藉此爭取員工努力執行這些策略行動方案。大多數企業宣稱它們希望鼓勵創意與創新,卻僅有少數運用流程公平來達到這些目標。他們正錯失一個創造價值的大好機會。哈佛商學院教授泰瑞莎.艾默伯(Teresa Amabile)針對在創意環境中工作的員工進行廣泛研究,以了解工作環境如何孕育或阻礙創意與創新。她持續發現,員工在營運方面擁有高度自主性的工作環境,會帶來高度的創造與創新。當然,營運自主性可視為流程公平的極端版本。
不過,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意味著幾乎沒有什麼員工可擁有完全的營運自主性,即使有也只是少數員工,因為每個人都有上司。在流程公平性較低的工作環境中,創意與創新往往受到壓抑,因為員工會認為,組織是由高階管理階層控制,或是員工會覺得,他們的想法會立即遭到駁回。相反地,如果員工相信主管對新想法抱持開放態度,且主管會重視他們對專案的貢獻,創意與創新較有可能蓬勃發展。以下的兩個例子,可看出流程公平如何吸引創新的員工及額外的顧客,以創造價值。
舉例來說,一家知名電機工程公司的執行長,希望把公司文化變得更能接受新觀念,因此,把一大群員工分成多個小組,每組有十名成員,要求每個小組提出十個改善公司業務的想法。接著,每位小組領導人會被帶進一個房間,裡面坐著該公司的高階主管,小組領導人被要求盡可能「推銷」小組的想法。高階主管則被要求盡可能「採納」各小組的想法。小組領導人就像蜜蜂看到蜂蜜一樣,圍繞著幾個向來出了名是懂得傾聽、也較接納新想法的高階主管,其他主管就被冷落在一旁,因為小組領導人根據過去經驗認為他們根本不會聽。
前進意外險公司(Progressive Casualty Insurance)就曾運用流程公平來創造價值。自1994年起,該公司開始提供自家和另外兩家競爭者的汽車保險費率,給潛在顧客作比較,即使前進意外險公司的費用不見得一定是最低的,但提供比價訊息已創造好感。潛在顧客覺得他們受到誠實對待,因此這樣的做法帶來更多新保單。為什麼沒有人人都這麼做?
流程公平既然這麼值得一試,你會以為高階主管普遍都會採用。可惜,許多人(甚至是大多數人)都沒有這麼做。他們若是依循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例子,就會表現良好,邱吉爾非常了解流程公平的成本效益。在轟炸珍珠港後的當天,邱吉爾對日本人宣戰,並在戰書最後寫下:「懷著高度敬意,我很榮幸能成為你忠誠的僕人,溫斯頓.邱吉爾。」他因信中恭敬的語調而被國人嚴厲批評,據說邱吉爾曾反駁說:「當你必須殺人時,保持禮貌並不會損失一分一毫。」
我曾在一個變革管理研討會中,教導四百位以上的經理人,我要求出席者對自己規畫與執行組織變革的表現評分。我也要求這些經理人的上司、同事、直屬部屬與顧客替他們評分。整份評估涵蓋超過三十個項目,而經理人在衡量流程公平性的項目上,全都給自己最高分:「在管理變革時,我會格外努力以有尊嚴及尊重的方式來對待大家。」但別人給的評價未必同樣正面,其實,這是唯一一項經理人自評分數明顯高於他人評價的項目。我們不清楚為什麼有這樣的認知差距,或許經理人打算以尊重的方式對待別人,但他們不善於解讀是否已成功地把這個心意傳達給別人,又或者,這只是一廂情願或自我感覺良好的想法。
有些經理人誤以為,對員工來說,提供具體資源永遠比恰當對待更有意義。在一個雞尾酒會中,一家大型國際級銀行執行長驕傲地告訴我,說他公司給解雇員工豐厚的遣散費。我讚賞他公司對那些失去工作的員工所展現的關心,然後,我問他對留任員工做了什麼。他帶著一點防備心回答說,只要對受裁員「影響」的員工做點補償就好,其他人「很幸運能保有工作」。然而,對失去工作的員工提供經濟支援之餘,還是有必要對受變革影響的人展現流程公平;順帶一提,其實每個人都受到影響了。諷刺的是,正因為流程公平的成本低廉,以數字為導向的高階主管才會低估它的價值。流程公平被忽略的另一個原因,是對高階主管來說,這麼做的一些好處並不明顯。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社會心理學家馬可.埃洛瓦伊尼奧(Marko Elovainio)與他的同事,近期針對超過31,000名芬蘭員工進行調查,檢視員工的負面生活事件(包括罹患重大疾病或配偶死亡),與該事件發生後三十個月內員工因病缺席的頻率,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負面生活事件是否會導致因病缺席,取決於事件發生之前,員工感受到多少流程公平。換句話說,事前未獲公平對待,將導致後續的缺席發生。
有時,企業政策會阻礙公平流程。比方說,法務部門可能不鼓勵經理人解釋自己的決策,因為資訊揭露或許會讓公司更容易面臨訴訟。大家認為寧願什麼都不說,也不要冒險讓揭露的資訊,日後在法庭上成了對公司不利的證詞。顯然,以法律角度來考量溝通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但沒必要考量得太過度。我們常見到企業保留的資訊當中,其實有部分資訊若能揭露,反而會帶來更多好處;比方說,除了裁員之外,曾考慮過的其他選項。
舉例來說,夏威夷的法律與醫療擁護者正在草擬一條法令,讓醫療從業人員能對醫療疏失道歉,卻不會增加訴訟風險。醫生通常會避免為任何錯誤道歉,因為他們深怕承認疏失會激怒病人,然後病人就較可能提出業務過失訴訟。事實正好相反:那些覺得自己不受尊重的病人,比認為自己受到有尊嚴對待的病人,更常提出業務過失訴訟。只要醫療從業人員的道歉,無法成為法庭上的證據,就表示法律容許醫生表達歉意,而無需擔心這麼做在法庭上會對他們不利。
那些堅信知識就是力量的經理人,可能會擔心執行流程公平會削弱他們的力量。畢竟,如果在決定事情該如何做時員工有發言權,誰還需要經理人?經理人若是讓其他人參與決策過程,有時的確會有喪失權力的風險,但大多數時候實施流程公平,會提高權力與影響力。當員工覺得在決策過程中別人有聽取他們的意見,就較可能會支持、而不只是遵循決策、上司和整個組織。避免尷尬情況的心態,是經理人不想實施流程公平的另一個原因。就像中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羅伯.佛爾格(Robert Folger)說的,那些規畫與執行艱難決策的經理人,往往會經歷矛盾的情緒。基於同情心,他們可能想接觸那些受影響的群體,向他們解釋決策背後的邏輯。然而,避免與他們接觸的心理也同樣強烈。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安迪.莫林斯基(Andy Molinsky)、哈佛商學院的約書亞.馬格里斯(Joshua Margolis)曾分析,為何經理人覺得很難以人際敏感度(international sensitivity)來執行必要之惡,例如解聘員工或宣布壞消息,而人際敏感度正是流程公平的關鍵要素。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導人必須管理自己內心的複雜情緒,包括罪惡感(像是因為不當的策略決策導致裁員),以及焦慮(不知是否有足夠的人際敏感度,以便得體地成這項任務)。經理人覺得很難處理這些不安的情緒,反而發現更容易做到的是,完全迴避這項議題及被這個議題影響的人。
這些情況也牽涉到「情緒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就像我們看到別人大笑,即使不知道為何而笑,也會跟著笑,同樣的,如果周圍的人感到焦慮與難過,我們也會有同樣的感受。而這樣的情緒感染,會讓人不安。難怪許多經理人會避開處於痛苦情緒的人。可惜,若是這麼做,這些經理人就不太可能執行流程公平。
我可以理解經理人的感受。幾年前,在某家電信公司進行史上第一次裁員後,我與該公司開始合作。執行長與資深管理團隊希望我與中階主管談談,告訴他們裁員會如何影響留下來的人,以及他們應如何協助直屬部屬「度過難關」。但中階主管覺得遭到背叛且感到擔憂,因此根本無心協助其他人回歸常軌。他們認為我就是問題所在,而且暗指我必須為裁員的決策承擔部分責任。當年巷我在試圖勸說這群憤怒又多疑的人時,完全可以理解,經理人受命要以同情的態度來面對憂傷的人們時,有多麼不自在。這遠比我想像的困難。
該公司的高階主管向我坦承他們刻意避開一般員工,這一部分是出於罪惡感,另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懷疑自己能否保持冷靜,來執行公平流程。那是本能反應,但是,忽略負面情緒,只會讓他們掙扎得更久。資深經理人若是願意與所有員工接觸,員工就會給予正面回應,組織也能重新感受到明確的目的。
Why It’s So Hard to Be Fair
每個人都知道,維持公平是成本最小、但成效卓著的做法,那麼,為什麼即使大多數人都希望得到公平待遇,高階主管在行事作為上,還是極少表現出公平的一面?
喬爾.布羅克納 Joel Brockner
當A公司決定裁員後,便支出大筆費用,為被解雇的員工提供安全保障,遣散方案包括好幾個星期的工資、大量的就業諮詢,以及最多長達一年的健康保險。然而,高階主管從不解釋為什麼裁員是不可避免的,也沒說明他們如何決定裁撤哪些工作。除此之外,許多負責傳遞裁員訊息給被解雇員工的中階主管,也處理得相當笨拙,只是敷衍地丟出一句「並不想這麼做」,就把燙手山芋扔給人力資源部門。即使是留任的員工,也無法認同這樣的處理方式。許多人在星期五開車回家的路上聽到這個消息,卻必須等到星期一,才能確定自己是否保住飯碗。直到九個月後,該公司仍必須不斷解釋這件事。公司不僅花費大筆法律費用,來處理不當解雇的訴訟,還必須進行另一波裁員,這主要是因為沒有妥善處理第一波裁員,導致員工生產力與士氣低落。
相反的,B公司裁員時,並沒有提供跟A公司一樣優渥的遣散方案,但B公司的資深經理人在實際裁員之前,就曾多次解釋這麼做的策略目的,而且高階與中階主管都隨時願意回答員工提出的問題,並對離職與留任員工表達他們的遺憾。部門主管與人力資源部門一起通知員工,他們的工作要被裁撤,在傳達這個訊息時,真誠地表達擔心。結果,沒有任何員工提起不當解雇訴訟。留任員工花了一些時間,來適應失去部分同事的事實,但都了解為何要裁員。在不到九個月之後,B公司的績效超越裁員之前的表現。雖然A公司在重整期間花費較多金錢,但B公司的流程公平性(process fairness)較高。換句話說,B公司員工相信自己受到公平對待。在面對與組織或人員有關的許多不同類型挑戰時,流程公平性都能帶來巨大的額外好處,從盡量降低成本到強化績效都包括在內。根據研究,當經理人執行流程公平性,員工回應的方式會直接或間接提升組織獲利。舉例來說,流程公平性讓新策略較容易獲得支持,也可以孕育出鼓勵創新的文化,而且,執行時不需要耗費太多成本。簡單來說,公平的流程極符合商業利益。既然如此,為何不見更多企業持續執行流程公平性?本文將檢視這個矛盾現象,並提出建議,讓你的組織提高流程公平性。
公平流程背後的邏輯
某個決定是否公平,最終還是要由每位員工自己決定。但一般來說,流程公平性有三大驅動因素。第一,員工認為自己參與了多少決策過程:是否有人徵詢並認真考量他的意見?第二,員工認為決策是如何制定與執行的:決策是否一致?決策是否基於正確資訊?錯誤是否可以修正?決策者是否盡量減少個人偏誤?事前是否充分告知?決策過程是否透明?第三,經理人如何執行:他們有沒有解釋為什麼做這樣的決策?他們是否尊重員工,主動聽取員工的考量,並理解員工的觀點?
值得注意的,是流程公平與結果公平(outcome fairness)不同,所謂的結果公平,是指員工對他們與公司交易後的最終結果作何判斷。流程公平並不保證員工能得到想要的結果,而是表示員工的意見有機會被聽見。舉一位與升遷擦身而過的員工為例。若他相信,獲得升遷的那位員工很適任,而主管也曾與他坦誠討論要如何做更好的準備,以爭取下次的升遷機會,那麼,這位員工的生產力與投入程度,可能會高過若是他認定升遷的那位是上司愛將,或是主管沒有給他任何努力方向的情況。當員工覺得被公司傷害,往往會展開報復,這麼一來,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1990年代中期,由杜克大學(Duke)的亞倫.林德(Allan Lind)和俄亥俄州立大學(Ohio State)的傑拉德.格林伯格(Jerald Greenberg)領導的一項針對近一千人的研究發現,員工是否會對不當解雇提出告訴,有一項主要決定因素,那就是員工對於解聘過程是否公平執行的觀感。認為自己受到高度公平對待的離職員工,只有1%會提起不當解雇的訴訟,相形之下,那些認為過程中未獲高度公平對待的前員工中,有17%會提起訴訟。如果把這些數據換算成金錢,以公平流程對待解聘員工,預期每裁員一百名員工就可省下128萬美元的成本。這個數字是根據1988年法律辯護成本是八萬美元來計算的,這是保守的估計,因為光是考慮到通貨膨脹,現在成本就已上漲到12萬美元。因此,縱然無法精確計算執行公平流程的財務成本,但至少可以說,對離職員工表達真誠的關懷,並以有尊嚴的方式對待他們,付出的代價將遠低於不這麼做。
同樣地,如果顧客認為自己在過程中獲得公平對待,也較不會對服務提供者提出訴訟。1997年,醫學研究人員溫蒂.萊文森(Wendy Levinson)與同事進行的研究發現,病患通常不會只因為醫療照顧不良,就告醫生醫療疏失,更重要的因素,在於醫生是否有花時間解釋治療做法,並耐心回答病人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以公平的流程來對待病人。至於那些沒這麼做的醫生,較可能在發生問題時,面臨醫療疏失的訴訟。
除了降低法律成本,流程公平也會降低偷竊率與流動率。管理與人力資源教授格林伯格的研究,檢視了兩家製造商如何處理減薪問題。其中一家製造商的副總裁,在一週工作結束時召開會議,並宣布所有員工將全面減薪15%,為期十週。他很簡潔地解釋原因、感謝員工,並回答幾個問題;整個過程在15分鐘內結束。另一家製造商實施一模一樣的減薪,不同的是由總裁對員工宣布。他告訴員工,他們已考慮過裁員等其他降低成本的選項,但減薪似乎是最不痛苦的選擇。總裁花了一個半鐘頭來回應員工的問題與擔憂,而他也一再表達遺憾不得不走上這一步。格林伯格發現,在減薪的十週期間,第二家公司的員工偷竊率較第一家低80%,而第二家員工辭職的可能性,也只有第一家的15分之1。許多高階主管喜歡先用錢來解決問題,但我的研究顯示,企業若是常態性實施流程公平,就可以降低費用。試想:問員工對某項新計畫的意見,或是向員工解釋你為什麼把某項工作交給他的同事,這樣做其實沒有什麼成本。當然,公司也應持續對員工提供具體的協助,但實施公平的流程,可讓公司在節省支出之餘,仍維持高度的員工滿意度。
想像一下外派人員若提早放棄他們的海外任務,會造成何種財務後果。一般認為,外派人員或他們的家人若無法適應新環境,就可能提早離開,因此,企業通常選擇付出高額成本,來協助外派人員度過調整期,像是支付房租、小孩的學費等。人力資源顧問榮恩.蓋隆茲克(Ron Garonzik)、羅格斯商學院(Rutgers Business School)教授菲莉斯.希格(Phyllis Siegel)和我,在2000年針對128位外派人員所作的研究發現,外派人員只要認為上司對待自己大致公平,那麼,對工作之外各種生活面向的適應程度,並不會影響他們是否提早離職的意願。換句話說,外派人員即使對住在國外並不特別感興趣,流程高度公平仍會吸引他們持續執行海外任務。
同樣地,有些企業設計昂貴的解決方案,來幫助員工應付現代工作壓力。他們在公司設置托兒所,也舉辦壓力管理工作坊,來降低缺席率與工作倦怠。這些努力都是值得讚許的,但流程公平也是有效的策略。當我和菲莉斯.希格針對數十個組織的近三百位員工進行調查時,發現只要員工覺得高階主管清楚說明自己的決定,並以有尊嚴與尊重的方式相待,工作/生活的衝突,對員工的投入程度並沒有那麼具體的影響。
當然,高階主管不該只強調流程公平,卻未提供具體支援。若想決定究竟該提供多少具體支援,最好的方式或許是運用報酬率遞減法則(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除了中度的財務協助之外,實施公平流程已證實更具成本效益,因為金錢雖然有效,但並非萬能。
以公平流程提升績效
流程公平性不僅可大幅降低成本,也有助於提升價值,激勵營運經理積極執行嚴謹的策略計畫,或是接受組織變革,而不是破壞它。這類價值雖不像直接降低成本那樣顯而易見,卻同樣影響企業獲利。其實,大部分的策略或組織變革計畫都敗在執行,而不是概念。幾年前,我曾與一家需要組織再造的金融服務公司執行長合作,而該銀行的營運經理表現得很抗拒,很快就中斷了整個執行過程。我建議執行長與資深管理團隊召開幾次全員參與的大會,並與營運經理進行非正式的焦點團體訪談。經過這些對談之後,情況逐漸明朗,經理覺得執行長與高階主管並未體認到他們要求的改變幅度有多大。有趣的是,這些經理並未要求更多資源,只希望高層了解他們面臨的困境。高階經理表現出真心想要了解營運經理的想法,因而創造了一個信任的環境,讓營運主管覺得可以安心表達抗拒變革的真正理由,這麼一來,高階主管經理人就能處理抗拒變革的根本原因。此外,營運主管覺得受到尊重,因此在實際執行組織再造期間,也以類似的公平流程對待直屬部屬,讓整個變革過程進行得更順利。
哈佛商學院的麥可.比爾(Michael Beer)、組織契合度中心(Center for Organizational Fitness)董事長羅素.艾森史泰特(Russell Eisenstat)近期提供證據顯示,許多組織有系統地實施流程公平,爭取到員工支持公司的策略,因而能夠獲取價值(這種系統性做法屬於一個稱為「策略契合度流程」〔strategic fitness process,簡稱SFP〕的行動學習方法)。策略契合度流程的關鍵因素,是指定一個任務小組,成員包括八位層級低於資深主管一到二級、廣受敬重的經理人。他們的任務,是與公司各部門約一百名員工面談,以了解組織有哪些長處有助於策略執行,以及有哪些弱點可能阻礙策略執行。任務小組成員把他們從訪談中得到的資訊,消化整理成幾個主要議題,再傳達給資深管理階層,接著,他們會討論如何更有效地推展策略。策略契合度是公平流程的一個典型例子:超過25家企業,包括BD醫療(Becton, Dickinson)、漢威聯合(Honeywell)、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惠普(HP)和默克藥廠(Merck),已成功運用這項工具,來強化策略行動方案的內容,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藉此爭取員工努力執行這些策略行動方案。大多數企業宣稱它們希望鼓勵創意與創新,卻僅有少數運用流程公平來達到這些目標。他們正錯失一個創造價值的大好機會。哈佛商學院教授泰瑞莎.艾默伯(Teresa Amabile)針對在創意環境中工作的員工進行廣泛研究,以了解工作環境如何孕育或阻礙創意與創新。她持續發現,員工在營運方面擁有高度自主性的工作環境,會帶來高度的創造與創新。當然,營運自主性可視為流程公平的極端版本。
不過,組織之所以存在,就意味著幾乎沒有什麼員工可擁有完全的營運自主性,即使有也只是少數員工,因為每個人都有上司。在流程公平性較低的工作環境中,創意與創新往往受到壓抑,因為員工會認為,組織是由高階管理階層控制,或是員工會覺得,他們的想法會立即遭到駁回。相反地,如果員工相信主管對新想法抱持開放態度,且主管會重視他們對專案的貢獻,創意與創新較有可能蓬勃發展。以下的兩個例子,可看出流程公平如何吸引創新的員工及額外的顧客,以創造價值。
舉例來說,一家知名電機工程公司的執行長,希望把公司文化變得更能接受新觀念,因此,把一大群員工分成多個小組,每組有十名成員,要求每個小組提出十個改善公司業務的想法。接著,每位小組領導人會被帶進一個房間,裡面坐著該公司的高階主管,小組領導人被要求盡可能「推銷」小組的想法。高階主管則被要求盡可能「採納」各小組的想法。小組領導人就像蜜蜂看到蜂蜜一樣,圍繞著幾個向來出了名是懂得傾聽、也較接納新想法的高階主管,其他主管就被冷落在一旁,因為小組領導人根據過去經驗認為他們根本不會聽。
前進意外險公司(Progressive Casualty Insurance)就曾運用流程公平來創造價值。自1994年起,該公司開始提供自家和另外兩家競爭者的汽車保險費率,給潛在顧客作比較,即使前進意外險公司的費用不見得一定是最低的,但提供比價訊息已創造好感。潛在顧客覺得他們受到誠實對待,因此這樣的做法帶來更多新保單。為什麼沒有人人都這麼做?
流程公平既然這麼值得一試,你會以為高階主管普遍都會採用。可惜,許多人(甚至是大多數人)都沒有這麼做。他們若是依循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例子,就會表現良好,邱吉爾非常了解流程公平的成本效益。在轟炸珍珠港後的當天,邱吉爾對日本人宣戰,並在戰書最後寫下:「懷著高度敬意,我很榮幸能成為你忠誠的僕人,溫斯頓.邱吉爾。」他因信中恭敬的語調而被國人嚴厲批評,據說邱吉爾曾反駁說:「當你必須殺人時,保持禮貌並不會損失一分一毫。」
我曾在一個變革管理研討會中,教導四百位以上的經理人,我要求出席者對自己規畫與執行組織變革的表現評分。我也要求這些經理人的上司、同事、直屬部屬與顧客替他們評分。整份評估涵蓋超過三十個項目,而經理人在衡量流程公平性的項目上,全都給自己最高分:「在管理變革時,我會格外努力以有尊嚴及尊重的方式來對待大家。」但別人給的評價未必同樣正面,其實,這是唯一一項經理人自評分數明顯高於他人評價的項目。我們不清楚為什麼有這樣的認知差距,或許經理人打算以尊重的方式對待別人,但他們不善於解讀是否已成功地把這個心意傳達給別人,又或者,這只是一廂情願或自我感覺良好的想法。
有些經理人誤以為,對員工來說,提供具體資源永遠比恰當對待更有意義。在一個雞尾酒會中,一家大型國際級銀行執行長驕傲地告訴我,說他公司給解雇員工豐厚的遣散費。我讚賞他公司對那些失去工作的員工所展現的關心,然後,我問他對留任員工做了什麼。他帶著一點防備心回答說,只要對受裁員「影響」的員工做點補償就好,其他人「很幸運能保有工作」。然而,對失去工作的員工提供經濟支援之餘,還是有必要對受變革影響的人展現流程公平;順帶一提,其實每個人都受到影響了。諷刺的是,正因為流程公平的成本低廉,以數字為導向的高階主管才會低估它的價值。流程公平被忽略的另一個原因,是對高階主管來說,這麼做的一些好處並不明顯。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社會心理學家馬可.埃洛瓦伊尼奧(Marko Elovainio)與他的同事,近期針對超過31,000名芬蘭員工進行調查,檢視員工的負面生活事件(包括罹患重大疾病或配偶死亡),與該事件發生後三十個月內員工因病缺席的頻率,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負面生活事件是否會導致因病缺席,取決於事件發生之前,員工感受到多少流程公平。換句話說,事前未獲公平對待,將導致後續的缺席發生。
有時,企業政策會阻礙公平流程。比方說,法務部門可能不鼓勵經理人解釋自己的決策,因為資訊揭露或許會讓公司更容易面臨訴訟。大家認為寧願什麼都不說,也不要冒險讓揭露的資訊,日後在法庭上成了對公司不利的證詞。顯然,以法律角度來考量溝通的內容,是非常重要的,但沒必要考量得太過度。我們常見到企業保留的資訊當中,其實有部分資訊若能揭露,反而會帶來更多好處;比方說,除了裁員之外,曾考慮過的其他選項。
舉例來說,夏威夷的法律與醫療擁護者正在草擬一條法令,讓醫療從業人員能對醫療疏失道歉,卻不會增加訴訟風險。醫生通常會避免為任何錯誤道歉,因為他們深怕承認疏失會激怒病人,然後病人就較可能提出業務過失訴訟。事實正好相反:那些覺得自己不受尊重的病人,比認為自己受到有尊嚴對待的病人,更常提出業務過失訴訟。只要醫療從業人員的道歉,無法成為法庭上的證據,就表示法律容許醫生表達歉意,而無需擔心這麼做在法庭上會對他們不利。
那些堅信知識就是力量的經理人,可能會擔心執行流程公平會削弱他們的力量。畢竟,如果在決定事情該如何做時員工有發言權,誰還需要經理人?經理人若是讓其他人參與決策過程,有時的確會有喪失權力的風險,但大多數時候實施流程公平,會提高權力與影響力。當員工覺得在決策過程中別人有聽取他們的意見,就較可能會支持、而不只是遵循決策、上司和整個組織。避免尷尬情況的心態,是經理人不想實施流程公平的另一個原因。就像中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的羅伯.佛爾格(Robert Folger)說的,那些規畫與執行艱難決策的經理人,往往會經歷矛盾的情緒。基於同情心,他們可能想接觸那些受影響的群體,向他們解釋決策背後的邏輯。然而,避免與他們接觸的心理也同樣強烈。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安迪.莫林斯基(Andy Molinsky)、哈佛商學院的約書亞.馬格里斯(Joshua Margolis)曾分析,為何經理人覺得很難以人際敏感度(international sensitivity)來執行必要之惡,例如解聘員工或宣布壞消息,而人際敏感度正是流程公平的關鍵要素。在這樣的情況下,領導人必須管理自己內心的複雜情緒,包括罪惡感(像是因為不當的策略決策導致裁員),以及焦慮(不知是否有足夠的人際敏感度,以便得體地成這項任務)。經理人覺得很難處理這些不安的情緒,反而發現更容易做到的是,完全迴避這項議題及被這個議題影響的人。
這些情況也牽涉到「情緒感染」(emotional contagion)。就像我們看到別人大笑,即使不知道為何而笑,也會跟著笑,同樣的,如果周圍的人感到焦慮與難過,我們也會有同樣的感受。而這樣的情緒感染,會讓人不安。難怪許多經理人會避開處於痛苦情緒的人。可惜,若是這麼做,這些經理人就不太可能執行流程公平。
我可以理解經理人的感受。幾年前,在某家電信公司進行史上第一次裁員後,我與該公司開始合作。執行長與資深管理團隊希望我與中階主管談談,告訴他們裁員會如何影響留下來的人,以及他們應如何協助直屬部屬「度過難關」。但中階主管覺得遭到背叛且感到擔憂,因此根本無心協助其他人回歸常軌。他們認為我就是問題所在,而且暗指我必須為裁員的決策承擔部分責任。當年巷我在試圖勸說這群憤怒又多疑的人時,完全可以理解,經理人受命要以同情的態度來面對憂傷的人們時,有多麼不自在。這遠比我想像的困難。
該公司的高階主管向我坦承他們刻意避開一般員工,這一部分是出於罪惡感,另一部分是因為他們懷疑自己能否保持冷靜,來執行公平流程。那是本能反應,但是,忽略負面情緒,只會讓他們掙扎得更久。資深經理人若是願意與所有員工接觸,員工就會給予正面回應,組織也能重新感受到明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