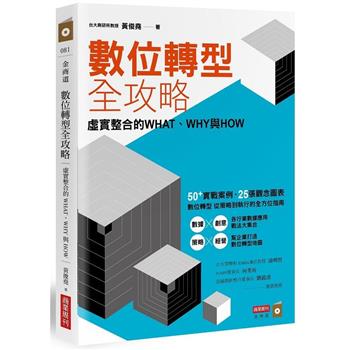導言 不斷再合理化的修練
數位轉型,是當代的「顯學」。
在企業端,無論是大型企業的領導人、中小企業的老闆、各式企業中的各階層主管,乃至剛入行的社會新鮮人,這幾年必定從不同的角度,直接間接感受到數位轉型的壓力。
有趣的是,各行各業人士意識到轉型壓力之際,除了跨國顧問業者近年「邊看、邊學、邊教」所集結而成的報告、媒體端常見較淺的報導、書市充斥的美國或中國數位原生企業「典範」外,常會覺得在可作為轉型參考的相關認知上,似乎還是比較零碎,像是缺了些什麼。
具體的一例。一位目前主要工作在於協助各行各業數位轉型的顧問業高階主管,閒聊之際,提及各種客戶都想知道「該怎麼『轉』」,想找些可供學習、參考的轉型個案。但在環境不斷變遷、轉型難有「終點」的局面下,卻很難找到真可完整提供給客戶的「數位轉型成功範例」。
而在這局中同樣略顯尷尬的,是全球的商學院。如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科技史專家大衛.埃奇頓(David Edgerton)教授所述,在大學裡被視為新研究主題者,常常是從業界既有的實作衍生而來。也因此,在快速變動的數位環境中,大學基本上比較處於不斷追趕的位置,而少扮演引領者的角色。雖然在全球龍頭商學院的高管教育端,已面臨必須為跨國企業開設數位轉型相關課程的壓力,但數位轉型相關的研究,迄今在「追趕」的壓力下,仍片段而有限。更有甚者,過往幾十年間作為商學院標準教程核心的若干概念架構,則被業界有識者看出已與現實脫節、落伍。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有意義的討論企業數位轉型,勢必會面對各種困難與限制。不求花俏但求攸關的話,應該還是要回到環境變遷的緣由與企業經營的根本,對數位轉型有系統的進行「本質性」的探討。
什麼是數位轉型的本質呢?這是個非常關鍵,卻較少被辯證的問題。要釐清這個問題,必須先理解為什麼企業需要進行數位轉型。
如果你回想一下,包括「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區塊鏈」、「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技術潮流,進入一般企業、媒體乃至大眾視野的時間,近則在三、五年前,遠則頂多七、八年前。就在這段時間裡,一方面「摩爾定律」的持續發威,讓那些屬於早年實驗室裡的項目 —— 數據運算、傳輸、儲存的成本,降低到可以商業化的地步;另一方面,各國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貨幣寬鬆政策釋出的熱錢,則化為這些技術商業化的龐大推力。
資本驅動著技術,滲透到市場上各個領域,錢也推著技術,尋找更合理的出路。因此才造就了金融圈的「Bank 3.0」甚至「Bank 4.0」轉型壓力,零售業紛紛投入的「全零售」、「新零售」,製造業面對的「工業4.0」浪潮,以及傳播領域零碎多元到令人目不暇給的「新媒體」變化。
錢推著技術找更合理的出路,讓能適當運用新技術的廠商,取代經營上顯出老態與疲態的廠商,是商業發展的定律。而昨天的合理作為,今天面對新的技術環境與顧客樣貌下「更合理」的可能性,便不再合理。在這樣的意義上,市場的發展、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就一時一刻看,求的是當下各面向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而放到時間軸線上,便見「不斷再合理化」(constantly re-rationalization)的動態。
數位轉型,本質上因此是企業面臨快速變動數位環境的「不斷再合理化」進程。
全球好幾個世代都知曉乃至熟悉的NBA名將喬丹(Michael Jordan),31歲那年曾從芝加哥公牛隊宣布退休,出人意外地加盟與公牛同一個老闆的職業棒球芝加哥白襪隊雙A小聯盟球隊。這位籃球天才,本著對於剛過世父親在他年幼時帶著他傳接棒球的追思,當時每天隨著球隊乘巴士奔波各地,早上六點半就到球場自主練打擊一個多小時,而後隨隊練習三小時,接著再自主練打擊半小時以上。如此執著與努力,換來的也只是整個球季0.202的打擊率。這過程中,喬丹常常提及自己的身心狀態和體態,其實都還停留在籃球球員的狀態,和棒球所需的修練功夫和體質還是有一段距離。1995年,他再度回到NBA的芝加哥公牛隊,在熟悉的情境中拾回往日的榮光,帶領公牛開啟一輪三連冠的神奇籃球紀錄。
企業的數位轉型,與喬丹從NBA轉到白襪隊打小聯盟棒球這事,有好幾處相似的地方。兩者的轉變,脈絡上看來轉變前後都似乎仍屬於「同一個領域」—— 喬丹轉行前後,參與的都是職業運動;企業數位轉型前後的現實,再怎麼說也都是企業的經營。但兩者轉變之際,各環節所需調整的面向之廣、幅度之深,箇中應對的各種難處,同樣都不是外人所容易體會。而無論喬丹在籃球場上戰績如何炫目,企業過往如何輝煌,轉換到新局面中,必然需要面對「在2A強度的比賽中打擊率卻只有0.202」一類的尷尬階段。同時,喬丹轉行後意識到自己身心狀態和體態仍留在籃球員狀態;企業數位轉型過程中,組織成員的思考與習慣很人性,而必然也有死守過往狀態的惰性。
而企業數位轉型與喬丹轉行一事的最大差別之處,則是喬丹理解到棒球與籃球的巨大差異之後,有餘裕再一次華麗轉身,回到老本行,再創職涯巔峰;但是數位轉型對多數企業而言,今日已非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的不歸路。
本書將有系統地與各行各業的讀者討論這「不得不走的不歸路」,應該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規畫、如何邁開步子走,長期而言能比較順遂些。
第1章,將從數位環境中企業轉型的必然性談起,詮釋數位轉型的「Why」與 「What」。在這樣的基礎上,第2章將探討「數位轉型策略」的多元視角,希望能提供一個涵蓋較為全面的轉型策略思考架構。
第3章到第5章,談的則是企業數位轉型「不斷再合理化」過程中的「How」。簡單地說,它們談的是「數位轉型的『轉法』」。第3章將討論對於數位轉型非常重要但常被忽視的基礎 —— 數據與創意,以及它們聯合奠定的顧客體驗修練。第4章,將探討企業內部需要改變的各個環節,本書稱之為數位轉型的「內功」。有「內功」當然相對就有「外功」;第5章便就著顧客經營由淺而深的脈絡,談數位轉型的「外功」。至於數位轉型過程中,耐心、膽識和常識的不可或缺,則將在最後的第6章中討論。
(書摘) 第二篇—第1章 這次不一樣
1.2 不只是流行風潮
企業的管理,在20世紀成為一門學問。尤其自1980年代《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問世,成為第一本暢銷全球的商業書籍之後,市場上每隔幾年便會就著新的名號,鼓動新一波的管理風潮。兩三個世代的經營者這些年間於是見證了如 「Z理論」、「反敗為勝」、「五項修練」、「時基競爭」、「企業流程再造」、「組織再造」、「6個標準差」、「基業長青」、「知識管理」、「藍海策略」、「平衡計分卡」、「精實創業」、「敏捷開發」等等管理流行風潮。這些流行風潮,往往聚焦於組織中的若干管理層面,透過易於理解的概念架構,倡導企業經營效率的提升之方。
譬如90年代流行的「企業流程再造」(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便鼓吹企業透過組織重整(restructuring)、縮小規模(downsize)、節省成本(cost down)等途徑,進行變革管理,以提升經營效率。追求「更高效率」這樣的經營觀影響至廣,決定了組織怎麼運用資源、評估績效、看待市場。過往談企業變革,因此多傾向透過各種工具性手段去「擰毛巾」,努力地把效率向上逼、把利潤擠出來。
在各種高管課程討論情境中,因此時有職涯歷程中曾經歷各種流行風潮的企業主管,質疑當下鑼鼓喧天、沸沸揚揚,在各行各業廣泛被關注甚至形成壓力的「數位轉型」,會不會只是又一波夾帶大量技術詞彙的新流行風潮,幾年後潮退了,便成過眼雲煙?
我們將以整本書的篇幅,來回答這個問題。最精簡的答案是:「這次不一樣。」
數位轉型的本質與關注重點,與過往對於幾十年間企業慣常的「變革」大相逕庭。而近年各行各業經營者面對數位轉型時,常有的困惑與懷疑,便常來自沒有意識到涵蓋甚廣的各種「這次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呢?本書將一層層去梳理、探討。簡單來說,所謂的「不一樣」,大致可歸納成以下幾點:
企業數位轉型是個受資本推動技術發展所驅動的「不斷再合理化」過程。
數位轉型對於多數企業而言,不是可有可無的經營選項,也不只是產、學、媒體炒作的產物,而是欲在市場中生存的必要改變。
企業的數位轉型牽涉到整個組織從對市場的假設,到組織內各階層、各功能別的各個環節。
就算隸屬於傳統定義的同一產業,不同企業因為既有資源與條件限制的差異,在如何「轉」這件事上可能就需要有截然不同的走法。
企業數位轉型為的不是短期利潤提升,而是長期的生存與成長。
企業數位轉型沒有可以涵蓋各業的「完整」理論架構,也不會有「導入即可使用」的「套裝解」(turnkey solution)。此外,若干經營者近幾十年已習慣引用的思考模式與概念架構,漸漸失去其攸關性。
過去管理界的轉型風潮中被奉為標竿者,常是在各領域經營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的大型企業。但當下談數位轉型,在各領域常被提出來當作師法對象者,卻常是一群數位原生企業。而就借鏡一事來說更為棘手的,是這些數位原生企業經營賴以發跡的純數位發展條件,又與多數實體原生企業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所需應對的各種虛實整合挑戰狀況,大為不同。
數位轉型一方面要求企業放棄過往經營的若干經驗累積,另一方面則又是個無法一蹴而就的累積過程。有意義的數位轉型,建基於數據與創意/想像力這兩項互為因果的關鍵能耐長期累積。
企業數位轉型需要經營者有不怕「跟別人不一樣」的膽識。這樣的膽識,來自常識與勇氣。
1.3 數位轉型的本質:不斷再合理化
這次不一樣。但真要掌握這「不一樣」的內涵,則需要理解我們眼下所見市場中,各種數位發展背後的基本邏輯。這所謂的基本邏輯,由技術發展與資本累積這兩條軸線相互交織而成;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最容易加以掌握。
談及歷史,如果回溯一下(譬如說以Google Trends去查)這幾年常常聽到的各種數位相關浪潮,譬如大數據、物聯網、工業4.0、區塊鏈、FinTech、新零售等等,會發現它們開始出現在媒體上,一般大眾首次聽聞的時間,大約就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也就是說,距離現今幾年前,數位浪潮挾著與各行各業都有關的技術、趨勢以及語彙,「忽然」席捲而來。而數位轉型的機會與壓力,也才隨之而生。
為什麼就在那幾年間發生呢?我們再從技術與資本這兩個面向加以理解。
先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在只有大型企業才可能擁有電腦,而一部電腦勢必以龐然大物之姿塞滿整個房間的1950年代,當時的電腦硬碟體積像是大型冰箱,需要四個大漢合力才能移動,但是容量以MB計,卻只有個位數。30多年後的1980年代,桌上型的個人電腦剛剛問世,一個15MB容量的硬碟,便要價美金兩三千元。再過30多年後的今天,大家隨身帶出門的手機上頭,隨隨便便就有64GB、128GB乃至256GB的儲存量。而同一支手機的運算能量,甚至遠超過人類於60年代後期登陸月球時,登月小艇上各種儀器設施的總運算能量。
這般歷史對照的背後,有一條對理解數位之局而言非常重要的技術軸線。這條軸線,就是由廣義的「摩爾定律」所代表的,技術持續進步下,數位運算、儲存乃至傳輸成本的不斷下降。正是因為這些成本不斷下降,幾年前開始,過去僅限於實驗室裡如雲端計算、AI(人工智慧)、VR/AR、區塊鏈、IOT(物聯網)等數位應用項目,才得以進入市場,開始商業化的應用。
而如果從資本的角度來詮釋,則前次金融海嘯之際,各國為應急而施行又猛又急的量化寬鬆(QE)政策,額外創造出大量貨幣。這些新出現在市場上的「熱錢」四處尋找出路,讓全球在2010~2017年間,隨著前述技術面的進展,而有了一波創業熱潮。資本所吹動的「風口」,除了鼓舞如所謂「獨角獸」企業一類的現象外,也推升加大了各種數位相關技術應用的商業化速度與力道。
就這樣,錢推著技術尋找應用的出口,挹注各種數位相關的創新;各種創新隨後則改變了不同市場中既有的遊戲規則。用白話來說,錢的本質,便是它會不斷地追求以更合適的方式,去讓錢滾錢。也就是說,資本的慣性是循著市場上「最合理」的方式去累積,並且會不斷尋覓「更合理」的累積方向。依照社會經濟學巨擘韋伯(Max Weber)對資本主義市場發展所做的詮釋,現代經濟體中的資本,有著不斷尋覓「更合理」發展的「合理化」動能 —— 透過理性的計算,時時追求當下最合理的資源運用,以求報酬的最大化。
資本的累積,產業的興衰,市場中新模式的發展,因此便在「不斷再合理化」的歷程中堆疊、變化。根據這樣的詮釋,所謂的「合理」或「不合理」,便都視既有環境條件,而有其階段性。譬如說航海,人類從史前到有歷史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憑藉風帆航海;這在只有風帆的當時,自然是「最合理」的。但是,當輪船出現、相關技術到位達一定程度之後,再用風帆去謀求大量的商品運載,便不再合理了。這個階段「最合理」的運輸,靠的是蒸汽引擎推動的輪船。見微知著,在資本累積的過程中,市場上尋求「更合理」出路的金錢,便這般不斷透過創新的應用,推動著各種顛覆過往模式的新模式出現。
如果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則工商業的發展,其實是透過環環相扣的里程碑,長時間層層堆疊而成。每一個新里程碑的出現,都以前一個階段的發展成熟作為必要條件。若沒有複式簿記(現代會計系統的前身)的出現、合理的記帳方式被廣為接受,熟人和生人之間就很難集資組公司。而若沒有出現像荷屬東印度公司或英屬東印度公司這種公司型態的組織,在大航海時代從單次航行的募資、單次航行結算解散,發展到股東長期分擔利潤與風險、長期經營事業,那麼18世紀的蒸汽機技術,便很難大規模藉由鐵道公司、輪船公司、大規模紡織廠、礦場企業而開花結果成工業革命。而就是靠工業革命奠下的生產、物流基礎,讓20世紀初工廠通了電之後,便有福特T-car一類的大規模生產線。如果沒有大規模生產複雜產品的經驗與技術累積,那麼像智慧型手機這類數位時代各種新商業模式的觸媒,便不可能量產普及。
近20年,由數位原生企業打頭陣、全球實體原生企業隨之接踵投入的數位轉型,進行整合「位元」與「原子」的虛實整合。放到歷史發展的框架中看,那麼企業的數位轉型,就可說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也是自由市場中,資本驅動技術發展「不斷再合理化」常態的現階段歷程。
在這樣的背景下,若微觀地考量個別企業,那麼企業的經營,勢必也需要意識到過往「最合理」的做法,無論如何只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終將被「更合理」的作法所取代。因此,企業為了長期的生存,勢必需要與時俱進地「不斷再合理化」。因此,有意義的企業數位轉型,是企業在多變數位化環境中「不斷再合理化」的過程。
數位轉型,是當代的「顯學」。
在企業端,無論是大型企業的領導人、中小企業的老闆、各式企業中的各階層主管,乃至剛入行的社會新鮮人,這幾年必定從不同的角度,直接間接感受到數位轉型的壓力。
有趣的是,各行各業人士意識到轉型壓力之際,除了跨國顧問業者近年「邊看、邊學、邊教」所集結而成的報告、媒體端常見較淺的報導、書市充斥的美國或中國數位原生企業「典範」外,常會覺得在可作為轉型參考的相關認知上,似乎還是比較零碎,像是缺了些什麼。
具體的一例。一位目前主要工作在於協助各行各業數位轉型的顧問業高階主管,閒聊之際,提及各種客戶都想知道「該怎麼『轉』」,想找些可供學習、參考的轉型個案。但在環境不斷變遷、轉型難有「終點」的局面下,卻很難找到真可完整提供給客戶的「數位轉型成功範例」。
而在這局中同樣略顯尷尬的,是全球的商學院。如倫敦大學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科技史專家大衛.埃奇頓(David Edgerton)教授所述,在大學裡被視為新研究主題者,常常是從業界既有的實作衍生而來。也因此,在快速變動的數位環境中,大學基本上比較處於不斷追趕的位置,而少扮演引領者的角色。雖然在全球龍頭商學院的高管教育端,已面臨必須為跨國企業開設數位轉型相關課程的壓力,但數位轉型相關的研究,迄今在「追趕」的壓力下,仍片段而有限。更有甚者,過往幾十年間作為商學院標準教程核心的若干概念架構,則被業界有識者看出已與現實脫節、落伍。
在這樣的背景下,要有意義的討論企業數位轉型,勢必會面對各種困難與限制。不求花俏但求攸關的話,應該還是要回到環境變遷的緣由與企業經營的根本,對數位轉型有系統的進行「本質性」的探討。
什麼是數位轉型的本質呢?這是個非常關鍵,卻較少被辯證的問題。要釐清這個問題,必須先理解為什麼企業需要進行數位轉型。
如果你回想一下,包括「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區塊鏈」、「虛擬實境/擴增實境」等技術潮流,進入一般企業、媒體乃至大眾視野的時間,近則在三、五年前,遠則頂多七、八年前。就在這段時間裡,一方面「摩爾定律」的持續發威,讓那些屬於早年實驗室裡的項目 —— 數據運算、傳輸、儲存的成本,降低到可以商業化的地步;另一方面,各國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貨幣寬鬆政策釋出的熱錢,則化為這些技術商業化的龐大推力。
資本驅動著技術,滲透到市場上各個領域,錢也推著技術,尋找更合理的出路。因此才造就了金融圈的「Bank 3.0」甚至「Bank 4.0」轉型壓力,零售業紛紛投入的「全零售」、「新零售」,製造業面對的「工業4.0」浪潮,以及傳播領域零碎多元到令人目不暇給的「新媒體」變化。
錢推著技術找更合理的出路,讓能適當運用新技術的廠商,取代經營上顯出老態與疲態的廠商,是商業發展的定律。而昨天的合理作為,今天面對新的技術環境與顧客樣貌下「更合理」的可能性,便不再合理。在這樣的意義上,市場的發展、企業的經營與管理,就一時一刻看,求的是當下各面向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而放到時間軸線上,便見「不斷再合理化」(constantly re-rationalization)的動態。
數位轉型,本質上因此是企業面臨快速變動數位環境的「不斷再合理化」進程。
全球好幾個世代都知曉乃至熟悉的NBA名將喬丹(Michael Jordan),31歲那年曾從芝加哥公牛隊宣布退休,出人意外地加盟與公牛同一個老闆的職業棒球芝加哥白襪隊雙A小聯盟球隊。這位籃球天才,本著對於剛過世父親在他年幼時帶著他傳接棒球的追思,當時每天隨著球隊乘巴士奔波各地,早上六點半就到球場自主練打擊一個多小時,而後隨隊練習三小時,接著再自主練打擊半小時以上。如此執著與努力,換來的也只是整個球季0.202的打擊率。這過程中,喬丹常常提及自己的身心狀態和體態,其實都還停留在籃球球員的狀態,和棒球所需的修練功夫和體質還是有一段距離。1995年,他再度回到NBA的芝加哥公牛隊,在熟悉的情境中拾回往日的榮光,帶領公牛開啟一輪三連冠的神奇籃球紀錄。
企業的數位轉型,與喬丹從NBA轉到白襪隊打小聯盟棒球這事,有好幾處相似的地方。兩者的轉變,脈絡上看來轉變前後都似乎仍屬於「同一個領域」—— 喬丹轉行前後,參與的都是職業運動;企業數位轉型前後的現實,再怎麼說也都是企業的經營。但兩者轉變之際,各環節所需調整的面向之廣、幅度之深,箇中應對的各種難處,同樣都不是外人所容易體會。而無論喬丹在籃球場上戰績如何炫目,企業過往如何輝煌,轉換到新局面中,必然需要面對「在2A強度的比賽中打擊率卻只有0.202」一類的尷尬階段。同時,喬丹轉行後意識到自己身心狀態和體態仍留在籃球員狀態;企業數位轉型過程中,組織成員的思考與習慣很人性,而必然也有死守過往狀態的惰性。
而企業數位轉型與喬丹轉行一事的最大差別之處,則是喬丹理解到棒球與籃球的巨大差異之後,有餘裕再一次華麗轉身,回到老本行,再創職涯巔峰;但是數位轉型對多數企業而言,今日已非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的不歸路。
本書將有系統地與各行各業的讀者討論這「不得不走的不歸路」,應該如何思考、如何理解、如何規畫、如何邁開步子走,長期而言能比較順遂些。
第1章,將從數位環境中企業轉型的必然性談起,詮釋數位轉型的「Why」與 「What」。在這樣的基礎上,第2章將探討「數位轉型策略」的多元視角,希望能提供一個涵蓋較為全面的轉型策略思考架構。
第3章到第5章,談的則是企業數位轉型「不斷再合理化」過程中的「How」。簡單地說,它們談的是「數位轉型的『轉法』」。第3章將討論對於數位轉型非常重要但常被忽視的基礎 —— 數據與創意,以及它們聯合奠定的顧客體驗修練。第4章,將探討企業內部需要改變的各個環節,本書稱之為數位轉型的「內功」。有「內功」當然相對就有「外功」;第5章便就著顧客經營由淺而深的脈絡,談數位轉型的「外功」。至於數位轉型過程中,耐心、膽識和常識的不可或缺,則將在最後的第6章中討論。
(書摘) 第二篇—第1章 這次不一樣
1.2 不只是流行風潮
企業的管理,在20世紀成為一門學問。尤其自1980年代《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書問世,成為第一本暢銷全球的商業書籍之後,市場上每隔幾年便會就著新的名號,鼓動新一波的管理風潮。兩三個世代的經營者這些年間於是見證了如 「Z理論」、「反敗為勝」、「五項修練」、「時基競爭」、「企業流程再造」、「組織再造」、「6個標準差」、「基業長青」、「知識管理」、「藍海策略」、「平衡計分卡」、「精實創業」、「敏捷開發」等等管理流行風潮。這些流行風潮,往往聚焦於組織中的若干管理層面,透過易於理解的概念架構,倡導企業經營效率的提升之方。
譬如90年代流行的「企業流程再造」(BPR,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便鼓吹企業透過組織重整(restructuring)、縮小規模(downsize)、節省成本(cost down)等途徑,進行變革管理,以提升經營效率。追求「更高效率」這樣的經營觀影響至廣,決定了組織怎麼運用資源、評估績效、看待市場。過往談企業變革,因此多傾向透過各種工具性手段去「擰毛巾」,努力地把效率向上逼、把利潤擠出來。
在各種高管課程討論情境中,因此時有職涯歷程中曾經歷各種流行風潮的企業主管,質疑當下鑼鼓喧天、沸沸揚揚,在各行各業廣泛被關注甚至形成壓力的「數位轉型」,會不會只是又一波夾帶大量技術詞彙的新流行風潮,幾年後潮退了,便成過眼雲煙?
我們將以整本書的篇幅,來回答這個問題。最精簡的答案是:「這次不一樣。」
數位轉型的本質與關注重點,與過往對於幾十年間企業慣常的「變革」大相逕庭。而近年各行各業經營者面對數位轉型時,常有的困惑與懷疑,便常來自沒有意識到涵蓋甚廣的各種「這次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呢?本書將一層層去梳理、探討。簡單來說,所謂的「不一樣」,大致可歸納成以下幾點:
企業數位轉型是個受資本推動技術發展所驅動的「不斷再合理化」過程。
數位轉型對於多數企業而言,不是可有可無的經營選項,也不只是產、學、媒體炒作的產物,而是欲在市場中生存的必要改變。
企業的數位轉型牽涉到整個組織從對市場的假設,到組織內各階層、各功能別的各個環節。
就算隸屬於傳統定義的同一產業,不同企業因為既有資源與條件限制的差異,在如何「轉」這件事上可能就需要有截然不同的走法。
企業數位轉型為的不是短期利潤提升,而是長期的生存與成長。
企業數位轉型沒有可以涵蓋各業的「完整」理論架構,也不會有「導入即可使用」的「套裝解」(turnkey solution)。此外,若干經營者近幾十年已習慣引用的思考模式與概念架構,漸漸失去其攸關性。
過去管理界的轉型風潮中被奉為標竿者,常是在各領域經營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的大型企業。但當下談數位轉型,在各領域常被提出來當作師法對象者,卻常是一群數位原生企業。而就借鏡一事來說更為棘手的,是這些數位原生企業經營賴以發跡的純數位發展條件,又與多數實體原生企業在數位轉型過程中,所需應對的各種虛實整合挑戰狀況,大為不同。
數位轉型一方面要求企業放棄過往經營的若干經驗累積,另一方面則又是個無法一蹴而就的累積過程。有意義的數位轉型,建基於數據與創意/想像力這兩項互為因果的關鍵能耐長期累積。
企業數位轉型需要經營者有不怕「跟別人不一樣」的膽識。這樣的膽識,來自常識與勇氣。
1.3 數位轉型的本質:不斷再合理化
這次不一樣。但真要掌握這「不一樣」的內涵,則需要理解我們眼下所見市場中,各種數位發展背後的基本邏輯。這所謂的基本邏輯,由技術發展與資本累積這兩條軸線相互交織而成;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最容易加以掌握。
談及歷史,如果回溯一下(譬如說以Google Trends去查)這幾年常常聽到的各種數位相關浪潮,譬如大數據、物聯網、工業4.0、區塊鏈、FinTech、新零售等等,會發現它們開始出現在媒體上,一般大眾首次聽聞的時間,大約就在2012年到2015年之間。也就是說,距離現今幾年前,數位浪潮挾著與各行各業都有關的技術、趨勢以及語彙,「忽然」席捲而來。而數位轉型的機會與壓力,也才隨之而生。
為什麼就在那幾年間發生呢?我們再從技術與資本這兩個面向加以理解。
先從技術的角度來看。在只有大型企業才可能擁有電腦,而一部電腦勢必以龐然大物之姿塞滿整個房間的1950年代,當時的電腦硬碟體積像是大型冰箱,需要四個大漢合力才能移動,但是容量以MB計,卻只有個位數。30多年後的1980年代,桌上型的個人電腦剛剛問世,一個15MB容量的硬碟,便要價美金兩三千元。再過30多年後的今天,大家隨身帶出門的手機上頭,隨隨便便就有64GB、128GB乃至256GB的儲存量。而同一支手機的運算能量,甚至遠超過人類於60年代後期登陸月球時,登月小艇上各種儀器設施的總運算能量。
這般歷史對照的背後,有一條對理解數位之局而言非常重要的技術軸線。這條軸線,就是由廣義的「摩爾定律」所代表的,技術持續進步下,數位運算、儲存乃至傳輸成本的不斷下降。正是因為這些成本不斷下降,幾年前開始,過去僅限於實驗室裡如雲端計算、AI(人工智慧)、VR/AR、區塊鏈、IOT(物聯網)等數位應用項目,才得以進入市場,開始商業化的應用。
而如果從資本的角度來詮釋,則前次金融海嘯之際,各國為應急而施行又猛又急的量化寬鬆(QE)政策,額外創造出大量貨幣。這些新出現在市場上的「熱錢」四處尋找出路,讓全球在2010~2017年間,隨著前述技術面的進展,而有了一波創業熱潮。資本所吹動的「風口」,除了鼓舞如所謂「獨角獸」企業一類的現象外,也推升加大了各種數位相關技術應用的商業化速度與力道。
就這樣,錢推著技術尋找應用的出口,挹注各種數位相關的創新;各種創新隨後則改變了不同市場中既有的遊戲規則。用白話來說,錢的本質,便是它會不斷地追求以更合適的方式,去讓錢滾錢。也就是說,資本的慣性是循著市場上「最合理」的方式去累積,並且會不斷尋覓「更合理」的累積方向。依照社會經濟學巨擘韋伯(Max Weber)對資本主義市場發展所做的詮釋,現代經濟體中的資本,有著不斷尋覓「更合理」發展的「合理化」動能 —— 透過理性的計算,時時追求當下最合理的資源運用,以求報酬的最大化。
資本的累積,產業的興衰,市場中新模式的發展,因此便在「不斷再合理化」的歷程中堆疊、變化。根據這樣的詮釋,所謂的「合理」或「不合理」,便都視既有環境條件,而有其階段性。譬如說航海,人類從史前到有歷史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憑藉風帆航海;這在只有風帆的當時,自然是「最合理」的。但是,當輪船出現、相關技術到位達一定程度之後,再用風帆去謀求大量的商品運載,便不再合理了。這個階段「最合理」的運輸,靠的是蒸汽引擎推動的輪船。見微知著,在資本累積的過程中,市場上尋求「更合理」出路的金錢,便這般不斷透過創新的應用,推動著各種顛覆過往模式的新模式出現。
如果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則工商業的發展,其實是透過環環相扣的里程碑,長時間層層堆疊而成。每一個新里程碑的出現,都以前一個階段的發展成熟作為必要條件。若沒有複式簿記(現代會計系統的前身)的出現、合理的記帳方式被廣為接受,熟人和生人之間就很難集資組公司。而若沒有出現像荷屬東印度公司或英屬東印度公司這種公司型態的組織,在大航海時代從單次航行的募資、單次航行結算解散,發展到股東長期分擔利潤與風險、長期經營事業,那麼18世紀的蒸汽機技術,便很難大規模藉由鐵道公司、輪船公司、大規模紡織廠、礦場企業而開花結果成工業革命。而就是靠工業革命奠下的生產、物流基礎,讓20世紀初工廠通了電之後,便有福特T-car一類的大規模生產線。如果沒有大規模生產複雜產品的經驗與技術累積,那麼像智慧型手機這類數位時代各種新商業模式的觸媒,便不可能量產普及。
近20年,由數位原生企業打頭陣、全球實體原生企業隨之接踵投入的數位轉型,進行整合「位元」與「原子」的虛實整合。放到歷史發展的框架中看,那麼企業的數位轉型,就可說是經濟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也是自由市場中,資本驅動技術發展「不斷再合理化」常態的現階段歷程。
在這樣的背景下,若微觀地考量個別企業,那麼企業的經營,勢必也需要意識到過往「最合理」的做法,無論如何只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終將被「更合理」的作法所取代。因此,企業為了長期的生存,勢必需要與時俱進地「不斷再合理化」。因此,有意義的企業數位轉型,是企業在多變數位化環境中「不斷再合理化」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