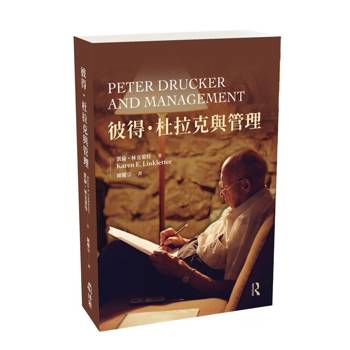第1章 歐洲人杜拉克
■ 引言
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曾寫道,杜拉克與美國另一位「外來訪客」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有許多共同之處:「杜拉克與托克維爾對這個國家及其機構所做的概括描述,比我們任何土生土長的兒女都更全面、更值得一讀」(Bennis, 1985, p. 27)。如同托克維爾,杜拉克是美國文化的旁觀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奧地利知識界所接受的教育與教養,以及親眼目睹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興起和德國社會機構失靈的經驗,為他日後成為以管理為核心的社會理論設計師做好了準備。出於歷史的偶然來到工業化的美國之後,杜拉克以美國為藍圖,尋求建立一個由各類機構組成的正常運作的社會,以避免像歐洲那樣發生社會結構分崩離析的情況。杜拉克擁有政治哲學、文學、經濟、社會學及其他學科方面的豐富知識,又有著身為歐洲移民的獨特視角,因此能夠在更大的變動與延續脈絡下觀察世界。他親身經歷的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動盪和極權統治所造成的大規模破壞,讓他很早就認識到必須在變動與延續之間取得平衡。在少年時期的奧地利經驗和青年時期的德國經驗驅使之下,杜拉克終其一生都在尋求建立一個由各類機構組成的尚可忍受的社會,以賦予人們存在的意義,並防止他目睹過的歷史重演。
■ 旁觀者杜拉克
在訪談和回憶錄中,杜拉克所講述的關於他人生與事業發展的故事,都一致強調了他在美國社會中所扮演的觀察者或旁觀者的角色。他經常引用出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詩劇《浮士德》(Faust)的一句話來自況:「生而能見,守望是務(Born to see, meant to look)」(Drucker, 1995)。透過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他讓自己與他聲稱所屬的文化保持距離。他生於奧地利,在德國受教育,卻像許多移民那樣被吸引到美國,那是因為美國在許多方面與舊世界的歐洲形成了對照。但與此同時,他為了成為美國人,又試圖擺脫歐洲人的身分,因而為自己打造出局外人而不是局內人的認同。身為自我形塑而成的旁觀者,杜拉克為自己譜寫了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身分:既不完全是美國人,也不完全是歐洲人。雖然他保留了奧地利口音,但他是以美國旁觀者的身分寫作,並藉此取得了對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發言權。不過,身為一個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Mises)、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逃離歐洲的人,杜拉克也只能從移民的視角寫作。他精心打造的這種身分認同選擇性地模糊了他的歐洲移民身分,但與此同時,這個身分也讓他無法完全投入和同化於美國的生活。
杜拉克的旁觀者身分對他很有用,有助於調和他那實際上不可能完全同化的狀況。其他移民在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中也經歷類似的困境,並且像杜拉克那樣,建構了局外人的身分。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在邊緣上》(On the Boundary)為他的自傳命名,藉此表達了他在美國社會邊緣的局外人處境。其他如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e Adorno)和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則採取類似托克維爾的立場,以局外人的眼光批評美國文化的同質性和麻木心智的作用(Heilbut, 1983)。不過,杜拉克則是將其旁觀者的身分,實際應用在他擔任的顧問角色上;他藉由與客戶的組織保持距離,維持了他的客觀性。南加州大學管理學教授華倫.班尼斯表示,杜拉克曾告訴他,顧問工作的訣竅之一就是「當一個局外人」(Bennis, 1985, p. 25)。
但局外人的身分還有另一項重要的功能。這種身分讓他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意義和地位,這對他來說是極其重要的課題;與此同時,這種身分也保障了他的個體性和獨特性。正如管理學教授班尼斯曾經評論的那樣,「彼得.杜拉克究竟歸屬何處並不清楚」。他顯然不歸屬於企業界,從來不曾成為他所分析的大型商業或非營利組織的一員。他在學術界不曾有過歸屬感,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我不是學者,我生活中向來有很大部分的時間是待在大學之外。」就功能性而言,旁觀者的角色讓杜拉克得以另闢蹊徑,在美國社會確立他自己的位置和地位,作為一名作家和觀察者公開闡述其「異於常人的觀點」,因為「旁觀者注定要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Drucker, 1978, p. 6)。
■ 在維也納的童年
若要理解杜拉克的管理理論,就必須瞭解他早年在奧地利和德國的生活背景。生於1909 年的杜拉克成長於維也納一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他父親亞多夫(Adolph)是一名經濟學家和政府高官,擔任過奧匈帝國政府的外貿局主任,曾發起薩爾茲堡音樂節,後來成為一名國際律師。他母親卡洛琳.龐迪(Caroline Bondi)學醫,也是很有天賦的音樂家(見圖1.1)。他姨丈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娶卡洛琳的妹妹)是重要的法學家和哲學家,也是奧地利戰後憲法的設計者(關於杜拉克對凱爾森理論的看法,本書第2 章有較詳盡的討論)。杜拉克後來形容凱爾森為「典型的政治學家⋯⋯他是一位擅長抽象思考的哲學家,重視法律和懲罰的本質」(Arnn, Masugi, and Schramm, 1984)。少年杜拉克在一個知識氛圍濃厚的環境中成長,得以親炙涵蓋文學、哲學、科學等範圍廣泛的討論,這樣的環境猶如庇護所,讓他避開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奧地利的動盪局勢(Tarrant, 1976; Drucker, 1978)。從許多方面來看,杜拉克所接受的,更像是戰前奧匈帝國君主制時代的教養。長期從德國與杜拉克通信的定價策略專家赫曼.西蒙(Hermann Simon)指出,杜拉克是「舊時代的人」,是維也納這種獨特環境下的產物,那裡「非常強調文化、藝術、音樂、歷史意識、都市性和國際開放⋯⋯另一位著名的威尼斯人﹝原文如此﹞、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稱之為『昨日的世界』」(Simon, 2002, p. 1)。
茨威格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把哈布斯堡王朝時代的維也納,形容為一個已經消失的安穩、充滿文化氣息、秩序井然的世界。在戰前的維也納,知識生產範圍之廣,令人驚歎: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的十二聲音階(twelve-tone scale)、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與心理分析、魯斯(Adolf Loos)與現代建築、維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對哲學學科的重構、克林姆(Gustav Klimt)與分離派(Secession)運動等等,不一而足。杜拉克曾有相當長的時間流連於霍夫曼史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主持的沙龍,那是早期維也納知識社會的縮影,政府高官、哈布斯堡王室成員、藝術家、哲學家等光輝熠熠的人物出入其間,彼此間形成了各種親密圈子。這些圈子所構成的,絕不會是一個大眾工業社會,而是一個關係緊密、擁有獨特文化與知識認同的都市,一個「夢之都」。
哈布斯堡王朝於1918 年覆滅而奧地利在一次大戰後開始衰落時,杜拉克年僅九歲。他對戰爭爆發的那段時間印象模糊,只隱約記得當時他和家人在海邊度假,但不記得這趟度假之旅由於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而提前結束(Drucker, 1978, pp. 34-35)。對於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年和帝國滅亡的後續影響,他則有所記憶。在戰爭之前,奧地利的高雅文化多半是由皇室和上層階級資助,因此隨著他們的衰亡,社會與經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動。光是通貨膨脹就足以造成巨大的壓力。1919 年,6 奧地利克朗相等於1 美元;到了1922 年8 月,要83,000 克朗才換得到1 美元(Large, 1990)。亞多夫.杜拉克的母親在丈夫斐迪南.龐德(Ferdinand Bond)去世後繼承了一筆可觀的遺產,但這筆財富因戰後通貨膨脹,幾乎化為烏有。根據杜拉克的說法,他奶奶的生活品質因此而大打折扣,「窮得像教堂裡的老鼠」(Drucker, 1978, pp. 10-13)。
■ 宗教背景
杜拉克向來不談論信仰與宗教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姆.史塔福(Tim Stafford)注意到,杜拉克雖然是一名基督徒,但他似乎「決心讓自己的信仰成為他面向讀者時一個次要的特徵。即便在寫作關於一些可以輕易歸入神學範疇的課題時,杜拉克也幾乎不曾以神學或聖經語彙來自我表達」。正如史塔福所指出,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Stafford, 1999, p. 44)。
猶太文化根源
杜拉克的宗教身分向來備受猜測和研究。似乎很明顯的是,如同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奧地利和德國的許多家族,杜拉克家族中有一些成員是猶太人。杜拉克曾告訴作家安茱兒.蓋博(Andrea Gabor)說,與他同一個時代和階級的幾乎每一名奧地利人,都會有猶太人親戚(Gabor, 2000, p. 300)。儘管那個時代的奧地利社會相當國際化,但反猶太主義始終存在,因此,未奉行猶太信仰的猶太人為了讓日子更為好過而改信基督宗教的情況,並非罕見。
根據彼得.史塔巴克(Peter Starbuck)在他書中的說法,杜拉克的父母就血統而言是猶太人,但他們在杜拉克出生前即已改信基督教路德宗。他們沒有在猶太教堂舉行婚禮,這表示他們是未奉行猶太教規的猶太人。他們後來從維也納的一個猶太人社區,搬到一個新教徒社區─ 第十九區德布靈(Dobling)的大街。他們所領到的市籍證書(Heimatschein)讓這個猶太家庭得以在這一區設籍居住。德布靈屬於富裕社區,有許多個別設計的大宅。杜拉克出生後不久就在路德教堂受洗(Starbuck, 2012, pp. 9-10)。
史塔巴克指出,有奧地利官方文件可資證明他的這些說法,儘管他在書中沒有註明資料來源。杜拉克的姨丈漢斯.凱爾森是猶太人,出生於布拉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如同那個時代的許多猶太人,凱爾森並非虔誠的猶太教徒,但猶太血統卻讓他在事業上面對諸多困難。為了避免遭到迫害和喪失工作機會,他在1905 年改信天主教(Lieblich, 2015)。杜拉克的妻子桃莉絲.杜拉克(Doris Drucker)在她的回憶錄中曾談到猶太人及其後裔的世界。根據桃莉絲的說法,她家族裡有「不是猶太人的猶太人」,其中包括她的奶奶。這類未奉行猶太教規的猶太人在他們正統猶太教鄰居看來並不是猶太人;以杜拉克家來說,他們慶祝的是聖誕節和復活節,而不是光明節(Hanukah)或逾越節(Passover)。桃莉絲的家鄉庫尼斯坦(Koenigstein)是一個多元族群與宗教信仰的小鎮,居民中有羅馬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新教徒,以及少數的猶太家庭(Drucker, 2004, pp. 70-71)。
這段家族歷史十分重要,因為它足以說明,在杜拉克的成長歲月中,宗教信仰對他和他生活圈子裡的其他人來說是相對不重要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和奧地利,至少是其較為富裕的地區,是各種不同族群共存之地。雖然反猶太主義確實存在,但並不像幾年後在納粹政權下那麼猖獗。桃莉絲在她的回憶錄中說,一旦納粹上台,即便她取得法律學位,也會因為其猶太血統而無法執業(Drucker, 2004, pp. 178-179)。桃莉絲透露的這些細節,讓我們瞭解到杜拉克和家人在納粹掌權後所面對的兩難處境。即便他們已經是基督徒,他們仍有親人屬於猶太裔,因此還是有可能成為納粹政權迫害的對象。
杜拉克的基督信仰
雖然杜拉克的基督徒身分不再是爭議性議題,但他究竟秉持著怎樣的基督信仰,則仍有所爭議。身為福音派基督徒的史塔福對此有敏銳的觀察。他指出,杜拉克認為信仰是個人的事,並認為個人的精神事務都屬於私事的範疇。在《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書中,杜拉克認為教會之所以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席捲歐洲,是因為宗教無法為一個人的社會生活提供意義:
自身的宗教經驗對個人來說也許是無價的;或許可以讓他恢復平靜,或許可以給他個人專屬的上帝,為他的職責和本性賦予理性的解釋。但基督教無法重塑社會,不能使社會和社群生活變得合理。(Drucker,1939a, p. 102;《經濟人的終結》,2020 年博雅出版,p. 140)
一方面生活在實體世界,另一方面卻又意識到這個實體世界終究沒有意義,這當中的張力在杜拉克看來,就是「沒有人可成為基督徒的根本原因所在。你只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基督徒。你知道嗎,每當有人說我是基督徒,我就不禁要皺眉頭」(Buford, 1991, p. 9)。除了社會生活經驗之外,認為宗教是私事的觀念,足以說明當杜拉克在面對似乎沒有希望的戰後社會時,齊克果思想對他的影響之大。這個觀念也足以說明為什麼他在著作中從不明確討論宗教或其影響力。
已有學者探討過基督教對杜拉克著作的影響,或這些著作的基督教根源(參見Bonaparte and Flaherty, 1970; Tarrant, 1976; Beatty, 1998; Linkletter and Maciariello, 2009)。另有一些人對杜拉克本人的個人宗教性表達了較為強烈的觀感。梅因哈特認為,杜拉克著作的精髓在於「他那深深根植於基督教傳統的毫不妥協地追求道德目的的衝動,以及其與作為經理人重要美德的實用智慧的關連」(Meynhardt, 2010, p. 618)。反之,圖比亞娜和亞爾認為,「杜拉克的道德之作與貫穿德國社會理論的潛在神學動機緊密相連」,他無非是一名「世俗化的德國神學家」(Toubianaand Yair, 2012, P. 170)。最後,費南德茲把杜拉克定位為一位「精神哲學家」,驅策他的是一個滲透在他管理著作中的內在道德指南針(Fernandez, 2009)。
似乎已很清楚,儘管杜拉克有可能是擁有個人宗教信仰的精神個體,但他的著作更多是得益於他對道德目的的堅持,而不是神學或特定的宗教信仰。杜拉克對於作為一門學科的神學是頗為不屑的(雖然他無疑非常重視宗教哲學)。關於神學,他認為:
人們極其厭倦於神學⋯⋯我很同情他們。我一直都認為,上帝顯然是喜愛多樣性的。祂可是創造了兩萬五千種蒼蠅。如果祂和我認識的某些神學家一樣的話,那就只會有一種蒼蠅了。(Steinfels, 2005)
據杜拉克的二十多年老友彼得.帕謝克透露,在他們多次的對話中,宗教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杜拉克在給自己定位的時候。杜拉克援引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的用語,說自己是一名「基督教保守無政府主義者」:
一個保守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 是的,那大致上就是我!我年紀越大,就越懷疑社會能否滿足人類希望實現的所有承諾。我認為過去50 年最核心的經驗之一,就是我們對那些煽動行為(Volksvergluckung)越來越感到失望,並且逐漸意識到,我們頂多只能讓社會變得可以容忍,而絕不可能讓它臻於完美⋯⋯這是一個保守的觀念,也是一個基督教式的觀念,因為它著重的是個人及其信仰,並且是要在來世而不是在現世當中追求事物的完美狀態。我是個保守的基督徒,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對於政府─ 不,這個詞用錯了,應該是說對於權力,我越來越有所警惕⋯⋯我一直都認為,權力是核心問題所在,對權力的渴望,而不是對性的渴望,是人類最大的罪⋯⋯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有別於傳統的無政府主義者,我同意治理與政府有存在的必要。(Paschek, 2020, p. 57)
如同帕謝克向筆者轉述的,杜拉克表明他自認是基督徒,因為他相信有些東西是超越社會的,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尊嚴並得到尊重。對杜拉克來說,精神性是與一個人的整體人格融為一體的,而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會具備的特徵(Paschek, 2023a, 2023b)。
■ 引言
華倫.班尼斯(Warren Bennis)曾寫道,杜拉克與美國另一位「外來訪客」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有許多共同之處:「杜拉克與托克維爾對這個國家及其機構所做的概括描述,比我們任何土生土長的兒女都更全面、更值得一讀」(Bennis, 1985, p. 27)。如同托克維爾,杜拉克是美國文化的旁觀者。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奧地利知識界所接受的教育與教養,以及親眼目睹國家社會主義在德國興起和德國社會機構失靈的經驗,為他日後成為以管理為核心的社會理論設計師做好了準備。出於歷史的偶然來到工業化的美國之後,杜拉克以美國為藍圖,尋求建立一個由各類機構組成的正常運作的社會,以避免像歐洲那樣發生社會結構分崩離析的情況。杜拉克擁有政治哲學、文學、經濟、社會學及其他學科方面的豐富知識,又有著身為歐洲移民的獨特視角,因此能夠在更大的變動與延續脈絡下觀察世界。他親身經歷的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動盪和極權統治所造成的大規模破壞,讓他很早就認識到必須在變動與延續之間取得平衡。在少年時期的奧地利經驗和青年時期的德國經驗驅使之下,杜拉克終其一生都在尋求建立一個由各類機構組成的尚可忍受的社會,以賦予人們存在的意義,並防止他目睹過的歷史重演。
■ 旁觀者杜拉克
在訪談和回憶錄中,杜拉克所講述的關於他人生與事業發展的故事,都一致強調了他在美國社會中所扮演的觀察者或旁觀者的角色。他經常引用出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詩劇《浮士德》(Faust)的一句話來自況:「生而能見,守望是務(Born to see, meant to look)」(Drucker, 1995)。透過刻意把自己塑造成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他讓自己與他聲稱所屬的文化保持距離。他生於奧地利,在德國受教育,卻像許多移民那樣被吸引到美國,那是因為美國在許多方面與舊世界的歐洲形成了對照。但與此同時,他為了成為美國人,又試圖擺脫歐洲人的身分,因而為自己打造出局外人而不是局內人的認同。身為自我形塑而成的旁觀者,杜拉克為自己譜寫了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身分:既不完全是美國人,也不完全是歐洲人。雖然他保留了奧地利口音,但他是以美國旁觀者的身分寫作,並藉此取得了對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發言權。不過,身為一個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Mises)、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赫伯特.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在差不多同一個時期逃離歐洲的人,杜拉克也只能從移民的視角寫作。他精心打造的這種身分認同選擇性地模糊了他的歐洲移民身分,但與此同時,這個身分也讓他無法完全投入和同化於美國的生活。
杜拉克的旁觀者身分對他很有用,有助於調和他那實際上不可能完全同化的狀況。其他移民在成為美國人的過程中也經歷類似的困境,並且像杜拉克那樣,建構了局外人的身分。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在邊緣上》(On the Boundary)為他的自傳命名,藉此表達了他在美國社會邊緣的局外人處境。其他如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e Adorno)和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則採取類似托克維爾的立場,以局外人的眼光批評美國文化的同質性和麻木心智的作用(Heilbut, 1983)。不過,杜拉克則是將其旁觀者的身分,實際應用在他擔任的顧問角色上;他藉由與客戶的組織保持距離,維持了他的客觀性。南加州大學管理學教授華倫.班尼斯表示,杜拉克曾告訴他,顧問工作的訣竅之一就是「當一個局外人」(Bennis, 1985, p. 25)。
但局外人的身分還有另一項重要的功能。這種身分讓他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意義和地位,這對他來說是極其重要的課題;與此同時,這種身分也保障了他的個體性和獨特性。正如管理學教授班尼斯曾經評論的那樣,「彼得.杜拉克究竟歸屬何處並不清楚」。他顯然不歸屬於企業界,從來不曾成為他所分析的大型商業或非營利組織的一員。他在學術界不曾有過歸屬感,這一點他自己也承認:「⋯⋯我不是學者,我生活中向來有很大部分的時間是待在大學之外。」就功能性而言,旁觀者的角色讓杜拉克得以另闢蹊徑,在美國社會確立他自己的位置和地位,作為一名作家和觀察者公開闡述其「異於常人的觀點」,因為「旁觀者注定要從不同的角度看事物」(Drucker, 1978, p. 6)。
■ 在維也納的童年
若要理解杜拉克的管理理論,就必須瞭解他早年在奧地利和德國的生活背景。生於1909 年的杜拉克成長於維也納一個上層中產階級家庭。他父親亞多夫(Adolph)是一名經濟學家和政府高官,擔任過奧匈帝國政府的外貿局主任,曾發起薩爾茲堡音樂節,後來成為一名國際律師。他母親卡洛琳.龐迪(Caroline Bondi)學醫,也是很有天賦的音樂家(見圖1.1)。他姨丈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娶卡洛琳的妹妹)是重要的法學家和哲學家,也是奧地利戰後憲法的設計者(關於杜拉克對凱爾森理論的看法,本書第2 章有較詳盡的討論)。杜拉克後來形容凱爾森為「典型的政治學家⋯⋯他是一位擅長抽象思考的哲學家,重視法律和懲罰的本質」(Arnn, Masugi, and Schramm, 1984)。少年杜拉克在一個知識氛圍濃厚的環境中成長,得以親炙涵蓋文學、哲學、科學等範圍廣泛的討論,這樣的環境猶如庇護所,讓他避開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奧地利的動盪局勢(Tarrant, 1976; Drucker, 1978)。從許多方面來看,杜拉克所接受的,更像是戰前奧匈帝國君主制時代的教養。長期從德國與杜拉克通信的定價策略專家赫曼.西蒙(Hermann Simon)指出,杜拉克是「舊時代的人」,是維也納這種獨特環境下的產物,那裡「非常強調文化、藝術、音樂、歷史意識、都市性和國際開放⋯⋯另一位著名的威尼斯人﹝原文如此﹞、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稱之為『昨日的世界』」(Simon, 2002, p. 1)。
茨威格的回憶錄《昨日的世界》(The World of Yesterday)把哈布斯堡王朝時代的維也納,形容為一個已經消失的安穩、充滿文化氣息、秩序井然的世界。在戰前的維也納,知識生產範圍之廣,令人驚歎:荀白克(Arnold Schoenberg)的十二聲音階(twelve-tone scale)、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與心理分析、魯斯(Adolf Loos)與現代建築、維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對哲學學科的重構、克林姆(Gustav Klimt)與分離派(Secession)運動等等,不一而足。杜拉克曾有相當長的時間流連於霍夫曼史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主持的沙龍,那是早期維也納知識社會的縮影,政府高官、哈布斯堡王室成員、藝術家、哲學家等光輝熠熠的人物出入其間,彼此間形成了各種親密圈子。這些圈子所構成的,絕不會是一個大眾工業社會,而是一個關係緊密、擁有獨特文化與知識認同的都市,一個「夢之都」。
哈布斯堡王朝於1918 年覆滅而奧地利在一次大戰後開始衰落時,杜拉克年僅九歲。他對戰爭爆發的那段時間印象模糊,只隱約記得當時他和家人在海邊度假,但不記得這趟度假之旅由於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而提前結束(Drucker, 1978, pp. 34-35)。對於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年和帝國滅亡的後續影響,他則有所記憶。在戰爭之前,奧地利的高雅文化多半是由皇室和上層階級資助,因此隨著他們的衰亡,社會與經濟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動。光是通貨膨脹就足以造成巨大的壓力。1919 年,6 奧地利克朗相等於1 美元;到了1922 年8 月,要83,000 克朗才換得到1 美元(Large, 1990)。亞多夫.杜拉克的母親在丈夫斐迪南.龐德(Ferdinand Bond)去世後繼承了一筆可觀的遺產,但這筆財富因戰後通貨膨脹,幾乎化為烏有。根據杜拉克的說法,他奶奶的生活品質因此而大打折扣,「窮得像教堂裡的老鼠」(Drucker, 1978, pp. 10-13)。
■ 宗教背景
杜拉克向來不談論信仰與宗教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姆.史塔福(Tim Stafford)注意到,杜拉克雖然是一名基督徒,但他似乎「決心讓自己的信仰成為他面向讀者時一個次要的特徵。即便在寫作關於一些可以輕易歸入神學範疇的課題時,杜拉克也幾乎不曾以神學或聖經語彙來自我表達」。正如史塔福所指出,這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Stafford, 1999, p. 44)。
猶太文化根源
杜拉克的宗教身分向來備受猜測和研究。似乎很明顯的是,如同19 世紀末、20 世紀初奧地利和德國的許多家族,杜拉克家族中有一些成員是猶太人。杜拉克曾告訴作家安茱兒.蓋博(Andrea Gabor)說,與他同一個時代和階級的幾乎每一名奧地利人,都會有猶太人親戚(Gabor, 2000, p. 300)。儘管那個時代的奧地利社會相當國際化,但反猶太主義始終存在,因此,未奉行猶太信仰的猶太人為了讓日子更為好過而改信基督宗教的情況,並非罕見。
根據彼得.史塔巴克(Peter Starbuck)在他書中的說法,杜拉克的父母就血統而言是猶太人,但他們在杜拉克出生前即已改信基督教路德宗。他們沒有在猶太教堂舉行婚禮,這表示他們是未奉行猶太教規的猶太人。他們後來從維也納的一個猶太人社區,搬到一個新教徒社區─ 第十九區德布靈(Dobling)的大街。他們所領到的市籍證書(Heimatschein)讓這個猶太家庭得以在這一區設籍居住。德布靈屬於富裕社區,有許多個別設計的大宅。杜拉克出生後不久就在路德教堂受洗(Starbuck, 2012, pp. 9-10)。
史塔巴克指出,有奧地利官方文件可資證明他的這些說法,儘管他在書中沒有註明資料來源。杜拉克的姨丈漢斯.凱爾森是猶太人,出生於布拉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如同那個時代的許多猶太人,凱爾森並非虔誠的猶太教徒,但猶太血統卻讓他在事業上面對諸多困難。為了避免遭到迫害和喪失工作機會,他在1905 年改信天主教(Lieblich, 2015)。杜拉克的妻子桃莉絲.杜拉克(Doris Drucker)在她的回憶錄中曾談到猶太人及其後裔的世界。根據桃莉絲的說法,她家族裡有「不是猶太人的猶太人」,其中包括她的奶奶。這類未奉行猶太教規的猶太人在他們正統猶太教鄰居看來並不是猶太人;以杜拉克家來說,他們慶祝的是聖誕節和復活節,而不是光明節(Hanukah)或逾越節(Passover)。桃莉絲的家鄉庫尼斯坦(Koenigstein)是一個多元族群與宗教信仰的小鎮,居民中有羅馬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新教徒,以及少數的猶太家庭(Drucker, 2004, pp. 70-71)。
這段家族歷史十分重要,因為它足以說明,在杜拉克的成長歲月中,宗教信仰對他和他生活圈子裡的其他人來說是相對不重要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和奧地利,至少是其較為富裕的地區,是各種不同族群共存之地。雖然反猶太主義確實存在,但並不像幾年後在納粹政權下那麼猖獗。桃莉絲在她的回憶錄中說,一旦納粹上台,即便她取得法律學位,也會因為其猶太血統而無法執業(Drucker, 2004, pp. 178-179)。桃莉絲透露的這些細節,讓我們瞭解到杜拉克和家人在納粹掌權後所面對的兩難處境。即便他們已經是基督徒,他們仍有親人屬於猶太裔,因此還是有可能成為納粹政權迫害的對象。
杜拉克的基督信仰
雖然杜拉克的基督徒身分不再是爭議性議題,但他究竟秉持著怎樣的基督信仰,則仍有所爭議。身為福音派基督徒的史塔福對此有敏銳的觀察。他指出,杜拉克認為信仰是個人的事,並認為個人的精神事務都屬於私事的範疇。在《經濟人的終結》(The End of Economic Man)一書中,杜拉克認為教會之所以不能阻止法西斯主義席捲歐洲,是因為宗教無法為一個人的社會生活提供意義:
自身的宗教經驗對個人來說也許是無價的;或許可以讓他恢復平靜,或許可以給他個人專屬的上帝,為他的職責和本性賦予理性的解釋。但基督教無法重塑社會,不能使社會和社群生活變得合理。(Drucker,1939a, p. 102;《經濟人的終結》,2020 年博雅出版,p. 140)
一方面生活在實體世界,另一方面卻又意識到這個實體世界終究沒有意義,這當中的張力在杜拉克看來,就是「沒有人可成為基督徒的根本原因所在。你只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基督徒。你知道嗎,每當有人說我是基督徒,我就不禁要皺眉頭」(Buford, 1991, p. 9)。除了社會生活經驗之外,認為宗教是私事的觀念,足以說明當杜拉克在面對似乎沒有希望的戰後社會時,齊克果思想對他的影響之大。這個觀念也足以說明為什麼他在著作中從不明確討論宗教或其影響力。
已有學者探討過基督教對杜拉克著作的影響,或這些著作的基督教根源(參見Bonaparte and Flaherty, 1970; Tarrant, 1976; Beatty, 1998; Linkletter and Maciariello, 2009)。另有一些人對杜拉克本人的個人宗教性表達了較為強烈的觀感。梅因哈特認為,杜拉克著作的精髓在於「他那深深根植於基督教傳統的毫不妥協地追求道德目的的衝動,以及其與作為經理人重要美德的實用智慧的關連」(Meynhardt, 2010, p. 618)。反之,圖比亞娜和亞爾認為,「杜拉克的道德之作與貫穿德國社會理論的潛在神學動機緊密相連」,他無非是一名「世俗化的德國神學家」(Toubianaand Yair, 2012, P. 170)。最後,費南德茲把杜拉克定位為一位「精神哲學家」,驅策他的是一個滲透在他管理著作中的內在道德指南針(Fernandez, 2009)。
似乎已很清楚,儘管杜拉克有可能是擁有個人宗教信仰的精神個體,但他的著作更多是得益於他對道德目的的堅持,而不是神學或特定的宗教信仰。杜拉克對於作為一門學科的神學是頗為不屑的(雖然他無疑非常重視宗教哲學)。關於神學,他認為:
人們極其厭倦於神學⋯⋯我很同情他們。我一直都認為,上帝顯然是喜愛多樣性的。祂可是創造了兩萬五千種蒼蠅。如果祂和我認識的某些神學家一樣的話,那就只會有一種蒼蠅了。(Steinfels, 2005)
據杜拉克的二十多年老友彼得.帕謝克透露,在他們多次的對話中,宗教只出現過一次,那就是杜拉克在給自己定位的時候。杜拉克援引亨利.亞當斯(Henry Adams)的用語,說自己是一名「基督教保守無政府主義者」:
一個保守的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者─ 是的,那大致上就是我!我年紀越大,就越懷疑社會能否滿足人類希望實現的所有承諾。我認為過去50 年最核心的經驗之一,就是我們對那些煽動行為(Volksvergluckung)越來越感到失望,並且逐漸意識到,我們頂多只能讓社會變得可以容忍,而絕不可能讓它臻於完美⋯⋯這是一個保守的觀念,也是一個基督教式的觀念,因為它著重的是個人及其信仰,並且是要在來世而不是在現世當中追求事物的完美狀態。我是個保守的基督徒,也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對於政府─ 不,這個詞用錯了,應該是說對於權力,我越來越有所警惕⋯⋯我一直都認為,權力是核心問題所在,對權力的渴望,而不是對性的渴望,是人類最大的罪⋯⋯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是無政府主義者,但有別於傳統的無政府主義者,我同意治理與政府有存在的必要。(Paschek, 2020, p. 57)
如同帕謝克向筆者轉述的,杜拉克表明他自認是基督徒,因為他相信有些東西是超越社會的,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尊嚴並得到尊重。對杜拉克來說,精神性是與一個人的整體人格融為一體的,而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才會具備的特徵(Paschek, 2023a, 202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