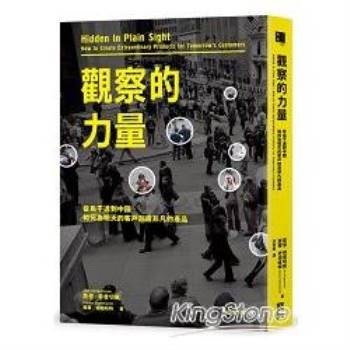緒論以全新眼光看待平凡活動
或許你會覺得我這一行充滿異國情調、冒險犯難,甚至有點光怪陸離,但最終我只是在努力理解人們行事的動機。
我的工作有一大部分是發現及解析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之事──許多聞名全球的公司願意砸重金了解的事。這份工作或許需要到猶他州做週日禮拜;步上東京市郊某家倉儲式DIY大賣場的走道;或在破曉時分起床記錄某條郊區街道是怎樣醒來向世界道早安。
其他時候我會注意極端、放眼未來,主動出擊,以便更了解那些今日尚屬異數、但也許有朝一日將蔚為主流的行為:到馬來西亞向放高利貸的人借錢;在遙遠的中國沙漠費盡唇舌請警察不要拘留我;騎摩托車載人穿梭於尖峰時段的坎帕拉;或把錢將口袋塞得鼓鼓的,漫步於里約幾條犯罪猖獗的街道。
大部分事情都一樣的高風險、高報酬。
就我個人而言,覺得在上海陪同女伴進行買鞋探險,比在喀布爾討論二手AK步槍的價錢更危險。在上海的鞋店,只要顯露出相機的蹤跡,保全人員就會找上你,認定你是想搞「反向工程」的競爭對手。在喀布爾,沒人擔心拿相機揮來揮去的外國人,槍在這兒早已被視為雅致的複製品,來者皆可買。
沒錯,我的工作確實有它的魅力。我曾躲了一天衛兵、睡在馬雅神殿的屋頂,一覺醒來便迎接叢林樹葉上方的絕美晨曦。也曾將腳踏車綁在椰子船上,小心翼翼沿著蚊子海岸航行。當你喜愛自己做的事,並明白那可能對你出手大方的客戶極具價值,工作與玩樂之間的界線就會刻意模糊了。
從平凡情境看到市場火花
通常我都會隨身攜帶相機,而現在帶的則是一部由厚重拆到最精簡的佳能EOS 5D Mark II,它創造的價值早已超越了它的定價,為我們的後代捕捉了千千萬萬個瞬間,讓我們用來分析,讓夥伴、研究參與人員和其他人得以觀看。我不是專業攝影師,但你可以說我是專業的平凡觀察員。
每造訪一個地方,我幾乎都會花很多時間觀察當地平凡人用平凡的物品做平凡的事:拿手機打電話、從皮夾抽取現鈔或信用卡、拿加油槍加油。在這些平凡情境中我看到的──隱藏於其他人「一覽無遺」之中的──或許正是能為客戶開啟尚未開發之全球市場的火花。我試著找出能賦予客戶明確競爭優勢的機會,無論他們供應的是低技術的肥皂條或最高科技的無線網路。有些機會純由獲利驅動;其他則結合獲利和協助處理世界最迫切社會問題的心願:醫療、教育和貧窮等等。
我在這種種情境中看到的是我們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驅動人類行為的刺激因素。「為什麼,」我反覆地問:「為什麼他們要那樣做呢?為什麼要用那種特別的方式做呢?」
了解決定背後真正的「為什麼」
如果你想了解人,就必須了解人是如何在原始狀態、在自然環境、在混亂及灰色地帶、在有因果關係、不斷變遷的世界運作。
我非常尊敬能夠進行嚴密科學實驗、密切觀察更改一項或多項變因會如何影響結果的學術研究人員。他們的發現為我的工作奠定穩固的基礎(就如同你在本書所見的一切)。過去堪稱是蹩腳學者的我,後來雖然開始領略到非傳統的客群尋找法,卻赫然發現,自己根本不可能將生命本質硬塞進枯燥的學術期刊論文裡了。
我的工作──以及這本書──是先在表面下收集一些雜七雜八的事實,再用這些零碎的東西,以更多彩多姿、更有質感的方式看世界。接下來,我們可以運用這些嶄新的觀念鍛造出更好的關係、解決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製造更實用、更令人嚮往的物品,進而更欣賞這個世界原來的風貌。
改變焦距,放大細節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我們有七十多億 個理由必須調整觀察的距離:要改變焦距,放大細節。東京一座火車站、貝魯特一間咖啡館、喀布爾一名學校教師的公寓──才能聚焦於整張「大圖」。拜網際網路、現代物流和供應鏈所賜,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顧客(或你顧客的顧客),但果不努力找出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想要什麼和為什麼想要的細微差異,你將會喪失這些機會。
當然,世界上也並非人人都想要同樣的東西,也不是人人都買得起同樣的東西,但你一定會訝異人們會設法得到什麼,以及他們想要什麼──就算資源貧乏。全世界有近八成的民眾每天生活費不到十美元, 但卻有超過半數的人口擁有手機。
這些數字說明了發展中世界的購買力,也闡明像手機這樣極具吸引力的技術可以重新塑造全球市場。本書裡,你會一再看到我舉手機為例;固然有部分是因為我個人生涯有一大段重要時期投效於通訊業,但更重要的是,手機是近來最顯著的最大「破壞力」之一──個人又便利的連結。那或許看來已不夠激進,但把手伸進口袋取出一件裝置就可隨時隨地立刻聯繫到幾乎任何人,以及可當眾也可私下這麼做的選擇,這兩件事已讓全球各地的人際互動改頭換面。
「技術」不應該讓你多想一下
當你輕彈開關,使房間燈火通明之際,你不會特地去思考燈之所以能亮起的一切要素:家裡的線路;用來製造燈罩的模子;燈泡;讓全城鎮線路得以串接的實驗和最後的標準化作業;如何發電、儲電和運電。在那間原本漆黑的房間,有比了解燈為什麼會亮更要緊的事,比如小心不要被咖啡桌絆倒。當你按下開關,「技術」不會讓你多想一下。
不會,也不應該──只要它設計得夠好,足以「正常運作」。雖然有生動活潑的全球技術場景,但社會只有一小群人有肚量忍受主流民眾認為「還不到位」之事。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就大部分商品而言,如果現行標準看來夠好,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去嘗試或許可以但也或許不可以運作的新事物呢?
這裡值得先退一步,討論我所謂「技術」一詞的含意。在我職業生涯的許多時間點上,包含了在東京一家研究室擔任概念設計科學研究員期間,既埋首於尖端技術,也與一群技術專家為伍──他們的職責是擴展事物的極限,從蓄電池到燃料電池,從新款顯示器到新型態的無線連結不一而足。我也曾為許多全球頂尖技術及工程公司效力,曾獲授權購買最新科技、研究世界一些最高科技的城市(東京、首爾、舊金山等),以及造訪一些早世界其他地區一步推廣新技術的社區。要做好我的工作,就需要對技術發展到哪裡,以及要往何處去有基礎的認識。
當新技術變成理所當然
但,當我想到「技術」,非單指電子或其相關服務,我給「技術」下的定義遠比這還廣泛,包括初始覺知(initial awareness)及決定採納的驅動因素;消費者對於某種技術的感知價值(perceived value)的理解程度,以及那些假設有多正確;那個價值又是如何逐步應用於真實世界等等。如你將在本書後文所見,我也深感興趣的是,當初我們對於某種技術用途所抱持的假設,如何在技術推出後發生變化。技術不限於有電池、顯示器、網路連結或電線之類的東西,儘管愈來愈多物品擁有這些特徵。在歷史的不同階段,鐵製平底鍋、機械錶和鉛筆都曾被視為現代科技的工具,直到人們開始將其性能、穩定製造及長久存在視為理所當然時,它們便開始被認為習以為常,不被注意。
每一項被放上市場的新技術,在推出時都有它將如何運用的主張或假想,但唯有透過真實的體驗,「用途」才會確立,且為背景、個性、動力和所得等諸多因素形塑。有些技術到達了演化的里程碑,促進或激勵了新的用法,或新的採納原因。就電子郵件或聊天室而言,激勵因素或許是網路的功效:更多人同時在網路上會帶來更大的效益,而這種效益又會吸引更多人上網。對電話等技術產品來說,那或許是尺寸縮小、可以攜帶,以及便於攜帶該產品的環境。電池壽命、堅固耐用或價錢也是重點。
新的使用者、新的使用環境和新的使用方式都會造就新的行為模式,而新的行為模式會反過來改變我們對於某項技術的期望。
舊技術不是消失,只是不再受到注意
有些公司傾向直接讓技術以最天然未加工的型態推出,看市場(或子市場,如早期用戶)作何反應。諸如中國、日本和南韓等國──通常是靠近製造過程的國家──較屬意在市場看到較多實驗,因為先推出再精煉設計的成本較低。(個人對於日本電子製造業的觀察是:許多產品會先為日本市場設計,通常要到第三版才成熟得可以進軍較不寬容的國際市場。)而且有既有品牌要保護的公司通常會對上市商品較保守,不想弄倒現有的搖錢樹。
「舊技術消失不再受到注意」的假設,大抵上是西方的想法。這類技術的退場之所以較為平順,是因為沒有人提醒我們技術在那裡;因為技術如預期運作;因為當這一類的技術失靈時,它不會整體遭到取代,而只有部分(想想烤麵包機)或不會凸顯隱含技術的組合方式(想想噴墨印表機的墨水匣)被替換;抑或是因為它包含某種商業模式,使我們難以詳加思考持續使用成本(想想訂閱)。但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公共建設沒那麼可靠且使用情況較可能超過負荷,也有較多資源受限的消費者,以及鼓勵審慎考慮使用成本的商業模式。
如此一來,消費者便會想起商品隱含的技術,於是他們所在的社會對於技術會保有較高的素養(literacy)。一如技術在全球採納不均,它的退場也不平均。過去我曾投入多年時間追蹤維修文化在從阿富汗到印度、奈及利亞到印尼各地的演變,以及人們如何取得素養、技能和感悟力來修理最複雜的技術。這不意味著了解技術的渴望在那些地方特別強,而是那裡了解技術、領會技術可能有不同使用方式的必要性在比較高,因為它基本上算是一種實用的謀生本領。如我將在後文探討的,這種了解技術根本特性的高度意識、素養和動力,可能造就出乎原設計師預料的不同使用模式(如果有所謂設計師的話),以及值得注意的新商業機會。
無視可能帶來的周邊效益
二○○六年,我造訪烏干達時,曾經深入了解人們樂於分享通訊工具(特別是手機)和自己擁有的程度。對客戶來說,這個答案會影響他們到底要重新設計既有產品,或繼續製造數億件已經上市的商品。此次計畫包括調查一種名為村落電話的新服務:將手機通訊帶到當時處於網路末端(時至今日,這些地方幾乎全為網路涵蓋,足見變遷速度之快)的鄉村。計畫由美國葛萊敏基金會(Grameen Foundation USA)與當地微型貸款組織及MTN(區域行動電信供應商)合辦,並由諾基亞(Nokia)和三星(Samsung)支援手機。案子固然有趣,但最令我驚訝的是親眼目睹一個遠早於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業務,儘管沒有設計過程,也沒有正式的服務供應商:行動銀行(mobile banking)的先例之一。
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是個熙來攘往的都會中心,人口超過一百四十萬。一如許多城市,它也以工作機會吸引一波波來自烏干達鄉間的移民。那些移民常把家人留在村裡,由於該地許多農村缺乏民眾負擔得起的基礎通訊建設,這種分離更顯得難熬。村落電話計畫提供了技術──手機、車用蓄電池(電網不及之地的常見電力來源),以及電視一般的強力天線,插入電話就能接受到最遠三十公里外的手機訊號(預設值接近二十公里)。
微型貸款組織提供貸款給居住特定村落的企業家(通常為女性),而之後她可向借用電話的村民收取費用。毫無意外地,供應通訊給之前沒有通訊的地方是非常吸引人的生意,民眾也願意花錢購買便利。但村落電話背後的組織,以及在那個空間工作的每一個人,皆無視於這種連通性可能帶來的周邊效益。他們沒看到自己擁有或可協助人們克服迫切日常問題的工具,因為他們並未費心研究問題出在哪裡──例如遠距轉移金錢的需要。
窮則變,變則通
讓我們假設阿基基想從坎帕拉把錢送回村裡給妻子瑪莎妮。在過去,他有兩種方式可以做這件事:一是開立銀行帳戶(如果他有必要的文件,也被視為有益的顧客),把錢存進去,傳話回村裡說帳戶有錢了,然後請瑪莎妮搭一段路途遙遠的計程車到最近的銀行把錢領出來。除了搭計程車的不便和費用,銀行處理系統亦時有延誤,意味著村民上銀行不見得領得到錢。銀行也不太願意處理這種小金額提款,所以瑪莎妮得等到阿基基存到「合理」存款金額才能提領。阿基基的另一個辦法是請駛往家鄉的公車司機幫忙把現金交給瑪莎妮,但沒人敢保證司機會把錢交給對的人,或他值得信賴。這完全不是所謂的安全交易。
我們就是在沒有柏油路的烏干達鄉村進行研究的那段期間,反覆聽到人們談到「sente」,談到在無法取得正式匯款服務之下,卻能夠透過現有通訊商業模式及公共建設提供替代方法來送錢。阿基基不必直接送現金給瑪莎妮,可拿那筆錢向群集在坎帕拉納卡塞洛市場(Nakasero Market)的眾多攤販之一購買行動電話通話額度,而他也不必親自使用(事實上,二○○六年時阿基基沒有手機的可能性高得多) ,他可以打電話給村裡電話亭業者,給她使用通話時間的密碼,讓她得以跟使用的村民收取費用,之後,業者會將與通話時間等值的現金,在扣除二至三成的交易佣金後支付給瑪莎妮。無需銀行、無需公車、無需計程車,問題迎刃而解。
沒有人知道是誰率先嘗試這種非正式的「sente」程序。沒有剪綵儀式,沒有媒體歌功頌德,沒有紀念性的匾額,也沒有首次交易的確實紀錄。事情很單純,就是有人試著想出如何運用現有資源來節省時間與心力。而這種實務迅速傳播開來,因為那些電話亭通常也是資訊流動的社交中心,所以對一名顧客奏效的方式,很快便傳給另一名顧客知情。儘管葛萊敏基金會、大型行動通訊業者和手機製造商等組織盡心盡力,但要設計出如此順應當地風土民情的東西,仍超出他們所想像。
順應民情,將通話時間兌換為貨幣的業務
這種非正式的sente絕非完美:沒有自動化的收受機制(收受者必須回電給寄送者確認錢已送達);偶有混亂:錢誤送到同名同姓的人手上;佣金金額可能引發爭執;有時電話亭業者無法一口氣兌現所有通話時間。雖然現有的行為展現了需求,但這些顯而易見的缺點,仍暗示一個設計正式服務的機會。
約莫同一時間,在鄰國肯亞,英國沃達豐通訊(Vodafone UK)的尼克‧休斯(Nick Hughes)和蘇西‧隆尼(Sosie Lonie),正拿著英國國際發展部的種子基金進行試驗,探究更有效率的微型貸款支付方式。隨著試驗進行,從與顧客的互動之中清楚反映出一點:商業性的人際轉款服務甚有機會。二○○七年開辦之際,他們預計第一年能吸引二十萬名顧客,而這個數字他們不到一個月便達成。這些預付的顧客多數都為電話追加通話時間;有些則在實行在地版的sente。今天,肯亞的M-Pesa被公認為世界最成功的行動銀行服務之一。而烏干達電信(Uganda Telecom)也在那時開辦正式的手機錢包業務:M-Sente。
以下這些與轉移通話時間,以及將通話時間兌為貨幣有關的實務,在行動銀行的成長方面扮演著要角:增進民眾對手機用途的素養;建立對轉移抽象事物(通話時間、金錢)的信任;協助鑑定需要改善的領域;以及最重要的,灌注對可能成果的期待。
要探究現有行為,並理解如何運用此一洞見做為推知未來的基礎,有許多種方法。其一是找出「突發行為」(emergent behavior),基本上就是人們最近才開始做,而如果條件正確,可能會變得普遍的事情。而可能誘發突發行為的因素包括文化模因(cultural meme)──例如:奧運金牌得主在頒獎台上比的手勢、瓦解根深蒂固社會規範的天然災害,以及採納某種商業模式與後續規避它的方式,例如:手機顧客打給對方後立刻掛斷,做為不必被收通話費的聯絡方式。
有個技巧可以顯現或強化這種行為,就是誘發會刺激人們採取新行動的情境。另一種較合乎道德的技巧則是找出已置身極端情境(至少從主流觀點來看)的人──所處情勢或背景迫使他們無視現存社會或法律規範,而充分利用可用資源者。我們稱之為不得已的創新。這些人則常被稱為「極端」或「先驅使用者」。
不合常理的行為背後必有因
新山是馬來西亞位於星馬邊界上的邊境城鎮,市容破舊,以想要砍幾毛油價的經濟觀光客、取道進入城市工作的移民工和多采多姿的夜生活聞名。當地似乎也有賭博問題,因為這裡住宅街道的特色之一是依附在路標之上、琳瑯滿目的高利短期貸款廣告,而殘留的舊廣告痕跡在在表明:此地貸款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
一個客戶想在新山推出新的全球行動金融服務,所以我和一支團隊來到這裡,探究當地民眾對金錢的態度和作為,而這個反常現象激起了我們的好奇:為什麼會有人以百分之百的利率借錢兩天呢?那不合常理,但既然發生,就一定有它的道理。為探究這點,我們原本可以訪問那些極端或先驅使用者,但還有一個較具同理心的方式,可真正讓研究人員設身處地:我們決定自己申辦這些貸款,了解極端融資的詳情。除了實質抵押品(他們扣留我們一台相機到還完債為止),高利貸業者的風險降低策略還包括開車到我們住的地方、影印我的女助理艾妮塔的身分證,以及拿他的照相手機拍她的照片。這最後一項舉動無非暗示:她就是終極抵押品。
相信多數讀者會想當然耳地認定,你是你的身分唯一的擁有者,雖可能被歹徒冒用,但你就是不能簽字放棄。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情況,對於那些幾乎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個人身分(以及隨之而來的名聲)是他們唯一擁有的抵押品,而實際上,他們已經把它交給其他人掌控了。以新山為例,未按時償還借款者,首先是住家會被潑紅色油漆,如果這樣還不還錢,那他們的照片會被張貼在社區各處,附帶一句「別借錢給這個人」,讓借方的家人感到丟臉、幫他還錢來保護貸方的投資。事實證明這種手法的威脅猶如芒刺在背,使人不得不準時還款,因為在馬來西亞文化,「向人借錢」的標籤顯然非常可恥,足以為高利貸業者加油添薪。污名不能用美金和林吉特(ringgit,馬來西亞貨幣)衡量,但同樣是經濟因素。
運用「為什麼」找出影響人們做決定的因素
這種「對比的理性」──文化價值的差異導致決策過程不同──幾乎可以在任何跨文化互動之中起作用,因此培養一種第六感格外重要:了解「為什麼」。
為什麼中低階層的印度人不接受塔塔納努(Tata Nano)這種針對他們的預算設計、起價約兩千九百美元的汽車?為什麼反倒傾心於貴十一倍的馬魯帝鈴木男高音(Maruti Suzuki Alto)?一般的觀念是,低所得民眾會消費符合其微薄預算的商品和服務,即所謂便宜貨。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你運用「為什麼」的觀念,藉由和最清楚事實的人──即他們自己──討論挖掘低所得民眾想要什麼的真相,你會發現:他們堪稱世上最難搞的一群顧客。正因他們必須讓每一盧比發揮最大效益,他們最負擔不起的就是設計不良的產品。就算手上有兩千九百美元,他們也承受不起把錢花在一部據說會自己著火的車子,而落得無車可用且無法替換的代價。
納努仍有無窮的潛力,因為一部兩千九百美元的汽車──能開的一部──仍可能成為改變市場的破壞性因素,就像一百美元的筆記型電腦或二十美元的手機那樣。這些物品如果真能協助人們克服面臨的主要障礙──運輸、教育、通訊等等──並且設計成令人嚮往、會為其擁有者傳達正面形象傳達的物品,仍可能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強而有力的工具。想要提供這類解決方案的企業、非營利組織、政府及科學家,必須先就他們意欲服務的對象進行抽絲剝繭、著重細微差異的了解。人們為什麼會過那樣的生活?如何在受薪工作匱乏時應付生活成本?有哪些因素在任何特定的轉折點刺激他們的決定?
或許你會覺得我這一行充滿異國情調、冒險犯難,甚至有點光怪陸離,但最終我只是在努力理解人們行事的動機。
我的工作有一大部分是發現及解析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之事──許多聞名全球的公司願意砸重金了解的事。這份工作或許需要到猶他州做週日禮拜;步上東京市郊某家倉儲式DIY大賣場的走道;或在破曉時分起床記錄某條郊區街道是怎樣醒來向世界道早安。
其他時候我會注意極端、放眼未來,主動出擊,以便更了解那些今日尚屬異數、但也許有朝一日將蔚為主流的行為:到馬來西亞向放高利貸的人借錢;在遙遠的中國沙漠費盡唇舌請警察不要拘留我;騎摩托車載人穿梭於尖峰時段的坎帕拉;或把錢將口袋塞得鼓鼓的,漫步於里約幾條犯罪猖獗的街道。
大部分事情都一樣的高風險、高報酬。
就我個人而言,覺得在上海陪同女伴進行買鞋探險,比在喀布爾討論二手AK步槍的價錢更危險。在上海的鞋店,只要顯露出相機的蹤跡,保全人員就會找上你,認定你是想搞「反向工程」的競爭對手。在喀布爾,沒人擔心拿相機揮來揮去的外國人,槍在這兒早已被視為雅致的複製品,來者皆可買。
沒錯,我的工作確實有它的魅力。我曾躲了一天衛兵、睡在馬雅神殿的屋頂,一覺醒來便迎接叢林樹葉上方的絕美晨曦。也曾將腳踏車綁在椰子船上,小心翼翼沿著蚊子海岸航行。當你喜愛自己做的事,並明白那可能對你出手大方的客戶極具價值,工作與玩樂之間的界線就會刻意模糊了。
從平凡情境看到市場火花
通常我都會隨身攜帶相機,而現在帶的則是一部由厚重拆到最精簡的佳能EOS 5D Mark II,它創造的價值早已超越了它的定價,為我們的後代捕捉了千千萬萬個瞬間,讓我們用來分析,讓夥伴、研究參與人員和其他人得以觀看。我不是專業攝影師,但你可以說我是專業的平凡觀察員。
每造訪一個地方,我幾乎都會花很多時間觀察當地平凡人用平凡的物品做平凡的事:拿手機打電話、從皮夾抽取現鈔或信用卡、拿加油槍加油。在這些平凡情境中我看到的──隱藏於其他人「一覽無遺」之中的──或許正是能為客戶開啟尚未開發之全球市場的火花。我試著找出能賦予客戶明確競爭優勢的機會,無論他們供應的是低技術的肥皂條或最高科技的無線網路。有些機會純由獲利驅動;其他則結合獲利和協助處理世界最迫切社會問題的心願:醫療、教育和貧窮等等。
我在這種種情境中看到的是我們多數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驅動人類行為的刺激因素。「為什麼,」我反覆地問:「為什麼他們要那樣做呢?為什麼要用那種特別的方式做呢?」
了解決定背後真正的「為什麼」
如果你想了解人,就必須了解人是如何在原始狀態、在自然環境、在混亂及灰色地帶、在有因果關係、不斷變遷的世界運作。
我非常尊敬能夠進行嚴密科學實驗、密切觀察更改一項或多項變因會如何影響結果的學術研究人員。他們的發現為我的工作奠定穩固的基礎(就如同你在本書所見的一切)。過去堪稱是蹩腳學者的我,後來雖然開始領略到非傳統的客群尋找法,卻赫然發現,自己根本不可能將生命本質硬塞進枯燥的學術期刊論文裡了。
我的工作──以及這本書──是先在表面下收集一些雜七雜八的事實,再用這些零碎的東西,以更多彩多姿、更有質感的方式看世界。接下來,我們可以運用這些嶄新的觀念鍛造出更好的關係、解決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製造更實用、更令人嚮往的物品,進而更欣賞這個世界原來的風貌。
改變焦距,放大細節
從商業的角度來看,我們有七十多億 個理由必須調整觀察的距離:要改變焦距,放大細節。東京一座火車站、貝魯特一間咖啡館、喀布爾一名學校教師的公寓──才能聚焦於整張「大圖」。拜網際網路、現代物流和供應鏈所賜,全世界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是你的顧客(或你顧客的顧客),但果不努力找出他們是誰,以及他們想要什麼和為什麼想要的細微差異,你將會喪失這些機會。
當然,世界上也並非人人都想要同樣的東西,也不是人人都買得起同樣的東西,但你一定會訝異人們會設法得到什麼,以及他們想要什麼──就算資源貧乏。全世界有近八成的民眾每天生活費不到十美元, 但卻有超過半數的人口擁有手機。
這些數字說明了發展中世界的購買力,也闡明像手機這樣極具吸引力的技術可以重新塑造全球市場。本書裡,你會一再看到我舉手機為例;固然有部分是因為我個人生涯有一大段重要時期投效於通訊業,但更重要的是,手機是近來最顯著的最大「破壞力」之一──個人又便利的連結。那或許看來已不夠激進,但把手伸進口袋取出一件裝置就可隨時隨地立刻聯繫到幾乎任何人,以及可當眾也可私下這麼做的選擇,這兩件事已讓全球各地的人際互動改頭換面。
「技術」不應該讓你多想一下
當你輕彈開關,使房間燈火通明之際,你不會特地去思考燈之所以能亮起的一切要素:家裡的線路;用來製造燈罩的模子;燈泡;讓全城鎮線路得以串接的實驗和最後的標準化作業;如何發電、儲電和運電。在那間原本漆黑的房間,有比了解燈為什麼會亮更要緊的事,比如小心不要被咖啡桌絆倒。當你按下開關,「技術」不會讓你多想一下。
不會,也不應該──只要它設計得夠好,足以「正常運作」。雖然有生動活潑的全球技術場景,但社會只有一小群人有肚量忍受主流民眾認為「還不到位」之事。從消費者的觀點來看,就大部分商品而言,如果現行標準看來夠好,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去嘗試或許可以但也或許不可以運作的新事物呢?
這裡值得先退一步,討論我所謂「技術」一詞的含意。在我職業生涯的許多時間點上,包含了在東京一家研究室擔任概念設計科學研究員期間,既埋首於尖端技術,也與一群技術專家為伍──他們的職責是擴展事物的極限,從蓄電池到燃料電池,從新款顯示器到新型態的無線連結不一而足。我也曾為許多全球頂尖技術及工程公司效力,曾獲授權購買最新科技、研究世界一些最高科技的城市(東京、首爾、舊金山等),以及造訪一些早世界其他地區一步推廣新技術的社區。要做好我的工作,就需要對技術發展到哪裡,以及要往何處去有基礎的認識。
當新技術變成理所當然
但,當我想到「技術」,非單指電子或其相關服務,我給「技術」下的定義遠比這還廣泛,包括初始覺知(initial awareness)及決定採納的驅動因素;消費者對於某種技術的感知價值(perceived value)的理解程度,以及那些假設有多正確;那個價值又是如何逐步應用於真實世界等等。如你將在本書後文所見,我也深感興趣的是,當初我們對於某種技術用途所抱持的假設,如何在技術推出後發生變化。技術不限於有電池、顯示器、網路連結或電線之類的東西,儘管愈來愈多物品擁有這些特徵。在歷史的不同階段,鐵製平底鍋、機械錶和鉛筆都曾被視為現代科技的工具,直到人們開始將其性能、穩定製造及長久存在視為理所當然時,它們便開始被認為習以為常,不被注意。
每一項被放上市場的新技術,在推出時都有它將如何運用的主張或假想,但唯有透過真實的體驗,「用途」才會確立,且為背景、個性、動力和所得等諸多因素形塑。有些技術到達了演化的里程碑,促進或激勵了新的用法,或新的採納原因。就電子郵件或聊天室而言,激勵因素或許是網路的功效:更多人同時在網路上會帶來更大的效益,而這種效益又會吸引更多人上網。對電話等技術產品來說,那或許是尺寸縮小、可以攜帶,以及便於攜帶該產品的環境。電池壽命、堅固耐用或價錢也是重點。
新的使用者、新的使用環境和新的使用方式都會造就新的行為模式,而新的行為模式會反過來改變我們對於某項技術的期望。
舊技術不是消失,只是不再受到注意
有些公司傾向直接讓技術以最天然未加工的型態推出,看市場(或子市場,如早期用戶)作何反應。諸如中國、日本和南韓等國──通常是靠近製造過程的國家──較屬意在市場看到較多實驗,因為先推出再精煉設計的成本較低。(個人對於日本電子製造業的觀察是:許多產品會先為日本市場設計,通常要到第三版才成熟得可以進軍較不寬容的國際市場。)而且有既有品牌要保護的公司通常會對上市商品較保守,不想弄倒現有的搖錢樹。
「舊技術消失不再受到注意」的假設,大抵上是西方的想法。這類技術的退場之所以較為平順,是因為沒有人提醒我們技術在那裡;因為技術如預期運作;因為當這一類的技術失靈時,它不會整體遭到取代,而只有部分(想想烤麵包機)或不會凸顯隱含技術的組合方式(想想噴墨印表機的墨水匣)被替換;抑或是因為它包含某種商業模式,使我們難以詳加思考持續使用成本(想想訂閱)。但在世界大部分的地方,公共建設沒那麼可靠且使用情況較可能超過負荷,也有較多資源受限的消費者,以及鼓勵審慎考慮使用成本的商業模式。
如此一來,消費者便會想起商品隱含的技術,於是他們所在的社會對於技術會保有較高的素養(literacy)。一如技術在全球採納不均,它的退場也不平均。過去我曾投入多年時間追蹤維修文化在從阿富汗到印度、奈及利亞到印尼各地的演變,以及人們如何取得素養、技能和感悟力來修理最複雜的技術。這不意味著了解技術的渴望在那些地方特別強,而是那裡了解技術、領會技術可能有不同使用方式的必要性在比較高,因為它基本上算是一種實用的謀生本領。如我將在後文探討的,這種了解技術根本特性的高度意識、素養和動力,可能造就出乎原設計師預料的不同使用模式(如果有所謂設計師的話),以及值得注意的新商業機會。
無視可能帶來的周邊效益
二○○六年,我造訪烏干達時,曾經深入了解人們樂於分享通訊工具(特別是手機)和自己擁有的程度。對客戶來說,這個答案會影響他們到底要重新設計既有產品,或繼續製造數億件已經上市的商品。此次計畫包括調查一種名為村落電話的新服務:將手機通訊帶到當時處於網路末端(時至今日,這些地方幾乎全為網路涵蓋,足見變遷速度之快)的鄉村。計畫由美國葛萊敏基金會(Grameen Foundation USA)與當地微型貸款組織及MTN(區域行動電信供應商)合辦,並由諾基亞(Nokia)和三星(Samsung)支援手機。案子固然有趣,但最令我驚訝的是親眼目睹一個遠早於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業務,儘管沒有設計過程,也沒有正式的服務供應商:行動銀行(mobile banking)的先例之一。
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是個熙來攘往的都會中心,人口超過一百四十萬。一如許多城市,它也以工作機會吸引一波波來自烏干達鄉間的移民。那些移民常把家人留在村裡,由於該地許多農村缺乏民眾負擔得起的基礎通訊建設,這種分離更顯得難熬。村落電話計畫提供了技術──手機、車用蓄電池(電網不及之地的常見電力來源),以及電視一般的強力天線,插入電話就能接受到最遠三十公里外的手機訊號(預設值接近二十公里)。
微型貸款組織提供貸款給居住特定村落的企業家(通常為女性),而之後她可向借用電話的村民收取費用。毫無意外地,供應通訊給之前沒有通訊的地方是非常吸引人的生意,民眾也願意花錢購買便利。但村落電話背後的組織,以及在那個空間工作的每一個人,皆無視於這種連通性可能帶來的周邊效益。他們沒看到自己擁有或可協助人們克服迫切日常問題的工具,因為他們並未費心研究問題出在哪裡──例如遠距轉移金錢的需要。
窮則變,變則通
讓我們假設阿基基想從坎帕拉把錢送回村裡給妻子瑪莎妮。在過去,他有兩種方式可以做這件事:一是開立銀行帳戶(如果他有必要的文件,也被視為有益的顧客),把錢存進去,傳話回村裡說帳戶有錢了,然後請瑪莎妮搭一段路途遙遠的計程車到最近的銀行把錢領出來。除了搭計程車的不便和費用,銀行處理系統亦時有延誤,意味著村民上銀行不見得領得到錢。銀行也不太願意處理這種小金額提款,所以瑪莎妮得等到阿基基存到「合理」存款金額才能提領。阿基基的另一個辦法是請駛往家鄉的公車司機幫忙把現金交給瑪莎妮,但沒人敢保證司機會把錢交給對的人,或他值得信賴。這完全不是所謂的安全交易。
我們就是在沒有柏油路的烏干達鄉村進行研究的那段期間,反覆聽到人們談到「sente」,談到在無法取得正式匯款服務之下,卻能夠透過現有通訊商業模式及公共建設提供替代方法來送錢。阿基基不必直接送現金給瑪莎妮,可拿那筆錢向群集在坎帕拉納卡塞洛市場(Nakasero Market)的眾多攤販之一購買行動電話通話額度,而他也不必親自使用(事實上,二○○六年時阿基基沒有手機的可能性高得多) ,他可以打電話給村裡電話亭業者,給她使用通話時間的密碼,讓她得以跟使用的村民收取費用,之後,業者會將與通話時間等值的現金,在扣除二至三成的交易佣金後支付給瑪莎妮。無需銀行、無需公車、無需計程車,問題迎刃而解。
沒有人知道是誰率先嘗試這種非正式的「sente」程序。沒有剪綵儀式,沒有媒體歌功頌德,沒有紀念性的匾額,也沒有首次交易的確實紀錄。事情很單純,就是有人試著想出如何運用現有資源來節省時間與心力。而這種實務迅速傳播開來,因為那些電話亭通常也是資訊流動的社交中心,所以對一名顧客奏效的方式,很快便傳給另一名顧客知情。儘管葛萊敏基金會、大型行動通訊業者和手機製造商等組織盡心盡力,但要設計出如此順應當地風土民情的東西,仍超出他們所想像。
順應民情,將通話時間兌換為貨幣的業務
這種非正式的sente絕非完美:沒有自動化的收受機制(收受者必須回電給寄送者確認錢已送達);偶有混亂:錢誤送到同名同姓的人手上;佣金金額可能引發爭執;有時電話亭業者無法一口氣兌現所有通話時間。雖然現有的行為展現了需求,但這些顯而易見的缺點,仍暗示一個設計正式服務的機會。
約莫同一時間,在鄰國肯亞,英國沃達豐通訊(Vodafone UK)的尼克‧休斯(Nick Hughes)和蘇西‧隆尼(Sosie Lonie),正拿著英國國際發展部的種子基金進行試驗,探究更有效率的微型貸款支付方式。隨著試驗進行,從與顧客的互動之中清楚反映出一點:商業性的人際轉款服務甚有機會。二○○七年開辦之際,他們預計第一年能吸引二十萬名顧客,而這個數字他們不到一個月便達成。這些預付的顧客多數都為電話追加通話時間;有些則在實行在地版的sente。今天,肯亞的M-Pesa被公認為世界最成功的行動銀行服務之一。而烏干達電信(Uganda Telecom)也在那時開辦正式的手機錢包業務:M-Sente。
以下這些與轉移通話時間,以及將通話時間兌為貨幣有關的實務,在行動銀行的成長方面扮演著要角:增進民眾對手機用途的素養;建立對轉移抽象事物(通話時間、金錢)的信任;協助鑑定需要改善的領域;以及最重要的,灌注對可能成果的期待。
要探究現有行為,並理解如何運用此一洞見做為推知未來的基礎,有許多種方法。其一是找出「突發行為」(emergent behavior),基本上就是人們最近才開始做,而如果條件正確,可能會變得普遍的事情。而可能誘發突發行為的因素包括文化模因(cultural meme)──例如:奧運金牌得主在頒獎台上比的手勢、瓦解根深蒂固社會規範的天然災害,以及採納某種商業模式與後續規避它的方式,例如:手機顧客打給對方後立刻掛斷,做為不必被收通話費的聯絡方式。
有個技巧可以顯現或強化這種行為,就是誘發會刺激人們採取新行動的情境。另一種較合乎道德的技巧則是找出已置身極端情境(至少從主流觀點來看)的人──所處情勢或背景迫使他們無視現存社會或法律規範,而充分利用可用資源者。我們稱之為不得已的創新。這些人則常被稱為「極端」或「先驅使用者」。
不合常理的行為背後必有因
新山是馬來西亞位於星馬邊界上的邊境城鎮,市容破舊,以想要砍幾毛油價的經濟觀光客、取道進入城市工作的移民工和多采多姿的夜生活聞名。當地似乎也有賭博問題,因為這裡住宅街道的特色之一是依附在路標之上、琳瑯滿目的高利短期貸款廣告,而殘留的舊廣告痕跡在在表明:此地貸款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
一個客戶想在新山推出新的全球行動金融服務,所以我和一支團隊來到這裡,探究當地民眾對金錢的態度和作為,而這個反常現象激起了我們的好奇:為什麼會有人以百分之百的利率借錢兩天呢?那不合常理,但既然發生,就一定有它的道理。為探究這點,我們原本可以訪問那些極端或先驅使用者,但還有一個較具同理心的方式,可真正讓研究人員設身處地:我們決定自己申辦這些貸款,了解極端融資的詳情。除了實質抵押品(他們扣留我們一台相機到還完債為止),高利貸業者的風險降低策略還包括開車到我們住的地方、影印我的女助理艾妮塔的身分證,以及拿他的照相手機拍她的照片。這最後一項舉動無非暗示:她就是終極抵押品。
相信多數讀者會想當然耳地認定,你是你的身分唯一的擁有者,雖可能被歹徒冒用,但你就是不能簽字放棄。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情況,對於那些幾乎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個人身分(以及隨之而來的名聲)是他們唯一擁有的抵押品,而實際上,他們已經把它交給其他人掌控了。以新山為例,未按時償還借款者,首先是住家會被潑紅色油漆,如果這樣還不還錢,那他們的照片會被張貼在社區各處,附帶一句「別借錢給這個人」,讓借方的家人感到丟臉、幫他還錢來保護貸方的投資。事實證明這種手法的威脅猶如芒刺在背,使人不得不準時還款,因為在馬來西亞文化,「向人借錢」的標籤顯然非常可恥,足以為高利貸業者加油添薪。污名不能用美金和林吉特(ringgit,馬來西亞貨幣)衡量,但同樣是經濟因素。
運用「為什麼」找出影響人們做決定的因素
這種「對比的理性」──文化價值的差異導致決策過程不同──幾乎可以在任何跨文化互動之中起作用,因此培養一種第六感格外重要:了解「為什麼」。
為什麼中低階層的印度人不接受塔塔納努(Tata Nano)這種針對他們的預算設計、起價約兩千九百美元的汽車?為什麼反倒傾心於貴十一倍的馬魯帝鈴木男高音(Maruti Suzuki Alto)?一般的觀念是,低所得民眾會消費符合其微薄預算的商品和服務,即所謂便宜貨。事實並非如此。如果你運用「為什麼」的觀念,藉由和最清楚事實的人──即他們自己──討論挖掘低所得民眾想要什麼的真相,你會發現:他們堪稱世上最難搞的一群顧客。正因他們必須讓每一盧比發揮最大效益,他們最負擔不起的就是設計不良的產品。就算手上有兩千九百美元,他們也承受不起把錢花在一部據說會自己著火的車子,而落得無車可用且無法替換的代價。
納努仍有無窮的潛力,因為一部兩千九百美元的汽車──能開的一部──仍可能成為改變市場的破壞性因素,就像一百美元的筆記型電腦或二十美元的手機那樣。這些物品如果真能協助人們克服面臨的主要障礙──運輸、教育、通訊等等──並且設計成令人嚮往、會為其擁有者傳達正面形象傳達的物品,仍可能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強而有力的工具。想要提供這類解決方案的企業、非營利組織、政府及科學家,必須先就他們意欲服務的對象進行抽絲剝繭、著重細微差異的了解。人們為什麼會過那樣的生活?如何在受薪工作匱乏時應付生活成本?有哪些因素在任何特定的轉折點刺激他們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