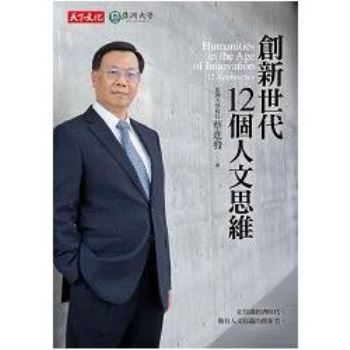創校不過十餘年的亞洲大學,卻已經在國際囊括許多榮耀──英國《泰晤士報》「2014年創校五十年內全球百大潛力大學」全球第九十九名、「2015年亞洲百大最佳大學」全球第九十三名、「2015年金磚五國暨新興經濟體二十三國百大大學」全球第八十六名、「2015~2016年全球八百大最佳大學」全球第六百七十名,成為全球最年輕的「四個百大」大學。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說:「一所真正的大學必須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學術性的教學,二是科學的研究,三是創造性的文化生活。」亞大,正朝著這個方向邁進,而本書則將由主導這一切的幕後推手──亞大創校校長、同時也是現任校長的蔡進發,親自闡述他的治校理念、人生故事與省思,為年輕學子提供未來二十年的生命指南。
本書收錄蔡進發所寫給年輕人的十二種人文思維:創新、跨領域學習、獨立思考、專注、國際化、美學、理性與感性、性別平等、價值判斷、終身學習、成敗以及社會服務,全是依據他過去在美國求學、教學、研究和回國後從事教育工作的心得而寫成。
在這本書裡,蔡進發的眼光不局限在台灣,而是以全世界做為理想的場域,用他多年來所見所聞淬鍊出獨到的人生看法與心靈感觸,勇敢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勵年輕人拓展自己人生的深度與廣度。
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教育,也是蔡進發所熟悉的地方,因此,本書一開始,談到亞大的誕生,便從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史丹佛大學等校談起,也描繪了當初心目中理想大學的起創點。
大學在近一千年前起源於義大利,如今的波隆納大學被公認為世界第一所大學,它的建築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巴洛克風格為主。亞大創校時便以教育初衷來砥礪自己,因此,將巴洛克風格定為學校建築的標記。
哈佛大學是美國文理學科的起源,創校團隊特地從哈佛大學帶回一塊紅磚,以這一塊磚為基準,每一棟校舍的建材、顏色,都和它嚴整一致,如同當初立定以哈佛追求卓越、人文關懷精神來辦學的初衷一般。
這個起點是由外而內的漸進過程,如同本書中談到的「境教」,希望營造一個合宜的環境,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下,一點一滴形塑學子們「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的價值觀。亞大有一個膾炙人口的講座──「諾貝爾在亞大」,講者從嫻熟經濟、財政到擅長科技、醫學,每個人的專業都達到巔峰成就,人生歷練也不同凡響,因而說起故事來句句珠璣。
有一年,生理醫學獎得主、威爾剛理論之父穆拉德(Dr. Ferid Murad),在亞大分享自己的學習過程時,指出一句對他影響至深的話:「我的老師說,『我在課堂上講的,有百分之五十是對的,百分之五十是錯的。』」
這句震人心的話,所代表的正是本書希望告訴讀者的,即使面對授課老師與學術權威,每個人都得獨立思考,自己判斷哪些是對、哪些是錯,哪些該做、哪些不能苟同。也正因為獨立思考如此關鍵,以致於當我們放眼世界,便不難發現,各級學校紛紛以教育改革,提升下一世代的思考能力。
然而,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穆拉德卻是一位可樂的愛好者,就連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是,為什麼?原來,在他們求學的年代,美國還不流行喝咖啡提神,可樂才是主流;每當做實驗的時間冗長,身體疲倦,內心卻不願放下,便會抓一把零錢到販賣機投幣,買一罐可樂,連沒飯都沒吃,就回到實駣室大口灌下。
得到「補給」之後,又能拚上幾個小時。垃圾桶裡至少累積了四、五個可樂空罐,記錄下這群人為了做好一件事是如何地專注、心無旁騖。
從世界的另一端回到台灣,創辦亞洲大學,蔡進發堅信,大學的本質就是國際化。大學是傳授與創造知識的地方,必須隨時掌握全球趨勢、訊息和產業動態,甚至掌握全世界的最新知識,因此,不應該也不允許將觸角局限在一個區域。
台灣年輕人的未來,也應該建構在全世界之上,而非局限在自己的家鄉。只是,近年來台灣經濟趨於成熟,能夠雇用的人數有限,因此年輕人的國際移動力,也就是在海外做事的能力,變得更加重要。
然而,一所學校要培養出人格成熟的青年,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美學教育。而美術館,是提供美學教育重要的學習場域。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主張用觀念去界定「美之本質」,是西方美學的起源。柏拉圖則是哲學美學的開創者,他繼承蘇格拉底的說法,提出「美的本質」問題,以哲學思辨去探討審美的對象和美學原理,在西元前三、四百年就開創了西方美學的研究。在東方,大概也在西元前五百年左右,就有審美方面的論述,例如孔子提「里仁為美」、孟子說「充實之謂美」、老子稱「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莊子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遠在古代,孔子就是美學教育的提倡者,近如民國初年,蔡元培校長也在北京大學倡導美學教育。
在如今的台灣,許多大學都樂意設立圖書館、實驗室,因為裡面的藏書、設備,反映一所學校的學術深度,卻很少看到大學設立美術館。但是在亞大,卻這麼做了,本書中也娓娓道來美學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當初設立的緣由。
同樣在精神層面,本書還探討了理性與感性的作用與關係。理性是邏輯分析的能力、感性是情感同理的能力,兩者平衡,才有成熟的人格去面對複雜的人生。可是,生於網路世代的人,感性、理性都不成熟的狀況特別明顯。
感性太過,造成極端的情緒問題;理性太過,卻失去對人性情義的理解,這樣的人格,大家應該也不陌生,就如那些只知道根據法律條文判決,卻違背常識、脫離社會現象的「恐龍法官」。
1980年代的比利時,有件討論許久、值得深思的案子。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半夜時分,有位女子從陽台跌到馬路上,陷入昏迷。一名路過的男子發現了,趁機洗劫她身上的財物,卻擔心她無人搭救而傷重不治,於是離開前先報警。事後警察從監視器中看到經過,起訴了這名男子。
這個案子在布魯塞爾討論許久,最後,這名男子被判無罪。法官的判決書這樣寫著:「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脆弱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相對於拯救生命,搶劫財物不值得一提。
「雖然就法律來說,我們不該因為一個人的善行而赦免他其他的犯罪,但是如果判決他有罪,將對社會秩序產生極度負面的影響,我寧願看到下一個搶劫犯拯救一條生命,也不願看到遵守法律的無罪者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法律判決固然依賴純粹理性的邏輯推論,但是一位法官如果感性與理性平衡,就能全面衡量情、理、法的輕重得失,做出最有利於社會的判決。
本書也談到了性別平等的問題,而這一切的根本,其實可以說是源自於尊重和平等。尊重,意謂著尊重他的差異及獨立;平等,則是給予相同的機會。如果能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就會理解,戀愛、結婚、成家是每個生命都享有的權利,社會尊重每個生命的選擇,就不該因為他的性別選擇而有差別待遇。那麼,許多同性戀愛、同性婚姻的爭議,也就豁然而解了。
不過,尊重不代表放任。在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學校、家長不僅應該提供他們完整的性教育,也要培養他們獨立負責的能力,幫助他們了解事情的因果關係,為自己的選擇負起最後責任。
父母以身作則尊重差異,是給下一代最好的示範。蔡進發坦誠,他那個世代的人,受教育及傳統影響,要完全放棄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大部分人一時可能有些難度,但還是會盡力提高自覺,時時提醒自己。
他以六百年前的警訊提醒當代的人們,來自農村的少女貞德,以瘦弱的身軀穿起盔甲,率領軍隊奔向戰火最前線,終於扭轉了法國的頹勢,最後卻因為不公平的審判而死於熊熊烈火。因此,我們應該也必須記住,六百年後的現在,不應該再有任何理由毀滅任何異於凡俗的靈魂。
法國小說家兼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曾說過:「人生就是你所有抉擇的總和。」(Life is the sum of all your choices.)本書也從「價值觀」的角度切入,說明那是每個人心中的一把尺,它決定你要做什麼、不做什麼或怎麼做。
不過,蔡進發提醒,年輕人應該勇於嘗試、勇於挑戰,卻不認為應該一味堅持自我。這中間的平衡點,可以用《大學》所說的「止於至善」來評估。
至善,是考慮每一個人的利益、損失,讓整體結果達到最佳狀態。有些人常堅持自己的想法,並以擇善固執美其名,但如果個人的堅持影響整體的最佳利益,則整體的最佳利益應該為最高指導原則。
人生就是一連串學習的過程,張忠謀便曾在一場演講中指出,當他回顧幾十年的工作生涯,發現只有前五年,用得到在大學、研究所所學的20%∼30%,之後的工作生涯,直接用到的部分幾乎等於零。
對於即將獨自揚帆進入人生大海的年輕人,這番話也許聽得驚心動魄,不過我相信,對每個已經在社會歷練的人來說,這番話再真實不過。進入職場,要不被淘汰甚至掌握機會謀得發展,必得與時俱進,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終身學習。
自我學習的方法很多元,除了閱讀,進入社會工作後,出差或旅行的機會也將增加,在蔡進發的經驗中,這是學習的大好機會,一方面幫你檢驗你所知的,同時讓你認識你未知的。這段不斷努力的過程,本書提出一個觀點,就是一個階段的成或敗,不代表永遠的成或敗。莫札特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莫札特三歲展現音樂天賦,六歲譜出小步舞曲,十一歲寫出第一部歌劇,十三歲被大主教提名為樂團首席,當真是無上風光。如果此時人生戛然而止,莫札特就是世人眼中永遠的音樂神童。
可惜,人生必須不斷往前。莫札特十七歲這年,樂團換了一位親王新主教管理。他限制莫札特的創作領域,甚至公開嘲笑他是飯桶、智障。一顆耀眼的鑽石突然掉入泥濘,年輕的心靈必然痛苦莫名。
如果莫札特憤恨所有努力不過鏡花水月,從此自暴自棄,他的人生大概也就淪為眾人惋惜的「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幸好,他並未放棄自己。
當命運之神再度眷顧莫札特,從慕尼黑寄來一份歌劇創作的邀請,他立刻抓住機會表現,結果首演時獲得熱烈迴響,之後並以獨立作曲家的身分到奧地利,從此展開自由創作。
在莫札特短短三十五年的人生中,留下許多重要音樂類型的作品:協奏曲、奏鳴曲、交響樂、小夜曲、嬉遊曲等,成為後來古典音樂的主要形式,撼動了音樂史的發展。
人的一生總是起起伏伏,現在眼中的成功或失敗,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後再回首,豈知不是另一番光景?放在時間的長河裡,成功或失敗難有定論,換一個角度觀察,成敗也難有絕對的定義,但是,只要每件事都全力以赴,問心無愧,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以正面的態度看待,就是成功。
這是個混亂的時代。貧富差距、國際衝突、溫室效應⋯⋯,很多問題政府不見得有能力解決,反倒在民間,透過服務的力量,更能有效率的降低富人與窮人、富國與窮國的衝突;尤其是年輕人的浪漫熱情,更能打破現實的框架。
本書希望為年輕人培養更宏大的胸懷氣度,便將社會服務納入其中。社會服務是這個時代的公民素養,培養新時代的公民,大學責無旁貸。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我每天不斷提醒自己,我的生活,不管內在或外在,都奠基在他人(包括活著的和逝去的)的努力成果之上。因此,我必須盡力奉獻自己,希望以同等的貢獻回報長久以來從他人身上所獲得的一切。」(A hundred times every day I remind myself that my inner and outer life are based on the labors of other men, living and dead, and that I must exert myself in order to give in the same measure as I have received and am still receiving.)一段話,為這個篇章、這種精神,做了最好的說明。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說:「一所真正的大學必須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學術性的教學,二是科學的研究,三是創造性的文化生活。」亞大,正朝著這個方向邁進,而本書則將由主導這一切的幕後推手──亞大創校校長、同時也是現任校長的蔡進發,親自闡述他的治校理念、人生故事與省思,為年輕學子提供未來二十年的生命指南。
本書收錄蔡進發所寫給年輕人的十二種人文思維:創新、跨領域學習、獨立思考、專注、國際化、美學、理性與感性、性別平等、價值判斷、終身學習、成敗以及社會服務,全是依據他過去在美國求學、教學、研究和回國後從事教育工作的心得而寫成。
在這本書裡,蔡進發的眼光不局限在台灣,而是以全世界做為理想的場域,用他多年來所見所聞淬鍊出獨到的人生看法與心靈感觸,勇敢與年輕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勵年輕人拓展自己人生的深度與廣度。
美國擁有世界一流的大學教育,也是蔡進發所熟悉的地方,因此,本書一開始,談到亞大的誕生,便從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維吉尼亞大學、史丹佛大學等校談起,也描繪了當初心目中理想大學的起創點。
大學在近一千年前起源於義大利,如今的波隆納大學被公認為世界第一所大學,它的建築以文藝復興時期的巴洛克風格為主。亞大創校時便以教育初衷來砥礪自己,因此,將巴洛克風格定為學校建築的標記。
哈佛大學是美國文理學科的起源,創校團隊特地從哈佛大學帶回一塊紅磚,以這一塊磚為基準,每一棟校舍的建材、顏色,都和它嚴整一致,如同當初立定以哈佛追求卓越、人文關懷精神來辦學的初衷一般。
這個起點是由外而內的漸進過程,如同本書中談到的「境教」,希望營造一個合宜的環境,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下,一點一滴形塑學子們「做人有品德」、「做事有品質」、「生活有品味」的價值觀。亞大有一個膾炙人口的講座──「諾貝爾在亞大」,講者從嫻熟經濟、財政到擅長科技、醫學,每個人的專業都達到巔峰成就,人生歷練也不同凡響,因而說起故事來句句珠璣。
有一年,生理醫學獎得主、威爾剛理論之父穆拉德(Dr. Ferid Murad),在亞大分享自己的學習過程時,指出一句對他影響至深的話:「我的老師說,『我在課堂上講的,有百分之五十是對的,百分之五十是錯的。』」
這句震人心的話,所代表的正是本書希望告訴讀者的,即使面對授課老師與學術權威,每個人都得獨立思考,自己判斷哪些是對、哪些是錯,哪些該做、哪些不能苟同。也正因為獨立思考如此關鍵,以致於當我們放眼世界,便不難發現,各級學校紛紛以教育改革,提升下一世代的思考能力。
然而,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穆拉德卻是一位可樂的愛好者,就連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也是,為什麼?原來,在他們求學的年代,美國還不流行喝咖啡提神,可樂才是主流;每當做實驗的時間冗長,身體疲倦,內心卻不願放下,便會抓一把零錢到販賣機投幣,買一罐可樂,連沒飯都沒吃,就回到實駣室大口灌下。
得到「補給」之後,又能拚上幾個小時。垃圾桶裡至少累積了四、五個可樂空罐,記錄下這群人為了做好一件事是如何地專注、心無旁騖。
從世界的另一端回到台灣,創辦亞洲大學,蔡進發堅信,大學的本質就是國際化。大學是傳授與創造知識的地方,必須隨時掌握全球趨勢、訊息和產業動態,甚至掌握全世界的最新知識,因此,不應該也不允許將觸角局限在一個區域。
台灣年輕人的未來,也應該建構在全世界之上,而非局限在自己的家鄉。只是,近年來台灣經濟趨於成熟,能夠雇用的人數有限,因此年輕人的國際移動力,也就是在海外做事的能力,變得更加重要。
然而,一所學校要培養出人格成熟的青年,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美學教育。而美術館,是提供美學教育重要的學習場域。
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主張用觀念去界定「美之本質」,是西方美學的起源。柏拉圖則是哲學美學的開創者,他繼承蘇格拉底的說法,提出「美的本質」問題,以哲學思辨去探討審美的對象和美學原理,在西元前三、四百年就開創了西方美學的研究。在東方,大概也在西元前五百年左右,就有審美方面的論述,例如孔子提「里仁為美」、孟子說「充實之謂美」、老子稱「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莊子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遠在古代,孔子就是美學教育的提倡者,近如民國初年,蔡元培校長也在北京大學倡導美學教育。
在如今的台灣,許多大學都樂意設立圖書館、實驗室,因為裡面的藏書、設備,反映一所學校的學術深度,卻很少看到大學設立美術館。但是在亞大,卻這麼做了,本書中也娓娓道來美學教育的重要性,以及當初設立的緣由。
同樣在精神層面,本書還探討了理性與感性的作用與關係。理性是邏輯分析的能力、感性是情感同理的能力,兩者平衡,才有成熟的人格去面對複雜的人生。可是,生於網路世代的人,感性、理性都不成熟的狀況特別明顯。
感性太過,造成極端的情緒問題;理性太過,卻失去對人性情義的理解,這樣的人格,大家應該也不陌生,就如那些只知道根據法律條文判決,卻違背常識、脫離社會現象的「恐龍法官」。
1980年代的比利時,有件討論許久、值得深思的案子。
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半夜時分,有位女子從陽台跌到馬路上,陷入昏迷。一名路過的男子發現了,趁機洗劫她身上的財物,卻擔心她無人搭救而傷重不治,於是離開前先報警。事後警察從監視器中看到經過,起訴了這名男子。
這個案子在布魯塞爾討論許久,最後,這名男子被判無罪。法官的判決書這樣寫著:「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脆弱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相對於拯救生命,搶劫財物不值得一提。
「雖然就法律來說,我們不該因為一個人的善行而赦免他其他的犯罪,但是如果判決他有罪,將對社會秩序產生極度負面的影響,我寧願看到下一個搶劫犯拯救一條生命,也不願看到遵守法律的無罪者對他人的苦難視而不見。」
法律判決固然依賴純粹理性的邏輯推論,但是一位法官如果感性與理性平衡,就能全面衡量情、理、法的輕重得失,做出最有利於社會的判決。
本書也談到了性別平等的問題,而這一切的根本,其實可以說是源自於尊重和平等。尊重,意謂著尊重他的差異及獨立;平等,則是給予相同的機會。如果能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就會理解,戀愛、結婚、成家是每個生命都享有的權利,社會尊重每個生命的選擇,就不該因為他的性別選擇而有差別待遇。那麼,許多同性戀愛、同性婚姻的爭議,也就豁然而解了。
不過,尊重不代表放任。在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學校、家長不僅應該提供他們完整的性教育,也要培養他們獨立負責的能力,幫助他們了解事情的因果關係,為自己的選擇負起最後責任。
父母以身作則尊重差異,是給下一代最好的示範。蔡進發坦誠,他那個世代的人,受教育及傳統影響,要完全放棄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大部分人一時可能有些難度,但還是會盡力提高自覺,時時提醒自己。
他以六百年前的警訊提醒當代的人們,來自農村的少女貞德,以瘦弱的身軀穿起盔甲,率領軍隊奔向戰火最前線,終於扭轉了法國的頹勢,最後卻因為不公平的審判而死於熊熊烈火。因此,我們應該也必須記住,六百年後的現在,不應該再有任何理由毀滅任何異於凡俗的靈魂。
法國小說家兼哲學家卡繆(Albert Camus)曾說過:「人生就是你所有抉擇的總和。」(Life is the sum of all your choices.)本書也從「價值觀」的角度切入,說明那是每個人心中的一把尺,它決定你要做什麼、不做什麼或怎麼做。
不過,蔡進發提醒,年輕人應該勇於嘗試、勇於挑戰,卻不認為應該一味堅持自我。這中間的平衡點,可以用《大學》所說的「止於至善」來評估。
至善,是考慮每一個人的利益、損失,讓整體結果達到最佳狀態。有些人常堅持自己的想法,並以擇善固執美其名,但如果個人的堅持影響整體的最佳利益,則整體的最佳利益應該為最高指導原則。
人生就是一連串學習的過程,張忠謀便曾在一場演講中指出,當他回顧幾十年的工作生涯,發現只有前五年,用得到在大學、研究所所學的20%∼30%,之後的工作生涯,直接用到的部分幾乎等於零。
對於即將獨自揚帆進入人生大海的年輕人,這番話也許聽得驚心動魄,不過我相信,對每個已經在社會歷練的人來說,這番話再真實不過。進入職場,要不被淘汰甚至掌握機會謀得發展,必得與時俱進,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終身學習。
自我學習的方法很多元,除了閱讀,進入社會工作後,出差或旅行的機會也將增加,在蔡進發的經驗中,這是學習的大好機會,一方面幫你檢驗你所知的,同時讓你認識你未知的。這段不斷努力的過程,本書提出一個觀點,就是一個階段的成或敗,不代表永遠的成或敗。莫札特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莫札特三歲展現音樂天賦,六歲譜出小步舞曲,十一歲寫出第一部歌劇,十三歲被大主教提名為樂團首席,當真是無上風光。如果此時人生戛然而止,莫札特就是世人眼中永遠的音樂神童。
可惜,人生必須不斷往前。莫札特十七歲這年,樂團換了一位親王新主教管理。他限制莫札特的創作領域,甚至公開嘲笑他是飯桶、智障。一顆耀眼的鑽石突然掉入泥濘,年輕的心靈必然痛苦莫名。
如果莫札特憤恨所有努力不過鏡花水月,從此自暴自棄,他的人生大概也就淪為眾人惋惜的「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幸好,他並未放棄自己。
當命運之神再度眷顧莫札特,從慕尼黑寄來一份歌劇創作的邀請,他立刻抓住機會表現,結果首演時獲得熱烈迴響,之後並以獨立作曲家的身分到奧地利,從此展開自由創作。
在莫札特短短三十五年的人生中,留下許多重要音樂類型的作品:協奏曲、奏鳴曲、交響樂、小夜曲、嬉遊曲等,成為後來古典音樂的主要形式,撼動了音樂史的發展。
人的一生總是起起伏伏,現在眼中的成功或失敗,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後再回首,豈知不是另一番光景?放在時間的長河裡,成功或失敗難有定論,換一個角度觀察,成敗也難有絕對的定義,但是,只要每件事都全力以赴,問心無愧,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以正面的態度看待,就是成功。
這是個混亂的時代。貧富差距、國際衝突、溫室效應⋯⋯,很多問題政府不見得有能力解決,反倒在民間,透過服務的力量,更能有效率的降低富人與窮人、富國與窮國的衝突;尤其是年輕人的浪漫熱情,更能打破現實的框架。
本書希望為年輕人培養更宏大的胸懷氣度,便將社會服務納入其中。社會服務是這個時代的公民素養,培養新時代的公民,大學責無旁貸。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我每天不斷提醒自己,我的生活,不管內在或外在,都奠基在他人(包括活著的和逝去的)的努力成果之上。因此,我必須盡力奉獻自己,希望以同等的貢獻回報長久以來從他人身上所獲得的一切。」(A hundred times every day I remind myself that my inner and outer life are based on the labors of other men, living and dead, and that I must exert myself in order to give in the same measure as I have received and am still receiving.)一段話,為這個篇章、這種精神,做了最好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