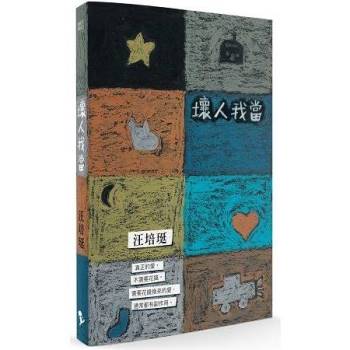「你好像白雪公主裡的,那個什麼媽媽……」
先生臨要出門去搭飛機了,大門口,他撂下這話。
「給毒蘋果的壞皇后。」我幫他補充。
「對對對……」關上門,我開始檢討,即使先生只是隨口說說──
我真的是給毒蘋果的壞媽媽?
昨天是星期六,一早,姊姊揹著登山大背包出門。
她參加了Hong Kong Awards for Young People(AYP)的活動。
她說,AYP是世界性的組織,分金銀銅三個階段:
十四歲,屬於最初級的銅牌。想拿到這個銅牌證書,必須完成三項活動,
其中一項是,登山健走、露營過夜。
十四歲的女生(男生也可以參加),四人一組,除了盥洗衣物外,背包裡有:
兩天一夜的食物、煮飯的鍋子、燃料,還有水。
水是最可怕的。一個人要分擔三公升的水,水多重啊。
還有帳棚,還有鐵撬。帶鐵撬做什麼?挖坑洞當臨時廁所……
我不知道姊姊為什麼要參加這個活動?她來說服我的時候,我沒仔細聽。
「這個認證,對將來申請大學有幫助。」
孩子錯估媽媽了,以為這樣的理由最可以讓媽媽說好。
只要是課外活動,我才不管跟成績有沒有關連,孩子想參加,我全部都說好。
只有一種例外,「瑞士滑雪,七天五夜,費用十萬」。
學校舉辦的,不是學校的學生還不能去。姊姊愛死了,但是我說no。
她好愛,她好愛跟同學一起,但是我一點也不拐彎抹角地拒絕:
「等你出了社會,存到第一個十萬元,
那一天,我們可以再將這件事拿出來討論。」
賺十萬或許不難,存十萬哪?
為什麼有幾百萬人,不只連十萬都存不到,還落到卡奴的地步。
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媽媽不出這個錢,所以你沒辦法去。」
AYP主辦單位心裡有數,讓孩子接受考驗前,先舉行了一天來回的暖身健走。
一組四人,都是女生,沒有老師帶領,拿著地圖找路,自己走到目的地。
多遠?十五公里。暖身賽一回來,就有人退出活動了。
所以兩天一夜的健走是什麼光景?
十四歲的女生,背包超過十公斤,兩天走三十五公里,
自己搭帳棚,自己煮飯,自己收拾。
每一件大小事,都自己來,沒有一個大人幫忙。
有人要退出,大家都頗有微詞。
我卻說:「退出也是一種勇氣。逞強,才是弱者的表現。」
星期天的下午,我跟先生從電影院出來,先生的手機響了,
「姊姊,你還好嗎?會不會很累?」出去玩很少㖪累的姊姊,這回,連聲音都累了。
「爸爸馬上去學校接你。」
「你要五點多才可以走?可是爸爸等會兒要去機場,時間來不及……」
先生將電話搶去,「好好好,你等會兒坐計程車回來。回來好好休息……」
坐計程車,屬於奢侈消費,沒特別理由,孩子應搭大眾運輸工具。
但這時候我沒說話。
兩個小時後,先生要出門去機場了,我送他到門口穿鞋。
他心疼女兒,又再次交代我要讓女兒好好休息。
我開口問了我的疑問:「她有錢坐計程車回來嗎?」
路程不短,車資大約港幣一百二十元。
「我記得她皮包裡應該不到一百元,是不是到家後我去幫她付錢呢?」
「昨天我有多給她。你啊,也太狠心了吧,才給她五十元。」
先生的語氣沒有指責,只有嘲笑。嘲笑我這個壞媽媽,
「你好像白雪公主裡的,那個什麼媽媽……」
我還笑了,趕快幫滿腦子只有公事沒有童話的他,補上,「給毒蘋果的壞皇后。」
對對對對對……
【好人你做,壞人我當】
我是狠心的媽媽嗎?我和先生白手起家,都沒有浪費的個性。
步入中年經濟穩定後,先生平時花錢,大致沒有什麼顧慮;
再加上因為花的錢從台幣一下子轉成港幣,沒法很直覺地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錢。
我平和地跟先生陳述這個事實:
「你知道姊姊坐計程車回家,要花多少錢嗎?」不等他換算,「是台幣六百元。」
從他的表情知道,此刻他才發覺這個事實。
「那是香港滿街跑的菲傭,一天的薪水,也是你們公司快遞員半天的薪水。」
他要出門了,我沒機會跟他長篇大論,只能點到為止──
孩子小小年紀,千萬不能讓他們覺得,花錢是容易的事。
花錢真的很容易,但那得是你自己賺來的。
花別人的錢,花成習慣了,那不是愛他,那是剝奪他努力開創人生的動力。
*
我躲在暖暖的被窩裡寫稿,聽到姊姊進門了,
趕緊從被窩裡跳出,從房間奔到客廳──
姊姊的臉色蒼白,這個週末剛好有寒流,山上的氣溫恐怕要接近零度。
你有一口氣走二十公里,換口氣再走二十公里的經驗嗎?
還要揹這麼大的背包,除非逃難,不然我做不到。
「媽媽,我頭好痛,喉嚨也痛,我要先去睡覺了。」
「你要不要先洗個熱水澡?」我陪她進了浴室。
姊姊小時候,最喜歡一邊洗澡,一邊還要媽媽在旁邊跟她聊天。
近一年來,她忙,我也忙,我們好久沒這樣了。
雖然累,泡在熱水裡,姊姊開始唧唧喳喳地說活動有多好玩。
可是我心裡還是納悶,揹這麼重的大背包,走這麼遠的路,
到底「好玩」會藏在什麼地方呢?
不消走上三十分鐘,我會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
而且他們走的是山路,上坡下坡的。
我不是給白雪公主吃毒蘋果的壞皇后,
是因為我知道,什麼時候該狠心,而且該狠心的時候不可以心軟。
有太多的父母,就是因為沒花時間愛孩子,所以對小孩花錢示愛,
花得心甘情願、花得心花怒放。
真正的愛,不需要花錢。需要花錢換來的愛,通常都有副作用。
後記:
既然你有力氣走三十五公里,怎麼會沒有力氣坐捷運回家呢?
身體不舒服,可以是例外。
不然,我堅決反對隨口叫孩子坐計程車回家。
坐計程車當然舒服多了,但是,你現在不給孩子「堅強」的機會,
等他入了社會,你覺得他的第一份薪水,足夠讓她花這個錢嗎?
與其讓孩子長大後哎聲嘆氣、怨天尤人,
拿不出一點堅強的毅力面對現實,為什麼我們不在孩子小的時候,
就助他一臂之力,培養他們「一切靠自己」的勇氣呢。
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的「沙丁魚」公車嗎?
我留美回國的第一份工作,那時候還沒有捷運,每天上下班我還在擠沙丁魚公車。
微薄的薪水、擁擠的公車、初入社會的壓力……
原來,小時候培養出來的毅力,可以用一輩子。
順遂的人生,會不會也是從擠「沙丁魚」公車裡,擠出來的。
你絕對可以寵你的孩子,但是不要用錢,要用你的愛。
【好男人多得是】
「姊姊,你明天早上幾點出門?」星期五的晚上,睡前媽媽去關心孩子。
「有誰要跟你去養老院?」孩子跟誰出門,當然是父母要關心的事。
「某某某和某某某。」我聽到了那個男孩的名字。
「你們去了養老院,要幫老人做什麼?」這是學校裡社區義工的選項之一。
「教老人一些簡單的英文,唱歌給他們聽,帶他們去傳統市場買菜……」
「買菜?傳統市場?」我真想說,你好像沒帶我去過耶。
對了,我還不是老人。
「對了,某某某不是很會唱歌嗎?」
我的意思是他可以發揮所長,另一個目的是,「打探軍情」──
進入青少年的孩子,尤其是跟異性有關的事,
不願意跟父母說,正常的不得了,而且媽媽也不想心臟病發作。
今天,孩子剛好有話在肚子裡,被我遇上。
「我不想理他了,他太不成熟了。」
「怎麼了?」打探軍情,話不可以太多,以免露了馬腳。
「最近XX的心情不好,昨天在學校又哭了,
他就說為什麼我的朋友都這麼不快樂?為什麼不想開一點就好?
「很多事情就是沒辦法想開啊,不是你嘴巴說,就可以馬上做到……
可是可是,他就是沒辦法了解。」
姊姊最近對他的微詞頗多。
我其實比誰都害怕他們會走上「分手」一途。
因為我知道,走了甲,還會有乙,與其這樣換來換去心神不寧,還不如「專情」一點。
對嘛,專情,對任何階段的人來說,應該都是比較好的。
我說:「姊姊,你知道嗎,男生都比較晚熟,你要給他時間,等他長大變成熟。」
星期六的下午,爸爸媽媽帶著弟弟,跟姊姊約在電影院門口,
因為她早上去養老院做義工。
我們還沒走到電影院門口,姊姊突然在媽媽的背後出現,
只喊了一聲媽媽,眼淚馬上決堤。「怎麼了?」我有點被嚇到。
我心裡也有數,她剛剛是跟誰出門,可能發生什麼事。
她沒說話,只是猛掉眼淚。我也說不出別的話,只能猛說怎麼了。
孩子遇上感情的挫折,還敢在父母面前掉眼淚,
我們一定是很民主的家庭。
我跟她說過這個年齡不能交男朋友,她說沒有;
我也跟她說這個年齡談感情,會讓自己分心,功課顧不了,她也說不會。
這個節骨眼上,父母最可能說出來的話是:
「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能交男朋友,你看,哭哭啼啼浪費時間,
為什麼不拿這個力氣去讀書……」
看,我多厲害,只說「怎麼了」,什麼別的話也沒。
但是,媽媽在弟弟的眼裡,還是不及格。
其實我也只說了三次怎麼了,弟弟就拉我到一旁,小聲地說:
「閉上你的嘴巴,不要說話。」唉,我們家的小孩真嚴格。
「可是我關心她啊。」
「不要說話。」弟弟縮短了句型,加重了語氣。
他意思可能是,不說話,也是一種安慰。
其實弟弟的心裡比媽媽還著急。
買好了票,弟弟說:「我想吃爆米花。」
「好,你跟姊姊吃一份就好,你們不喜歡吃甜的,喜歡吃鹹的,對嗎?」
「不,我們要吃原味的,等一下姊姊的眼淚就可以讓爆米花變鹹了。」
真是高級又好笑的笑話,但是我們倆都沒笑。
爸爸帶姊姊去買爆米花時,看著姊姊的背影,弟弟竟然在我耳邊說:
「沒關係,好男人多的是,慢慢找就有了。」
天啊,你幾歲啊,說這什麼台詞哪。不過我心裡的回答卻是:
「好男人真的很多,但是可以讓你幸福的,不多,遇上了就要把握。」
【我去撞牆好了】
我認識他七年了,第一次對他這麼兇。
其實,我只是很嚴肅地衝進房間,對他說了五個字:「阿弟,你出來。」
他的奶奶在房間睡午覺,
他卻進進出出地去吵奶奶,吵到個性最好的奶奶都快要發脾氣了。
他跳下床,奔到客廳的沙發上坐著,我知道,他完全不習慣我這樣子對他說話──
我也從來沒見過他如此的神情。
當時家裡只有三個人,奶奶繼續睡覺,我也回到餐桌繼續寫稿。
才七歲的小孩,竟然一個人對著窗戶外面發呆,一動也不動地看著窗外的天空。
我有些於心不忍,但沒馬上過去安慰他。
因為我的作法並沒有超過大人管教該有的範圍。
今天如果是我的小孩犯錯了,我不會更凶,也不會更和善,
我的語氣就是讓你知道你做錯事了。
而且,當他的眼睛望向窗外時,他小小的腦袋瓜子正在快速地轉動呢──
可能是反省,可能是難過,可能是不平……
不論是什麼,我都要適時給孩子安靜思考的機會。
十分鐘過後,他突然跳下沙發,拔腿衝進房間,拿出樂高積木再衝回客廳,
慢慢地,他的神情才恢復了正常。
一個小時後,等他有點忘了這件事後,我才若無其事地走過跟他聊聊他的樂高。
為什麼要一個小時後?
你如果做錯事,剛被老闆罵了一頓,希望馬上有人來跟你說話嗎?
這時候任何人說任何事,你的腦袋會不會有轟轟的、什麼也聽不進去的感覺呢?
他剛剛快速地衝過我的身邊,是不是就是暫時不想聽到我的責備呢?
兩個小時之後,我剛好要出門辦事。
趁著跟他說拜拜時,輕描淡寫地說:
「奶奶常常睡不好,睡不好身體不健康,身體不健康就不能活很久。
我們盡量不要吵奶奶睡覺。」
他非常愛奶奶,我這麼說不是威脅,因為我沒有一句話造假,
我只是將事情說得「夠清楚」,讓小孩更容易明白。
我摸摸他的頭,摸摸他的背,他什麼話也沒說,
但是,從他臉上的表情,你會知道他聽懂了。
到了晚上,我在他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媽媽身邊躺下
(晚上我就像個小孩似的睡在媽媽的身邊,這是父親生病後開始的習慣),
我隨口問:「今天阿弟吵你睡覺啊?」
「沒有啊。」
「沒有?!那你怎麼在房間喊得這麼大聲,罵他罵得好兇啊?你不是睡著又被吵醒嗎?」
「沒有,我沒有睡著,我正在點眼藥。」
「什麼!你沒睡著?那你為什麼罵他這麼大聲?」
「我正要睡,急著趕他走,就大聲了起來。」
「唉呀,媽媽啊,你以後不要這麼大聲說話,你害我誤會阿弟了。」
當下我好難過,要不是已經晚上十一點了,我真想衝去他的房間跟他說對不起。
*
第二天一早,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後,家裡只剩下了我和他。
我在客廳一聽到他睡醒,就趕快衝到他的床邊坐下,劈頭第一句話就是:
「阿弟,姑姑要跟你說對不起。」
他的眼睛睜得好大。他當然忘了昨天那件事。
於是我慢慢地說出,我怎麼誤會他了。
才七歲的他,聽得明明白白。
最後我問他,姑姑做錯事了,你要不要處罰我?
我伸出手來,意思是你可以打我一下。
你猜,他會不會打我呢?
不會不會。不是只有他不會,全天下的孩子都不會。
他一邊笑一邊搖頭。
然後我不放棄,開始搞笑,「那,我去撞牆好了。」
然後順勢把頭往床墊上連撞三下。他的笑容更大了。
大人就是小孩的榜樣,包括說聲對不起。
後記:
事後,我問起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阿弟當時有那個表情?」
他在家裡被罵的機會不少──
個性好動的小孩,遇上時間體力耐心不夠的大人,小孩被大人罵的機會不會少。
我常常看到他被大人罵,可是,
我怎麼從沒見過他那個「望向窗外一動不動」的表情呢?
那十分鐘,他好像變成了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很少被人「訓斥」,如果遇上了,就是這個樣子,要好一會兒才能「恢復」。
我從來沒見過我的孩子被罵還繼續我行我素的樣子。
【一二三木頭人】
來香港五年多,日子有點過膩了。
「把拔,」我開始呻吟,「每個週末都是沙田,你都不帶我去吃大餐。」
香港什麼沒有就是有大餐,但我要的不是大餐,我要有變化的日子。
隔天早上,我看見先生在翻書,香港人這麼挑吃,
能在市場生存的,沒兩下子真功夫一定不行。
當我和先生尋著書上的線索走進店裡時,兩個人都呆掉了。
剛剛在商場裡停好車,步行大約十分鐘,
一走入旺角的街道,你會馬上明瞭人山人海的定義。
先生讓手機帶路,我們倆就彷彿是第一次出遊的鄉巴佬,
隨著手機上的指示在人群裡穿梭。
到了這把年紀,我們還有這等好奇,也算是一種幸福。
X記,香港喜歡以什麼記當店名。
今天不是有書推薦,我們不會隨便走進任何一家。
站在門口觀望時,覺得還好,就是一家香港隨處可見的茶餐廳,
門口有半面的玻璃窗,裡面掛的也是最常見的燒臘燒鵝燒雞。
我們一鼓作氣往裡走,店很小,大約六張桌子,桌子很舊;
讓我們坐下的,是中間的一張大桌,可容八個人。
坐下時,我猶豫了,因為桌上還放著抹布,
而且那種放法,不像是忘了沒拿走,
所以我也弄不懂放在桌上要幹嘛。
平常進餐廳,我很挑位置,坐哪吃,與吃什麼,對我同等重要。
如果有隱密性較高的booths包廂,當然是我的首選。
但是在香港吃飯,能遇上讓你選的機會不多,
有位子坐,就要謝天了。
這家小店卻有兩處booths,但我卻寧願坐開放的大桌──
每樣東西既不整潔也不乾淨,
在這種氛圍的地方吃飯,隱蔽的同義詞,可能是噁心。
大桌只有兩個客人,我們坐了下來,
因為四周沒擠著人,才造就了我們沒轉身就走的機緣。
如果八人桌已經做了六個人,我和先生就會找藉口走人了。
勉強坐下,穿著白色外套的侍者往旁邊一站,我嚇了好大一跳──
他的白外套,是我這輩子看過最髒的一件白衣服,
整個腹部位置都是黃澄澄的油漬,
我甚至不敢往上看他的模樣,一定跟衣服很匹配。
然後我和先生就瞪著也是髒兮兮的菜單,很有默契地胡亂點了兩樣:
腰潤及第粥、魚腩豆腐煲。
我倆心裡可能都想著同一件事情:
不要點太多,如果苗頭不對,馬上可以落跑。
「老闆,再一個皮蛋瘦肉粥好了。」因為那碗粥實在不大。
小小的店裡,有四位侍者,每個人的白外套都是又縐又髒。
既然那麼不愛乾淨,為什麼不換個不顯髒的顏色?
倒上來的兩杯茶,我循線看到一疊盛杯子的大鋁盤,
各個都好像剛參加完大械鬥回來似的,凹凸不平、歪七扭八;
一旁的兩個大茶壺,拜託也該退休了吧,
連把手都用破布和鐵絲纏了又纏……
再往後朝廚房方向看去,我的視線馬上又被嚇了回來:
好幾落的碗盤堆放著……
我怕我再往下看,等會兒就沒法吃東西了。
我和先生面面相覷,整個空間裡,大概就屬先生的那張臉最乾淨。
他看看我,小聲說:「一二三木頭人。」
唉,只有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因為我倆一副就像是突然被丟進食人族的部落裡,
除了扭動脖子四處察看外,身體完全僵硬。
三樣食物來了,我倆就沒再說半句話了。
低頭猛吃,一直吃到盤子見底,
連最後一湯匙的粥,我都從碗底刮乾淨吃下。好吃!
付完帳出來,我們倆餘悸猶存,沿路一句話都沒說,
最後走進了一家窗明几淨的甜品店,總算逃回了文明。
在雙皮奶和芝麻糊的前面,先生問:
「你剛剛有沒有發現,桌上的那杯茶,都沒有人喝。」整家店?
「對,我看了,我們對面的兩家人,
我們這桌的另外四個人,從頭到尾,杯子都是滿的。」
「我也沒喝。」我說:
「誰會這麼笨呢,我看到他們都是一隻手挾四個杯茶,
五個手指都在茶裡耶。」
「我喝了,兩口。才發現大家都沒喝。」
虧你還說你是跑過大江南北見過世面的,要我帶你去收驚嗎?
先生臨要出門去搭飛機了,大門口,他撂下這話。
「給毒蘋果的壞皇后。」我幫他補充。
「對對對……」關上門,我開始檢討,即使先生只是隨口說說──
我真的是給毒蘋果的壞媽媽?
昨天是星期六,一早,姊姊揹著登山大背包出門。
她參加了Hong Kong Awards for Young People(AYP)的活動。
她說,AYP是世界性的組織,分金銀銅三個階段:
十四歲,屬於最初級的銅牌。想拿到這個銅牌證書,必須完成三項活動,
其中一項是,登山健走、露營過夜。
十四歲的女生(男生也可以參加),四人一組,除了盥洗衣物外,背包裡有:
兩天一夜的食物、煮飯的鍋子、燃料,還有水。
水是最可怕的。一個人要分擔三公升的水,水多重啊。
還有帳棚,還有鐵撬。帶鐵撬做什麼?挖坑洞當臨時廁所……
我不知道姊姊為什麼要參加這個活動?她來說服我的時候,我沒仔細聽。
「這個認證,對將來申請大學有幫助。」
孩子錯估媽媽了,以為這樣的理由最可以讓媽媽說好。
只要是課外活動,我才不管跟成績有沒有關連,孩子想參加,我全部都說好。
只有一種例外,「瑞士滑雪,七天五夜,費用十萬」。
學校舉辦的,不是學校的學生還不能去。姊姊愛死了,但是我說no。
她好愛,她好愛跟同學一起,但是我一點也不拐彎抹角地拒絕:
「等你出了社會,存到第一個十萬元,
那一天,我們可以再將這件事拿出來討論。」
賺十萬或許不難,存十萬哪?
為什麼有幾百萬人,不只連十萬都存不到,還落到卡奴的地步。
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媽媽不出這個錢,所以你沒辦法去。」
AYP主辦單位心裡有數,讓孩子接受考驗前,先舉行了一天來回的暖身健走。
一組四人,都是女生,沒有老師帶領,拿著地圖找路,自己走到目的地。
多遠?十五公里。暖身賽一回來,就有人退出活動了。
所以兩天一夜的健走是什麼光景?
十四歲的女生,背包超過十公斤,兩天走三十五公里,
自己搭帳棚,自己煮飯,自己收拾。
每一件大小事,都自己來,沒有一個大人幫忙。
有人要退出,大家都頗有微詞。
我卻說:「退出也是一種勇氣。逞強,才是弱者的表現。」
星期天的下午,我跟先生從電影院出來,先生的手機響了,
「姊姊,你還好嗎?會不會很累?」出去玩很少㖪累的姊姊,這回,連聲音都累了。
「爸爸馬上去學校接你。」
「你要五點多才可以走?可是爸爸等會兒要去機場,時間來不及……」
先生將電話搶去,「好好好,你等會兒坐計程車回來。回來好好休息……」
坐計程車,屬於奢侈消費,沒特別理由,孩子應搭大眾運輸工具。
但這時候我沒說話。
兩個小時後,先生要出門去機場了,我送他到門口穿鞋。
他心疼女兒,又再次交代我要讓女兒好好休息。
我開口問了我的疑問:「她有錢坐計程車回來嗎?」
路程不短,車資大約港幣一百二十元。
「我記得她皮包裡應該不到一百元,是不是到家後我去幫她付錢呢?」
「昨天我有多給她。你啊,也太狠心了吧,才給她五十元。」
先生的語氣沒有指責,只有嘲笑。嘲笑我這個壞媽媽,
「你好像白雪公主裡的,那個什麼媽媽……」
我還笑了,趕快幫滿腦子只有公事沒有童話的他,補上,「給毒蘋果的壞皇后。」
對對對對對……
【好人你做,壞人我當】
我是狠心的媽媽嗎?我和先生白手起家,都沒有浪費的個性。
步入中年經濟穩定後,先生平時花錢,大致沒有什麼顧慮;
再加上因為花的錢從台幣一下子轉成港幣,沒法很直覺地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錢。
我平和地跟先生陳述這個事實:
「你知道姊姊坐計程車回家,要花多少錢嗎?」不等他換算,「是台幣六百元。」
從他的表情知道,此刻他才發覺這個事實。
「那是香港滿街跑的菲傭,一天的薪水,也是你們公司快遞員半天的薪水。」
他要出門了,我沒機會跟他長篇大論,只能點到為止──
孩子小小年紀,千萬不能讓他們覺得,花錢是容易的事。
花錢真的很容易,但那得是你自己賺來的。
花別人的錢,花成習慣了,那不是愛他,那是剝奪他努力開創人生的動力。
*
我躲在暖暖的被窩裡寫稿,聽到姊姊進門了,
趕緊從被窩裡跳出,從房間奔到客廳──
姊姊的臉色蒼白,這個週末剛好有寒流,山上的氣溫恐怕要接近零度。
你有一口氣走二十公里,換口氣再走二十公里的經驗嗎?
還要揹這麼大的背包,除非逃難,不然我做不到。
「媽媽,我頭好痛,喉嚨也痛,我要先去睡覺了。」
「你要不要先洗個熱水澡?」我陪她進了浴室。
姊姊小時候,最喜歡一邊洗澡,一邊還要媽媽在旁邊跟她聊天。
近一年來,她忙,我也忙,我們好久沒這樣了。
雖然累,泡在熱水裡,姊姊開始唧唧喳喳地說活動有多好玩。
可是我心裡還是納悶,揹這麼重的大背包,走這麼遠的路,
到底「好玩」會藏在什麼地方呢?
不消走上三十分鐘,我會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
而且他們走的是山路,上坡下坡的。
我不是給白雪公主吃毒蘋果的壞皇后,
是因為我知道,什麼時候該狠心,而且該狠心的時候不可以心軟。
有太多的父母,就是因為沒花時間愛孩子,所以對小孩花錢示愛,
花得心甘情願、花得心花怒放。
真正的愛,不需要花錢。需要花錢換來的愛,通常都有副作用。
後記:
既然你有力氣走三十五公里,怎麼會沒有力氣坐捷運回家呢?
身體不舒服,可以是例外。
不然,我堅決反對隨口叫孩子坐計程車回家。
坐計程車當然舒服多了,但是,你現在不給孩子「堅強」的機會,
等他入了社會,你覺得他的第一份薪水,足夠讓她花這個錢嗎?
與其讓孩子長大後哎聲嘆氣、怨天尤人,
拿不出一點堅強的毅力面對現實,為什麼我們不在孩子小的時候,
就助他一臂之力,培養他們「一切靠自己」的勇氣呢。
還記得我們小時候的「沙丁魚」公車嗎?
我留美回國的第一份工作,那時候還沒有捷運,每天上下班我還在擠沙丁魚公車。
微薄的薪水、擁擠的公車、初入社會的壓力……
原來,小時候培養出來的毅力,可以用一輩子。
順遂的人生,會不會也是從擠「沙丁魚」公車裡,擠出來的。
你絕對可以寵你的孩子,但是不要用錢,要用你的愛。
【好男人多得是】
「姊姊,你明天早上幾點出門?」星期五的晚上,睡前媽媽去關心孩子。
「有誰要跟你去養老院?」孩子跟誰出門,當然是父母要關心的事。
「某某某和某某某。」我聽到了那個男孩的名字。
「你們去了養老院,要幫老人做什麼?」這是學校裡社區義工的選項之一。
「教老人一些簡單的英文,唱歌給他們聽,帶他們去傳統市場買菜……」
「買菜?傳統市場?」我真想說,你好像沒帶我去過耶。
對了,我還不是老人。
「對了,某某某不是很會唱歌嗎?」
我的意思是他可以發揮所長,另一個目的是,「打探軍情」──
進入青少年的孩子,尤其是跟異性有關的事,
不願意跟父母說,正常的不得了,而且媽媽也不想心臟病發作。
今天,孩子剛好有話在肚子裡,被我遇上。
「我不想理他了,他太不成熟了。」
「怎麼了?」打探軍情,話不可以太多,以免露了馬腳。
「最近XX的心情不好,昨天在學校又哭了,
他就說為什麼我的朋友都這麼不快樂?為什麼不想開一點就好?
「很多事情就是沒辦法想開啊,不是你嘴巴說,就可以馬上做到……
可是可是,他就是沒辦法了解。」
姊姊最近對他的微詞頗多。
我其實比誰都害怕他們會走上「分手」一途。
因為我知道,走了甲,還會有乙,與其這樣換來換去心神不寧,還不如「專情」一點。
對嘛,專情,對任何階段的人來說,應該都是比較好的。
我說:「姊姊,你知道嗎,男生都比較晚熟,你要給他時間,等他長大變成熟。」
星期六的下午,爸爸媽媽帶著弟弟,跟姊姊約在電影院門口,
因為她早上去養老院做義工。
我們還沒走到電影院門口,姊姊突然在媽媽的背後出現,
只喊了一聲媽媽,眼淚馬上決堤。「怎麼了?」我有點被嚇到。
我心裡也有數,她剛剛是跟誰出門,可能發生什麼事。
她沒說話,只是猛掉眼淚。我也說不出別的話,只能猛說怎麼了。
孩子遇上感情的挫折,還敢在父母面前掉眼淚,
我們一定是很民主的家庭。
我跟她說過這個年齡不能交男朋友,她說沒有;
我也跟她說這個年齡談感情,會讓自己分心,功課顧不了,她也說不會。
這個節骨眼上,父母最可能說出來的話是:
「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能交男朋友,你看,哭哭啼啼浪費時間,
為什麼不拿這個力氣去讀書……」
看,我多厲害,只說「怎麼了」,什麼別的話也沒。
但是,媽媽在弟弟的眼裡,還是不及格。
其實我也只說了三次怎麼了,弟弟就拉我到一旁,小聲地說:
「閉上你的嘴巴,不要說話。」唉,我們家的小孩真嚴格。
「可是我關心她啊。」
「不要說話。」弟弟縮短了句型,加重了語氣。
他意思可能是,不說話,也是一種安慰。
其實弟弟的心裡比媽媽還著急。
買好了票,弟弟說:「我想吃爆米花。」
「好,你跟姊姊吃一份就好,你們不喜歡吃甜的,喜歡吃鹹的,對嗎?」
「不,我們要吃原味的,等一下姊姊的眼淚就可以讓爆米花變鹹了。」
真是高級又好笑的笑話,但是我們倆都沒笑。
爸爸帶姊姊去買爆米花時,看著姊姊的背影,弟弟竟然在我耳邊說:
「沒關係,好男人多的是,慢慢找就有了。」
天啊,你幾歲啊,說這什麼台詞哪。不過我心裡的回答卻是:
「好男人真的很多,但是可以讓你幸福的,不多,遇上了就要把握。」
【我去撞牆好了】
我認識他七年了,第一次對他這麼兇。
其實,我只是很嚴肅地衝進房間,對他說了五個字:「阿弟,你出來。」
他的奶奶在房間睡午覺,
他卻進進出出地去吵奶奶,吵到個性最好的奶奶都快要發脾氣了。
他跳下床,奔到客廳的沙發上坐著,我知道,他完全不習慣我這樣子對他說話──
我也從來沒見過他如此的神情。
當時家裡只有三個人,奶奶繼續睡覺,我也回到餐桌繼續寫稿。
才七歲的小孩,竟然一個人對著窗戶外面發呆,一動也不動地看著窗外的天空。
我有些於心不忍,但沒馬上過去安慰他。
因為我的作法並沒有超過大人管教該有的範圍。
今天如果是我的小孩犯錯了,我不會更凶,也不會更和善,
我的語氣就是讓你知道你做錯事了。
而且,當他的眼睛望向窗外時,他小小的腦袋瓜子正在快速地轉動呢──
可能是反省,可能是難過,可能是不平……
不論是什麼,我都要適時給孩子安靜思考的機會。
十分鐘過後,他突然跳下沙發,拔腿衝進房間,拿出樂高積木再衝回客廳,
慢慢地,他的神情才恢復了正常。
一個小時後,等他有點忘了這件事後,我才若無其事地走過跟他聊聊他的樂高。
為什麼要一個小時後?
你如果做錯事,剛被老闆罵了一頓,希望馬上有人來跟你說話嗎?
這時候任何人說任何事,你的腦袋會不會有轟轟的、什麼也聽不進去的感覺呢?
他剛剛快速地衝過我的身邊,是不是就是暫時不想聽到我的責備呢?
兩個小時之後,我剛好要出門辦事。
趁著跟他說拜拜時,輕描淡寫地說:
「奶奶常常睡不好,睡不好身體不健康,身體不健康就不能活很久。
我們盡量不要吵奶奶睡覺。」
他非常愛奶奶,我這麼說不是威脅,因為我沒有一句話造假,
我只是將事情說得「夠清楚」,讓小孩更容易明白。
我摸摸他的頭,摸摸他的背,他什麼話也沒說,
但是,從他臉上的表情,你會知道他聽懂了。
到了晚上,我在他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媽媽身邊躺下
(晚上我就像個小孩似的睡在媽媽的身邊,這是父親生病後開始的習慣),
我隨口問:「今天阿弟吵你睡覺啊?」
「沒有啊。」
「沒有?!那你怎麼在房間喊得這麼大聲,罵他罵得好兇啊?你不是睡著又被吵醒嗎?」
「沒有,我沒有睡著,我正在點眼藥。」
「什麼!你沒睡著?那你為什麼罵他這麼大聲?」
「我正要睡,急著趕他走,就大聲了起來。」
「唉呀,媽媽啊,你以後不要這麼大聲說話,你害我誤會阿弟了。」
當下我好難過,要不是已經晚上十一點了,我真想衝去他的房間跟他說對不起。
*
第二天一早,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後,家裡只剩下了我和他。
我在客廳一聽到他睡醒,就趕快衝到他的床邊坐下,劈頭第一句話就是:
「阿弟,姑姑要跟你說對不起。」
他的眼睛睜得好大。他當然忘了昨天那件事。
於是我慢慢地說出,我怎麼誤會他了。
才七歲的他,聽得明明白白。
最後我問他,姑姑做錯事了,你要不要處罰我?
我伸出手來,意思是你可以打我一下。
你猜,他會不會打我呢?
不會不會。不是只有他不會,全天下的孩子都不會。
他一邊笑一邊搖頭。
然後我不放棄,開始搞笑,「那,我去撞牆好了。」
然後順勢把頭往床墊上連撞三下。他的笑容更大了。
大人就是小孩的榜樣,包括說聲對不起。
後記:
事後,我問起自己這個問題:「為什麼阿弟當時有那個表情?」
他在家裡被罵的機會不少──
個性好動的小孩,遇上時間體力耐心不夠的大人,小孩被大人罵的機會不會少。
我常常看到他被大人罵,可是,
我怎麼從沒見過他那個「望向窗外一動不動」的表情呢?
那十分鐘,他好像變成了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很少被人「訓斥」,如果遇上了,就是這個樣子,要好一會兒才能「恢復」。
我從來沒見過我的孩子被罵還繼續我行我素的樣子。
【一二三木頭人】
來香港五年多,日子有點過膩了。
「把拔,」我開始呻吟,「每個週末都是沙田,你都不帶我去吃大餐。」
香港什麼沒有就是有大餐,但我要的不是大餐,我要有變化的日子。
隔天早上,我看見先生在翻書,香港人這麼挑吃,
能在市場生存的,沒兩下子真功夫一定不行。
當我和先生尋著書上的線索走進店裡時,兩個人都呆掉了。
剛剛在商場裡停好車,步行大約十分鐘,
一走入旺角的街道,你會馬上明瞭人山人海的定義。
先生讓手機帶路,我們倆就彷彿是第一次出遊的鄉巴佬,
隨著手機上的指示在人群裡穿梭。
到了這把年紀,我們還有這等好奇,也算是一種幸福。
X記,香港喜歡以什麼記當店名。
今天不是有書推薦,我們不會隨便走進任何一家。
站在門口觀望時,覺得還好,就是一家香港隨處可見的茶餐廳,
門口有半面的玻璃窗,裡面掛的也是最常見的燒臘燒鵝燒雞。
我們一鼓作氣往裡走,店很小,大約六張桌子,桌子很舊;
讓我們坐下的,是中間的一張大桌,可容八個人。
坐下時,我猶豫了,因為桌上還放著抹布,
而且那種放法,不像是忘了沒拿走,
所以我也弄不懂放在桌上要幹嘛。
平常進餐廳,我很挑位置,坐哪吃,與吃什麼,對我同等重要。
如果有隱密性較高的booths包廂,當然是我的首選。
但是在香港吃飯,能遇上讓你選的機會不多,
有位子坐,就要謝天了。
這家小店卻有兩處booths,但我卻寧願坐開放的大桌──
每樣東西既不整潔也不乾淨,
在這種氛圍的地方吃飯,隱蔽的同義詞,可能是噁心。
大桌只有兩個客人,我們坐了下來,
因為四周沒擠著人,才造就了我們沒轉身就走的機緣。
如果八人桌已經做了六個人,我和先生就會找藉口走人了。
勉強坐下,穿著白色外套的侍者往旁邊一站,我嚇了好大一跳──
他的白外套,是我這輩子看過最髒的一件白衣服,
整個腹部位置都是黃澄澄的油漬,
我甚至不敢往上看他的模樣,一定跟衣服很匹配。
然後我和先生就瞪著也是髒兮兮的菜單,很有默契地胡亂點了兩樣:
腰潤及第粥、魚腩豆腐煲。
我倆心裡可能都想著同一件事情:
不要點太多,如果苗頭不對,馬上可以落跑。
「老闆,再一個皮蛋瘦肉粥好了。」因為那碗粥實在不大。
小小的店裡,有四位侍者,每個人的白外套都是又縐又髒。
既然那麼不愛乾淨,為什麼不換個不顯髒的顏色?
倒上來的兩杯茶,我循線看到一疊盛杯子的大鋁盤,
各個都好像剛參加完大械鬥回來似的,凹凸不平、歪七扭八;
一旁的兩個大茶壺,拜託也該退休了吧,
連把手都用破布和鐵絲纏了又纏……
再往後朝廚房方向看去,我的視線馬上又被嚇了回來:
好幾落的碗盤堆放著……
我怕我再往下看,等會兒就沒法吃東西了。
我和先生面面相覷,整個空間裡,大概就屬先生的那張臉最乾淨。
他看看我,小聲說:「一二三木頭人。」
唉,只有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因為我倆一副就像是突然被丟進食人族的部落裡,
除了扭動脖子四處察看外,身體完全僵硬。
三樣食物來了,我倆就沒再說半句話了。
低頭猛吃,一直吃到盤子見底,
連最後一湯匙的粥,我都從碗底刮乾淨吃下。好吃!
付完帳出來,我們倆餘悸猶存,沿路一句話都沒說,
最後走進了一家窗明几淨的甜品店,總算逃回了文明。
在雙皮奶和芝麻糊的前面,先生問:
「你剛剛有沒有發現,桌上的那杯茶,都沒有人喝。」整家店?
「對,我看了,我們對面的兩家人,
我們這桌的另外四個人,從頭到尾,杯子都是滿的。」
「我也沒喝。」我說:
「誰會這麼笨呢,我看到他們都是一隻手挾四個杯茶,
五個手指都在茶裡耶。」
「我喝了,兩口。才發現大家都沒喝。」
虧你還說你是跑過大江南北見過世面的,要我帶你去收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