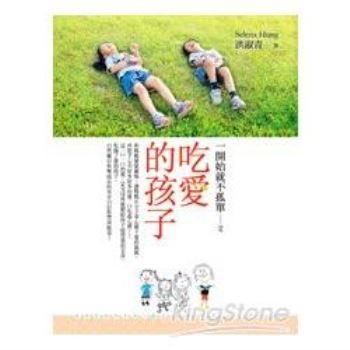上學儀式:祝妳在家裡快樂、吃愛的行為
可能是和爸爸媽媽的關係太親密了,也或許是和爸爸媽媽從來沒分開過,我這樣提高自我價值地分析zozo、yoyo對父母的依戀。
我不怕別人笑,也不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來觀看寶貝的「分離焦慮」:都已經上幼兒園一學期了,怎麼還沒停止哭泣,怎麼還有「我要媽媽,我需要爸爸」這種不離不棄的撒嬌呢?
孩子上學的前半年,我們家天天上演苦肉計,天天有分離千萬里的離情依依,尤其是和媽媽之間那條斷不了的隱形線,真是讓線兩端的她們與我都吃盡了苦頭。
每日的「離情依依」讓我們很苦惱,寶貝哭著進教室,我也哭著進車裡。
老公果斷又殘忍地分析著,問題好像就在我和她們之間的牽絆。
那該如何是好?
最終的結論是我最好待在家裡,把道別說掰掰的儀式往前調整,讓寶貝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適應從家裡進入學校的氣氛。於是,我必須按捺住想親自送女兒上學的慾望,在家裡和女兒道別。
說也奇怪,在家裡和媽媽Say Goodbye,她們似乎就比較不會黏媽媽,只是要有一長串的「吃愛」儀式。
什麼是「吃愛」呢?首先,她們要和我緊緊相抱,密不透氣的擁抱,然後我得在她們的右手親一下、左手親一下,親完後,寶貝緊緊握住這分我給的愛,然後「狼吞虎嚥」地嚥下這團愛。
yoyo就像是吃下一大口美食一樣,嘴裡不斷咀嚼著,最後在她胸前撇畫兩邊,意味著打開心房,然後吃下這分愛,這就叫做「吃愛」。
這分「愛」的餐點通常都是yoyo點的,她非得在早餐過後來一客「愛之餐」,否則是無法從家裡順利進入校園的。
zozo可就理性多了!她和我緊緊相擁、互親臉頰,然後親親她嘴巴剛好的高度──我的肚臍處,就可以得到滿滿的滿足。此外,她會補說一句:「快點把我的愛吃下去!」
別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喔,我還得在她們下樓進車庫後,趕緊到陽台邊,等待和她們最後一次道別。
當車子駛出家門,她們姊妹倆會探出頭往二樓陽台望,並且大喊:「媽媽再見!媽媽祝妳在家裡快樂!媽媽下午見喔!媽媽,嗯啊(親親)……」
這兩個貼心又可愛的寶貝,就這樣隨著車子的離去,慢慢離開我的視線。
她們離家後,我總是失落地幫她們在陽台上種的小植物澆澆水,期望她們和小植物一樣快快長大,心裡還悠悠迴盪著她們的祝福:祝妳在家裡快樂。
到了學校,難道情況就好多了嗎?當然沒有!此時真正的重任才開始落到爸爸的肩上。爸爸陪著zozo把書包、水壺歸位,把所有應該在學校的情緒都歸位;zozo總是緩慢地換著學校室內鞋,似乎想拖延一點時間,掙得多一點和爸爸的親密時間。
另外一頭的yoyo亦是如此,學校的資料都繳交了,她還賴著爸爸不肯放手,非得到了爸爸真要離去的時刻,她才又開始強烈地要求「吃愛」,一樣需要爸爸親吻她的雙手,一樣大口大口地吃著愛,她吃下去的這分愛,足以支撐她在學校一整天。
最後,她掛著兩行淚水,壓抑著心中離別的痛楚,和爸爸說再見。
爸爸走了,yoyo還在後頭揮手,每隔幾步,爸爸再回頭,她還杵在那兒……再走幾步,還得回頭和她揮揮手;爸爸上了車,會拉下車窗和她揮揮手;等車子迴轉時,那小小一點的yoyo還站在原處,痴痴地望著爸爸。
這次,車子真的要開走了,「zozo、yoyo,上學加油!」爸爸的心揪在一塊。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下學期才慢慢緩和,yoyo已經不需要「吃愛」了,她和媽媽親親、抱抱後,就開心地往二樓陽台大喊:「媽媽,祝妳在家裡快樂!」
到了學校後,她主動放下書包、水壺,還是像從前一樣故意拖延一下時間,想和爸爸多恩愛一會兒。但和從前不一樣的是,她也不需要「吃」爸爸的愛了,這下反而讓爸爸患得患失,害羞地問:「不用吃愛了喔?還要不要吃愛啊?這樣爸爸會不習慣耶。」看來,也許該吃愛的是爸爸和媽媽了。
我的孩子說他畫不出來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要你做一件事卻心有餘而力不足,例如畫一幅畫,腦子裡有畫面,手卻無法自在地描繪出腦海裡的畫面,許多人或許因此多少有一點對攝影的喜愛,想要把自己腦子裡美好的畫面直接經由那神奇的機器呈現出來。
我們為什麼畫不出來?成年人或許可以說:「沒有學過。」但是當孩子對我們說:「我畫不出來!」難道一個繪畫課程或美術班可以直接解決他們的難題?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的孩子有時會畫不出自己想畫的東西。
我記得兩歲多的yoyo,也曾經有這樣的情況,她希望爸爸幫她畫一幅開車的圖,她說:「我不會畫。」
這時候,凡是輔導孩子、幫助孩子的你,可不是發揮樂善好施精神的時候。如果你覺得這個「題目」對你而言輕而易舉,或許不要急著以過來人的姿態說:「這樣也不會,媽媽(爸爸)教你!」相反地,萬一你本來就自認為沒有「繪畫天分」,沒有「藝術修養」,也不需馬上去請教「專家」。根據我們家的經驗,這裡的重點在於孩子的問題與成人的想法大不相同。
不幫孩子畫畫,並不是不理會孩子的困擾,而是試著找出孩子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幫助他越過心理障礙:為什麼寶貝會畫不出來?該如何引導他?
因為每個小孩都是個案,所以只能去摸索適合你的寶貝的路徑。這裡提供的,只是針對成人的一些提醒,適用性應該比較高,畢竟我們的教育歷程大同小異。
首先,要犧牲自己的時間參與。在幼兒畫圖時適時地「參與」,只要不是帶著「教導」的意味,對於營造創作時自由快樂的氣氛還是有所幫助的。有那麼幾次,左右姊妹希望我和她們一起畫畫,雖然知道不應該畫畫給孩子看,但此時的出發點已經是親子共樂,而孩子也希望媽媽也能和她們一起開心作畫,所以我和她們一起畫了幾幅接力作品。孩子會觀察環境,也會觀察人的反應,她們看到媽媽所畫的內容,也看到我的態度,尤其是後者最重要,不管孩子與你自己畫得如何,整個過程都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這是暗示孩子:畫畫是沒有負擔的事。話說回來,只要拋棄成見,不計「成敗」,和幼兒一起塗鴉亂畫一定是最放鬆的時光。
至於引導的方式,雖說基本上沒有一個萬用的程序,但是在過程中嘗試放棄自己的理解,積極體會孩子們的眼光,絕對是唯一不可「懶惰」的準則。
就以這位朋友的心肝寶貝J想畫恐龍為例:J想畫恐龍卻畫不出來,他希望媽媽能幫他畫一隻恐龍。
此時,大人必須注意的是要先「忘記恐龍的長相」。雖然我們在腦袋裡免不了有一個如圖片或電影裡「正確的」恐龍形象,但是不能作為預設的結果,如此一來會干擾孩子的想像,讓他們喪失動筆的動機。當幼兒說他畫不出來,通常表示他沒有動機,這時或許可以問他:「你想畫一隻什麼樣的恐龍?」如果一時難以表達,我們可以再試著用問答的方式慢慢地引導孩子,營造出一個故事的情境,幫助他去想像那個畫面,那個畫面中可能包含著:恐龍處在何處?牠在做什麼?牠在想什麼事情?牠身旁有什麼?……這些問答的目的,是要將孩子對恐龍的喜愛,轉換成一種實際的想像。
這些原因可能是各式各樣的細節,甚至重點不在恐龍身上,而是其他你想像不到的非關主題的事物。在編造故事的過程中,通常孩子會突然發現他畫畫的「真實的動機」,進而動手下筆,這時你就等著接受一切結果了。
當孩子透過故事性的引導,不管他畫出什麼樣子,就算是三頭六臂的怪物,或只是幾個大圈圈,你都得接受,都要認同他心裡所想的樣子。不要讓他覺得你期待他畫出什麼,更不能有任何言語上的批評,或是不贊同的表情。我們必須和孩子一起分享他所創造出來的故事,真誠地感覺他獨特的創作。
然後將這幅畫收藏起來,這是我們唯一的責任。
六歲以前的孩子,由於心智尚未成熟到對事物「整體」進行觀察,也缺乏「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連結認知。所以不應該強求模仿「正確形象」的描寫力,就讓孩子自在地畫出他心中的想像吧!如果在這個時期過度要求孩子畫出所謂正確形象的圖像,後果會怎樣呢?那就是他以後真的都畫不出來了!因為孩子會覺得畫畫是有標準答案的,孩子們會朝向有讚美的那條窄路走去,會自我檢驗,而這樣的他如果無法達到「標準答案」,就不會主動提筆來作畫。
身為父母的你,到時可能真的要提起畫筆幫孩子畫畫了。
偷看他世界的方法
妞妞妹今年才三歲多,她跟媽媽說想去學畫畫,因為老師說她的畫好醜。
故事其實不這麼簡短,但我讀得好憂心,難道還有老師不知道他的一言一語影響著孩子一輩子?難道還有老師不知道孩子需要的是正面鼓勵、而非負面的否定?
嚴格來說,「學齡前兒童繪畫」其實不能算是「繪畫」,如果用「心智成長」的眼光來看,那比較像是孩子自由地在材料中遊戲,我們成人只是「不小心」偷窺了他們的世界。我想妞妞妹媽媽已經有分享孩子的世界的心理準備,只是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在環境的預備狀態,如果我們希望多多瞭解孩子,那麼在家中可以隨時準備好材料,成人就會得到更多這種「不小心」的機會。
萬一孩子在學校有負面經驗(尤其是老師的不認同),那麼更需要加強他的正面經驗,來克服那個可能無心的老師所具有的權威感在孩子心中所造成的卻步。家裡的支持(每一個人)是非常重要的,刻意的誇獎也是應該的,就當成發揮想像力的時刻與他一起討論作品的各種細節。孩童在塗鴉階段(通常在二到四歲)最希望別人聽他描述各種可能隨手拈來的細節(這時成人不要以「繪畫」概念來面對眼前這堆通常難以分辨的創作),一旦小孩有了順利的分享經驗,他會不斷地找機會用各種材料透露他的想法與夢想。不過,對於曾經直接給予他負面經驗的人來說,可能就沒有這分福氣了。
以下是我們在家裡常做的事:讓孩子有各種大小的畫冊、零散的小紙條、空紙盒……等,還要有隨手可得的筆,當然也要有隨手收集、編上日期的準備。zozo、yoyo很早就開始學習這個用數字「建立檔案」的工作,間接也讓她們對日期有清楚的概念。她們會數日子,將事件與時間順序連結起來;會自己發現以前畫的方式和現在有了區別。
孩子有時會記得以前畫的感覺,有時會重新編故事,他們慢慢融入屬於自己的語言世界,確定這些東西有人聆聽與閱讀,隨時都可以分享。久而久之,由其他地方不經意產生的障礙對他來說應該就只是小事了,這就是我們能做的部分。一言以蔽之,就是讓他的自由創作取得「合法性」。
進一步說,既然我們已經將幼兒的繪畫行為看成「心智成長」的紀錄,理論上就不能再以「美術發展」的線性觀點來評價。例如:透視法、合理比例與結構、準確的色彩、正確的工具使用……等,這些相當程度依賴確定知識的「專業動作」常常過於要求精準,以至於幼兒無法充分表現他確實的內在感覺,以及專屬於他自己的「邏輯」。在兒童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客觀地」評價其表現成果之前,我們寧願看到他為了展現得到某物的慾望,而將手腳「不正確」地扭曲伸長,也不希望他為了畫得「正確」而總是在結構上傷透腦筋。這個所謂「客觀的」或「理智的」參與,與孩子生活經驗的大量累積有關,他會意識到較為明確的「社會關係」,並且在圖面上以適當的空間來表現。一般來說,這是九歲以後的心智問題,不過在資訊發達充滿感官刺激的城市裡,可能會提早來臨。
然而不論幼兒的成長環境如何豐富,站在「自然」與「自我成長」的教育立場,我認為所有強調作品品質的「繪畫班」都不應讓學齡前兒童碰觸,那些願意不計後果陪你的孩子玩上一、兩個小時的老師,不管體力上的付出或是理念上的堅持,都值得讓我們尊重。
可能是和爸爸媽媽的關係太親密了,也或許是和爸爸媽媽從來沒分開過,我這樣提高自我價值地分析zozo、yoyo對父母的依戀。
我不怕別人笑,也不怕別人用異樣的眼光來觀看寶貝的「分離焦慮」:都已經上幼兒園一學期了,怎麼還沒停止哭泣,怎麼還有「我要媽媽,我需要爸爸」這種不離不棄的撒嬌呢?
孩子上學的前半年,我們家天天上演苦肉計,天天有分離千萬里的離情依依,尤其是和媽媽之間那條斷不了的隱形線,真是讓線兩端的她們與我都吃盡了苦頭。
每日的「離情依依」讓我們很苦惱,寶貝哭著進教室,我也哭著進車裡。
老公果斷又殘忍地分析著,問題好像就在我和她們之間的牽絆。
那該如何是好?
最終的結論是我最好待在家裡,把道別說掰掰的儀式往前調整,讓寶貝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適應從家裡進入學校的氣氛。於是,我必須按捺住想親自送女兒上學的慾望,在家裡和女兒道別。
說也奇怪,在家裡和媽媽Say Goodbye,她們似乎就比較不會黏媽媽,只是要有一長串的「吃愛」儀式。
什麼是「吃愛」呢?首先,她們要和我緊緊相抱,密不透氣的擁抱,然後我得在她們的右手親一下、左手親一下,親完後,寶貝緊緊握住這分我給的愛,然後「狼吞虎嚥」地嚥下這團愛。
yoyo就像是吃下一大口美食一樣,嘴裡不斷咀嚼著,最後在她胸前撇畫兩邊,意味著打開心房,然後吃下這分愛,這就叫做「吃愛」。
這分「愛」的餐點通常都是yoyo點的,她非得在早餐過後來一客「愛之餐」,否則是無法從家裡順利進入校園的。
zozo可就理性多了!她和我緊緊相擁、互親臉頰,然後親親她嘴巴剛好的高度──我的肚臍處,就可以得到滿滿的滿足。此外,她會補說一句:「快點把我的愛吃下去!」
別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喔,我還得在她們下樓進車庫後,趕緊到陽台邊,等待和她們最後一次道別。
當車子駛出家門,她們姊妹倆會探出頭往二樓陽台望,並且大喊:「媽媽再見!媽媽祝妳在家裡快樂!媽媽下午見喔!媽媽,嗯啊(親親)……」
這兩個貼心又可愛的寶貝,就這樣隨著車子的離去,慢慢離開我的視線。
她們離家後,我總是失落地幫她們在陽台上種的小植物澆澆水,期望她們和小植物一樣快快長大,心裡還悠悠迴盪著她們的祝福:祝妳在家裡快樂。
到了學校,難道情況就好多了嗎?當然沒有!此時真正的重任才開始落到爸爸的肩上。爸爸陪著zozo把書包、水壺歸位,把所有應該在學校的情緒都歸位;zozo總是緩慢地換著學校室內鞋,似乎想拖延一點時間,掙得多一點和爸爸的親密時間。
另外一頭的yoyo亦是如此,學校的資料都繳交了,她還賴著爸爸不肯放手,非得到了爸爸真要離去的時刻,她才又開始強烈地要求「吃愛」,一樣需要爸爸親吻她的雙手,一樣大口大口地吃著愛,她吃下去的這分愛,足以支撐她在學校一整天。
最後,她掛著兩行淚水,壓抑著心中離別的痛楚,和爸爸說再見。
爸爸走了,yoyo還在後頭揮手,每隔幾步,爸爸再回頭,她還杵在那兒……再走幾步,還得回頭和她揮揮手;爸爸上了車,會拉下車窗和她揮揮手;等車子迴轉時,那小小一點的yoyo還站在原處,痴痴地望著爸爸。
這次,車子真的要開走了,「zozo、yoyo,上學加油!」爸爸的心揪在一塊。
這樣的情況一直到下學期才慢慢緩和,yoyo已經不需要「吃愛」了,她和媽媽親親、抱抱後,就開心地往二樓陽台大喊:「媽媽,祝妳在家裡快樂!」
到了學校後,她主動放下書包、水壺,還是像從前一樣故意拖延一下時間,想和爸爸多恩愛一會兒。但和從前不一樣的是,她也不需要「吃」爸爸的愛了,這下反而讓爸爸患得患失,害羞地問:「不用吃愛了喔?還要不要吃愛啊?這樣爸爸會不習慣耶。」看來,也許該吃愛的是爸爸和媽媽了。
我的孩子說他畫不出來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要你做一件事卻心有餘而力不足,例如畫一幅畫,腦子裡有畫面,手卻無法自在地描繪出腦海裡的畫面,許多人或許因此多少有一點對攝影的喜愛,想要把自己腦子裡美好的畫面直接經由那神奇的機器呈現出來。
我們為什麼畫不出來?成年人或許可以說:「沒有學過。」但是當孩子對我們說:「我畫不出來!」難道一個繪畫課程或美術班可以直接解決他們的難題?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的孩子有時會畫不出自己想畫的東西。
我記得兩歲多的yoyo,也曾經有這樣的情況,她希望爸爸幫她畫一幅開車的圖,她說:「我不會畫。」
這時候,凡是輔導孩子、幫助孩子的你,可不是發揮樂善好施精神的時候。如果你覺得這個「題目」對你而言輕而易舉,或許不要急著以過來人的姿態說:「這樣也不會,媽媽(爸爸)教你!」相反地,萬一你本來就自認為沒有「繪畫天分」,沒有「藝術修養」,也不需馬上去請教「專家」。根據我們家的經驗,這裡的重點在於孩子的問題與成人的想法大不相同。
不幫孩子畫畫,並不是不理會孩子的困擾,而是試著找出孩子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幫助他越過心理障礙:為什麼寶貝會畫不出來?該如何引導他?
因為每個小孩都是個案,所以只能去摸索適合你的寶貝的路徑。這裡提供的,只是針對成人的一些提醒,適用性應該比較高,畢竟我們的教育歷程大同小異。
首先,要犧牲自己的時間參與。在幼兒畫圖時適時地「參與」,只要不是帶著「教導」的意味,對於營造創作時自由快樂的氣氛還是有所幫助的。有那麼幾次,左右姊妹希望我和她們一起畫畫,雖然知道不應該畫畫給孩子看,但此時的出發點已經是親子共樂,而孩子也希望媽媽也能和她們一起開心作畫,所以我和她們一起畫了幾幅接力作品。孩子會觀察環境,也會觀察人的反應,她們看到媽媽所畫的內容,也看到我的態度,尤其是後者最重要,不管孩子與你自己畫得如何,整個過程都要保持愉快的心情,這是暗示孩子:畫畫是沒有負擔的事。話說回來,只要拋棄成見,不計「成敗」,和幼兒一起塗鴉亂畫一定是最放鬆的時光。
至於引導的方式,雖說基本上沒有一個萬用的程序,但是在過程中嘗試放棄自己的理解,積極體會孩子們的眼光,絕對是唯一不可「懶惰」的準則。
就以這位朋友的心肝寶貝J想畫恐龍為例:J想畫恐龍卻畫不出來,他希望媽媽能幫他畫一隻恐龍。
此時,大人必須注意的是要先「忘記恐龍的長相」。雖然我們在腦袋裡免不了有一個如圖片或電影裡「正確的」恐龍形象,但是不能作為預設的結果,如此一來會干擾孩子的想像,讓他們喪失動筆的動機。當幼兒說他畫不出來,通常表示他沒有動機,這時或許可以問他:「你想畫一隻什麼樣的恐龍?」如果一時難以表達,我們可以再試著用問答的方式慢慢地引導孩子,營造出一個故事的情境,幫助他去想像那個畫面,那個畫面中可能包含著:恐龍處在何處?牠在做什麼?牠在想什麼事情?牠身旁有什麼?……這些問答的目的,是要將孩子對恐龍的喜愛,轉換成一種實際的想像。
這些原因可能是各式各樣的細節,甚至重點不在恐龍身上,而是其他你想像不到的非關主題的事物。在編造故事的過程中,通常孩子會突然發現他畫畫的「真實的動機」,進而動手下筆,這時你就等著接受一切結果了。
當孩子透過故事性的引導,不管他畫出什麼樣子,就算是三頭六臂的怪物,或只是幾個大圈圈,你都得接受,都要認同他心裡所想的樣子。不要讓他覺得你期待他畫出什麼,更不能有任何言語上的批評,或是不贊同的表情。我們必須和孩子一起分享他所創造出來的故事,真誠地感覺他獨特的創作。
然後將這幅畫收藏起來,這是我們唯一的責任。
六歲以前的孩子,由於心智尚未成熟到對事物「整體」進行觀察,也缺乏「部分」與「部分」之間的連結認知。所以不應該強求模仿「正確形象」的描寫力,就讓孩子自在地畫出他心中的想像吧!如果在這個時期過度要求孩子畫出所謂正確形象的圖像,後果會怎樣呢?那就是他以後真的都畫不出來了!因為孩子會覺得畫畫是有標準答案的,孩子們會朝向有讚美的那條窄路走去,會自我檢驗,而這樣的他如果無法達到「標準答案」,就不會主動提筆來作畫。
身為父母的你,到時可能真的要提起畫筆幫孩子畫畫了。
偷看他世界的方法
妞妞妹今年才三歲多,她跟媽媽說想去學畫畫,因為老師說她的畫好醜。
故事其實不這麼簡短,但我讀得好憂心,難道還有老師不知道他的一言一語影響著孩子一輩子?難道還有老師不知道孩子需要的是正面鼓勵、而非負面的否定?
嚴格來說,「學齡前兒童繪畫」其實不能算是「繪畫」,如果用「心智成長」的眼光來看,那比較像是孩子自由地在材料中遊戲,我們成人只是「不小心」偷窺了他們的世界。我想妞妞妹媽媽已經有分享孩子的世界的心理準備,只是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在環境的預備狀態,如果我們希望多多瞭解孩子,那麼在家中可以隨時準備好材料,成人就會得到更多這種「不小心」的機會。
萬一孩子在學校有負面經驗(尤其是老師的不認同),那麼更需要加強他的正面經驗,來克服那個可能無心的老師所具有的權威感在孩子心中所造成的卻步。家裡的支持(每一個人)是非常重要的,刻意的誇獎也是應該的,就當成發揮想像力的時刻與他一起討論作品的各種細節。孩童在塗鴉階段(通常在二到四歲)最希望別人聽他描述各種可能隨手拈來的細節(這時成人不要以「繪畫」概念來面對眼前這堆通常難以分辨的創作),一旦小孩有了順利的分享經驗,他會不斷地找機會用各種材料透露他的想法與夢想。不過,對於曾經直接給予他負面經驗的人來說,可能就沒有這分福氣了。
以下是我們在家裡常做的事:讓孩子有各種大小的畫冊、零散的小紙條、空紙盒……等,還要有隨手可得的筆,當然也要有隨手收集、編上日期的準備。zozo、yoyo很早就開始學習這個用數字「建立檔案」的工作,間接也讓她們對日期有清楚的概念。她們會數日子,將事件與時間順序連結起來;會自己發現以前畫的方式和現在有了區別。
孩子有時會記得以前畫的感覺,有時會重新編故事,他們慢慢融入屬於自己的語言世界,確定這些東西有人聆聽與閱讀,隨時都可以分享。久而久之,由其他地方不經意產生的障礙對他來說應該就只是小事了,這就是我們能做的部分。一言以蔽之,就是讓他的自由創作取得「合法性」。
進一步說,既然我們已經將幼兒的繪畫行為看成「心智成長」的紀錄,理論上就不能再以「美術發展」的線性觀點來評價。例如:透視法、合理比例與結構、準確的色彩、正確的工具使用……等,這些相當程度依賴確定知識的「專業動作」常常過於要求精準,以至於幼兒無法充分表現他確實的內在感覺,以及專屬於他自己的「邏輯」。在兒童開始以自己的方式「客觀地」評價其表現成果之前,我們寧願看到他為了展現得到某物的慾望,而將手腳「不正確」地扭曲伸長,也不希望他為了畫得「正確」而總是在結構上傷透腦筋。這個所謂「客觀的」或「理智的」參與,與孩子生活經驗的大量累積有關,他會意識到較為明確的「社會關係」,並且在圖面上以適當的空間來表現。一般來說,這是九歲以後的心智問題,不過在資訊發達充滿感官刺激的城市裡,可能會提早來臨。
然而不論幼兒的成長環境如何豐富,站在「自然」與「自我成長」的教育立場,我認為所有強調作品品質的「繪畫班」都不應讓學齡前兒童碰觸,那些願意不計後果陪你的孩子玩上一、兩個小時的老師,不管體力上的付出或是理念上的堅持,都值得讓我們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