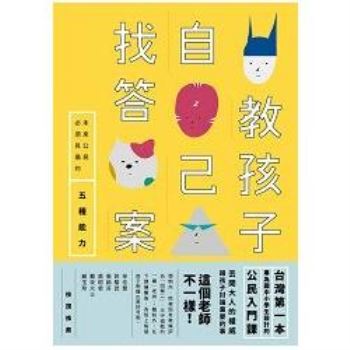緣起:關於「龜」(ㄍㄨ)要給分這件事
期中考的國語試卷,出現一題一字多音的題目:「龜」,原解應該是「ㄐㄩㄣ」,「龜裂」。班上有個可愛孩子,他填了:「ㄍㄨ」我一讀就笑了,覺得也很有道理,給分。
這件事我也貼到臉書,沒想到引起大家的共鳴。我決定將當時的想法,以及因為質疑所思考的內容寫出來。一方面讓與我不同意見的朋友一起交流,也讓某些不願直接面對我的家長或同事們,隔著一段距離也能明白我的想法。於是我為自己列出問答。
●問題一:考「國語」用「台語」寫答案怎麼能算對?
這個問題我想分三個部分來回答。
首先,我雖然不是語言學家,但學習語文經驗裡就能發現,任何不同的語文只要在同一個族群裡流轉就一定會產生界線上的模糊,否則我們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外來語。有多少人說台語的時候就是會夾雜一些國語。我們不會去質疑那些鄉土劇說:「你們不是應該講全台語的嗎?怎麼可以參雜國語呢?!」既然如此,「國語」考題中的某題,以台語發音回答,在語言流動上非常合理。比例原則也算符合。
再來,臺灣語言發展歷史中,非北京話體系的族群語言曾經被嚴重壓迫過。即使後來政府對這段歷史有一些反省,讓學校裡也有了每周一節的本土語,但台語的發展早就錯過可以精緻深耕且普羅使用的機會,怎麼說?就我而言,在家裡、或和某些長輩朋友一起、在我媽媽家,或回南部時,我那口流利的台語才會上身,其他地方,尤其是課堂,我根本已經喪失用全台語上課的能力。我用「喪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原本可以,而是我覺得原本是有機會可以。一個民族的語言絕對不可能活在字典,或博物館的收藏中,語言必須在人們的生活不斷使用才有可能存活,語言的發展透過人們的使用而有機轉化成各種可能的形式。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我們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轉變,科學上、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甚至在教育,每個細微的或巨大的變化,都不斷改變人們語言的使用,而原本那些弱勢的語言有機會讓它的子民們,在這種時代的變遷中變得豐富強大,我的台語也是。可是,現在看起來是有點難了。語言的使用和流通,常常必須建立在一種寬容和多元的基礎上,才能讓這個語言與其他的語言並存,且越加融洽與豐富。孩子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鼓勵這樣的發展,並珍惜這種細微的可能,不是嗎?最後,我們確實是考「國語」,可是,我們有「國」嗎?連個國都沒有,還執著什麼「國語」?(說起這個就一肚子火啊!)
●問題二:如果這樣可以給分,那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的孩子用他們族群的發音,老師都能知道而給分嗎?
老師當然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語言。但是,這不就是教學相長最美妙的地方嗎?孩子有可能被我們誤改,但只要他能提出說明,我有機會將分數補救回來,同時也多學了一個字的讀法,還可以讓全班都學會,這樣不是很好?
●問題三:有爭議的給分應該要全學年商量或由出題老師認定,妳自行決定給分,造成其他老師的困擾?
就我的立場,這個發音沒有爭議,請有爭議的人自行開會解決。再則老師改考卷,本來就應該有一定的空間來決定是否給分,否則,小孩有些字該閉合沒有閉、該直有點歪、該長的有點短,都要開會商量嗎?不管給分或不給分,老師都應該發展出自己的論述來服人(我現在就正在做這件事),困擾不該由別人來決定,也不能因為你有困擾,而強制要求別人必須服從齊一的標準,這沒有道理!
●問題四:你這樣會不會造成小孩有樣學樣,考卷不會寫就用台語發音?
說真的,我覺得這樣還滿好的......(會怎樣嗎?)
●問題五:如果有小孩自己創一個發音,說,我就是這樣唸這個字的,妳怎麼回應?
我會告訴他,要構成語言必須有哪些要件?「能溝通」是首要,所以,只要能證明他這樣唸有人懂,那我一定會給分。另外,我覺得這個孩子不是天才就是辯才,我會很珍惜這樣的孩子。就算是小孩也有撼動語言發展可能。
*
〈國小老師反死刑──從「人神共憤」的小端倪說起〉
國慶日要到了,江國慶的生日也要到了。如果他還在,應該是三十七歲生日。冤案令人痛心疾首,但非冤案,你就安心了嗎?
曾勇夫說:「人神共憤的先執行(死刑)。」
廢死聯盟的張娟芬說:「你可有見過八歲的罪大惡極?」
我是個國小老師,「八歲」正在我的執業轄區範圍,我在找「八歲的罪大惡極」,很肯定的,沒有。但是誰鋪一條路,讓那個孩子往罪大惡極、人神共憤的方向走去?如果他有別的選擇,他難道真的願意往那個方向去?但罪大惡極的端倪卻有跡可尋。
十歲的柚子,是我當註冊組長時接到的特殊就學個案。柚子的爸爸是個警察,媽媽是爸爸的外遇對象。柚子一出生就在保姆家長大,遇特別節慶或長假,媽媽才接回家。後來接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上小學之後,媽媽接回家同住,但柚子常偷跑回奶媽家。在家也常被媽媽哥哥責備。奶媽、奶爸雖對柚子疼愛,但礙於柚子媽媽的壓力,還有自家人也不歡迎,不敢收留柚子。柚子索性一塊紙板就睡在奶媽家的樓梯間。後來,媽媽也放棄找他,柚子成了社會局的個案。
安置柚子的機構位在我的學校學區,社工帶柚子來辦轉入手續時,正是炎熱的酷暑。他帶著純真可愛的笑容,卻身穿長袖。上學兩天,他沒來了。聯絡社工,說因為他逃離機構,自己搭車去找奶媽。找回柚子後,社工決定先讓柚子在機構穩定一陣子,再來上學。站在註冊組長的立場,我對這個決定相當不以為然。我答應上、放學都接送柚子,不會讓他有機會途中離開。
通常放學後,柚子就到我的辦公室寫作業。我再騎著摩托車送他回機構。我看著他工整的筆跡慢慢地在作業簿上筆畫、他笑著吃點心;有時在寫作業的時候睡著了、有時也幫我送東西給其他老師。坐在機車後座,他孩子氣的撥弄我的馬尾,他的笑容純真裡透著慧黠,我完全看不到社工口中,那個狡猾詭計多端的孩子。這樣美好的時光持續一陣子,無預警的,他又逃了。這次警察怎麼也捉不到他。
我和柚子的奶媽取得聯繫,長談了好久,奶媽掉著眼淚哭訴這個可憐的孩子,這幾天又睡在奶媽家的大樓樓梯間。爺爺(奶爸)常常半夜拿著被子幫他蓋上。擔心警察來抓,他常常一有風吹草動,就趕緊躲起來。
我決定自己去找他。那天晚上,我先生開著跟同事借來的車,帶著兩個小小孩,到我們很不熟悉的遠方找孩子,拜訪奶媽和爺爺後,我們一起找他。柚子像一隻受傷的小野獸,在黑暗的巷弄裡跟我們捉迷藏。我們在黑暗裡跟他喊話:我邀請柚子來住我家、我答應每天給他喜歡的飲料、想辦法轉回原來的學校,找原來的好朋友......一直到深夜,我們無功而返。回程的車上,我抱著自己已經熟睡的孩子,想著柚子覺得好心痛。十歲的孩子,不是應該還在媽媽懷裡撒嬌嗎?柚子卻已經開始露宿街頭、躲警察......我不得不想到,再大一點,他會怎麼跟一群同樣命運的孩子,一起在黑暗巷弄裡活躍他們的青春,然後逐漸往那個「罪大惡極」靠近。
心痛的是,他不過是個需要愛的孩子。
一開始我譴責柚子的母親,為什麼生下了孩子,又不肯好好照顧他?後來隱約知道她的狀況。柚子來自一段不得見光的感情,加上原就有需要扶養的孩子,工作也不穩定,心力交瘁後,也只能放手希望國家接管。
之後我氣柚子的社工,甚至毫不留情的指責她沒盡到責任,她很無奈的說,手上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個個案,她如何無微不至照顧每一個個案?我又無言了。
我在這個大體制的齒輪裡接觸柚子,但自己不也無能為力?媽媽無能為力、奶媽無能為力、社工無能為力......一連串的無能為力,鋪成一條往黑暗巷道裡的路,他還能有什麼選擇?看清這一連串無能為力的絕望,讓我憤怒得要直指國家的錯誤。而偏偏這個國家體制的建立每個人都有份。
柚子沒做錯任何事,他只是因為找不到渴求的愛,而從現有的體制逃走;體制裡的人往往善惡分明卻不知反省。我能在體制裡有安穩的生存、能受教育、能安心的工作,豈是因為我是一個好人?而是我有福氣、有能力成為好人。那些在體制外的暗巷裡的,又豈是懶惰或劣根性那樣簡單?如果可以如果有能力,誰不要成為一個「好人」?聖經不也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反對體罰,因為我相信每個做錯事的孩子,都是需要幫助的孩子;我反對死刑,因為我覺得死刑畫下了一條粗暴的線,讓全體的人喪失反省、喪失與另一邊的連結。為惡的、不善的、非我族類的就往另一邊踢去,從此與我無關,了不起再多謾罵幾句,更劃清界限。否則「死刑」是做什麼用的呢?不就是要殺「人神共憤、罪大惡極」。去吧!遙遠的,我聽不見的槍聲。
可是,因為我是國小老師,我的學生中出了一個總統,我未必能沾什麼光;但未來我的學生裡出了一個罪大惡極,我卻難辭其咎。沒有死刑,我和這個社會還有機會想想怎麼彌補錯誤,如果那個罪大惡極就這樣被國家殺了,我怎麼跟好幾年前,那個罪大惡極的小端倪交代?我怎麼毫無掛慮地擁抱他,說:「這個世界還有好多人都愛你。」
期中考的國語試卷,出現一題一字多音的題目:「龜」,原解應該是「ㄐㄩㄣ」,「龜裂」。班上有個可愛孩子,他填了:「ㄍㄨ」我一讀就笑了,覺得也很有道理,給分。
這件事我也貼到臉書,沒想到引起大家的共鳴。我決定將當時的想法,以及因為質疑所思考的內容寫出來。一方面讓與我不同意見的朋友一起交流,也讓某些不願直接面對我的家長或同事們,隔著一段距離也能明白我的想法。於是我為自己列出問答。
●問題一:考「國語」用「台語」寫答案怎麼能算對?
這個問題我想分三個部分來回答。
首先,我雖然不是語言學家,但學習語文經驗裡就能發現,任何不同的語文只要在同一個族群裡流轉就一定會產生界線上的模糊,否則我們怎麼會有這麼多的外來語。有多少人說台語的時候就是會夾雜一些國語。我們不會去質疑那些鄉土劇說:「你們不是應該講全台語的嗎?怎麼可以參雜國語呢?!」既然如此,「國語」考題中的某題,以台語發音回答,在語言流動上非常合理。比例原則也算符合。
再來,臺灣語言發展歷史中,非北京話體系的族群語言曾經被嚴重壓迫過。即使後來政府對這段歷史有一些反省,讓學校裡也有了每周一節的本土語,但台語的發展早就錯過可以精緻深耕且普羅使用的機會,怎麼說?就我而言,在家裡、或和某些長輩朋友一起、在我媽媽家,或回南部時,我那口流利的台語才會上身,其他地方,尤其是課堂,我根本已經喪失用全台語上課的能力。我用「喪失」的意思並不是說我原本可以,而是我覺得原本是有機會可以。一個民族的語言絕對不可能活在字典,或博物館的收藏中,語言必須在人們的生活不斷使用才有可能存活,語言的發展透過人們的使用而有機轉化成各種可能的形式。尤其是近幾十年來我們的生活有非常非常大的轉變,科學上、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甚至在教育,每個細微的或巨大的變化,都不斷改變人們語言的使用,而原本那些弱勢的語言有機會讓它的子民們,在這種時代的變遷中變得豐富強大,我的台語也是。可是,現在看起來是有點難了。語言的使用和流通,常常必須建立在一種寬容和多元的基礎上,才能讓這個語言與其他的語言並存,且越加融洽與豐富。孩子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我們也必須鼓勵這樣的發展,並珍惜這種細微的可能,不是嗎?最後,我們確實是考「國語」,可是,我們有「國」嗎?連個國都沒有,還執著什麼「國語」?(說起這個就一肚子火啊!)
●問題二:如果這樣可以給分,那原住民、客家、新住民的孩子用他們族群的發音,老師都能知道而給分嗎?
老師當然不可能精通所有的語言。但是,這不就是教學相長最美妙的地方嗎?孩子有可能被我們誤改,但只要他能提出說明,我有機會將分數補救回來,同時也多學了一個字的讀法,還可以讓全班都學會,這樣不是很好?
●問題三:有爭議的給分應該要全學年商量或由出題老師認定,妳自行決定給分,造成其他老師的困擾?
就我的立場,這個發音沒有爭議,請有爭議的人自行開會解決。再則老師改考卷,本來就應該有一定的空間來決定是否給分,否則,小孩有些字該閉合沒有閉、該直有點歪、該長的有點短,都要開會商量嗎?不管給分或不給分,老師都應該發展出自己的論述來服人(我現在就正在做這件事),困擾不該由別人來決定,也不能因為你有困擾,而強制要求別人必須服從齊一的標準,這沒有道理!
●問題四:你這樣會不會造成小孩有樣學樣,考卷不會寫就用台語發音?
說真的,我覺得這樣還滿好的......(會怎樣嗎?)
●問題五:如果有小孩自己創一個發音,說,我就是這樣唸這個字的,妳怎麼回應?
我會告訴他,要構成語言必須有哪些要件?「能溝通」是首要,所以,只要能證明他這樣唸有人懂,那我一定會給分。另外,我覺得這個孩子不是天才就是辯才,我會很珍惜這樣的孩子。就算是小孩也有撼動語言發展可能。
*
〈國小老師反死刑──從「人神共憤」的小端倪說起〉
國慶日要到了,江國慶的生日也要到了。如果他還在,應該是三十七歲生日。冤案令人痛心疾首,但非冤案,你就安心了嗎?
曾勇夫說:「人神共憤的先執行(死刑)。」
廢死聯盟的張娟芬說:「你可有見過八歲的罪大惡極?」
我是個國小老師,「八歲」正在我的執業轄區範圍,我在找「八歲的罪大惡極」,很肯定的,沒有。但是誰鋪一條路,讓那個孩子往罪大惡極、人神共憤的方向走去?如果他有別的選擇,他難道真的願意往那個方向去?但罪大惡極的端倪卻有跡可尋。
十歲的柚子,是我當註冊組長時接到的特殊就學個案。柚子的爸爸是個警察,媽媽是爸爸的外遇對象。柚子一出生就在保姆家長大,遇特別節慶或長假,媽媽才接回家。後來接回家的次數越來越少。上小學之後,媽媽接回家同住,但柚子常偷跑回奶媽家。在家也常被媽媽哥哥責備。奶媽、奶爸雖對柚子疼愛,但礙於柚子媽媽的壓力,還有自家人也不歡迎,不敢收留柚子。柚子索性一塊紙板就睡在奶媽家的樓梯間。後來,媽媽也放棄找他,柚子成了社會局的個案。
安置柚子的機構位在我的學校學區,社工帶柚子來辦轉入手續時,正是炎熱的酷暑。他帶著純真可愛的笑容,卻身穿長袖。上學兩天,他沒來了。聯絡社工,說因為他逃離機構,自己搭車去找奶媽。找回柚子後,社工決定先讓柚子在機構穩定一陣子,再來上學。站在註冊組長的立場,我對這個決定相當不以為然。我答應上、放學都接送柚子,不會讓他有機會途中離開。
通常放學後,柚子就到我的辦公室寫作業。我再騎著摩托車送他回機構。我看著他工整的筆跡慢慢地在作業簿上筆畫、他笑著吃點心;有時在寫作業的時候睡著了、有時也幫我送東西給其他老師。坐在機車後座,他孩子氣的撥弄我的馬尾,他的笑容純真裡透著慧黠,我完全看不到社工口中,那個狡猾詭計多端的孩子。這樣美好的時光持續一陣子,無預警的,他又逃了。這次警察怎麼也捉不到他。
我和柚子的奶媽取得聯繫,長談了好久,奶媽掉著眼淚哭訴這個可憐的孩子,這幾天又睡在奶媽家的大樓樓梯間。爺爺(奶爸)常常半夜拿著被子幫他蓋上。擔心警察來抓,他常常一有風吹草動,就趕緊躲起來。
我決定自己去找他。那天晚上,我先生開著跟同事借來的車,帶著兩個小小孩,到我們很不熟悉的遠方找孩子,拜訪奶媽和爺爺後,我們一起找他。柚子像一隻受傷的小野獸,在黑暗的巷弄裡跟我們捉迷藏。我們在黑暗裡跟他喊話:我邀請柚子來住我家、我答應每天給他喜歡的飲料、想辦法轉回原來的學校,找原來的好朋友......一直到深夜,我們無功而返。回程的車上,我抱著自己已經熟睡的孩子,想著柚子覺得好心痛。十歲的孩子,不是應該還在媽媽懷裡撒嬌嗎?柚子卻已經開始露宿街頭、躲警察......我不得不想到,再大一點,他會怎麼跟一群同樣命運的孩子,一起在黑暗巷弄裡活躍他們的青春,然後逐漸往那個「罪大惡極」靠近。
心痛的是,他不過是個需要愛的孩子。
一開始我譴責柚子的母親,為什麼生下了孩子,又不肯好好照顧他?後來隱約知道她的狀況。柚子來自一段不得見光的感情,加上原就有需要扶養的孩子,工作也不穩定,心力交瘁後,也只能放手希望國家接管。
之後我氣柚子的社工,甚至毫不留情的指責她沒盡到責任,她很無奈的說,手上大大小小有五六十個個案,她如何無微不至照顧每一個個案?我又無言了。
我在這個大體制的齒輪裡接觸柚子,但自己不也無能為力?媽媽無能為力、奶媽無能為力、社工無能為力......一連串的無能為力,鋪成一條往黑暗巷道裡的路,他還能有什麼選擇?看清這一連串無能為力的絕望,讓我憤怒得要直指國家的錯誤。而偏偏這個國家體制的建立每個人都有份。
柚子沒做錯任何事,他只是因為找不到渴求的愛,而從現有的體制逃走;體制裡的人往往善惡分明卻不知反省。我能在體制裡有安穩的生存、能受教育、能安心的工作,豈是因為我是一個好人?而是我有福氣、有能力成為好人。那些在體制外的暗巷裡的,又豈是懶惰或劣根性那樣簡單?如果可以如果有能力,誰不要成為一個「好人」?聖經不也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反對體罰,因為我相信每個做錯事的孩子,都是需要幫助的孩子;我反對死刑,因為我覺得死刑畫下了一條粗暴的線,讓全體的人喪失反省、喪失與另一邊的連結。為惡的、不善的、非我族類的就往另一邊踢去,從此與我無關,了不起再多謾罵幾句,更劃清界限。否則「死刑」是做什麼用的呢?不就是要殺「人神共憤、罪大惡極」。去吧!遙遠的,我聽不見的槍聲。
可是,因為我是國小老師,我的學生中出了一個總統,我未必能沾什麼光;但未來我的學生裡出了一個罪大惡極,我卻難辭其咎。沒有死刑,我和這個社會還有機會想想怎麼彌補錯誤,如果那個罪大惡極就這樣被國家殺了,我怎麼跟好幾年前,那個罪大惡極的小端倪交代?我怎麼毫無掛慮地擁抱他,說:「這個世界還有好多人都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