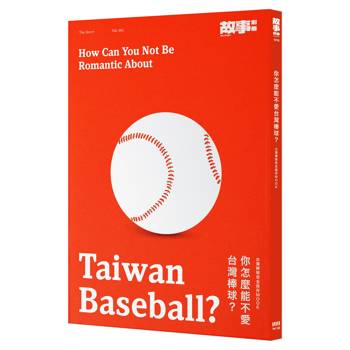回到九○年代,從台北市立棒球場的第一場中職球賽說起
專訪《台北市立棒球場》曾文誠
文╱温伯學
職棒風光開打,元年便達成百萬人次入場的佳績,全民不分老小都為職棒瘋狂,《民生報》每日更新戰報,《職業棒球》雜誌持續暢銷 ⋯⋯那是社會剛剛解嚴、狂躁的九〇年代初,職棒順勢成為紓解台灣社會激情的重要管道,同時,它必須在草創的混亂中站穩腳步,開創台灣棒球職業化的道路。
職棒元年首場比賽,於一九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開打。統一獅對上兄弟象,第一球由象隊投手張永昌投出,獅隊首棒打者曾智偵隨後獲得保送上壘。四局上半,統一獅隊三壘手汪俊良敲出中職史上第一支全壘打,全場氣氛沸騰到最高點,大鼓、汽笛聲齊鳴。
資深球評曾文誠仍清楚記得那一記全壘打的畫面。當時他在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出版的官方雜誌《職業棒球》擔任記者,親眼見證了這歷史的一刻。當天,台北市立棒球場座無虛席,僅能容納一萬四千五百人的球場,破天荒擠入一萬八千多名球迷,盛況空前,球迷以最直接的熱情,回應了他們對於職棒的期待。
「其實在正式開打前,聯盟曾舉辦球迷會,就已經可以感受到球迷對於職棒是多麼期待。」曾文誠說。
事實上,當時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聯盟,但有一群人,努力克服重重挑戰與困難,使台灣繼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澳洲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六個擁有職棒的國家。
混亂又美好的九○年代
對於很多老球迷來說,九○年代是一個混亂又美好的年代。
台灣剛宣布解嚴,社會充滿躁動不安卻又蓄勢待發的活力,人們一邊衝撞既有體制,一邊嘗試各種嶄新的可能。在棒球場上,經歷過七〇年代三級棒球「三冠王」的美夢、八〇年代成棒在世界舞台大放異彩的榮景,棒球逐漸成為台灣身處受挫的國際政治中,少數能被世界看見的運動項目之一。一次又一次的熬夜看比賽、一次又一次的加油吶喊,不僅累積起跨世代的集體記憶,也讓棒球在台灣社會占據無可取代的地位。
然而,當時的台灣尚未建立完整的職業棒球制度,導致一批批的菁英國手,只能遠赴海外尋求機會,無法在家鄉落地發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有「台灣職棒之父」之稱的兄弟大飯店董事長洪騰勝,憑著對於棒球的熱愛,決定以一己之力推動台灣棒球運動職業化。他遊說統一、味全、三商企業成立球團、投身職棒,並效法日職、美職,創辦《職業棒球》刊物、打造球隊吉祥物、建立啦啦隊制度,為中職日後發展奠定關鍵基礎。
職棒開打後,迅速風靡全台,而曾是台北市唯一可舉辦正式棒球比賽的「台北市立棒球場」,無疑是承載最多老球迷記憶情感的所在。「不只職棒,只要是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辦的比賽,都是重要的比賽」,曾文誠回憶,光從八〇年代起算,就有輔仁大學和文化大學棒球兩強對抗的梅花旗,成棒甲組的錦標賽中正杯、國慶盃,和棒協固定舉辦的國際邀請賽等精采賽事;職棒成立後,多場重要關鍵賽事:開幕賽、明星賽、冠軍賽,幾乎都在這座球場輪番上演。
球員的精采表現、球迷震耳欲聾的應援、年少時逃票進場看比賽的回憶,甚至是輸球時球迷憤怒拆座椅砸球場、球員與球迷爆發衝突的失控場面,以及簽賭案爆發後,空蕩冷清的觀眾席──球員與球迷間的喜悅與激情、混亂與失落,全都深深烙印在這座球場之中。
二○○○年,台北市立棒球場因設備老舊、年久失修,決定停用並拆除,原址改建成現今的「台北小巨蛋」。隨著這座球場走入歷史,一個時代的棒球風景,也被定格在最雋永的時光裡。
時隔二十年,就在中職歷經五次簽賭案、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並重新站起之際,一個名為《台北市立棒球場》的 Podcast 節目誕生。由資深球評曾文誠與梁功斌主持,節目以這座已不存在,但擁有許多球迷共同記憶的球場為名,回望台灣職棒草創時期的熱血與混亂,也重新梳理台灣棒球如何走過傷痕、繼續前行。
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二○二○年,曾文誠應同是知名球評的製作人王啟恩Adam之邀,投入《台北市立棒球場》的錄製。他怕單口說故事欠缺火花,於是找到曾參與職棒成立的要角梁功斌加入,最初只當「兩個老人家來聊聊以前的事情」,連能不能撐完一季都沒有把握,未料麥克風一開,資深與新進球迷便連連敲碗,時至二○二六年初已播畢六季。
兩人從閒聊講古,到訪問球員、教練、球團老闆、記者、球迷⋯⋯六年下來已有深厚的「中職口述歷史」份量。若嚴肅地看待,這是以Podcas 形式在為台灣職業棒球留下珍貴史料;但若輕鬆聆聽,普羅大眾也能隨節目開頭的jingle穿梭時空,和兩位主持人一同回到職棒方興未艾的九〇年代。
「《台北市立棒球場》這個名稱應該就涵蓋了一切。」曾文誠說道。節目談的是台灣職棒史,而曾經的台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許多老球迷來說,更是啟蒙棒球人生的重要聖地。
曾文誠仍記得,從永和老家只要搭一班公車就能抵達台北市立棒球場,當時的球場和早期的二輪戲院一樣,不清場,一入座就可以看上一整天。他特別喜歡到本壘板後座位區,坐在那聽一群老人家聊天看棒球,「沒想到一回神,我也變成老人家了。」今年已六十五歲的他笑說。
「我當時的生活除了棒球、還是棒球。」曾文誠說,他是貨真價實的棒球癡、棒球狂。正因如此,年少的他見到報紙上《職業棒球》徵人廣告時,便決定不顧一切地辭去穩定的貿易公司工作,加入前景難料的中職,擔任雜誌記者。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曾文誠正式到《職業棒球》報到。對他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生命歲月,在中職工作的期間,他每晚都想著第二天要趕快去上班,甚至覺得「休假是很浪費生命的」。尤其看著洪騰勝親力親為參與大小會議、帶頭整理場地,飯店員工也都身兼二職協助籌辦職棒,「看他以身作則,我們會覺得必須跟上去,一起為棒球拚一次看看。」
中職草創之初,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當時報導體育新聞的指標媒體《民生報》連續用多篇專欄抨擊中職,認為台灣的球員與觀眾數量都不足以支撐職業化發展。但外界愈是不看好,反而愈是激起團隊堅定的凝聚力。曾文誠回憶:「籌備期間,同事們都未曾想過失敗,反而有種『革命前夕』的亢奮,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躁動時代下投出的第一球
幾乎在開打後的第一周,職棒熱度就延燒開來,狠狠打臉事前看衰的媒體輿論。曾文誠點出,儘管初期職棒比賽並沒有電視live轉播,只有中廣主播兼職播報,以及兄弟大飯店的發財車在全台穿街走巷宣傳,但憑藉這些土法煉鋼的宣傳方式,職棒仍一炮而紅。
「那時候《職業棒球》是書店排行榜的熱門暢銷書,銷量以十萬本起跳,當年新聞局還有規定,一本雜誌最多只能刊登十五張廣告,我們的業務同事每天接下廣告訂單電話接到手軟,供不應求。」曾文誠提及,為求公平,洪騰勝要求《職業棒球》的封面人物要讓四隊球星輪流露出,編輯們也不辱使命,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企劃,包括:「萬人迷」王光輝、「盜帥」林益增 、「四大天王」黃平洋、陳義信、涂鴻欽、謝長亨⋯⋯細數第一代的職棒球星,大多是成棒時期的國手,更有從少棒時期便家喻戶曉的球員,他們一路來到職棒舞台,繼續發光發熱。曾文誠表示,當時做《職業棒球》雜誌並不困難,「其實根本不用宣傳這部戲裡頭的劇情在演什麼,大家光看卡司,就知道內容一定會很好看。」
除了強大的球星陣容外,回顧九〇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氛圍,便會發覺職棒的成功並非偶然。才剛宣布解嚴的台灣,有無限可能在眼前展開,然而娛樂的選項卻十分有限:電視還未脫離三台的限制、網路還未盛行,包廂式 KTV 也才出現不久。橫空出世的職棒提供了精采好看的比賽,讓人民無可抒發的激情有了去處。
與此同時,職棒元年正碰上了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體制內,時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受到黨內保守勢力的挑戰,引發「二月政爭」;體制外,不滿「萬年國會」的全台大學生正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前抗議,廣場中央立起了高達七公尺的「野百合花」模型作為精神象徵。
相傳,中職元年的開幕戰原先是想請總統李登輝擔任開球嘉賓,礙於政局動盪未能成行,最終才請來「世界全壘打王」王貞治參與開球儀式,以標誌性的「金雞獨立式」揮出第一棒。
街頭運動激烈的能量,直接灌注到球賽現場。場上一有不如意的判決,寶特瓶、雞蛋、便當,甚至將座椅拆下丟進場內都是家常便飯,如此混亂暴力的場景,也反映出球迷對於棒球的激情,曾文誠笑稱:「就像開餐廳雖然不想碰到奧客,但總好過都沒有人上門。」
然而,止不住的躁動,卻也釀成日後難以收拾的球場荒唐事件。
從草莽中生長的棒球文化
採訪當日,台北市正下著毛毛細雨──曾文誠指著窗外說,如果當年因為這樣的雨勢停賽,球迷極有可能會聚集在台北市立棒球場的牌樓前鼓譟,「而聯盟就在球場的正對面,只隔一條南京東路。雜誌總編輯從大門看見球迷正氣勢洶洶跨過馬路,要到聯盟辦公室抗議時,馬上大喊:『暴民來了、暴民來了。』要我們立刻把鐵門拉下來。」球迷的瘋狂與對球賽的需索,是今日難以想像的,「我們都感受到,全台灣唯一的休閒活動好像只有看棒球。」
曾文誠所描述的「暴民」並非偶發事件。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職棒剛開打兩個多月,熱度居高不下,當日又正好是端午節假日,球迷們都買好了票,準備進場觀賞兄弟象與三商虎的對決。天公卻不作美,上午聯盟就因為雨勢宣布了停賽。不料正午立完蛋以後,天氣倏忽轉晴,且日頭大好,於是球迷漸漸群聚鼓譟,要求比賽重新開打。
那時站在第一線與球迷交涉的,正是任職於聯盟播報組的梁功斌。他一邊安撫球迷、一邊接到高層的決議,表示聯盟正透過電話、BB call、廣播等各種手段,把已經放假回家的球員找回來打比賽。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這一回讓球迷嘗到甜頭,接著便一發不可收拾。十天後,六月七日的龍象大戰,天氣一樣是由雨轉晴,球迷再度聚眾,不同的是龍隊球員已趕不回球場,最終聯盟仍抵擋不了狂熱的群眾,只好讓制服整齊的兄弟象隊下場,與嚼著檳榔、穿著吊嘎,形象草莽的球迷打友誼賽。
這些如今聽起來誇張的事件,不僅顯示職棒的火紅程度,也反映出新成立的聯盟還有許多未盡完善之處:「職業」的想像落實到規範時,該如何畫出與球迷的界線;聯盟「一元化」的領導下該怎麼平衡各球團間的利益;更關鍵的是,當比賽熱度、社會關注在短時間內高度集中,而制度與監管機制尚未同步到位時,是否也在為日後各種灰色地帶,乃至於不當利益的介入,埋下了風險的種子?以上這些問題,都必須在未來一次次的衝突與挫折中尋求解答。
當棒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一路走來雖然顛簸,但可以確定的是,職棒的創建漸漸使棒球脫離「為國爭光」單一且距離遙遠的敘事,落地成為民眾的日常。人們即使不到現場,也能透過廣播、報紙、錄影帶、電視台、串流網路看見台灣棒球的蛻變。
中職自草創至今已走過近四十個年頭,對於台灣棒球造成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曾文誠回答,首先,既然稱作「職業棒球」,那它就是不折不扣的商業行為,自然會長出各式的經營方針,間接促進棒球文化生根茁壯。再者,職棒是穩定且周而復始的存在,不像國際賽需要在短時間內凝聚士氣。
「中華職棒的行事曆從元年到現在都是一樣的:三月春訓、四月開幕、七月明星賽、十月季後賽,所以對球迷來講,它讓棒球徹底融入日常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但對於曾文誠這種工作與人生都徹底投入棒球的老球迷而言,棒球遠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都是用職棒多少年,來紀錄我的人生軌跡的,有時候都還要換算一下,職棒三十六年──那是西元幾年?」
他說,身邊的球迷朋友都是如此,習慣用台灣獨有的「職棒紀年」溝通,像是活在另一個平行的棒球時空,在那裡,球迷對棒球的熱愛始終如一、永不消減。
專訪《台北市立棒球場》曾文誠
文╱温伯學
職棒風光開打,元年便達成百萬人次入場的佳績,全民不分老小都為職棒瘋狂,《民生報》每日更新戰報,《職業棒球》雜誌持續暢銷 ⋯⋯那是社會剛剛解嚴、狂躁的九〇年代初,職棒順勢成為紓解台灣社會激情的重要管道,同時,它必須在草創的混亂中站穩腳步,開創台灣棒球職業化的道路。
職棒元年首場比賽,於一九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開打。統一獅對上兄弟象,第一球由象隊投手張永昌投出,獅隊首棒打者曾智偵隨後獲得保送上壘。四局上半,統一獅隊三壘手汪俊良敲出中職史上第一支全壘打,全場氣氛沸騰到最高點,大鼓、汽笛聲齊鳴。
資深球評曾文誠仍清楚記得那一記全壘打的畫面。當時他在中華職業棒球聯盟出版的官方雜誌《職業棒球》擔任記者,親眼見證了這歷史的一刻。當天,台北市立棒球場座無虛席,僅能容納一萬四千五百人的球場,破天荒擠入一萬八千多名球迷,盛況空前,球迷以最直接的熱情,回應了他們對於職棒的期待。
「其實在正式開打前,聯盟曾舉辦球迷會,就已經可以感受到球迷對於職棒是多麼期待。」曾文誠說。
事實上,當時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聯盟,但有一群人,努力克服重重挑戰與困難,使台灣繼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澳洲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六個擁有職棒的國家。
混亂又美好的九○年代
對於很多老球迷來說,九○年代是一個混亂又美好的年代。
台灣剛宣布解嚴,社會充滿躁動不安卻又蓄勢待發的活力,人們一邊衝撞既有體制,一邊嘗試各種嶄新的可能。在棒球場上,經歷過七〇年代三級棒球「三冠王」的美夢、八〇年代成棒在世界舞台大放異彩的榮景,棒球逐漸成為台灣身處受挫的國際政治中,少數能被世界看見的運動項目之一。一次又一次的熬夜看比賽、一次又一次的加油吶喊,不僅累積起跨世代的集體記憶,也讓棒球在台灣社會占據無可取代的地位。
然而,當時的台灣尚未建立完整的職業棒球制度,導致一批批的菁英國手,只能遠赴海外尋求機會,無法在家鄉落地發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有「台灣職棒之父」之稱的兄弟大飯店董事長洪騰勝,憑著對於棒球的熱愛,決定以一己之力推動台灣棒球運動職業化。他遊說統一、味全、三商企業成立球團、投身職棒,並效法日職、美職,創辦《職業棒球》刊物、打造球隊吉祥物、建立啦啦隊制度,為中職日後發展奠定關鍵基礎。
職棒開打後,迅速風靡全台,而曾是台北市唯一可舉辦正式棒球比賽的「台北市立棒球場」,無疑是承載最多老球迷記憶情感的所在。「不只職棒,只要是在台北市立棒球場舉辦的比賽,都是重要的比賽」,曾文誠回憶,光從八〇年代起算,就有輔仁大學和文化大學棒球兩強對抗的梅花旗,成棒甲組的錦標賽中正杯、國慶盃,和棒協固定舉辦的國際邀請賽等精采賽事;職棒成立後,多場重要關鍵賽事:開幕賽、明星賽、冠軍賽,幾乎都在這座球場輪番上演。
球員的精采表現、球迷震耳欲聾的應援、年少時逃票進場看比賽的回憶,甚至是輸球時球迷憤怒拆座椅砸球場、球員與球迷爆發衝突的失控場面,以及簽賭案爆發後,空蕩冷清的觀眾席──球員與球迷間的喜悅與激情、混亂與失落,全都深深烙印在這座球場之中。
二○○○年,台北市立棒球場因設備老舊、年久失修,決定停用並拆除,原址改建成現今的「台北小巨蛋」。隨著這座球場走入歷史,一個時代的棒球風景,也被定格在最雋永的時光裡。
時隔二十年,就在中職歷經五次簽賭案、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並重新站起之際,一個名為《台北市立棒球場》的 Podcast 節目誕生。由資深球評曾文誠與梁功斌主持,節目以這座已不存在,但擁有許多球迷共同記憶的球場為名,回望台灣職棒草創時期的熱血與混亂,也重新梳理台灣棒球如何走過傷痕、繼續前行。
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二○二○年,曾文誠應同是知名球評的製作人王啟恩Adam之邀,投入《台北市立棒球場》的錄製。他怕單口說故事欠缺火花,於是找到曾參與職棒成立的要角梁功斌加入,最初只當「兩個老人家來聊聊以前的事情」,連能不能撐完一季都沒有把握,未料麥克風一開,資深與新進球迷便連連敲碗,時至二○二六年初已播畢六季。
兩人從閒聊講古,到訪問球員、教練、球團老闆、記者、球迷⋯⋯六年下來已有深厚的「中職口述歷史」份量。若嚴肅地看待,這是以Podcas 形式在為台灣職業棒球留下珍貴史料;但若輕鬆聆聽,普羅大眾也能隨節目開頭的jingle穿梭時空,和兩位主持人一同回到職棒方興未艾的九〇年代。
「《台北市立棒球場》這個名稱應該就涵蓋了一切。」曾文誠說道。節目談的是台灣職棒史,而曾經的台北市立棒球場對於許多老球迷來說,更是啟蒙棒球人生的重要聖地。
曾文誠仍記得,從永和老家只要搭一班公車就能抵達台北市立棒球場,當時的球場和早期的二輪戲院一樣,不清場,一入座就可以看上一整天。他特別喜歡到本壘板後座位區,坐在那聽一群老人家聊天看棒球,「沒想到一回神,我也變成老人家了。」今年已六十五歲的他笑說。
「我當時的生活除了棒球、還是棒球。」曾文誠說,他是貨真價實的棒球癡、棒球狂。正因如此,年少的他見到報紙上《職業棒球》徵人廣告時,便決定不顧一切地辭去穩定的貿易公司工作,加入前景難料的中職,擔任雜誌記者。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曾文誠正式到《職業棒球》報到。對他來說,那是一段難忘的生命歲月,在中職工作的期間,他每晚都想著第二天要趕快去上班,甚至覺得「休假是很浪費生命的」。尤其看著洪騰勝親力親為參與大小會議、帶頭整理場地,飯店員工也都身兼二職協助籌辦職棒,「看他以身作則,我們會覺得必須跟上去,一起為棒球拚一次看看。」
中職草創之初,外界並不看好台灣成立職棒,當時報導體育新聞的指標媒體《民生報》連續用多篇專欄抨擊中職,認為台灣的球員與觀眾數量都不足以支撐職業化發展。但外界愈是不看好,反而愈是激起團隊堅定的凝聚力。曾文誠回憶:「籌備期間,同事們都未曾想過失敗,反而有種『革命前夕』的亢奮,我們正在創造台灣棒球的歷史。」
躁動時代下投出的第一球
幾乎在開打後的第一周,職棒熱度就延燒開來,狠狠打臉事前看衰的媒體輿論。曾文誠點出,儘管初期職棒比賽並沒有電視live轉播,只有中廣主播兼職播報,以及兄弟大飯店的發財車在全台穿街走巷宣傳,但憑藉這些土法煉鋼的宣傳方式,職棒仍一炮而紅。
「那時候《職業棒球》是書店排行榜的熱門暢銷書,銷量以十萬本起跳,當年新聞局還有規定,一本雜誌最多只能刊登十五張廣告,我們的業務同事每天接下廣告訂單電話接到手軟,供不應求。」曾文誠提及,為求公平,洪騰勝要求《職業棒球》的封面人物要讓四隊球星輪流露出,編輯們也不辱使命,留下許多令人難忘的企劃,包括:「萬人迷」王光輝、「盜帥」林益增 、「四大天王」黃平洋、陳義信、涂鴻欽、謝長亨⋯⋯細數第一代的職棒球星,大多是成棒時期的國手,更有從少棒時期便家喻戶曉的球員,他們一路來到職棒舞台,繼續發光發熱。曾文誠表示,當時做《職業棒球》雜誌並不困難,「其實根本不用宣傳這部戲裡頭的劇情在演什麼,大家光看卡司,就知道內容一定會很好看。」
除了強大的球星陣容外,回顧九〇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氛圍,便會發覺職棒的成功並非偶然。才剛宣布解嚴的台灣,有無限可能在眼前展開,然而娛樂的選項卻十分有限:電視還未脫離三台的限制、網路還未盛行,包廂式 KTV 也才出現不久。橫空出世的職棒提供了精采好看的比賽,讓人民無可抒發的激情有了去處。
與此同時,職棒元年正碰上了台灣民主轉型的關鍵時刻:體制內,時任總統與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受到黨內保守勢力的挑戰,引發「二月政爭」;體制外,不滿「萬年國會」的全台大學生正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前抗議,廣場中央立起了高達七公尺的「野百合花」模型作為精神象徵。
相傳,中職元年的開幕戰原先是想請總統李登輝擔任開球嘉賓,礙於政局動盪未能成行,最終才請來「世界全壘打王」王貞治參與開球儀式,以標誌性的「金雞獨立式」揮出第一棒。
街頭運動激烈的能量,直接灌注到球賽現場。場上一有不如意的判決,寶特瓶、雞蛋、便當,甚至將座椅拆下丟進場內都是家常便飯,如此混亂暴力的場景,也反映出球迷對於棒球的激情,曾文誠笑稱:「就像開餐廳雖然不想碰到奧客,但總好過都沒有人上門。」
然而,止不住的躁動,卻也釀成日後難以收拾的球場荒唐事件。
從草莽中生長的棒球文化
採訪當日,台北市正下著毛毛細雨──曾文誠指著窗外說,如果當年因為這樣的雨勢停賽,球迷極有可能會聚集在台北市立棒球場的牌樓前鼓譟,「而聯盟就在球場的正對面,只隔一條南京東路。雜誌總編輯從大門看見球迷正氣勢洶洶跨過馬路,要到聯盟辦公室抗議時,馬上大喊:『暴民來了、暴民來了。』要我們立刻把鐵門拉下來。」球迷的瘋狂與對球賽的需索,是今日難以想像的,「我們都感受到,全台灣唯一的休閒活動好像只有看棒球。」
曾文誠所描述的「暴民」並非偶發事件。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職棒剛開打兩個多月,熱度居高不下,當日又正好是端午節假日,球迷們都買好了票,準備進場觀賞兄弟象與三商虎的對決。天公卻不作美,上午聯盟就因為雨勢宣布了停賽。不料正午立完蛋以後,天氣倏忽轉晴,且日頭大好,於是球迷漸漸群聚鼓譟,要求比賽重新開打。
那時站在第一線與球迷交涉的,正是任職於聯盟播報組的梁功斌。他一邊安撫球迷、一邊接到高層的決議,表示聯盟正透過電話、BB call、廣播等各種手段,把已經放假回家的球員找回來打比賽。
會吵的孩子有糖吃,這一回讓球迷嘗到甜頭,接著便一發不可收拾。十天後,六月七日的龍象大戰,天氣一樣是由雨轉晴,球迷再度聚眾,不同的是龍隊球員已趕不回球場,最終聯盟仍抵擋不了狂熱的群眾,只好讓制服整齊的兄弟象隊下場,與嚼著檳榔、穿著吊嘎,形象草莽的球迷打友誼賽。
這些如今聽起來誇張的事件,不僅顯示職棒的火紅程度,也反映出新成立的聯盟還有許多未盡完善之處:「職業」的想像落實到規範時,該如何畫出與球迷的界線;聯盟「一元化」的領導下該怎麼平衡各球團間的利益;更關鍵的是,當比賽熱度、社會關注在短時間內高度集中,而制度與監管機制尚未同步到位時,是否也在為日後各種灰色地帶,乃至於不當利益的介入,埋下了風險的種子?以上這些問題,都必須在未來一次次的衝突與挫折中尋求解答。
當棒球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一路走來雖然顛簸,但可以確定的是,職棒的創建漸漸使棒球脫離「為國爭光」單一且距離遙遠的敘事,落地成為民眾的日常。人們即使不到現場,也能透過廣播、報紙、錄影帶、電視台、串流網路看見台灣棒球的蛻變。
中職自草創至今已走過近四十個年頭,對於台灣棒球造成最深刻的影響是什麼?曾文誠回答,首先,既然稱作「職業棒球」,那它就是不折不扣的商業行為,自然會長出各式的經營方針,間接促進棒球文化生根茁壯。再者,職棒是穩定且周而復始的存在,不像國際賽需要在短時間內凝聚士氣。
「中華職棒的行事曆從元年到現在都是一樣的:三月春訓、四月開幕、七月明星賽、十月季後賽,所以對球迷來講,它讓棒球徹底融入日常中,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但對於曾文誠這種工作與人生都徹底投入棒球的老球迷而言,棒球遠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都是用職棒多少年,來紀錄我的人生軌跡的,有時候都還要換算一下,職棒三十六年──那是西元幾年?」
他說,身邊的球迷朋友都是如此,習慣用台灣獨有的「職棒紀年」溝通,像是活在另一個平行的棒球時空,在那裡,球迷對棒球的熱愛始終如一、永不消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