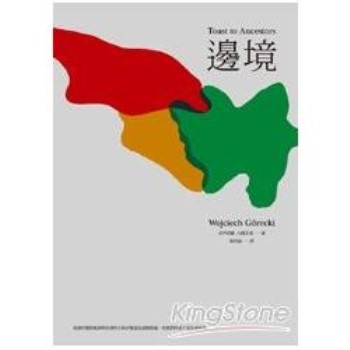故事有關亞賽拜然、喬治亞和亞美尼亞這三個前蘇聯國家,他們目前正致力於建立獨立的國家地位。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在幾世紀前曾為繁榮的王國,卻受環伺的強鄰所粉碎。亞賽拜然不曾以統一國家的形式存在( 除了1918-1920年這段時期之外),但在證明自身存在的權力時,往往樂於提到過去。
亞賽拜然人、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大半都不懷疑他們屬於歐洲。
我於上世紀九○年代初開始造訪這些地方,當時這地區被稱為外高加索(如今最常被稱為「南高加索」)。新興國家的誕生伴隨著戰爭、造反和政變,黑社會在此蓬勃發展,匪盜橫行而貧窮蔓延。後來簽訂了停戰協議,匪盜的財產受到合法化,國家的貨幣也得到強化,繼之而來的是脆弱的穩定期。當然,我們在觀察喬治亞於2008年時發生的慘劇時,可發現「歷史的終結」(註:杭亭頓的觀點)並未出現。
我曾多次到過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更在亞賽拜然住過五年,基於此因素和其它結構性的考量,我將亞賽拜然自成一篇,而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則合成一篇另述。
《邊境》可說是《高加索星球》這本書的延續,該書的焦點在北高加索,尤其是俄羅斯聯邦中的山地共和國。
沃伊切赫‧古瑞斯基
?
「你自己到不了的」,克林提出警告,「出城後向南走,你會經過往洛克巴坦的第一和第二個出口,然後是往普塔的出口。一公里後出現一條往右轉的泥土路,我們就在這條路上見。」
從市中心最好是走石油商大道,接著穿過百沃弗,此處的沙皇監獄仍開放著,史達林曾在此服監,之後前往斯伊霍沃。
「巴庫郊區非常廣闊、景色如畫且充滿異國風」,半世紀前,瓦茨瓦夫.庫巴茨基(Wac3aw Kubacki)如此寫道。「堆疊、條編、修補;蘆葦稈、麥稈和棚屋;極端的宿營地,由鐵板、電線、破魚網、扯裂的袋子、紙箱、繩索和碎裂裝茶箱湊合成的整體。以「可用」廢棄物建成的七彩城市,自得自在。」
這個世界四十年來,或者可說是四百年來一成不變,只有使用的材料改變,到處充斥著來自暴發戶的豪華領地及膨脹消費下產生的塑膠垃圾。貧民窟就堆擠在擁有吸引人的水療中心和私人沙灘的優雅旅館及飯店圍牆後面,那兒住著西方的石油從業人員,他們是鑽井平台、抽油站、油輪和油管方面的專家,他們在自己國內享受不起這樣的奢華生活。在亞賽拜然決定將石油輸往西方後,旅館及飯店業在近幾年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名字大多取為:「巴巴多斯」、「拉瑪達」、「新月海灘」等。
最後我們穿過旅館和貧民窟,就此離開巴庫。左方可見裏海,但無法到達岸邊,海岸被鉅大的產業所佔據,包括造船廠、煉油廠和一些共產主義高峰時期所建的工廠,現今已被現代化,但難以進行改造,將之拆除重建可能要容易些。在糾結的管路和生鏽的廢鐵堆中,廠房及大型集油槽間穿插著石棉瓦蓋的屋子,人們就在此生活。(類似的房子我曾在巴瓦罕和畢比埃伊巴特的老油田中見過,它們被閃著光澤的油池所圍繞,要走過必須鋪上木板,這些都是首波石油潮的遺留,就如同高爾基筆下的巴庫,地獄的樣貌應就是這樣了,就算給契訶夫百萬盧比,他也不願住在這兒。
右側鐵道外點綴著戈布斯坦斯克的錐狀山峰,植被稀疏的草原上有稀疏的草、灌木、梗草,路邊放牧著白、灰、棕和黑色的綿羊群。
土壤和其上生長的植物皆呈褐色,為太陽曬焦,佈滿灰塵。在庫拉河入海處的薩里揚努夫附近,顏色才明亮起來,而鮮綠色則得在三百公里外的伊朗邊境,屬亞熱帶的塔利什才見得到(至喬治亞邊界的距離為二倍,由埃拉特向西行,然後通過庫拉低地及小高加索山脈側邊),今天的目的地比較近,距巴庫二十多、至多三十公里。
「喬治亞和亞美尼亞靠黑海和安那托利亞與古歐洲及之後的拜占庭維持聯繫」,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cinski )在《柯爾克孜下馬》一書中寫道,「他們自此接受基督宗教,抵抗伊斯蘭在這片土地上的擴張。」「歐洲對亞賽拜然的影響則變弱,成為次要。高加索山及亞美尼亞高原形成歐洲與亞賽拜然間的屏障,亞賽拜然的東部漸入平原,交通方便且地勢開放,使亞賽拜然成為中亞的前哨站。」
克林在一輛老拉達中等著,如此破舊不堪的車讓他羞於開上路。車無前燈和後視鏡,車後玻璃也以夾板取代,而前方的擋風玻璃在幾經破壞後,僅勉強維持於原處,扭曲的車輪在沙上留下歪曲線條,彷彿成千醉漢騎自行車自此經過,大概連最貪腐的警察也不放過這樣的破車,不過克林也沒錢賄賂。他將拉達車開到十字路口,然後伺機而動,有時他開這車運幾袋煤球或幾串香蕉,不過路程僅限於公路到家和家到公路這一段。
我們跟著他,道路緩和地蜿蜒而上,深入戈布斯坦斯克山區,很快地海岸就自眼前消失了。老實說,這根本不能說是山,此區的山丘不過三、四百公尺,往西走山勢才逐漸走高,在午後的陽光下,它們看來像是征服月球或討論火星生命等影片中的荒蕪場景。這些山丘除了覆蓋其上的稀疏雜草,和我們行進中的道路外,一無所有,連棵矮樹或較大的石塊也沒有,毫無人跡,似乎連鳥也不飛來此地。我知道這只是錯覺,草叢中必盤旋著蛇和無以計數的昆蟲,而數公里外即是造船廠、煉油廠和連接巴庫、德黑蘭及第比利斯的公路。手機可通。我還是直覺地檢查了油箱和飲水量。
都怪那些錐狀山丘。這裡有半數的山為休火山,它們並非沉睡,感覺像緊張的午後小睡,附近是活動旺盛的活火山群集地,每隔片刻就吞吐出帶鐵味的冷泥,高達數公尺,但也有高度僅數公分的微火山,其實是地表的開口,自其中吐出泥濘的泡沫。最大的火山可將泥柱拋出數百公尺遠,幸好它們隔幾年、甚至幾十年才爆發一次。
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附近的山洞中發現了大量的岩畫,至少有數千年的歷史。相信古高加索和斯堪的那維亞有關聯的托爾.海爾達爾(Thor Heyerdahl),在此找到類似維京船的船圖。
山洞外數公里處的山中隱藏著加爾亞圖伊皮爾(黑騎士)。皮爾為聖地,是民族的神聖之所。皮爾最常指的是聖人之墓(波斯語中意味神聖、鬍鬚半白的老者),但在阿爾提翁島則以崇拜隕石為皮爾,而薩比拉巴德以崇拜蛇為皮爾,在距離度假勝地 「Green Village」 和 「Cardinal」相鄰的那布拉南,皮爾指的是樹叢。被葬在天然石窖中的神秘騎士,應該是位隱士、蘇菲酋長或當地的羅賓漢吧!經過加固的墓穴當繞三圈而行。「偉人,強壯的皮爾。」墓穴的看守人這麼對我說。什麼時候的人? 「三百年前,或者千年前吧!」 我因好奇而沿著碎石路找到這裡,路就在皮爾這兒終止了。守墓人還告訴我,必須將石塊往鄰近的岩石上扔,如果停在某個缺口上,祈求就會獲得成全。我照著投去,不過石塊滾了下來,嘲弄我想像的意向。
戈布斯坦斯克山的另一隱蔽處在火山環繞的山谷間,山谷本身看來就像個火山口,蘇菲﹛哈密德墓地也就在此展開。傳說,哈密德死後屍體被放在駱駝上,之後駱駝停下的地方就成為他的葬身處,此為聖者的旨意。那已是古早時候的事了,至少三百年前或千年前吧!哈密德墓穴旁立著駱駝石像,墓地沿著周邊展開,每個人都想依傍聖者,好更接近天堂。千百座墓中最古老者早就湮沒於荒草間,較新的墓上還殘留阿拉伯碑文,更新一些的有西里爾刻字,且畫上鮮明的色彩,十數年間將不褪色。到處雕刻著與死者有關的物品,如酒館老闆的墓以茶壺裝飾,而私家司機的墓則以卡車圖案裝飾。新墓以拉丁字符為主,但阿拉伯字母也逐漸可見。
夜晚自蘇菲雅﹛哈密德墓園可望見三迦超(Sangacza﹛)的光輝,這是一座超現代化的終點站,由英國石油公司經營,為裏海的石油及天然氣以油管經由黑海和地中海輸送的起點。
這條路數度分叉開來,有時這些支路又合在一起,有時卻消失在最近的坡地中。克林是對的,沒有嚮導到不了,下個轉彎處後是一片不大的高原,在其邊緣處,也就是下一座山丘前端,蹲伏著一座窮困的農莊,就是這兒了!
亞賽拜然人、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大半都不懷疑他們屬於歐洲。
我於上世紀九○年代初開始造訪這些地方,當時這地區被稱為外高加索(如今最常被稱為「南高加索」)。新興國家的誕生伴隨著戰爭、造反和政變,黑社會在此蓬勃發展,匪盜橫行而貧窮蔓延。後來簽訂了停戰協議,匪盜的財產受到合法化,國家的貨幣也得到強化,繼之而來的是脆弱的穩定期。當然,我們在觀察喬治亞於2008年時發生的慘劇時,可發現「歷史的終結」(註:杭亭頓的觀點)並未出現。
我曾多次到過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更在亞賽拜然住過五年,基於此因素和其它結構性的考量,我將亞賽拜然自成一篇,而喬治亞和亞美尼亞則合成一篇另述。
《邊境》可說是《高加索星球》這本書的延續,該書的焦點在北高加索,尤其是俄羅斯聯邦中的山地共和國。
沃伊切赫‧古瑞斯基
?
「你自己到不了的」,克林提出警告,「出城後向南走,你會經過往洛克巴坦的第一和第二個出口,然後是往普塔的出口。一公里後出現一條往右轉的泥土路,我們就在這條路上見。」
從市中心最好是走石油商大道,接著穿過百沃弗,此處的沙皇監獄仍開放著,史達林曾在此服監,之後前往斯伊霍沃。
「巴庫郊區非常廣闊、景色如畫且充滿異國風」,半世紀前,瓦茨瓦夫.庫巴茨基(Wac3aw Kubacki)如此寫道。「堆疊、條編、修補;蘆葦稈、麥稈和棚屋;極端的宿營地,由鐵板、電線、破魚網、扯裂的袋子、紙箱、繩索和碎裂裝茶箱湊合成的整體。以「可用」廢棄物建成的七彩城市,自得自在。」
這個世界四十年來,或者可說是四百年來一成不變,只有使用的材料改變,到處充斥著來自暴發戶的豪華領地及膨脹消費下產生的塑膠垃圾。貧民窟就堆擠在擁有吸引人的水療中心和私人沙灘的優雅旅館及飯店圍牆後面,那兒住著西方的石油從業人員,他們是鑽井平台、抽油站、油輪和油管方面的專家,他們在自己國內享受不起這樣的奢華生活。在亞賽拜然決定將石油輸往西方後,旅館及飯店業在近幾年間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名字大多取為:「巴巴多斯」、「拉瑪達」、「新月海灘」等。
最後我們穿過旅館和貧民窟,就此離開巴庫。左方可見裏海,但無法到達岸邊,海岸被鉅大的產業所佔據,包括造船廠、煉油廠和一些共產主義高峰時期所建的工廠,現今已被現代化,但難以進行改造,將之拆除重建可能要容易些。在糾結的管路和生鏽的廢鐵堆中,廠房及大型集油槽間穿插著石棉瓦蓋的屋子,人們就在此生活。(類似的房子我曾在巴瓦罕和畢比埃伊巴特的老油田中見過,它們被閃著光澤的油池所圍繞,要走過必須鋪上木板,這些都是首波石油潮的遺留,就如同高爾基筆下的巴庫,地獄的樣貌應就是這樣了,就算給契訶夫百萬盧比,他也不願住在這兒。
右側鐵道外點綴著戈布斯坦斯克的錐狀山峰,植被稀疏的草原上有稀疏的草、灌木、梗草,路邊放牧著白、灰、棕和黑色的綿羊群。
土壤和其上生長的植物皆呈褐色,為太陽曬焦,佈滿灰塵。在庫拉河入海處的薩里揚努夫附近,顏色才明亮起來,而鮮綠色則得在三百公里外的伊朗邊境,屬亞熱帶的塔利什才見得到(至喬治亞邊界的距離為二倍,由埃拉特向西行,然後通過庫拉低地及小高加索山脈側邊),今天的目的地比較近,距巴庫二十多、至多三十公里。
「喬治亞和亞美尼亞靠黑海和安那托利亞與古歐洲及之後的拜占庭維持聯繫」,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cinski )在《柯爾克孜下馬》一書中寫道,「他們自此接受基督宗教,抵抗伊斯蘭在這片土地上的擴張。」「歐洲對亞賽拜然的影響則變弱,成為次要。高加索山及亞美尼亞高原形成歐洲與亞賽拜然間的屏障,亞賽拜然的東部漸入平原,交通方便且地勢開放,使亞賽拜然成為中亞的前哨站。」
克林在一輛老拉達中等著,如此破舊不堪的車讓他羞於開上路。車無前燈和後視鏡,車後玻璃也以夾板取代,而前方的擋風玻璃在幾經破壞後,僅勉強維持於原處,扭曲的車輪在沙上留下歪曲線條,彷彿成千醉漢騎自行車自此經過,大概連最貪腐的警察也不放過這樣的破車,不過克林也沒錢賄賂。他將拉達車開到十字路口,然後伺機而動,有時他開這車運幾袋煤球或幾串香蕉,不過路程僅限於公路到家和家到公路這一段。
我們跟著他,道路緩和地蜿蜒而上,深入戈布斯坦斯克山區,很快地海岸就自眼前消失了。老實說,這根本不能說是山,此區的山丘不過三、四百公尺,往西走山勢才逐漸走高,在午後的陽光下,它們看來像是征服月球或討論火星生命等影片中的荒蕪場景。這些山丘除了覆蓋其上的稀疏雜草,和我們行進中的道路外,一無所有,連棵矮樹或較大的石塊也沒有,毫無人跡,似乎連鳥也不飛來此地。我知道這只是錯覺,草叢中必盤旋著蛇和無以計數的昆蟲,而數公里外即是造船廠、煉油廠和連接巴庫、德黑蘭及第比利斯的公路。手機可通。我還是直覺地檢查了油箱和飲水量。
都怪那些錐狀山丘。這裡有半數的山為休火山,它們並非沉睡,感覺像緊張的午後小睡,附近是活動旺盛的活火山群集地,每隔片刻就吞吐出帶鐵味的冷泥,高達數公尺,但也有高度僅數公分的微火山,其實是地表的開口,自其中吐出泥濘的泡沫。最大的火山可將泥柱拋出數百公尺遠,幸好它們隔幾年、甚至幾十年才爆發一次。
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附近的山洞中發現了大量的岩畫,至少有數千年的歷史。相信古高加索和斯堪的那維亞有關聯的托爾.海爾達爾(Thor Heyerdahl),在此找到類似維京船的船圖。
山洞外數公里處的山中隱藏著加爾亞圖伊皮爾(黑騎士)。皮爾為聖地,是民族的神聖之所。皮爾最常指的是聖人之墓(波斯語中意味神聖、鬍鬚半白的老者),但在阿爾提翁島則以崇拜隕石為皮爾,而薩比拉巴德以崇拜蛇為皮爾,在距離度假勝地 「Green Village」 和 「Cardinal」相鄰的那布拉南,皮爾指的是樹叢。被葬在天然石窖中的神秘騎士,應該是位隱士、蘇菲酋長或當地的羅賓漢吧!經過加固的墓穴當繞三圈而行。「偉人,強壯的皮爾。」墓穴的看守人這麼對我說。什麼時候的人? 「三百年前,或者千年前吧!」 我因好奇而沿著碎石路找到這裡,路就在皮爾這兒終止了。守墓人還告訴我,必須將石塊往鄰近的岩石上扔,如果停在某個缺口上,祈求就會獲得成全。我照著投去,不過石塊滾了下來,嘲弄我想像的意向。
戈布斯坦斯克山的另一隱蔽處在火山環繞的山谷間,山谷本身看來就像個火山口,蘇菲﹛哈密德墓地也就在此展開。傳說,哈密德死後屍體被放在駱駝上,之後駱駝停下的地方就成為他的葬身處,此為聖者的旨意。那已是古早時候的事了,至少三百年前或千年前吧!哈密德墓穴旁立著駱駝石像,墓地沿著周邊展開,每個人都想依傍聖者,好更接近天堂。千百座墓中最古老者早就湮沒於荒草間,較新的墓上還殘留阿拉伯碑文,更新一些的有西里爾刻字,且畫上鮮明的色彩,十數年間將不褪色。到處雕刻著與死者有關的物品,如酒館老闆的墓以茶壺裝飾,而私家司機的墓則以卡車圖案裝飾。新墓以拉丁字符為主,但阿拉伯字母也逐漸可見。
夜晚自蘇菲雅﹛哈密德墓園可望見三迦超(Sangacza﹛)的光輝,這是一座超現代化的終點站,由英國石油公司經營,為裏海的石油及天然氣以油管經由黑海和地中海輸送的起點。
這條路數度分叉開來,有時這些支路又合在一起,有時卻消失在最近的坡地中。克林是對的,沒有嚮導到不了,下個轉彎處後是一片不大的高原,在其邊緣處,也就是下一座山丘前端,蹲伏著一座窮困的農莊,就是這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