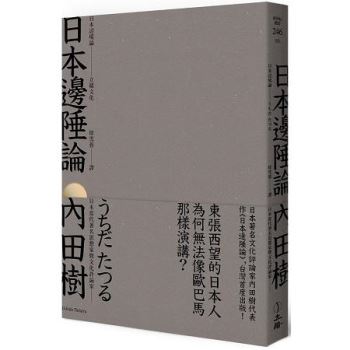日本人為何無法像歐巴馬那樣演講
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歐巴馬對著來到華盛頓的兩百萬聽眾做了一場歷史性的就職演說。那是一場相當傑出的演講。為此,我認為日本人多少會感到有些落寞,困惑「為何日本首相沒辦法像他那樣?」當然,每個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不同,但更重要的是結構性問題。各位記得嗎?該就職演說的「重點」在於提到建國先賢的段落。
為了我們,他們只帶著簡單的行李就遠渡重洋,來到這裡追求新天地。為了我們,他們辛勤勞動,開墾西部,風吹日曬,篳路藍縷。為了我們,他們在康考特、蓋茲堡、諾曼第、溪生等地奮戰,喪生。他們胼手胝足,犧牲奉獻。心之所願就是為後人打造美好家園。(……)他們想把美國建設成超越個人野心之總和的國家;在這裡,不論出身,無拘貧富,超越黨派,每個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夢想。他們走過的路,我們必將追隨。我們至今仍是世上最繁榮、興盛的國家。(……)我們必須再度奮起,撢落身上的塵埃,再造強大的美國。
很感動吧!無論是清教徒、來自非洲的奴隸、西部拓荒者,或亞洲移民,前人的眼淚與血汗都是為了此時此地的「我們」而流的。「美國人」超越了人種、宗教、文化差異,從前人那裡得到了「禮物」,同時也繼承了將它流芳後世的「責任」。美國人之所以是美國人,乃因過去的美國人就是這麼做的。這就是美國人採用的「民族物語」。
美國人的民族性在建國之初就做了「初始設定」,發展不順代表偏離了初衷。倘若美國運作不順暢(就像電腦操作失誤般),只要回歸初始設定即可。國家面臨重大關鍵時,也只需回到問題的起源即可,那就是:「我們當初創立這個國家的目的為何?」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卻想反問:真是「理所當然」嗎?對此,我持懷疑的態度。至少我們日本人就不會「那樣想」。面臨國家危機時,我們不會回歸「最初創立這個國家的目的為何」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國家並非基於某種理念創造的;換言之,我們缺乏一個得以回歸的初始設定。我們並不會認為對馬的武士是「為了我們」而跟元朝和高麗同盟軍作戰,也不覺得關原之役士兵的血是「為了我們」而流,更不會認為屯田兵千辛萬苦開拓北海道是「為了我們」。我們周遭根本沒人在歌頌他們的偉大,說:我們此刻的繁榮是先人的血汗換來的,我們必須繼承他們的使命與夢想,並流傳給下一代。至少我個人並不曾看過。
對距今比較近的戰爭亡者,大家應該記憶猶存,因此也並不是沒人追問他們為何而死?如此的死亡又為我們帶來了什麼?但是,問題的答案卻相當分歧。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人,死亡的意義在我們國民之間也不具共識。就某些人來看,這些陣亡者是「護國英靈」,對另一批人而言卻是「戰爭共犯」,可謂評價兩極。他們為何而死?死亡的代價給我們帶來什麼?留給後人哪些未竟的志業?而我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遺產與使命?該如何傳承給下一代?很可悲地,日本國民對這些問題都沒有共識。
被動員參與沖繩之役的大和戰艦年輕士官,對自己要在戰略中邁向無意義的死亡深感苦惱。他們在士官室裡熱烈討論著將臨的死亡意義何在。其中一位海軍大尉在爭論後所做的總結,被吉田滿寫進《大和戰艦之末日》裡。
不進步則無戰勝之可能,失敗後之覺醒方為最佳之道。日本太輕視進步,長期拘泥於個人之潔癖與德義,忘卻進步的真義。失敗後不覺醒,日本怎能得救?此時仍不覺醒,更待何時?身先士卒乃我等衷心之所願,為日本重生肝腦塗地亦在所不惜。
許多青年願意「為日本重生肝腦塗地」。他們犧牲性命,為的是給後人帶來和平與繁榮。我們得到了他們自我奉獻的「禮物」。問題是,我們是否妥善回應了他們所託付的「真正的進步」?甚至,接下如此託付的我們,是否持續講述著他們的「故事」呢?
答案是沒有。而且這狀況也不是今天才開始的;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我們幾乎不曾談論從先人那裡繼承並應流傳後世的,是怎樣的歷史遺產。相對地,我們談的是和其他國家的比較。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我們才能談論自己
我們並不以「日本必須如此」為準據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形象。是不能還是不做,那是下一個問題。我們一味熱中的是與他國的比較。唯有使用「其他國家那樣,而我們卻這樣,所以必須以他國為標準,進行自我矯正」的句型,才有能力「討論經國濟民之大業」。
歐巴馬就職演說後,有人請當時的總理大臣發表感想。他說:「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強國的協助是有必要的。」我認為這是典型日本人會有的言論。當首相想要表達「日本在世界上是怎樣的國家」時,首先浮上腦海的就是「經濟力排行」。我們若在軍事上佔優勢,或ODA、國際學力測驗等名列前茅,那麼,首相最先想到的就是這方面的「排行榜」,並會拿來陳述日本的國際角色,以及對美國有何用處。在這裡,我們完全看不到與GDP、軍事預算、諾貝爾獎得獎人數等無關,屬於該國獨有,且別國無法取代的存在理由。也就是缺乏本質的、不變的概念。
想當然耳,經濟排行榜每年都在變化,不能做為國民主體性的指標。若想以「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概念來建構美日關係,就意味著日後若變成「第三位」或「第五位」,對美關係可能會因而改變。但對這種發言大家竟然都不覺得「奇怪」,才是我認為最「奇怪」的事。
若有音樂家被問到與其他音樂家的合作展望時,回答「我想以排行榜第二名的音樂家」和對方合作,那麼,大家一定會嗤笑是個無稽的回答。排行榜每週都會變化,理論上和一個音樂家獨創的音樂無關。除卻「我想做怎樣的音樂,你想做怎樣的音樂」這種與未來創作相關的問題,並無法討論音樂合作的發展。明明在音樂上知道如此,到了外交上卻忘記「我想創造怎樣的國家,你的國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問題。對此,我感到相當不可思議。外交構想是視野的展現,與經濟力的排行理論上並不相干。應該提到的是「他國欠缺,而我國獨具之處」,但首相腦子裡浮現的卻是「經濟力排行」。或許與個人特質有關,但若沒有人覺得這回答很「奇怪」,那就是全體國民的問題了。
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我們才能描繪本國的形象。此外,我們也無法討論國家戰略。每當要觸碰這類議題時,思考就會自動陷入停止的狀態。這是日本人顯著的國民性。記得大塚英志先生曾策畫一場作文比賽,主題是請高中生執筆日本憲法。後來高橋源一郎先生告訴我,其中一位參賽者寫道:希望日本成為一個「中等國家」。我聽了和他相視而笑,不約而同說出「好中肯喔!」。「中等國家」的說法讓我們很有「感覺」。此話怎講?因為,除了日本人,再也沒有別的國民會這樣遣詞用字了。我想這個高中生的發言應該會讓許多日本人產生共鳴,覺得「言之有理」吧!因為這句話精準地掌握了日本人設定的國家形象。
右邊有「那個國家」,左邊則是「這個國家」,而我們處於他們之間的某個地方。唯有這樣,我們才能闡述自己的國家定位。但這並非在說日本人不夠堅毅,或沒有原則,我想表達的是:日本原本就是這樣的國家。因此,這個高中生完美道出了日本的國家本質。日本這個國家並非基於某種理念而建國的;是先有了這個國家,再根據自己與其他國的關係,決定自身的相對地位。我們先參照其他國家的看法,之後再決定本國的視野。
歐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各大報社論最先討論的都是「新總統對日本的態度是親善的還是威嚇的。他們會回應日本的要求,亦或輕視日本」這樣的問題。比起探討美國對東亞戰略的「內涵」,具體而言,我們優先討論的是與日本接觸時,他們的「語氣、表情、態度」如何的問題。對方表現若較溫和,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會比較敢提出要求。倘若對方的態度不妥協,那麼即使不情願,也只好默默承受。總之就是要看對方的臉色行事。像這樣,日本媒體最關心的,並非美國外交戰略的「內涵」,而是他們表現出來的「態度」。號稱「外交達人」的,都自信滿滿且眾口一致地宣稱:「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根本」。這樣說應該有其道理。但並不意味美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一致,也不代表比起其他國家,美國會更優先考慮日本的利益。無庸置疑地,美國唯一考量的是自己的國家利益。也只有當他們精算出,若顧慮日本的好處將有利於美國時,他們才會這麼做。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當美國提出有損日本國家利益的要求時,仍無法撼動那些「外交達人」對於「唯有美日同盟一途」才是正確道路的執念。而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不合常理的判斷,乃因我們內在共享一種奇妙的憑據,認為「有時美國的要求不利於日本,這代表他們在情感上對日本比較親密。因為,唯有對『自己人』才會毫無顧忌提出無理的要求。」
小泉內閣時代曾推動「結構改革.制度緩和」的政策。講難聽一點,這是一種系統性的調整,目的是為了方便美國企業在日本從事經濟活動並提高利潤。讓美國更自由地掠奪日本,是這個體系昭然若揭的目的,但結構改革論者卻不覺得對方心懷不軌,甚至相信讓美國在日本市場盡情發揮,便能強化美日之間的「親密關係」。他們認為這樣能優先保障日本的國家利益。
日本對伊拉克戰爭所做的「人力貢獻」也是一樣。我們的政治人物理應能判斷這非但不是一場正義之戰,甚至會給國際社會帶來更大的混亂(倘若無法理解這一點,只能說他們的認知能力很有問題)。但即便如此,日本政府還是從頭到尾協助了小布希打這場毀滅性的戰爭。他們推斷美國會覺得比起「支援正義的戰爭」,「支援不義之戰」更顯現出日本是美國的「自己人」。他們認為支援孤立無援之戰,會比獲得國際社會認同的戰爭更能增進親密程度(或許吧!)。但其實就像《昭和殘俠傳》一樣,會這麼想的只有日本人而已。而且我們所傳遞的「親密」訊息,美國人恐怕是無法切身感受的(在理性上或許可以)。
日本人對於「親密感」的執著,優先重視各情境下的親密關係,勝過自我主體性的貫徹,這種傾向曾讓露絲.潘乃德甚感訝異,有關這一點,她已在《菊與刀》一書中指出了。
被俘虜的日本兵為她提供了研究語料。最令她詫異的行動莫過於異於歐美,日本兵會進一步協助敵軍一事。她在書中的描述如下:這些長年吃公家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竟然告知敵軍日本彈藥庫之所在,詳述軍隊的兵力配置,協助我軍撰寫文宣,搭乘我軍轟炸機引導追蹤軍事目標。就像翻開生命的新篇章,即使新舊頁面寫的東西截然不同,他們仍同樣忠實地實踐新扉頁上的內容。
日本人在各種情境下面對比自己強大的對象時,都會相當自然地表現出親密與無防備的態度,這種傾向與身為軍國主義者毫無悖離。池部良也曾記載過相同事例。池部從中國華北轉戰南方,之後晉升陸軍中尉,並在印尼的哈馬黑拉島直至戰爭結束。畢業於英文系、英語流利的他,被砲兵連隊長任命扮演與澳洲軍隊斡旋的角色。任職命令下達後,據說連隊長是這麼問他的。
「『對了,和洋鬼子、不、和白人見面時,第一句話要說什麼?』
『……』。由於問題來得突然,我本來應該知道的,一時卻找不出合適的英語回答。
『Thank you,對嗎?
而且聽說白人初次見面時都會擁抱、親嘴。所以我也得那麼做嗎?』」
陸軍大學出身的職業軍人向來很會欺負池部這種從學生晉升的士官或徵兵,如今態度丕變,卑屈得令他錯愕。他覺得這些人不是該負起戰敗責任,切腹謝罪嗎?但若對照潘乃德的著作來看,這似乎是日本職業軍人理所當然的反應。
永遠都要優先考慮自己與當時掌權者的親疏關係,這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不斷灌輸給日本人的教誨。而這種意識形態若非與我們國民性深切契合,那場戰爭根本就不會發生。
比起自身思想與行動的一致性,應該優先考慮的是當下的親密關係。總之就是「識時務」,以被動態勢向對方傳達恭順、親密的訊息。這種態度就是丸山真男說的「超國家主義心理」,而且早已定型化了。
丸山的解釋是這樣的。日本軍人並非依據首尾一致的政治意識形態行動,「天皇代表著終極價值,對於天皇的相對接近感」才是統整一切行動秩序的指標。
「對於這個終極實體的接近度,不僅是個別權力支配,也是讓全國機構運作的精神動力。制約官僚或軍人行為最重要的,並非合法性的意識,而是地位更優越的人,以及更接近絕對價值體的存在。(……)此處所指國家、社會地位的價值標準,與其說是社會職能,毋寧是與天皇的距離。」與當下最有權勢者在空間上的遠近親疏,暫且決定了我是什麼,以及該如何行動。這絕非老掉牙的故事。即便到了現代日本,這個機制仍運作得相當順暢。當然,那並非以天皇為頂點的權力階級制。至今依舊制約官僚、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行動的,是他們和他們所認定之「絕對價值」的接近度。主要資源都被挹注在學習如何分辨「與誰親近比較有利」,而非邏輯性地判斷「什麼才正確」。換言之,與其靠自己來做正確的判斷,不如找出那個「能做正確判斷的人」,並站在他「身邊」。這才是應該列為優先考慮的事。
在某個並非此處的他方,有一個等同世界中心的「絕對價值」。如何接近它?怎樣遠離它?這種距離意識決定了我們的思維與行動模式。接下來,我在本書中要稱這種人為「邊陲人」。
二○○九年一月二十日,歐巴馬對著來到華盛頓的兩百萬聽眾做了一場歷史性的就職演說。那是一場相當傑出的演講。為此,我認為日本人多少會感到有些落寞,困惑「為何日本首相沒辦法像他那樣?」當然,每個政治人物的個人特質不同,但更重要的是結構性問題。各位記得嗎?該就職演說的「重點」在於提到建國先賢的段落。
為了我們,他們只帶著簡單的行李就遠渡重洋,來到這裡追求新天地。為了我們,他們辛勤勞動,開墾西部,風吹日曬,篳路藍縷。為了我們,他們在康考特、蓋茲堡、諾曼第、溪生等地奮戰,喪生。他們胼手胝足,犧牲奉獻。心之所願就是為後人打造美好家園。(……)他們想把美國建設成超越個人野心之總和的國家;在這裡,不論出身,無拘貧富,超越黨派,每個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夢想。他們走過的路,我們必將追隨。我們至今仍是世上最繁榮、興盛的國家。(……)我們必須再度奮起,撢落身上的塵埃,再造強大的美國。
很感動吧!無論是清教徒、來自非洲的奴隸、西部拓荒者,或亞洲移民,前人的眼淚與血汗都是為了此時此地的「我們」而流的。「美國人」超越了人種、宗教、文化差異,從前人那裡得到了「禮物」,同時也繼承了將它流芳後世的「責任」。美國人之所以是美國人,乃因過去的美國人就是這麼做的。這就是美國人採用的「民族物語」。
美國人的民族性在建國之初就做了「初始設定」,發展不順代表偏離了初衷。倘若美國運作不順暢(就像電腦操作失誤般),只要回歸初始設定即可。國家面臨重大關鍵時,也只需回到問題的起源即可,那就是:「我們當初創立這個國家的目的為何?」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我卻想反問:真是「理所當然」嗎?對此,我持懷疑的態度。至少我們日本人就不會「那樣想」。面臨國家危機時,我們不會回歸「最初創立這個國家的目的為何」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國家並非基於某種理念創造的;換言之,我們缺乏一個得以回歸的初始設定。我們並不會認為對馬的武士是「為了我們」而跟元朝和高麗同盟軍作戰,也不覺得關原之役士兵的血是「為了我們」而流,更不會認為屯田兵千辛萬苦開拓北海道是「為了我們」。我們周遭根本沒人在歌頌他們的偉大,說:我們此刻的繁榮是先人的血汗換來的,我們必須繼承他們的使命與夢想,並流傳給下一代。至少我個人並不曾看過。
對距今比較近的戰爭亡者,大家應該記憶猶存,因此也並不是沒人追問他們為何而死?如此的死亡又為我們帶來了什麼?但是,問題的答案卻相當分歧。即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人,死亡的意義在我們國民之間也不具共識。就某些人來看,這些陣亡者是「護國英靈」,對另一批人而言卻是「戰爭共犯」,可謂評價兩極。他們為何而死?死亡的代價給我們帶來什麼?留給後人哪些未竟的志業?而我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遺產與使命?該如何傳承給下一代?很可悲地,日本國民對這些問題都沒有共識。
被動員參與沖繩之役的大和戰艦年輕士官,對自己要在戰略中邁向無意義的死亡深感苦惱。他們在士官室裡熱烈討論著將臨的死亡意義何在。其中一位海軍大尉在爭論後所做的總結,被吉田滿寫進《大和戰艦之末日》裡。
不進步則無戰勝之可能,失敗後之覺醒方為最佳之道。日本太輕視進步,長期拘泥於個人之潔癖與德義,忘卻進步的真義。失敗後不覺醒,日本怎能得救?此時仍不覺醒,更待何時?身先士卒乃我等衷心之所願,為日本重生肝腦塗地亦在所不惜。
許多青年願意「為日本重生肝腦塗地」。他們犧牲性命,為的是給後人帶來和平與繁榮。我們得到了他們自我奉獻的「禮物」。問題是,我們是否妥善回應了他們所託付的「真正的進步」?甚至,接下如此託付的我們,是否持續講述著他們的「故事」呢?
答案是沒有。而且這狀況也不是今天才開始的;一直以來都是這樣。我們幾乎不曾談論從先人那裡繼承並應流傳後世的,是怎樣的歷史遺產。相對地,我們談的是和其他國家的比較。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我們才能談論自己
我們並不以「日本必須如此」為準據來建立自己的國家形象。是不能還是不做,那是下一個問題。我們一味熱中的是與他國的比較。唯有使用「其他國家那樣,而我們卻這樣,所以必須以他國為標準,進行自我矯正」的句型,才有能力「討論經國濟民之大業」。
歐巴馬就職演說後,有人請當時的總理大臣發表感想。他說:「世界第一、第二大經濟強國的協助是有必要的。」我認為這是典型日本人會有的言論。當首相想要表達「日本在世界上是怎樣的國家」時,首先浮上腦海的就是「經濟力排行」。我們若在軍事上佔優勢,或ODA、國際學力測驗等名列前茅,那麼,首相最先想到的就是這方面的「排行榜」,並會拿來陳述日本的國際角色,以及對美國有何用處。在這裡,我們完全看不到與GDP、軍事預算、諾貝爾獎得獎人數等無關,屬於該國獨有,且別國無法取代的存在理由。也就是缺乏本質的、不變的概念。
想當然耳,經濟排行榜每年都在變化,不能做為國民主體性的指標。若想以「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的概念來建構美日關係,就意味著日後若變成「第三位」或「第五位」,對美關係可能會因而改變。但對這種發言大家竟然都不覺得「奇怪」,才是我認為最「奇怪」的事。
若有音樂家被問到與其他音樂家的合作展望時,回答「我想以排行榜第二名的音樂家」和對方合作,那麼,大家一定會嗤笑是個無稽的回答。排行榜每週都會變化,理論上和一個音樂家獨創的音樂無關。除卻「我想做怎樣的音樂,你想做怎樣的音樂」這種與未來創作相關的問題,並無法討論音樂合作的發展。明明在音樂上知道如此,到了外交上卻忘記「我想創造怎樣的國家,你的國家」依然是最重要的問題。對此,我感到相當不可思議。外交構想是視野的展現,與經濟力的排行理論上並不相干。應該提到的是「他國欠缺,而我國獨具之處」,但首相腦子裡浮現的卻是「經濟力排行」。或許與個人特質有關,但若沒有人覺得這回答很「奇怪」,那就是全體國民的問題了。
唯有透過與他國的比較,我們才能描繪本國的形象。此外,我們也無法討論國家戰略。每當要觸碰這類議題時,思考就會自動陷入停止的狀態。這是日本人顯著的國民性。記得大塚英志先生曾策畫一場作文比賽,主題是請高中生執筆日本憲法。後來高橋源一郎先生告訴我,其中一位參賽者寫道:希望日本成為一個「中等國家」。我聽了和他相視而笑,不約而同說出「好中肯喔!」。「中等國家」的說法讓我們很有「感覺」。此話怎講?因為,除了日本人,再也沒有別的國民會這樣遣詞用字了。我想這個高中生的發言應該會讓許多日本人產生共鳴,覺得「言之有理」吧!因為這句話精準地掌握了日本人設定的國家形象。
右邊有「那個國家」,左邊則是「這個國家」,而我們處於他們之間的某個地方。唯有這樣,我們才能闡述自己的國家定位。但這並非在說日本人不夠堅毅,或沒有原則,我想表達的是:日本原本就是這樣的國家。因此,這個高中生完美道出了日本的國家本質。日本這個國家並非基於某種理念而建國的;是先有了這個國家,再根據自己與其他國的關係,決定自身的相對地位。我們先參照其他國家的看法,之後再決定本國的視野。
歐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各大報社論最先討論的都是「新總統對日本的態度是親善的還是威嚇的。他們會回應日本的要求,亦或輕視日本」這樣的問題。比起探討美國對東亞戰略的「內涵」,具體而言,我們優先討論的是與日本接觸時,他們的「語氣、表情、態度」如何的問題。對方表現若較溫和,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會比較敢提出要求。倘若對方的態度不妥協,那麼即使不情願,也只好默默承受。總之就是要看對方的臉色行事。像這樣,日本媒體最關心的,並非美國外交戰略的「內涵」,而是他們表現出來的「態度」。號稱「外交達人」的,都自信滿滿且眾口一致地宣稱:「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根本」。這樣說應該有其道理。但並不意味美國與日本的國家利益一致,也不代表比起其他國家,美國會更優先考慮日本的利益。無庸置疑地,美國唯一考量的是自己的國家利益。也只有當他們精算出,若顧慮日本的好處將有利於美國時,他們才會這麼做。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當美國提出有損日本國家利益的要求時,仍無法撼動那些「外交達人」對於「唯有美日同盟一途」才是正確道路的執念。而之所以會發生這種不合常理的判斷,乃因我們內在共享一種奇妙的憑據,認為「有時美國的要求不利於日本,這代表他們在情感上對日本比較親密。因為,唯有對『自己人』才會毫無顧忌提出無理的要求。」
小泉內閣時代曾推動「結構改革.制度緩和」的政策。講難聽一點,這是一種系統性的調整,目的是為了方便美國企業在日本從事經濟活動並提高利潤。讓美國更自由地掠奪日本,是這個體系昭然若揭的目的,但結構改革論者卻不覺得對方心懷不軌,甚至相信讓美國在日本市場盡情發揮,便能強化美日之間的「親密關係」。他們認為這樣能優先保障日本的國家利益。
日本對伊拉克戰爭所做的「人力貢獻」也是一樣。我們的政治人物理應能判斷這非但不是一場正義之戰,甚至會給國際社會帶來更大的混亂(倘若無法理解這一點,只能說他們的認知能力很有問題)。但即便如此,日本政府還是從頭到尾協助了小布希打這場毀滅性的戰爭。他們推斷美國會覺得比起「支援正義的戰爭」,「支援不義之戰」更顯現出日本是美國的「自己人」。他們認為支援孤立無援之戰,會比獲得國際社會認同的戰爭更能增進親密程度(或許吧!)。但其實就像《昭和殘俠傳》一樣,會這麼想的只有日本人而已。而且我們所傳遞的「親密」訊息,美國人恐怕是無法切身感受的(在理性上或許可以)。
日本人對於「親密感」的執著,優先重視各情境下的親密關係,勝過自我主體性的貫徹,這種傾向曾讓露絲.潘乃德甚感訝異,有關這一點,她已在《菊與刀》一書中指出了。
被俘虜的日本兵為她提供了研究語料。最令她詫異的行動莫過於異於歐美,日本兵會進一步協助敵軍一事。她在書中的描述如下:這些長年吃公家飯、極端的國家主義者,竟然告知敵軍日本彈藥庫之所在,詳述軍隊的兵力配置,協助我軍撰寫文宣,搭乘我軍轟炸機引導追蹤軍事目標。就像翻開生命的新篇章,即使新舊頁面寫的東西截然不同,他們仍同樣忠實地實踐新扉頁上的內容。
日本人在各種情境下面對比自己強大的對象時,都會相當自然地表現出親密與無防備的態度,這種傾向與身為軍國主義者毫無悖離。池部良也曾記載過相同事例。池部從中國華北轉戰南方,之後晉升陸軍中尉,並在印尼的哈馬黑拉島直至戰爭結束。畢業於英文系、英語流利的他,被砲兵連隊長任命扮演與澳洲軍隊斡旋的角色。任職命令下達後,據說連隊長是這麼問他的。
「『對了,和洋鬼子、不、和白人見面時,第一句話要說什麼?』
『……』。由於問題來得突然,我本來應該知道的,一時卻找不出合適的英語回答。
『Thank you,對嗎?
而且聽說白人初次見面時都會擁抱、親嘴。所以我也得那麼做嗎?』」
陸軍大學出身的職業軍人向來很會欺負池部這種從學生晉升的士官或徵兵,如今態度丕變,卑屈得令他錯愕。他覺得這些人不是該負起戰敗責任,切腹謝罪嗎?但若對照潘乃德的著作來看,這似乎是日本職業軍人理所當然的反應。
永遠都要優先考慮自己與當時掌權者的親疏關係,這是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不斷灌輸給日本人的教誨。而這種意識形態若非與我們國民性深切契合,那場戰爭根本就不會發生。
比起自身思想與行動的一致性,應該優先考慮的是當下的親密關係。總之就是「識時務」,以被動態勢向對方傳達恭順、親密的訊息。這種態度就是丸山真男說的「超國家主義心理」,而且早已定型化了。
丸山的解釋是這樣的。日本軍人並非依據首尾一致的政治意識形態行動,「天皇代表著終極價值,對於天皇的相對接近感」才是統整一切行動秩序的指標。
「對於這個終極實體的接近度,不僅是個別權力支配,也是讓全國機構運作的精神動力。制約官僚或軍人行為最重要的,並非合法性的意識,而是地位更優越的人,以及更接近絕對價值體的存在。(……)此處所指國家、社會地位的價值標準,與其說是社會職能,毋寧是與天皇的距離。」與當下最有權勢者在空間上的遠近親疏,暫且決定了我是什麼,以及該如何行動。這絕非老掉牙的故事。即便到了現代日本,這個機制仍運作得相當順暢。當然,那並非以天皇為頂點的權力階級制。至今依舊制約官僚、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行動的,是他們和他們所認定之「絕對價值」的接近度。主要資源都被挹注在學習如何分辨「與誰親近比較有利」,而非邏輯性地判斷「什麼才正確」。換言之,與其靠自己來做正確的判斷,不如找出那個「能做正確判斷的人」,並站在他「身邊」。這才是應該列為優先考慮的事。
在某個並非此處的他方,有一個等同世界中心的「絕對價值」。如何接近它?怎樣遠離它?這種距離意識決定了我們的思維與行動模式。接下來,我在本書中要稱這種人為「邊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