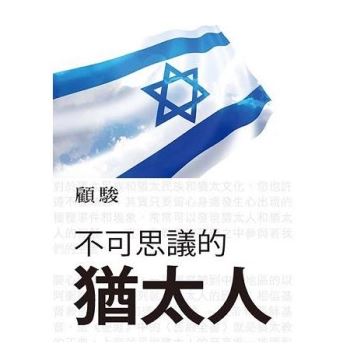聖經的民族 上帝的智慧
猶太民族是為人類貢獻了《聖經》的民族。
所謂「聖經」,顧名思義,就是具有至高神聖性的典籍。
猶太人給了《聖經》以如此之高的地位,《聖經》對猶太人又意味著什麼?
人類中的大部分跟著猶太人,給了《聖經》以如此之高的地位,《聖經》對人類文化意著什麼?
對猶太民族來說,這樣小小一本書可以在二千五百年中作為一個流散民族的樊籬,使她「散而不亡」;可作為其根本大法,使她能應付一切挑戰,並最終成為一個「取得了過多成就」的民族;這不等於說,《聖經》中已包含著猶太民族得以延存、成功和走在時代前端的「密碼」嗎?也就是說,猶太智慧以獨特的文化積澱形成,深埋於看似神話的故事言論背後,一代代人在虔誠信奉中,有意無意地承繼了民族的智慧,提升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技巧。
而對於整個人類世界來說,這樣一個小小民族的小小一本書竟分別孕育出當今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兩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感召如此之多的善男信女皈依上帝、或天主、或真主,並可以讓神學家從中找到神的旨意,道德家從中找到人倫的準則,社會學家找到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革命家找到反抗暴君的公義,《聖經》在人類歷史如此長的時期內、如此無所不在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和心理,從而實際改變著人類的現實存在,以至於今日還被公認為對世界歷史影響最大的十本書之首!
這不等於說,世界歷史是人類受《聖經》中的密碼所「左右」而留下的一條行進軌跡嗎?也就是說,上古時代的猶太人以自己的獨特智慧,融合了當時國際環境中的「世界智慧」,發現了人類社會文化的普遍問題,通過《聖經》的記載和傳播,使之成為今日真正的世界性智慧。
那麼,由此出發,我們能否進一步從《聖經》中分離出人類社會生活的若干基本特徵,解析出人類歷史進程的若干原初公式?換言之,我們能否從「猶太上帝」的道理中,發掘出人類社會存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道理?能否覓得古老民族保持青春的一般方法?能否找到一切民族及其一切成員可以藉以取得成功的一般秘訣?
帶著這樣一些根本性的智慧問題,我們走進《聖經》的殿堂,由《創世紀》開始,讓「上帝之道」(言辭)來澄清我們對神奇的猶太智慧的一片混沌。
倫理的民族 道德的智慧
猶太教在道德學家那裡有一個別名,叫做「倫理一神教」。這個名稱表明:耶和華上帝眼中的第一等大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相對於「神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言的。因為上帝造就了人類共同的祖先,所以人類世世代代一切成員都必須在上帝面前「自卑」。除此之外,任何一個人都毋須、甚至不得向任何一個人、任何一種物「自卑」。
因為向他人他物的「自卑」就是「跪拜他神」,這是在忌邪的耶和華上帝眼中為惡之事。
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人不怕下跪,就怕下跪在他人跟前;人不怕受神的約束,就怕有人可以不受神的約束;人不怕唯一的神,就怕假冒偽劣的「人」神!
所以,在正宗的「神與人的關係」支配下的「人與人的關係」是天然的平等關係、天然的民主關係、天然的法律關係、天然的最合乎道德之關係!
書的民族 學習的智慧
猶太民族素以「書的民族」著稱於世。這本「書」首先當然指的是《聖經》(舊約全書)。在第一章的篇首語中,我們已談過《聖經》對世界文化的意義、對西方文明的貢獻和對猶太民族本身價值,在此就不再重複。
必須看到,《聖經》在猶太人的心目中雖然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它根本起著一種文化淵源的作用,更生動而完整地記錄了猶太人生活方式、更豐富而全面地集中了猶太民族智慧、更具體而直接地影響著猶太人生活的是另一本書:《塔木德》。從前面兩章中我們所引用的材料,大家一定已經有所感覺。因此,在本章中,我們「偷樑換柱」,把「那本書」換成「這本書」,一則便於從另一層面發掘猶太智慧,二則擴大讀者對猶太典籍和猶太文化史的了解。畢竟,一般人了解甚或熟讀《聖經》的多,而知道《塔木德》的少。
所謂「書的民族」的第二層意思,指的是猶太民族對書(由特指的那本書而延及其他一切書)及書中所蘊藏的知識,還有對讀書過程的嗜好。書的民族是思考的民族、求知的民族、教育的民族、知識的民族、神學的民族,也是講究科學的民族。
人們所認為的決定二十世紀人類思想的三位重量級人士―—物理宇宙的愛因斯坦、人類社會學的馬克思、精神分析學的弗洛伊德,竟都是猶太裔人士,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竟有十五%是猶太人,都令人信服地證明這個民族在「書」的領域中,確有卓越不凡的智慧。
在本章中,我們就以猶太人這一本「書」的特徵為中心,對其相關智慧稍作開掘。
律法的民族 守法的智慧
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出現於公元前三十世紀,是美尼斯王國統一埃及時頒布的。遠古律法中著名的《烏爾納姆法典》(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和《漢穆拉比法典》(公元前十八世紀)都不是猶太人的作品。然而,「律法的民族」這頂桂冠卻不偏不倚地戴在猶太人的頭上。這並不奇怪。
猶太人是一個很早就自覺、系統地從事律法的建設與完善的民族。公元前十三世紀前後的「摩西十誡」為猶太民族打下律法體係的樁基:「巴比倫之囚」時期或其後,《聖經》、尤其是其中的「摩西五經」,為猶太民族的律法體系構築起主幹框架。據偉大的猶太學者邁蒙尼德拉比的權威統計,《聖經》中共包含了613條具體誡命,其中368條是「不准做的」,245條是「必須做的」。在大流散的歷程中,有關《托拉》中的戒律之注釋、實施細則以及其他規定、法典的大量產生,使得猶太人的國家尚未作為一種純粹的幻想在人們頭腦中浮現之前,猶太民族的法律實體已經完成,而其中從法哲學到具體細則,都不乏人類法律史上開拓性的創設。
而且,正因為政治實體的闕如,法律實體在猶太人的生活中發揮著現代之前在其他任何一個民族中都見所未見的作用。
《托拉》成為民族的樊籬,律法成為連結民族的紐帶:猶太人首先不是一個由「血緣」、「地緣」,而是由「上帝的律法」結合成的民族。
以民族在人類法律建設中的這眾多貢獻,以律法在民族生存中的這樣一種地位,以民族成員的這樣一種法律素質,這個民族不能稱之為「律法的民族」的話,還有什麼樣的民族能以此相稱?
不過,猶太民族在律法方面如此繁多而廣泛的建樹,卻給我們這本小書帶來一個無法克服的大難題。以我們的安排,這裡的篇幅只夠蜻蜓點水似地涉獵一下猶太人極為豐富,甚至過於豐富的律法智慧中的一角。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鬼使神差,我們選中的也許恰恰是最有違猶太人「本意」(但絕對不會有違他們本性)的守法智慧―—變通法律而遵守之智慧。
猶太民族是為人類貢獻了《聖經》的民族。
所謂「聖經」,顧名思義,就是具有至高神聖性的典籍。
猶太人給了《聖經》以如此之高的地位,《聖經》對猶太人又意味著什麼?
人類中的大部分跟著猶太人,給了《聖經》以如此之高的地位,《聖經》對人類文化意著什麼?
對猶太民族來說,這樣小小一本書可以在二千五百年中作為一個流散民族的樊籬,使她「散而不亡」;可作為其根本大法,使她能應付一切挑戰,並最終成為一個「取得了過多成就」的民族;這不等於說,《聖經》中已包含著猶太民族得以延存、成功和走在時代前端的「密碼」嗎?也就是說,猶太智慧以獨特的文化積澱形成,深埋於看似神話的故事言論背後,一代代人在虔誠信奉中,有意無意地承繼了民族的智慧,提升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技巧。
而對於整個人類世界來說,這樣一個小小民族的小小一本書竟分別孕育出當今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兩個: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感召如此之多的善男信女皈依上帝、或天主、或真主,並可以讓神學家從中找到神的旨意,道德家從中找到人倫的準則,社會學家找到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革命家找到反抗暴君的公義,《聖經》在人類歷史如此長的時期內、如此無所不在地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和心理,從而實際改變著人類的現實存在,以至於今日還被公認為對世界歷史影響最大的十本書之首!
這不等於說,世界歷史是人類受《聖經》中的密碼所「左右」而留下的一條行進軌跡嗎?也就是說,上古時代的猶太人以自己的獨特智慧,融合了當時國際環境中的「世界智慧」,發現了人類社會文化的普遍問題,通過《聖經》的記載和傳播,使之成為今日真正的世界性智慧。
那麼,由此出發,我們能否進一步從《聖經》中分離出人類社會生活的若干基本特徵,解析出人類歷史進程的若干原初公式?換言之,我們能否從「猶太上帝」的道理中,發掘出人類社會存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道理?能否覓得古老民族保持青春的一般方法?能否找到一切民族及其一切成員可以藉以取得成功的一般秘訣?
帶著這樣一些根本性的智慧問題,我們走進《聖經》的殿堂,由《創世紀》開始,讓「上帝之道」(言辭)來澄清我們對神奇的猶太智慧的一片混沌。
倫理的民族 道德的智慧
猶太教在道德學家那裡有一個別名,叫做「倫理一神教」。這個名稱表明:耶和華上帝眼中的第一等大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所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相對於「神與人之間的關係」而言的。因為上帝造就了人類共同的祖先,所以人類世世代代一切成員都必須在上帝面前「自卑」。除此之外,任何一個人都毋須、甚至不得向任何一個人、任何一種物「自卑」。
因為向他人他物的「自卑」就是「跪拜他神」,這是在忌邪的耶和華上帝眼中為惡之事。
全知全能的上帝知道:人不怕下跪,就怕下跪在他人跟前;人不怕受神的約束,就怕有人可以不受神的約束;人不怕唯一的神,就怕假冒偽劣的「人」神!
所以,在正宗的「神與人的關係」支配下的「人與人的關係」是天然的平等關係、天然的民主關係、天然的法律關係、天然的最合乎道德之關係!
書的民族 學習的智慧
猶太民族素以「書的民族」著稱於世。這本「書」首先當然指的是《聖經》(舊約全書)。在第一章的篇首語中,我們已談過《聖經》對世界文化的意義、對西方文明的貢獻和對猶太民族本身價值,在此就不再重複。
必須看到,《聖經》在猶太人的心目中雖然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但它根本起著一種文化淵源的作用,更生動而完整地記錄了猶太人生活方式、更豐富而全面地集中了猶太民族智慧、更具體而直接地影響著猶太人生活的是另一本書:《塔木德》。從前面兩章中我們所引用的材料,大家一定已經有所感覺。因此,在本章中,我們「偷樑換柱」,把「那本書」換成「這本書」,一則便於從另一層面發掘猶太智慧,二則擴大讀者對猶太典籍和猶太文化史的了解。畢竟,一般人了解甚或熟讀《聖經》的多,而知道《塔木德》的少。
所謂「書的民族」的第二層意思,指的是猶太民族對書(由特指的那本書而延及其他一切書)及書中所蘊藏的知識,還有對讀書過程的嗜好。書的民族是思考的民族、求知的民族、教育的民族、知識的民族、神學的民族,也是講究科學的民族。
人們所認為的決定二十世紀人類思想的三位重量級人士―—物理宇宙的愛因斯坦、人類社會學的馬克思、精神分析學的弗洛伊德,竟都是猶太裔人士,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竟有十五%是猶太人,都令人信服地證明這個民族在「書」的領域中,確有卓越不凡的智慧。
在本章中,我們就以猶太人這一本「書」的特徵為中心,對其相關智慧稍作開掘。
律法的民族 守法的智慧
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出現於公元前三十世紀,是美尼斯王國統一埃及時頒布的。遠古律法中著名的《烏爾納姆法典》(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和《漢穆拉比法典》(公元前十八世紀)都不是猶太人的作品。然而,「律法的民族」這頂桂冠卻不偏不倚地戴在猶太人的頭上。這並不奇怪。
猶太人是一個很早就自覺、系統地從事律法的建設與完善的民族。公元前十三世紀前後的「摩西十誡」為猶太民族打下律法體係的樁基:「巴比倫之囚」時期或其後,《聖經》、尤其是其中的「摩西五經」,為猶太民族的律法體系構築起主幹框架。據偉大的猶太學者邁蒙尼德拉比的權威統計,《聖經》中共包含了613條具體誡命,其中368條是「不准做的」,245條是「必須做的」。在大流散的歷程中,有關《托拉》中的戒律之注釋、實施細則以及其他規定、法典的大量產生,使得猶太人的國家尚未作為一種純粹的幻想在人們頭腦中浮現之前,猶太民族的法律實體已經完成,而其中從法哲學到具體細則,都不乏人類法律史上開拓性的創設。
而且,正因為政治實體的闕如,法律實體在猶太人的生活中發揮著現代之前在其他任何一個民族中都見所未見的作用。
《托拉》成為民族的樊籬,律法成為連結民族的紐帶:猶太人首先不是一個由「血緣」、「地緣」,而是由「上帝的律法」結合成的民族。
以民族在人類法律建設中的這眾多貢獻,以律法在民族生存中的這樣一種地位,以民族成員的這樣一種法律素質,這個民族不能稱之為「律法的民族」的話,還有什麼樣的民族能以此相稱?
不過,猶太民族在律法方面如此繁多而廣泛的建樹,卻給我們這本小書帶來一個無法克服的大難題。以我們的安排,這裡的篇幅只夠蜻蜓點水似地涉獵一下猶太人極為豐富,甚至過於豐富的律法智慧中的一角。由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鬼使神差,我們選中的也許恰恰是最有違猶太人「本意」(但絕對不會有違他們本性)的守法智慧―—變通法律而遵守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