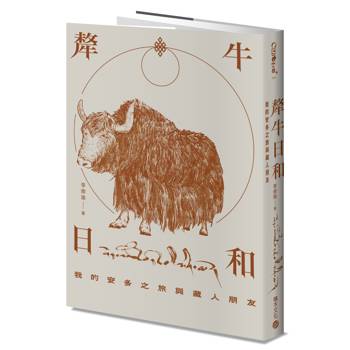序, 或是自介
二○二一年六月,運氣好到不可思議,我在新冠疫情升到三級的同時搬進台南新家。疫情和大雨轟炸中,同樣住在台南的作家朋友黃崇凱建議我,反正在家也是閒著,不如寫一篇關於《馴羊記》的評論。托他的福,文章改了幾次後登上OKAPI 書評。我想,應該是因為那次的鼓勵,讓我覺得可以真的開始寫本關於西藏的書了。
早在我還在日本念書時,某年春假回台灣參加西藏抗暴遊行,同行朋友就建議我可以把自己的田野紀錄寫下來。雖然聽了覺得心動,但說到執行,我一直是個懶惰的人。每次打開電腦和田野筆記,都是打了幾個字之後就卡住放棄。當時只有日文寫作的需求,覺得自己沒辦法切換用中文寫東西。
我會踏入西藏研究的世界,是因為一連串的巧合。剛成年的時候,興趣是騎機車旅行和環島,去過一些部落,開始對台灣原住民產生興趣。接著加入山服隊,又重考進東華大學民族文化系,但都在中途放棄。當完兵到日本學日語,意外學得不錯,好像發現了自己的天賦。不過後來才知道,我人生中的外語技能,全都點在日語上了。總之那時候因為日語不錯,決定留在日本讀大學。想到之前半途而廢的民族文化研究,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人類學。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的當下,我正在神戶的租屋處和日語學校朋友打電動。我們都考上大學,即將在下個月各奔東西,因此不想放過任何可以一起鬼混的時間。我們玩得太投入,甚至不知道有地震,直到傍晚去買晚餐,在車站前拿到報紙的號外刊,才知道出大事了。
那段時間日本全國籠罩在不安的空氣中,各大學都在討論要不要如期開學,或是思考是否要在不適合慶祝的時節舉行開學典禮,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展開了大學生活。大學位於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畔,而我為了方便上學,選擇住在學校旁的農村裡,租屋是一間古老大宅的倉庫。明明就是老倉庫,卻起了個有點微妙的名字:藏部House。藏在日文是倉庫的意思,部只是為了表現b的發音,用漢字轉寫Club 的諧音梗。回想起來,學校在湖邊和住進有「藏」字為名的物件,真是個有趣的偶然。
我就讀的科系可說是文學院加社科院的綜合拼盤。日本史、東亞考古學、現代韓國論、現代中國論、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都可以在大一大二修課,然後選擇一門專業,跟著教授寫畢業論文。我在入學前就看過教授名單,知道有不少人類學的教授,想說可以回台灣做田野調查,寫一篇原住民相關的論文,搞不好還能以田野為藉口回台灣長住一段時間,節省些留學開銷。
開學第一周,學校幫留學生辦了一場歡迎會,讓全校的留學生來白吃白喝,也讓對外國人有興趣的日本學生可以一起同樂,認識彼此。剛從日語學校畢業的我,早就習慣滿滿外國人的場合,況且當時不管到哪個學校,中國留學生都占大多數,對我這個在日本不太想講中文的人來說有點煩。畢竟,他們一聽到你從台灣來,馬上就切換成普通話,還要強迫推銷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觀念。
歡迎會上,我和一個大鬍子教授對到眼,於是開始聊天。他的名字叫棚瀨慈郎,是系上其中一位文化人類學教授,我問棚瀨教授研究的田野是哪裡,他回答:西藏。
「天啊!西藏!好酷!但西藏有什麼啊?」我心想,開始問他關於西藏的問題,棚瀨教授說歡迎會有些無聊,不然換個地方聊吧。我表示同感,教授問我住在哪,我回答學校後面村子的時候,他說那麼巧,他也住那,不如去他家吧,於是我們就去他家吃飯聊天。那天的話題其實大多圍繞在台灣,原因是教授最近才剛去台灣旅遊。我的人生和西藏連上線,也許該回溯到那個瞬間。
因為認識了棚瀨教授,我在大一就選修原本是高年級選修課的基礎藏語和印度西藏文化論。稍微知道西藏和中國的複雜關係後,我在大二選了在讀賣新聞當過記者的荒井利明教授開的﹁現代中國概論﹂課程,進而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
消化中國議題,對我而言不只是學習新知,也是重新建構自己的認同和史觀。從留學日本開始,我被強迫面對「台灣人是什麼」這一個問題。二○○九年我一到日本,就在辦理居留時,看到自己居留證的國籍欄位被寫上「台灣省.中國」。當下我試著和帶我去辦證件的日語老師抗議,但這是個無法更改的政治現實。在日語學校的下課時間,中國學生會試著挑釁,笑著問我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聽說其他台灣同學會因此和他們吵起來,但我選擇和平,跟著他們一起笑,回答:「你們說是就是吧。」
這些心裡的複雜情感就這樣被我帶進大學。三一一震災之後,因為台灣人的熱情捐款,意外地改變了日台關係。日本人﹁忽然發現﹂台灣人和中國人不一樣,我們的證件在短短一年,就從中國台灣省變成台灣。不過,我還是得面對從小接受的國編館中國教育和心中那塊中華民國虛構領土。出身自外省家庭也讓我對許多事情感到困惑。家中長輩一直很討厭,提到時總是不忘損幾句的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人口中是完全不同的樣貌。我進大學後,學到的所有東西都衝擊著體內的史觀。
我和棚瀨慈郎教授熟稔以後,發現我們的興趣喜好非常相似,他便開始建議我去西藏看看。正巧,在我入學的同年,學校來了幾個藏人留學生,他們從青海省的大學日文系畢業,被日本人老師介紹來我們學校,由棚瀨教授照顧。和他們喝酒吃飯交流之餘,也聽他們說了很多自身經歷,讓我對西藏產生更多興趣。二○一二年某天,棚瀨教授問我暑假要不要一起去青海,藏人留學生D要回老家,可以接待我們。我聽了非常開心,覺得不能錯過這次機會。同時,教授也建議我去中國其他地方看看,於是我買了從大阪到上海的船票,決定先前往上海和北京,接著再去西寧市和教授他們會合。
那次的旅行讓我徹底地迷上了西藏和中國,回日本後更認真地閱讀相關知識。也是在那時,棚瀨教授說因為和青海的大學簽了交流協定,我們學校的學生也可以去當地交換,叫我考慮看看。青海省西寧市對一個不會中文的日本學生來說可能是個難關,但如果是對想要探索西藏文化又精通華語的學生來說,應該是天國般的地方。我猶豫一下,便決定不要放棄這個機會,而我也成為從本校唯一前往青海的交換學生……
半年的青海交換學生生活,除了每天的藏語課以外,我認識了許多藏人,也在課餘時間去了不少地方。其中,因緣際會認識的同校藏學系學生塔巴,曾邀我去他的老家T村玩,雖然只有短短幾天,但我也萌生了再去的念頭。於是,我在大四要寫論文時,選擇把田野從台灣原住民換成青海的T村,同時也決定要升學進入研究所,繼續探索西藏。
那幾年的夏天不是在出田野就是在旅行,但都離不開西藏。進到博士課程後,我的心情載浮載沉,覺得自己並不喜歡,又或者也無法產出論文,但對西藏的愛沒有絲毫減少。回台灣工作一段時間,心中還是想著要進藏,於是又復學回到日本湖畔的校園,想著跳島去西藏。當時,甚至有動過去西寧做個小生意當據點,以便留在那邊的念頭。
天不從人願,我在二○一九年最後一次去青海時,在當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迫空氣,猶豫再三,決定暫緩田野計畫,先回台灣觀望和尋找替代方案。隔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世界封閉,我和當地的連結剩下偶爾和藏人朋友們傳傳訊息和視訊通話,直到現在。
被問到為什麼想要寫西藏時,我常常陷入沉思,如果不想寫研究論文,市面上的西藏出版物已經夠多了,西藏不需要再被我消費一次。但在台灣看到的西藏論述,我又大多無法全部買單。西藏被夾在中國國族和西方人權兩種大敘事之下,被塑造成兩種極端的形象—從封建被解放的中國少數民族和被中華帝國壓迫的苦難民族。但我在當地生活實際感受到的,是和這兩種形象離得遙遠,有種微妙親近感的空氣。
我喜歡的人類學作家阿潑,在幫鄧湘漪之《流亡日日》寫的書評中,提到她在中國遇見歌頌黨的藏人時受到的衝擊。在台灣,接觸到的西藏意識形態偏向達賴喇嘛和流亡政權,但在中國境內的數百萬藏人,生活和意識形態非常多樣複雜,絕非鐵板一塊。藏人朋友們在日本可以暢談各種禁忌,但回到中國境內,大家便會語帶保留,對時政的意見批評都變得幽微。我思考了很久在當地感受到的親近感是什麼,最後終於得到自己的答案,似乎就是從白色恐怖到經濟起飛時期,長輩談論政治時依然語帶保留的那種台灣氛圍。
二○一四年夏天,台灣學運爆發不久,我在面試京都大學碩士班時,曾被一位教授問道:「你覺得台灣人的身分會不會影響你做研究時的立場?」當時的我有些不知所措,學運結束後的自己的確民族主義高漲,但我還是回答了我會盡量保持中立之類的場面話。
「我在書中想寫的,是充滿自己立場的東西。」也許是受人類學訓練和自身個性影響,總是不想明確表達立場和突顯自己,所以到可以說出這句話為止,我花了很多時間掙扎和反省。
我對西藏的認知,是建構自台灣的生命經驗、日本留學和青海生活的總和。旅行、留學和田野,是我認識西藏的三種方式,所以我將文章分成這三個部分。我在二○一三年九月到隔年一月在西寧市的青海民族大學交換學生,扣掉二○一八年回台灣工作不算,二○一二年到二○一九年的每年夏天,我都在西藏各地旅行和做田野調查。二○一四年八月第一次到T村,二○一六年的五月和六月,為了碩士論文再去T村進行了較長的田野調查。
我試著描寫自己熟悉的一些事物,建構一個不那麼沉重的西藏。雖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西藏終究無法完全從西方和共產中國的兩種大敘事脫離,但我希望透過書寫,讓大家知道更日常的一些面向,因此我選了旅行點滴、最親密的當地人和熟悉的地方當作關鍵字。數年的藏地遊歷中,和師匠的對話以及所見所聞,成為對比田野的材料,對我而言是相當貴重的經驗。
文章中出現的藏人,以英文代號命名的人是我在日本認識的,表示對方有留學經驗;用中文出現的,是我在藏區認識的藏人。當然,為了保護當事人,這些名字都是假名,以藏人常見的名字拼貼出現。至於地名,除了村莊名稱我以代號稱呼外,都使用真實名稱,省略的部分,則是我覺得有些敏感不想直說,但我想在網路時代也不難查到的東西。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進,我發現自己的書寫有其時效性。二○一二年我第一次進藏,正逢習近平上任,荒井老師和許多學者都期待習近平和他父親一樣是個改革派,但結果是十幾年來政治環境不斷緊縮,我感受到的周圍氣氛也趨向負面緊張。二○一九年最後一次的西藏經驗,更是讓我感到沉重苦悶,T村家裡的共產黨員爸爸首度鬆口,小聲批評了黨的領導人。也是那個瞬間,讓我聯想到台灣和西藏的相似—全民拚經濟,但政治歸政治,×× 歸×× 的氛圍。讀懂空氣,大概是我在日本學會最有用的技能。如果讀者能從我的文字中嗅到一些西藏的氣味,那就是我最大的榮幸吧。
二○二一年六月,運氣好到不可思議,我在新冠疫情升到三級的同時搬進台南新家。疫情和大雨轟炸中,同樣住在台南的作家朋友黃崇凱建議我,反正在家也是閒著,不如寫一篇關於《馴羊記》的評論。托他的福,文章改了幾次後登上OKAPI 書評。我想,應該是因為那次的鼓勵,讓我覺得可以真的開始寫本關於西藏的書了。
早在我還在日本念書時,某年春假回台灣參加西藏抗暴遊行,同行朋友就建議我可以把自己的田野紀錄寫下來。雖然聽了覺得心動,但說到執行,我一直是個懶惰的人。每次打開電腦和田野筆記,都是打了幾個字之後就卡住放棄。當時只有日文寫作的需求,覺得自己沒辦法切換用中文寫東西。
我會踏入西藏研究的世界,是因為一連串的巧合。剛成年的時候,興趣是騎機車旅行和環島,去過一些部落,開始對台灣原住民產生興趣。接著加入山服隊,又重考進東華大學民族文化系,但都在中途放棄。當完兵到日本學日語,意外學得不錯,好像發現了自己的天賦。不過後來才知道,我人生中的外語技能,全都點在日語上了。總之那時候因為日語不錯,決定留在日本讀大學。想到之前半途而廢的民族文化研究,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人類學。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日本東北發生大地震的當下,我正在神戶的租屋處和日語學校朋友打電動。我們都考上大學,即將在下個月各奔東西,因此不想放過任何可以一起鬼混的時間。我們玩得太投入,甚至不知道有地震,直到傍晚去買晚餐,在車站前拿到報紙的號外刊,才知道出大事了。
那段時間日本全國籠罩在不安的空氣中,各大學都在討論要不要如期開學,或是思考是否要在不適合慶祝的時節舉行開學典禮,我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展開了大學生活。大學位於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畔,而我為了方便上學,選擇住在學校旁的農村裡,租屋是一間古老大宅的倉庫。明明就是老倉庫,卻起了個有點微妙的名字:藏部House。藏在日文是倉庫的意思,部只是為了表現b的發音,用漢字轉寫Club 的諧音梗。回想起來,學校在湖邊和住進有「藏」字為名的物件,真是個有趣的偶然。
我就讀的科系可說是文學院加社科院的綜合拼盤。日本史、東亞考古學、現代韓國論、現代中國論、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等,都可以在大一大二修課,然後選擇一門專業,跟著教授寫畢業論文。我在入學前就看過教授名單,知道有不少人類學的教授,想說可以回台灣做田野調查,寫一篇原住民相關的論文,搞不好還能以田野為藉口回台灣長住一段時間,節省些留學開銷。
開學第一周,學校幫留學生辦了一場歡迎會,讓全校的留學生來白吃白喝,也讓對外國人有興趣的日本學生可以一起同樂,認識彼此。剛從日語學校畢業的我,早就習慣滿滿外國人的場合,況且當時不管到哪個學校,中國留學生都占大多數,對我這個在日本不太想講中文的人來說有點煩。畢竟,他們一聽到你從台灣來,馬上就切換成普通話,還要強迫推銷大家都是中國人的觀念。
歡迎會上,我和一個大鬍子教授對到眼,於是開始聊天。他的名字叫棚瀨慈郎,是系上其中一位文化人類學教授,我問棚瀨教授研究的田野是哪裡,他回答:西藏。
「天啊!西藏!好酷!但西藏有什麼啊?」我心想,開始問他關於西藏的問題,棚瀨教授說歡迎會有些無聊,不然換個地方聊吧。我表示同感,教授問我住在哪,我回答學校後面村子的時候,他說那麼巧,他也住那,不如去他家吧,於是我們就去他家吃飯聊天。那天的話題其實大多圍繞在台灣,原因是教授最近才剛去台灣旅遊。我的人生和西藏連上線,也許該回溯到那個瞬間。
因為認識了棚瀨教授,我在大一就選修原本是高年級選修課的基礎藏語和印度西藏文化論。稍微知道西藏和中國的複雜關係後,我在大二選了在讀賣新聞當過記者的荒井利明教授開的﹁現代中國概論﹂課程,進而開始對中國產生興趣。
消化中國議題,對我而言不只是學習新知,也是重新建構自己的認同和史觀。從留學日本開始,我被強迫面對「台灣人是什麼」這一個問題。二○○九年我一到日本,就在辦理居留時,看到自己居留證的國籍欄位被寫上「台灣省.中國」。當下我試著和帶我去辦證件的日語老師抗議,但這是個無法更改的政治現實。在日語學校的下課時間,中國學生會試著挑釁,笑著問我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聽說其他台灣同學會因此和他們吵起來,但我選擇和平,跟著他們一起笑,回答:「你們說是就是吧。」
這些心裡的複雜情感就這樣被我帶進大學。三一一震災之後,因為台灣人的熱情捐款,意外地改變了日台關係。日本人﹁忽然發現﹂台灣人和中國人不一樣,我們的證件在短短一年,就從中國台灣省變成台灣。不過,我還是得面對從小接受的國編館中國教育和心中那塊中華民國虛構領土。出身自外省家庭也讓我對許多事情感到困惑。家中長輩一直很討厭,提到時總是不忘損幾句的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本人口中是完全不同的樣貌。我進大學後,學到的所有東西都衝擊著體內的史觀。
我和棚瀨慈郎教授熟稔以後,發現我們的興趣喜好非常相似,他便開始建議我去西藏看看。正巧,在我入學的同年,學校來了幾個藏人留學生,他們從青海省的大學日文系畢業,被日本人老師介紹來我們學校,由棚瀨教授照顧。和他們喝酒吃飯交流之餘,也聽他們說了很多自身經歷,讓我對西藏產生更多興趣。二○一二年某天,棚瀨教授問我暑假要不要一起去青海,藏人留學生D要回老家,可以接待我們。我聽了非常開心,覺得不能錯過這次機會。同時,教授也建議我去中國其他地方看看,於是我買了從大阪到上海的船票,決定先前往上海和北京,接著再去西寧市和教授他們會合。
那次的旅行讓我徹底地迷上了西藏和中國,回日本後更認真地閱讀相關知識。也是在那時,棚瀨教授說因為和青海的大學簽了交流協定,我們學校的學生也可以去當地交換,叫我考慮看看。青海省西寧市對一個不會中文的日本學生來說可能是個難關,但如果是對想要探索西藏文化又精通華語的學生來說,應該是天國般的地方。我猶豫一下,便決定不要放棄這個機會,而我也成為從本校唯一前往青海的交換學生……
半年的青海交換學生生活,除了每天的藏語課以外,我認識了許多藏人,也在課餘時間去了不少地方。其中,因緣際會認識的同校藏學系學生塔巴,曾邀我去他的老家T村玩,雖然只有短短幾天,但我也萌生了再去的念頭。於是,我在大四要寫論文時,選擇把田野從台灣原住民換成青海的T村,同時也決定要升學進入研究所,繼續探索西藏。
那幾年的夏天不是在出田野就是在旅行,但都離不開西藏。進到博士課程後,我的心情載浮載沉,覺得自己並不喜歡,又或者也無法產出論文,但對西藏的愛沒有絲毫減少。回台灣工作一段時間,心中還是想著要進藏,於是又復學回到日本湖畔的校園,想著跳島去西藏。當時,甚至有動過去西寧做個小生意當據點,以便留在那邊的念頭。
天不從人願,我在二○一九年最後一次去青海時,在當地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迫空氣,猶豫再三,決定暫緩田野計畫,先回台灣觀望和尋找替代方案。隔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世界封閉,我和當地的連結剩下偶爾和藏人朋友們傳傳訊息和視訊通話,直到現在。
被問到為什麼想要寫西藏時,我常常陷入沉思,如果不想寫研究論文,市面上的西藏出版物已經夠多了,西藏不需要再被我消費一次。但在台灣看到的西藏論述,我又大多無法全部買單。西藏被夾在中國國族和西方人權兩種大敘事之下,被塑造成兩種極端的形象—從封建被解放的中國少數民族和被中華帝國壓迫的苦難民族。但我在當地生活實際感受到的,是和這兩種形象離得遙遠,有種微妙親近感的空氣。
我喜歡的人類學作家阿潑,在幫鄧湘漪之《流亡日日》寫的書評中,提到她在中國遇見歌頌黨的藏人時受到的衝擊。在台灣,接觸到的西藏意識形態偏向達賴喇嘛和流亡政權,但在中國境內的數百萬藏人,生活和意識形態非常多樣複雜,絕非鐵板一塊。藏人朋友們在日本可以暢談各種禁忌,但回到中國境內,大家便會語帶保留,對時政的意見批評都變得幽微。我思考了很久在當地感受到的親近感是什麼,最後終於得到自己的答案,似乎就是從白色恐怖到經濟起飛時期,長輩談論政治時依然語帶保留的那種台灣氛圍。
二○一四年夏天,台灣學運爆發不久,我在面試京都大學碩士班時,曾被一位教授問道:「你覺得台灣人的身分會不會影響你做研究時的立場?」當時的我有些不知所措,學運結束後的自己的確民族主義高漲,但我還是回答了我會盡量保持中立之類的場面話。
「我在書中想寫的,是充滿自己立場的東西。」也許是受人類學訓練和自身個性影響,總是不想明確表達立場和突顯自己,所以到可以說出這句話為止,我花了很多時間掙扎和反省。
我對西藏的認知,是建構自台灣的生命經驗、日本留學和青海生活的總和。旅行、留學和田野,是我認識西藏的三種方式,所以我將文章分成這三個部分。我在二○一三年九月到隔年一月在西寧市的青海民族大學交換學生,扣掉二○一八年回台灣工作不算,二○一二年到二○一九年的每年夏天,我都在西藏各地旅行和做田野調查。二○一四年八月第一次到T村,二○一六年的五月和六月,為了碩士論文再去T村進行了較長的田野調查。
我試著描寫自己熟悉的一些事物,建構一個不那麼沉重的西藏。雖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西藏終究無法完全從西方和共產中國的兩種大敘事脫離,但我希望透過書寫,讓大家知道更日常的一些面向,因此我選了旅行點滴、最親密的當地人和熟悉的地方當作關鍵字。數年的藏地遊歷中,和師匠的對話以及所見所聞,成為對比田野的材料,對我而言是相當貴重的經驗。
文章中出現的藏人,以英文代號命名的人是我在日本認識的,表示對方有留學經驗;用中文出現的,是我在藏區認識的藏人。當然,為了保護當事人,這些名字都是假名,以藏人常見的名字拼貼出現。至於地名,除了村莊名稱我以代號稱呼外,都使用真實名稱,省略的部分,則是我覺得有些敏感不想直說,但我想在網路時代也不難查到的東西。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進,我發現自己的書寫有其時效性。二○一二年我第一次進藏,正逢習近平上任,荒井老師和許多學者都期待習近平和他父親一樣是個改革派,但結果是十幾年來政治環境不斷緊縮,我感受到的周圍氣氛也趨向負面緊張。二○一九年最後一次的西藏經驗,更是讓我感到沉重苦悶,T村家裡的共產黨員爸爸首度鬆口,小聲批評了黨的領導人。也是那個瞬間,讓我聯想到台灣和西藏的相似—全民拚經濟,但政治歸政治,×× 歸×× 的氛圍。讀懂空氣,大概是我在日本學會最有用的技能。如果讀者能從我的文字中嗅到一些西藏的氣味,那就是我最大的榮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