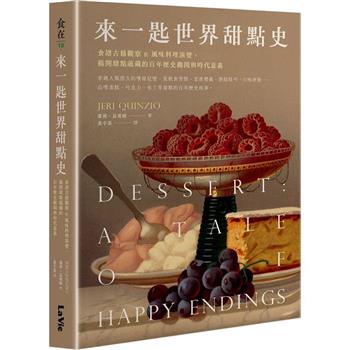第一章
人類古老的飲食習慣
為小康菲糖喝采
當時舉行婚禮和嘉年華會,也像我們今日拋灑五彩碎紙(paper confetti)般,在空中拋撒康菲蜜餞。1891年出版的《華特.史考特爵士日記》(Journal of Sir Walter Scott)中,史考特爵士回憶了一場活動中,「讚美的話語就像義大利嘉年華會的糖豆一樣,四處飛揚。」在當時,製作大量康菲蜜餞是十分昂貴的,因此有些製造商便會偷工減料,將杏仁或是種子先裹上麵粉,再於糖漿中攪拌,這代表他們只須使用少量的糖,就能快速地裹上更厚的糖衣。如果少許麵粉能加速製程、降低成本,那麼更多麵粉豈不是更妙?這種方法使得康菲蜜餞的製造變得更便宜、快速,而且成品一樣可食用,不過的確沒有原來精緻的版本那麼可口了。另一個解決辦法,則是製作不可食用,僅用來拋灑的「替代版康菲蜜餞」(ersatz comts)。這些假康菲蜜餞的原料為灰泥(plaster),製作成糖衣杏仁的形狀與尺寸後成籃販賣,在節慶中投撒在朋友、愛人與嘉年華會遊行時的陌生人身上。扔康菲蜜餞也被視為一種調情手段,以求吸引對方注意。
德國大文豪歌德在年近四十時,花了二年在義大利各地旅遊,並在1787-1788 年於《義大利之旅》(Italian Journey)一書中,描寫了他對該國度的印象與習俗。歌德稱羅馬嘉年華會為「一場小型戰爭,大部分的時候只是在嬉鬧,但時不時卻過於認眞。」他描述到戴著面具的與會者,他們或行走、或乘坐四輪馬車,擠滿大街小巷,人們從陽台觀望盛會,小販扛著裝滿了灰泥小丸的籃子,在人叢中穿梭販賣給穿著戲服狂歡的群眾。狂歡者購買成磅的彈丸武裝自己,將彈丸裝在數個袋中或是綁在手帕裡。有些女子則會將自己的彈丸裝在漂亮且鑲金或銀的籃子中。
根據歌德的說法,最令人難以抗拒的標的物,便是修道院長(abbés),一被灰泥糖碎擊中,他們黑色的大衣便立刻佈滿灰白斑點。但不僅是他們,無人能夠免於戰火波及,男人們會向漂亮的女孩投擲糖碎引起她們的注意,女人則鬼鬼祟祟地朝俊美的年輕男子丟糖碎。花不上多長的時間,馬車和大衣、帽子和街道,似乎都被覆上了一層白雪般的彈丸。除了偶有樂極生悲的小插曲,這場盛會可說是極為歡樂。歌德寫道,戴著假面的與會者一不小心,便太過用力地用糖碎砸中了心儀的女士,這樣的情形不時發生。此時,女子的朋友們便憤而回敬他。只有警察以及懸掛在數個角落駭人的絞刑索(corde),能預防這些衝突升溫至危險的程度。大部分的時候,慶典愉悅嬉鬧,灰泥的塵土也很快便淸掃乾淨,一切相安無事。很快地,嘉年華會的與會者們學會穿戴防塵衣,保護他們精心打扮的裝束不被灰泥塵土弄髒。他們甚至還會使用鋼線面罩來預防雙眼受傷,因為灰泥彈丸要是命中眼睛,可是會釀下嚴重損傷的。(有些嘉年華會的參與者開始使用有如迷你煤鏟般的勺子來投擲彈丸,而非親手投擲,因此防禦措施也逐漸成了必要策略)
到了1844 -1845年,根據英國大文豪狄更斯親身觀察,這種小型戰爭急劇升溫擴大。儘管狄更斯對於大夥兒的遊戲精神十分欽佩—大部分的嘉年華與會者都算是和氣,他仍然戴著鋼線面具以自保。他在《義大利風光》(Pictures from Italy)中寫道,就連四輪馬車也披戴著防塵套:「所有的四輪馬車都是露天的,並使用白棉布或是印花棉襯布小心地覆蓋,來避免精美的裝飾受到連續投擲攻擊。」狄更斯如是描寫了模擬戰事:
「在一地僵持甚久之後,四輪馬車會開始與其他四輪馬車,或是位於高度較低之窗口的人們,進行策略性的交戰。而位在較高處陽台或是窗口的觀眾,則會加入這場爭戰,並且倒下成袋的糖碎,如雲朵般從天而降,攻擊雙方,一瞬間,就將下方的人們染得跟磨坊工人一樣雪白。」
十九世紀時,不論是為了取代具有危險性的灰泥糖碎,還是僅作為創新產品發明,一項同名商品就此誕生。1894 年由倫敦的文具公司J. & E. 貝拉(J. & E. Bella)委託製作,亨利.德.土魯斯- 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在廣告海報上描繪了一個微笑著的快樂年輕女子,沐浴在繽紛且無害的紙製糖碎之下。和灰泥糖碎相比起來,可說是一大進步。這些碎紙任人愛怎麼拋就怎麼拋。它們價格便宜、充滿節慶喜氣,而且十分輕盈,被砸中時的感觸根本不及糖碎的一丁點。五彩碎紙不會在衣物上留下斑污,因此再也無需配戴面罩和防塵衣了。這也難怪,產品推出初始,新聞報導便表露極度的興奮之情。1894年的3月26日,紐約時報報導,在巴黎的大道上,鋪上了一條新的地毯:「五彩碎紙創造了觸感柔軟、外觀別緻,新穎而極致品味的天鵝絨毯。」五彩碎紙成了遊行、婚禮和嘉年華會的霸主。它取代了灰泥糖碎,並且讓康菲蜜餞、糖碎和糖衣甜食不再被當作彈藥,重返它們的甜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