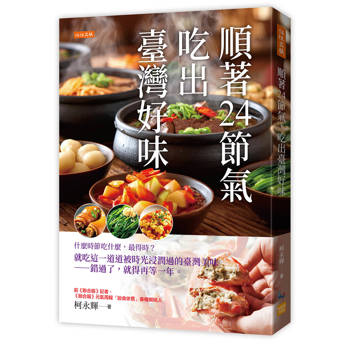潤餅,你家放高麗菜還是豆芽菜
清明是氣象節氣,也是民俗節日,傳統上,漢人多在這時掃墓、祭祖。
唐代詩人杜牧的詩句「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加上自幼隨長輩到墳地除草、硩(teh,壓)墓紙時常伴的細雨交織,形塑出我對清明的最初印象:淒風苦雨、草木含悲,甚至帶點鬼影幢幢的神祕氛圍。
唯一讓我期待的,是祭祖後可以吃「潤餅𩛩(kauh)」,藉此安撫對先人與未知死後世界感到恐懼的幼小心靈。
吃潤餅,堪稱是我人生最早的自助餐體驗。餐桌上擺滿一盤盤豐盛食材,有燙或炒過的豆芽菜、紅蘿蔔絲、高麗菜碎、豆乾絲、蛋絲、芹菜、香菜、肉絲等,多是冷吃且素多於葷。
食用時,先攤開薄可透光卻又極富彈性的潤餅皮,輕輕灑些花生糖粉,再依個人喜好夾取各式菜色後包成一捲,便能大口咬下,那種甜鹹交織、脆軟並陳的豐滿口感,瞬間讓人充分感覺到什麼叫做扎實的存在感,彷彿將一整個春天濃縮其中。
「何物清明祭掃紛,盤堆薄薄餅啖芬。獻餘未許齊人乞,捲起佳肴遺細君。」這首詩是臺灣詩人林逢春(1868~1936年),在1933年發表的〈臺灣節序故事雜詠.清明之薄餅〉,以《孟子.離婁下》記述一名齊國人在墳場乞討祭品食用,回家卻向妻妾謊稱是與富貴人家用餐的「齊人乞墦」典故,凸顯自己要把祭祖佳餚親手捲入薄餅,悉心留給愛妻品嘗,讓人讀來心頭一暖。
潤餅的「潤」字來源,向來眾說紛紜。飲食作家陳淑華認為,潤字是由「年」轉化而來,一年好似一輪,於是年餅轉成輪餅,輪音又轉成潤,吃潤餅就是吃年餅,寓意辭舊迎新,因此有些臺灣家庭也會在尾牙(按:農曆12月26日)或過年吃潤餅。另外也有人認為潤餅皮薄而軟,從臺語軟(nńg)的音韻轉成潤餅。我則想,潤餅皮柔軟但不易破裂,臺語形容為韌(jūn),是否因諧音而成了潤?
但無論語源為何,「潤」字似乎都為這道食物,增添了幾分溫潤而堅韌的生命力。
潤餅可追溯自漢代吃春盤的習俗,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記載「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人們在春天品嘗應時蔬菜,期盼一年豐收,隨著時間演變與方便取食,春盤中的食材逐漸包進餅皮,演變為今日的潤餅。
美食作家陳靜宜曾考證潤餅餡料,發現潤餅堪稱「沒有文字的族譜」:如果你家的潤餅會放燉爛的高麗菜,可能與廈門的飲食習慣有關;放大量豆芽菜,或與福州有淵源;泉州人偏好紅蘿蔔絲;皇帝豆是臺南潤餅的印記;金門或廈門人則會加入碎貢糖。這一捲,捲起了家族、文化與土地的氣息。
空心菜,蘊藏對「好兄弟」的體貼
空心菜在臺灣全年可見,而以5至10月所產最脆嫩,可依菜葉大小與型態區分品種。
竹葉種的葉片狹長如竹葉,莖細長,口感細緻,是市場主流,多在旱地栽種,雲林西螺、莿桐及桃園八德為主要產區;大葉種的葉片寬大偏心型,莖呈粗管狀,口感清脆,多在水田、溪邊或池沼種植,俗稱「水蕹菜」,以宜蘭礁溪、南投名間生產者最著名。
我曾在夏日路經名間,買回路邊小農販售自家種植的水蕹菜,看它的塊頭比一般空心菜大,一度讓我懷疑莖葉是否已粗老。但回家用菜刀切斷維管束時,那清脆的涮涮聲,就足以證明它的爽脆。
下廚時若有閒情,不妨抓起整束切過的空心菜,對著陽光欣賞其橫斷面之美,那水靈的青色與中空結構,讓我想起中國作家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其中的主角翠翠在渡口守望無望的愛情,「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空心菜的空,原是最飽滿的懸念。
其實,空心植物如竹、小麥、稻子、蘆葦等,從演化論來看,是相對進化的植物,省卻莖中間的髓部材質,成就管狀支撐,省資源又能加速生長,競爭力更強。空,是進化的留白。
而從烹飪角度來看,空心菜受熱的表面積加大,更快熟,且因其富含鐵質,容易氧化變黑或過熟,適合大火快炒,因此熱炒店裡常有沙茶牛肉炒空心菜等菜色。我女兒不吃牛,卻獨愛腐乳炒(拌)空心菜,與香港美食家蔡瀾所好不謀而合。
「籬邊甕菜剪還生,勞少功多省力耕。滋味休嫌真淡泊,吾儒素質本來清。」日治時期提倡以臺語作為兒童修身教材的教師劉克明(1884~1967年),在〈寄園雜作〉其四這首詩裡,以空心菜的淡泊滋味自況,展現儒者不慕虛華的人格。我相信,他也偏愛蕹菜湯的清白之美。
除了日常餐桌,蕹菜湯還會出現在臺灣中元普渡的祭品之列,理由各家說法不同,但都蘊含著對好兄弟的體貼與人情味。
其一是空心菜比較廉價,如果較弱勢的好兄弟沒有搶到美食,可以吃空心菜配飯填飽肚子,此說還衍生出一句閩南諺語「做鬼,也搶無蕹菜湯」,形容人動作慢或懶惰,就算當了鬼,也搶不到最便宜的普渡祭品。
另一個說法是相傳人過世後成為鬼魂,若沒有經過放焰口等儀式,所有食物入口皆火,而蕹菜湯性寒,能消解這團火焰,讓好兄弟得以進食。
此外,中元普渡的蕹菜湯(蕹菜水)並非真正煮熟成湯,只是將新鮮或稍微川燙的空心菜放入水盆,象徵人鬼關係「半生不熟」,主人待客「有誠無心」,提醒好兄弟吃完後早些離開,不要留戀於此。
紅蟳米糕,與螃蟹的初識
臺灣四面環海,食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蟳和梭子蟹。晚清嘉義詩人賴惠川(1887~1962年)的〈蟳〉詩云:「螃蟹相形十倍差,巨螯雙舉海之涯。臺西當港仁盈殼,不落尋常百姓家。」點出了海蟳的體型較大,海港現捕之蟳,蟹膏、蟹黃飽滿,是昂貴食材,非一般家庭能輕易負擔。
蟳是青蟹,懷卵母蟹稱紅蟳,公的為菜蟳,未受精的母蟹則稱處女蟳。我與螃蟹初識,是與家人一同出席婚宴,宴席上紅蟳米糕的油亮蟹膏,是少年記憶裡最早的奢華。紅亮的外觀喜氣洋洋,或許也是許多人與蟹的初戀。
梭子蟹以蟹殼如梭兩端尖得名,包括三點蟹、花蟹、石蟳等,因新北萬里的海蟹捕獲量占全臺最大宗,新北市近年來便把臺灣西北漁場的這三種螃蟹,以「萬里蟹」品牌行銷。其中,又以三點蟹產量最大,蟹殼薄軟,肉質細嫩清雅;花蟹個頭大,肉多鮮甜,是愛吃肥厚蟹腳的饕客首選;石蟳個頭小,蟹肉絲絲分明,肉質彈牙。
「蟹宜獨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鹽湯煮熟,自剝自食為妙。」清代才子袁枚在《隨園食單》的主張,獲得食林讚揚,只是鹽水煮蟹恐讓螃蟹的部分鮮味、甜味物質溶解到水裡,反而降低風味;而李漁在《閒情偶寄》裡主張「蒸而熟之,貯以冰盤,列之几上……則氣與味絲毫不漏」。水煮或清蒸兩派各有所好,但最重要的是掌握火候,否則風味盡失。
最雅致的蟹饌,莫過於宋代林洪《山家清供》裡的「蟹釀橙」:把新鮮橙子切去頂蓋,挖出瓤肉,再把剔好的蟹肉、蟹膏塞入,灑入酒、醋後蓋上頂皮隔水加熱,橙皮加熱釋放出芳香精油,讓蟹肉吸足橙香,又鮮又香,且用小勺舀著吃,姿態優雅,充滿「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興」的秋日情懷。
蟹粥、蟹麵,可品原味;嗆蟹、避風塘炒蟹、咖哩蟹等濃重口味,則更貼近螃蟹橫行霸道的張揚性格,適合凡夫俗子放鬆吃喝的酒酣耳熱,「趁少年,擱乾一杯,趁咧馬西(按:臺語中較常使用重複的「馬西馬西」[máse-má-se],形容人酒醉不清醒的樣子)予我將你閣攬一下!」友人們神采風揚喊起酒拳,「螃蟹一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麼大個,眼一擠呀,脖一縮,爬呀爬呀過沙河」,真是「哥倆好呀一對寶」的美好時光。
烏魚、烏金,來自大海的財富
「大雪。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雖然在臺灣,我們難以見到千里冰封、萬里飄雪的景象,但節氣的更迭,仍標誌著冬天已然登堂入室。對漁人而言,這不僅是日子的推進,更是與海中精靈的信約之期。
臺灣節氣諺語「大雪大到」,精準說明了烏魚群順著親潮南下,大量湧進臺灣海峽的時節,宣告著一年一度的烏魚季開啟。晚清嘉義詩人林臥雲詩云:「為避寒潮逐隊來,年年守信不須猜。」烏魚每年在同一時間洄游至此,像是信守著與漁民的古老約定,因此被譽為「信魚」。
臺灣西部的捕烏漁民此時也大舉出動,撈捕這集體行動的魚群,並利用中南部冬天乾燥的特性,將已孕雌魚的卵巢及魚卵,鹽漬日晒製成金黃剔透的烏魚子。這份來自大海豐厚的回報,被暱稱為烏金,是漁民實實在在的「年終獎金」。
臺灣之所以盛產烏魚子,與烏魚的繁殖習性有密切關係。牠們從渤海一帶往南游,準備到臺灣南端的東港與菲律賓一帶產卵,在游抵臺灣西南部時最為肥美,對漁民來說,簡直是自動送上門的財富。
因此早在十七世紀初,閩粵沿海漁民便駕船到臺灣大員一帶(即臺江內海邊)和澎湖捕烏魚,並住上幾個月,直到隔年春天轉南風才返鄉,後來便逐漸有人定居臺灣。有人說,臺灣漢人移民最早就是被烏金吸引而來。
荷蘭人統治臺灣時期,看上這塊龐大利益,開始對漁民徵收什一稅(即繳納所得的十分之一),後來明鄭、清領時代也都跟進。清道光年間來臺為官的劉家謀在〈海音詩〉一百首之十七曾寫下「烏魚歲晚無消息,累得鹽官仰屋嗟」,生動描寫出當烏魚漁汛期一晚,連帶影響到烏魚子的生意,讓賴以課稅的鹽官仰屋興嘆的窘境。
日人治臺後,比較自身的鰆魚子(形色如墨條,稱「唐墨」)與臺灣的烏魚子,發現臺灣醃製方式略有不同。為追求更上乘的風味,日人陸續請來專家教導洗鹽、日晒乾燥等技術。如今,臺灣的烏魚子製作工藝已臻成熟且複雜,歷經取卵、清洗、醃漬、脫鹽、整形、壓製與日晒乾燥等多道程序,每一步都體現了匠人的用心,以及精確掌握海風、日照的變化。
歷經晚清、日治、民國的史學家連橫在《臺灣通史》裡提到烏魚子的食用之道:「食時濡酒,文火烤之,皮起細胞,不可過焦,切為薄片,味極甘香,為臺南之珍饈。」這份吃法和講究,與今無異。
烏魚子主要產於臺灣中南部,然而,從臺中梧棲、彰化鹿港、嘉義東石、臺南到高雄旗津,都聲稱自己產製者最佳。晚清鹿港詩人莊太岳(1880~1938年)的〈鹿江竹枝詞〉就寫過這種瑜亮情結:「烏魚大獲萬三三,典盡釵環為口饞。本港從來魚子好,果然風味勝臺南。」詩中描寫為了品嘗心愛的烏魚子,不惜典當首飾的瘋狂,更反映出「烏魚子是自家好」的心態。
或許,這份偏執與差異,並不在地域,而在於每位師傅對家鄉海風的獨特理解與用心。
清明是氣象節氣,也是民俗節日,傳統上,漢人多在這時掃墓、祭祖。
唐代詩人杜牧的詩句「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加上自幼隨長輩到墳地除草、硩(teh,壓)墓紙時常伴的細雨交織,形塑出我對清明的最初印象:淒風苦雨、草木含悲,甚至帶點鬼影幢幢的神祕氛圍。
唯一讓我期待的,是祭祖後可以吃「潤餅𩛩(kauh)」,藉此安撫對先人與未知死後世界感到恐懼的幼小心靈。
吃潤餅,堪稱是我人生最早的自助餐體驗。餐桌上擺滿一盤盤豐盛食材,有燙或炒過的豆芽菜、紅蘿蔔絲、高麗菜碎、豆乾絲、蛋絲、芹菜、香菜、肉絲等,多是冷吃且素多於葷。
食用時,先攤開薄可透光卻又極富彈性的潤餅皮,輕輕灑些花生糖粉,再依個人喜好夾取各式菜色後包成一捲,便能大口咬下,那種甜鹹交織、脆軟並陳的豐滿口感,瞬間讓人充分感覺到什麼叫做扎實的存在感,彷彿將一整個春天濃縮其中。
「何物清明祭掃紛,盤堆薄薄餅啖芬。獻餘未許齊人乞,捲起佳肴遺細君。」這首詩是臺灣詩人林逢春(1868~1936年),在1933年發表的〈臺灣節序故事雜詠.清明之薄餅〉,以《孟子.離婁下》記述一名齊國人在墳場乞討祭品食用,回家卻向妻妾謊稱是與富貴人家用餐的「齊人乞墦」典故,凸顯自己要把祭祖佳餚親手捲入薄餅,悉心留給愛妻品嘗,讓人讀來心頭一暖。
潤餅的「潤」字來源,向來眾說紛紜。飲食作家陳淑華認為,潤字是由「年」轉化而來,一年好似一輪,於是年餅轉成輪餅,輪音又轉成潤,吃潤餅就是吃年餅,寓意辭舊迎新,因此有些臺灣家庭也會在尾牙(按:農曆12月26日)或過年吃潤餅。另外也有人認為潤餅皮薄而軟,從臺語軟(nńg)的音韻轉成潤餅。我則想,潤餅皮柔軟但不易破裂,臺語形容為韌(jūn),是否因諧音而成了潤?
但無論語源為何,「潤」字似乎都為這道食物,增添了幾分溫潤而堅韌的生命力。
潤餅可追溯自漢代吃春盤的習俗,東漢崔寔《四民月令》記載「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人們在春天品嘗應時蔬菜,期盼一年豐收,隨著時間演變與方便取食,春盤中的食材逐漸包進餅皮,演變為今日的潤餅。
美食作家陳靜宜曾考證潤餅餡料,發現潤餅堪稱「沒有文字的族譜」:如果你家的潤餅會放燉爛的高麗菜,可能與廈門的飲食習慣有關;放大量豆芽菜,或與福州有淵源;泉州人偏好紅蘿蔔絲;皇帝豆是臺南潤餅的印記;金門或廈門人則會加入碎貢糖。這一捲,捲起了家族、文化與土地的氣息。
空心菜,蘊藏對「好兄弟」的體貼
空心菜在臺灣全年可見,而以5至10月所產最脆嫩,可依菜葉大小與型態區分品種。
竹葉種的葉片狹長如竹葉,莖細長,口感細緻,是市場主流,多在旱地栽種,雲林西螺、莿桐及桃園八德為主要產區;大葉種的葉片寬大偏心型,莖呈粗管狀,口感清脆,多在水田、溪邊或池沼種植,俗稱「水蕹菜」,以宜蘭礁溪、南投名間生產者最著名。
我曾在夏日路經名間,買回路邊小農販售自家種植的水蕹菜,看它的塊頭比一般空心菜大,一度讓我懷疑莖葉是否已粗老。但回家用菜刀切斷維管束時,那清脆的涮涮聲,就足以證明它的爽脆。
下廚時若有閒情,不妨抓起整束切過的空心菜,對著陽光欣賞其橫斷面之美,那水靈的青色與中空結構,讓我想起中國作家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其中的主角翠翠在渡口守望無望的愛情,「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空心菜的空,原是最飽滿的懸念。
其實,空心植物如竹、小麥、稻子、蘆葦等,從演化論來看,是相對進化的植物,省卻莖中間的髓部材質,成就管狀支撐,省資源又能加速生長,競爭力更強。空,是進化的留白。
而從烹飪角度來看,空心菜受熱的表面積加大,更快熟,且因其富含鐵質,容易氧化變黑或過熟,適合大火快炒,因此熱炒店裡常有沙茶牛肉炒空心菜等菜色。我女兒不吃牛,卻獨愛腐乳炒(拌)空心菜,與香港美食家蔡瀾所好不謀而合。
「籬邊甕菜剪還生,勞少功多省力耕。滋味休嫌真淡泊,吾儒素質本來清。」日治時期提倡以臺語作為兒童修身教材的教師劉克明(1884~1967年),在〈寄園雜作〉其四這首詩裡,以空心菜的淡泊滋味自況,展現儒者不慕虛華的人格。我相信,他也偏愛蕹菜湯的清白之美。
除了日常餐桌,蕹菜湯還會出現在臺灣中元普渡的祭品之列,理由各家說法不同,但都蘊含著對好兄弟的體貼與人情味。
其一是空心菜比較廉價,如果較弱勢的好兄弟沒有搶到美食,可以吃空心菜配飯填飽肚子,此說還衍生出一句閩南諺語「做鬼,也搶無蕹菜湯」,形容人動作慢或懶惰,就算當了鬼,也搶不到最便宜的普渡祭品。
另一個說法是相傳人過世後成為鬼魂,若沒有經過放焰口等儀式,所有食物入口皆火,而蕹菜湯性寒,能消解這團火焰,讓好兄弟得以進食。
此外,中元普渡的蕹菜湯(蕹菜水)並非真正煮熟成湯,只是將新鮮或稍微川燙的空心菜放入水盆,象徵人鬼關係「半生不熟」,主人待客「有誠無心」,提醒好兄弟吃完後早些離開,不要留戀於此。
紅蟳米糕,與螃蟹的初識
臺灣四面環海,食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蟳和梭子蟹。晚清嘉義詩人賴惠川(1887~1962年)的〈蟳〉詩云:「螃蟹相形十倍差,巨螯雙舉海之涯。臺西當港仁盈殼,不落尋常百姓家。」點出了海蟳的體型較大,海港現捕之蟳,蟹膏、蟹黃飽滿,是昂貴食材,非一般家庭能輕易負擔。
蟳是青蟹,懷卵母蟹稱紅蟳,公的為菜蟳,未受精的母蟹則稱處女蟳。我與螃蟹初識,是與家人一同出席婚宴,宴席上紅蟳米糕的油亮蟹膏,是少年記憶裡最早的奢華。紅亮的外觀喜氣洋洋,或許也是許多人與蟹的初戀。
梭子蟹以蟹殼如梭兩端尖得名,包括三點蟹、花蟹、石蟳等,因新北萬里的海蟹捕獲量占全臺最大宗,新北市近年來便把臺灣西北漁場的這三種螃蟹,以「萬里蟹」品牌行銷。其中,又以三點蟹產量最大,蟹殼薄軟,肉質細嫩清雅;花蟹個頭大,肉多鮮甜,是愛吃肥厚蟹腳的饕客首選;石蟳個頭小,蟹肉絲絲分明,肉質彈牙。
「蟹宜獨食,不宜搭配他物,最好以淡鹽湯煮熟,自剝自食為妙。」清代才子袁枚在《隨園食單》的主張,獲得食林讚揚,只是鹽水煮蟹恐讓螃蟹的部分鮮味、甜味物質溶解到水裡,反而降低風味;而李漁在《閒情偶寄》裡主張「蒸而熟之,貯以冰盤,列之几上……則氣與味絲毫不漏」。水煮或清蒸兩派各有所好,但最重要的是掌握火候,否則風味盡失。
最雅致的蟹饌,莫過於宋代林洪《山家清供》裡的「蟹釀橙」:把新鮮橙子切去頂蓋,挖出瓤肉,再把剔好的蟹肉、蟹膏塞入,灑入酒、醋後蓋上頂皮隔水加熱,橙皮加熱釋放出芳香精油,讓蟹肉吸足橙香,又鮮又香,且用小勺舀著吃,姿態優雅,充滿「有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興」的秋日情懷。
蟹粥、蟹麵,可品原味;嗆蟹、避風塘炒蟹、咖哩蟹等濃重口味,則更貼近螃蟹橫行霸道的張揚性格,適合凡夫俗子放鬆吃喝的酒酣耳熱,「趁少年,擱乾一杯,趁咧馬西(按:臺語中較常使用重複的「馬西馬西」[máse-má-se],形容人酒醉不清醒的樣子)予我將你閣攬一下!」友人們神采風揚喊起酒拳,「螃蟹一呀爪八個,兩頭尖尖這麼大個,眼一擠呀,脖一縮,爬呀爬呀過沙河」,真是「哥倆好呀一對寶」的美好時光。
烏魚、烏金,來自大海的財富
「大雪。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也。」雖然在臺灣,我們難以見到千里冰封、萬里飄雪的景象,但節氣的更迭,仍標誌著冬天已然登堂入室。對漁人而言,這不僅是日子的推進,更是與海中精靈的信約之期。
臺灣節氣諺語「大雪大到」,精準說明了烏魚群順著親潮南下,大量湧進臺灣海峽的時節,宣告著一年一度的烏魚季開啟。晚清嘉義詩人林臥雲詩云:「為避寒潮逐隊來,年年守信不須猜。」烏魚每年在同一時間洄游至此,像是信守著與漁民的古老約定,因此被譽為「信魚」。
臺灣西部的捕烏漁民此時也大舉出動,撈捕這集體行動的魚群,並利用中南部冬天乾燥的特性,將已孕雌魚的卵巢及魚卵,鹽漬日晒製成金黃剔透的烏魚子。這份來自大海豐厚的回報,被暱稱為烏金,是漁民實實在在的「年終獎金」。
臺灣之所以盛產烏魚子,與烏魚的繁殖習性有密切關係。牠們從渤海一帶往南游,準備到臺灣南端的東港與菲律賓一帶產卵,在游抵臺灣西南部時最為肥美,對漁民來說,簡直是自動送上門的財富。
因此早在十七世紀初,閩粵沿海漁民便駕船到臺灣大員一帶(即臺江內海邊)和澎湖捕烏魚,並住上幾個月,直到隔年春天轉南風才返鄉,後來便逐漸有人定居臺灣。有人說,臺灣漢人移民最早就是被烏金吸引而來。
荷蘭人統治臺灣時期,看上這塊龐大利益,開始對漁民徵收什一稅(即繳納所得的十分之一),後來明鄭、清領時代也都跟進。清道光年間來臺為官的劉家謀在〈海音詩〉一百首之十七曾寫下「烏魚歲晚無消息,累得鹽官仰屋嗟」,生動描寫出當烏魚漁汛期一晚,連帶影響到烏魚子的生意,讓賴以課稅的鹽官仰屋興嘆的窘境。
日人治臺後,比較自身的鰆魚子(形色如墨條,稱「唐墨」)與臺灣的烏魚子,發現臺灣醃製方式略有不同。為追求更上乘的風味,日人陸續請來專家教導洗鹽、日晒乾燥等技術。如今,臺灣的烏魚子製作工藝已臻成熟且複雜,歷經取卵、清洗、醃漬、脫鹽、整形、壓製與日晒乾燥等多道程序,每一步都體現了匠人的用心,以及精確掌握海風、日照的變化。
歷經晚清、日治、民國的史學家連橫在《臺灣通史》裡提到烏魚子的食用之道:「食時濡酒,文火烤之,皮起細胞,不可過焦,切為薄片,味極甘香,為臺南之珍饈。」這份吃法和講究,與今無異。
烏魚子主要產於臺灣中南部,然而,從臺中梧棲、彰化鹿港、嘉義東石、臺南到高雄旗津,都聲稱自己產製者最佳。晚清鹿港詩人莊太岳(1880~1938年)的〈鹿江竹枝詞〉就寫過這種瑜亮情結:「烏魚大獲萬三三,典盡釵環為口饞。本港從來魚子好,果然風味勝臺南。」詩中描寫為了品嘗心愛的烏魚子,不惜典當首飾的瘋狂,更反映出「烏魚子是自家好」的心態。
或許,這份偏執與差異,並不在地域,而在於每位師傅對家鄉海風的獨特理解與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