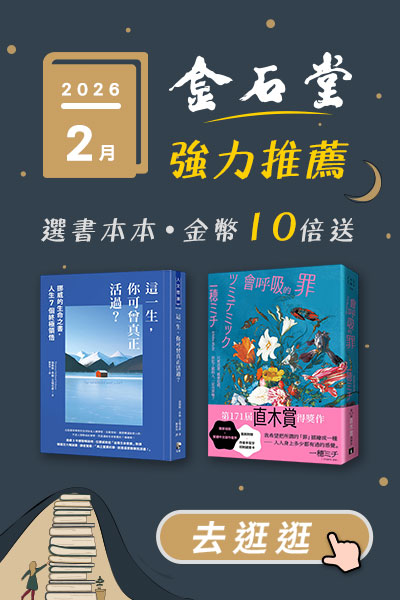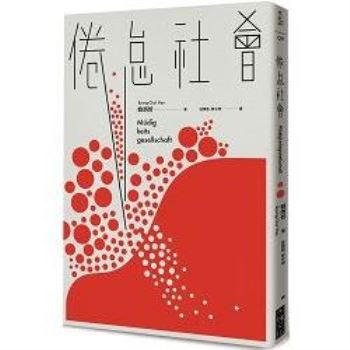【內容摘錄 】精神暴力(節錄)
每個時代都有它主流的疾病。如同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病菌的時代。後來,抗生素的發明終結了這樣的一個時代。今天,我們已經不是生活在病毒的時代。但是,當我們面臨流行性感冒大肆流行的時刻,內心仍然會有強烈的恐懼。感謝免疫科技的發達,讓我們可以把對流感病毒擴散的恐懼拋到腦後。二十一世紀之初的流行性疾病,從病理學的角度來看,這類疾病既不是透過細菌,也不是透過病毒,而是經由神經元的病變所引起。神經元所引發的疾病,如憂鬱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邊緣性人格疾患或者是身心俱疲症候群,主導了二十一世紀病理的樣貌。它們並非傳染病,而是一種因為組織壞死而造成的梗塞現象。這些現象並非肇因於免疫學上的否定他者(der Andere),而是因為過度活躍的「積極與肯定」(Positivität)所引發的。如此一來,以否定「外來者」為基礎的免疫科技,也將失去它現有的主導地位。
上個世紀是免疫防衛的時代,是一個裡面與外面,朋友與敵人,或是自身(Eigenem)與外來者(Fremdem)之間有著清楚界線的時期,甚至冷戰也是依循上述免疫防衛的思維模式在進行。而上個世紀免疫防衛,完全是由軍事上的部署指令(Dispositiv)所主導的思維模式,所使用的也正是冷戰的語彙。攻擊與防衛決定了免疫的行動。這種免疫行動的部署指令,從生物學的領域擴大到社會學,甚至擴及到整體社會的層面,但有個盲目的特徵:對所有外來的事物,都採取抵抗防衛的行為。免疫防衛的對象正是這種外來性。即便這個「外來者」並不懷有任何敵意,而且也沒有散發出任何威脅性,卻仍然會基於他的「他者性」(Andersheit),而被排除在外。
最近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社會論述,很明顯套用了免疫學的詮釋模式。儘管免疫論述已經蔚為風潮,並不能因此就把這個現象作為當今社會的組織比過去更符合免疫標準的一種組織結構的象徵。事實上,當典範本身成為被反省批判的對象,往往也象徵著這個典範開始沒落。不久前,已經不知不覺發生了典範的轉移。冷戰結束之際,剛好就開始進行典範的轉移。當前社會逐漸呈現全面擺脫免疫的組織與防禦思維的座標,這些現象全都透過「他者性」和「外來性」的消失呈現出來。「他者性」是免疫學的基本範疇,因為任何免疫的反應,都是一種對於「他者性」所產生的反動。不過,現在卻將「他者性」視為是「差異性」(Differenz),因而不會對它產生任何的免疫反應。後免疫學時代,也就是後現代的「差異性」,不會讓人難以忍受,就免疫的層面而言,它們是「相同者」(das Gleiche)。「差異性」同時意味缺少了「外來性」所產生的刺痛感,那麼一來,強烈的免疫反應也可能因此消失。「外來性」除去了原有的尖銳性,而成為消費經濟計算公式的權數,「外來者」被美化為是具有異國情調的人。「觀光客」可以恣意地四處旅遊,因為觀光客或消費者並不是「免疫防衛要攻擊的對象」。
甚至,連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特(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理論,也立論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上。他認為:「過去幾年,隨便挑一天,都能在報紙上,甚至是同一個版面上,找到表面上看來是不同事件的報導,比如,對抗新的流行性疾病的擴散,反對被控傷害人權的外國元首引渡的申請,加強打擊非法移民入境的措施,以及剷除最新型電腦病毒的策略,這些不同現象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一點也沒有,只要人們仍然保持獨立閱讀不同版面(如醫藥、法律、社會政策和電腦科技)的習慣,就不會發現它們相互關聯的地方。不過,這些事件的意義將隨著詮釋的範疇而有所改變。詮釋的範疇本身的特殊性,正好具備了橫向切斷它們各自獨立的用字遣詞、然後將它們只集中在同一個意義視域(Sinnhorizont)上的能力。就如同本書的標題,很明顯的,我將它的範疇設定在「免疫化」(Immunisierung)。〔……〕然後,上述所提及的事件,在不考慮用字措辭上的異質性(Dishomogenität)下,全部可以歸結到一種面對危機的自我保護反應。」艾斯波西特指出的這麼多事件中,沒有一樁事件能夠證實我們仍然身處一個免疫防衛的年代。即使所謂的移民者,也不是現今免疫防衛上的「他者」,更準確地說,不是「外來者」。因為「外來者」有可能會帶來真正的危險,或是會讓人產生恐懼;移民者或難民通常比較像是社會的負擔,而不是社會的威脅。電腦病毒的問題,也不再被歸為龐大的社會惡意。艾斯波西特之所以會如此認為,並非偶然。因為他分析免疫時所引用的資料,並不是當今社會現有的問題,幾乎完全是過去的資料。
然而,免疫學的典範和全球化的進程並不一致,因為引起免疫反應的他者性,在去除疆界的過程中消失了。依照免疫學所建構的世界,有著一種特殊的地誌景觀(Topologie),也就是由邊界、緩衝地帶和邊界柵欄,透過籬笆、壕溝和圍牆清楚標誌著,這些地誌標示有效阻止了全面性的交換和交流進程。現今,普遍的濫交(Promiskuität)涵蓋了所有的生活領域,而這和缺乏引發免疫反應的他者性,兩者是互為因果的。雜交(Hybridisierung),不僅是當今主流文化理論的論述,也完全支配著今日的生活方式,這與免疫化的概念背道而行,因為免疫學上的「超敏反應」(Hyperästhesie)不容許有雜交的情形。
否定辯證法是免疫力的基本特徵。免疫學上的他者就是否定,他者滲入了自身,進而尋求否定自身。當自身沒有能力否定他者時,會被他者否定而毀滅。自身免疫性的自我防衛,確切地說,是以否定的否定的方式進行。自身透過否定他者的否定性自我保衛。即使是免疫預防,即疫苗接種,也是遵循否定辯證法的法則。只需給予自身他者的微量刺激因子,就可以誘導出免疫反應。否定的否定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引起死亡的危險,因為免疫預防不需要面對他者本身。人們心甘情願接受一點暴力,使自己在面對可能致命的較大暴力時,獲得保護。他者性的消失,意味著我們生活在否定性貧乏的時代。儘管,二十一世紀的神經疾病依然跟隨辯證法的法則,但不是否定性的辯證,而是肯定性的辯證;它們是「過度肯定性」下產生的病理表現。
【內容摘錄 】一篇講稿:憂鬱症的社會(節錄)(二○一○年講於卡爾斯魯爾大學哲學系)
卡夫卡在他神祕莫測的晦澀短篇小說《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中,將普羅米修斯神話改寫成幾則傳說。第一則改寫成:「神祇累了,老鷹累了,傷口也筋疲力盡地癒合了。」我自己也改寫了普羅米修斯神話,延伸出另外一種解釋,將之轉換成內在心靈的場景,也就是當今強調功績至上的社會中,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的心理機制。這個主體會對自己施以暴力,與自己產生衝突。眾所周知,普羅米修斯將火偷給人類,同時也帶來了勞動。而在當今時代,功績主體誤以為自己享有自由,實際上卻如同普羅米修斯一樣,牢牢給束縛住了。日日啄食普羅米修斯不斷新長出的肝臟的老鷹,被詮釋為另一個引發衝突的自我(Ego)。從這點看來,可以說普羅米修斯與老鷹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自我剝削的關係。有人說,感受不到痛苦的肝臟,其痛苦就是疲倦。因此,普羅米修斯可以理解成極度疲倦的自我剝削主體。
不過,卡夫卡呈現出一種有療癒能力的倦怠,一種會癒合傷口的倦怠:「神祇累了,老鷹累了,傷口也筋疲力盡地癒合了。」而我在這本《倦怠社會》的結尾,同樣也指出一種具有療癒力的倦怠,來反駁折磨自己的自我倦怠(Ich-Müdigkeit),這種自我倦怠來自於對自我過度關注和反覆自我折磨。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倦怠,讓自我得以信任世界,可視為「較少的自我更為豐富」的倦怠,一種「信賴世界」的健康倦怠。自我倦怠是一種單獨的倦怠,是一種沒有世界、對世界的知識貧瘠、會毀滅世界且與世隔離的倦怠,會摧毀與他人之間的關聯,只利於自戀型的自我參照(Selbstbezug)。
進一步探討現今功績主體的精神之前,我想先討論規訓主體(Disziplinarsubjekt)。佛洛伊德提出的自我(Ich),就是一種規訓主體。佛洛伊德主張的心理機制,是一種壓抑的強迫機制,充滿了奴役人、壓制人的誡條和禁令。他這種心理機制正如同規訓社會,須借助圍牆、門檻、邊界和崗哨才得以存在。因此,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只有在備受壓抑的社會中才有實踐的可能,因為這種社會的體制,奠基於誡條和禁令帶來的否定。然而今日社會是一個追求績效的社會,自詡是自由社會,不斷除去誡條和禁令的否定性。在功績至上的社會中,舉足輕重的情態動詞並非佛洛伊德主張的「應該」(Sollen),而是「能夠」(Können)。這種社會轉變,同時也引起內在心靈的結構變化。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與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規訓主體,擁有「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佛洛伊德的心理機制受到否定、壓抑以及恐懼越界所左右,自我是一個「恐懼的場域」(Angststätte)。在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身上卻看不見否定,他(指功績主體)反而是肯定的主體。倘若潛意識必然與否定和壓抑所具備的否定性掛鉤,那麼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就不具有潛意識,他是後佛洛伊德時代的主體。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並非不受制於時代,而是規訓社會中,受到禁令和壓抑的否定性所控制的產物。不過,我們早已離開了規訓社會。
佛洛伊德的「自我」執行勞動主要是為了履行義務,這與康德的服從主體(Gehorsamssubjekt)有共同之處。在康德的理論中,良知接收了超我(Über-Ich)的位置。康德的道德主體同樣也屈從於「暴力」(Gewalt):「人人都有良知,且發現內在有個法官在監視自己、威嚇自己,甚至還發覺自己受到敬重(與恐懼相連結的敬重)。這種透過法則在他內心滋長的暴力,不是他自身(任意)所做,而是已內化成他的本質。」康德的主體和佛洛伊德的主體一樣,同樣也會分裂。主體會根據「他者」(Ander)的命令行動,然而他者卻又是自己的一部分:「這種原初的智性和道德(因為具備義務的概念)的稟賦,亦即『良知』,是獨特的。即使其職責正是人類本身的職責,人卻不得不藉由理性才得以看見,彷彿受到『另一個人』的命令一樣。」康德把人這種分裂稱為「雙重的自我」(doppeltes Selbst)或者「雙重人格」(zweifache Persönlichkeit)。道德的主體是被告,同時也是法官。
服從主體並非欲望主體(Lustsubjekt),而是義務主體(Pflichtsubjekt)。因此,康德學說的主體,從事的是義務勞動,且會壓抑自己的「喜好」。這時,康德的上帝就出現了,「一個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道德存在」。這位上帝不僅主管刑罰與審判,同時也是「回饋」(Gratifikation)機構。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只是我們很少深入思索。道德主體作為義務主體,雖然壓抑了一切能帶來樂趣的喜好,以有利德行的培養,但是道德之神也會「酬謝」他在痛苦中完成職責,賜予幸福。「幸福完全根據倫理比例『分配』。」道德主體能為倫理承擔痛苦,所以肯定能得到回饋,而且在此不會出現回饋危機,因為上帝不會說謊,是值得信賴的。
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不從事義務勞動,他(指功績主體)的座右銘不是服從、法則、履行義務,而是自由、欲望與喜好。他對於勞動的期待,在於能夠滿足欲望。勞動之於他,是一種樂趣。他不會聽從他人命令採取行動,主要只聽從「自己」。說穿了,就是自己的老闆,如此一來,他擺脫了「權威他者」對他的否定。但是擺脫他者,不僅只代表了解放和解脫,其辯證在於,它又發展出了新的束縛。本應是擺脫他者的束縛,卻突變成自戀型的自我參照。而自戀型的自我參照,要為今日功績主體的眾多精神疾病負起最大責任。
與他者缺乏連結,會導致回饋危機。回饋代表了認同,所以需要他者機構或第三者機構,畢竟要自我酬賞或者認同自己是不可能的。康德認為上帝是回饋機構,回饋且肯定道德成就。如果回饋結構受到干擾,功績主體就會感覺自己被迫要創造更多績效。因此,與他者缺乏連結,可說是可能引起回饋危機的「超驗」(transzendental)條件。此外,現今的生產關係也連帶造成了回饋危機。最後完成的「成品」不再是「獨立」勞動的結果了。現今的生產關係妨礙了「終止」(Abschluss),說得確切一點,現代人的勞動是「開放的」,欠缺了開頭與結尾的「終止形式」(Abschlussformen)。
每個時代都有它主流的疾病。如同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病菌的時代。後來,抗生素的發明終結了這樣的一個時代。今天,我們已經不是生活在病毒的時代。但是,當我們面臨流行性感冒大肆流行的時刻,內心仍然會有強烈的恐懼。感謝免疫科技的發達,讓我們可以把對流感病毒擴散的恐懼拋到腦後。二十一世紀之初的流行性疾病,從病理學的角度來看,這類疾病既不是透過細菌,也不是透過病毒,而是經由神經元的病變所引起。神經元所引發的疾病,如憂鬱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邊緣性人格疾患或者是身心俱疲症候群,主導了二十一世紀病理的樣貌。它們並非傳染病,而是一種因為組織壞死而造成的梗塞現象。這些現象並非肇因於免疫學上的否定他者(der Andere),而是因為過度活躍的「積極與肯定」(Positivität)所引發的。如此一來,以否定「外來者」為基礎的免疫科技,也將失去它現有的主導地位。
上個世紀是免疫防衛的時代,是一個裡面與外面,朋友與敵人,或是自身(Eigenem)與外來者(Fremdem)之間有著清楚界線的時期,甚至冷戰也是依循上述免疫防衛的思維模式在進行。而上個世紀免疫防衛,完全是由軍事上的部署指令(Dispositiv)所主導的思維模式,所使用的也正是冷戰的語彙。攻擊與防衛決定了免疫的行動。這種免疫行動的部署指令,從生物學的領域擴大到社會學,甚至擴及到整體社會的層面,但有個盲目的特徵:對所有外來的事物,都採取抵抗防衛的行為。免疫防衛的對象正是這種外來性。即便這個「外來者」並不懷有任何敵意,而且也沒有散發出任何威脅性,卻仍然會基於他的「他者性」(Andersheit),而被排除在外。
最近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社會論述,很明顯套用了免疫學的詮釋模式。儘管免疫論述已經蔚為風潮,並不能因此就把這個現象作為當今社會的組織比過去更符合免疫標準的一種組織結構的象徵。事實上,當典範本身成為被反省批判的對象,往往也象徵著這個典範開始沒落。不久前,已經不知不覺發生了典範的轉移。冷戰結束之際,剛好就開始進行典範的轉移。當前社會逐漸呈現全面擺脫免疫的組織與防禦思維的座標,這些現象全都透過「他者性」和「外來性」的消失呈現出來。「他者性」是免疫學的基本範疇,因為任何免疫的反應,都是一種對於「他者性」所產生的反動。不過,現在卻將「他者性」視為是「差異性」(Differenz),因而不會對它產生任何的免疫反應。後免疫學時代,也就是後現代的「差異性」,不會讓人難以忍受,就免疫的層面而言,它們是「相同者」(das Gleiche)。「差異性」同時意味缺少了「外來性」所產生的刺痛感,那麼一來,強烈的免疫反應也可能因此消失。「外來性」除去了原有的尖銳性,而成為消費經濟計算公式的權數,「外來者」被美化為是具有異國情調的人。「觀光客」可以恣意地四處旅遊,因為觀光客或消費者並不是「免疫防衛要攻擊的對象」。
甚至,連義大利哲學家艾斯波西特(Roberto Esposito)的免疫理論,也立論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上。他認為:「過去幾年,隨便挑一天,都能在報紙上,甚至是同一個版面上,找到表面上看來是不同事件的報導,比如,對抗新的流行性疾病的擴散,反對被控傷害人權的外國元首引渡的申請,加強打擊非法移民入境的措施,以及剷除最新型電腦病毒的策略,這些不同現象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一點也沒有,只要人們仍然保持獨立閱讀不同版面(如醫藥、法律、社會政策和電腦科技)的習慣,就不會發現它們相互關聯的地方。不過,這些事件的意義將隨著詮釋的範疇而有所改變。詮釋的範疇本身的特殊性,正好具備了橫向切斷它們各自獨立的用字遣詞、然後將它們只集中在同一個意義視域(Sinnhorizont)上的能力。就如同本書的標題,很明顯的,我將它的範疇設定在「免疫化」(Immunisierung)。〔……〕然後,上述所提及的事件,在不考慮用字措辭上的異質性(Dishomogenität)下,全部可以歸結到一種面對危機的自我保護反應。」艾斯波西特指出的這麼多事件中,沒有一樁事件能夠證實我們仍然身處一個免疫防衛的年代。即使所謂的移民者,也不是現今免疫防衛上的「他者」,更準確地說,不是「外來者」。因為「外來者」有可能會帶來真正的危險,或是會讓人產生恐懼;移民者或難民通常比較像是社會的負擔,而不是社會的威脅。電腦病毒的問題,也不再被歸為龐大的社會惡意。艾斯波西特之所以會如此認為,並非偶然。因為他分析免疫時所引用的資料,並不是當今社會現有的問題,幾乎完全是過去的資料。
然而,免疫學的典範和全球化的進程並不一致,因為引起免疫反應的他者性,在去除疆界的過程中消失了。依照免疫學所建構的世界,有著一種特殊的地誌景觀(Topologie),也就是由邊界、緩衝地帶和邊界柵欄,透過籬笆、壕溝和圍牆清楚標誌著,這些地誌標示有效阻止了全面性的交換和交流進程。現今,普遍的濫交(Promiskuität)涵蓋了所有的生活領域,而這和缺乏引發免疫反應的他者性,兩者是互為因果的。雜交(Hybridisierung),不僅是當今主流文化理論的論述,也完全支配著今日的生活方式,這與免疫化的概念背道而行,因為免疫學上的「超敏反應」(Hyperästhesie)不容許有雜交的情形。
否定辯證法是免疫力的基本特徵。免疫學上的他者就是否定,他者滲入了自身,進而尋求否定自身。當自身沒有能力否定他者時,會被他者否定而毀滅。自身免疫性的自我防衛,確切地說,是以否定的否定的方式進行。自身透過否定他者的否定性自我保衛。即使是免疫預防,即疫苗接種,也是遵循否定辯證法的法則。只需給予自身他者的微量刺激因子,就可以誘導出免疫反應。否定的否定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引起死亡的危險,因為免疫預防不需要面對他者本身。人們心甘情願接受一點暴力,使自己在面對可能致命的較大暴力時,獲得保護。他者性的消失,意味著我們生活在否定性貧乏的時代。儘管,二十一世紀的神經疾病依然跟隨辯證法的法則,但不是否定性的辯證,而是肯定性的辯證;它們是「過度肯定性」下產生的病理表現。
【內容摘錄 】一篇講稿:憂鬱症的社會(節錄)(二○一○年講於卡爾斯魯爾大學哲學系)
卡夫卡在他神祕莫測的晦澀短篇小說《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中,將普羅米修斯神話改寫成幾則傳說。第一則改寫成:「神祇累了,老鷹累了,傷口也筋疲力盡地癒合了。」我自己也改寫了普羅米修斯神話,延伸出另外一種解釋,將之轉換成內在心靈的場景,也就是當今強調功績至上的社會中,功績主體(Leistungssubjekt)的心理機制。這個主體會對自己施以暴力,與自己產生衝突。眾所周知,普羅米修斯將火偷給人類,同時也帶來了勞動。而在當今時代,功績主體誤以為自己享有自由,實際上卻如同普羅米修斯一樣,牢牢給束縛住了。日日啄食普羅米修斯不斷新長出的肝臟的老鷹,被詮釋為另一個引發衝突的自我(Ego)。從這點看來,可以說普羅米修斯與老鷹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自我剝削的關係。有人說,感受不到痛苦的肝臟,其痛苦就是疲倦。因此,普羅米修斯可以理解成極度疲倦的自我剝削主體。
不過,卡夫卡呈現出一種有療癒能力的倦怠,一種會癒合傷口的倦怠:「神祇累了,老鷹累了,傷口也筋疲力盡地癒合了。」而我在這本《倦怠社會》的結尾,同樣也指出一種具有療癒力的倦怠,來反駁折磨自己的自我倦怠(Ich-Müdigkeit),這種自我倦怠來自於對自我過度關注和反覆自我折磨。還有另外一種形式的倦怠,讓自我得以信任世界,可視為「較少的自我更為豐富」的倦怠,一種「信賴世界」的健康倦怠。自我倦怠是一種單獨的倦怠,是一種沒有世界、對世界的知識貧瘠、會毀滅世界且與世隔離的倦怠,會摧毀與他人之間的關聯,只利於自戀型的自我參照(Selbstbezug)。
進一步探討現今功績主體的精神之前,我想先討論規訓主體(Disziplinarsubjekt)。佛洛伊德提出的自我(Ich),就是一種規訓主體。佛洛伊德主張的心理機制,是一種壓抑的強迫機制,充滿了奴役人、壓制人的誡條和禁令。他這種心理機制正如同規訓社會,須借助圍牆、門檻、邊界和崗哨才得以存在。因此,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只有在備受壓抑的社會中才有實踐的可能,因為這種社會的體制,奠基於誡條和禁令帶來的否定。然而今日社會是一個追求績效的社會,自詡是自由社會,不斷除去誡條和禁令的否定性。在功績至上的社會中,舉足輕重的情態動詞並非佛洛伊德主張的「應該」(Sollen),而是「能夠」(Können)。這種社會轉變,同時也引起內在心靈的結構變化。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與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規訓主體,擁有「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佛洛伊德的心理機制受到否定、壓抑以及恐懼越界所左右,自我是一個「恐懼的場域」(Angststätte)。在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身上卻看不見否定,他(指功績主體)反而是肯定的主體。倘若潛意識必然與否定和壓抑所具備的否定性掛鉤,那麼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就不具有潛意識,他是後佛洛伊德時代的主體。佛洛伊德的潛意識並非不受制於時代,而是規訓社會中,受到禁令和壓抑的否定性所控制的產物。不過,我們早已離開了規訓社會。
佛洛伊德的「自我」執行勞動主要是為了履行義務,這與康德的服從主體(Gehorsamssubjekt)有共同之處。在康德的理論中,良知接收了超我(Über-Ich)的位置。康德的道德主體同樣也屈從於「暴力」(Gewalt):「人人都有良知,且發現內在有個法官在監視自己、威嚇自己,甚至還發覺自己受到敬重(與恐懼相連結的敬重)。這種透過法則在他內心滋長的暴力,不是他自身(任意)所做,而是已內化成他的本質。」康德的主體和佛洛伊德的主體一樣,同樣也會分裂。主體會根據「他者」(Ander)的命令行動,然而他者卻又是自己的一部分:「這種原初的智性和道德(因為具備義務的概念)的稟賦,亦即『良知』,是獨特的。即使其職責正是人類本身的職責,人卻不得不藉由理性才得以看見,彷彿受到『另一個人』的命令一樣。」康德把人這種分裂稱為「雙重的自我」(doppeltes Selbst)或者「雙重人格」(zweifache Persönlichkeit)。道德的主體是被告,同時也是法官。
服從主體並非欲望主體(Lustsubjekt),而是義務主體(Pflichtsubjekt)。因此,康德學說的主體,從事的是義務勞動,且會壓抑自己的「喜好」。這時,康德的上帝就出現了,「一個擁有至高無上權力的道德存在」。這位上帝不僅主管刑罰與審判,同時也是「回饋」(Gratifikation)機構。這個觀點非常重要,只是我們很少深入思索。道德主體作為義務主體,雖然壓抑了一切能帶來樂趣的喜好,以有利德行的培養,但是道德之神也會「酬謝」他在痛苦中完成職責,賜予幸福。「幸福完全根據倫理比例『分配』。」道德主體能為倫理承擔痛苦,所以肯定能得到回饋,而且在此不會出現回饋危機,因為上帝不會說謊,是值得信賴的。
晚期現代的功績主體不從事義務勞動,他(指功績主體)的座右銘不是服從、法則、履行義務,而是自由、欲望與喜好。他對於勞動的期待,在於能夠滿足欲望。勞動之於他,是一種樂趣。他不會聽從他人命令採取行動,主要只聽從「自己」。說穿了,就是自己的老闆,如此一來,他擺脫了「權威他者」對他的否定。但是擺脫他者,不僅只代表了解放和解脫,其辯證在於,它又發展出了新的束縛。本應是擺脫他者的束縛,卻突變成自戀型的自我參照。而自戀型的自我參照,要為今日功績主體的眾多精神疾病負起最大責任。
與他者缺乏連結,會導致回饋危機。回饋代表了認同,所以需要他者機構或第三者機構,畢竟要自我酬賞或者認同自己是不可能的。康德認為上帝是回饋機構,回饋且肯定道德成就。如果回饋結構受到干擾,功績主體就會感覺自己被迫要創造更多績效。因此,與他者缺乏連結,可說是可能引起回饋危機的「超驗」(transzendental)條件。此外,現今的生產關係也連帶造成了回饋危機。最後完成的「成品」不再是「獨立」勞動的結果了。現今的生產關係妨礙了「終止」(Abschluss),說得確切一點,現代人的勞動是「開放的」,欠缺了開頭與結尾的「終止形式」(Abschlussfor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