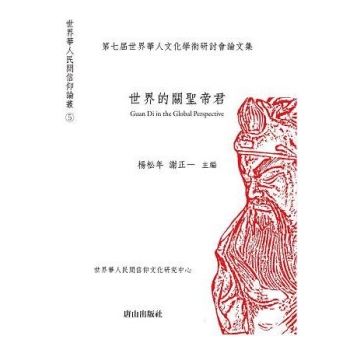節錄自〈儒學與儒教,文廟與武廟〉/龔鵬程
本文以宜蘭市的碧霞宮和礁溪鄉的協天廟這兩座廟宇為例,一方面介紹其與儒家、孔廟、儒教的關係;一方面藉此討論儒家的宗教性組織、社會性組織在推動儒家思想教化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則也據以檢討明清以降,儒學朝儒教形式發展的趨向,希望能為儒學與孔廟研究打開一個新面向。
我要談的第一個例子是宜蘭縣的縣定古蹟碧霞宮。
為什麼這幾位鸞堂的主事者會倡議興建碧霞宮呢?道理非常簡單,碧霞宮就是一種鸞堂。〈簡介〉第四段說,碧霞宮「朔望日扶鸞稟告,依神諭分派予鸞,扶鸞問乩」,就是這個道理。
扶乩扶鸞是古老的方術,魏晉即已非常盛行。但鸞堂的出現及流行,是很晚的事。清中葉時,大陸各地均有鸞堂出現,至道光庚子年(1840),由於「救劫論」的宗教思想出現,使得鸞堂蓬勃發展,鸞書大量問世,形成一個全國性的宗教熱潮。這股熱潮持續不斷,以致梁啟超已有「乩壇盈城」稱之。在這些鸞堂聖神所降的鸞文中,大概都是說:為了解消清末的大劫,唯一的辦法只有透過行善來挽回天心。此一論述,隨鸞堂運動的開展而深入人心,也使得傳統上以慈善救濟為主要工作的善堂紛紛與鸞堂相結合,鸞堂的宗教勢力遂越來越大。許多民間教派也接受了這種方術,用來作為人神溝通的宗教儀式。諸如道院、世界紅卍字會、一貫道,以及臺灣的慈惠堂以及各廟宇神壇等都是。
節錄自〈淺論哥老會中的關聖信仰〉/殷必雄
一千七百餘年前,中國歷史三國時代蜀漢武將關羽,在走下人生舞臺之後,非但沒有隨著時間漸逝,而淹沒於中國浩瀚地歷史記憶中。反而昇華進入神的殿堂,成為萬人崇敬的「武聖關公」。
在關聖信仰的傳播過程中,中國說部四大奇書之一的《三國演義》無疑地起了極大地作用。劉、關、張桃園三結義的典故,不但在中國人的世界裡是婦孺皆曉,並且對中國人的社會習俗、思想人格影響深遠,尤其是「異性結義」這個社會現象,世所罕見。產生於清代早期的「哥老會」、「天地會」,也就是近世通稱的「洪門」會黨,將「異性結義」這個習俗臻於極致。然而以幫會面貌聞世的「哥老會」、「天地會」,其骨子裡仍然是秘密宗教性質。香堂中不但設關聖的神像,「天地會」在推舉「紅棍」的時候還必須以「擲爻」的方式請示「五祖」,在得到「五祖」同意後方得封為「紅棍」步位。無論「哥老會」還是「天地會」,於開香堂的各個階段必須念誦的條賦文辭裡,對「桃園三結義」的推崇,對關聖希賢之情處處可見。香堂裡每日早晚上香,鮮花素果敬拜關聖,跟一般廟壇也沒麼兩樣。因此,「哥老會」、「天地會」會眾,亦可稱之為關聖信仰之信徒。由於「哥老會」在清末國民革命的歷史當中有不可磨滅地偉大貢獻。因此本文著重於「哥老會」中關聖信仰的探討。
因為清末甲骨文的發現,研究商代歷史有了豐富的考古資料,並得以與典籍記載相互驗證。甲骨上的文字記載地是殷人占卜的內容。殷商卜辭中有大量商代宗教信仰的材料,對瞭解中國人獨特的宗教觀有非常大的幫助。
漢代社會任俠風氣極盛,三國時代亦然。司馬遷著《史記》、班固造《漢書》,皆有〈遊俠列傳〉。相傳關聖也是因為任俠殺人而亡命奔涿郡,方得遇劉備、張飛而與之結拜。自明人羅貫中撰《三國演義》以降,有關「俠」、「俠義」的故事成為傳奇、小說歷久不衰的題材,說唱、戲曲亦多所取才三國,如是,「俠義」觀念,以及對「俠客」的嚮往深深沁入中國人民內心,每逢亂世,勇毅之士倍出,行「俠」之人不絕於途,是為中國歷史悠遠的傳統。而「行俠仗義」思想更直接影響了後世的「秘密宗教」與「幫會」,因而在清末革命之時「哥老會」會眾能以堅強不屈的毅力,犧牲生命,前仆後繼,奮戰到底,終於完成革命,肇建民國。探求「哥老會」會眾樸素思想裡的「俠義」觀念實源自關聖信仰。因之探討「哥老會」中的關聖信仰時,必須先對「俠義」觀念有所瞭解。故以本文先由殷商卜辭中尋找古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源頭,並論及中國原始宗教與道教的宇宙觀,以及由漢代演變至現代的「俠義」觀,一路延伸到「哥老會」中的關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