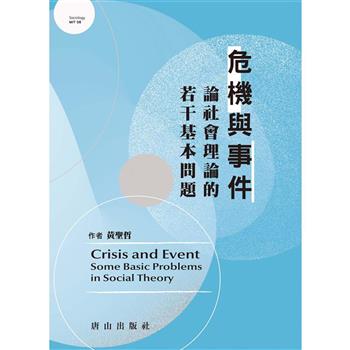節錄自〈玩與遊戲──認同的構成要件〉
依筆者之見,在社會理論的範圍內,米德最主要的貢獻是其自我理論和意義理論,為求論證的密度,本文只討論自我理論的部分。
米德認為,自我的產生首先仰賴於語言的運作,具有普遍性的符號運作形成了社會溝通的基礎。思維則是依賴內心的自我對話而進行,這其中預設了一個「一般化的他者」(the generalized other),語言即代表了這個一般化的他者,藉由語言──一般化的他者,個體隸屬於某一個特定的共同體。
自我的形成仰賴於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兒童社會化的過程主要是由玩(play)與遊戲(game)的活動表現出來。「玩」模仿的是「有意義的他者」,在角色扮演的遊戲中,兒童所模仿的只能是具體的他者的角色。常見的是:扮演媽媽、老師、警察、消防員等等,被米德用當時的語言稱為「採取他者的態度」(taking the attitude of the other)。角色在現今社會學的理解中,通常被視為社會對占據某一位置的行動者的行為的期待。「態度」是一個充滿主觀主義色彩的用語,我們建議,將之視為廣義的行動,並將之嵌入行動理論的討論之中。
米德道:「兒童們聚在一起玩印第安人遊戲。這意味著,這個兒童具有某一組刺激,這組刺激可以在他自己的內心之中導致它們將在其他人那裡導致的反應,而且,這些刺激還將與一個印第安人相對應。」
這種「玩」與「角色模仿」的理論,與班雅明所討論的人類普遍具有的模仿能力,有異曲同工之處。 「玩」只是兒童社會化的初步階段,更重要的是「遊戲」的階段。藉由參與遊戲(競賽),他不再只是單純地扮演具體的他者的角色,而是將自身「一般化」,同時置於眾多他者的角色之中,他得學會如何與其他角色協同運作(co-operation),而不是僅僅閉鎖在自身的角色之中。
最明顯的例子是棒球與足球。尤其是棒球,米德非常具有美國風格地引以為顯例:「如果他(兒童)參加由九個人進行的棒球比賽,那麼,他就必須在自己的位置上考慮他在其他每一位置上作出的反應。為了發揮他自己的作用,他必須瞭解其他每一個人準備作什麼。他必須承擔所有這些角色。」
在遊戲參與中,兒童由「有意義的他者」的模仿,進入到更抽象的「一般化他者」的思考程序之中,他進入到「有組織的角色」之中,例如:擔任足球的守門員或打棒球時的捕手。對米德而言,這個抽象化一般他者的遊戲階段對於形成個體的自我意識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遊戲中,兒童學會組織起「一般化他者」的反應,他必須同時至少將三、四個個體在他自己的「態度」中呈現出來:「這種組織是以遊戲規則的形式提出來。兒童們對各種規則非常感興趣。為了使自己擺脫各種難題,他們往往當場制定各種規則。這遊戲所具有的部分樂趣就是得出這些規則。因此,這些規則就是某種特定的態度所導致的一組反應。
依筆者之見,在社會理論的範圍內,米德最主要的貢獻是其自我理論和意義理論,為求論證的密度,本文只討論自我理論的部分。
米德認為,自我的產生首先仰賴於語言的運作,具有普遍性的符號運作形成了社會溝通的基礎。思維則是依賴內心的自我對話而進行,這其中預設了一個「一般化的他者」(the generalized other),語言即代表了這個一般化的他者,藉由語言──一般化的他者,個體隸屬於某一個特定的共同體。
自我的形成仰賴於一個社會化的過程,兒童社會化的過程主要是由玩(play)與遊戲(game)的活動表現出來。「玩」模仿的是「有意義的他者」,在角色扮演的遊戲中,兒童所模仿的只能是具體的他者的角色。常見的是:扮演媽媽、老師、警察、消防員等等,被米德用當時的語言稱為「採取他者的態度」(taking the attitude of the other)。角色在現今社會學的理解中,通常被視為社會對占據某一位置的行動者的行為的期待。「態度」是一個充滿主觀主義色彩的用語,我們建議,將之視為廣義的行動,並將之嵌入行動理論的討論之中。
米德道:「兒童們聚在一起玩印第安人遊戲。這意味著,這個兒童具有某一組刺激,這組刺激可以在他自己的內心之中導致它們將在其他人那裡導致的反應,而且,這些刺激還將與一個印第安人相對應。」
這種「玩」與「角色模仿」的理論,與班雅明所討論的人類普遍具有的模仿能力,有異曲同工之處。 「玩」只是兒童社會化的初步階段,更重要的是「遊戲」的階段。藉由參與遊戲(競賽),他不再只是單純地扮演具體的他者的角色,而是將自身「一般化」,同時置於眾多他者的角色之中,他得學會如何與其他角色協同運作(co-operation),而不是僅僅閉鎖在自身的角色之中。
最明顯的例子是棒球與足球。尤其是棒球,米德非常具有美國風格地引以為顯例:「如果他(兒童)參加由九個人進行的棒球比賽,那麼,他就必須在自己的位置上考慮他在其他每一位置上作出的反應。為了發揮他自己的作用,他必須瞭解其他每一個人準備作什麼。他必須承擔所有這些角色。」
在遊戲參與中,兒童由「有意義的他者」的模仿,進入到更抽象的「一般化他者」的思考程序之中,他進入到「有組織的角色」之中,例如:擔任足球的守門員或打棒球時的捕手。對米德而言,這個抽象化一般他者的遊戲階段對於形成個體的自我意識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遊戲中,兒童學會組織起「一般化他者」的反應,他必須同時至少將三、四個個體在他自己的「態度」中呈現出來:「這種組織是以遊戲規則的形式提出來。兒童們對各種規則非常感興趣。為了使自己擺脫各種難題,他們往往當場制定各種規則。這遊戲所具有的部分樂趣就是得出這些規則。因此,這些規則就是某種特定的態度所導致的一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