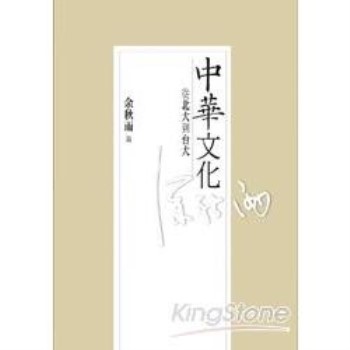閃問
問: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很多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政府部門都參與了。簡化漢字不僅僅是減少筆劃,還包括精簡總字數、減少異形、異讀、古讀等等工程。據唐德剛先生回憶,大陸在五十年代公佈的簡化漢字方案,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看了還不斷地擊節讚賞。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簡化,是古代書法家們寫草書時已經反復用過的。時至今日,一個人選用哪種字體都是自己的自由,現在由電腦轉換字體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強令改變十多億人的文化習慣,卻缺少足夠的理由。連終生只會寫繁體字的毛澤東,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只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而已。
問:在網路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冠冕在臺灣曾流行一陣子,但一直不很清楚「大師」的真正定義是什麼?在西方比如說天主教「封聖」、英國女王「封爵」、某種獎項「桂冠」得主……都很明顯,泛說的「大師」是否能有較為周延的定義或標準?
答:在民間,「大師」是指路邊算命卜卦的人。後來,大陸行政當局為了保護民間工藝,評選過一批「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製作大師……,主要是指各項民間工藝的當代傳人。這裏所說的「師」,帶有「師傅」的意思,都是親自動手的製作工匠。除了以上兩種,第三種「大師」,是對剛剛去世的專業人士的尊稱。例如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去世了,追悼會上就稱為「國學大師」;一位老畫家去世了,報紙上就稱為「繪畫大師」。中國歷來遵守「死者為大」的原則,這就使「大師」的稱呼聽起來不太吉利。即使還活著,大多也已經「日暮鄉關」。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是有苦衷的。他們告訴我,大學的理工科早就設立了很多不同層級的高端研究所,但是文化藝術學科卻沒有,因此經過評選,決定全上海在藝術學科設立兩個「大師工作室」。除了我,還有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周教授今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對這件事,我與他們商量了好幾個月,希望能去掉「大師」二字,以免產生某種不良的感覺,但他們說這已經成為制度,很難再改動。
由此可見,這個辭彙並沒有太明確的含義,只是教育行政部門表示重視的一種級別劃分而已,不必深究。我在工作室掛牌那天說了這樣一段打趣的話:「一個人,先做大人,再做老人,因此老的地位高於大。我已經做了幾十年的老師,今年由老降為大,似乎也不算什麼,不要當真。」
問: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繫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答: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馬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歷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以政治為業」的人越少越好。
問: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答:「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文革」災難中反覆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製造「民粹」。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我曾在一個演講中說過:「民粹」對於民主的傷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使人嚮往民主,「民粹」使人誤會民主。
問:我們生活在一個安逸的年代,屬於政治、經濟、科技的盛世。我所擔憂的是,我們許多文化精神卻在流逝、在消退,我們是否需要再有一個戰亂的時代,才能迎來再一次的文化繁榮?
答:以為戰亂能推進文化精神,是一種致命的誤會。這種誤會,大多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影視作品種下的惡果。
戰亂,永遠是文明的最大摧殘者。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毀於戰亂。如果說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災難會帶來抗震救災的大愛精神,但我們不能為了培植這種大愛精神而期待地震。
戰亂確實有可能激發英勇氣概,但更多的卻是非人道的殘忍。而要消除這種殘忍在人們心靈裡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費遠比戰亂更長的時間。墨子說,一心只想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統治集團,他們會用千言萬語論述戰爭的必要性,而對普通民眾而言,則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戰爭。因此,他提出,為了普天下的「兼愛」,必須堅持「非攻」。
問:現在的城市越來越像工地,不斷在拆,不斷地建,我們似乎難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別提心中的安穩了。請問余老師,您怎麼看目前包裹在「現代化進程」 中的大拆大建?
答:我們原來的生態實在太落後、太簡陋了,可以用「髒、亂、差」三字來概括。因此,「現代化進程」是必須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過幾年就安靜了。
在這個問題上,不少文化人給大家製造了一個誤會。他們總是宣稱,我們是從和睦的古典社會一步跨入喧鬧的現代社會的,因此誘使大家進入了一個「是古典,還是現代」的偽命題之中。
其實,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告訴大家,「古典」早已過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時代就過去了。而且那時的「古典」也不精彩。後來,兵荒馬亂、連年災害、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多數中國人陷於最低劣的生態之中,現在的「大拆大建」,是針對這種生態而來的。
即使被現在一批文人描繪得精彩絕倫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也是一種低劣生態,我長期生活其間,深有體會。狹小而陰暗的房間和樓梯,處處都可以互窺和偷聽;沒有衛生間,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馬桶」的呼聲,整個城區臭氣熏天;沒有煤氣,家家戶戶都在生煤球爐,因此臭氣又裹卷在嗆鼻的煤煙中,使人張不開眼……
中國民眾有權利過得好一點,千萬不要為了寫文章、玩文化,去偽造和美化過往的生態。我們的前輩一直沒有找到像樣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們的虛假強加給他們。
問:前段時間曾經有人聲稱他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不知道秋雨老師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答: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圖。在今天世界各地,富裕雖然令人羨慕卻缺少話語支持,貧困雖然令人同情卻缺少實質幫助。因此,「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說法,有某種針對性。
但是,如果把這兩句話進行理論琢磨,就立即顯得簡陋了。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辦事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辦之事;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講話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言之痛。那麼,官員的宿命就只能是:隨說隨辦,無論貧富。
問:閱讀深邃細膩的文學作品時,覺得簡體字的表述無法到位,您有同感嗎?大陸也有聲音說逐漸回復繁體字,有可能嗎?
答:我的閱讀,兩種字體各占其半,倒沒有產生您的感覺,只認為那只是一個習慣問題。五四時期胡適、魯迅他們提倡白話文,也曾經使很多學者深感痛苦,覺得白話文只用於低層世俗實用,失去了表述高雅情致的功能。但後來事實證明,情況並不是這樣。漢字簡化,自魏晉南北朝之後代代都在做,每次都會遇到不習慣的問題。現代的漢字簡化運動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比五四運動還早,由陸費逵、錢玄同先生發起,到三十年代出現過好幾個簡化方案,很多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政府部門都參與了。簡化漢字不僅僅是減少筆劃,還包括精簡總字數、減少異形、異讀、古讀等等工程。據唐德剛先生回憶,大陸在五十年代公佈的簡化漢字方案,在美國的胡適之先生看了還不斷地擊節讚賞。因為其中很大一部分簡化,是古代書法家們寫草書時已經反復用過的。時至今日,一個人選用哪種字體都是自己的自由,現在由電腦轉換字體也非常方便,但是如果要強令改變十多億人的文化習慣,卻缺少足夠的理由。連終生只會寫繁體字的毛澤東,也沒有下過這種命令。他只是讓自己的詩詞印了一些繁體字版本而已。
問:在網路上看到上海成立了「余秋雨大師工作室」,「大師」的冠冕在臺灣曾流行一陣子,但一直不很清楚「大師」的真正定義是什麼?在西方比如說天主教「封聖」、英國女王「封爵」、某種獎項「桂冠」得主……都很明顯,泛說的「大師」是否能有較為周延的定義或標準?
答:在民間,「大師」是指路邊算命卜卦的人。後來,大陸行政當局為了保護民間工藝,評選過一批「民間工藝大師」,例如根雕大師、刺繡大師、紫砂壺製作大師……,主要是指各項民間工藝的當代傳人。這裏所說的「師」,帶有「師傅」的意思,都是親自動手的製作工匠。除了以上兩種,第三種「大師」,是對剛剛去世的專業人士的尊稱。例如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去世了,追悼會上就稱為「國學大師」;一位老畫家去世了,報紙上就稱為「繪畫大師」。中國歷來遵守「死者為大」的原則,這就使「大師」的稱呼聽起來不太吉利。即使還活著,大多也已經「日暮鄉關」。
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以我的名義設立「大師工作室」,是有苦衷的。他們告訴我,大學的理工科早就設立了很多不同層級的高端研究所,但是文化藝術學科卻沒有,因此經過評選,決定全上海在藝術學科設立兩個「大師工作室」。除了我,還有一個是上海音樂學院周小燕教授的大師工作室(周教授今年已經九十六歲高齡)。對這件事,我與他們商量了好幾個月,希望能去掉「大師」二字,以免產生某種不良的感覺,但他們說這已經成為制度,很難再改動。
由此可見,這個辭彙並沒有太明確的含義,只是教育行政部門表示重視的一種級別劃分而已,不必深究。我在工作室掛牌那天說了這樣一段打趣的話:「一個人,先做大人,再做老人,因此老的地位高於大。我已經做了幾十年的老師,今年由老降為大,似乎也不算什麼,不要當真。」
問:一九一九年的時候,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號召當時德國的青年以政治為業。聯繫我自己在政府部門實習的經歷,曾經有一個領導跟我說,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但是我現在看周圍的同學很多都是熱衷於進投資銀行,進諮詢公司,喜歡投身於政治、從基層做起的北大、清華的同學還是非常少,我就非常疑惑,政治還是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
答:我不認為政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事業。從來不是,儘管有時看起來像是。中國由於幾千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沉澱成兩種心理:本能地覬覦官場,又本能地仇視官場。這兩種心理看似對立其實出於同根,都不利於人文理性的建立。馬克斯‧韋伯是一個社會學家,又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的歐洲,說那樣的話很可以理解的。他身後的德國歷史證明,那種主張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災難。我始終認為,一個社會,「以政治為業」的人越少越好。
問:您認為在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民主和多數人的暴政之間求得平衡點?
答:「多數人的暴政」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概念。「多數人」極易盲從,「多數人」無法實證,「多數人」難以反駁,但「多數人」又常常被看做「民主」。這是我在「文革」災難中反覆看到的事實,幾乎顛覆了我以前接受的所有政治常識。一切反對民主卻又要偽裝民主的人,都會利用暴民,製造「民粹」。我敢斷言,人類滅亡的原因,除了自然災害外,一定是暴民受到了挑唆而廣泛失控。
我曾在一個演講中說過:「民粹」對於民主的傷害,超過專制。因為專制使人嚮往民主,「民粹」使人誤會民主。
問:我們生活在一個安逸的年代,屬於政治、經濟、科技的盛世。我所擔憂的是,我們許多文化精神卻在流逝、在消退,我們是否需要再有一個戰亂的時代,才能迎來再一次的文化繁榮?
答:以為戰亂能推進文化精神,是一種致命的誤會。這種誤會,大多是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和各種影視作品種下的惡果。
戰亂,永遠是文明的最大摧殘者。人類十分之九以上的文明,都毀於戰亂。如果說有正面成果,那就像地震災難會帶來抗震救災的大愛精神,但我們不能為了培植這種大愛精神而期待地震。
戰亂確實有可能激發英勇氣概,但更多的卻是非人道的殘忍。而要消除這種殘忍在人們心靈裡留下的毒素,往往要花費遠比戰亂更長的時間。墨子說,一心只想發動戰爭的只能是統治集團,他們會用千言萬語論述戰爭的必要性,而對普通民眾而言,則沒有任何理由接受戰爭。因此,他提出,為了普天下的「兼愛」,必須堅持「非攻」。
問:現在的城市越來越像工地,不斷在拆,不斷地建,我們似乎難以找到安身之所,更別提心中的安穩了。請問余老師,您怎麼看目前包裹在「現代化進程」 中的大拆大建?
答:我們原來的生態實在太落後、太簡陋了,可以用「髒、亂、差」三字來概括。因此,「現代化進程」是必須的,大拆大建是免不了的。忍一忍吧,過幾年就安靜了。
在這個問題上,不少文化人給大家製造了一個誤會。他們總是宣稱,我們是從和睦的古典社會一步跨入喧鬧的現代社會的,因此誘使大家進入了一個「是古典,還是現代」的偽命題之中。
其實,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告訴大家,「古典」早已過去,至少在我曾祖父的時代就過去了。而且那時的「古典」也不精彩。後來,兵荒馬亂、連年災害、階級鬥爭、政治運動,多數中國人陷於最低劣的生態之中,現在的「大拆大建」,是針對這種生態而來的。
即使被現在一批文人描繪得精彩絕倫的上海「石庫門」房子,也是一種低劣生態,我長期生活其間,深有體會。狹小而陰暗的房間和樓梯,處處都可以互窺和偷聽;沒有衛生間,天天早上是一片「倒馬桶」的呼聲,整個城區臭氣熏天;沒有煤氣,家家戶戶都在生煤球爐,因此臭氣又裹卷在嗆鼻的煤煙中,使人張不開眼……
中國民眾有權利過得好一點,千萬不要為了寫文章、玩文化,去偽造和美化過往的生態。我們的前輩一直沒有找到像樣的安身之所,不要把我們的虛假強加給他們。
問:前段時間曾經有人聲稱他要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不知道秋雨老師是否贊同這種觀點?
答:我理解他的善良意圖。在今天世界各地,富裕雖然令人羨慕卻缺少話語支持,貧困雖然令人同情卻缺少實質幫助。因此,「為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的說法,有某種針對性。
但是,如果把這兩句話進行理論琢磨,就立即顯得簡陋了。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辦事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辦之事;天下看來最不需要你講話的地方,一定還有難言之痛。那麼,官員的宿命就只能是:隨說隨辦,無論貧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