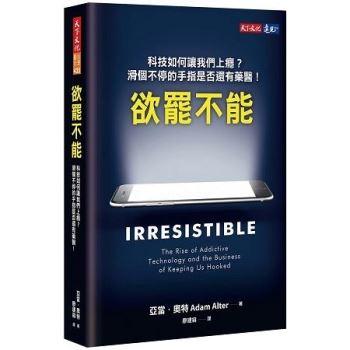絕不使用自己賣的東西
2010年蘋果新品發表會上,賈伯斯(Steve Jobs)公開發表了iPad:
這個裝置的功能太棒了……提供了最好的網頁瀏覽方式,遠比筆記型電腦和智慧型手機好得多……能提供不可思議的體驗……用來收發郵件方便得不得了,輸入文字的手感美妙極了。
在九十分鐘的產品發表會上,賈伯斯說明了iPad為何是看照片、聽音樂、利用iTunes U上課、瀏覽臉書、玩遊戲,以及使用無數應用程式的最佳工具。他認為每個人都該擁有一台iPad。
但賈伯斯不讓自己的孩子使用這個裝置。2010年底,賈伯斯告訴《紐約時報》記者比爾頓(Nick Bilton),他的孩子從沒用過iPad。「我們在家會限制孩子對科技產品的使用。」比爾頓後來發現,其他科技界巨人也會對自己的孩子實施類似的規定。《連線》前總編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家中嚴格規定孩子使用每種電子裝置的時間,他的五個孩子都不能在自己的房間裡使用有螢幕的裝置。「因為我們親眼目睹科技帶來的危險。」部落格、推特與內容平台Medium創辦人威廉斯(Evan Williams)為兩個年幼的兒子買了數百本書,卻不讓他們使用iPad。一家分析公司的創辦人古爾德(Lesley Gold)則嚴格禁止孩子在週間使用有螢幕的裝置,只在孩子必須以電腦完成作業時,才給與通融。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為賈伯斯傳記蒐集資料時,曾與賈伯斯的家人共進晚餐,他告訴比爾頓:「沒有任何一個人拿出iPad或筆電,賈伯斯的孩子不依賴電子裝置。」製造科技產品的人似乎都嚴格遵守販毒的基本原則:絕不使用自己賣的東西。
這些事實令人感到不安。全球最偉大、最知名的科技專家,私底下為何對科技產品避之唯恐不及?你能想像假如宗教領袖不讓自己的孩子成為信徒,會引發多麼強烈的抗議嗎?許多科技界與非科技界的專家,都曾與我分享過類似的觀點。好幾位電玩開發者告訴我,他們絕不玩以讓人上癮聞名的「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一位運動成癮的心理學家認為,運動手錶很危險,還說它是「全世界最愚蠢的東西」,並發誓絕不買這類產品;一位網路成癮康復中心的創辦人告訴我,她避免使用最近三年內上市的科技產品。她的手機總是關靜音,而且經常故意亂放手機,讓自己不受誘惑、不會時常想查看電郵。她最喜歡的電腦遊戲是1993年上市的「迷霧之島」(Myst),當時電腦的運算速度慢到無法處理影片圖像。她說,她願意玩「迷霧之島」的唯一理由是,這款遊戲會讓她的電腦每半小時當機一次,而重新啟動需要花很多時間。
Instragram共同創辦人霍奇穆斯(Greg Hochmuth)發現,他的產品會讓人上癮。他說:「主題標籤永遠看不完。它擁有自己的生命,就像有機體一樣,讓人們念念不忘。」和許多社群媒體平台一樣,Instragram是個無底洞。臉書的內容沒有止境;Netflix會自動播放影片下一集;交友應用程式Tinder鼓勵用戶不斷滑動螢幕畫面,尋找更好的對象。這些應用程式與網站用戶享受了不少好處,卻往往難以節制用量。設計倫理學家哈里斯(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
無法忽視的成癮現象
這些科技專家的憂心不是沒有理由的。在奮力挑戰各種可能性之際,他們發現了兩件事。
第一,我們對成癮的理解太狹隘了。我們往往認為成癮只會發生在某些「天生有成癮基因」的人身上,像是廢棄空屋裡的海洛因成癮者、菸不離手的尼古丁成癮者、把藥丸當飯吃的處方簽物質成癮者。這些標籤暗示著:成癮者與其他人不同,他們有一天或許會戒掉癮頭,但在那之前,他們只能乖乖被歸類。事實上,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賈伯斯很清楚這件事,儘管iPad的各種優點不太可能會讓孩子上癮,但孩子很容易受到iPad的誘惑,所以他不讓孩子玩iPad。這些創業家意識到:自己所推銷的工具刻意設計得讓人無法抗拒,並吸引每一個人。成癮者與其他人彼此並沒有一條清楚的分界線,只要取得或體驗過某些科技產品,所有人都有可能會上癮。
第二,數位時代的大環境是史上最容易促成人類上癮的環境。1960年代,人們只需面對屈指可數的誘惑:香菸、酒,與難以取得且價格昂貴的毒品。到了2010年,人們還需面對環境裡的各種誘惑:臉書、Instagram、色情影片、電郵、線上購物等等。這列清單有一長串,我們需要面對人類史上最多的誘惑,而我們才剛開始體會這些誘惑的威力。
比爾頓訪問的科技專家有很強的戒心,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設計出來的是令人難以抗拒的科技產品。相較於1990年代與2000年代早期的科技,現代科技既有效率,又容易上癮。全世界有數億人口使用Instagram,與別人即時分享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然後這些生活點滴會立刻被他人以留言和按讚的方式給與評價。以前下載一首歌曲需要一小時,現在只需要幾秒鐘就夠了。以前那些會因為下載速度過慢而不想下載的情況,現在早已不復存在。科技為我們帶來了便利、快速與自動化的服務,同時也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人類行為有一部分受到一連串反射性成本效益計算的驅使,根據這個計算結果,我們會決定某個行為要做一次、兩次、一百次,或根本不做。當益處遠遠大於害處,我們很可能會一直去做某件事,尤其是當這個行為啟動了對的神經機制。
臉書和Instagram的按讚、完成「魔獸」任務所得到的獎勵,或是看見自己的貼文被數百位用戶分享,這些都會啟動上述的神經機制。創造並修改科技產品、電玩與互動式體驗的人非常厲害,他們透過數百萬用戶進行數千次的測試,找出哪些招數有效、哪些沒用,哪種背景顏色、字型和音效可以使用戶最投入,而且把挫折感降到最低。隨著使用體驗不斷演化,這個體驗逐漸變成讓人無法抗拒的武器。2004年的臉書很有趣,2016年的臉書則會使人欲罷不能。
人類的成癮行為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了,但直到近數十年,才變得更加普遍、難以拒絕,並成為主流。成癮行為不會讓化學物質直接進入我們體內,但會產生相同的效果,因為它會讓人欲罷不能,而且經過精心設計。有些成癮行為非常古老,例如賭博和運動;有些則是比較新,例如追劇和滑手機。然而,所有的成癮行為都變得愈來愈難以抗拒。
下一代的隱憂
今日,八至十八歲的孩子平均把1/3的時間拿來睡覺,1/3用來上學,剩下1/3則是專注於新興科技產品,包括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視和筆記型電腦。這些孩子透過螢幕與朋友溝通的時數,比他們與別人面對面說話的時間還要多。自21世紀以來,孩子不使用螢幕玩遊戲的時間減少了20%,也就是說,他們使用螢幕的時間大約提高了20%。這些統計數字本身並無好壞之分,因為世界本來就一直在改變,直到2012年有六位學者證明,這種變化會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
2012年夏天,有五十一名孩童到洛杉磯近郊參加夏令營。這些孩子來自南加州一所公立學校,男女比例相近,年紀為十一或十二歲,種族與社經背景多元且平衡。他們每個人在家裡都有自己的電腦,擁有半支手機的使用權,每天花1小時與朋友傳訊息,大約看2.5小時的電視,並花1小時打電玩遊戲。
在接下來的一週,這群孩子要把手機、電視與遊戲主機留在家裡,他們要去健行、學習如何使用羅盤以及用弓箭射箭。他們還要學習如何用營火烹煮食物,分辨可食用與有毒植物。大人不會刻意教他們要直視對方眼睛或面對面說話,因為沒有了科技產品,這些互動會自然發生。他們不再透過螢幕上的LOL或顯示笑臉的顏文字得知朋友的心情,而是與身邊的同伴一起大笑、微笑,或是一起難過和生氣。
這群孩子在星期一上午報到後,會先進行一個簡短的測驗:非語言行為診斷分析第二版(DANVA2)。這個測驗很好玩,也曾在臉書上流行過,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解讀一堆陌生人的情緒狀態。這個測驗有半數的題目會請你看陌生人臉孔的照片,剩下的題目則是請你聽別人朗讀一段句子,然後你要判斷他們的情緒是快樂、悲傷、生氣或害怕。
這聽起來似乎很簡單,其實不然。有些臉孔和聲音很容易判斷,屬於「高張力」的情緒。但有些臉孔和聲音展現的是較細微的情緒,像是判斷蒙娜麗莎究竟是在微笑、覺得無聊、還是心情不好。我自己也做了DANVA2,結果有些題目答錯了。我覺得某個男性的聲音聽起來有些沮喪,但正確答案是感到有點害怕。參加夏令營的孩子也跟我差不多,平均起來,他們在四十八道題目中有十四題答錯。
經過四天的營隊生活後,這群孩子準備要回家了。離開之前,研究者請他們再做一次DANVA2。研究者認為,不受科技產品干擾一週後的面對面互動,可以讓這些孩子對情緒線索更加敏感。有證據顯示,熟能生巧的原則適用於情緒線索的解讀能力。在與人群隔絕環境下長大的孩子,例如在叢林一直與狼群生活的野男孩,永遠學不會解讀情緒線索。另外,被迫陷入孤立狀態的人,在擺脫與人隔絕的處境後,對於與他人互動會不知所措。對某些人來說,這種情況有可能會持續一輩子。當孩子彼此花時間相處,他們會透過不斷獲得的回饋,學習如何解讀情緒線索。當玩伴的手裡抓著玩具,並向你伸出手,你可能以為他想和你一起玩這個玩具,但當你看到他的表情,就會明白他其實要用玩具攻擊你。
解讀情緒是一種精細微妙的技巧,這種能力廢而不用就會萎縮消失,經過練習就會進步。研究者在夏令營的孩子身上也看到了這個效果,這群孩子第二次的測驗成績比第一次進步許多。第一次測驗結束後,研究者並沒有告訴他們正確答案,但他們第二次測驗的錯誤率下降了33%。研究者在同一所學校找來一群控制組,同樣進行兩次測驗。這些孩子沒有參加夏令營,他們在星期一上午與星期五下午也做了相同的測驗,第二次測驗的錯誤率下降了20%,這或許是相同測驗做了兩次所造成的效果,但他們的下降率顯然比不上參加夏令營的同學。
在都市待一週和在郊外待一週有很多的差別,除了科技產品不在身邊和與朋友面對面相處外,還有許多原因能解釋這兩群孩子在測驗上呈現的差異。我們無法確知真正的原因是什麼,但我們得到的結論無庸置疑:在進行可提升社會互動品質的測驗時,與同儕在大自然裡相處的孩子,表現會比長時間盯著發光螢幕看的孩子更好。
學習面對面溝通
孩子對成癮行為特別沒有抵抗力,因為他們不像成人具有自制力,能防止自己發展出成癮習慣。法制社會的對策是禁止孩童購買菸酒,但很少國家對行為成癮採取任何管制。現在孩子玩互動式科技遊戲可以一次玩好幾個小時,也可以在父母允許的範圍內盡情打電玩遊戲。韓國與中國曾經想過要施行所謂的「灰姑娘法」,禁止孩童在半夜12點到清晨6點間打電玩遊戲。
我們為何不讓孩子長時間玩互動式科技遊戲?為何許多科技專家禁止自己的孩子使用他們設計與公開推銷的產品?原因在於,還要等好幾年之後,我們才能知道過度使用科技產品會對孩子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第一個iPhone世代現在才八、九歲,而第一個iPad世代現在才六、七歲。他們還沒有進入青春期,因此,我們無從得知他們與現在的青少年有什麼不同,但我們知道要透過哪些線索尋找答案。我們過去常進行的一些基本心智活動,現在都由科技代勞。1990年代以前的青少年可以記住數十組電話號碼,他們互動的對象是同儕,而非科技裝置;他們自己創造玩樂活動,而不是從99美分的應用程式獲得人工製造的樂趣。
幾年前,我開始對所謂的「困境免疫」產生興趣,也就是努力解決心智難題。例如試著記住一組電話號碼,或是決定閒閒沒事的週日下午要做些什麼。這麼做能讓你對未來遭遇的心智難題產生免疫力,如同疫苗能讓你對疾病免疫一樣。舉例來說,看書比看電視更困難。
有許多證據顯示,少量的心智難題對我們有益。年輕人若在解開複雜的心智難題前,先解答難度較高的題目,而非簡單的題目,他們的解題表現會比較好。遇到挑戰的青少年運動員也會有更優異的表現,例如我們發現,大學籃球校隊若在球季開始前接受了嚴格的訓練,他們在球季的表現會更好。這些溫和的預先努力非常重要,如果我們為了讓孩子更輕鬆,給孩子一個會幫他做好很多事的科技裝置,結果使孩子沒有機會得到鍛鍊,這其實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危險性有多高。
太過依賴科技產品會導致「數位失憶」現象。兩個調查結果顯示,數千名美國與歐洲成人難以記住許多重要的電話號碼。他們說不出孩子的手機號碼,以及公司的總機號碼。另一項調查中,91%的受訪者認為手機是大腦的延伸。多數人表示,他們遇到問題時,會先上網搜尋答案,而不是試著從記憶裡尋找答案。70%的人表示,如果智慧型手機遺失,他們會感到驚慌或難過,即使只是暫時遺失。多數人說,智慧型手機裡儲存的某些資訊,是他們自己記不得,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的。
麻省理工大學心理學家透克(Sherry Turkle)也指出,科技使孩子的溝通能力變差,許多孩子與大人寧可傳送文字訊息也不願打電話聯絡。傳送文字訊息時,我們可以把自己想傳達的訊息調整得很精確,說話卻無法如此。對於別人傳來的笑話,如果你平常會用「哈哈」回應,那麼回覆「哈哈哈」表示這個笑話特別好笑,或是「哈哈哈哈」表示你快笑死了。當你生氣時,你可以用輕蔑的「K」回覆對方*;如果你氣炸了,可以乾脆不回覆。如果你想提高音量,可以用「!」,想要大吼大叫,可以用「!!」甚至「!!!」,這些表達方式的強度與符號數量成正比,「哈」或「!」的數量是算得出來的。
因此,對於害怕冒險、擔心說錯話的人來說,傳送文字訊息是最理想的溝通方式。但是用文字溝通有一個嚴重的缺點,那就是自然隨興和含糊不清的元素不見了。非語言線索消失,訊息裡將不再有停頓、輕快的語調、出其不意的笑聲、嘲弄等可強調某些意味的元素。少了這些線索,孩子就很難學會面對面溝通。
透克引述了喜劇藝人路易C.K.(Louis C.K.)在2013年上歐布萊恩的節目時,提到的個人觀察。路易C.K.說,他不是在養小孩,而是在培養未來的大人。他說:「手機是有毒的,而且對孩子的危害格外嚴重。」
他們跟別人說話時不會看著對方,也沒有同理心。現在的孩子很刻薄,因為他們正透過嘗試錯誤來學習。他們看到一個小孩後對他說:「你好胖。」接下來他們會看見對方的臉露出難過的表情,然後他們心裡明白:「哦,讓別人產生這種反應感覺很不好。」但是當他們用文字訊息寫了「你好胖」後,他們會說:「嗯,好好笑,我喜歡。」
對路易C.K.而言,面對面的溝通極為關鍵,因為那是唯一的方法,能讓孩子明白自己說的話會對別人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美國,訊息對話中以「K」回覆對方,有懶得回答、想草草結束對話的意味,有些人認為是極不禮貌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