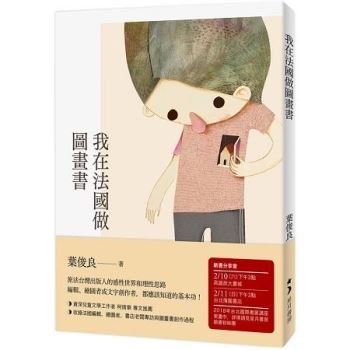第四章
為原創童書繪本作藝術指導
閱讀牽涉的不只是讀者的知性理解,他是具體時空下的美感經驗。讀者沒有受到感動時,他只是接收一些片斷冰冷的訊息,日子久了就忘了。能感動讀者的圖文才能為「他」所懂。
「編輯」這個職稱在大出版社裡可以細分為三個不同的職位:藝術指導、編輯和發行人。在規模比較小的出版社,這些工作可能由同一個人承擔。也就是說,編輯在面對圖文作者、討論創作內容的時候,他採取藝術指導的觀點,扮演藝術指導的角色。同一個編輯在面對讀者的時候,則必須扮演發行人的角色,讓最多的人看見某一本書與某個作者的價值。
並不是只有童書繪本需要藝術指導 (direction artistique)。其他領域如戲劇、舞蹈、電影、展覽等,需要在創造、表達與溝通各個環節協調一致,也需要藝術指導。
創作兒童圖畫故事書,簡單說來就是作者和藝術指導一起合作,透過繪本的形式說好一個故事。童書創作不是作者一個人的事,而是一群人的事。圖文作者的本職是透過他們所創造的圖畫和文字,感動讀者。但是一本書除了圖畫和文字之外,還有許多層面不是圖文作者所能夠花時間十足掌握的,包括字型選擇、字體大小、圖文位置、印刷用的紙張、印量、市場所能接受的版式與售價等。一本書的創作過程如果沒有藝術指導,這些環節會出現自相矛盾或銜接不良的情況,明眼人一下子就看得出來。
但是藝術指導的功能,不只是消極地避免一本書的顏色款式穿搭出現錯誤而已。
某些為孩子買書的家長偏重童書的教育功能,把傳授知識、品德與教養的內容視為正餐,把書的藝術表現當作點心,如果說正餐不能少,那麼點心沒有也餓不著。
也有人認為,希望把孩子栽培成音樂家或畫家的家長,才會講求童書的藝術表現,其他人不需要。
這個觀點忽略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閱讀牽涉的不只是讀者的知性理解,它是具體時空之下的美感經驗。當讀者沒有受到感動的時候,他只是接收一些片斷與冰冷的訊息和知識,日子久了就忘了。能感動讀者的圖文才能為他所「懂」。童書出版社藝術指導的責任即在於,透過圖書的構思與設計讓這樣的美感經驗成為可能。
如果作者對於藝術指導的工作內容有基本的了解,如果編輯對作者的創作思維有基本的認識,那麼彼此找到合適的工作夥伴的機會就比較大。出版社的編輯和作者沒有上司對部屬的縱向權力關係,如果決定在一起說好一個故事,那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雙方都期待能彼此配合,認定共同目標,發揮各自的才華,互相輝映,互相成就。
藝術指導的第一個責任:決定和誰合作
如果沒有好的作者一起配合,編輯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沒有米,巧婦無論如何也巧不起來。我們也可以把編輯想像成衝浪選手:一個欠缺才華或功力的作者像是一個沒有浪的海灣,在那裡,編輯是完全沒有展現能力的機會的。這是為什麼好的編輯非常留意他和哪些作者合作,並積極了解作者的特殊性,就好比有自信的木匠必須充分了解他所要雕刻的木材屬性,是一樣的道理。
從藝術指導的角度來看,好的作者和繪者符合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對文學與人性了解透徹。這個原則適用於文字作者,更適用於繪者。文字作者不是會賣弄文筆、杜撰故事就好,他要寫出很多人想看、一看再看的故事。因為是寫給兒童看的故事,所以很多書的內容如果不是取材於日常生活,就是創造一個超乎現實邏輯的奇幻世界。這些題材在沒有才華與功力的作者筆下可以變得很平庸,了無新意;但是對人性了解透徹的、善於駕馭文字的作者卻可以透過平凡的主題,呈現我們視而不見的生活真實面,擴展我們的生活經驗。這是我們所需要的作者。
至於繪者,他要具備精確細膩的表達能力,但是只靠純熟的繪畫技巧並不能成就一個童書插畫家。他是故事文字的第一個讀者,不能「大約讀懂」就好,而是要徹底讀懂文字作者所要表達的意境。並非所有識字的人都能做到這一件事,它需要文學閱讀的素養和能力,而這又與繪者的人生歷練脫離不了關係。
一篇好的文字有主次、有節奏、有情感,提供不同層次的閱讀樂趣。我收到一篇好的文字稿,交給某個可能合作的繪者讀時,我不會急著要他畫草圖給我看。我要他先告訴我他從文字裡讀到什麼,以便觀察他是否有讀到故事的精髓。沒有圖畫的文字好比一塊建築基地,上面什麼都還沒有蓋但是有高低起伏的地貌。我帶繪者走進這一塊基地,用意在於觀察他親近這地貌的方式。
我還是建築師的時候,曾經去蘇州造訪一些園林。除了美麗的鋪地與細緻的亭台樓閣之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些園林的地貌。來到某處拾級而上,只需三公尺的落差就足以讓身體感受去遠郊登山的興味。小石堆高處蓋了一座精巧的涼亭,坐在涼亭裡可以俯瞰水塘的荷花與游魚。從涼亭走下來,繞過水塘走上一條曲折的廊道,那廊道竟然也不是平的,而是個緩坡。走在這樣一個庭園裡,身體的每一種感官都被愉悅地喚醒。這種經驗,不要說平面圖,就連照片都很難傳達。
如果把整個圖畫書比喻成建築空間,故事文字就好像建築物起造之前的地皮,不管是天然的還是人造的,它有高有低,有始有終。我們多走幾回就會慢慢地得到一些靈感,知道這裡該放個亭子,那裡該種一棵桂花樹,用不留鑿痕的方式讓進來的人走過之後說「好舒服好暢快」,之後還會再想走第二次,第三次。
如果繪者看不見地貌的特性、優勢與限制,他很可能在不適合的地方蓋亭子、挖水塘。那亭子再怎麼精雕細琢都不能彌補這個錯誤與失敗。如果繪者的文學素養或人生閱歷和某一篇文字的意向不同調,他會遠離作者本意去發想,使作品變調或變得貧瘠。身為編輯,如果我在繪者構思草圖之前看到這一點還貿然邀請他為故事創作插圖,那我就沒有盡到編輯的責任,作者和繪者沒有一個會感到滿意,讀者就更不用說了。相反地,如果針對某個文字,能找到一個兼具文學素養與人生閱歷的繪者,那麼計劃已經成功了一半。
好的作者和繪者的第二個條件是:除了才華還要自我鍛煉,培養功力。圖文創作者並非每一次提筆都信手拈來,水到渠成。很多插畫家在成為專業創作者之後仍然隨身攜帶畫筆,不管是什麼場合都可以畫進寫生簿,這是我所要提出的「鍛煉」的觀念。
有一句話說「十八般武藝」,又說「基本功」 。並非人人都要十項全能,有些人只會一項技能,如果能做到世界第一,那也非常了不起。但是不管在哪一項領域努力,鍛煉都是不可少的。有一些專業技能可能用到的機會不多,它仍是養成過程中不可輕忽的步驟,因為當你需要用它的時候,臨時去學,學不來也學不好。
如果拿音樂作比喻,聲樂家有不同的音域,男高音有男高音的音域,女低音有女低音的音域。沒有人能夠從男低音唱到女高音,不過在他的音域裡他必須要鍛煉自己的聲音,一個人音色好但是音域窄,能夠交給他詮釋的曲目自然少。有些曲目需要音域廣、肺活量足的聲樂家去詮釋,那麼有才華又有鍛煉的聲樂家,就比較容易得到重用機會。
不同的圖文作者各有其擅長的主題和表現方式,這是他特色的一部分。當出版社收到一篇好的文字作品,編輯必須仔細衡量它的趣味、張力與強度,如果它與某繪者的趣味、張力與強度都相當,便可以考慮讓繪者讀這一篇文字,讓他為整個故事創作插畫。
一篇故事的主調可能是輕鬆詼諧,充滿冥想詩意或者高潮迭起,冒險刺激。它也可能是令人又哭又笑的悲喜劇。一篇故事如果要在成千上萬的書海裡脫穎而出,打動讀者,需要編輯扮演調音師的角色,為作品定調:文字和插畫需要同波長有共鳴,它們也必須和讀者同波長有共鳴。
編輯需要告訴圖文作者,這裡快一些,那裡慢一些,這裡需要多一些溫度,那裡需要少一些亮度。這,有功力的創作者可以配合得來,沒有功力的創作者配合不來。經常勤練武功的創作者可以很快地調整做法,舉重若輕,完成的成品超乎編輯的期待。沒有備而不用的武功的創作者,需要舉五斤的地方他只舉得三斤,做起來會覺得很吃力,也會覺得編輯在找他麻煩,但其實不是。在創作一本書的過程中,作者和編輯交換意見、修改圖文是正常的現象,但是因找不到敘事的立足點而一改再改,則不是創作的常態。這顯示了很可能當初彼此選錯了人。
作者尋找出版社合作出書時需要花費很多心血。而一旦找到合適又願意合作的出版社,他應該放心讓出版社發揮專業,把一本書編輯到比他想像的還要好。
有一位作者寫了一篇故事投稿給鴻飛,她對圖畫感覺很敏銳,但是沒有插畫的訓練與功力,我們便著手尋找適合的繪者來參與創作。她不停地給我一串插畫家的名字,像是在上餐館選菜單,因為她覺得這些繪者的插畫風格符合文字的氣質。
表面上她似乎在幫助我,實際上我很快地嗅到越俎代庖的氣氛。藝術指導不是她想的那樣。藝術指導不只讀某個作者的文字,他還讀很多不同作家的文字,這讓他得以用獵鷹似的眼睛看穿文字背後的深層力量。這些力量該用什麼方式和繪者與讀者產生交會?作者本身不見得是最清楚的人。
藝術指導找繪者,不是把他當成作者雙手的延伸。他必須尋找力量相當、音域適合而且音域夠廣的繪者,讓他讀文字。如果確定繪者能讀懂文字,藝術指導會放手讓他自由運用創造力去詮釋文字,而不是處處干預他,要求他取悅文字作者。
如果繪者自我設限或受作者限制,不淋漓盡致發揮創作者的能量,我會感到不滿:我找他是要他自我挑戰,畫出能感動自己和別人的作品,而不是在交作業。
藝術指導的第二個責任:幫助創作者超越自我
出版社的編輯或許可以幫助作者把平庸的構想變成佳作,但是他最大的用處是幫助作者把佳作變成傑作。
創作不能安於平庸,創作講究卓越。創作者的價值來自於他的特色。特色是創作者用一生的時間去追求的東西。特色為什麼重要?因為它是邁向傑作的路徑。沒有特色,便不成傑作。創作者發展獨特的觀察世界、描繪世界的方式,耕耘十年、二十年,作品經過積澱而成熟有特色,人們會捧著錢來請他繼續「做他自己」。
他只要做好自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發揮出來,那就是他的價值所在。人們是不會捧著錢去請一個沒有特色的人做他自己的。
藝術指導和創作者一樣,要能看見還不存在的東西,把它勾畫出來,讓雙方了解前進的方向,並用熱情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貢獻出來。
藝術指導和創作者必須有共通的語言,才能在一起工作。我在建築學院學習到這一個語言,它是設計的語言,也是創作的語言。一塊空地,一開始什麼都沒有,建築師根據業主的客觀需要和主觀期待,想像一棟建築物,想像從哪個地方走近建築物,如何穿越它。這是所謂的「動線」,人體移動的路線。我還不知道這裡應該鋪設階梯還是斜坡,應該鋪木地板還是大理石地磚,但是我知道應該讓使用者從A點移動到B點,沿途空間有寬窄有明暗有高低,形成一個完整美妙的體驗。
再比如說「屏蔽」:我知道這裡要區隔兩個空間,但不表示一定要砌一座牆。它可以是屏風,半透明或全透明的玻璃牆,及腰的或達天花板的書櫃等。
在計劃初始,各種不同的可能性是開放的。通過一步一步檢驗抓穩大原則後,才能有條理地設計各個細部空間。如果一開始就選擇浴室地磚的材料和顏色,結果動線卻是亂無章法,讓人走進屋子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裡走,這不是一個專業的建築師該做的事。
這個循次漸進的創作方式,可以透過「分鏡圖」(chemin de fer)應用在童書繪本創作領域。分鏡圖是一系列的草圖。編輯和圖文作者對於故事要怎麼講、每個圖畫的大小與構圖會有各自初步的想法,要透過分鏡圖來溝通,檢驗文字和圖畫的位置和內容是否相襯。
但是藝術指導的功能不只是被動地檢查書頁哪裡可以放文字,他透過分鏡圖,預先看到圖畫敘事的弱點與應該加強的地方,提醒作者和繪者。正常的情況下,這些弱點的數量不會太多,而且經過我的提醒之後,創作者會主動去思考,尋找屬於他的新表達方式,不需要我告訴他怎麼做。當他找到了解決方式,他會很高興也會有成就感,因為這創作來自於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