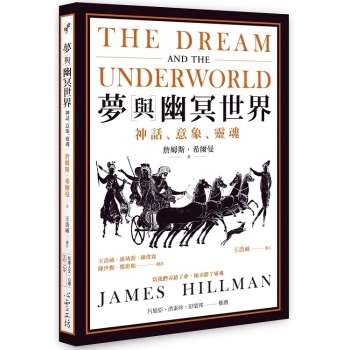【導讀】佛洛伊德、榮格與希爾曼:關於原型心理學(節錄) / 王浩威/作家、心理治療師、本書審訂者
希爾曼的靈魂之旅
一九五四年,二十四歲的詹姆斯‧希爾曼帶著新婚妻子到了蘇黎世。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要學習任何榮格心理學,說不定也還不太清楚這玩意是什麼。他們到瑞士原本是要到策馬特滑雪的,這是他們漫長蜜月旅行的一部分。
出生在美國的亞特蘭大,父親是旅館鉅亨的希爾曼,一九四四到四六年二次大戰期間服役於歐洲的美國海軍醫療部隊,退役後先進入巴黎的索邦大學,取得了英文文學研究的學位;然後再到愛爾蘭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獲得關於心智與道德科學的學位。畢業以後,自然地,和他相伴多年的女友結婚了。
這是他這人生中三次婚姻的第一次。沒想到,就在婚禮進行時,希爾曼昏倒了。這是怎麼回事?希爾曼雖然困惑,但並沒有停止原來的旅行計劃。生活富裕的這對新人,仍然繼續原來計劃好的蜜月旅行,先是去了非洲,然而又到了喀什米爾待了一年。在那個地方,他第一次接觸到榮格的作品,只是當時並沒有特別覺得受吸引。
二次大戰結束的歐洲到處都是廢墟,但戰後的人心卻是興奮的,一切欣欣向榮。所謂的精神分析或分析心理學,在這個時候已經是人人知曉的時髦流行,開始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了。不巧的是,一九三八年好不容易逃出納粹魔掌而離開維也納的佛洛伊德,扺達倫敦卻很快在第二年就去世。榮格雖然早在一九一三年就被佛洛伊德趕出精神分析陣營,但他戰前出版的《尋找靈魂的現代人》,當時成為歐美的暢銷書,到戰後依然熱賣。因此,在一般大眾心目中,榮格可以說是在佛洛伊德去世之後,心理學界最閃亮的明星了。
在策馬特與新婚妻子一起滑雪的希爾曼,對於自己當時在婚禮的昏厥一直相當不解。當他們在山上時,一位昔日的朋友提起了山下蘇黎世的榮格,他就決定搭火車下山去,想找個榮格學圈的人做做所謂的心理分析。
這一趟靈魂之旅其實還有點複雜。希爾曼夫婦坐著火車到了蘇黎世又離開,來來去去兩、三趟,猶豫許久才終於開始了分析歷程。當時榮格的個案已經太多,希爾曼先找另一位分析師進行分析。後來又先後試了幾位,直到一九五三年接受了梅爾(C. A. Meier)的分析才定下來。
梅爾是榮格當時的當家大弟子,也是一九四八年蘇黎世榮格中心創辦時的負責人。總之,希爾曼開始接受分析了,也同時加入了蘇黎世榮格中心二戰後才開始的分析師訓練學程。他在一九五八年獲得分析師資格。
在蘇黎世的歲月裡,希爾曼與他同期的同學顯然是相當不同的。一來,在這個學程裡並沒有太多他這樣「正常」的年輕人。按照他寫給美國友人信件的講法,這些同學「大多是老太太、崇拜榮格的愚蠢女人,以及一群男同性戀⋯⋯」。二來,他在巴黎和都柏林的學術訓練,讓他的背景明顯不同於其他的師長或同學。法國的人文思想在西方世界向來是自成一格的。在他進入索邦讀書的時候,巴黎的知識份子圈子已經又漸漸恢復了戰前的活力。其中有幾個當時活躍的知識份子對希爾曼影響特別深,包括法國伊斯蘭學者考賓(Henry Corbin)、詩學哲學家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和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這些人在他日後的思想發展中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一般的讀者,如果對法國當代知識傳統略有涉獵,必然知道這幾個人對後來的六O年代思潮,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到後現代,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可以說在法國思想的知識系譜中都是佔有一席之地的。
一九五八年成為榮格分析師以後的希爾曼,因為學術上的潛力從學生變成了老師,繼續留下來擔任這個中心的學習負責人。他在婚禮的昏厥,讓二十四歲的他一直留在蘇黎世,到一九七八年回美國為止,又住了另一個二十四年。
對他來說,原來的歐洲文學與哲學的訓練基礎,反而特別能幫助他進入榮格的思想世界。他因為這些哲學素養,很快就掌握了榮格以意象為主的心理學理念;但卻也因為這樣更清楚的哲學素養,讓他更能梳理出榮格思想背後的哲學,因此開始想要提出一個比榮格本身更純粹的榮格思想。
作為榮格第二代弟子的他,想法顯然不同於大部分第一代弟子,譬如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1915-1998)和雅可比(Jolande Jacobi, 1890-1973)。當然,還是有些人是支持他的,例如年紀大他七歲的古根彪爾─克雷格(Adolf Guggenbühl-Craig, 1923-2008),就始終都站在他這一邊。然而,也是因為有希爾曼這樣的榮格弟子,榮格一直不接受有所謂的榮格學派而認為每一個人都要成為他自己的想法,才果真更徹底地被執行;同樣的,也是因為希爾曼,榮格學派不至於像佛洛伊德學派一樣,在六、七O年代陷入過度強調正統而壓抑了新的發展的困境。
佛洛伊德的企圖
為什麼說是尋找一個更純粹的榮格思想呢?關於這一點,要從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差異說起。
關於榮格和佛洛伊德的關係,一九O六到一九O三這短短七年,從熱情深交到絕情分裂的過程,文獻上已經有太多討論了;但是,為了說明希爾曼的位置,我們還是必須再說一次,而且是從佛洛伊德那個時代的科學氛圍說起。
一八九五年,也就是佛洛伊德與布羅伊爾(Josef Breuer, 1842-1925)共同出版《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的那一年,佛洛伊德他同時也在這年的秋天開始進行另一篇重要的論文:〈科學心理學的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在文章裡,佛洛伊德試著為潛抑作用尋找神經生理學上的解釋,認為這是三種神經元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佛洛伊德原本是從事神經生理學研究的。他離開了學術圈,開始成為開業醫師,才開始注意到歇斯底里的症狀及治療,也因此產生「談話治療」(talking cure)的想法。從談話治療這個觀念出發,才有了後來的精神分析。當佛洛伊德構思的精神分析理論體系剛剛起步的時候,他就希望心中醞釀的這套新的心理學,能夠奠基在神經生理學這一類的「具體的」科學基礎之上。所以在這篇文章的一開頭,佛洛伊德這樣寫著:「這計劃的企圖是想要提出可以成為自然科學的心理學:它的目標,就是探討心靈的過程是如何由特定物質粒子的數量所決定的狀態呈現出來,心理學的一切將藉此而變得平白直述,不再有任何矛盾。」
佛洛伊德這樣的企圖是可以理解的。在離開了維也納大學神經生理研究室的學術團隊,而決定成為一位神經精神科的開業醫師時,他還是期待自己可以成為被當時的科學學術圈所接受的科學家。他曾經一度以為自己把握了一個好機會,可以透過在維也納醫學會發表論文的機會得到肯定。沒想到,他介紹男性歇斯底里的這一場演講,卻遭到了維也納醫學圈同行哄堂訕笑羞辱,年輕的佛洛伊德簡直是無地自容。
於是,如何在同行的面前重新站起來,而且是提出經得起科學考驗的突破性想法,也就成為佛洛伊德內心一直存在的情結。這是他發展精神分析理論最初的動力,當然,他自然也希望將精神分析發展得更科學,讓廣大的科學界,特別是醫學界,願意接受精神分析成為當時的進步科學的一份子。
理性典範與浪漫思潮的更迭
佛洛伊德發明精神分析的當時,他所處的科學環境正經歷著一連串的演化。
整個科學結構在十九世紀的短短一百年內,就經歷了好幾場的激烈革命,典範一個接著一個替換。曾經主導十八世紀下半場的啟蒙時代或理性時代,眾思想家所建立的論述,既有理性主義,也有經驗主義的。二者的主張有著根本的不同。理性主義的方法是演繹(Deduction),經驗主義是歸納(Induction)。然而,彼此的想法雖然頗有分歧,終究還是將人類的思想帶往越來越理性和科學的方向。
十八世紀初走向機械論的自然科學,在十八世紀末引發了新的反彈,也就是浪漫主義的抬頭。此時,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再次重新結合,包括政治、文學、詩、藝術,又回到合為一體的傳統。人和自然不再對立,不再像啟蒙時代時代的人急著「征服」自然;相反地,浪漫主義主張重回自然,傾聽自然的聲音。浪漫主義科學家覺得啟蒙時代所鼓勵的價值造成了科學的濫用,他們覺得科學不該是只為了人類福祉,也應該對大自然友善。浪漫主義科學家反對折解、化約的傾向,認為當一件事物被拆解,所拆解出來的各種成分/部分和「整體」還是有所不同的,我們甚至在拆解過程中失去了更重要的價值;他們在認識論上是樂觀的,認為人終究還是跟自然連結一體;他們也強調創造力、體驗和天賦;也強調科學家的角色在於科學知識的發現,從大自然發現的知識是為了更瞭解人類本質,因而我們對大自然應有更高的尊敬。
這一波風潮讓人開始注意到無意識的存在,人類非理性的意義也獲得的肯定。這時候的醫學,強調的是整個人的完整性,所以經常以一整本書來描述單一一個病人,包括他的生活和病症。而這一切都影響了日後的神經醫學的發展,當然也影響了精神分析。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浪漫主義開始受到了繼承啟蒙思想的實證主義挑戰。實證主義,由孔德(Auguste Comte)回溯十三世紀培根的作品開始,慢慢成為新的科學定義,也成為了新的世界觀。這樣的理論不斷發展,包括二十世紀中期邏輯實證論的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都可以劃分在這個新的傳統下。於是,浪漫主義時代所還原,主張回到過去人與自然一體的世界觀,這時候又被重新翻轉。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想要將個人視為一部可以拆解的機器;大自然同樣也是如此,在實證主義者的眼中都是可以拆解的。
這時候,剛好人類知識體系開始從一切都是哲學的狀態,慢慢分出更多不同的學科,包括醫學,更不用提後來才獨立出來的心理學。對過去的知識分子而言,成為知識分子的訓練目的是要對這個世界有全面性的理解;而現在的知識分子則只被要求專攻某一領域,成為某一種專家而已。
化約,或不斷拆解的科學態度,成為所謂「科學」的主流,甚至成為一套想法是否能是科學的唯一檢證標準。這樣的態度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的社會,而且越來越嚴格。人們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人體和大自然的所有祕密,只要透過足夠的分析和拆解,一切就可以不再是問題。批評者則說這樣的態度是「科學主義」,對「只有符合實證的才是科學的」這樣的看法不以為然。原本「科學」這一個詞所含括的範圍其實是更廣濶的,但在實證主義的主導下,變得只有狹義定義的科學了。儘管如此,一切依然朝向越來越「科學」的方向走了。
就這樣,主流的醫學開始強調有系統、可分解的知識。甚至,伴隨著這樣的態度,原本的實證主義可能還不夠,計量科學又成為新的標準。結果是,一切的學問最好要可以量化,甚至是有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才是科學。
走向田野的浪漫主義心理學
佛洛伊德選擇了實證主義,或者說,實證主義選擇了他,因為那一個時代的氛圍就是如此。在十九世紀末,實證主義代表的是下一個更進步的時代。但是,二十世紀七O年代以後,當心理學從實證主義走向量化科學,佛洛伊德也逐漸被甩出心理學領域。
這樣的科學典範演變過程,影響著我們對心理學的定義。
從這樣的脈絡之下重新看榮格,也許我們更可以瞭解一九O六年才開始與榮格密集通信、一九O七年才第一次與榮格見面的佛洛伊德,為何馬上熱切地認定榮格是他的皇儲子,又為什麼在一九一一年他們開始出現歧異,甚至到一九一三年完全決裂。
對於原來跟隨布魯勒(Paul Eugen Bleuler, 1857-1939)在蘇黎世大學附設伯格霍茲里(Burghölzli)精神病院學習精神醫學的榮格,從一開始認識佛洛伊德的時候,一方面著迷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成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和佛洛伊德不一樣的。
一九O六年早春,三十一歲、在蘇黎世的榮格,在好好閱讀了《夢的解析》以後,將他自己的論文〈字詞聯想關於診斷的研究〉(Diagnostic Association Studies)寄給五十歲、在維也納的佛洛伊德,開始兩個人濃厚的友誼和密集的通信。
在頻繁的書信討論中,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一封信,榮格感覺有必要將他們的差異描述出來,並且辨認出五點,是「我們的見解不同的地方」。第一點是關於榮格正在研究不同的臨床「材料」。第三點是關於他們在經驗上的差異(榮格比佛洛伊德年輕十九歲)。第四點是關於「精神分析的天份」,榮格感覺佛洛伊德擁有更多,「無論是數量與品質」。第五點,榮格引述這個「缺點」:他並沒有直接從佛洛伊德那裡獲得訓練,及欠缺跟這位年長老師的接觸。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點:「我的教養,我們的環境,與我的科學前提,無論如何,不同於你的」。
在新年那天(1907年 1月1日),佛洛伊德回信了,但根本就沒有處理榮格辨認的這些差異,但前人是相當在乎榮格這樣的察覺。他在信裡懇求榮格:「我請求你……不要偏離我太遠,既然你實際上已跟我非常接近。」
希爾曼的靈魂之旅
一九五四年,二十四歲的詹姆斯‧希爾曼帶著新婚妻子到了蘇黎世。他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要學習任何榮格心理學,說不定也還不太清楚這玩意是什麼。他們到瑞士原本是要到策馬特滑雪的,這是他們漫長蜜月旅行的一部分。
出生在美國的亞特蘭大,父親是旅館鉅亨的希爾曼,一九四四到四六年二次大戰期間服役於歐洲的美國海軍醫療部隊,退役後先進入巴黎的索邦大學,取得了英文文學研究的學位;然後再到愛爾蘭都柏林的三一學院,獲得關於心智與道德科學的學位。畢業以後,自然地,和他相伴多年的女友結婚了。
這是他這人生中三次婚姻的第一次。沒想到,就在婚禮進行時,希爾曼昏倒了。這是怎麼回事?希爾曼雖然困惑,但並沒有停止原來的旅行計劃。生活富裕的這對新人,仍然繼續原來計劃好的蜜月旅行,先是去了非洲,然而又到了喀什米爾待了一年。在那個地方,他第一次接觸到榮格的作品,只是當時並沒有特別覺得受吸引。
二次大戰結束的歐洲到處都是廢墟,但戰後的人心卻是興奮的,一切欣欣向榮。所謂的精神分析或分析心理學,在這個時候已經是人人知曉的時髦流行,開始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了。不巧的是,一九三八年好不容易逃出納粹魔掌而離開維也納的佛洛伊德,扺達倫敦卻很快在第二年就去世。榮格雖然早在一九一三年就被佛洛伊德趕出精神分析陣營,但他戰前出版的《尋找靈魂的現代人》,當時成為歐美的暢銷書,到戰後依然熱賣。因此,在一般大眾心目中,榮格可以說是在佛洛伊德去世之後,心理學界最閃亮的明星了。
在策馬特與新婚妻子一起滑雪的希爾曼,對於自己當時在婚禮的昏厥一直相當不解。當他們在山上時,一位昔日的朋友提起了山下蘇黎世的榮格,他就決定搭火車下山去,想找個榮格學圈的人做做所謂的心理分析。
這一趟靈魂之旅其實還有點複雜。希爾曼夫婦坐著火車到了蘇黎世又離開,來來去去兩、三趟,猶豫許久才終於開始了分析歷程。當時榮格的個案已經太多,希爾曼先找另一位分析師進行分析。後來又先後試了幾位,直到一九五三年接受了梅爾(C. A. Meier)的分析才定下來。
梅爾是榮格當時的當家大弟子,也是一九四八年蘇黎世榮格中心創辦時的負責人。總之,希爾曼開始接受分析了,也同時加入了蘇黎世榮格中心二戰後才開始的分析師訓練學程。他在一九五八年獲得分析師資格。
在蘇黎世的歲月裡,希爾曼與他同期的同學顯然是相當不同的。一來,在這個學程裡並沒有太多他這樣「正常」的年輕人。按照他寫給美國友人信件的講法,這些同學「大多是老太太、崇拜榮格的愚蠢女人,以及一群男同性戀⋯⋯」。二來,他在巴黎和都柏林的學術訓練,讓他的背景明顯不同於其他的師長或同學。法國的人文思想在西方世界向來是自成一格的。在他進入索邦讀書的時候,巴黎的知識份子圈子已經又漸漸恢復了戰前的活力。其中有幾個當時活躍的知識份子對希爾曼影響特別深,包括法國伊斯蘭學者考賓(Henry Corbin)、詩學哲學家巴修拉(Gaston Bachelard)和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這些人在他日後的思想發展中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一般的讀者,如果對法國當代知識傳統略有涉獵,必然知道這幾個人對後來的六O年代思潮,從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到後現代,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可以說在法國思想的知識系譜中都是佔有一席之地的。
一九五八年成為榮格分析師以後的希爾曼,因為學術上的潛力從學生變成了老師,繼續留下來擔任這個中心的學習負責人。他在婚禮的昏厥,讓二十四歲的他一直留在蘇黎世,到一九七八年回美國為止,又住了另一個二十四年。
對他來說,原來的歐洲文學與哲學的訓練基礎,反而特別能幫助他進入榮格的思想世界。他因為這些哲學素養,很快就掌握了榮格以意象為主的心理學理念;但卻也因為這樣更清楚的哲學素養,讓他更能梳理出榮格思想背後的哲學,因此開始想要提出一個比榮格本身更純粹的榮格思想。
作為榮格第二代弟子的他,想法顯然不同於大部分第一代弟子,譬如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1915-1998)和雅可比(Jolande Jacobi, 1890-1973)。當然,還是有些人是支持他的,例如年紀大他七歲的古根彪爾─克雷格(Adolf Guggenbühl-Craig, 1923-2008),就始終都站在他這一邊。然而,也是因為有希爾曼這樣的榮格弟子,榮格一直不接受有所謂的榮格學派而認為每一個人都要成為他自己的想法,才果真更徹底地被執行;同樣的,也是因為希爾曼,榮格學派不至於像佛洛伊德學派一樣,在六、七O年代陷入過度強調正統而壓抑了新的發展的困境。
佛洛伊德的企圖
為什麼說是尋找一個更純粹的榮格思想呢?關於這一點,要從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差異說起。
關於榮格和佛洛伊德的關係,一九O六到一九O三這短短七年,從熱情深交到絕情分裂的過程,文獻上已經有太多討論了;但是,為了說明希爾曼的位置,我們還是必須再說一次,而且是從佛洛伊德那個時代的科學氛圍說起。
一八九五年,也就是佛洛伊德與布羅伊爾(Josef Breuer, 1842-1925)共同出版《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的那一年,佛洛伊德他同時也在這年的秋天開始進行另一篇重要的論文:〈科學心理學的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在文章裡,佛洛伊德試著為潛抑作用尋找神經生理學上的解釋,認為這是三種神經元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佛洛伊德原本是從事神經生理學研究的。他離開了學術圈,開始成為開業醫師,才開始注意到歇斯底里的症狀及治療,也因此產生「談話治療」(talking cure)的想法。從談話治療這個觀念出發,才有了後來的精神分析。當佛洛伊德構思的精神分析理論體系剛剛起步的時候,他就希望心中醞釀的這套新的心理學,能夠奠基在神經生理學這一類的「具體的」科學基礎之上。所以在這篇文章的一開頭,佛洛伊德這樣寫著:「這計劃的企圖是想要提出可以成為自然科學的心理學:它的目標,就是探討心靈的過程是如何由特定物質粒子的數量所決定的狀態呈現出來,心理學的一切將藉此而變得平白直述,不再有任何矛盾。」
佛洛伊德這樣的企圖是可以理解的。在離開了維也納大學神經生理研究室的學術團隊,而決定成為一位神經精神科的開業醫師時,他還是期待自己可以成為被當時的科學學術圈所接受的科學家。他曾經一度以為自己把握了一個好機會,可以透過在維也納醫學會發表論文的機會得到肯定。沒想到,他介紹男性歇斯底里的這一場演講,卻遭到了維也納醫學圈同行哄堂訕笑羞辱,年輕的佛洛伊德簡直是無地自容。
於是,如何在同行的面前重新站起來,而且是提出經得起科學考驗的突破性想法,也就成為佛洛伊德內心一直存在的情結。這是他發展精神分析理論最初的動力,當然,他自然也希望將精神分析發展得更科學,讓廣大的科學界,特別是醫學界,願意接受精神分析成為當時的進步科學的一份子。
理性典範與浪漫思潮的更迭
佛洛伊德發明精神分析的當時,他所處的科學環境正經歷著一連串的演化。
整個科學結構在十九世紀的短短一百年內,就經歷了好幾場的激烈革命,典範一個接著一個替換。曾經主導十八世紀下半場的啟蒙時代或理性時代,眾思想家所建立的論述,既有理性主義,也有經驗主義的。二者的主張有著根本的不同。理性主義的方法是演繹(Deduction),經驗主義是歸納(Induction)。然而,彼此的想法雖然頗有分歧,終究還是將人類的思想帶往越來越理性和科學的方向。
十八世紀初走向機械論的自然科學,在十八世紀末引發了新的反彈,也就是浪漫主義的抬頭。此時,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再次重新結合,包括政治、文學、詩、藝術,又回到合為一體的傳統。人和自然不再對立,不再像啟蒙時代時代的人急著「征服」自然;相反地,浪漫主義主張重回自然,傾聽自然的聲音。浪漫主義科學家覺得啟蒙時代所鼓勵的價值造成了科學的濫用,他們覺得科學不該是只為了人類福祉,也應該對大自然友善。浪漫主義科學家反對折解、化約的傾向,認為當一件事物被拆解,所拆解出來的各種成分/部分和「整體」還是有所不同的,我們甚至在拆解過程中失去了更重要的價值;他們在認識論上是樂觀的,認為人終究還是跟自然連結一體;他們也強調創造力、體驗和天賦;也強調科學家的角色在於科學知識的發現,從大自然發現的知識是為了更瞭解人類本質,因而我們對大自然應有更高的尊敬。
這一波風潮讓人開始注意到無意識的存在,人類非理性的意義也獲得的肯定。這時候的醫學,強調的是整個人的完整性,所以經常以一整本書來描述單一一個病人,包括他的生活和病症。而這一切都影響了日後的神經醫學的發展,當然也影響了精神分析。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浪漫主義開始受到了繼承啟蒙思想的實證主義挑戰。實證主義,由孔德(Auguste Comte)回溯十三世紀培根的作品開始,慢慢成為新的科學定義,也成為了新的世界觀。這樣的理論不斷發展,包括二十世紀中期邏輯實證論的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都可以劃分在這個新的傳統下。於是,浪漫主義時代所還原,主張回到過去人與自然一體的世界觀,這時候又被重新翻轉。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想要將個人視為一部可以拆解的機器;大自然同樣也是如此,在實證主義者的眼中都是可以拆解的。
這時候,剛好人類知識體系開始從一切都是哲學的狀態,慢慢分出更多不同的學科,包括醫學,更不用提後來才獨立出來的心理學。對過去的知識分子而言,成為知識分子的訓練目的是要對這個世界有全面性的理解;而現在的知識分子則只被要求專攻某一領域,成為某一種專家而已。
化約,或不斷拆解的科學態度,成為所謂「科學」的主流,甚至成為一套想法是否能是科學的唯一檢證標準。這樣的態度一直延伸到我們現在的社會,而且越來越嚴格。人們開始相信自己可以找到人體和大自然的所有祕密,只要透過足夠的分析和拆解,一切就可以不再是問題。批評者則說這樣的態度是「科學主義」,對「只有符合實證的才是科學的」這樣的看法不以為然。原本「科學」這一個詞所含括的範圍其實是更廣濶的,但在實證主義的主導下,變得只有狹義定義的科學了。儘管如此,一切依然朝向越來越「科學」的方向走了。
就這樣,主流的醫學開始強調有系統、可分解的知識。甚至,伴隨著這樣的態度,原本的實證主義可能還不夠,計量科學又成為新的標準。結果是,一切的學問最好要可以量化,甚至是有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的,才是科學。
走向田野的浪漫主義心理學
佛洛伊德選擇了實證主義,或者說,實證主義選擇了他,因為那一個時代的氛圍就是如此。在十九世紀末,實證主義代表的是下一個更進步的時代。但是,二十世紀七O年代以後,當心理學從實證主義走向量化科學,佛洛伊德也逐漸被甩出心理學領域。
這樣的科學典範演變過程,影響著我們對心理學的定義。
從這樣的脈絡之下重新看榮格,也許我們更可以瞭解一九O六年才開始與榮格密集通信、一九O七年才第一次與榮格見面的佛洛伊德,為何馬上熱切地認定榮格是他的皇儲子,又為什麼在一九一一年他們開始出現歧異,甚至到一九一三年完全決裂。
對於原來跟隨布魯勒(Paul Eugen Bleuler, 1857-1939)在蘇黎世大學附設伯格霍茲里(Burghölzli)精神病院學習精神醫學的榮格,從一開始認識佛洛伊德的時候,一方面著迷於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成就,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和佛洛伊德不一樣的。
一九O六年早春,三十一歲、在蘇黎世的榮格,在好好閱讀了《夢的解析》以後,將他自己的論文〈字詞聯想關於診斷的研究〉(Diagnostic Association Studies)寄給五十歲、在維也納的佛洛伊德,開始兩個人濃厚的友誼和密集的通信。
在頻繁的書信討論中,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一封信,榮格感覺有必要將他們的差異描述出來,並且辨認出五點,是「我們的見解不同的地方」。第一點是關於榮格正在研究不同的臨床「材料」。第三點是關於他們在經驗上的差異(榮格比佛洛伊德年輕十九歲)。第四點是關於「精神分析的天份」,榮格感覺佛洛伊德擁有更多,「無論是數量與品質」。第五點,榮格引述這個「缺點」:他並沒有直接從佛洛伊德那裡獲得訓練,及欠缺跟這位年長老師的接觸。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點:「我的教養,我們的環境,與我的科學前提,無論如何,不同於你的」。
在新年那天(1907年 1月1日),佛洛伊德回信了,但根本就沒有處理榮格辨認的這些差異,但前人是相當在乎榮格這樣的察覺。他在信裡懇求榮格:「我請求你……不要偏離我太遠,既然你實際上已跟我非常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