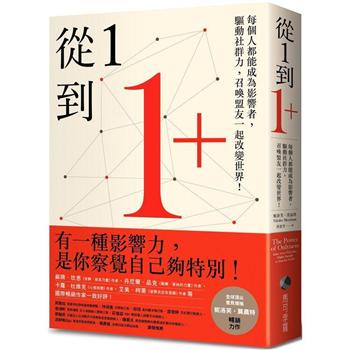第一章 大哉問
告訴我,你打算怎樣過這不凡又珍貴的一生?
──詩人瑪莉.奧利佛(Mary Oliver)
可貴的想法
三名少年使「美國童軍」(Boy Scouts of America)改變了歧視性的政策;一名想要拯救親手足的哥哥,使整個醫療照護產業開始處理之前「無法治癒」的疾病;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團結起來,為一樁七十年前的戰爭罪行追討正義。
少不更事者、生了病的人、遭到漠視的人──這些人通常不屬於想法會被重視的那類人。想法是否有人聽取,往往是看發言者是誰,看他背後的靠山有多強大,而不是看想法本身有多重要。所以,如果少不更事者、病人、遭到漠視的人成功地發揮影響力,他們的成就對我們其他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別人往往會說我們的主張沒人在意,那是因為聽起來太刺耳了,或是因為我們缺乏一定的資格,或者就只因為提出的要求「太過」。難道我們的主張就不能也有一樣的機會嗎?
難道那些想法不該出頭嗎?
二○一一年我開始撰寫這個概念時,我難以用文字表達這種感覺。我不想只是單純主張:新的想法和觀點對現代的創意經濟很重要──雖然它們確實很重要;或如今靠網絡(network)匯集在一起的人也可以執行大規模的專案,那不再是大型階層組織的專利;或時代變了,我們不必再為了完成事情而「迎合」組織。我想要提出的是,任何人──甚至是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很重要。
我想主張的關鍵概念是,地球上的七十五億人,人人皆有價值可以貢獻。怎麼說呢?你在世上占有的位置,是只有你能站立的一席之地,運作著你的過往與經歷、願景和希望。你從那個獨自占有的位置,提出獨特的觀點、新穎的見解,甚至突破性的點子。如今你可以透過網絡的力量來推廣並實現那些想法,你等於掌握了新的手段,用以撼動世界。
我試著以現有的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我想找的字眼必須是一個名詞,它必須傳達出每個人都有創造價值的能力,同時即使是瘋狂的點子也有機會大放異彩,因為「網絡」讓任何人都可以跳過傳統的守門人以及他們認定的框架。當時我正在為《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撰稿,我和編輯莎拉.葛林.卡邁可(Sarah Green Carmichael)反覆斟酌了一些用字,最後我們意識到任何字典收錄的詞彙都無法涵蓋這個概念。不過,由於我倆在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都曾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當時主流文化告訴我們,這樣的「特立獨行」使我們的想法被邊緣化、失去意義。我們因此心想,不如就讓我們來顛覆那個概念吧,我們想反過來主張:每個人的「獨到之處」(only)都是一種優勢。於是,「onlyness」(獨一無二)這個字眼就在那次靈光乍現時誕生了。透過這種獨一無二的力量,一個人先是提出了源於自身背景而有的構想,並在志同道合的社群協助下醞釀那個想法,接著透過共同行動,使得這個想法產生力量影響世界。
創造這股閃電的風暴其實已經醞釀好一陣子了。我之前常在想,是不是任何人都夠格擁有成功的機會?還是每個人一定要符合某種形象,才有可能讓自己的想法獲得重視?那兩種看法之間的拉扯,對我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且聽我分享三個故事,讓我說明我是如何發現自己的「獨一無二」。
八本書和兩套衣服
一九八六年的某天,我走過加州庫帕提諾(Cupertino)這個我住的郊區附近,進到當地的溫切爾甜甜圈店時,並不知道我的人生整個都將改變了。我以為一兩個小時──最多四個小時後,我就會回家,沒想到結果完全錯了。
那年我十八歲,當天稍早我先回到家,意外發現家裡來了一群阿姨,她們正忙著以香料、酥油、米和雞肉烹煮印度香飯。她們七嘴八舌的,我聽不出是誰先對我宣布,總之有人告訴我,我的媒妁婚姻顯然已經訂下了。我未來的丈夫是個鰥夫,他會給我媽一幢房子,從此以後我媽(扶養三個孩子的印度離婚婦女)再也不用煩惱財務問題了。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宣告了我的未來,聽起來像是一種解脫,也為我的人生翻開了新的篇章。 我快滿五歲時就來到美國,在這裡長大,但我一直知道以這種方式成婚是我的責任。我不知道那個訊息究竟是何時或以什麼方式灌輸給我的,但顯然那就是我的命運。我對母親百依百順,所以願意為她及家人那麼做,尤其是一想到她以移民的身分,帶我們來追尋美國夢,並為此做了種種犧牲,讓我更願意為她做「正確的事」。
儘管如此,私底下我仍然有著心願未了。於是,我轉頭向開明的舅舅札法求助。舅舅早先來到美國上大學,現在是帕羅奧圖(Palo Alto)某大藥廠的主管。他是我們家在商討婚姻時的男性代表,因為我父親早就離開我們了。我問舅舅:「他(新郎)知道我想上大學嗎?」當時我正在讀社區大學,並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入學延後一年。舅舅回答:「不知道,妳母親不讓我提起這件事,妳可以婚後再跟他討論。」
這番話的意思不斷在我的腦中翻攪,因為那表示我至少還要再延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上大學。根據傳統的媒妁婚約,我不能在婚前認識新郎,我們也許可以打招呼,或是在其他人的陪同下一起坐在同一個房間裡,但他不會知道我的人生目標,我也不會知道他的人生目標。告訴他我想做什麼,那太反常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考慮到這種情況,我試著說服舅舅,甚至哀求了一番。從那些阿姨的閒聊中,我知道新郎的家裡有管家、廚師,還有一個保母負責照顧他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他住在附近山上的豪宅裡,所以肯定不是為了找我去幫忙家務而娶我。我相信,如果他事先知道我有意上大學,應該會答應讓我去接受教育。但是,如果我必須跟他慢慢培養關係,等到適當時機才提出求學的要求,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而我在未經母親的許可下,自己取得延後入學柏克萊一年的資格,到時肯定也會失效了。而新郎會讓我至少繼續讀社區大學嗎?
在我重視的諸多事情之中,教育顯得很不同。在我身處的文化裡,教育往往是那些被期待要做出決策的男性的專利。但我也想獲得平等的立足點,接受教育,以便有能力主導自己的未來。
舅舅表示,不過那件事情已經談完了。我看得出來他站在我這邊,但他也無能為力。他說:「沒辦法做什麼。」 我一聽心亂如麻,原有的勇氣逐漸潰散。過了幾小時後,家裡那些鬧烘烘的活動結束了,客人皆已離去,但我還有一個孤注一擲的行動計畫正要登場。
我用一種誇張的語氣,告訴我媽我要離家出走了。接著,我開始把書本和衣物塞進紙箱裡,書的比重遠遠超過衣服,但沒放牙刷,反正那不重要,那些東西只是我做戲的道具。母親站在我的房間裡看著我時,我抗議道:「反正我只是產品,你們的交易少了我就無法成交!」我離家時堅稱:妳只要跟我保證,妳會先問他要不要讓我上大學就好了!
午後時分,在吃完蘋果炸餡餅和甜餅圈後,我抱著那個紙箱,拖著沉重的腳步,來到我就讀的德安扎社區大學(De Anza)打電話。
這時電話另一頭的母親已經氣急敗壞,講不出完整的句子,但嗓門還是很大。我們的對話就像聾子互相叫囂一樣,彼此都聽不到對方的說法。於是,我掛了電話,打電話給大我七歲的已婚姊姊。她提醒我:「媽說妳不回家的話,她會自殺。」那時我才意識到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解決。不過,跟我姊講完電話後,我還是覺得我
告訴我,你打算怎樣過這不凡又珍貴的一生?
──詩人瑪莉.奧利佛(Mary Oliver)
可貴的想法
三名少年使「美國童軍」(Boy Scouts of America)改變了歧視性的政策;一名想要拯救親手足的哥哥,使整個醫療照護產業開始處理之前「無法治癒」的疾病;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團結起來,為一樁七十年前的戰爭罪行追討正義。
少不更事者、生了病的人、遭到漠視的人──這些人通常不屬於想法會被重視的那類人。想法是否有人聽取,往往是看發言者是誰,看他背後的靠山有多強大,而不是看想法本身有多重要。所以,如果少不更事者、病人、遭到漠視的人成功地發揮影響力,他們的成就對我們其他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別人往往會說我們的主張沒人在意,那是因為聽起來太刺耳了,或是因為我們缺乏一定的資格,或者就只因為提出的要求「太過」。難道我們的主張就不能也有一樣的機會嗎?
難道那些想法不該出頭嗎?
二○一一年我開始撰寫這個概念時,我難以用文字表達這種感覺。我不想只是單純主張:新的想法和觀點對現代的創意經濟很重要──雖然它們確實很重要;或如今靠網絡(network)匯集在一起的人也可以執行大規模的專案,那不再是大型階層組織的專利;或時代變了,我們不必再為了完成事情而「迎合」組織。我想要提出的是,任何人──甚至是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很重要。
我想主張的關鍵概念是,地球上的七十五億人,人人皆有價值可以貢獻。怎麼說呢?你在世上占有的位置,是只有你能站立的一席之地,運作著你的過往與經歷、願景和希望。你從那個獨自占有的位置,提出獨特的觀點、新穎的見解,甚至突破性的點子。如今你可以透過網絡的力量來推廣並實現那些想法,你等於掌握了新的手段,用以撼動世界。
我試著以現有的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但總覺得少了點什麼。我想找的字眼必須是一個名詞,它必須傳達出每個人都有創造價值的能力,同時即使是瘋狂的點子也有機會大放異彩,因為「網絡」讓任何人都可以跳過傳統的守門人以及他們認定的框架。當時我正在為《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撰稿,我和編輯莎拉.葛林.卡邁可(Sarah Green Carmichael)反覆斟酌了一些用字,最後我們意識到任何字典收錄的詞彙都無法涵蓋這個概念。不過,由於我倆在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都曾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當時主流文化告訴我們,這樣的「特立獨行」使我們的想法被邊緣化、失去意義。我們因此心想,不如就讓我們來顛覆那個概念吧,我們想反過來主張:每個人的「獨到之處」(only)都是一種優勢。於是,「onlyness」(獨一無二)這個字眼就在那次靈光乍現時誕生了。透過這種獨一無二的力量,一個人先是提出了源於自身背景而有的構想,並在志同道合的社群協助下醞釀那個想法,接著透過共同行動,使得這個想法產生力量影響世界。
創造這股閃電的風暴其實已經醞釀好一陣子了。我之前常在想,是不是任何人都夠格擁有成功的機會?還是每個人一定要符合某種形象,才有可能讓自己的想法獲得重視?那兩種看法之間的拉扯,對我自己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且聽我分享三個故事,讓我說明我是如何發現自己的「獨一無二」。
八本書和兩套衣服
一九八六年的某天,我走過加州庫帕提諾(Cupertino)這個我住的郊區附近,進到當地的溫切爾甜甜圈店時,並不知道我的人生整個都將改變了。我以為一兩個小時──最多四個小時後,我就會回家,沒想到結果完全錯了。
那年我十八歲,當天稍早我先回到家,意外發現家裡來了一群阿姨,她們正忙著以香料、酥油、米和雞肉烹煮印度香飯。她們七嘴八舌的,我聽不出是誰先對我宣布,總之有人告訴我,我的媒妁婚姻顯然已經訂下了。我未來的丈夫是個鰥夫,他會給我媽一幢房子,從此以後我媽(扶養三個孩子的印度離婚婦女)再也不用煩惱財務問題了。他們你一言我一語地宣告了我的未來,聽起來像是一種解脫,也為我的人生翻開了新的篇章。 我快滿五歲時就來到美國,在這裡長大,但我一直知道以這種方式成婚是我的責任。我不知道那個訊息究竟是何時或以什麼方式灌輸給我的,但顯然那就是我的命運。我對母親百依百順,所以願意為她及家人那麼做,尤其是一想到她以移民的身分,帶我們來追尋美國夢,並為此做了種種犧牲,讓我更願意為她做「正確的事」。
儘管如此,私底下我仍然有著心願未了。於是,我轉頭向開明的舅舅札法求助。舅舅早先來到美國上大學,現在是帕羅奧圖(Palo Alto)某大藥廠的主管。他是我們家在商討婚姻時的男性代表,因為我父親早就離開我們了。我問舅舅:「他(新郎)知道我想上大學嗎?」當時我正在讀社區大學,並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入學延後一年。舅舅回答:「不知道,妳母親不讓我提起這件事,妳可以婚後再跟他討論。」
這番話的意思不斷在我的腦中翻攪,因為那表示我至少還要再延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上大學。根據傳統的媒妁婚約,我不能在婚前認識新郎,我們也許可以打招呼,或是在其他人的陪同下一起坐在同一個房間裡,但他不會知道我的人生目標,我也不會知道他的人生目標。告訴他我想做什麼,那太反常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考慮到這種情況,我試著說服舅舅,甚至哀求了一番。從那些阿姨的閒聊中,我知道新郎的家裡有管家、廚師,還有一個保母負責照顧他上一段婚姻留下的孩子,他住在附近山上的豪宅裡,所以肯定不是為了找我去幫忙家務而娶我。我相信,如果他事先知道我有意上大學,應該會答應讓我去接受教育。但是,如果我必須跟他慢慢培養關係,等到適當時機才提出求學的要求,結果如何就很難說了。而我在未經母親的許可下,自己取得延後入學柏克萊一年的資格,到時肯定也會失效了。而新郎會讓我至少繼續讀社區大學嗎?
在我重視的諸多事情之中,教育顯得很不同。在我身處的文化裡,教育往往是那些被期待要做出決策的男性的專利。但我也想獲得平等的立足點,接受教育,以便有能力主導自己的未來。
舅舅表示,不過那件事情已經談完了。我看得出來他站在我這邊,但他也無能為力。他說:「沒辦法做什麼。」 我一聽心亂如麻,原有的勇氣逐漸潰散。過了幾小時後,家裡那些鬧烘烘的活動結束了,客人皆已離去,但我還有一個孤注一擲的行動計畫正要登場。
我用一種誇張的語氣,告訴我媽我要離家出走了。接著,我開始把書本和衣物塞進紙箱裡,書的比重遠遠超過衣服,但沒放牙刷,反正那不重要,那些東西只是我做戲的道具。母親站在我的房間裡看著我時,我抗議道:「反正我只是產品,你們的交易少了我就無法成交!」我離家時堅稱:妳只要跟我保證,妳會先問他要不要讓我上大學就好了!
午後時分,在吃完蘋果炸餡餅和甜餅圈後,我抱著那個紙箱,拖著沉重的腳步,來到我就讀的德安扎社區大學(De Anza)打電話。
這時電話另一頭的母親已經氣急敗壞,講不出完整的句子,但嗓門還是很大。我們的對話就像聾子互相叫囂一樣,彼此都聽不到對方的說法。於是,我掛了電話,打電話給大我七歲的已婚姊姊。她提醒我:「媽說妳不回家的話,她會自殺。」那時我才意識到這件事情沒有那麼容易解決。不過,跟我姊講完電話後,我還是覺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