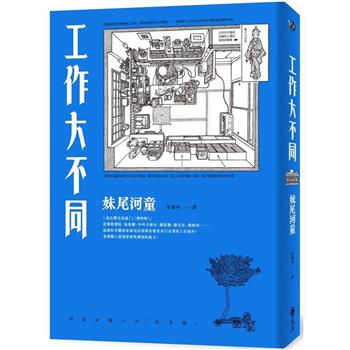加藤唐九郎的轆轤場
說到「加藤唐九郎先生」,在陶藝界簡直像神明般的存在;不過他倒是那種人家稱呼他為「唐九郎先生」也不以為意的人。
「那種稱人為『大師』的風潮我可是一點兒都不喜歡。個性特色的什麼都沒有。其實我是覺得,不用敬稱直接叫名字不是比較有力?但光這樣好像也不行,所以只要叫『唐九郎先生』就可以啦。」
一開始交談,不知不覺便忘了對方可是高齡八十八的長者。
曾有一段時期,他對電話的構造很感興趣,只要有關電話的事都想知道,徹徹底底調查過一番。
四年前文字處理機還頗為罕見的時代,他就已經購置了一台,而且玩得不亦樂乎。
有關他朝氣蓬勃、充滿好奇心的事蹟太多了。我明知這問題太過陳腐,但還是開口問問看了:
「請問您保持年輕的祕訣是什麼?」
「說我年輕,還不如說像個小孩吧。小孩對感興趣的事情不老愛問『為什麼?』,人長大後,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慢慢變少了哪。就算碰到不懂的事,也裝出一臉知道的樣子。這樣人很快就會變老。你在《藝術新潮》雜誌裡寫的那篇關於達文西的文章很有趣呢。我不知道他當時就已經接觸舞台布景的事,興趣可真廣泛。所以他也很年輕。達文西並不把藝術和科學分開思考,兩者都出自同一主幹。國家也一樣,政治、經濟、文化必須平衡發展才成;文化裡的藝術和科學也不能有所偏廢。」
「對了,聽說您已經參觀過『筑波科學萬國博覽會』,覺得如何呢?」
「那我就老實不客氣說了。如果仔細思考要如何讓大眾真正認識基礎科學,那科學博覽會實在沒啥意義呢。雖然影像等表現手法十分華麗眩目,的確達到了招攬觀眾的目的,但與其強調表面的成果,科學研究的過程、今後的發展方向等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也應該要告訴民眾。二十世紀都快結束了,但對於二十一世紀的走向卻完全沒有提及,實在是很遺憾呢。」
唐九郎先生提出了相當尖銳的意見。
「想要參觀工作場所啊。哪裡好呢?因為我燒陶的地方不只一個……。現在正在燒窯,那就去轆轤場好了。」
前往轆轤場之前先參觀了「陶藝紀念館」。展示室中央的櫃子裡擺了一個直徑六十公分的大盤子,白色的底色上頭畫了兩尾鯰魚,筆觸充滿力道。上面寫著創作於「大正七年」,這麼說來,是唐九郎先生二十歲時的作品了。從這件作品可以清楚知道,唐九郎先生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是位出眾的陶藝家。
「說到二十歲,聽說您那時學過小提琴……?」
「那時候為了認識歐洲,想說透過小提琴來實際體驗一下,應該是個不錯的方法。我的小提琴老師是德國人,所以也了解到德國人的精神和氣質。他的教法滿親切的,不過理論上的要求就很嚴格。就這樣邊理解箇中道理地一路學了下來。」
那時候唐九郎先生還信了基督教,認識井上藤藏牧師後在思想上受其相當影響,投入社會主義運動,度過了善感的青春時代。
「那時被警察逮捕過好幾次,關進拘留所,被視為異端份子或怪人之流的也習以為常了。連住附近的朋友都說:『那傢伙終於瘋了。』」
回顧當時的時代背景,正是處於經濟不景氣的谷底。唐九郎先生說:
「現在的思想還是一樣喔。」
接著話題轉到「權力的結構」,唐九郎先生不禁激動得咬牙切齒,假牙嘎吱作響,緊握拳頭敲著桌面說:
「權力創造不出作品來的。藝術不需要權力的光環。教育也是,問題在於作法。所謂教育並不是指書本,更不是指學校建築。有學歷和有學問根本是兩碼子事,真正學到手的才叫學問,而學歷這東西是不需要的。」
後來還談到他與畢卡索的交遊、訪問中國之旅等等,話題不限時空地飛縱交錯,酣暢淋漓。
聽人家說,他到現在讀書量依舊十分驚人。書庫裡一排排大型移動式書架,像個圖書館一樣。
唐九郎先生從三十六歲著手編著,花了七年光陰才完成人稱不朽名著的《原色陶器大辭典》共六卷,想來他從年輕時便是位努力鑽研學問的人。就算平時沒接觸陶藝,應該也有許多人從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年)的「永仁壺事件」而聽過陶藝家「加藤唐九郎」之名吧。那個壺當年被鑑定為「鎌倉時代古物」並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其實是二十三年前、唐九郎先生三十九歲時的作品,後來交給別人。唐九郎先生自己承認「的確是我做的」,成為喧騰一時的社會新聞。我印象很深刻,當時曾有「陶藝作品的價值應該依據年代或其他因素來決定?」的質疑。
我請唐九郎先生坐到轆轤前做個茶碗。轆轤一轉動,茶碗便在他手中逐漸隆起成形。
「轆轤的操作其實很簡單,大約就像學騎自行車的難度而已,稍做練習誰都能上手。困難的是入窯燒製。而用火就像遇上魔女一般,可是沒辦法讓你隨心所欲的。」
「出窯後的作品最後大多敲碎處理掉嗎?」
「是啊,因為我想應該能做出更好的來。但這不代表我追求的是高超的技術,因為有些就算燒得不好也能撼動人心。不過,好作品不容易做出來。所以才一直不斷敲碎毀掉。」
真令人折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