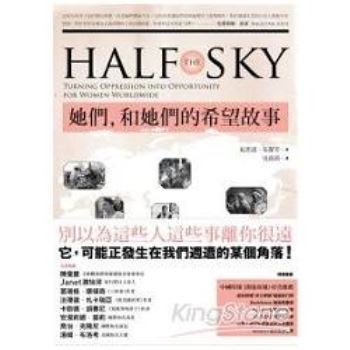女孩效應
要是沒有女人,有多少男人會是今日的模樣?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
──馬克.吐溫
絲瑞.拉思是名散發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烏溜溜的秀髮從淡褐色的圓潤臉龐滑落下來。處於人山人海街市當中的她,站在一台手推車旁邊,平靜、超然地訴說自己的故事。她經常把黑眼珠前方的頭髮撥開,這也許是不自覺的緊張動作,是唯一透露焦慮或創傷的訊息。然後她把手放下,口中娓娓道出她的漫長旅程,修長的手指在空中比畫揮動,呈現不協調的優雅。
拉思個子嬌小、骨架纖細,活潑美麗、善良愉悅,她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鮮明外向的個性有著天壤之別。當天空驟然下起一陣熱帶大雨,把我們淋得全身濕透,她只是開懷大笑,急忙把我們帶到一個鐵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響之際,她愉快地繼續述說自己的故事。然而對於一位柬埔寨的鄉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與討喜的個性是惹禍上身的天賜禮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與樂觀的自信,又加重了幾許危險性。
拉思十五歲時,家裡缺錢,於是她決定到泰國當洗碗工兩個月,幫忙負擔家計。父母擔心她的安危,但是拉思安排與四位朋友同行,她們也將在同一家泰式餐廳工作,於是父母放了心。人力仲介把她們帶入泰國內地,然後交給流氓幫派,幫派又把她們帶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拉思初次瞥見吉隆坡乾淨寬闊的大道與閃閃發亮的高樓大廈,包括當時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不禁嘆為觀止,覺得這個地方親切宜人、安全無虞。然而,歹徒把拉思和另外兩名女孩關進一間卡拉OK酒吧,那其實是一家妓院。大夥兒稱一名將近四十歲的流氓為「老大」,他接管這些女孩,表示他付了錢把她們買下來,現在她們得把這筆錢還清:「妳們非得給我好好努力賺錢不可,債還清了,我就把妳們送回家。」他一再保證她們若是乖乖合作,最後就會被釋放。
拉思明白自己落入什麼下場之後,晴天霹靂。老大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裡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打死不從,令客人大為火光。「於是老大發飆,甩我耳光,兩手交替著打。」她回憶道,口氣透著無可奈何的認命態度。「我臉上的傷痕過了兩個禮拜才好。」然後老大和其他幫派份子輪番強暴她,用拳頭揍她。
「妳要是不乖乖服務客人,」老大一邊揍她一邊說:「我們就把妳揍死,妳想這樣嗎?」於是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嗚咽啜泣,拒絕主動合作。老大強迫她吞下一顆藥丸,幫派份子稱為「快樂丸」或「搖頭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麼,但是快樂丸讓她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不住搖頭晃腦,讓她昏昏欲睡、幸福快樂、任人擺佈。藥效過了之後,拉思又開始傷心流淚,而且不夠乖巧聽話,因為他們要她對所有客人發出燦爛的笑容,但是她做不到,於是老大說不再把時間浪費在她身上──她要嘛就乖乖聽話,否則就把她幹掉。拉思只好讓步。所有女孩全年無休地被迫在妓院工作,一天工作長達十五小時。她們平時不准穿衣服,這樣比較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費或錢財藏在身上,她們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保險套。她們被打得悽慘,直到學會看到客人時保持面帶笑容、佯裝開心,因為男人看到紅著眼睛、形容枯槁的女孩,可不會付那麼多錢跟她們上床。這些女孩從來不准上街,工作也從來沒拿到一分錢。
「他們只給我們食物吃,但是給的不多,因為客人不喜歡胖女孩。」拉思說。女孩們在監督之下,由巴士往返載送於妓院與公寓之間,她們有十幾個住在那棟公寓的第十層樓,大門由外頭反鎖。有一天晚上,幾個女孩到陽台上,把一條五英寸寬的長木板從曬衣服的掛物架上撬鬆,然後架往距離十二英尺遠的隔壁棟陽台上。木板晃動得十分厲害,但是拉思絕望至極,打算孤注一擲,於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吋一吋地往前挪動。
「我們有四個人這麼做,」她說:「其他人怕得不敢嘗試,因為木板真的晃得厲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裡我更害怕。我們覺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裡好。反正留下來,最後也是死路一條。」
到了隔壁棟陽台時,女孩們大聲敲擊窗戶,吵醒了一臉吃驚的住戶。她們不會說馬來語,因此不太能跟他溝通,但是住戶讓她們進入公寓,然後從前門出去。女孩們搭乘電梯下樓,在寂靜的街道上四處遊走,直到找到警察局進去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們趕走,後來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她們。拉思在馬來西亞嚴峻的反移民法之下坐牢一年,接著,她照理會遭到遣返回國。馬來西亞警察把她載到泰國邊界時,她以為警察是護送她回家,結果卻是再度賣給人口販子,人口販子又把她賣給一家泰國妓院。
拉思所歷經的這段波折,讓我們瞥見世界許多地方的婦女所慣常遭受的殘暴對待,這樣的暴行慢慢受到矚目,公認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人權問題之一。
然而,這項議題所牽涉到的問題,幾乎還沒有出現在全球議程裡。的確,我們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報導國際事務時,無法想像有一天會撰寫這本書。我們當時深信,會讓人眉頭深鎖的外交政策問題應該是崇高複雜的,比如禁止核武擴散。在當時,很難想像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憂慮於孕產婦死亡率或女性外陰殘割問題。當時,對於婦女的迫害是邊緣議題,是那種女童軍認為值得而去募款的目標。我們寧可探討深奧難懂的「嚴肅問題」。
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一起擔任《紐約時報》記者時,自身覺醒之旅的產物,而該旅程的第一個里程碑位於中國。潔芳是生長於紐約市的華裔美國人,思道是在美國奧勒崗州岩希爾鎮附近一座綿羊與櫻桃農場長大的俄勒岡州人。我們結婚後搬到中國,七個月後竟然站在天安門廣場邊緣,目睹中國人民解放軍向爭取民主的抗議示威者發射自動武器,這次的大屠殺奪走了四百到八百人的性命,震驚了全世界。那是當年最為重大的人權事件,似乎是所能想像中最為震撼的人權侵犯。
隔年,我們發現了一項人口統計學研究,雖不起眼但相當嚴謹,概述了某個人權違反情況,奪走的性命比天安門事件多出幾十萬人。這則研究發現中國每年有三萬九千名女嬰夭折,因為父母給予女嬰的醫療照護與關照,遠不及男嬰所得到的──而這只是生命第一年的情況。中國計畫生育協會的政府官員李宏規如此解釋:「如果男嬰生病,父母可能會立刻把他帶去醫院,但如果是女嬰生病,父母可能會說:『這個嘛,看她明天會不會好一點。』」這些女嬰原本可以救活,結果現在每週的女嬰死亡人數,等同於天安門事件的抗議者死亡人數。那些中國女嬰從來沒有站上新聞的任何篇幅。我們開始思考主要報導取向是否偏頗。
類似的情況也在其他國家浮現,尤其是南非和伊斯蘭教世界。在印度,因為嫁妝不夠而處罰媳婦或是為了讓男人再娶而殺滅妻子的「火燒新娘」,大約是每兩個小時發生一起,但是這種消息很少成為新聞。在巴基斯坦的姊妹城伊斯蘭馬巴德與拉瓦爾品第,光是過去九年來,就有五千名婦女因為被認為違抗不從,而被家人或姻親浸入煤油後點火焚燒──或者被硫酸燒灼,後者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況也許還更悲慘。要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以這種速率把婦女活活燒死,可以想像抗議之聲會有多麼強烈。然而政府沒有直接牽涉,人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一位重要的異議份子在中國遭逮捕時,我們會寫一篇頭版新聞;而十萬名女孩常態性地遭到綁架及非法賣到妓院,我們甚至不認為這是新聞。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記者往往擅於報導特定日子發生的事件,卻疏於報導每日常態性發生的事情──比如婦女每日遭受的殘暴對待。疏忽這個主題並不是只有我們記者,美國對外援助中,特別針對婦女的不到百分之一。
充滿熱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發展一套性別不平等的評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們性別不平等所包含的風險。「超過一億名婦女失蹤。」沈恩在一九九○年刊載於《紐約書評》的一篇經典之作中如此寫道,開創了一片嶄新的研究領域。沈恩表示,在正常情況下,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還長,因此,世界許多地方通常女性人數多於男性。就連在貧窮地區,比如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許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還多。然而在極為重男輕女的地區,婦女從人間蒸發了。就中國的總人口數來看,每一百名女性相對於一百○七名男性(而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也是相對於一百○七名男性,巴基斯坦則是一百一十一名男性。這跟生物學無關,的確,在印度西南方的喀拉拉邦,女性的教育機會與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其女性多於男性,就跟美國相同。
沈恩教授發現,上述人口性別比例的含意,即今日全球有一億零七百萬的女性行蹤不明。後續研究所計算的「失蹤女性」人數稍有不同,介於六千萬到一億零一百萬之間。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兩百萬名女孩因為性別歧視而消失。
西方國家有其性別問題,但在富裕國家,性別歧視老是跟薪資不平等、體育隊伍資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歡的碰觸有關;而在世界許多地方,性別歧視卻是致命的。比如在印度,母親帶著女兒去接種疫苗的比例少於兒子──光是這一點,就要為印度五分之一的失蹤女性負責。研究發現,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嚴重於送去醫院的男孩時,才會被帶入醫院。整體而言,印度一至五歲的女孩跟同年紀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百分之五十;最保守的估計是,每四分鐘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於性別歧視。
一位身材魁梧、留著一臉落腮鬍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經跟我們表示:他的妻兒都生了病,他要妻兒都存活下來,但是孰輕孰重相當清楚:兒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寶,而妻子是可以取代的,於是他只為兒子買藥。「她總是大小病不斷,」他冷冷地評論自己的妻子,「所以幫她買藥不值得。」
現代化及科技發達,有可能加重這樣的歧視。從一九九○年代開始,超音波儀器普及醫院,讓孕婦能夠知道胎兒的性別──如果發現是女的,則會墮胎。在中國福建省,一名農夫談到超音波時相當激動,咆哮著說:「這樣我們就再也不用生女兒了!」
中國和印度為了防止性別選擇性墮胎,現在禁止醫生及超音波技術人員告知孕婦胎兒的性別,然而這個解決辦法並不完善。研究顯示,當父母被禁止選擇性地把女胎墮掉時,就有更多的女兒在嬰兒時期夭折。母親不會刻意殺死不得不產下的女嬰,但是在照顧方面卻馬虎草率。伯朗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以下令人心痛的折衷之道:平均而言,允許選擇性墮胎一百名女胎,就能避免十五名女嬰夭折。
女孩虐待事件的全球統計數字高得令人麻木。看來,過去五十年來遭到殺害的女孩,比死於二十世紀所有戰鬥的男性還多;正因為她們是女的。任何一個十年當中,在常態性的「性別屠殺」中喪命的女孩人數,遠多於二十世紀所有大屠殺中慘遭殺害的人數。
十九世紀,主要的道德挑戰是奴役制度;二十世紀,則是對於極權主義的抗爭。我們相信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道德挑戰,將會是全球對於性別平等的奮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賣到泰國妓院後,妓院老闆並沒有毆打她,也沒有時時監控她,因此兩個月之後,她逃了出去,憑自己的力量回到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國後遇到一位社工人員,而接觸到幫助遭非法販賣女孩重建新生命的救援團體,亦即「美國柬埔寨援助機構」。他們撥出捐贈基金裡的四百美元,買了一個小推車和些許商品為起步,讓拉思開始成為街頭小販。在波貝(Poipet)這個邊界小鎮,拉思在泰國及柬埔寨海關之間的露天場地找到一塊好地方,跨越泰國及柬埔寨邊界的旅客都會走過這片跟足球場大小相當的長條地帶,兩邊沿途都是販賣飲料、點心和紀念品的小販。
拉思在小推車裡擺上琳瑯滿目的商品,包括襯衫和帽子、訂製珠寶、筆記本、筆及小玩具。現在,她甜美的長相及外向的個性開始發揮作用,把她轉變為銷售力一流的售貨員。她努力攢錢,投資購買新貨品,生意變得興榮旺盛,有辦法贍養父母及兩個妹妹。她結婚了,育有一兒,也開始為他準備教育經費。
拉思的最終勝利,提醒我們女孩要是得到機會,不管是接受教育或是微型貸款,她們就不只是廉價裝飾或奴隸;她們之中有許多人是能夠經營事業的。請今天就去跟拉思聊聊天(在你買了那頂帽子之後),你會發現她散發自信,因為她賺取可觀的收入,能夠為她的妹妹和小兒子提供更好的未來。本書的許多故事叫人看得心痛,但是以下這個真理請銘記在心:女人不是禍水,而是解決之道。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劇,而是契機。
這就是我們拜訪潔芳祖先的村莊時所記取的教訓。那座村莊位於中國南方,在稻田之間、泥路的盡頭。多年來我們定期踩著廣東台山地區的泥土小徑前往順水村,這是潔芳父系祖父生長的村子。傳統上,中國是較為壓抑及扼殺女性的地方之一,我們可以在潔芳的家族歷史中看到這種情況的跡象。的確,我們在第一次拜訪時,不經意發現了一個家族祕密:原來潔芳還有一位長久失聯的繼祖母。潔芳的祖父帶著這位第一任妻子前往美國,但是所生的孩子都是女兒,於是祖父休了她,把她帶回順水村,另在當地娶了一名更年輕的第二任妻子,再帶她前往美國。年輕這位就是潔芳的祖母,她不負眾望生下一名兒子──潔芳的父親,於是前妻及幾個女兒就從家族記憶中抹去。
我們每一次探索順水村和周遭的村落時,都有一件事情讓我們百思不解:年輕婦女都到哪裡去了?年輕男性不是在稻田間揮汗如雨地辛勤耕種,就是在樹蔭下懶洋洋地幫自己搧風,但是年輕婦女和女孩卻幾乎不見蹤影。當時,廣東省是中國經濟爆發的中心,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各處成立,我們踏進這些工廠時,終於見到她們的芳蹤。這些工廠生產的鞋子、玩具和襯衫充斥美國購物商城,帶來的經濟成長率可以說是史上前所未見──也締造了反貧窮計畫中最有效的紀錄。這些工廠彷彿是雌蜂群聚的嘈雜蜂窩;中國沿海地區的工廠中,組裝生廠線上的員工有八成是女性,而在東亞的製造業生產線,女性至少占七成。亞洲的經濟爆發,主要是大幅賦予女性經濟權的自然結果。「她們手指較小,比較適合縫紉。」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廠的經理對我們解釋。「她們乖巧順從,工作比男人還認真努力,」一家玩具工廠的老闆表示:「而且我們可以付她們較低的工資。」
婦女的確是該地區發展策略的關鍵。詳細研究東亞蓬勃發展的經濟學家注意到一個普遍的模式,這些年輕女性以前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微不足道,現在國家把她們注入正式經濟,大幅提升勞動力。基本的處方就是緩和壓制,不只讓男孩接受教育,也讓教育普及於女孩,並且讓女性有搬遷到城市及在工廠工作的自由,然後因為晚婚和減少生育而受益於「人口紅利時期」。同時,婦女還會資助晚輩親人的教育,把薪資的一部分用來儲蓄而提升國民儲蓄率。這樣的模式稱為「女孩效應」。由於女性染色體的XX組成,這也稱為「雙X解方」。
要是沒有女人,有多少男人會是今日的模樣?少之又少,先生,少之又少啊!
──馬克.吐溫
絲瑞.拉思是名散發自信的柬埔寨少女,她烏溜溜的秀髮從淡褐色的圓潤臉龐滑落下來。處於人山人海街市當中的她,站在一台手推車旁邊,平靜、超然地訴說自己的故事。她經常把黑眼珠前方的頭髮撥開,這也許是不自覺的緊張動作,是唯一透露焦慮或創傷的訊息。然後她把手放下,口中娓娓道出她的漫長旅程,修長的手指在空中比畫揮動,呈現不協調的優雅。
拉思個子嬌小、骨架纖細,活潑美麗、善良愉悅,她不起眼的瘦弱身材,跟她鮮明外向的個性有著天壤之別。當天空驟然下起一陣熱帶大雨,把我們淋得全身濕透,她只是開懷大笑,急忙把我們帶到一個鐵皮屋下躲雨。大雨在上方叮咚作響之際,她愉快地繼續述說自己的故事。然而對於一位柬埔寨的鄉村少女而言,拉思迷人的外貌與討喜的個性是惹禍上身的天賜禮物,而她信任他人的天性與樂觀的自信,又加重了幾許危險性。
拉思十五歲時,家裡缺錢,於是她決定到泰國當洗碗工兩個月,幫忙負擔家計。父母擔心她的安危,但是拉思安排與四位朋友同行,她們也將在同一家泰式餐廳工作,於是父母放了心。人力仲介把她們帶入泰國內地,然後交給流氓幫派,幫派又把她們帶到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拉思初次瞥見吉隆坡乾淨寬闊的大道與閃閃發亮的高樓大廈,包括當時世界最高的雙子星大樓,不禁嘆為觀止,覺得這個地方親切宜人、安全無虞。然而,歹徒把拉思和另外兩名女孩關進一間卡拉OK酒吧,那其實是一家妓院。大夥兒稱一名將近四十歲的流氓為「老大」,他接管這些女孩,表示他付了錢把她們買下來,現在她們得把這筆錢還清:「妳們非得給我好好努力賺錢不可,債還清了,我就把妳們送回家。」他一再保證她們若是乖乖合作,最後就會被釋放。
拉思明白自己落入什麼下場之後,晴天霹靂。老大把她鎖進一個房間,裡面的客人逼她性交,她打死不從,令客人大為火光。「於是老大發飆,甩我耳光,兩手交替著打。」她回憶道,口氣透著無可奈何的認命態度。「我臉上的傷痕過了兩個禮拜才好。」然後老大和其他幫派份子輪番強暴她,用拳頭揍她。
「妳要是不乖乖服務客人,」老大一邊揍她一邊說:「我們就把妳揍死,妳想這樣嗎?」於是拉思不再反抗,只是嗚咽啜泣,拒絕主動合作。老大強迫她吞下一顆藥丸,幫派份子稱為「快樂丸」或「搖頭丸」。她不太清楚那是什麼,但是快樂丸讓她有一個小時的時間不住搖頭晃腦,讓她昏昏欲睡、幸福快樂、任人擺佈。藥效過了之後,拉思又開始傷心流淚,而且不夠乖巧聽話,因為他們要她對所有客人發出燦爛的笑容,但是她做不到,於是老大說不再把時間浪費在她身上──她要嘛就乖乖聽話,否則就把她幹掉。拉思只好讓步。所有女孩全年無休地被迫在妓院工作,一天工作長達十五小時。她們平時不准穿衣服,這樣比較不容易逃跑,或是把小費或錢財藏在身上,她們也不准要求客人使用保險套。她們被打得悽慘,直到學會看到客人時保持面帶笑容、佯裝開心,因為男人看到紅著眼睛、形容枯槁的女孩,可不會付那麼多錢跟她們上床。這些女孩從來不准上街,工作也從來沒拿到一分錢。
「他們只給我們食物吃,但是給的不多,因為客人不喜歡胖女孩。」拉思說。女孩們在監督之下,由巴士往返載送於妓院與公寓之間,她們有十幾個住在那棟公寓的第十層樓,大門由外頭反鎖。有一天晚上,幾個女孩到陽台上,把一條五英寸寬的長木板從曬衣服的掛物架上撬鬆,然後架往距離十二英尺遠的隔壁棟陽台上。木板晃動得十分厲害,但是拉思絕望至極,打算孤注一擲,於是跨坐在木板上,一吋一吋地往前挪動。
「我們有四個人這麼做,」她說:「其他人怕得不敢嘗試,因為木板真的晃得厲害。我也很害怕,不敢往下看,但是留在那裡我更害怕。我們覺得就算摔下去死掉,也比留在那裡好。反正留下來,最後也是死路一條。」
到了隔壁棟陽台時,女孩們大聲敲擊窗戶,吵醒了一臉吃驚的住戶。她們不會說馬來語,因此不太能跟他溝通,但是住戶讓她們進入公寓,然後從前門出去。女孩們搭乘電梯下樓,在寂靜的街道上四處遊走,直到找到警察局進去求救。警察先是想把她們趕走,後來以非法移民的罪名逮捕她們。拉思在馬來西亞嚴峻的反移民法之下坐牢一年,接著,她照理會遭到遣返回國。馬來西亞警察把她載到泰國邊界時,她以為警察是護送她回家,結果卻是再度賣給人口販子,人口販子又把她賣給一家泰國妓院。
拉思所歷經的這段波折,讓我們瞥見世界許多地方的婦女所慣常遭受的殘暴對待,這樣的暴行慢慢受到矚目,公認是本世紀最主要的人權問題之一。
然而,這項議題所牽涉到的問題,幾乎還沒有出現在全球議程裡。的確,我們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報導國際事務時,無法想像有一天會撰寫這本書。我們當時深信,會讓人眉頭深鎖的外交政策問題應該是崇高複雜的,比如禁止核武擴散。在當時,很難想像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憂慮於孕產婦死亡率或女性外陰殘割問題。當時,對於婦女的迫害是邊緣議題,是那種女童軍認為值得而去募款的目標。我們寧可探討深奧難懂的「嚴肅問題」。
因此,這本書是我們兩人一起擔任《紐約時報》記者時,自身覺醒之旅的產物,而該旅程的第一個里程碑位於中國。潔芳是生長於紐約市的華裔美國人,思道是在美國奧勒崗州岩希爾鎮附近一座綿羊與櫻桃農場長大的俄勒岡州人。我們結婚後搬到中國,七個月後竟然站在天安門廣場邊緣,目睹中國人民解放軍向爭取民主的抗議示威者發射自動武器,這次的大屠殺奪走了四百到八百人的性命,震驚了全世界。那是當年最為重大的人權事件,似乎是所能想像中最為震撼的人權侵犯。
隔年,我們發現了一項人口統計學研究,雖不起眼但相當嚴謹,概述了某個人權違反情況,奪走的性命比天安門事件多出幾十萬人。這則研究發現中國每年有三萬九千名女嬰夭折,因為父母給予女嬰的醫療照護與關照,遠不及男嬰所得到的──而這只是生命第一年的情況。中國計畫生育協會的政府官員李宏規如此解釋:「如果男嬰生病,父母可能會立刻把他帶去醫院,但如果是女嬰生病,父母可能會說:『這個嘛,看她明天會不會好一點。』」這些女嬰原本可以救活,結果現在每週的女嬰死亡人數,等同於天安門事件的抗議者死亡人數。那些中國女嬰從來沒有站上新聞的任何篇幅。我們開始思考主要報導取向是否偏頗。
類似的情況也在其他國家浮現,尤其是南非和伊斯蘭教世界。在印度,因為嫁妝不夠而處罰媳婦或是為了讓男人再娶而殺滅妻子的「火燒新娘」,大約是每兩個小時發生一起,但是這種消息很少成為新聞。在巴基斯坦的姊妹城伊斯蘭馬巴德與拉瓦爾品第,光是過去九年來,就有五千名婦女因為被認為違抗不從,而被家人或姻親浸入煤油後點火焚燒──或者被硫酸燒灼,後者這種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情況也許還更悲慘。要是巴基斯坦或印度政府以這種速率把婦女活活燒死,可以想像抗議之聲會有多麼強烈。然而政府沒有直接牽涉,人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一位重要的異議份子在中國遭逮捕時,我們會寫一篇頭版新聞;而十萬名女孩常態性地遭到綁架及非法賣到妓院,我們甚至不認為這是新聞。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記者往往擅於報導特定日子發生的事件,卻疏於報導每日常態性發生的事情──比如婦女每日遭受的殘暴對待。疏忽這個主題並不是只有我們記者,美國對外援助中,特別針對婦女的不到百分之一。
充滿熱忱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沈恩(Amartya Sen),發展一套性別不平等的評估方法,深切地提醒我們性別不平等所包含的風險。「超過一億名婦女失蹤。」沈恩在一九九○年刊載於《紐約書評》的一篇經典之作中如此寫道,開創了一片嶄新的研究領域。沈恩表示,在正常情況下,女性的壽命比男性還長,因此,世界許多地方通常女性人數多於男性。就連在貧窮地區,比如大部分的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許多地方,女性也比男性還多。然而在極為重男輕女的地區,婦女從人間蒸發了。就中國的總人口數來看,每一百名女性相對於一百○七名男性(而新生兒的男女比例差距更大);印度也是相對於一百○七名男性,巴基斯坦則是一百一十一名男性。這跟生物學無關,的確,在印度西南方的喀拉拉邦,女性的教育機會與平等程度居印度之冠,其女性多於男性,就跟美國相同。
沈恩教授發現,上述人口性別比例的含意,即今日全球有一億零七百萬的女性行蹤不明。後續研究所計算的「失蹤女性」人數稍有不同,介於六千萬到一億零一百萬之間。每一年,全球至少又有兩百萬名女孩因為性別歧視而消失。
西方國家有其性別問題,但在富裕國家,性別歧視老是跟薪資不平等、體育隊伍資金不足,或是上司不令人喜歡的碰觸有關;而在世界許多地方,性別歧視卻是致命的。比如在印度,母親帶著女兒去接種疫苗的比例少於兒子──光是這一點,就要為印度五分之一的失蹤女性負責。研究發現,一般而言,女孩的病情唯有嚴重於送去醫院的男孩時,才會被帶入醫院。整體而言,印度一至五歲的女孩跟同年紀的男孩相比,其死亡的可能性多了百分之五十;最保守的估計是,每四分鐘就有一名印度小女孩死於性別歧視。
一位身材魁梧、留著一臉落腮鬍的阿富汗人希丹夏曾經跟我們表示:他的妻兒都生了病,他要妻兒都存活下來,但是孰輕孰重相當清楚:兒子是必不可少的珍寶,而妻子是可以取代的,於是他只為兒子買藥。「她總是大小病不斷,」他冷冷地評論自己的妻子,「所以幫她買藥不值得。」
現代化及科技發達,有可能加重這樣的歧視。從一九九○年代開始,超音波儀器普及醫院,讓孕婦能夠知道胎兒的性別──如果發現是女的,則會墮胎。在中國福建省,一名農夫談到超音波時相當激動,咆哮著說:「這樣我們就再也不用生女兒了!」
中國和印度為了防止性別選擇性墮胎,現在禁止醫生及超音波技術人員告知孕婦胎兒的性別,然而這個解決辦法並不完善。研究顯示,當父母被禁止選擇性地把女胎墮掉時,就有更多的女兒在嬰兒時期夭折。母親不會刻意殺死不得不產下的女嬰,但是在照顧方面卻馬虎草率。伯朗大學的發展經濟學家錢楠筠(Nancy Qian)量化了以下令人心痛的折衷之道:平均而言,允許選擇性墮胎一百名女胎,就能避免十五名女嬰夭折。
女孩虐待事件的全球統計數字高得令人麻木。看來,過去五十年來遭到殺害的女孩,比死於二十世紀所有戰鬥的男性還多;正因為她們是女的。任何一個十年當中,在常態性的「性別屠殺」中喪命的女孩人數,遠多於二十世紀所有大屠殺中慘遭殺害的人數。
十九世紀,主要的道德挑戰是奴役制度;二十世紀,則是對於極權主義的抗爭。我們相信在邁入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道德挑戰,將會是全球對於性別平等的奮力追求。
拉思再度被賣到泰國妓院後,妓院老闆並沒有毆打她,也沒有時時監控她,因此兩個月之後,她逃了出去,憑自己的力量回到柬埔寨。
拉思回到祖國後遇到一位社工人員,而接觸到幫助遭非法販賣女孩重建新生命的救援團體,亦即「美國柬埔寨援助機構」。他們撥出捐贈基金裡的四百美元,買了一個小推車和些許商品為起步,讓拉思開始成為街頭小販。在波貝(Poipet)這個邊界小鎮,拉思在泰國及柬埔寨海關之間的露天場地找到一塊好地方,跨越泰國及柬埔寨邊界的旅客都會走過這片跟足球場大小相當的長條地帶,兩邊沿途都是販賣飲料、點心和紀念品的小販。
拉思在小推車裡擺上琳瑯滿目的商品,包括襯衫和帽子、訂製珠寶、筆記本、筆及小玩具。現在,她甜美的長相及外向的個性開始發揮作用,把她轉變為銷售力一流的售貨員。她努力攢錢,投資購買新貨品,生意變得興榮旺盛,有辦法贍養父母及兩個妹妹。她結婚了,育有一兒,也開始為他準備教育經費。
拉思的最終勝利,提醒我們女孩要是得到機會,不管是接受教育或是微型貸款,她們就不只是廉價裝飾或奴隸;她們之中有許多人是能夠經營事業的。請今天就去跟拉思聊聊天(在你買了那頂帽子之後),你會發現她散發自信,因為她賺取可觀的收入,能夠為她的妹妹和小兒子提供更好的未來。本書的許多故事叫人看得心痛,但是以下這個真理請銘記在心:女人不是禍水,而是解決之道。女孩的苦境不再是悲劇,而是契機。
這就是我們拜訪潔芳祖先的村莊時所記取的教訓。那座村莊位於中國南方,在稻田之間、泥路的盡頭。多年來我們定期踩著廣東台山地區的泥土小徑前往順水村,這是潔芳父系祖父生長的村子。傳統上,中國是較為壓抑及扼殺女性的地方之一,我們可以在潔芳的家族歷史中看到這種情況的跡象。的確,我們在第一次拜訪時,不經意發現了一個家族祕密:原來潔芳還有一位長久失聯的繼祖母。潔芳的祖父帶著這位第一任妻子前往美國,但是所生的孩子都是女兒,於是祖父休了她,把她帶回順水村,另在當地娶了一名更年輕的第二任妻子,再帶她前往美國。年輕這位就是潔芳的祖母,她不負眾望生下一名兒子──潔芳的父親,於是前妻及幾個女兒就從家族記憶中抹去。
我們每一次探索順水村和周遭的村落時,都有一件事情讓我們百思不解:年輕婦女都到哪裡去了?年輕男性不是在稻田間揮汗如雨地辛勤耕種,就是在樹蔭下懶洋洋地幫自己搧風,但是年輕婦女和女孩卻幾乎不見蹤影。當時,廣東省是中國經濟爆發的中心,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各處成立,我們踏進這些工廠時,終於見到她們的芳蹤。這些工廠生產的鞋子、玩具和襯衫充斥美國購物商城,帶來的經濟成長率可以說是史上前所未見──也締造了反貧窮計畫中最有效的紀錄。這些工廠彷彿是雌蜂群聚的嘈雜蜂窩;中國沿海地區的工廠中,組裝生廠線上的員工有八成是女性,而在東亞的製造業生產線,女性至少占七成。亞洲的經濟爆發,主要是大幅賦予女性經濟權的自然結果。「她們手指較小,比較適合縫紉。」一家女用手提包工廠的經理對我們解釋。「她們乖巧順從,工作比男人還認真努力,」一家玩具工廠的老闆表示:「而且我們可以付她們較低的工資。」
婦女的確是該地區發展策略的關鍵。詳細研究東亞蓬勃發展的經濟學家注意到一個普遍的模式,這些年輕女性以前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微不足道,現在國家把她們注入正式經濟,大幅提升勞動力。基本的處方就是緩和壓制,不只讓男孩接受教育,也讓教育普及於女孩,並且讓女性有搬遷到城市及在工廠工作的自由,然後因為晚婚和減少生育而受益於「人口紅利時期」。同時,婦女還會資助晚輩親人的教育,把薪資的一部分用來儲蓄而提升國民儲蓄率。這樣的模式稱為「女孩效應」。由於女性染色體的XX組成,這也稱為「雙X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