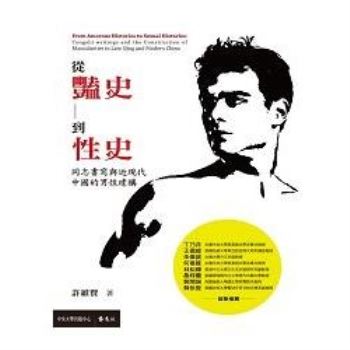程蝶衣/張國榮:優伶/幽靈─再現等於消失
歷史與京劇《霸王別姬》的主題是一個女人(妃妾)對另一個男人(帝王)的絕對忠誠和奉獻,李碧華把它重寫成是一個現實生活中扮演虞姬的「(假)女人」對一個扮演霸王的男伶的忠誠和背叛,進一步把它置換成兩個男伶對京劇藝術的忠誠和背叛。陳凱歌則在李碧華的基礎上,突出菊仙的救贖性,展示了「男/女」的絕對忠誠和「男/男」的絕對背叛,重複了異性戀霸權的思維邏輯。《霸王別姬》無論在歷史,或京戲舞台上,它本來就是異性戀的經典模範版本,主題不外強調女人對男人的從一而終─「忠誠」是其亙古不變的教義。但京劇「男扮女裝」的表演方式,讓這個牢固不破的主題,在後人看來有了遐想的空間。在李碧華的「女性自戀」鏡像裡,它被改寫成是一個「(假)女人」對另一個男人的不得善終─「背叛」是小說一以貫之的命題,「文化自戀」被合法化成一種邊緣敘事,對抗國族的男性中心主義,同性愛敘事在那裡只是要達到消解國族話語的手段。陳凱歌以他的「男性依戀」,附著於國族的神話和歷史,雖然企圖打破了這個自戀鏡像,但小說《霸王別姬》裡國族歷史文化對傳統京劇藝術的改寫和否定,很多時候被陳凱歌倒轉回來,解釋成是蝶衣對小樓發生情感衝突的根源。
這一切導致蝶衣對小樓的欲望,不斷在這塊四面楚歌的歷史鏡像上無所遁形,殘存在敘事者和大部分觀者意識下的只是對同性愛的恐懼。飾演程蝶衣的一代香港巨星張國榮,他正是在世紀末的媒體聚焦下讓自己的同性愛傾向通過扮演一個優伶「現身」(come out)。廖炳惠在張國榮2004年自盡後重看《霸王別姬》,他覺得程蝶衣這個角色似乎早已預設張國榮在日後生活現實中所顯現的三角關係及其自我毀滅意志。姑且不論張國榮的感情是否受困於廖炳惠所言之鑿鑿的「三角關係」,僅就張國榮的同志身分而言,《霸王別姬》的敘事倒是預先書寫了世紀末巨星的預知死亡紀事。張國榮在生前的一場講稿透露,電影《霸王別姬》的結局不同於原著,包括程蝶衣的自盡,是他和張豐毅二人構思出來的(張國榮 2007: 30);張國榮之所以安排蝶衣死亡,他的解釋概括下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虞姬個性執著,要死在霸王面前;其二,蝶衣想以自殺來完成原著故事的情節;其三,蝶衣不能接受自己和霸王的年華老去,當他發現在現實生活裡,他與師哥沒有了以往那種親密的感覺,他寧可選擇以虞姬來結束他的生命,做一場真正的《霸王別姬》。除了第二個原因是電影藝術效果上的考量,第一個和第三個原因顯而易見非常貼近張國榮最後選擇自殺的心理狀態,可見張國榮的自盡在當初處理《霸王別姬》的結局時就埋下了伏筆。這份講稿更重要的是洩露了張國榮在參演《霸王別姬》時,所遭受到的極度壓抑狀態:
陳凱歌改編的電影《霸王別姬》,卻充滿了極端的「恐同意識」,扭曲了同性戀獨立自主的選擇意向……我認為導演陳凱歌的取鏡很壓抑,過分壓抑……陳凱歌在電影裡一直不想清楚表明兩個男人的感情,而借鞏俐(筆者按:飾菊仙)來平衡故事裡同性關係的情節,這便提升了鞏俐在電影裡的地位。所以,作為一個演員,我只有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對同性那份義無反顧的堅持,借著適當的眼神和動作,傳遞給觀眾……但在拍攝過程中,作為一個演員,我的演繹必得平衡導演對同性戀取材的避忌……(張國榮 2007: 32-33)二十世紀末的罔兩主體在《霸王別姬》裡是以程蝶衣/張國榮,這兩個「優伶/藝人」的職業身分現身,他們都可被視為是晚清豔史脈絡下的《品花寶鑑》杜琴言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投胎轉世,一個投生於電影小說,另一個誕生於演藝界。程蝶衣生不逢時,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歷史把他打入牛馬鬼神的行列。即使革命還沒來到,段小樓新婚之夜,程蝶衣早已預感自己只是個「老了的小鬼」(李碧華 2006: 143)。十九世紀的優伶,投胎來到二十世紀不上五十年,已經是「幽靈」了,而且還是「蒼老的幽靈」。張國榮在二十世紀末要以年輕的肉身擔當扮演這一具「蒼老的幽靈」,其藝術的高難度可想而知。幸好張國榮是一名同志,投入角色不會太困難。但導演取鏡時卻刻意淡化了其中的同性愛再現政治,又在導演/編劇以「女人彩妝」的嚴格規訓下,張國榮的同性愛表演在主流觀眾眼中,很可能只能越顯得像一個小女人那樣小打小鬧,並沒有如張國榮所以為的「或許我的確是顛覆了《霸王別姬》這套電影的演繹」(張國榮 2007: 32)。況且1990年代初張國榮還未宣布「出櫃」,張國榮在《霸王別姬》的整個扮演,只變成了一個極度曲折和艱難的「現身」演習而已。17 雖然電影在萬眾矚目下開拍和上映,可是大部分普通的港台觀眾不想看到什麼同性愛,他們只看到一個現代香港的優伶如何不可思議糾纏上一個其貌不揚的大陸演員張豐毅。大陸的普通老百姓更看不到電影裡有什麼同性愛,它不過是一個演戲入魔的舊社會戲子愛上戲裡的男主角;而這一切大陸人/香港人/台灣人看不到或不願看到的,西方學者們卻自認看到了,但他們更多看到的似乎又只是同性愛的東方主義景觀,小說電影裡的中國歷史在某些論者的詮釋下全部變成同性愛主題的注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利用來說明更嚴肅的什麼?似乎程蝶衣/張國榮從幕前到幕後所實實在在面臨四面楚歌的同志再現/生存問題都是次要問題。一些西方學者用它來診斷中國革命歷史的病態和變態(張高山 2004: 146-149)。
台灣學者廖炳惠利用它來說明台灣、香港和大陸三個地區所構成的緊張關係,台灣像個同性戀者(蝶衣)曾經一心一意想與大陸師兄(小樓)門戶相通,卻被迫於情勢而獨立門戶,香港就如一個煙花女(菊仙)因不經意的誓約,而導致被大陸明媒正娶(廖炳惠 2004: 35)。18 有些大陸學者卻利用它來說明第五代導演如何崇洋媚外進行東方主義和全球化的勾結。香港作家梁秉鈞利用它來闡釋香港如何在大中國導演的掌鏡下,曖昧的香港被邊緣化以至成了一個不能表白自我的主體(2003: 107-108),但梁秉鈞大概沒想到的是,霸王南來香港的那一段被刪,要追究下來也不是大陸導演陳凱歌的主意,這是張國榮和張豐毅的決定,因為他們有感在大時代的浪濤中,電影是難以安排霸王渡江南來(張國榮 2007: 30)。
電影《霸王別姬》從拍攝到放映的前前後後,似乎只有全世界的八卦記者和讀者對程蝶衣/張國榮的性傾向感興趣,但他們大多數在進行的活動不是去瞭解或改善優伶/藝人面對著的罔兩再現/生存問題,而是持續偷窺著這兩具為了滿足觀者視覺效果而被導演/編劇「極度陰性化」的同志主體,以進一步「證實」和強化各自對同性愛的刻板印象。
這一切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霸王別姬》雖然熱烘烘進入1990年代華語小說和電影的議論之中,可是文本裡的罔兩主體和性欲卻被政治歷史、流行文化符號和性史敘事機制迅速「轉喻」、「剪接」或「刪剪」。在政治歷史和性史敘事機制話語過於強大的舞台螢幕上,大家只能透過歷史的刀光劍影,對同志主體被商品化的在場給予捕風捉影的描繪。張國榮一如程蝶衣那樣或許當年過於天真,他們倆以為自己的現身和「獻身」於表演藝術,可以讓自己與觀眾更接近同性愛的真相,最後一幕他們倆才意識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除了自盡「謝罪」,他們還有什麼更好可以成全自己同性愛欲望的方式?現在人們連歷史的真相都已經放棄去釐清,過量的「歷史化」話語傷害了生活本身,歷史也緊隨其後同樣退化(尼采 2007: 11)。我們似乎很難希翼人們去瞭解兩個男人是否相愛的真相。因而在這種「女性自戀」和「男性依戀」聯手打造的時代光影裡,在四面楚歌的政治歷史和性史敘事被商品化的噪音中,人們始終不可能看見同志完整的罔兩主體,因為這些優伶/幽靈的出場和再現,等於他的消失。
歷史與京劇《霸王別姬》的主題是一個女人(妃妾)對另一個男人(帝王)的絕對忠誠和奉獻,李碧華把它重寫成是一個現實生活中扮演虞姬的「(假)女人」對一個扮演霸王的男伶的忠誠和背叛,進一步把它置換成兩個男伶對京劇藝術的忠誠和背叛。陳凱歌則在李碧華的基礎上,突出菊仙的救贖性,展示了「男/女」的絕對忠誠和「男/男」的絕對背叛,重複了異性戀霸權的思維邏輯。《霸王別姬》無論在歷史,或京戲舞台上,它本來就是異性戀的經典模範版本,主題不外強調女人對男人的從一而終─「忠誠」是其亙古不變的教義。但京劇「男扮女裝」的表演方式,讓這個牢固不破的主題,在後人看來有了遐想的空間。在李碧華的「女性自戀」鏡像裡,它被改寫成是一個「(假)女人」對另一個男人的不得善終─「背叛」是小說一以貫之的命題,「文化自戀」被合法化成一種邊緣敘事,對抗國族的男性中心主義,同性愛敘事在那裡只是要達到消解國族話語的手段。陳凱歌以他的「男性依戀」,附著於國族的神話和歷史,雖然企圖打破了這個自戀鏡像,但小說《霸王別姬》裡國族歷史文化對傳統京劇藝術的改寫和否定,很多時候被陳凱歌倒轉回來,解釋成是蝶衣對小樓發生情感衝突的根源。
這一切導致蝶衣對小樓的欲望,不斷在這塊四面楚歌的歷史鏡像上無所遁形,殘存在敘事者和大部分觀者意識下的只是對同性愛的恐懼。飾演程蝶衣的一代香港巨星張國榮,他正是在世紀末的媒體聚焦下讓自己的同性愛傾向通過扮演一個優伶「現身」(come out)。廖炳惠在張國榮2004年自盡後重看《霸王別姬》,他覺得程蝶衣這個角色似乎早已預設張國榮在日後生活現實中所顯現的三角關係及其自我毀滅意志。姑且不論張國榮的感情是否受困於廖炳惠所言之鑿鑿的「三角關係」,僅就張國榮的同志身分而言,《霸王別姬》的敘事倒是預先書寫了世紀末巨星的預知死亡紀事。張國榮在生前的一場講稿透露,電影《霸王別姬》的結局不同於原著,包括程蝶衣的自盡,是他和張豐毅二人構思出來的(張國榮 2007: 30);張國榮之所以安排蝶衣死亡,他的解釋概括下來有三個原因:其一是虞姬個性執著,要死在霸王面前;其二,蝶衣想以自殺來完成原著故事的情節;其三,蝶衣不能接受自己和霸王的年華老去,當他發現在現實生活裡,他與師哥沒有了以往那種親密的感覺,他寧可選擇以虞姬來結束他的生命,做一場真正的《霸王別姬》。除了第二個原因是電影藝術效果上的考量,第一個和第三個原因顯而易見非常貼近張國榮最後選擇自殺的心理狀態,可見張國榮的自盡在當初處理《霸王別姬》的結局時就埋下了伏筆。這份講稿更重要的是洩露了張國榮在參演《霸王別姬》時,所遭受到的極度壓抑狀態:
陳凱歌改編的電影《霸王別姬》,卻充滿了極端的「恐同意識」,扭曲了同性戀獨立自主的選擇意向……我認為導演陳凱歌的取鏡很壓抑,過分壓抑……陳凱歌在電影裡一直不想清楚表明兩個男人的感情,而借鞏俐(筆者按:飾菊仙)來平衡故事裡同性關係的情節,這便提升了鞏俐在電影裡的地位。所以,作為一個演員,我只有盡力做好自己的本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對同性那份義無反顧的堅持,借著適當的眼神和動作,傳遞給觀眾……但在拍攝過程中,作為一個演員,我的演繹必得平衡導演對同性戀取材的避忌……(張國榮 2007: 32-33)二十世紀末的罔兩主體在《霸王別姬》裡是以程蝶衣/張國榮,這兩個「優伶/藝人」的職業身分現身,他們都可被視為是晚清豔史脈絡下的《品花寶鑑》杜琴言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投胎轉世,一個投生於電影小說,另一個誕生於演藝界。程蝶衣生不逢時,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歷史把他打入牛馬鬼神的行列。即使革命還沒來到,段小樓新婚之夜,程蝶衣早已預感自己只是個「老了的小鬼」(李碧華 2006: 143)。十九世紀的優伶,投胎來到二十世紀不上五十年,已經是「幽靈」了,而且還是「蒼老的幽靈」。張國榮在二十世紀末要以年輕的肉身擔當扮演這一具「蒼老的幽靈」,其藝術的高難度可想而知。幸好張國榮是一名同志,投入角色不會太困難。但導演取鏡時卻刻意淡化了其中的同性愛再現政治,又在導演/編劇以「女人彩妝」的嚴格規訓下,張國榮的同性愛表演在主流觀眾眼中,很可能只能越顯得像一個小女人那樣小打小鬧,並沒有如張國榮所以為的「或許我的確是顛覆了《霸王別姬》這套電影的演繹」(張國榮 2007: 32)。況且1990年代初張國榮還未宣布「出櫃」,張國榮在《霸王別姬》的整個扮演,只變成了一個極度曲折和艱難的「現身」演習而已。17 雖然電影在萬眾矚目下開拍和上映,可是大部分普通的港台觀眾不想看到什麼同性愛,他們只看到一個現代香港的優伶如何不可思議糾纏上一個其貌不揚的大陸演員張豐毅。大陸的普通老百姓更看不到電影裡有什麼同性愛,它不過是一個演戲入魔的舊社會戲子愛上戲裡的男主角;而這一切大陸人/香港人/台灣人看不到或不願看到的,西方學者們卻自認看到了,但他們更多看到的似乎又只是同性愛的東方主義景觀,小說電影裡的中國歷史在某些論者的詮釋下全部變成同性愛主題的注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利用來說明更嚴肅的什麼?似乎程蝶衣/張國榮從幕前到幕後所實實在在面臨四面楚歌的同志再現/生存問題都是次要問題。一些西方學者用它來診斷中國革命歷史的病態和變態(張高山 2004: 146-149)。
台灣學者廖炳惠利用它來說明台灣、香港和大陸三個地區所構成的緊張關係,台灣像個同性戀者(蝶衣)曾經一心一意想與大陸師兄(小樓)門戶相通,卻被迫於情勢而獨立門戶,香港就如一個煙花女(菊仙)因不經意的誓約,而導致被大陸明媒正娶(廖炳惠 2004: 35)。18 有些大陸學者卻利用它來說明第五代導演如何崇洋媚外進行東方主義和全球化的勾結。香港作家梁秉鈞利用它來闡釋香港如何在大中國導演的掌鏡下,曖昧的香港被邊緣化以至成了一個不能表白自我的主體(2003: 107-108),但梁秉鈞大概沒想到的是,霸王南來香港的那一段被刪,要追究下來也不是大陸導演陳凱歌的主意,這是張國榮和張豐毅的決定,因為他們有感在大時代的浪濤中,電影是難以安排霸王渡江南來(張國榮 2007: 30)。
電影《霸王別姬》從拍攝到放映的前前後後,似乎只有全世界的八卦記者和讀者對程蝶衣/張國榮的性傾向感興趣,但他們大多數在進行的活動不是去瞭解或改善優伶/藝人面對著的罔兩再現/生存問題,而是持續偷窺著這兩具為了滿足觀者視覺效果而被導演/編劇「極度陰性化」的同志主體,以進一步「證實」和強化各自對同性愛的刻板印象。
這一切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霸王別姬》雖然熱烘烘進入1990年代華語小說和電影的議論之中,可是文本裡的罔兩主體和性欲卻被政治歷史、流行文化符號和性史敘事機制迅速「轉喻」、「剪接」或「刪剪」。在政治歷史和性史敘事機制話語過於強大的舞台螢幕上,大家只能透過歷史的刀光劍影,對同志主體被商品化的在場給予捕風捉影的描繪。張國榮一如程蝶衣那樣或許當年過於天真,他們倆以為自己的現身和「獻身」於表演藝術,可以讓自己與觀眾更接近同性愛的真相,最後一幕他們倆才意識到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除了自盡「謝罪」,他們還有什麼更好可以成全自己同性愛欲望的方式?現在人們連歷史的真相都已經放棄去釐清,過量的「歷史化」話語傷害了生活本身,歷史也緊隨其後同樣退化(尼采 2007: 11)。我們似乎很難希翼人們去瞭解兩個男人是否相愛的真相。因而在這種「女性自戀」和「男性依戀」聯手打造的時代光影裡,在四面楚歌的政治歷史和性史敘事被商品化的噪音中,人們始終不可能看見同志完整的罔兩主體,因為這些優伶/幽靈的出場和再現,等於他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