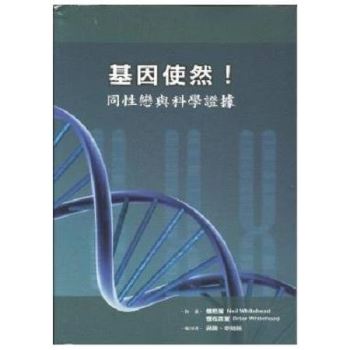第一章 基因能產生性傾向嗎?
如果我真的想認識你,你給我一份你的DNA分析報告,會有用嗎?或是給我一大塊你的脂肪細胞和碳水化合物?理解你的基因在指甲裡產生蛋白質的方式,會有助於我搞懂你為何一緊張就會咬指甲嗎?妳DNA含氮鹼基(nitrogenous bases)的結構,會幫助我瞭解為何妳星期六偏愛藍絲帶嗎?是顏料的化學成分使林布蘭(Rembrandt)的《自畫像》如此傳神嗎?是振動的物理現象使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那樣壯麗恢弘嗎?
我們可以爭辯說,顏料的化學成分和振動的物理現象,給自畫像和交響曲增加了一些東西。但大多數人都會說,二者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當有人企圖主張,人類行為(尤其是同性戀行為,本書主要的探討議題)乃由基因所支配時,主流遺傳學家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做出回應。對遺傳學家來說,這等爭論早在30年前便已定案。幾乎每一個行為,都是既先天而又後天的。遺傳學家非常沮喪地嘀咕:「這些同運人士在做什麼,想要讓時光倒流,主張同性戀只會來自遺傳嗎?!」
魯麥克爵士(Sir Michael Rutter)在他的書《基因和行為》(Genes and Behaviour)中說道:
任何不帶偏見但嚴格審查的研究,都得出以下明確的結論,在幾乎所有類型的行為、和各種形式的精神病理障礙或心智失調上,都兼有大量的遺傳影響和環境效應……沒有一項研究的結果,與全然「基因決定論」的觀點絲毫相容。
然而,本書將議論,任何基因對同性戀的影響,都是微弱且間接的,僅佔了所有影響的10%。(每個人的行為,都至少有那麼多的遺傳成分;沒有基因,便決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人類行為。)本書也將議論,關於環境對同性戀的影響,機遇的影響力是最強的;機遇,即個人對生活中隨機事件的反應。反應的意思是,它開始成為一種習性,構建成自己的人格,從而導致同性戀的反應。
我們應當經常稱呼同性戀為「同性吸引」(Same-sex Attraction, SSA),異性戀為「異性吸引」(Opposite Sex Attraction, OSA);而不是網路上常說的性活動!說同性吸引比較合適,是因為同性戀起初並非與性欲有關,儘管它可以在實踐中變得如此。同性吸引能更準確地表達出這種與同性別者間的強烈聯繫。所以基因的影響是間接的,它們創造一個擁有巨大潛能的生物體,藉由互動和改變來回應環境,但互動的細節是後天的。遇到喧囂、快速移動的車輛,而腎上腺素激增、想要逃跑的一匹野馬,可以通過教導,變成在車陣中從容邁步,毫無恐懼。學習是另一個環境影響,距離基因就更遠了。牠們的基因是否曾預知會有人來訓練牠們呢?當然不會。所以,即使動物也會成為超越他們DNA的生物,因為我們可以教牠們。猴子可以學會簡單的手語,進行有限的溝通。該語言的細節是牠們的DNA可以預告的嗎?不!那完全是外來的;人類發明,教給牠們。
人類
遺傳學家歐曼(G.S. Omenn)和莫圖斯基(A.G. Motulsky),當他們談到從基因結構預告行為的困難時,說道:「想從簡單的分析法來理解行為,根本是緣木求魚;就像想對一本書作化學分析,以尋求話語的弦外之音一樣,是毫無希望的。」13(參增圖1-7)
甚至連成熟的動物都不能被牠的基因完全地預告。更何況是人類?每個人的指紋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從基因詳細預測出來。在器官功能的層面上,基因的控制甚至更遙不可及。任何針對心跳速率的基因配方,頂多不過是開出一個潛能處方,以應對環境而已。
人類大腦是所知最複雜的物體,甚至比銀河系還複雜。正如某個智慧婦人所言,在腦中有足夠的空間容納靈魂!唯獨人類能自我覺察,並能覺察自己的腦。他們能寫出交響曲、寫詩、發展出特別的概念、說出充滿靈感的話,感動他人去作夢,去計畫,去愛去哭,去笑,去敬拜。我們現在不就是在談論另一個向度,談論靈性、另一個層面了嗎?此刻DNA有何置喙的餘地?有人敢說靈性可以從某人的基因裡完全地預測嗎?是否從出生便可以從基因完全地預測,我們這些作家會用英文打字,且把正在讀的這些字打進微軟的程式裡?當然不!
我們開始生活,就被迫攀爬我們基因的特殊梯子。但我們是在環境中製造和設計我們所爬的梯子。
為什麼要讓自己的基因來支配我們?為什麼要停留在動物的層面?為什麼不超越我們的基因?這不就是身為人的本質嗎?我們是可以超越基因、首先踏步前進的人類。
如果我真的想認識你,你給我一份你的DNA分析報告,會有用嗎?或是給我一大塊你的脂肪細胞和碳水化合物?理解你的基因在指甲裡產生蛋白質的方式,會有助於我搞懂你為何一緊張就會咬指甲嗎?妳DNA含氮鹼基(nitrogenous bases)的結構,會幫助我瞭解為何妳星期六偏愛藍絲帶嗎?是顏料的化學成分使林布蘭(Rembrandt)的《自畫像》如此傳神嗎?是振動的物理現象使貝多芬的第七號交響曲那樣壯麗恢弘嗎?
我們可以爭辯說,顏料的化學成分和振動的物理現象,給自畫像和交響曲增加了一些東西。但大多數人都會說,二者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當有人企圖主張,人類行為(尤其是同性戀行為,本書主要的探討議題)乃由基因所支配時,主流遺傳學家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做出回應。對遺傳學家來說,這等爭論早在30年前便已定案。幾乎每一個行為,都是既先天而又後天的。遺傳學家非常沮喪地嘀咕:「這些同運人士在做什麼,想要讓時光倒流,主張同性戀只會來自遺傳嗎?!」
魯麥克爵士(Sir Michael Rutter)在他的書《基因和行為》(Genes and Behaviour)中說道:
任何不帶偏見但嚴格審查的研究,都得出以下明確的結論,在幾乎所有類型的行為、和各種形式的精神病理障礙或心智失調上,都兼有大量的遺傳影響和環境效應……沒有一項研究的結果,與全然「基因決定論」的觀點絲毫相容。
然而,本書將議論,任何基因對同性戀的影響,都是微弱且間接的,僅佔了所有影響的10%。(每個人的行為,都至少有那麼多的遺傳成分;沒有基因,便決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人類行為。)本書也將議論,關於環境對同性戀的影響,機遇的影響力是最強的;機遇,即個人對生活中隨機事件的反應。反應的意思是,它開始成為一種習性,構建成自己的人格,從而導致同性戀的反應。
我們應當經常稱呼同性戀為「同性吸引」(Same-sex Attraction, SSA),異性戀為「異性吸引」(Opposite Sex Attraction, OSA);而不是網路上常說的性活動!說同性吸引比較合適,是因為同性戀起初並非與性欲有關,儘管它可以在實踐中變得如此。同性吸引能更準確地表達出這種與同性別者間的強烈聯繫。所以基因的影響是間接的,它們創造一個擁有巨大潛能的生物體,藉由互動和改變來回應環境,但互動的細節是後天的。遇到喧囂、快速移動的車輛,而腎上腺素激增、想要逃跑的一匹野馬,可以通過教導,變成在車陣中從容邁步,毫無恐懼。學習是另一個環境影響,距離基因就更遠了。牠們的基因是否曾預知會有人來訓練牠們呢?當然不會。所以,即使動物也會成為超越他們DNA的生物,因為我們可以教牠們。猴子可以學會簡單的手語,進行有限的溝通。該語言的細節是牠們的DNA可以預告的嗎?不!那完全是外來的;人類發明,教給牠們。
人類
遺傳學家歐曼(G.S. Omenn)和莫圖斯基(A.G. Motulsky),當他們談到從基因結構預告行為的困難時,說道:「想從簡單的分析法來理解行為,根本是緣木求魚;就像想對一本書作化學分析,以尋求話語的弦外之音一樣,是毫無希望的。」13(參增圖1-7)
甚至連成熟的動物都不能被牠的基因完全地預告。更何況是人類?每個人的指紋都是獨一無二的,無法從基因詳細預測出來。在器官功能的層面上,基因的控制甚至更遙不可及。任何針對心跳速率的基因配方,頂多不過是開出一個潛能處方,以應對環境而已。
人類大腦是所知最複雜的物體,甚至比銀河系還複雜。正如某個智慧婦人所言,在腦中有足夠的空間容納靈魂!唯獨人類能自我覺察,並能覺察自己的腦。他們能寫出交響曲、寫詩、發展出特別的概念、說出充滿靈感的話,感動他人去作夢,去計畫,去愛去哭,去笑,去敬拜。我們現在不就是在談論另一個向度,談論靈性、另一個層面了嗎?此刻DNA有何置喙的餘地?有人敢說靈性可以從某人的基因裡完全地預測嗎?是否從出生便可以從基因完全地預測,我們這些作家會用英文打字,且把正在讀的這些字打進微軟的程式裡?當然不!
我們開始生活,就被迫攀爬我們基因的特殊梯子。但我們是在環境中製造和設計我們所爬的梯子。
為什麼要讓自己的基因來支配我們?為什麼要停留在動物的層面?為什麼不超越我們的基因?這不就是身為人的本質嗎?我們是可以超越基因、首先踏步前進的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