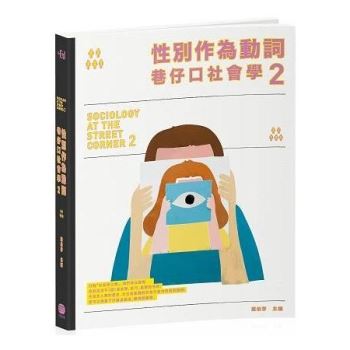所有婚姻制度都是歷史偶然:解構反同婚神話
王宏仁◎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反對同志婚姻的團體,最喜歡講保衛傳統家庭價值了,例如副總統陳建仁曾在接見反同團體後,接受訪問時說:「我們必須在台灣文化和對家庭、婚姻價值的理念脈絡下去考量同性婚姻。」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婚姻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但是,什麼是台灣文化的家庭、婚姻價值呢?什麼是「人倫秩序」呢?難道是反同婚團體說:「一男一女的婚姻具有自然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嗎?
這種訴諸「傳統、自然」的說法,其實就是羅蘭‧巴特說的神話論述:「神話的任務就是讓歷史的意圖,得到自然的正當性,讓偶成的事件看起來像是永恆的事物」。反同團體目前的歷史意圖,就是讓大家相信:婚姻本來就是一男一女的,家庭有「自然的」生育跟教養功能,透過這樣的論述,讓偶然的一夫一妻制度、自然生育養育的神話,成為永恆。
大家都知道一夫一妻根本不是台灣的傳統,三妻四妾多的是,童養媳、過繼習慣也滿地是,沒有什麼「自然」生育跟「養育」的事情,例如才不過七十年前的日治時期戶口登記,「妾」可以是合法的婚姻,另外還有許多我們現代人無法理解的家族關係登記,例如螟蛉子、養女、私生子、庶子、媳婦仔、從兄、從兄違……,這些多元家庭的故事,就留給其他作者來說。
這裡我們要講的是「自由結婚、自由戀愛」。透過百年前,一些衛道人士論述「自由結婚與戀愛」的報章文章,來看看當時「正常的、自然的、傳統的家庭價值」是什麼?也看看當年「從古至今不變的家庭價值」,如何在1970年代的短短十年間崩解,甚至我們都已經忘記,台灣曾經歷過很長的「奉父母之命,憑媒妁之言」年代。
你們竟然要自由結婚,跟禽獸不是一樣嗎?
傳統台灣漢人的男女婚姻,不論是成年男女、童養媳或招贅婚,基本上都是兩個家庭的結合,男女雙方的婚姻締結是取決於雙方的父母。日本殖民台灣之後,仍保留這樣的慣習。台灣總督府法院在1908年的判例說:「依據(台灣)舊慣,婚姻或離婚非僅依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尚須遵從尊親屬(一般是父母)之意思。」也因為有這種習慣,才會出現未經過父母同意而雙方「私奔」這種字眼。還有,夫妻要離婚,也不是隨便就OK的,還必須父母同意才可以,這種奉父母之命的異性戀婚姻,可是維繫了好幾百年的傳統啊!
此外,日治時代的法律規定,男子三十歲、女子二十五歲以下,如果要結婚,必須經過「戶長」的同意。也因為如此,即使有自由戀愛,但父母仍然掌握了關鍵的否決權,以自由戀愛為基礎的婚姻,在當時可以說根本不存在。
那麼婚姻的意義,在當時是如何看待呢?在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十六日,《台灣日日新報》的一篇「議論」,發表有關於「自由結婚辯」,一開頭就寫「有人來問我關於婚姻的事情,如果不是父母的命令或媒妁之言而結婚的,以前的人就鄙視之,稱做『野合』(不是打野砲的意思喔,是指跟野獸一樣的交合),但是現今卻說是自由、文明。……那麼婚姻到底是為了什麼呢?它不單只是為了男女兩個人,而是為了子孫延續、為了社會成立、為了國家保存、為了造化自然。如果僅僅只是為了男女『一時情緒的偏差』而結婚,那實在非常偏頗。……如果忘記上述的原因,就會變成『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跟禽獸有何差別呢?」
這種看法,跟一個世紀以後的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反對同婚的說法,一模一樣。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同性婚姻議題牧函〉一開頭就寫道:「婚姻與家庭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婚姻是指一男一女成人自願的結合,以共同生活為目的,並獲得社會和法律認可的獨特關係。在婚姻關係中,經由夫妻性行為,就有自然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因此婚姻關係可能發展成為父母與子女的家庭關係。因為婚姻具有生育與教養子女的功能,而生育與教養子女使得社會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所以全世界各國皆立法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關係。」
它一開始就先定義了什麼才是「自然的」,所謂的「自然」,就是一夫一妻制度,而且要「自然生育」。不過這個定義,不僅一點都不符合台灣的傳統(一夫多妻妾),也忽視過去半世紀來生殖科技為人類帶來的影響,例如試管嬰兒一開始也被視為「違背自然」,因為沒有夫妻之間的性行為,但現在還有人會說使用試管嬰兒生小孩的人不自然嗎?此外,該論述也訴諸「自然一代又一代延續下去」,跟百年前反對自由婚姻的說法,是不是如出一轍?百年前只有聽爸媽的話,人類才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延續下去,現在則是要聽基督長老教會的話,人類才不會滅亡。
你還會相信這種神(ㄍㄨㄟˇ)話嗎?
自由戀愛好可怕啊!!
那麼現在社會所讚賞的自由戀愛,當年的社會是如何看待呢?
1926年的《台灣日日新報》作者楊鐘鈺寫道:「如果婚姻不聽父母的話,也不問對方的階級跟德行,而號稱是自由戀愛,這樣子的兩個人,跟嫖客、娼妓,有何不同呢?我還沒看過嫖客跟娼妓會孝養其父母舅姑的!」這種將「不符合社會期待的愛情」,貼上「娼妓、嫖客」的標籤,跟現在反同論述,把同志愛情貼上「愛滋傳染、性濫交」的汙名標籤,是不是很類似?反正反對的一方,一定要把非常規的愛情,跟非常規的性行為,扯在一起就是了。
另外一則自由戀愛的新聞標題是:「女子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丟棄在廁所,自由戀愛的悲劇」,描述一位十八歲女性與二十三歲的情人未婚生子,因為擔心養父母發現,而絞殺剛出生的嬰兒。仔細看報導內容,關鍵在於養父母要求二十三歲的男子必須給聘金600圓才肯讓他們結婚,在1917年的公學校教員,一個月的薪水才17圓;在1930年代,一個月20圓即可溫飽。因此家長向男方要求600圓的聘金,根本就是故意阻撓,這名男子拿不出來,因此女孩就被養父母關在房間不得出門。請問,這齣悲劇是來自於自由戀愛還是父母?
當時的報章報導「自由戀愛」或「自由結婚」時,有兩個特點:首先、幾乎都是一面倒負面消息,就蒐集到的五十則新聞中,只有一則新聞是比較正面地報導「自由戀愛」,其他的新聞如「高工學生被退學,中自由戀愛毒」、「自由戀愛,產下一女,男竟娶他女」、「便所內捉姦,青年自由戀愛」、「離婚多是自由結婚者」、「高雄市內一對青年男女,自由結婚不成,投西子灣而死」……等。自由戀愛被看成是「中毒」、悲劇人生的開始,或只能在廁所偷偷摸摸進行。
第二個特點就是,如果出現悲劇的情節,幾乎都是一個模式:蠢女人跟壞男人,這個蠢女人可能是被「市井無賴少年誘拐去」,或者因為高唱自由戀愛的新時代女性,但「見識不足」,悲劇收場。例如一則報導為:「自由戀愛結婚未久,便惹起離異訴訟,見識不足少女極宜鑒戒」,描述一位在台銀桃園支店工作的女性,被「打扮的光鮮亮麗的青年簡慢居所迷惑,膽敢違背父母之命,把這麼好的工作辭掉,以達成她的自由戀愛願望。但是她卻不知道,這個男子根本就是遊手好閒、揮霍之徒。唉,青年的見識不足,只為了一時之間的愛情,不考慮將來的結果,造成今日這種後果,真一失足成千古恨也!」
所有的婚姻制度,都是歷史的偶然
由此可見,在1945年之前的台灣社會,所謂的「傳統」且「自然」的婚姻,就是要聽爸爸媽媽的話,透過媒人婆,找到階級相當的人來結婚。如果膽敢高唱「自由戀愛、自由結婚」,那就會「嚴重影響家庭價值、社會文化、倫理道德、教育、兒童福祉、社會和諧,甚至是人民的身心健康!」(套用反同人士的話語!)好可怕啊~~難怪許多家長都被嚇得要去學校抗議性別平等教材。
但是那些反對自由結婚、自由戀愛的衛道人士,大概無法想像,才幾年的光景,他們的玻璃心就碎滿地了。根據2001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資料統計,在1950年以前出生者,仍有高達47%是透過相親或媒人介紹而結婚,有8%是父母安排或介紹,這兩者加總起來就高達55%了,自己互相認識而結婚的才16%。但是才不過十年的光景,隨著台灣經濟在1965年之後快速發展,城鄉移民快速增加,傳統的媒人或父母介紹的比例,急速降低到17%,自己互相認識的比例急速增加到44%。1950至1959年出生的人,他們二十歲的時候就是1970至1979年,正是台灣城鄉移民跟經濟發展最急速的時候,整個婚配過程也急速變化,透過父母介紹跟媒妁之言而認識結婚的比例從此之後再也沒有回升過了。
台灣社會從此進入這些衛道人士所擔心的恐怖世界:「無紀律之民、無秩序之世」,再也回不去了,好悲慘啊!
「先自由戀愛而結婚」的意識形態跟實作,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它是整體社會制度變遷,特別是工業化發展,提供個人可以脫離家庭經濟生活而財務獨立,才可能出現以個人主義為主的自由戀愛跟婚姻,這個現象跟西方、日本的發展相當類似。同樣地,同志婚姻也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逐步成為新的一種家庭組織形態,它就如試管嬰兒、代理孕母的新現象一樣。目前反對同婚的說法,除了「自然」、「傳統價值」之外,還能拿什麼來說嘴呢?唯一的只有道德式的宣教,而且是「唯我獨尊」的三流道德式說法而已,在一個社會已經發展到分眾、多元、龐雜的時代,用單一的道德觀來抵擋歷史的洪流,這是註定被輾壓過去,而且成為未來的笑柄而已!
你嘛用心洗:美髮沙龍的身體工作
陳美華◎中山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誰來做身體工作?
我開始留意到美髮業源自於五年前某個冬日午後,在台中一家全國知名美髮連鎖店的親身體驗。一走進店裡,盛行於台式服務業的招呼語「歡迎光臨~」此起彼落的聲音,響遍整個店。
一位穿著時髦,頭上頂著流行的玉米燙的年輕助理帶著甜美笑容過來招呼我,帶我坐下,問清楚我要剪髮後,就輕輕抓起我的右手開始按摩。但我的手臂不僅全無放鬆的感覺,反而像被菜瓜布刷過一樣。不用看,我都感覺得到她雙手像是爬滿了魚鱗。這家店的規定至少按摩三至五分鐘,洗頭五至八分鐘。我忍耐地等她做完按摩,再幫我洗頭。
她是九月才入學的高一美髮班新生,家住彰化二水。跟大多數的美髮建教生一樣,家裡並不富裕,希望「學一技之長,至少可以養活自己」。這是她開始美髮生涯的第二個月,但每天洗頭又不能戴手套,雙手都受傷了。她去看醫生,醫生說只有一個選擇:改行別做了。好不容易才來到台中,怎麼可能退縮?她選擇繼續工作,「死馬當活馬醫」。
這類故事在美髮界並非新鮮事。之後我訪問的美髮助理、(高檔名店)設計師、店長、年收入千萬的知名連鎖店一級主管都提過洗頭洗到「手流血」、「手裂掉」、「靱帶受傷」,甚至「洗到泡泡都變成紅色,還說是客人頭髮掉色」的故事。弔詭的是,每個設計師的手都保養得相當好。洗頭助理和設計師的雙手間的反差,反映的是美麗產業中誰在執行身體工作(body work)的低階苦差事。
英國女性主義社會學家卡蘿•沃克維茲(Carol Wolkowitz)以身體工作(body work)一詞,來概念化那些在他人的身體上勞動或提供服務的工作。這類使人舒適、美化、強壯、健康、獲得快感,甚至藉由不斷操練而習得某些技藝的身體工作,包括被視為3D(dirty骯髒的、dangerous危險的、demeaning貶抑的)的照護產業、維持健康的醫療專業、打造身體的美容美體產業、休閒運動產業,以及提供性快感的性產業。身體工作廣泛涵蓋了最美、最香、最時尚的美體產業,也包括光譜另一端那些最髒、最臭、把屎把尿的照顧產業以及處理大體的殯葬業。
在這些和客人的身體接觸程度不一的工作中,愈是涉及直接處理身體體液、排泄物、嘔吐物的工作,如奶媽、幼教、看護、護士、性工作,女性集中的現象愈明顯,也愈容易淪為「骯髒工作」,廉價的女性外籍移工也常是主要的勞動力。身體工作者的專業也建立在能夠無視難聞氣味、噁心體液,而在那些難以親近的身體上執行工作。此外,因為勞動對象是活活生的人體,因而,工作者在執行勞務的過程中常被期待(有時也真的)提供適度的關愛(care)與溫情。因此就有社會學者以「親密勞動」(intimate labor)一詞來凸顯身體工作者和客戶間高密度的親密互動。
洗頭是美髮業中工作者和客人身體接觸最頻繁的一環,最底層的洗頭助理是最主要的身體工作者。助理除了洗頭,還必須依各店家規定幫客人按摩肩頸、搥背,最後負責清掃散落一地的頭髮,讓沙龍隨時保持光鮮亮麗。因而,從助理開始按摩、洗頭、沖水,再吹整至乾爽的過程有時超過三十分鐘。有些消費者在按得很放鬆、洗得很舒服之餘,幾乎在躺著洗頭的臥椅上睡著。這也是消費者把上美髮沙龍視為放鬆、寵愛自己的原因,甚至連日本觀光客都特別安排到美髮沙龍「體」驗「台式」的洗頭享受。
洗頭是要用感情的!
台灣美髮沙龍林立,傲視全球的豪華洗頭服務,收費卻極其低廉。全國性大型連鎖店打出「洗頭150、剪髮200」的廣告,對街的在地知名連鎖店可能就打出「洗頭99、洗+剪288」搶市。激烈競爭下,洗頭已不只是去汙、止癢、回復頭皮清潔,或是做造型的工作,而是環繞著洗頭進行各種身體工作的繁複演繹:有的在客戶躺在躺椅上時,貼心地在客人雙膝上蓋上防寒小毯,有的在額頭上貼吸油紙以防水花噴濺到客人的臉上,有的甚至提供「洗眼睛」的服務,先以溫水清洗雙眼,再用溫熱的毛巾熱敷雙眼,有的用精油進行頭皮按摩,有的乾脆大幅擴張上半身按摩的範圍與時間──目的都在充分取悅客戶,滿足消費端「體」驗小確幸的享受。
問題是,當人們享受洗頭時,洗頭助理的工作「體」驗又是什麼?
美髮工作者大多都會同意,洗頭是最基本的,但要做得好並不容易。即便洗頭助理經過無數的假人頭練習,但因為頭型、真假髮質地的差異,面對真人頭時往往很難拿揑客人的感受。於是,助理經常互相把對方的頭、肩頸當成練習的原始材料,有時設計師得貢獻自己的頭來洗,以便了解助理的洗頭功夫。洗頭難,但究竟「難」在哪裡?很多受訪者無法說得很清楚。國中畢業開始當學徒,五十歲成為知名連鎖店一級經理人的老師傅認為,關鍵是「指腹要用力、指甲要硬,刷、刷、刷,這樣她才會爽」、四十多歲手上有兩家店的店長則認為「重點洗,客人有感覺就可以」,但這些對多數無法「體」會的初學者而言,似乎只能以「一直練」、「洗久就會了」、「有些客人就是很難搞」來自我安慰。
洗頭助理的難題其實就是身體工作者的難題:當勞動的對象不是器械、物件,而是一個個活生生、有知覺、有想法,會哭、會笑、會痛、會爽的人身肉體時,感受、覺察客戶各種身體知覺的能力,就成為勞動的核心。頭,其實是很特別的部位,除了那些無力抗拒只能任人摸頭的小孩,以及如膠似漆的情侶之外,成年男女的頭其實是很少被人碰觸的,因而一般人也很難想像、感受另一個人的頭在層層白色泡沫覆蓋下,被十個手指頭來回抓洗、觸摸,讓溫水沖過的感覺。然而,無法掌握客人的身體感受,美髮助理就無法掌握客人究竟是否滿意。因此,洗頭時我們常聽到助理以柔和的語氣詢問,這水溫可以嗎?這力道行嗎?還有哪裡要再加強嗎?並隨時留意有沒有過多的泡沫或水流入客人耳朵、弄髒客人衣物,惹來客人不偷快。聲音也是有表情的,如果人們只是聽到儀式性的詢問,不免覺得助理「不用心」。
現在已有兩家連鎖店的Paul,回憶自己當洗頭助理時,第一天幫客人洗頭就被三名設計師點名批評「洗得好爛」而深覺受挫,後來慢慢體會出要「練手指的柔軟度⋯⋯去感受這個客人的脈動和情緒」。他開始用雙手去感覺,因為手是有感情的,「當你摸到客人那一剎那,其實無形中就有東西流露到你的身體裡」。
Paul的說法很抽象,也很難理解。可是在疾病蔓延的年代,洗到流血都「不能戴手套」的行規,看重的並不是乾淨/骯髒、健康/有病的界線,而是「手套會讓你失去觸感」、「比較感覺不到東西」,甚至影響判斷。當學徒時一直為洗頭所苦的阿菲,即使已晉升台北東區頂級沙龍設計師,還是認為洗頭是這行最「難」的差事,畢竟「美感」或「設計」都可以有自己的眼光或品味,不過洗頭不行。她花了很長的時間跟我談她對洗頭的「體」悟:
阿菲:所以,我當助理的時候很痛苦啊,因為……其實我覺得最難的是洗頭耶,洗頭要用感情。
美華:(爆笑)哈哈哈,洗頭要用感情。
阿菲:對啊,因為那是身體的互動,你要控制節奏,他才會舒服。而且……服務的那個人,他要感受……去感受你身體裡面需要他的部分,比如說……他在幫你按(摩)的時候,他如果夠用心,他會感覺到你很疲憊。
美華:嗯,每個按摩師傅都這樣說。
阿菲:其實我覺得洗頭滿難的,然後你的力道啊那些,就全部都要有一個連貫性,不然你其中一個節奏斷掉了,那個感覺就不好,就好像一首歌嘛……老闆教我的時候他就說,洗頭像……他說洗頭就像做愛一樣,就想像你在跟對方做愛,用那樣的感受去洗頭就對了。
美華:哇,他這樣講你就突然豁然開朗了。
阿菲:不然我就沒耐心,可是我就覺得一天要做幾次愛啊,這麼多……洗到二十顆,我覺得很累耶,不爽。……但是有時候看客人很舒服,我就覺得很高興。
洗頭要用感情,因為那是「身體的互動」。洗頭表面上是腳在站、嘴在講、手在洗的體力勞動,但「心」、「關懷」透過指尖被大量動員。這不只是把頭洗乾淨而已,還必須留意客人「皺眉」、「動一下頭或身體」等細微地肢體表現所傳達的身體感受,並適時給予回應。事實上,周邊不少朋友在抱怨洗得不好的助理時,往往不只說「洗得很不好」,而是喜歡加一句「就是很不用心!」這類負面評價反映的正是消費端不僅希望被洗乾淨,更期待能被細「心」呵護的無理要求。洗頭,因而不只是洗頭,而是一個必須「用『心』洗」的工作。「洗頭像做愛」毋寧是個精巧的比喻,它點明了這是一個身體對身體、心對心的勞動過程,問題是,當「做愛」成為工作,一天洗二、三十顆頭時也只有疲累的份。
肉體享樂的代價
享樂是有代價的,底層的身體工作者付出身心俱疲的代價。2014年全台服務業的月平均工時為173.4小時,月平均薪資為48,815元;但美容美髮業的月平均工時高達205.9小時,月平均薪資只有26,480元,敬陪末座。美髮及美容美體產業明顯是個女性集中、高工時、低工資的工作。
在人們愈來愈重視身體養護的年代,美髮從業者只是眾多低薪、苦勞、又必須有關愛心的身體工作者的一小部分。作為消費者,我們對各類身體工作者的期待往往不只是身體的養護,而是更多流露於指尖、聲音語調與身體姿態所呈現出來的關懷、呵護,甚或刻意營造的尊貴感。這些肉體享樂的期待使得身體工作者必須承擔更甚於以往同類勞動者的無酬工作──必須隨時體察客人的身體感受與情緒,並學會一種特定的肢體勞動過程來展現客人的尊貴性。美髮沙龍有意識地要求助理必須用「心」對待客戶,但其實只給付了「洗頭」這看得見的體力活的薪資,至於助理用「心」寵受客人、用「感情」洗頭的部分則全然無酬。用「心」的助理幫店家贏取回頭客,但利潤累積在店家,而不是回饋到助理的薪水袋。我們必須揭示底層勞動者的無酬勞動被遮蔽、隱藏的做事,以朝向更合理、更平等的勞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