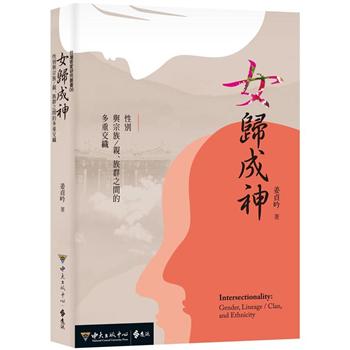宗族作為父系繼嗣體制,強調以男性繼承為核心,相對於男性具有的永久資格,女性在宗族內的定位為暫時性成員或輔助從屬的角色,因而,女性與宗族在不同領域跟議題會發展出有別於永久成員的男性不同的關係結構。成為宗族祖先,是宗族自我生成的重要結構,原生女兒多數被排除在成為本宗祖先的生產過程,因此,本章將集中討論女性跟公廳、祖塔等過世後安置有關面向,特別在與其他兄弟手足相較下的女兒跟本宗的關係,第一部分討論女性跟原生宗族的關係,探討藉由各種規範讓女性在系統內的被排除,以及女性自身的自我規訓;第二部分討論被界定為「失序」於「婚姻身分」的女性與宗族的關係結構;第三部分討論女性在「婚姻身分」下,跟宗族的多面向關係結構;第四部分探討掉出此一結構邊界之外的例外,凸顯結構性的漏接如何困住行動者,最後再以邊界之外的例外狀態轉而呈現宗族成員的自我行動的趨向,以及擴張結構的可能。
宗族具有血緣、地緣與親緣性質,其運作機制的性別規範是基於儒家倫常原則,五倫具有支配地位,規範著行動者彼此間的關係。金觀濤、劉青峰(1993: 31)指出此一「宗法性家族組織不是簡單的血緣團體,而是以儒家倫理為原則所建立起來的基本單位」。宗族作為父系繼嗣體制的型態之一,儒家倫常具有支配父權、夫權跟男權行使支配從屬關係的原則地位。儒家倫常在現代家庭興起後,雖依舊具有支配地位,但在法律持續對家庭親屬、居住關係、子女姓氏、財產繼承等面向的平權修法,逐漸培力出家庭內不同行動者的自主權與協商權力。而宗族超家庭結合體似乎看起來也跟著現代家庭的變遷軌跡,成員結構看似有鬆解跡象,規範成員的支配力逐漸薄弱,然宗族就像一個具有自我再製的系統,持續生產出構成系統的基本元素。系統也並非一再僵固地再製支配從屬結構,成員在與宗法間持續既有倫常邏輯的維繫之際,也會「順便帶入」各種不同於既定的秩序與規範的實踐行動,企圖在場域結構中呈現行動主體與能動,以回應現世生活的經驗情境與感受認知。宗族組織在權力關係、生產關係、情感關係與象徵關係上,無不持續促進延續父系香火並同時有更多祖先的形成、同宗網絡與各種資源交換關係的積累、親屬結構與文化結構關係交織等的「自我生成」的再製。宗族系統的運作猶如魯曼所指的社會系統具有的「自我生成的再製」(魯顯貴 1998;高宣揚 2002)性質,包括自身(制度與機制)以及周邊(與在地社會的政經、文化領域等的結合)。宗族是社會的次級團體系統,以生育與持續生產祖先的機制,透過下一世代的出生與祖先形成的循環,構成宗族本體的自我再製。自我再製系統在「系統自身的邊界(bourdary)與組織內部的結構,都是自我組織的(self-organizing)」(Ritzer and Goodman 2004: 465-467)。
也就是說,「同宗男性血親」與「男丁家戶長」兩個軸線,作為組織界線也作為組織的結構。這些性質都讓系統保證運作的相對獨立性,並能視情境脈絡因素隨機應變,因而「系統的自我參照(self-reference)也是封閉性(closed system)」的(高宣揚 2002: 198)。外部成員的加入有兩種可能,一是將作為修正絕嗣困境而領養、收養的男性繼承人,經通過儀式轉化成為血脈繼承者,再者就是將加入男丁家戶內協助生產與再生產的女性配偶,這兩種方式皆為定義的自我修復與生成結構的自我生產,持續穩固結構與關係網絡,協助系譜的延展性。
因而,宗族系統的自我再製的封閉性,在界線與組織結構上都具有自我參照與自我生產的特性,在此一結構面向的另外一面,即是被疏離與排除的種種,包括「非生育的」、「非男性的」所共同交織出的各種可能,例如女性、非生育的、同性戀/性慾的等,加上傳統文化結構至今都把「生育」與「婚姻」結合成為同一結構,交織出「生育」與「婚姻」相互作用且作為判斷的倫理位置。以性別與婚姻身分發展為「邊界」的標準,如同MacKinnon(1989)所指出,性別是權力問題,而非差異問題。本章將討論宗族作為一個系統,有哪些排除原生女性成員的相關性別規範,再以「婚姻身分」別,從「未婚女兒」、「離婚女兒」、「已婚女兒」,到「入門媳婦(婆婆)」的宗族位置,探討這些女性過世葬期合火後的安置,特別是跟宗族關係密切的上公廳入祖塔,以呈現女性因婚姻身分在這個面向被體制系統性的安置與排除,同時也將指出部分行動者並未當一個「沉默的」受苦者,總是透過不同的反思行動(或指示兒女行動)與安排,撐出行動主體與宗族結構間的自在場域。
宗族具有血緣、地緣與親緣性質,其運作機制的性別規範是基於儒家倫常原則,五倫具有支配地位,規範著行動者彼此間的關係。金觀濤、劉青峰(1993: 31)指出此一「宗法性家族組織不是簡單的血緣團體,而是以儒家倫理為原則所建立起來的基本單位」。宗族作為父系繼嗣體制的型態之一,儒家倫常具有支配父權、夫權跟男權行使支配從屬關係的原則地位。儒家倫常在現代家庭興起後,雖依舊具有支配地位,但在法律持續對家庭親屬、居住關係、子女姓氏、財產繼承等面向的平權修法,逐漸培力出家庭內不同行動者的自主權與協商權力。而宗族超家庭結合體似乎看起來也跟著現代家庭的變遷軌跡,成員結構看似有鬆解跡象,規範成員的支配力逐漸薄弱,然宗族就像一個具有自我再製的系統,持續生產出構成系統的基本元素。系統也並非一再僵固地再製支配從屬結構,成員在與宗法間持續既有倫常邏輯的維繫之際,也會「順便帶入」各種不同於既定的秩序與規範的實踐行動,企圖在場域結構中呈現行動主體與能動,以回應現世生活的經驗情境與感受認知。宗族組織在權力關係、生產關係、情感關係與象徵關係上,無不持續促進延續父系香火並同時有更多祖先的形成、同宗網絡與各種資源交換關係的積累、親屬結構與文化結構關係交織等的「自我生成」的再製。宗族系統的運作猶如魯曼所指的社會系統具有的「自我生成的再製」(魯顯貴 1998;高宣揚 2002)性質,包括自身(制度與機制)以及周邊(與在地社會的政經、文化領域等的結合)。宗族是社會的次級團體系統,以生育與持續生產祖先的機制,透過下一世代的出生與祖先形成的循環,構成宗族本體的自我再製。自我再製系統在「系統自身的邊界(bourdary)與組織內部的結構,都是自我組織的(self-organizing)」(Ritzer and Goodman 2004: 465-467)。
也就是說,「同宗男性血親」與「男丁家戶長」兩個軸線,作為組織界線也作為組織的結構。這些性質都讓系統保證運作的相對獨立性,並能視情境脈絡因素隨機應變,因而「系統的自我參照(self-reference)也是封閉性(closed system)」的(高宣揚 2002: 198)。外部成員的加入有兩種可能,一是將作為修正絕嗣困境而領養、收養的男性繼承人,經通過儀式轉化成為血脈繼承者,再者就是將加入男丁家戶內協助生產與再生產的女性配偶,這兩種方式皆為定義的自我修復與生成結構的自我生產,持續穩固結構與關係網絡,協助系譜的延展性。
因而,宗族系統的自我再製的封閉性,在界線與組織結構上都具有自我參照與自我生產的特性,在此一結構面向的另外一面,即是被疏離與排除的種種,包括「非生育的」、「非男性的」所共同交織出的各種可能,例如女性、非生育的、同性戀/性慾的等,加上傳統文化結構至今都把「生育」與「婚姻」結合成為同一結構,交織出「生育」與「婚姻」相互作用且作為判斷的倫理位置。以性別與婚姻身分發展為「邊界」的標準,如同MacKinnon(1989)所指出,性別是權力問題,而非差異問題。本章將討論宗族作為一個系統,有哪些排除原生女性成員的相關性別規範,再以「婚姻身分」別,從「未婚女兒」、「離婚女兒」、「已婚女兒」,到「入門媳婦(婆婆)」的宗族位置,探討這些女性過世葬期合火後的安置,特別是跟宗族關係密切的上公廳入祖塔,以呈現女性因婚姻身分在這個面向被體制系統性的安置與排除,同時也將指出部分行動者並未當一個「沉默的」受苦者,總是透過不同的反思行動(或指示兒女行動)與安排,撐出行動主體與宗族結構間的自在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