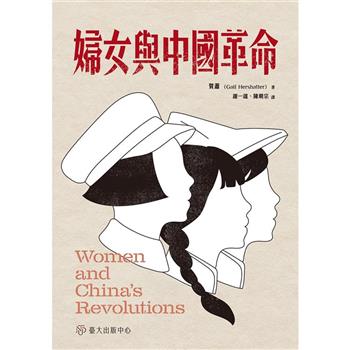1 帝制中國性別化勞動(1800-1840)〔摘錄〕
早在中國捲入鴉片戰爭(1839-1842)這場危機之前,清帝國生活早就已經面臨諸多變動。雖然帝制中國近兩千餘年,但19世紀初已逐漸浮現社會壓力的新徵兆。在這個日益流動與競爭的世界裡,士紳與一般百姓家庭女孩及婦女所承擔的勞動,對家庭福祉來說從未如此重要過。
1644年,中國東北的滿族征服中國,建立大清王朝,也同時開啟了一段擴張史。西征、內部移民、人口爆炸、經濟成長及各式思辨促成學術活躍發展,是清朝統治的前兩個世紀所呈現的重要特徵。跨區域貨品與觀念流通愈趨活躍。由新世界傳入的新作物因而出現新栽種模式,而隨販賣到歐洲的絲織品、陶瓷與茶葉交易,新世界的白銀也開始流入中國。
這些發展改變了每個地區與各種背景所有人的生計。此時,商機大增,許多男性也因經商而致富,但同時每個家庭的經濟壓力也與日俱增。勞動家庭的耕地也因為世代分割繼承而越來越破碎,為維持及改善家中生計,只能投入商業市場生產。男性為了找工作而離鄉背井數月或數年。有時為謀求更好生活,只得從人口稠密區舉家遷至人口稀少的內陸或邊疆地區。即便是特權家族也無法不受變遷影響,更難以取得與維持帝國精英階層身分。
本章將透過描繪兩位女性的故事,來勾勒19世紀初期這個動盪的世界。這兩位女性的故事是從不同資料匯整而成,而非直接由個人紀錄來重建的,但絕非虛構人物。提及兩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取自歷史研究,而這些文字紀錄往往是沉默無聲的(例如:關於性與情慾經驗,又或是替自己女兒纏足時是否也百感交集、心情複雜等),也因此相關描述必然不完整。其中一位女性,我稱其為李秀華,她一手打理這個多代同堂的士紳之家,但在當時新經濟壓力下面臨家道中落。另一位我稱之為黃氏的女性,即依循一般農家女性從夫姓之習慣來稱呼。黃氏出身普通農家,而當時紡織是讓一家勉能溫飽的重要基礎。我之所以將這兩位女性的故事都設定在當時中國經濟最富庶的江南,是因為該地區史料夠豐富,而得以建構出這兩人的故事。
當然,這兩則出身中國富庶地區的女性故事,顯然不足以代表全中國女性的處境。但從一開始,地方史料文獻多寡懸殊這樣的情況,就已經決定我們能否有把握呈現其他地區女性的樣貌,而且沒有單一人物能充分重現其他地區多樣女性勞動與生活狀態。而這兩則已婚婦女故事,也無法告訴我們更多關於遭拐賣女童、賣妻、青樓名妓、娼妓或違法犯紀者等故事。在接下來的故事中,我們只會在李秀華與黃氏擔憂女兒能否有個好歸宿時,瞥見上述這些女性的身影。然而,除自身處境外,這兩位江南女性道出更多故事。她們都各自身處於不同人際網路之中,而兩人的生命故事也有助於我們去找到,串聯起家與社會族群,且時而橫跨更廣範圍的關係。透過思考她們有哪些共同處,她們的生命軌跡又在何處產生分歧,她們所處的區域又跟其他低度開發地區有何不同,以及她們的世界又是如何變動等問題,我們可以開始理解19世紀中國生活所呈現的性別化樣態。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社會階層女性的工作狀況,而得以在帝國晚期活下來。
書香門第婦女
1832年,李秀華是位年過四旬的已婚婦女,負責打理這四代同堂一家上下生活起居、下一代教養與關心家人情緒等複雜家務瑣事。她必須確保一家大小都能吃飽穿暖、受教育及身體健康。她同時要負責照顧守寡的婆婆、督導家中三個僕人、管好替家中些許土地耕作的佃農、幫兩個女兒找到好對象,同時也要替兩個兒子討到好媳婦。此外,即便家境不如以往,她仍要負責維持這個家在地方街坊上的名聲地位,成為地方上諮詢及不時出錢出力的對象。有時她實在很想跟夫婿商討論這些家務,但他遠赴百里外在他省擔任縣官。光是一封信件往來可能就得耗費數月。因此,從實務層面來說,秀華是一家之主,即便從法律來看,一家之主這個位子應該是由男人來擔任。
由已婚婦女操持家務,這在19世紀中國已非剛出現之現象。帝制中國日常生活運作,即遵循「男主外、女主內」觀念。而在帝制中國政治思想之中,齊家即為治國平天下之基礎,因此內與外是彼此緊密連接、而非分開不相關的。家中每個成員皆被賦予學會各自角色分際的規矩,亦即親慈子孝衍生形成君臣倫理間的責任義務。家務事成為政治場域的縮影,兩者藉由倫理實踐而緊密結合。
然而,內外之別絕非輕易簡化成當代「公」與「私」概念,因為經濟生產、教育與宗教活動等許多事務也讓家成為兼具準公共活動性質的場域。身為名門望族之婦的秀華通常都待在深閨後院,也就是家庭婦女在家中最常活動的範圍。她也常到供奉夫家祖先牌位的大廳,因為夫婿不在家時她要負責擦拭整理神桌並更換供品。但當夫婿在家、有男性訪客上門交談時,她就不能出現在大廳,因為像她這樣身分背景的女性通常很少拋頭露面。而身負家庭興旺重責的秀華,不僅扮演家中重要角色,在地方街坊上一樣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就如同其他帝國晚期男性一般,秀華夫婿須離鄉背井數年。早在她所處年代的千餘年前,男性就已在科舉制度中競爭。男性為了在科舉中求得功名,得經過多年苦讀經籍與集注,科舉制度亦確保維持帝國官僚系統運作的男性,具備相同價值觀與高知識能力。士紳地位並非世襲而來,更不是單靠財富來決定,而是得看家中男丁是否有苦讀應試並一試成名的本事。即便是富賈人家,也都冀望家中子嗣能求得一官半職,或讓家中閨女嫁入官宦人家。順利通過高等科舉者,會被派到他鄉任官。這種「迴避制度」理想上避免了官職與個人親屬或姻親特殊考量之間產生利益衝突。因此對秀華這樣在家照顧年邁公婆、養兒育女與持家的官夫人來說,遠赴在他鄉任官的夫婿,時有婢妾相伴,這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19世紀初,這位官夫人與人母,深切感受到新壓力。1700年大清帝國人口近1.5億人、1800年業已倍增,而到1850年已成長3倍。與此同時,科舉錄取員額幾乎不變,但應考者準備的考試內容卻有增無減。因此,競逐官位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科舉考試的準備早在男孩3歲時就開始,並一路持續幾十年。理論上,科舉考試是所有男性都能參加的,但對有能力資助與督導男童長年準備應試的父母,科舉才算是現實考量。通常只有地主或富賈之家,才有餘力培育兒子來準備科舉。這些精英階層男孩只有一個責任:準備科舉。免除徭役就是該社會地位的象徵。
兒子年紀尚小時,準備科舉也幫到秀華得知如何讀古籍經典。這在書香門第並非罕見情況:19世紀中國女性識字率大約介在2%到10%左右,而如同江南這樣經濟高度發展地區的識字率則屬於前段。她出身書香世家,家中藏有全國各地書坊刊印銷售的刻版書。為滿足快速成長的讀者,書坊不僅刊印古籍經典,還會出些修養、養生、生意經等相關書籍,還針對特定讀者推出新小說與散文。親友們普遍認為,女孩要讀書識字,將來才能成為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
但女性讀書識字一事,也非完全沒有爭議。父親就曾對秀華提過,當時男性文人間的「婦學」論戰。他認同清代學者章學誠(1738-1801)的立場,其強調受經學教育的婦女,能成為夫婿道德行為指引及子女教養者。但章學誠對女性詩文創作抱持懷疑的態度,這很有可能是由於當時晚近著名文壇才女,都是青樓名妓,而非名媛閨秀。相較其他清代男性文人,尤以詩人袁枚(1716-1797)則鼓勵推崇閨秀才女創作。
合乎禮教懿德或彰顯詩才的婦學之爭雖懸而未決,但卻能從秀華所受的教育上發現這兩者並存的狀況。母親也曾教她讀書識字,帶她閱讀東漢女史學家班昭(45-116)傳授三從四德的《女誡》,還有唐代女官宋若莘撰、宋若昭註的女訓書《女論語》。
至於父親每每返鄉,便鼓勵秀華吟讀詩文甚而寫詩詞。她尤其期待母親收到姨媽來信的時刻。母親與姨媽自小親近,但當時各階層女性會因出嫁搬進公婆家而四散各方。待成年後來,母親與姨媽時常分享各自喜愛、甚至自己創作的詩詞。秀華結婚前一年,在地方小有名氣的大姨還送秀華一本裝幀精美的個人詩詞集,這本詩詞集是表兄為了大姨五十大壽而出版的。
秀華家中比較少看到小說,除了當時剛出版的《石頭記》(後稱《紅樓夢》)之外。這部描寫官宦之家錯綜複雜關係的小說,深深吸引著母親與姨媽們,並從中獲得詩詞創作靈感。還有由說唱曲藝「彈詞」傳抄發展成當時流行的韻文體「彈詞小說」。秀華幼時特別愛與姐妹們大聲朗讀《再生緣》女英雄孟麗君是如何一路女扮男裝到官至宰相的故事,還有《再造天》中孟麗君之女的傳奇故事。這些常處深閨後院的名媛閨秀與婦女,透過閱讀來想像與交流分享故事、勸世警言與傳奇冒險的寬廣世界。
一方面好奇母親安排的讀本之外還有哪些可讀,秀華一方面也跟兄弟們同塾師學習。隨之步入青少年後,她也跟著準備應試的兄弟們每夜背誦經書。而秀華在這段時間所聞所學,到了有小孩後也派上用場,教導子女背《千字文》、《百家姓》,還有帶他們讀四書五經及《孝經》。她以言傳身教來培養子女品德、傳授學習的重要性,一但子女行為舉止有所偏差也立即予以訓誡。特別在父親長年不在家,因而得母兼父職的秀華,她成為家中無比的道德權威並肩負重責大任。
早在中國捲入鴉片戰爭(1839-1842)這場危機之前,清帝國生活早就已經面臨諸多變動。雖然帝制中國近兩千餘年,但19世紀初已逐漸浮現社會壓力的新徵兆。在這個日益流動與競爭的世界裡,士紳與一般百姓家庭女孩及婦女所承擔的勞動,對家庭福祉來說從未如此重要過。
1644年,中國東北的滿族征服中國,建立大清王朝,也同時開啟了一段擴張史。西征、內部移民、人口爆炸、經濟成長及各式思辨促成學術活躍發展,是清朝統治的前兩個世紀所呈現的重要特徵。跨區域貨品與觀念流通愈趨活躍。由新世界傳入的新作物因而出現新栽種模式,而隨販賣到歐洲的絲織品、陶瓷與茶葉交易,新世界的白銀也開始流入中國。
這些發展改變了每個地區與各種背景所有人的生計。此時,商機大增,許多男性也因經商而致富,但同時每個家庭的經濟壓力也與日俱增。勞動家庭的耕地也因為世代分割繼承而越來越破碎,為維持及改善家中生計,只能投入商業市場生產。男性為了找工作而離鄉背井數月或數年。有時為謀求更好生活,只得從人口稠密區舉家遷至人口稀少的內陸或邊疆地區。即便是特權家族也無法不受變遷影響,更難以取得與維持帝國精英階層身分。
本章將透過描繪兩位女性的故事,來勾勒19世紀初期這個動盪的世界。這兩位女性的故事是從不同資料匯整而成,而非直接由個人紀錄來重建的,但絕非虛構人物。提及兩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取自歷史研究,而這些文字紀錄往往是沉默無聲的(例如:關於性與情慾經驗,又或是替自己女兒纏足時是否也百感交集、心情複雜等),也因此相關描述必然不完整。其中一位女性,我稱其為李秀華,她一手打理這個多代同堂的士紳之家,但在當時新經濟壓力下面臨家道中落。另一位我稱之為黃氏的女性,即依循一般農家女性從夫姓之習慣來稱呼。黃氏出身普通農家,而當時紡織是讓一家勉能溫飽的重要基礎。我之所以將這兩位女性的故事都設定在當時中國經濟最富庶的江南,是因為該地區史料夠豐富,而得以建構出這兩人的故事。
當然,這兩則出身中國富庶地區的女性故事,顯然不足以代表全中國女性的處境。但從一開始,地方史料文獻多寡懸殊這樣的情況,就已經決定我們能否有把握呈現其他地區女性的樣貌,而且沒有單一人物能充分重現其他地區多樣女性勞動與生活狀態。而這兩則已婚婦女故事,也無法告訴我們更多關於遭拐賣女童、賣妻、青樓名妓、娼妓或違法犯紀者等故事。在接下來的故事中,我們只會在李秀華與黃氏擔憂女兒能否有個好歸宿時,瞥見上述這些女性的身影。然而,除自身處境外,這兩位江南女性道出更多故事。她們都各自身處於不同人際網路之中,而兩人的生命故事也有助於我們去找到,串聯起家與社會族群,且時而橫跨更廣範圍的關係。透過思考她們有哪些共同處,她們的生命軌跡又在何處產生分歧,她們所處的區域又跟其他低度開發地區有何不同,以及她們的世界又是如何變動等問題,我們可以開始理解19世紀中國生活所呈現的性別化樣態。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同社會階層女性的工作狀況,而得以在帝國晚期活下來。
書香門第婦女
1832年,李秀華是位年過四旬的已婚婦女,負責打理這四代同堂一家上下生活起居、下一代教養與關心家人情緒等複雜家務瑣事。她必須確保一家大小都能吃飽穿暖、受教育及身體健康。她同時要負責照顧守寡的婆婆、督導家中三個僕人、管好替家中些許土地耕作的佃農、幫兩個女兒找到好對象,同時也要替兩個兒子討到好媳婦。此外,即便家境不如以往,她仍要負責維持這個家在地方街坊上的名聲地位,成為地方上諮詢及不時出錢出力的對象。有時她實在很想跟夫婿商討論這些家務,但他遠赴百里外在他省擔任縣官。光是一封信件往來可能就得耗費數月。因此,從實務層面來說,秀華是一家之主,即便從法律來看,一家之主這個位子應該是由男人來擔任。
由已婚婦女操持家務,這在19世紀中國已非剛出現之現象。帝制中國日常生活運作,即遵循「男主外、女主內」觀念。而在帝制中國政治思想之中,齊家即為治國平天下之基礎,因此內與外是彼此緊密連接、而非分開不相關的。家中每個成員皆被賦予學會各自角色分際的規矩,亦即親慈子孝衍生形成君臣倫理間的責任義務。家務事成為政治場域的縮影,兩者藉由倫理實踐而緊密結合。
然而,內外之別絕非輕易簡化成當代「公」與「私」概念,因為經濟生產、教育與宗教活動等許多事務也讓家成為兼具準公共活動性質的場域。身為名門望族之婦的秀華通常都待在深閨後院,也就是家庭婦女在家中最常活動的範圍。她也常到供奉夫家祖先牌位的大廳,因為夫婿不在家時她要負責擦拭整理神桌並更換供品。但當夫婿在家、有男性訪客上門交談時,她就不能出現在大廳,因為像她這樣身分背景的女性通常很少拋頭露面。而身負家庭興旺重責的秀華,不僅扮演家中重要角色,在地方街坊上一樣也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就如同其他帝國晚期男性一般,秀華夫婿須離鄉背井數年。早在她所處年代的千餘年前,男性就已在科舉制度中競爭。男性為了在科舉中求得功名,得經過多年苦讀經籍與集注,科舉制度亦確保維持帝國官僚系統運作的男性,具備相同價值觀與高知識能力。士紳地位並非世襲而來,更不是單靠財富來決定,而是得看家中男丁是否有苦讀應試並一試成名的本事。即便是富賈人家,也都冀望家中子嗣能求得一官半職,或讓家中閨女嫁入官宦人家。順利通過高等科舉者,會被派到他鄉任官。這種「迴避制度」理想上避免了官職與個人親屬或姻親特殊考量之間產生利益衝突。因此對秀華這樣在家照顧年邁公婆、養兒育女與持家的官夫人來說,遠赴在他鄉任官的夫婿,時有婢妾相伴,這早已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19世紀初,這位官夫人與人母,深切感受到新壓力。1700年大清帝國人口近1.5億人、1800年業已倍增,而到1850年已成長3倍。與此同時,科舉錄取員額幾乎不變,但應考者準備的考試內容卻有增無減。因此,競逐官位之激烈是前所未有的。科舉考試的準備早在男孩3歲時就開始,並一路持續幾十年。理論上,科舉考試是所有男性都能參加的,但對有能力資助與督導男童長年準備應試的父母,科舉才算是現實考量。通常只有地主或富賈之家,才有餘力培育兒子來準備科舉。這些精英階層男孩只有一個責任:準備科舉。免除徭役就是該社會地位的象徵。
兒子年紀尚小時,準備科舉也幫到秀華得知如何讀古籍經典。這在書香門第並非罕見情況:19世紀中國女性識字率大約介在2%到10%左右,而如同江南這樣經濟高度發展地區的識字率則屬於前段。她出身書香世家,家中藏有全國各地書坊刊印銷售的刻版書。為滿足快速成長的讀者,書坊不僅刊印古籍經典,還會出些修養、養生、生意經等相關書籍,還針對特定讀者推出新小說與散文。親友們普遍認為,女孩要讀書識字,將來才能成為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
但女性讀書識字一事,也非完全沒有爭議。父親就曾對秀華提過,當時男性文人間的「婦學」論戰。他認同清代學者章學誠(1738-1801)的立場,其強調受經學教育的婦女,能成為夫婿道德行為指引及子女教養者。但章學誠對女性詩文創作抱持懷疑的態度,這很有可能是由於當時晚近著名文壇才女,都是青樓名妓,而非名媛閨秀。相較其他清代男性文人,尤以詩人袁枚(1716-1797)則鼓勵推崇閨秀才女創作。
合乎禮教懿德或彰顯詩才的婦學之爭雖懸而未決,但卻能從秀華所受的教育上發現這兩者並存的狀況。母親也曾教她讀書識字,帶她閱讀東漢女史學家班昭(45-116)傳授三從四德的《女誡》,還有唐代女官宋若莘撰、宋若昭註的女訓書《女論語》。
至於父親每每返鄉,便鼓勵秀華吟讀詩文甚而寫詩詞。她尤其期待母親收到姨媽來信的時刻。母親與姨媽自小親近,但當時各階層女性會因出嫁搬進公婆家而四散各方。待成年後來,母親與姨媽時常分享各自喜愛、甚至自己創作的詩詞。秀華結婚前一年,在地方小有名氣的大姨還送秀華一本裝幀精美的個人詩詞集,這本詩詞集是表兄為了大姨五十大壽而出版的。
秀華家中比較少看到小說,除了當時剛出版的《石頭記》(後稱《紅樓夢》)之外。這部描寫官宦之家錯綜複雜關係的小說,深深吸引著母親與姨媽們,並從中獲得詩詞創作靈感。還有由說唱曲藝「彈詞」傳抄發展成當時流行的韻文體「彈詞小說」。秀華幼時特別愛與姐妹們大聲朗讀《再生緣》女英雄孟麗君是如何一路女扮男裝到官至宰相的故事,還有《再造天》中孟麗君之女的傳奇故事。這些常處深閨後院的名媛閨秀與婦女,透過閱讀來想像與交流分享故事、勸世警言與傳奇冒險的寬廣世界。
一方面好奇母親安排的讀本之外還有哪些可讀,秀華一方面也跟兄弟們同塾師學習。隨之步入青少年後,她也跟著準備應試的兄弟們每夜背誦經書。而秀華在這段時間所聞所學,到了有小孩後也派上用場,教導子女背《千字文》、《百家姓》,還有帶他們讀四書五經及《孝經》。她以言傳身教來培養子女品德、傳授學習的重要性,一但子女行為舉止有所偏差也立即予以訓誡。特別在父親長年不在家,因而得母兼父職的秀華,她成為家中無比的道德權威並肩負重責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