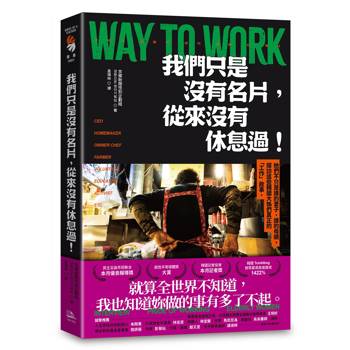【摘文1】「內人」這個名字太小了,裝不下喜子
我叫張喜子,1960年出生,是戰後的世代。原本住在江原道,你聽說過以蒸包聞名的安興吧?我的胎盤就埋在那裡。我3歲左右搬到忠南公州,在那裡讀到小學兩年級,以前爸爸賣米,媽媽經營一間叫做「忠南商會」的小雜貨店,在路旁賣車票等各種東西。那時的生活比較寬裕,因為我記得當時同學揹的是布制的書包,但我揹的是真正的皮革書包,還穿著皮鞋上學。
後來因為父親事業不順,我們搬到水原,住在水原的那兩個月,父母把哥哥和我寄養在隔壁人家家裡。當時我很害怕,擔心父母不會來接我們。
那時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有些孩子會被送到孤兒院,或是送給別人領養。我大概9歲就開始懂事了,我跟哥哥寄人籬下時,是由我來照顧大我3歲的哥哥;即使後來和父母住在一起,我還是覺得要好好表現,似乎是從那時開始得了「乖孩子病」,從不會喊累,總是以身作則。村裡的長輩們總說,喜子體內住著一條蟒蛇。
我下面還有跟我分別差3歲、6歲、9歲的弟弟妹妹,因此,身為五個兄弟姊妹的長女,我長大後還要照顧他們。59歲的妹妹現在打電話給我時,還是會說「好的,姊姊」,我真的是像媽媽一樣的姊姊。我最近經常在大腿上扎蜂針,真的很痛,但我總是一聲都不吭。中醫師說,第一次看到這麼能忍的人。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就習慣忍耐。
學校⋯⋯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能說出這件事。我之前高中讀夜間部,而且因為學費太貴了,我得打工賺錢,所以我白天在大學辦公室打雜,晚上去上課,讀夜間部的高中生都要這樣子半工半讀。晚上去上學這件事讓我覺得很丟臉,有好一段時間都沒能說出口,現在能說出口,代表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畢業後去運輸公司上班,當時教授們都阻止我,他們說運輸公司很危險,何必去那裡?他們要我繼續待在學校,在學校很舒適⋯⋯但我覺得自己每天都被當成涉世未深的人,似乎永遠都只是「張小姐」,我想要成長。
我在運輸公司從開收據、數錢的工作開始做起,後來進入會計部門。我真的很認真工作,就算被問到好幾年前的事情,我還是能說得很詳細,所以上司都只找我問事情。我領到薪水後一定會買書來看。我省吃儉用存下來的錢會先交給媽媽,至於剩餘的錢,我就自己省著用,過得還算開心。
我曾在下班後參加YWCA的手語講座,現在也常和當初上班認識的姊姊們約出來見面,一起聊天時,會聊到當初真的忍了很多。那時社會的風氣相當重男輕女,要是發生在現在,大家會說那是#MeToo事件,但當時我常聽到的卻是「因為你是女人啊⋯⋯」;走路走到一半被拍屁股、摸肩膀這種事屢見不鮮,就算很討厭也沒能抗議。
我叔叔幫我做媒,帶我去相親。媽媽說她沒臉見人,因為兒女還沒嫁出去很丟臉,當時我27歲,哥哥30歲。我透過相親認識先生後,他那一個月內每天都來找我、向我求婚,他從位於仁川的公司開兩個半小時的車到水原;最後,我們在認識一個月又二十天後就結婚了,等於是跟陌生人結婚(笑)。
那時似乎是在逃避,因為如果想要搬出來住,除了結婚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我那個月天天都看到他,對他的印象僅止於「他感覺是個老實人」。不過在那個年代,人們常常沒見過幾次面就結婚。
結婚後辭職是理所當然的,連穿的衣服都變得不一樣了,每天都穿著家居服做家事、照顧小孩,很自然地走上了賢妻良母的道路。第一次當媽媽、當媳婦⋯⋯真的很難,根本沒有人教我「如何當一個母親」!
我從沒想過要跟先生分攤家務或育兒,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準備早餐,送兩個兒子上學後就開始打掃家裡,忙得沒時間睡午覺,晚上也沒辦法早睡。孩子們還在念書時,會讀到晚上十二點,所以我都要開車去接他們。雖然家務也是工作,但我好像不覺得那是「工作」,久而久之,我的生活變成以孩子們的上學時間、丈夫的下班時間為分界點;而且婆家在京畿道華城務農,我週末也會去幫忙農活,那時候還為了能幫忙農活而考了駕照。
我也不是沒做過賺錢的工作,社區裡的媽媽們會一起做很多手工藝,作為一種副業⋯⋯我妹妹開了一家照片沖洗店,我也會去那裡繞繞,幫忙顧店,做了十年左右;趁白天做家務的空檔去幫忙,這樣一個月可以賺120萬韓元,我存下這些錢,居住環境也因此改善了,但是先生仍不認可我。
每次先生打電話來,劈頭就問:「孩子呢?」那時我覺得自己做的與其說是工作,倒不如說是在幫妹妹的忙。
後來IMF外匯危機爆發時,先生就申請名譽退職了,但我有收入,所以我叫他不用擔心,還讓他去旅行散心。他回來後看到我在工作,就問我:「要不要載你?」那好像是他第一次認可我所做的是「工作」。
後來公婆身體不好,我們就搬到他們家隔壁,公公需要洗腎,都是我開車送他去醫院。起初十年是每個月從安山往返首爾兩次,最後兩年是一週要去安山醫院三次。由於住得很近,我會做些小菜放在他們家、也幫忙打掃,等於我做了兩個家的家事,這樣的生活持續了很久(笑)。
公公去世後,我就把婆婆接到家裡,但後來婆婆罹患膽管癌,後來還是不敵病魔去世。送他們去醫院時,醫護人員都問我是不是女兒,我就這樣照顧了十五年。去年7月開始,我媽媽也搬過來住了,本來她的身體很硬朗,但現在也退化了,這種照顧沒完沒了(笑)。
每天要為長輩張羅三餐真的很困難,其實我早就預料到年紀大了得照顧父母,所以提前考取了照護員的證照。我就是接受了現狀,不覺得辛苦,也不感到委屈,可能是看在我照顧公婆的份上,先生對我媽媽也很好。
我不會對子女抱有期待,以後如果我生病了,我要搬到療養院;我們這一代好像就是這樣,現在看到兒子和兒媳一起工作、一起做家事就覺得很棒了,那畫面很美。
回顧我的人生,我總覺得自己虧欠家人。通常大家都把工作的人視為家裡的經濟支柱,不過,雖然我有賺錢,但我覺得我做的都是日常生活的事情,而不是在工作。我有個朋友當了奶奶,我就跟她一起(替還在上班的朋友的女兒)照顧孫女,照顧了五年。
那位朋友的女兒說:「喜子奶奶(朋友孫女對喜子的暱稱)是第一名的阿姨,到首爾一個月可以賺300萬到500萬韓元。」當時聽到這段話,我實在不敢置信──我好像從來沒跟什麼人提過我的名字,參加媽媽聚會時,就算彼此已經認識將近二十年,通常也不知道彼此的名字,因為只會互稱「○○的媽媽」。
你們說要做名片⋯⋯那我的頭銜應該是大姊、長媳、總務、照護員、韓式料理廚師、最佳司機?(笑)就直接說是志工好了,我以後也想繼續當志工。
兒子叫我去學諮商,他說我肯定能做得好,我想傾聽和我年齡相近的人的痛苦。當我思考自己是誰時,只會想到我是某人的媽媽、某人的妻子,但聊了這麼多之後,我覺得我是很不錯的人。謝謝你一直聽我說,也謝謝你問我做過的事,我現在要去幫媽媽做晚餐了。和我一樣同為「內人」的朋友們,我們都很棒,我們都辛苦了。
【摘文2】如果有一天,她們的勞動消失了
假設有個宇宙反派降落在韓國,這名壞蛋能在彈指之間讓特定族群消失,而他決心要暫時帶走60歲以上的婦女。這時,許多人陷入了悲痛,但可能也有一些人覺得:「年紀大的女性對經濟貢獻的比例不高,這應該不是最糟的情況吧?」
有些人很在意「數字」和「損失」。以2021年上半年來看,在2064萬6,569名受雇勞工中,60歲以上的女性有153萬3,410名,這表示她們一旦消失,勞動力將減少7.4%。然而,有些人卻因為要消失的是高齡婦女而鬆一口氣,因為他們在計算高齡女性的勞動在韓國國內生產毛額(GDP)中所占的比重、高齡女性中達到免稅門檻的勞工人數等數值後,對老人勞動抱持著厭惡態度,認為「這些老人的打工是建立在稅收上」、「用稅金供他們做粗活」,因此這些人感到樂觀。
沒想到,事實是──60歲以上的女性消失後,韓國立刻癱瘓了,因為從事「必要勞動」的工人有四分之一都消失了。
每四名必要勞動者中,就有一名是60歲以上的女性勞動者。我們分析統計廳對各地區僱用狀況調查的微觀資料(2021年上半年)發現,在整體必要勞動者336.79萬人(受雇勞工)中,60歲以上的女性有87萬4,185人(26%),若算入50歲以上的女性,其占比將達到42.1%。在全體受雇勞工中,高齡女性的存在感並不高,但只要用「必要勞動」這個放大鏡靠近觀察,她們的存在就變得非常明顯,令人驚訝。
必要勞動是新冠疫情後出現的概念,意指在災難中為了維持社會機能而不可或缺的工作,由於這些勞工在工作過程中不可避免會與人接觸,因此染病風險高,通常是保護民眾生命和身體、在危機狀況中支援弱勢群體的工作。大多數必要勞動者都不算在居家辦公的群體中,在疫情爆發初期,他們毫無防備地暴露在染疫風險中,等到疫苗開發出來後,他們才被指定為優先接種對象。儘管這麼做不僅是為了保護他們,也是因為社會沒有他們就無法運作。世界各國會以不同的詞來描述必要勞動,如Essential worker(必要勞動者)、Key worker(關鍵勞動者)、Frontline worker(前線勞動者)等,但本質是相同的。
什麼樣的職業是必要勞動?韓國於2021年5月18日制定了《指定必要業務及保護並支援從業人員之相關法律》(필수업무 지정 및 종사자 보호·지원에 관한 법률),然而,該法律只是將必要勞動者定義為「災難發生時,為了保護民眾的生命和身體或維持社會功能的穩定,而從事必要業務的人」,並沒有具體提到行業類別。
我們參考韓國標準職業分類,認為①家務助理及育兒保母、②護理師、③照顧及保健服務從業人員、④送貨員、⑤醫療保健相關從業人員、⑥社會福利相關從業人員、⑦汽車司機、⑧清潔人員及環境美化員31等八個職業屬於必要勞動,並參考了2020年12月政府發表的「必要勞動者的保護與支援對策」、首爾勞動權益中心和城東區政府的研究資料等32。為了使用標準職業分類的子分類統計數據,我們分析了統計廳各地區僱用調查微觀數據,年度數據則跟2021年最新數據一樣,統一使用上半年資料。
分析結果顯示,必要勞動者中67.4%是女性,32.6%是男性。除了送貨員和汽車司機之外,其他職業的女性比例都壓倒性地高過男性。女性比例最高的職位是家務助理及育兒保母(98.2%),其次依序是護理師(94.7%)、照顧及保健服務從業人員(93.8%)、醫療保健相關從業人員(91.4%)。
高齡女性的比例尤為突出,若將全體必要勞動者按年齡層人數排序,由高到低依序是五十來歲女性(16.2%)、六十來歲女性(15.7%)、四十來歲女性(11.2%),以及70歲以上女性(10.2%)。由此可見,說必要勞動是由女性、尤其是高齡女性支撐,並不為過。
【摘文3】在媽媽的勞動中,讀懂了女性的勞動
曾擔任大型出版社編輯的金恩華(35歲),在辭職後創辦了名為「女兒細胞」(딸세포)的一人出版社,她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媽媽養活了我》(나는 엄마가 먹여 살렸는데),這本書描寫了恩華媽媽的故事。恩華親自採訪了媽媽,並寫出媽媽的生活,她的出發點是希望媽媽不要對離婚感到羞愧,也希望讀者能將媽媽視為一位堅強的勞動者。恩華說:「寫完書後,我覺得舒服多了,因為我知道了媽媽不是(我)該守護的人,而是非常堅強的人。」
恩華在書中寫道:「媽媽一直以來都為了養活家人工作,但只有男性會得到『一家之主』或『主要生計者』這種光榮的稱謂。我想在這裡反對這點,並理直氣壯地說:『是媽媽養活了我,不,是媽媽救了我。如果沒有她的勞動,就不會有現在的我。媽媽是我們家的主要生計者,是真正的家長。』」
書籍出版後,恩華收到了很多女性讀者的回饋,她們也想寫出自己媽媽的生活,而且這些女兒也見證道,她們和她們的家,其實也是母親養活的。
我們去見了幾位像恩華這樣,以勞動角度看待母親的女兒,在與她們見面後聽到了她們的故事。1980至1990年出生的她們,為什麼會對媽媽的勞動感興趣呢?她們說,當她們開始從勞動者的視角看待母親時,也正在擴大視野,重新評價包括自己在內的「女性勞動」。
恩華人生的第一個記憶,是把椅子拿到廚房的洗水槽旁,踮起腳幫媽媽洗碗。「爸爸在經濟方面缺乏能力,又會施暴,所以母親看起來總是一副無可奈何。我從很小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應該要幫助媽媽。」很多女兒從小就能同理母親的情緒,並分擔母親在家庭中的勞動。恩華說:「從小開始,就是我在幫哥哥倒水,家裡自然而然形成了這樣的氣氛。」
恩華媽媽每天早上6點起床,為孩子們準備便當,也為生病的公婆做飯,總共要做十人份的飯菜。起初恩華媽媽是在工廠做女工,結婚後經營過民宿、漫畫店、韓服店,也在眼鏡工廠和出版物流中心工作過,如此養活了一家人;此外,還擔任照護員很長一段時間。儘管如此,媽媽卻常常感慨道:「我這一輩子都沒有什麼成就。」媽媽離婚後變得更負面,使恩華燃起一股必須保護媽媽的責任感。
前面提過的馬惠媛(36歲),她看著媽媽尹順子的一生時,心情同樣複雜無比。由於父母忙於生意,惠媛的兄弟姊妹在奶奶的撫養下長大。每當媽媽和奶奶吵架時,媽媽只會期待女兒們能夠理解。惠媛說:「如果我跟奶奶講話,媽媽就會傷心;但如果我跟媽媽講話,奶奶就會傷心,好像全家人將各種情緒都傾倒在我身上。」
在元美羅(36歲)的記憶中,媽媽看起來總是相當疲憊。家裡因為經濟困難而爭吵不休,使得媽媽總是精疲力盡。媽媽從外面工作回來後,要為奶奶做飯、還要做家事,美羅看到媽媽時感到既歉疚又鬱悶。「那時我才發現,媽媽下班回來後還要繼續工作。一方面覺得歉疚,另一方面又埋怨媽媽為什麼要這樣生活。」
自從美羅就職後,她逐漸能用不同的視角看待媽媽。美羅的爸爸是名木匠,卻因為工作途中受傷,她不得不開始賺錢養家,所以高中畢業後就在一間小公司上班。美羅說:「開始上班後,我才知道媽媽的人生沒有別的選擇。我雖然想上大學,卻無法讀大學,這情況就和媽媽國小畢業後馬上開始工作一樣。那時我才理解,原來媽媽在比我還小的時候,就被迫開始勞動。」後來,美羅憑藉自己的能力進入大學就讀。
即使深愛媽媽,要直視媽媽的生活並以文字記錄下來,也不容易。女兒們會自責自己造成家裡的經濟負擔。恩華說:「如果想觀察媽媽是什麼樣的人,就必須觀察我自己,因為媽媽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假如我是她的話,會做出怎樣的選擇?』這想法不斷讓我產生罪惡感、歉疚和埋怨等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