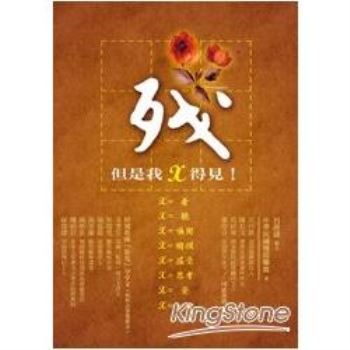第九篇:我能感受妳最美的臉
親暱地捏著老婆的臉頰,對著這張他從沒有見到,卻這麼親近的臉說:「臉啊,妳到底漂不漂亮呢?」
如果伴侶的眼睛看不見,那還需不需要裝扮?
首先,我們得面對一個迷思:盲人的伴侶,難道都隨隨便便、邋遢到家嗎?
對於范雪,她大概就會第一個站出來投反對票。
不當黃臉婆
「我要面對的不僅是家裡的先生,我會和他獨處,但我也要面對外面的世界。總不能出去讓人家說,我家有個黃臉婆。」
范雪的丈夫是名視障朋友,但她出門時,多半還是會化妝,范雪有句名言:「女人不化妝,跟沒穿衣服一樣」。她仔仔細細的化妝,一個步驟都不馬虎,粉底、胭脂、香水都是必備的。有一次,她陪丈夫出門,要丈夫等等,她要去補一下粧,她坐在梳妝台前,這一補就讓丈夫足足等了一個鐘頭,差點就要遲到了。
范雪買了多種牌子的化妝品,每種的瓶子形狀和功能都不一樣,香氣非常的濃,常常吸引丈夫好奇而打開化妝櫃,摸摸這些瓶子,詢問每種香氣的來源和功能。丈夫對范雪兩頰的腮紅,非常的好奇。范雪曾跟他閒言一句:「擦了這種腮紅,臉頰兩側就跟蘋果一樣紅撲撲的。」想不到丈夫正色問道:「臉頰變成紅蘋果,這對女人很重要嗎?」范雪沒好氣的回答:「不是變成蘋果,我又不是華盛頓蘋果,是很像蘋果的顏色。」
其實,范雪平常化妝,也沒有抹得大紅大綠的習慣。有一次在宴會上,有位女士的嘴唇擦成接近紫色的暗紅,她就看了很久,忍不住跟丈夫說悄悄話:「看哪,三點鐘方向有位太太的嘴,就像過熟的蘋果。」丈夫啼笑皆非答道:「我又看不到,看什麼看?」
感受妝扮
在一些正式的場合前,像范雪要出去見客戶,她會用眉筆畫睫毛,整套的粉底在梳妝台前忙著打扮。丈夫默默走過來,摸了摸她的瓶瓶罐罐,丟下一句評語:「喔,今天很慎重的樣子。」
丈夫對妻子的化妝,自有一番感受和接收的方式。最少可以分成十種方式:
第一, 摸妻子的化妝品,就可以知道她今天的打扮程度。
第二, 聞妻子身上的香味,也可以八九不離十。
第三, 問妻子今天美不美,讓她自己評分,從一到十。
第四, 聽聽別人對妻子的意見或評語。
第五, 從妻子停留在梳妝台前的時間長短,也可觀出一些端倪。
第六, 注意妻子在衣櫃前停留的時間,會不會拿出幾件衣服來做搭配。
第七, 聆聽妻子身上有沒有首飾發出的聲音。
第八, 和妻子一起出門後,聆聽別人的悄悄話。當然,別人若全無反應,那也是一種反應。
第九, 留意妻子會不會去美容院做頭髮。
第十, 憑直覺。有位丈夫就說,妻子化妝後講話的聲調會變得不一樣,這種感覺很微妙,或許是因為變得有自信了,他不知道的是,其他女性是否也是如此?
本身是盲人的曾淑媛提到,她參加的合唱團要上台表演前,視障的團員會自己化妝,或是互相化妝。她們穿著素樸的旗袍,表現出整體感,也用同樣的化妝模式,所以並不難。大體就是撲一點點的粉,把頭髮紮起梳成髻,噴一點點香水,這樣上台就顯得高雅亮麗。
平時練合唱時,大家已經很熟,不會去注意有沒有化妝的問題,但到了正式的場合,曾淑媛說,有了化妝和打扮,感覺就變得很不一樣,整個心情也莊重了起來。幾次以後,熟門熟路了,化妝一點也難不倒曾淑媛。
品味—不一定用看的
尤喜很喜歡老婆穿上平時不隨便穿的衣服。在那種場合中,老婆甚至連他穿什麼衣服,都會有意見。至於顏色怎麼搭配,衣著是否相襯合宜,就全由老婆大人來做定奪。
尤喜比較重視且有感覺的是衣服的質料。有些衣服軟軟的,穿在身上很舒服,他就問老婆:「這件衣服是什麼顏色的?」老婆就跟他說:「藍色的。」尤喜便記起來。有一天,小姪子來看他,剛好尤喜要換衣服,要小姪子挑衣服給他,小姪子不知該選那件,尤喜便說:「挑那件藍色的吧。」這句話,讓小姪子嚇了一跳。
尤喜有件衣服,質料是混紡的,感覺較粗,穿在身上總覺得燥熱。尤喜問道:「這件衣服是什麼顏色的?」老婆說:「紅色,很艷的紅。」尤喜說:「難怪。」在他的心裡,他始終覺得,每種顏色都是有感覺的,只是你要先開發自己感覺顏色的方式。
盲人對顏色、氣味,也許真的有一種特殊的感受,像昆蟲的觸鬚感官。艾爾帕西諾在電影《女人香》飾演的退休盲軍官,可以從女舞伴身上的香水,說出是何種牌子,逗得女舞伴芳心大亂。那不僅是艾爾帕西諾的個人魅力,其實,也是編導藉著這段劇情在向盲人的品味致意。如果,我說的是如果,跟艾爾帕西諾提起,台灣有句俗語說:「嫁給青瞑尪,抹粉無彩工。」他一定會從鼻孔噴氣地說:「我演過的那個角色肯定不會同意,至少,他會說,女人在我面前絕對不敢擦過於廉價的香水。」
與愛同行
艾信一直記得他和現任女朋友第一次見面時,嗅到的的一陣淡淡的香氣,後來他才知道,那並不是香水,而是某種品牌的洗衣精。後來他在其他女孩身上也嗅到過,卻沒有第一次從女朋友身上飄散出來時,那樣的印象深刻。或者應該說,讓他如此得如痴如醉。那天,艾信並沒有過於在意打扮和衣著,他喜歡讓自己穿上顯得有自信的衣服。他相信在他注意到這個女孩前,女孩就已經看了他很久,然後才跟他說:「你這件衣服真好看。」他們的交往,就是這樣開始的。
談到未來感情的進展,艾信說:「我大學時代就交過幾個女朋友,但多半只是興趣相投,走得比較近,後來也就自然而然的散了。和現在的女朋友雖然感情穩定,彼此認為還可以發展下去,但未來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能不能結成正果,我們都不敢打包票。」
現實裡,明眼女性嫁給盲人老公的比例,多過於明眼男性娶盲女的。尤喜說明這個現象時表示,「沒辦法,結婚不僅是兩個人的事,也涉及到雙方家長。」他不僅要獲得美人心,也花了許多時間和女方家長溝通。一開始,太太那一方的親屬都是反對的,擔心把女兒嫁給他,就是受罪的開始。「沒有辦法,」尤喜說,「我們選人家,人家也會選我們。」
尤喜還記得,他未來的岳母曾說道:「我女兒那麼的愛漂亮,如果以後嫁給你,會不會連她今天打扮的漂不漂亮都不知道,會不會一朵鮮花插在…」雖然沒有說下去,但尤喜已經知道未來岳母的擔憂,他趕緊說「在我心裡,她永遠都是最漂亮的,不管有沒有打扮,我每天都會讚美她。」
也許這句話打動了女孩的媽媽,以後他有機會到女孩家裡做客,女方家長待他就較為殷勤了。後來,靠著女孩的堅持,尤喜誠懇長久的溝通,讓他們相信,他雖然眼睛看不見,但並非是沒出息的。有了雙方家長的祝福,他們才一起攜手走上了紅毯。結婚兩年後,有一晚,尤喜勾動心弦地問道:「老婆,嫁給我妳覺得辛苦嗎?」
老婆笑道:「是啊,我是個現代的青蚵仔嫂。」
也許剛認識時,身體的條件會占很大的因素,但相處日久後,兩個人的個性合不合得來,才是決定能不能走下去的關鍵。尤喜現在會捏老婆的臉頰,對著這張他從沒有見到,卻這麼親近的臉說:「臉啊,妳到底漂不漂亮呢?」老婆就問:「說,你說啊。」他想起了幾年前跟丈母娘許過的承諾,正色說道:「那還用問嗎?在我心裡,這張臉永遠是最漂亮的。」
第五篇:盲人來報路
也許,未來有一天,在異鄉的街道,一個盲眼的異鄉人也能在被問路時,告訴你,這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咖啡館該怎麼走。
報路記
最簡單的問路,發生在每天的生活裡。有一個問路的人,也有一個被問路的人。遊戲規則其實簡單,又想當然耳:有人不知道該怎麼走,在路陣間迷失方向,他趕緊攀問一個剛好經過的路人,心想,也許這個人會知道該怎麼走。只見這個人停住,略做思索,也許兩個眼珠一轉,骨碌碌地溜出他的答案:「就前頭紅綠燈過了再右轉。」或者,眼白一翻,聳聳肩:「我也不知道。」
當然,問路,想必有個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問路的人,總會找個明眼人,心想憑他們的視力,能勝認指點迷津的任務。他們從沒有想過要找個盲眼人問路,「求道於盲」這類印象僅僅盤據在他們的腦海意識,簡直已成為一種信仰。他們想,如果一個看得見的人還得向盲人問路,那應該算是什麼,故意還是作弄?
在明眼人的教育養成過程裡,一個優雅文明的好公民應該勇於幫助盲人同胞。在路上看見盲人柱著手杖過馬路,應該過去幫忙牽著他過馬路。如果,有個盲人站在路邊,猶豫著要走向哪個方向,明眼人應該靠過去,熱心地問一句:「請問,你迷路了嗎?需不需要幫忙?」幫忙,總會從四面八方,從人們的唇間流向盲人,這真是個熱心的城市。
陳俊宏常常會覺得好笑又好氣,他拄著手杖站在紅磚道的印度紫檀樹下,涼風徐徐吹來,但沒多久,就會有聲音冒進來,衝著他說:「先生,您迷路了嗎?需要幫忙嗎?」心情好的時候,陳俊宏會說:「謝謝,我沒有迷路,這段路我很熟。」有一次,一個男孩的聲音一直纏著他,大概學校老師要他們日行一善吧,最後陳俊宏只好對個這個男孩說:「我正在欣賞樹上的鳥叫聲耶,請不要來打擾我。」一個盲人,失去了觀看顏色的能力,難道,就不能停下腳步,欣賞一陣鳥聲奏鳴嗎?
陳俊宏很熟悉他常走的路段,也許比明眼人還更熟悉。一個明眼人走在路上總是形色匆匆,只顧著看燈號和路標,更常漫不經心走路。但盲人心內自有他的道路地圖,他知道在第幾棵行道樹間的紅磚有個破角,雨天後踩踏下去會濺出水花。他知道在某條街道的轉角,某面牆壁顯得特別光滑。他也知道,從這裡出發再走幾步路,將會聞見獨特的麵粉香氣。
有一次,媽媽的新外傭要上街買東西,卻不認得路,媽媽要俊宏帶路,外傭看了看俊宏,卻不答腔。俊宏笑了笑,他知道外傭對他帶路的能力顯然有點懷疑,也不囉唆,當下帶著手杖就走出門,後面的腳步聲跟著他,卻保持著距離。陳俊宏照著自己的心內地圖和節奏,在街上左轉、右轉,熟悉的道路、氣味和聲音依然圍繞著他,最後,他停在商店前,後面的腳步聲緊緊跟上來。陳俊宏仍然微笑,這次,是帶著點那麼勝利的微笑。
捷運車站內,是陳俊宏另一張熟悉的心內地圖。迷宮般穿梭的捷運車站,常讓初來的旅客手足無措,繞走冤枉路。有一次,在昏暗的甬道間,有個聲音大概也沒發現陳俊宏是個盲人,就衝口問他:「請問出口在那裡?」陳俊宏不急不徐就跟他說:「別急,你再往前走十幾步,右轉,走約十五步,就會聽見一陣車子停住引擎的聲音,因為出口外面有個沒有行人穿越蜂鳴器的十字路口,然後再左轉,走六步,你就會聽見手扶梯的聲音。」那個人向他道謝,繼續趕路,大概一直想不透,怎會有人用「走幾步路」這麼精準和聲音在報路的呢?
陳俊宏笑著說:「問路,一點也難不倒我。」
盲人地圖
也許,盲人的心內地圖不同於明眼人,他們認路的本事,有如一場場戲或一座座舞台攤開在腦海裡,走路就像腦中的換幕,連帶的觸覺、走位、方向、氣味和聲音都要跟著更換。明眼人認路,靠的是地圖和街號標識,盲人卻靠戲劇感和印象,2009年以色列特拉維夫教育大學的拉哈夫(Orly Lahav)發明的「盲人地圖」則使用了觸感─結合三D觸覺技術和操作桿,取代盲人的手杖闖蕩陌生地。陳俊宏後來還報過幾次路,他描述起來,其實就像記憶中一場戲的報幕者。當然,盲人報路,絕對不同於明眼人,他會說:「在這個十字路口,特別得注意從右邊竄出的摩托車,當你聽見急踩煞車聲,往往就來不及了。」
陳俊宏用他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求道於盲」是句不合時宜的老生常談,若是你真的願意「求道於盲」,攤開在你想像裡,或許是一張更細膩的心靈地圖?或許,明眼人才該在一排行道樹下停下腳步,同時停下紛亂之心,欣賞流連在樹椏間的雀鳥啼唱。道可道,非常道,向盲人求的「道」絕不僅於問路,他們的方向感和立體感,和明眼人相較,可說另有天地。
陳俊宏回憶在讀國中時,做幾何題目,尤其是那種立體圖形的題目,陳俊宏說的都比老師還清楚。他覺得盲人的立體空間感,其實更不受到視覺的影響,會直截了當地「觀看」到立體的全貌。有一次,數學老師在說明一個立體圖形的面積該怎麼計算,同學聽得霧煞煞,因為他們的想像無法從紙上的二度空間轉為三度,只見陳俊宏舉手問道:「老師,如果把立方體轉過來再剖開來,會不會算得更快一點?」這種「看」法,連老師也覺得驚訝。
2009年,拉哈夫設計的這套盲人地圖,靠的也就是盲人的立體空間感。當時研究者發表了幾則盲人試用成功的個案,其中一位是住在美國麻州紐頓市卡羅盲人中心的婦女。她的視力接近全盲,試著用操作桿探索中心的環境和一座四層樓的建築等等。電腦完全模擬實景,將建築物和街道數位化建置在電腦內,這名女性觸摸操作桿探索環境,若前方遇到牆壁或阻礙,操作桿就無法再往前推。這名女性只試過三、四回合,就能夠試著戴上眼罩進入真實環境來。
拉哈夫說:「透過模擬和回饋,為盲人建構了一張認知地圖,等到他們真的來到真實世界,操作桿就彷彿是把高科技的手杖。」拉哈夫稱為「認知地圖」的,我們稱為「心靈地圖」。更多為盲人架設地圖的努力,實際上還是利用「聲音」。例如「看和聽地圖」(Look and Listen Map)還曾在2011年得到德國WissenWert競賽的大獎。這個計劃的正式名稱是「給盲人的新地圖:互動式的有聲書世界地圖」,要把整個世界地理都有聲化,融入到聽覺的世界裡來。這套偉大計劃的實現,靠的是電腦、智慧型手機、有聲書和衛星導航系統的結合,從此,盲人的心靈地圖就不再局限於像陳俊宏那樣的,以為盲人只能生活在他熟悉的路段。這個計劃邀請全世界的盲人和明眼人一起加入,運用最先進的科技系統,完成這張龐大的世界地圖。
也許,未來有一天,在異鄉的街道,一個盲眼的異鄉人也能在被問路時,告訴你,這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咖啡館該怎麼走。「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這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名言,然而,這會不會是都市裡一名盲人最平常的生活寫照?就像陳俊宏,最近他迷上帶著有聲的導航系統在陌生的街道探索,聆聽雀鳥的意外驚喜,或者嗅到一陣酥人心胸的咖啡香。
「求道於盲這絕對是人生的必要,有了這種經驗,才能打破明眼人的偏見,」陳俊宏說,「不是我在為我們這一族吹牛,因為,當你開口問了以後,不僅能知道路該怎麼走,你還能分享我們心中把地理關係演繹成一場戲,分享我們生命裡的小小滋味和小小的美滿。」
「小小的美滿」究竟是什麼?對一個明眼人來說,敢不敢偶而閉上眼睛,走一段熟悉的路,接受到不同的生命經驗?或者讓一個面帶勝利笑容的盲眼人,為你帶上一段路,那時才終究體會出「求道於盲」的「試說新解」其實就是:「勇敢的嘗試一段新的體驗。」當然,勇敢的去問,也包括在生活體驗裡面。
「求道於盲」讓陳俊宏勾起的聯想卻是Google,他說:「現代人,不管眼睛看不看得見,根本就是求道於Google吧。」那天,他看到一堆人坐車,好像是迷路了,正不知怎麼辦,一堆人開始研究起方向,然後他?見了一個很權威的聲音從亂中一枝獨秀,說道:「聽我的準沒錯,就往這個方向走。」車內唯一的盲人聆聽著有聲的導航系統,指出了最正確的方向。
「求道於盲」,真好,就讓我們從此放心的求盲於道吧。」
黑暗對話
明眼人倚賴視力進行溝通、理解和看見,當有人問說:「請問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看見』?」時,其實他想知道的並不僅是「看見」,而是「理解」和「知道」。那麼,明眼人蒙上眼睛,或者進入一個全黑的房間內,卻仍然被要求要持續溝通、理解和知道時,問題就來了,而且來得非常的戲劇化。
其實,這就是源基於德國的「黑暗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的設計原意。在台灣,也有「黑暗對話」,也有盲人同胞在黑暗的房間裡,成為組織和群眾溝通的帶領者,徹底地顛覆明眼與盲者間、領導與服從間、協助與等待援助間的既定戲碼。
謝泰山本身就是名「黑暗對話」的培訓師。談起「黑暗對話」,他的話匣子一開,顯得興奮異常。謝泰山說,當參與者進入「黑房」後,就是明眼人必須「求道於盲」的時候了。處在全然黑暗的兩個小時內,要玩遊戲、進行溝通、還得分組完成任務。而在這個暗黑的過程裡,一個人在光亮世界裡無法察覺的盲點、領導風格的缺陷,或者說白一點,他是不是像他自己所相信的那樣,是一個品格高貴的人,此時都會昭然若揭。
在光亮世界裡,明眼人必須靠眼神的捕捉來得到回饋,一個微妙的眼神,或是察覺別人臉上的反應,來知道他今天的穿著是否得體。把自己和別人的眼神都抹去後,顯現的,是一個稱為「性格原型」的東西。心理學家榮格當年在論「心理原型」時,是用神話角色來做人格分類的嘗試,如大地母親、治療者、魔術師、煉金術師這樣的類型,他其實也沒有想到,視力和失去視力,也可更接近人格的原型。
謝泰山表示,在「黑暗對話」裡,氣定神閒的是盲人,慌亂無助的反而是明眼人。謝泰山也聽過「求道於盲」、「青瞑的看戲」、「青瞑的毋驚槍」這類的成語和俗語,他說,一點也不是這樣,在全然的黑暗中,槍瞄準著一個明眼人,他也未必會知道。
「黑暗對話」起源於德國,一九八八年德國創立第一家非營利事業體「對話社會企業」,簡稱DSE(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創辦人叫安德烈.海勒奇博士(Dr. Andreas Heineelte),閱讀他的生平和創辦理念,當然充滿著崇高的理念,我們卻聯想起,也許每個人小時候都玩過的「蒙眼抓鬼」遊戲,由別人帶領你走一小段路,讓你轉幾個圈,當你失去方向感,只聞其聲卻不見其影時,你還有辦法抓到同伴所扮的「鬼」嗎?
也許,在德國的成長歲月裡,安德烈.海勒奇也玩過這樣的遊戲。也許,他曾經被放在一個黑暗的房間內,引發了他日後建造社會企業的構想。台灣則在二○一一年,由謝邦俊醫師獲得DSE的授權,成立了「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北DiD)。當台北有了這套活動後,謝泰山積極參與,目前已是活躍的視障培訓師。
在「黑暗對話工作坊」的說明中有這麼一段話:「活動是在完全隔離所有光源的漆黑環境中進行,除了促使參與者必須適應突如其來的短暫失能外,同時必須強迫自己慢下步調,觀照內在,忠實地省視自己的核心價值。」這段文字中,有沒有注意到關鍵詞「慢下步調」?在突如其來的短暫失能裡,人們才能學習做到「慢下步調」。
「黑暗對話工作坊」裡有個黑房,也有個光房。「黑房」往往聯想到「暗房」,在早期還要用底片沖洗照片的年代裡,把膠卷送進暗房經歷顯影過程,才能沖洗出明亮的照片。現在,隨著照相技術的發達,沖洗照片早就成為記憶。然而,對重新發現自己、顯現自己來說,「黑房」的設計無異就是能讓心顯影的一間「暗房」。
「你有沒有試過閉起眼睛、不看表情,而能彼此傾聽的經驗?那其實是種挑戰。」謝泰山說。
在黑暗裡,會讓我們聯想起什麼?心理學知名的剝奪知覺實驗,就在測試這個禁忌的邊緣。心理學家發現,視覺和其他感官被剝奪的人,容易焦慮、緊張、心跳加快,時間一長,就會影響身心健康。但還有更嚴重的是,剝奪視覺能力,也會讓明眼人失去了原本溝通的能力。
謝泰山說,一般人已習慣看網路、上臉書或到 Google 找資料,電子通訊設備已有如他們的「另一隻眼睛」。溝通時,有些人習慣使用白板、記事簿,一定要把自己要講、要記的文字都寫下來不可。然而,「黑暗對話」提供的是一個不能使用 Google,也沒有白板的溝通情境,這時,還要他們在時間限制內完成任務,會讓許多人因而慌了手腳。
有些平時當主管的人在黑房裡,還會照著過去的習慣說:「請看我這邊。」他和同事講話時,會不自覺地點頭、搖頭,屬下只要察言觀色,自然就會調整談話內容,彼此互通心意,溝通遊戲自此就算大功告成。謝泰山說,在黑房裡,已習於下命令的人,會更覺得不能適應,但往往經歷這段黑暗時光,他們的收穫也更加的豐富。
走出黑房,來到光房,分享從自主者變成非自主者的感受。在黑房裡接受過視障培訓師協助的人,更能夠深刻體驗,明眼人可能變成非自主者,而盲的人卻可能成為主宰與協助的角色。
這場經歷後,生起的是現代人始終缺少的一種美德,叫作「同理心」。走出自己原本熟悉、習以為常的世界,才有辦法空出心思,接納另一個不同的世界。
從此看來,「黑暗對話」提出的,也許是另一個生命教育的機會,不僅適用於盲和見的對比,適用於商業管理和職場溝通,將來也可運用在親子溝通間。許多親子──不管是做子女還是為人父母者,往往只習慣見到自己的世界,卻進不去對方的心思。在黑房裡,親子還可試著建立另一種溝通的方式,完成指派給他們的任務。
黑暗對話中的生命教育
「人們往往看到更悲苦的處境,藉此來提醒自己,就像那個老故事裡,一再怨嘆自己沒鞋子穿的人,有一天遇到了沒有腳的人。」所以,明眼人會覺得更悲苦的是「盲」,用此來提醒自己。然而,兩者只是感官經驗和世界的不同,是不一樣,卻不見得有階層和等級的差別。
在黑暗對話中,培養同理心的溝通是一項重點。其實同理心的養成不只是在這類的課程中而已,也應融入我們的社會教育當中。在台灣,「生命教育」可以說是教育界的顯學,其實,當年台灣學校推動生命教育,是以降低青少年自殺率和犯罪率為出發點的,到了現在,內容和理念一再地修正,也繼續擴充,做法從養小動物到種下一棵樹、照顧老人都算。但是,台灣實行的生命教育,似乎總是繁雜忙碌而不見得會有效果。
「生命教育」的最終目標,其實,仍離不開肯定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就如我們常說的,每個生命都會有它的價值,如果你覺得並不是這樣,那可能是你還沒有找到,你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和光陰去尋找。
看過《逆光飛翔》這部電影,見過鋼琴師黃裕翔的精湛表現,還有那總是笑笑的一張臉、氣定神閒的模樣,我們不免會深思,如果當年不是黃裕翔的媽媽這麼辛苦地去栽培他,讓他有機會利用自己的天賦去發光發熱,今天,我們就將失去道說一則傳奇的機會了。
親暱地捏著老婆的臉頰,對著這張他從沒有見到,卻這麼親近的臉說:「臉啊,妳到底漂不漂亮呢?」
如果伴侶的眼睛看不見,那還需不需要裝扮?
首先,我們得面對一個迷思:盲人的伴侶,難道都隨隨便便、邋遢到家嗎?
對於范雪,她大概就會第一個站出來投反對票。
不當黃臉婆
「我要面對的不僅是家裡的先生,我會和他獨處,但我也要面對外面的世界。總不能出去讓人家說,我家有個黃臉婆。」
范雪的丈夫是名視障朋友,但她出門時,多半還是會化妝,范雪有句名言:「女人不化妝,跟沒穿衣服一樣」。她仔仔細細的化妝,一個步驟都不馬虎,粉底、胭脂、香水都是必備的。有一次,她陪丈夫出門,要丈夫等等,她要去補一下粧,她坐在梳妝台前,這一補就讓丈夫足足等了一個鐘頭,差點就要遲到了。
范雪買了多種牌子的化妝品,每種的瓶子形狀和功能都不一樣,香氣非常的濃,常常吸引丈夫好奇而打開化妝櫃,摸摸這些瓶子,詢問每種香氣的來源和功能。丈夫對范雪兩頰的腮紅,非常的好奇。范雪曾跟他閒言一句:「擦了這種腮紅,臉頰兩側就跟蘋果一樣紅撲撲的。」想不到丈夫正色問道:「臉頰變成紅蘋果,這對女人很重要嗎?」范雪沒好氣的回答:「不是變成蘋果,我又不是華盛頓蘋果,是很像蘋果的顏色。」
其實,范雪平常化妝,也沒有抹得大紅大綠的習慣。有一次在宴會上,有位女士的嘴唇擦成接近紫色的暗紅,她就看了很久,忍不住跟丈夫說悄悄話:「看哪,三點鐘方向有位太太的嘴,就像過熟的蘋果。」丈夫啼笑皆非答道:「我又看不到,看什麼看?」
感受妝扮
在一些正式的場合前,像范雪要出去見客戶,她會用眉筆畫睫毛,整套的粉底在梳妝台前忙著打扮。丈夫默默走過來,摸了摸她的瓶瓶罐罐,丟下一句評語:「喔,今天很慎重的樣子。」
丈夫對妻子的化妝,自有一番感受和接收的方式。最少可以分成十種方式:
第一, 摸妻子的化妝品,就可以知道她今天的打扮程度。
第二, 聞妻子身上的香味,也可以八九不離十。
第三, 問妻子今天美不美,讓她自己評分,從一到十。
第四, 聽聽別人對妻子的意見或評語。
第五, 從妻子停留在梳妝台前的時間長短,也可觀出一些端倪。
第六, 注意妻子在衣櫃前停留的時間,會不會拿出幾件衣服來做搭配。
第七, 聆聽妻子身上有沒有首飾發出的聲音。
第八, 和妻子一起出門後,聆聽別人的悄悄話。當然,別人若全無反應,那也是一種反應。
第九, 留意妻子會不會去美容院做頭髮。
第十, 憑直覺。有位丈夫就說,妻子化妝後講話的聲調會變得不一樣,這種感覺很微妙,或許是因為變得有自信了,他不知道的是,其他女性是否也是如此?
本身是盲人的曾淑媛提到,她參加的合唱團要上台表演前,視障的團員會自己化妝,或是互相化妝。她們穿著素樸的旗袍,表現出整體感,也用同樣的化妝模式,所以並不難。大體就是撲一點點的粉,把頭髮紮起梳成髻,噴一點點香水,這樣上台就顯得高雅亮麗。
平時練合唱時,大家已經很熟,不會去注意有沒有化妝的問題,但到了正式的場合,曾淑媛說,有了化妝和打扮,感覺就變得很不一樣,整個心情也莊重了起來。幾次以後,熟門熟路了,化妝一點也難不倒曾淑媛。
品味—不一定用看的
尤喜很喜歡老婆穿上平時不隨便穿的衣服。在那種場合中,老婆甚至連他穿什麼衣服,都會有意見。至於顏色怎麼搭配,衣著是否相襯合宜,就全由老婆大人來做定奪。
尤喜比較重視且有感覺的是衣服的質料。有些衣服軟軟的,穿在身上很舒服,他就問老婆:「這件衣服是什麼顏色的?」老婆就跟他說:「藍色的。」尤喜便記起來。有一天,小姪子來看他,剛好尤喜要換衣服,要小姪子挑衣服給他,小姪子不知該選那件,尤喜便說:「挑那件藍色的吧。」這句話,讓小姪子嚇了一跳。
尤喜有件衣服,質料是混紡的,感覺較粗,穿在身上總覺得燥熱。尤喜問道:「這件衣服是什麼顏色的?」老婆說:「紅色,很艷的紅。」尤喜說:「難怪。」在他的心裡,他始終覺得,每種顏色都是有感覺的,只是你要先開發自己感覺顏色的方式。
盲人對顏色、氣味,也許真的有一種特殊的感受,像昆蟲的觸鬚感官。艾爾帕西諾在電影《女人香》飾演的退休盲軍官,可以從女舞伴身上的香水,說出是何種牌子,逗得女舞伴芳心大亂。那不僅是艾爾帕西諾的個人魅力,其實,也是編導藉著這段劇情在向盲人的品味致意。如果,我說的是如果,跟艾爾帕西諾提起,台灣有句俗語說:「嫁給青瞑尪,抹粉無彩工。」他一定會從鼻孔噴氣地說:「我演過的那個角色肯定不會同意,至少,他會說,女人在我面前絕對不敢擦過於廉價的香水。」
與愛同行
艾信一直記得他和現任女朋友第一次見面時,嗅到的的一陣淡淡的香氣,後來他才知道,那並不是香水,而是某種品牌的洗衣精。後來他在其他女孩身上也嗅到過,卻沒有第一次從女朋友身上飄散出來時,那樣的印象深刻。或者應該說,讓他如此得如痴如醉。那天,艾信並沒有過於在意打扮和衣著,他喜歡讓自己穿上顯得有自信的衣服。他相信在他注意到這個女孩前,女孩就已經看了他很久,然後才跟他說:「你這件衣服真好看。」他們的交往,就是這樣開始的。
談到未來感情的進展,艾信說:「我大學時代就交過幾個女朋友,但多半只是興趣相投,走得比較近,後來也就自然而然的散了。和現在的女朋友雖然感情穩定,彼此認為還可以發展下去,但未來可以發展到什麼程度,能不能結成正果,我們都不敢打包票。」
現實裡,明眼女性嫁給盲人老公的比例,多過於明眼男性娶盲女的。尤喜說明這個現象時表示,「沒辦法,結婚不僅是兩個人的事,也涉及到雙方家長。」他不僅要獲得美人心,也花了許多時間和女方家長溝通。一開始,太太那一方的親屬都是反對的,擔心把女兒嫁給他,就是受罪的開始。「沒有辦法,」尤喜說,「我們選人家,人家也會選我們。」
尤喜還記得,他未來的岳母曾說道:「我女兒那麼的愛漂亮,如果以後嫁給你,會不會連她今天打扮的漂不漂亮都不知道,會不會一朵鮮花插在…」雖然沒有說下去,但尤喜已經知道未來岳母的擔憂,他趕緊說「在我心裡,她永遠都是最漂亮的,不管有沒有打扮,我每天都會讚美她。」
也許這句話打動了女孩的媽媽,以後他有機會到女孩家裡做客,女方家長待他就較為殷勤了。後來,靠著女孩的堅持,尤喜誠懇長久的溝通,讓他們相信,他雖然眼睛看不見,但並非是沒出息的。有了雙方家長的祝福,他們才一起攜手走上了紅毯。結婚兩年後,有一晚,尤喜勾動心弦地問道:「老婆,嫁給我妳覺得辛苦嗎?」
老婆笑道:「是啊,我是個現代的青蚵仔嫂。」
也許剛認識時,身體的條件會占很大的因素,但相處日久後,兩個人的個性合不合得來,才是決定能不能走下去的關鍵。尤喜現在會捏老婆的臉頰,對著這張他從沒有見到,卻這麼親近的臉說:「臉啊,妳到底漂不漂亮呢?」老婆就問:「說,你說啊。」他想起了幾年前跟丈母娘許過的承諾,正色說道:「那還用問嗎?在我心裡,這張臉永遠是最漂亮的。」
第五篇:盲人來報路
也許,未來有一天,在異鄉的街道,一個盲眼的異鄉人也能在被問路時,告訴你,這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咖啡館該怎麼走。
報路記
最簡單的問路,發生在每天的生活裡。有一個問路的人,也有一個被問路的人。遊戲規則其實簡單,又想當然耳:有人不知道該怎麼走,在路陣間迷失方向,他趕緊攀問一個剛好經過的路人,心想,也許這個人會知道該怎麼走。只見這個人停住,略做思索,也許兩個眼珠一轉,骨碌碌地溜出他的答案:「就前頭紅綠燈過了再右轉。」或者,眼白一翻,聳聳肩:「我也不知道。」
當然,問路,想必有個約定俗成的潛規則。問路的人,總會找個明眼人,心想憑他們的視力,能勝認指點迷津的任務。他們從沒有想過要找個盲眼人問路,「求道於盲」這類印象僅僅盤據在他們的腦海意識,簡直已成為一種信仰。他們想,如果一個看得見的人還得向盲人問路,那應該算是什麼,故意還是作弄?
在明眼人的教育養成過程裡,一個優雅文明的好公民應該勇於幫助盲人同胞。在路上看見盲人柱著手杖過馬路,應該過去幫忙牽著他過馬路。如果,有個盲人站在路邊,猶豫著要走向哪個方向,明眼人應該靠過去,熱心地問一句:「請問,你迷路了嗎?需不需要幫忙?」幫忙,總會從四面八方,從人們的唇間流向盲人,這真是個熱心的城市。
陳俊宏常常會覺得好笑又好氣,他拄著手杖站在紅磚道的印度紫檀樹下,涼風徐徐吹來,但沒多久,就會有聲音冒進來,衝著他說:「先生,您迷路了嗎?需要幫忙嗎?」心情好的時候,陳俊宏會說:「謝謝,我沒有迷路,這段路我很熟。」有一次,一個男孩的聲音一直纏著他,大概學校老師要他們日行一善吧,最後陳俊宏只好對個這個男孩說:「我正在欣賞樹上的鳥叫聲耶,請不要來打擾我。」一個盲人,失去了觀看顏色的能力,難道,就不能停下腳步,欣賞一陣鳥聲奏鳴嗎?
陳俊宏很熟悉他常走的路段,也許比明眼人還更熟悉。一個明眼人走在路上總是形色匆匆,只顧著看燈號和路標,更常漫不經心走路。但盲人心內自有他的道路地圖,他知道在第幾棵行道樹間的紅磚有個破角,雨天後踩踏下去會濺出水花。他知道在某條街道的轉角,某面牆壁顯得特別光滑。他也知道,從這裡出發再走幾步路,將會聞見獨特的麵粉香氣。
有一次,媽媽的新外傭要上街買東西,卻不認得路,媽媽要俊宏帶路,外傭看了看俊宏,卻不答腔。俊宏笑了笑,他知道外傭對他帶路的能力顯然有點懷疑,也不囉唆,當下帶著手杖就走出門,後面的腳步聲跟著他,卻保持著距離。陳俊宏照著自己的心內地圖和節奏,在街上左轉、右轉,熟悉的道路、氣味和聲音依然圍繞著他,最後,他停在商店前,後面的腳步聲緊緊跟上來。陳俊宏仍然微笑,這次,是帶著點那麼勝利的微笑。
捷運車站內,是陳俊宏另一張熟悉的心內地圖。迷宮般穿梭的捷運車站,常讓初來的旅客手足無措,繞走冤枉路。有一次,在昏暗的甬道間,有個聲音大概也沒發現陳俊宏是個盲人,就衝口問他:「請問出口在那裡?」陳俊宏不急不徐就跟他說:「別急,你再往前走十幾步,右轉,走約十五步,就會聽見一陣車子停住引擎的聲音,因為出口外面有個沒有行人穿越蜂鳴器的十字路口,然後再左轉,走六步,你就會聽見手扶梯的聲音。」那個人向他道謝,繼續趕路,大概一直想不透,怎會有人用「走幾步路」這麼精準和聲音在報路的呢?
陳俊宏笑著說:「問路,一點也難不倒我。」
盲人地圖
也許,盲人的心內地圖不同於明眼人,他們認路的本事,有如一場場戲或一座座舞台攤開在腦海裡,走路就像腦中的換幕,連帶的觸覺、走位、方向、氣味和聲音都要跟著更換。明眼人認路,靠的是地圖和街號標識,盲人卻靠戲劇感和印象,2009年以色列特拉維夫教育大學的拉哈夫(Orly Lahav)發明的「盲人地圖」則使用了觸感─結合三D觸覺技術和操作桿,取代盲人的手杖闖蕩陌生地。陳俊宏後來還報過幾次路,他描述起來,其實就像記憶中一場戲的報幕者。當然,盲人報路,絕對不同於明眼人,他會說:「在這個十字路口,特別得注意從右邊竄出的摩托車,當你聽見急踩煞車聲,往往就來不及了。」
陳俊宏用他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求道於盲」是句不合時宜的老生常談,若是你真的願意「求道於盲」,攤開在你想像裡,或許是一張更細膩的心靈地圖?或許,明眼人才該在一排行道樹下停下腳步,同時停下紛亂之心,欣賞流連在樹椏間的雀鳥啼唱。道可道,非常道,向盲人求的「道」絕不僅於問路,他們的方向感和立體感,和明眼人相較,可說另有天地。
陳俊宏回憶在讀國中時,做幾何題目,尤其是那種立體圖形的題目,陳俊宏說的都比老師還清楚。他覺得盲人的立體空間感,其實更不受到視覺的影響,會直截了當地「觀看」到立體的全貌。有一次,數學老師在說明一個立體圖形的面積該怎麼計算,同學聽得霧煞煞,因為他們的想像無法從紙上的二度空間轉為三度,只見陳俊宏舉手問道:「老師,如果把立方體轉過來再剖開來,會不會算得更快一點?」這種「看」法,連老師也覺得驚訝。
2009年,拉哈夫設計的這套盲人地圖,靠的也就是盲人的立體空間感。當時研究者發表了幾則盲人試用成功的個案,其中一位是住在美國麻州紐頓市卡羅盲人中心的婦女。她的視力接近全盲,試著用操作桿探索中心的環境和一座四層樓的建築等等。電腦完全模擬實景,將建築物和街道數位化建置在電腦內,這名女性觸摸操作桿探索環境,若前方遇到牆壁或阻礙,操作桿就無法再往前推。這名女性只試過三、四回合,就能夠試著戴上眼罩進入真實環境來。
拉哈夫說:「透過模擬和回饋,為盲人建構了一張認知地圖,等到他們真的來到真實世界,操作桿就彷彿是把高科技的手杖。」拉哈夫稱為「認知地圖」的,我們稱為「心靈地圖」。更多為盲人架設地圖的努力,實際上還是利用「聲音」。例如「看和聽地圖」(Look and Listen Map)還曾在2011年得到德國WissenWert競賽的大獎。這個計劃的正式名稱是「給盲人的新地圖:互動式的有聲書世界地圖」,要把整個世界地理都有聲化,融入到聽覺的世界裡來。這套偉大計劃的實現,靠的是電腦、智慧型手機、有聲書和衛星導航系統的結合,從此,盲人的心靈地圖就不再局限於像陳俊宏那樣的,以為盲人只能生活在他熟悉的路段。這個計劃邀請全世界的盲人和明眼人一起加入,運用最先進的科技系統,完成這張龐大的世界地圖。
也許,未來有一天,在異鄉的街道,一個盲眼的異鄉人也能在被問路時,告訴你,這座城市最好的一家咖啡館該怎麼走。「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前往咖啡館的路上。」這是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名言,然而,這會不會是都市裡一名盲人最平常的生活寫照?就像陳俊宏,最近他迷上帶著有聲的導航系統在陌生的街道探索,聆聽雀鳥的意外驚喜,或者嗅到一陣酥人心胸的咖啡香。
「求道於盲這絕對是人生的必要,有了這種經驗,才能打破明眼人的偏見,」陳俊宏說,「不是我在為我們這一族吹牛,因為,當你開口問了以後,不僅能知道路該怎麼走,你還能分享我們心中把地理關係演繹成一場戲,分享我們生命裡的小小滋味和小小的美滿。」
「小小的美滿」究竟是什麼?對一個明眼人來說,敢不敢偶而閉上眼睛,走一段熟悉的路,接受到不同的生命經驗?或者讓一個面帶勝利笑容的盲眼人,為你帶上一段路,那時才終究體會出「求道於盲」的「試說新解」其實就是:「勇敢的嘗試一段新的體驗。」當然,勇敢的去問,也包括在生活體驗裡面。
「求道於盲」讓陳俊宏勾起的聯想卻是Google,他說:「現代人,不管眼睛看不看得見,根本就是求道於Google吧。」那天,他看到一堆人坐車,好像是迷路了,正不知怎麼辦,一堆人開始研究起方向,然後他?見了一個很權威的聲音從亂中一枝獨秀,說道:「聽我的準沒錯,就往這個方向走。」車內唯一的盲人聆聽著有聲的導航系統,指出了最正確的方向。
「求道於盲」,真好,就讓我們從此放心的求盲於道吧。」
黑暗對話
明眼人倚賴視力進行溝通、理解和看見,當有人問說:「請問你想要一個什麼樣的『看見』?」時,其實他想知道的並不僅是「看見」,而是「理解」和「知道」。那麼,明眼人蒙上眼睛,或者進入一個全黑的房間內,卻仍然被要求要持續溝通、理解和知道時,問題就來了,而且來得非常的戲劇化。
其實,這就是源基於德國的「黑暗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的設計原意。在台灣,也有「黑暗對話」,也有盲人同胞在黑暗的房間裡,成為組織和群眾溝通的帶領者,徹底地顛覆明眼與盲者間、領導與服從間、協助與等待援助間的既定戲碼。
謝泰山本身就是名「黑暗對話」的培訓師。談起「黑暗對話」,他的話匣子一開,顯得興奮異常。謝泰山說,當參與者進入「黑房」後,就是明眼人必須「求道於盲」的時候了。處在全然黑暗的兩個小時內,要玩遊戲、進行溝通、還得分組完成任務。而在這個暗黑的過程裡,一個人在光亮世界裡無法察覺的盲點、領導風格的缺陷,或者說白一點,他是不是像他自己所相信的那樣,是一個品格高貴的人,此時都會昭然若揭。
在光亮世界裡,明眼人必須靠眼神的捕捉來得到回饋,一個微妙的眼神,或是察覺別人臉上的反應,來知道他今天的穿著是否得體。把自己和別人的眼神都抹去後,顯現的,是一個稱為「性格原型」的東西。心理學家榮格當年在論「心理原型」時,是用神話角色來做人格分類的嘗試,如大地母親、治療者、魔術師、煉金術師這樣的類型,他其實也沒有想到,視力和失去視力,也可更接近人格的原型。
謝泰山表示,在「黑暗對話」裡,氣定神閒的是盲人,慌亂無助的反而是明眼人。謝泰山也聽過「求道於盲」、「青瞑的看戲」、「青瞑的毋驚槍」這類的成語和俗語,他說,一點也不是這樣,在全然的黑暗中,槍瞄準著一個明眼人,他也未必會知道。
「黑暗對話」起源於德國,一九八八年德國創立第一家非營利事業體「對話社會企業」,簡稱DSE(Dialogue Social Enterprise),創辦人叫安德烈.海勒奇博士(Dr. Andreas Heineelte),閱讀他的生平和創辦理念,當然充滿著崇高的理念,我們卻聯想起,也許每個人小時候都玩過的「蒙眼抓鬼」遊戲,由別人帶領你走一小段路,讓你轉幾個圈,當你失去方向感,只聞其聲卻不見其影時,你還有辦法抓到同伴所扮的「鬼」嗎?
也許,在德國的成長歲月裡,安德烈.海勒奇也玩過這樣的遊戲。也許,他曾經被放在一個黑暗的房間內,引發了他日後建造社會企業的構想。台灣則在二○一一年,由謝邦俊醫師獲得DSE的授權,成立了「黑暗對話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北DiD)。當台北有了這套活動後,謝泰山積極參與,目前已是活躍的視障培訓師。
在「黑暗對話工作坊」的說明中有這麼一段話:「活動是在完全隔離所有光源的漆黑環境中進行,除了促使參與者必須適應突如其來的短暫失能外,同時必須強迫自己慢下步調,觀照內在,忠實地省視自己的核心價值。」這段文字中,有沒有注意到關鍵詞「慢下步調」?在突如其來的短暫失能裡,人們才能學習做到「慢下步調」。
「黑暗對話工作坊」裡有個黑房,也有個光房。「黑房」往往聯想到「暗房」,在早期還要用底片沖洗照片的年代裡,把膠卷送進暗房經歷顯影過程,才能沖洗出明亮的照片。現在,隨著照相技術的發達,沖洗照片早就成為記憶。然而,對重新發現自己、顯現自己來說,「黑房」的設計無異就是能讓心顯影的一間「暗房」。
「你有沒有試過閉起眼睛、不看表情,而能彼此傾聽的經驗?那其實是種挑戰。」謝泰山說。
在黑暗裡,會讓我們聯想起什麼?心理學知名的剝奪知覺實驗,就在測試這個禁忌的邊緣。心理學家發現,視覺和其他感官被剝奪的人,容易焦慮、緊張、心跳加快,時間一長,就會影響身心健康。但還有更嚴重的是,剝奪視覺能力,也會讓明眼人失去了原本溝通的能力。
謝泰山說,一般人已習慣看網路、上臉書或到 Google 找資料,電子通訊設備已有如他們的「另一隻眼睛」。溝通時,有些人習慣使用白板、記事簿,一定要把自己要講、要記的文字都寫下來不可。然而,「黑暗對話」提供的是一個不能使用 Google,也沒有白板的溝通情境,這時,還要他們在時間限制內完成任務,會讓許多人因而慌了手腳。
有些平時當主管的人在黑房裡,還會照著過去的習慣說:「請看我這邊。」他和同事講話時,會不自覺地點頭、搖頭,屬下只要察言觀色,自然就會調整談話內容,彼此互通心意,溝通遊戲自此就算大功告成。謝泰山說,在黑房裡,已習於下命令的人,會更覺得不能適應,但往往經歷這段黑暗時光,他們的收穫也更加的豐富。
走出黑房,來到光房,分享從自主者變成非自主者的感受。在黑房裡接受過視障培訓師協助的人,更能夠深刻體驗,明眼人可能變成非自主者,而盲的人卻可能成為主宰與協助的角色。
這場經歷後,生起的是現代人始終缺少的一種美德,叫作「同理心」。走出自己原本熟悉、習以為常的世界,才有辦法空出心思,接納另一個不同的世界。
從此看來,「黑暗對話」提出的,也許是另一個生命教育的機會,不僅適用於盲和見的對比,適用於商業管理和職場溝通,將來也可運用在親子溝通間。許多親子──不管是做子女還是為人父母者,往往只習慣見到自己的世界,卻進不去對方的心思。在黑房裡,親子還可試著建立另一種溝通的方式,完成指派給他們的任務。
黑暗對話中的生命教育
「人們往往看到更悲苦的處境,藉此來提醒自己,就像那個老故事裡,一再怨嘆自己沒鞋子穿的人,有一天遇到了沒有腳的人。」所以,明眼人會覺得更悲苦的是「盲」,用此來提醒自己。然而,兩者只是感官經驗和世界的不同,是不一樣,卻不見得有階層和等級的差別。
在黑暗對話中,培養同理心的溝通是一項重點。其實同理心的養成不只是在這類的課程中而已,也應融入我們的社會教育當中。在台灣,「生命教育」可以說是教育界的顯學,其實,當年台灣學校推動生命教育,是以降低青少年自殺率和犯罪率為出發點的,到了現在,內容和理念一再地修正,也繼續擴充,做法從養小動物到種下一棵樹、照顧老人都算。但是,台灣實行的生命教育,似乎總是繁雜忙碌而不見得會有效果。
「生命教育」的最終目標,其實,仍離不開肯定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就如我們常說的,每個生命都會有它的價值,如果你覺得並不是這樣,那可能是你還沒有找到,你可能要花更多的功夫和光陰去尋找。
看過《逆光飛翔》這部電影,見過鋼琴師黃裕翔的精湛表現,還有那總是笑笑的一張臉、氣定神閒的模樣,我們不免會深思,如果當年不是黃裕翔的媽媽這麼辛苦地去栽培他,讓他有機會利用自己的天賦去發光發熱,今天,我們就將失去道說一則傳奇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