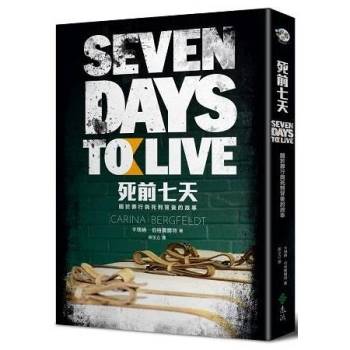食物,是個勾動情緒的話題。安東尼・葛瑞夫斯待在牢裡的最後四年,那段時間,每週他可以打一通電話出去,而這通電話總是打給同一個人--媽媽。
「沒有人比我媽媽煮得好吃。而且,奇怪的是,當生命中的所有事物都被剝奪走的時候,我完全沒辦法停止思念的事情,就是好吃的食物:媽媽煮的東西。我每天思念它們,想像它們。所以,當我終於等到了機會,我就每週打一次電話給她,問她在煮些什麼。」
每一次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樣。有時候,媽媽告訴他,說她如何把一整隻雞放進烤箱裡;有時候,她會描述自己如何煎牛排或煮一鍋肉。有時候他打電話去,媽媽正好在烘焙食物,她就會告訴他和餅乾與蛋糕有關的事。這樣的對話最後總是在相同的情況下結束--安東尼・葛瑞夫斯會變得沮喪,對她咆哮。安東尼・葛瑞夫斯在回憶中,搖搖頭。他解釋,這就好像是上了癮,他想問這樣的問題,卻沒辦法接受答案。同樣的過程,一週又一週地反覆進行,直到那一天到來。
「我事先完全不知道會被釋放,一切就這樣發生了。他們做出決定,兩小時之後,我得到指令,要我把自己的東西打包好,因為我要出獄了。我所有的罪名都被除去,我自由了。」
他就這麼突如其然地站到了監獄外的人行道上,準備進入律師的車子裡。那個片刻,他只有一件事非得先做不可。他借了手機,打電話給他媽媽。
「我問她同一件事,『妳在煮什麼?』因為我向她咆哮過那麼多次,她回答得有點猶豫;最後,她再一次問我,為什麼我想知道。」
他答道,「因為今天我要回來吃晚餐。」
「你明白那種感覺嗎?當你極其渴望某個東西,你這一輩子只想要那個東西,突然之間,好像整個宇宙為你打開了,讓你得到了那個渴望了那麼久的東西。在那個當下,情況就像那樣發生了。我的人生有十八年被人奪走,在那十八年半的時間裡,我不被准許碰觸我的媽媽或我的孩子。得知自己將在幾秒鐘之內,坐進一輛汽車,回家去見媽媽、擁抱她、擁抱我的孩子,那感覺真的是筆墨難以形容。」
安東尼・葛瑞夫斯說著說著哽咽了,但他仍然努力想要描述當時的情況:轉進那條街道、走出車子、摟住他的兒子,然後看到他媽媽越過草坪,身上穿著一件紫色和黃色相間的洋裝。他的嗓音破掉了。
「那個把你生下來了的女人,是你一生當中唯一無條件愛你的人,那個女人從來沒有停止相信你是清白的。而她就站在草地上、邊哭邊笑,張開了她的手臂;你一步步迎向那雙手臂,全然投入永不止息的母愛裡,然後感覺到那份愛將你包圍起來⋯⋯」
他的句子沒有說完,也不需要多說。
他安靜了很久。低頭看著桌子。吞咽著。
「在那樣的擁抱裡,我明白一切都會沒事的。那個擁抱告訴我,『媽媽現在抱住你了,媽媽不會再讓任何人傷害你。』她環繞著我的手臂告訴我,我到家了。」
安東尼・葛瑞夫斯解釋道,經過了這麼多年的監禁,讓他不至於崩潰和放棄的原因,就只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是被錯誤定罪的,他也深信終有一天,自己會站在草坪上被母親的雙臂環繞。他覺得,上帝為他定下了計劃,而所有這些事,只是那更大的計劃的一部分,為了到達某處,他必須先經歷這段旅程。只是,這是一回漫長而艱苦的旅行。
「孤立十八年,是會毀掉一個人的。它奪去人的情感生活。那些全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像是缺乏人與人的聯繫。想像一下,你從來沒有觸摸過另一個人。我不能擁抱我媽或我的孩子長達十八年。而擁抱,對我們人類來說,就像是汽油一樣。我們需要加油。我們需要補充汽油。如果你不把汽車油箱加滿,車子最後就會停下來。」
他喝了一大口檸檬汁,加了冰塊的汁液,快要滿出來了。然後,他試圖整理己的說法。
「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理解的。人是為了親密感而創造出來的。當你把那種感覺從一個人的身上拿掉,就一定要當心你創造出了什麼樣的人。在牢裡這麼多年,我沒辦法不去思考這件事,觸摸異性的感覺像什麼。觸摸和我媽媽的食物,是我最喜歡的主題。」
安東尼・葛瑞夫斯說,在他十八年的牢獄生涯裡,看過好幾個類似的案例。自殺的、他殺的、發瘋的。他告訴我,有個犯人的精神病非常嚴重,那人深信監獄本身就是個戰區。為了偽裝自己不被敵人認出來,那個犯人把自己的糞便塗在臉上。當獄警前來帶他去執行死刑時,他當場激動地堅決下令,要求「部隊把隊長給殺了」。
安東尼・葛瑞夫斯的故事好像永無止盡地,一個接一個湧出來。他描述道,有個囚犯不明白自己即將赴死,當時候到來,他還詢問其他犯人的意見,問自己該穿什麼去參加葬禮?完全不了解,自己就是那個要躺在棺材裡的人。葛瑞夫斯還告訴我,有個囚犯坐在牢房中央,慢條斯理地把他的床單撕成長條,然後把這些長條綁在自己的身上,放火自焚。有個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男性囚犯,有天用手把自己的眼球挖了出來,一口吞了下去。他還談到有個囚犯不被允許靠近任何刀片,因為只要他一拿到刀片,就會把自己身體的某個部位給切下來。不論安東尼・葛瑞夫斯可以怎麼切斷過去,在他遠離那些囚犯和監獄多年之後,那些人、那些回憶,仍將與他常相左右。
「單獨監禁讓人想死。」他平靜地說。
「那裡有人取消了自己的上訴。到了某個地步,他們寧願死,也不願繼續活在波蘭斯基死囚監獄裡。」
在我們見面的那天,距離他踏出監獄大門、打電話給他媽媽詢問晚餐吃什麼,已經過了三年了。
日子繼續向前走。他試著重新了解自己和他的兒子。當他入監服刑時,他的三個兒子分別是八歲、九歲和十二歲。現在,他們都長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兒女。他錯過了他們所有的童年時光,在將近廿年的歲月裡,他一年只能透過玻璃牢籠見他們幾次。他說,他和兒子之間有著很多的愛,他們試著建立關係,但那需要時間。從他離開波蘭斯基監獄以來,他晚上還是沒辦法好好睡覺。
「不是因為做惡夢。我沒有什麼惡夢好做的,還有什麼事會比我已經經歷過的來得更糟呢?我見過人撕裂他們的手腕、我見過割開自己的喉嚨、有人上吊、有人服藥自殺。還有什麼我沒有見過的事,會讓我做惡夢呢?我會失眠,是因為過去這麼多年來,我每天晚上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醒來。」
他說,他一次最多只能睡兩到三個小時;在自己睡著以前,夜裡還是會哭泣。即便他現在住在一個有百萬居民的城市裡,他仍會捲曲在床上、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孤單的人。他試著告訴我,監獄裡有什麼噪音。直到現在,他還是會在漫長的黑夜裡想起那持續不斷的噪音,所以在生理上,他其實無法一覺睡到天明。那監獄的聲響、死囚牢房的噪音;一整晚在你牢房外頭哐啷作響的金屬碰撞聲、大門開開關關、人的吼叫聲;每天晚上在漆黑中發生的事;男人因恐慌而涰泣、自言自語,因為開始出現精神分裂而擔驚害怕。噪音持續不斷,從未沈寂,永無安寧。
他又回到了親密關係的話題。談到自己躺在牢裡十八年,數以千計的夜晚,他如何渴望親密、憧憬親密。但他也談到,如今親密關係近在呎尺,他如何招架無力。安東尼・葛瑞夫斯邂逅了一名女子;當我問他,她是不是他女朋友時,他尷尬起來。
他說,「我還是人類。擁有一顆心,和所有人一樣有七情六欲。但我經歷了很多事,看過三百個人被處決,他們之中有很多人是我的朋友,有些人甚至比朋友還要親;在那裡,變得像個家庭。為了在那樣瘋狂的處境中存活,你必須把自己內心深處的某些地方關起來,而那些地方已經關閉很久很久了。但於此同時,你也會很想開放自己、想把自己交出來給某個人,在那種欲望之下,你的身體疼痛著。不過,我很小心。」
他告訴我,那位他還不願意說是自己女朋友的女子,完全理解這件事,而且也很有耐心。他們已經持續見面兩年半了。她來自德國,已在美國住了十二年。他說,他們正努力找出相處之道。此外,他也擔心如果稱她為女朋友,她可能會就此消失。
「她是社會運動人士,倡議反對死刑。聽說我被釋放,她就稍來訊息恭喜我,我們開始聊天,並決定碰面,接下來就不用我多說了。我不想為未來設限。我現在的感覺其實很像是剛剛才離開了一個到處都是界線、限制和規範的地方。」
他談了很多在他體內糾葛掙扎的感受;談到自己渴望和另外一個人親近,以及和另一個人親近有什麼困難,他也談到自己非常需要感情,卻又難以接受感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獄政制度應該要當心,當他們把我們建立人際關係的機會全都給奪走的時候,到底會創造什麼樣的人出來。你對一個人做那種事,不可能什麼後果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