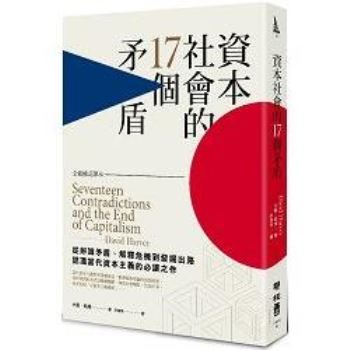矛盾1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我們購買的所有商品都各有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種價值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因為它們往往不一致,這構成了一種矛盾,而這種矛盾有時會造成危機。使用價值變化無窮(即使同一件商品也是),交換價值(在正常情況下)則是一致的,性質上也沒有不同(一美元就是一美元,永遠都是一美元;即使你拿到的是歐元,你也能知道它可以兌換多少美元)。
我們且以房屋為例,想想它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房屋的使用價值相當多元:它為我們提供一個遮風蔽雨的地方,讓我們建立家庭和感情生活;它是我們每天生活、生兒育女的場所(我們在房子裡煮食、做愛、吵架和撫養小孩);在不穩定的世界裡,房子保護我們的隱私和安全。房屋也可以成為某些人彰顯自身地位和社會歸屬感的工具,成為財富和權勢的象徵、個人和社會歷史記憶的符號,以及彰顯建築成就的標誌;它也可以只是一個旅遊景點,供遊客讚嘆建築之優美,例如像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落水山莊(Falling Water)那樣。房屋也可以成為胸懷大志的創新者之工場,例如矽谷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那個著名的車庫。我可以在地下室偷偷辦一間血汗工廠,或是用它來收留遭迫害的移民,又或者把它當作買賣性奴隸的基地。我還可以舉出房屋的許多不同用途。總之房屋的可能用途非常多樣,似乎無窮無盡,而且各種用途往往十分獨特。。
但房屋的交換價值又如何?在當代世界裡,我們一般必須購買或租下房子,才能享有使用房子的特權。我們必須為此付出金錢。問題是:為取得房子的使用權,我們必須付出多少交換價值?這個「多少」的問題,如何影響我們掌握自己想要和需要的房屋用途之能力?這問題聽起來很簡單,但答案其實相當複雜。不過,在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多數地方,房屋是一種投機商品,建出來在市場上銷售,任何人負擔得起和有需要都可以購買。這種房屋供給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就顯而易見。英國巴斯、布里斯托和倫敦等地著名的喬治式聯排屋,便是以這種方式興建於十八世紀末。後來這種投機建屋方式也出現在其他地方,在紐約市蓋出廉價公寓,在費城、里爾和里茲等工業城市建出勞工階層居住的排屋,而美國典型的市郊社區也採用這種建屋方式。房子的交換價值除了取決於基本的建造成本(勞力和物料的成本)外,還取決於另外兩項成本:投機建商希望賺取的利潤(他們承擔最初的必要資本支出,並支付相關貸款的利息),以及購買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也就是說,交換價值等於實際建造成本加上利潤、貸款利息和資本化的地租(地價)。建商的目的是取得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替其他人創造使用價值是達成這目的的手段。因為這種活動本質上是投機的,真正重要的是房子的潛在交換價值。不過,建商並非必賺不賠。他們顯然會精心策劃一切,尤其是房屋之銷售,盡可能避免虧損。但是,風險總是有的。在這種模式下,交換價值主導了房屋供給。
有鑒於許多人對房屋使用價值的需求未能得到滿足,各種社會力量(包括強烈希望把員工留在工作場所附近的雇主,例如吉百利〔Cadbury〕,以及基進和烏托邦思想的信奉者,例如歐文〔Robert Owen〕、傅立葉主義者和皮博迪〔George Peabody〕)和一些國家的地方與中央政府不時發起一些建屋計畫,借助公帑、慈善或家長式資金,以最低的成本滿足低下階層的房屋需求。如果大家普遍接受人人有權享有「體面的住家和合宜的居住環境」(如美國一九四九年的《住宅法》前言所稱),則使用價值考量顯然將再度成為房屋供給問題的焦點。這種政治立場對歐洲社會民主時代的房屋政策有重大影響,北美和一些開發中地區也受到某程度的影響。多年來,政府涉入房屋供給的程度顯然有起伏,政府對社會住宅的興趣也是這樣。但是,因為資助平價房屋的負擔考驗政府的財力(財政收入萎縮時尤其如此),交換價值考量常常再度悄悄地排擠使用價值考量。房屋建造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緊張狀況,有多種方法可以控管。但是,這種體制向來也有失控的階段,此時便會產生危機,例如二○○七至○九年美國、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市便經歷了這種狀況。此次危機並非史無前例。之前的類似例子包括一九八六年起的美國存貸危機,一九九二年斯堪的納維亞的房市崩盤,以及一九九○年的日本土地市場崩盤(終結了日本一九八○年代的經濟榮景)。
在主導多數資本主義地區的私營市場體系中,房屋供給還有額外的問題必須處理。首先,房屋是一種「高單價商品」,要使用很多年,不像食物那樣馬上被用掉。個人可能不夠錢一次付款買下房子。如果我不夠錢買房,我有兩個基本選擇。我可以向房東租房;房東可能專門做這種事:購入投機建商建造的房子,靠收租維生。我也可以借錢買房,可能是向親友借錢,也可能找金融機構辦理房屋抵押貸款。如果是辦房貸,我除了必須支付房子的全額交換價值外,償還房貸期間還必須每月支付貸款利息。還清房貸之後(可能需要三十年),我便完全擁有房子。在此情況下,房屋也成了一種儲蓄工具,我可以隨時拿這項資產的價值套取現金(至少我每月償還房貸,因而取得的部分價值是可以套現的)。房屋的價值會有一些會被維修保養的費用消耗掉,例如牆面每隔一段時間必須重新上漆,屋頂損壞必須修好。但是,我仍然可以期望隨著自己逐漸還清房貸,我掌握的房屋淨值將增加。
但是,利用房貸購屋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交易。利率五%、本金十萬美元的房貸分三十年償還,總還款額約為十九萬五千美元。也就是說,房貸戶為了取得最初價值十萬美元的資產,必須多付九萬五千美元。這樣的交易看來很沒道理。我為什麼願意這麼做呢?答案當然是我需要這房子的使用價值(我需要一個居住的地方),而我為此付出九萬五千美元,直到我完全取得房子的所有權。這就像我在三十年間花九萬五千美元租房,差別在於我最終可以取得整間房子的交換價值。這房子實際上成了一種儲蓄工具,替我儲存它的交換價值。但是,房屋的交換價值不是固定的。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波動,受各種社會狀況和力量影響。首先,它會受周遭房屋的交換價值影響。如果附近的房屋全都日趨破敗,又或者社區裡遷入愈來愈多「不對勁」的人,則我的房子很可能將貶值,即使我把它維持在一流的狀態也無法倖免。相反,社區環境「改善」,例如社區仕紳化,則可以提升我房子的價值,即使我並未投入任何資源。房市深受經濟學家所稱的「外部性」影響。屋主經常採取個別和集體行動,力求控制這些外部因素。不信的話,你可以提議在某個「體面的」社區建一個安置出獄者的中途之家,看看會發生什麼事!你將見識到大量的鄰避(NIMBY,不得在我家後院)政治運作:社區居民積極排斥他們不歡迎的人和活動,社區組織幾乎純粹以維護和提升區內房屋的價值為使命(例如社區內若有好學校,對住宅價值大有幫助)。為了保護自身儲蓄的價值,人們會有積極行動。不過,屋主有時也會損失他們利用房屋保存的儲蓄,例如政府或建商為了重新發展某個社區,可能會購入該區相當數量的房子,然後任由那些房子的狀況惡化,進而嚴重損害區內其他房屋的市場價值。
如果我想投資改善屋況,我可能會希望審慎行事,僅做那些顯然可以提升房子交換價值的事。市場上有很多提供相關建議的參考書(建一個配置最先進設備的廚房可替房子增值,在天花板上裝鏡子,或是在後院建一個鳥園,則是沒有用的)。
在全球許多地方,住宅所有權對愈來愈大部分的人口已經變得十分重要。維護和提升房屋資產價值,已經成為愈來愈大部分人口的重要政治目標和重要政治議題,因為消費者可以得到的房屋交換價值,一如建商所能賺到的交換價值那麼重要。但是,最近三十年左右,房屋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標的。我以三十萬美元買進一間房子,三年後它的市值升至四十萬美元。我可以把握機會做房貸再融資,把房子增值的那十萬美元換成現金,隨自己高興使用。交換價值不斷上升,使得房子成為熱門的投機標的。房屋成為一種方便利用的金牛(cash cow)或個人提款機,總合需求因此增強,市場上的房屋需求也日益高漲。在《大賣空》(The Big Short)一書中,邁克‧路易士(Michael Lewis)闡述了二○○八年金融市場崩盤之前發生的房屋投機潮。路易士有位重要消息來源雇用了一名保姆,她和她的姐妹一度在紐約市皇后區擁有六間房子。「她們買進第一間房子之後,房價大漲,放款機構建議她們做房貸再融資,拿走二十五萬美元的現金,而她們用這筆錢買了第二間房子。」第二間房子的市值也大漲,她們於是重施故技,繼續買房。「最後,市場持續下跌時,她們手上有五間房子,而且完全沒有能力償還房貸。」
房市的資產價值投機變得熾熱。但是,這種投機總是有某程度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元素。我借錢買房,然後房價上漲了。房屋市值不斷上漲吸引更多人買房。他們借入更多錢購買「好東西」(當放款機構資金非常充裕時,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房價進一步上漲,因此吸引更多人和機構參與房屋投機。結果造成一場「房地產泡沫」,而泡沫最終必然破滅。這種資產價值泡沫如何形成、為何形成,泡沫會有多大,以及泡沫破滅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取決於多種狀況和力量的具體情況。基於歷史經驗(例如美國房市便曾於一九二八、一九七三、一九八七和二○○八年崩盤),目前我們必須接受的是,這種投機狂熱和資產泡沫是資本主義歷史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中國向資本主義模式靠攏,該國房市也愈來愈容易出現投機熱潮和資產泡沫。我們稍後將再探討此中原因。在美國最近這次房市崩盤中,約四百萬人因為房貸止贖(借款人因為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而失去住家。這些人因為追求房屋的交換價值,結果喪失了房屋的使用價值。數不清的人仍處於房貸「溺水」的狀態:他們在房價高峰期買房,因為房價隨後大跌,他們欠金融機構的房貸比房子的市值還高。這些屋主必須承受巨大的損失,才能擺脫房屋所有權並遷居他方。在房市榮景的高峰期,房價太高了,許多人必須承受他們最終證實無力償還的債務,否則無法獲得房屋的使用價值。房市崩盤之後,這些人可能被迫抱著一些房屋使用價值而無法脫身,由此造成的財務負擔令他們的景況特別淒慘。簡而言之,因為不顧後果地追求交換價值,許多人喪失了取得並持續擁有房屋使用價值的能力。
類似問題也已經發生在租屋市場。在紐約市,約六○%的人口為租屋族;私募股權基金在房市高峰期買進許多出租的住宅大樓,希望藉由提高租金大賺一筆(即使它們面對有力的法規管制)。這些基金刻意壓低這些房子的現行使用價值,藉此替它們的再投資計畫辯解,但它們自己在金融市場崩盤中破產了,留下房客住在使用價值變差但租金反而變貴的房子裡,而且這些房子因為原本的主人破產而遭金融機構沒收,誰該負起屋主的責任往往並不清楚(如果你住在這種大樓裡,發現暖氣爐壞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該找誰處理問題)。近一○%的出租房屋遇到了這種問題。因為有人不顧後果地追求交換價值極大化,一大部分人可以享有的房屋使用價值受損了。當然,更慘的是,房市崩盤引發一場全球危機,結果全球經濟至今仍然很難康復。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資本主義下的房屋供給,已經從追求使用價值為主,變成以追求交換價值為主。因為這種怪異的轉變,房屋的使用價值日趨變質,首先是變成一種儲蓄手段,其次是變成一種投機工具,而利用這種投機工具的除了消費者,還有建商、金融業者和所有可受惠於房市榮景的人,包括房屋仲介、房貸放款人員、律師和保險經紀等等。為大眾提供足夠的房屋使用價值(傳統消費意義上的使用價值),愈來愈受制於不斷深化的交換價值考量。我們致力為愈來愈大比例的人口提供足夠和可負擔的房屋,結果卻是一場災難。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我們購買的所有商品都各有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種價值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因為它們往往不一致,這構成了一種矛盾,而這種矛盾有時會造成危機。使用價值變化無窮(即使同一件商品也是),交換價值(在正常情況下)則是一致的,性質上也沒有不同(一美元就是一美元,永遠都是一美元;即使你拿到的是歐元,你也能知道它可以兌換多少美元)。
我們且以房屋為例,想想它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房屋的使用價值相當多元:它為我們提供一個遮風蔽雨的地方,讓我們建立家庭和感情生活;它是我們每天生活、生兒育女的場所(我們在房子裡煮食、做愛、吵架和撫養小孩);在不穩定的世界裡,房子保護我們的隱私和安全。房屋也可以成為某些人彰顯自身地位和社會歸屬感的工具,成為財富和權勢的象徵、個人和社會歷史記憶的符號,以及彰顯建築成就的標誌;它也可以只是一個旅遊景點,供遊客讚嘆建築之優美,例如像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落水山莊(Falling Water)那樣。房屋也可以成為胸懷大志的創新者之工場,例如矽谷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那個著名的車庫。我可以在地下室偷偷辦一間血汗工廠,或是用它來收留遭迫害的移民,又或者把它當作買賣性奴隸的基地。我還可以舉出房屋的許多不同用途。總之房屋的可能用途非常多樣,似乎無窮無盡,而且各種用途往往十分獨特。。
但房屋的交換價值又如何?在當代世界裡,我們一般必須購買或租下房子,才能享有使用房子的特權。我們必須為此付出金錢。問題是:為取得房子的使用權,我們必須付出多少交換價值?這個「多少」的問題,如何影響我們掌握自己想要和需要的房屋用途之能力?這問題聽起來很簡單,但答案其實相當複雜。不過,在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多數地方,房屋是一種投機商品,建出來在市場上銷售,任何人負擔得起和有需要都可以購買。這種房屋供給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就顯而易見。英國巴斯、布里斯托和倫敦等地著名的喬治式聯排屋,便是以這種方式興建於十八世紀末。後來這種投機建屋方式也出現在其他地方,在紐約市蓋出廉價公寓,在費城、里爾和里茲等工業城市建出勞工階層居住的排屋,而美國典型的市郊社區也採用這種建屋方式。房子的交換價值除了取決於基本的建造成本(勞力和物料的成本)外,還取決於另外兩項成本:投機建商希望賺取的利潤(他們承擔最初的必要資本支出,並支付相關貸款的利息),以及購買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也就是說,交換價值等於實際建造成本加上利潤、貸款利息和資本化的地租(地價)。建商的目的是取得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替其他人創造使用價值是達成這目的的手段。因為這種活動本質上是投機的,真正重要的是房子的潛在交換價值。不過,建商並非必賺不賠。他們顯然會精心策劃一切,尤其是房屋之銷售,盡可能避免虧損。但是,風險總是有的。在這種模式下,交換價值主導了房屋供給。
有鑒於許多人對房屋使用價值的需求未能得到滿足,各種社會力量(包括強烈希望把員工留在工作場所附近的雇主,例如吉百利〔Cadbury〕,以及基進和烏托邦思想的信奉者,例如歐文〔Robert Owen〕、傅立葉主義者和皮博迪〔George Peabody〕)和一些國家的地方與中央政府不時發起一些建屋計畫,借助公帑、慈善或家長式資金,以最低的成本滿足低下階層的房屋需求。如果大家普遍接受人人有權享有「體面的住家和合宜的居住環境」(如美國一九四九年的《住宅法》前言所稱),則使用價值考量顯然將再度成為房屋供給問題的焦點。這種政治立場對歐洲社會民主時代的房屋政策有重大影響,北美和一些開發中地區也受到某程度的影響。多年來,政府涉入房屋供給的程度顯然有起伏,政府對社會住宅的興趣也是這樣。但是,因為資助平價房屋的負擔考驗政府的財力(財政收入萎縮時尤其如此),交換價值考量常常再度悄悄地排擠使用價值考量。房屋建造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緊張狀況,有多種方法可以控管。但是,這種體制向來也有失控的階段,此時便會產生危機,例如二○○七至○九年美國、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市便經歷了這種狀況。此次危機並非史無前例。之前的類似例子包括一九八六年起的美國存貸危機,一九九二年斯堪的納維亞的房市崩盤,以及一九九○年的日本土地市場崩盤(終結了日本一九八○年代的經濟榮景)。
在主導多數資本主義地區的私營市場體系中,房屋供給還有額外的問題必須處理。首先,房屋是一種「高單價商品」,要使用很多年,不像食物那樣馬上被用掉。個人可能不夠錢一次付款買下房子。如果我不夠錢買房,我有兩個基本選擇。我可以向房東租房;房東可能專門做這種事:購入投機建商建造的房子,靠收租維生。我也可以借錢買房,可能是向親友借錢,也可能找金融機構辦理房屋抵押貸款。如果是辦房貸,我除了必須支付房子的全額交換價值外,償還房貸期間還必須每月支付貸款利息。還清房貸之後(可能需要三十年),我便完全擁有房子。在此情況下,房屋也成了一種儲蓄工具,我可以隨時拿這項資產的價值套取現金(至少我每月償還房貸,因而取得的部分價值是可以套現的)。房屋的價值會有一些會被維修保養的費用消耗掉,例如牆面每隔一段時間必須重新上漆,屋頂損壞必須修好。但是,我仍然可以期望隨著自己逐漸還清房貸,我掌握的房屋淨值將增加。
但是,利用房貸購屋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交易。利率五%、本金十萬美元的房貸分三十年償還,總還款額約為十九萬五千美元。也就是說,房貸戶為了取得最初價值十萬美元的資產,必須多付九萬五千美元。這樣的交易看來很沒道理。我為什麼願意這麼做呢?答案當然是我需要這房子的使用價值(我需要一個居住的地方),而我為此付出九萬五千美元,直到我完全取得房子的所有權。這就像我在三十年間花九萬五千美元租房,差別在於我最終可以取得整間房子的交換價值。這房子實際上成了一種儲蓄工具,替我儲存它的交換價值。但是,房屋的交換價值不是固定的。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波動,受各種社會狀況和力量影響。首先,它會受周遭房屋的交換價值影響。如果附近的房屋全都日趨破敗,又或者社區裡遷入愈來愈多「不對勁」的人,則我的房子很可能將貶值,即使我把它維持在一流的狀態也無法倖免。相反,社區環境「改善」,例如社區仕紳化,則可以提升我房子的價值,即使我並未投入任何資源。房市深受經濟學家所稱的「外部性」影響。屋主經常採取個別和集體行動,力求控制這些外部因素。不信的話,你可以提議在某個「體面的」社區建一個安置出獄者的中途之家,看看會發生什麼事!你將見識到大量的鄰避(NIMBY,不得在我家後院)政治運作:社區居民積極排斥他們不歡迎的人和活動,社區組織幾乎純粹以維護和提升區內房屋的價值為使命(例如社區內若有好學校,對住宅價值大有幫助)。為了保護自身儲蓄的價值,人們會有積極行動。不過,屋主有時也會損失他們利用房屋保存的儲蓄,例如政府或建商為了重新發展某個社區,可能會購入該區相當數量的房子,然後任由那些房子的狀況惡化,進而嚴重損害區內其他房屋的市場價值。
如果我想投資改善屋況,我可能會希望審慎行事,僅做那些顯然可以提升房子交換價值的事。市場上有很多提供相關建議的參考書(建一個配置最先進設備的廚房可替房子增值,在天花板上裝鏡子,或是在後院建一個鳥園,則是沒有用的)。
在全球許多地方,住宅所有權對愈來愈大部分的人口已經變得十分重要。維護和提升房屋資產價值,已經成為愈來愈大部分人口的重要政治目標和重要政治議題,因為消費者可以得到的房屋交換價值,一如建商所能賺到的交換價值那麼重要。但是,最近三十年左右,房屋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標的。我以三十萬美元買進一間房子,三年後它的市值升至四十萬美元。我可以把握機會做房貸再融資,把房子增值的那十萬美元換成現金,隨自己高興使用。交換價值不斷上升,使得房子成為熱門的投機標的。房屋成為一種方便利用的金牛(cash cow)或個人提款機,總合需求因此增強,市場上的房屋需求也日益高漲。在《大賣空》(The Big Short)一書中,邁克‧路易士(Michael Lewis)闡述了二○○八年金融市場崩盤之前發生的房屋投機潮。路易士有位重要消息來源雇用了一名保姆,她和她的姐妹一度在紐約市皇后區擁有六間房子。「她們買進第一間房子之後,房價大漲,放款機構建議她們做房貸再融資,拿走二十五萬美元的現金,而她們用這筆錢買了第二間房子。」第二間房子的市值也大漲,她們於是重施故技,繼續買房。「最後,市場持續下跌時,她們手上有五間房子,而且完全沒有能力償還房貸。」
房市的資產價值投機變得熾熱。但是,這種投機總是有某程度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元素。我借錢買房,然後房價上漲了。房屋市值不斷上漲吸引更多人買房。他們借入更多錢購買「好東西」(當放款機構資金非常充裕時,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房價進一步上漲,因此吸引更多人和機構參與房屋投機。結果造成一場「房地產泡沫」,而泡沫最終必然破滅。這種資產價值泡沫如何形成、為何形成,泡沫會有多大,以及泡沫破滅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取決於多種狀況和力量的具體情況。基於歷史經驗(例如美國房市便曾於一九二八、一九七三、一九八七和二○○八年崩盤),目前我們必須接受的是,這種投機狂熱和資產泡沫是資本主義歷史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中國向資本主義模式靠攏,該國房市也愈來愈容易出現投機熱潮和資產泡沫。我們稍後將再探討此中原因。在美國最近這次房市崩盤中,約四百萬人因為房貸止贖(借款人因為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而失去住家。這些人因為追求房屋的交換價值,結果喪失了房屋的使用價值。數不清的人仍處於房貸「溺水」的狀態:他們在房價高峰期買房,因為房價隨後大跌,他們欠金融機構的房貸比房子的市值還高。這些屋主必須承受巨大的損失,才能擺脫房屋所有權並遷居他方。在房市榮景的高峰期,房價太高了,許多人必須承受他們最終證實無力償還的債務,否則無法獲得房屋的使用價值。房市崩盤之後,這些人可能被迫抱著一些房屋使用價值而無法脫身,由此造成的財務負擔令他們的景況特別淒慘。簡而言之,因為不顧後果地追求交換價值,許多人喪失了取得並持續擁有房屋使用價值的能力。
類似問題也已經發生在租屋市場。在紐約市,約六○%的人口為租屋族;私募股權基金在房市高峰期買進許多出租的住宅大樓,希望藉由提高租金大賺一筆(即使它們面對有力的法規管制)。這些基金刻意壓低這些房子的現行使用價值,藉此替它們的再投資計畫辯解,但它們自己在金融市場崩盤中破產了,留下房客住在使用價值變差但租金反而變貴的房子裡,而且這些房子因為原本的主人破產而遭金融機構沒收,誰該負起屋主的責任往往並不清楚(如果你住在這種大樓裡,發現暖氣爐壞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該找誰處理問題)。近一○%的出租房屋遇到了這種問題。因為有人不顧後果地追求交換價值極大化,一大部分人可以享有的房屋使用價值受損了。當然,更慘的是,房市崩盤引發一場全球危機,結果全球經濟至今仍然很難康復。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資本主義下的房屋供給,已經從追求使用價值為主,變成以追求交換價值為主。因為這種怪異的轉變,房屋的使用價值日趨變質,首先是變成一種儲蓄手段,其次是變成一種投機工具,而利用這種投機工具的除了消費者,還有建商、金融業者和所有可受惠於房市榮景的人,包括房屋仲介、房貸放款人員、律師和保險經紀等等。為大眾提供足夠的房屋使用價值(傳統消費意義上的使用價值),愈來愈受制於不斷深化的交換價值考量。我們致力為愈來愈大比例的人口提供足夠和可負擔的房屋,結果卻是一場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