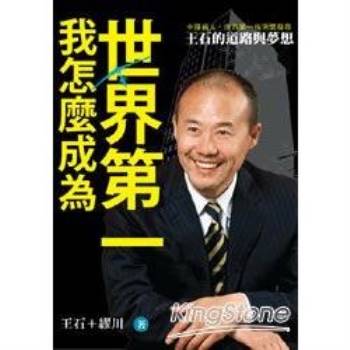■第一桶金
有一天,我坐小巴士去蛇口。在從深南路拐進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見路邊聳立著幾個巨大的白鐵罐。另外,在蛇口碼頭邊也有三座類似的金屬罐。跟附近的人打聽,才知道這是飼料廠的玉米儲藏倉。位於丁字路口的是泰國正大集團、美國大陸穀物公司與深圳養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正大康地;緊臨蛇口碼頭的飼料廠則是新加坡遠東集團投資的麵粉加工暨飼料廠――蛇口遠東金錢麵粉飼料企業。
「玉米?廣東不生產玉米啊!這些玉米打哪來的?」
「從香港來的。」
「香港也不產玉米啊?」
進一步追問,得知這些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
「為什麼廠家不直接從東北採購?」我帶著疑問前去找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盧達民先生,說起話來不急不徐,一口潮州口音:「公司也想從東北直接採購,以降低成本,只是解決不了運輸問題。」
「我來解決運輸問題,鐵路、海運都不成問題,我弄來的玉米,你們要嗎?」
「要!馬上就可以簽合約!廠裡正在試運轉,每年可處理三十萬噸,百分之七十是玉米,平均每個月的需求量在一萬七千噸左右。」
乖乖,一開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開L/C(信用狀)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只要正大康地肯開信用狀賣方,我就可以背書,開給真正的賣方,「空手套白狼」*1了。
「簽合約後,就開出去。」盧先生爽快地答應。
「付的是外匯嗎?」
「對我們來講,付外匯、人民幣都一樣。」
「貨是由外貿部門提供,我要求付外匯。」
「OK!」
其實,我並不清楚東北到深圳的運輸情況,但看在龐大的商機,我必須硬著頭皮往前衝。
首先,我去赤灣碼頭詢問航線情況。碼頭經理告訴我,剛落成的赤灣港目前只有從北歐進口的散裝化肥貨源,還沒有開通各地的航線。
「碼頭能泊靠多大的貨輪?」
「萬噸輪沒有問題。」
我接著前往廣州遠洋公司,詢問有無開通大連通往赤灣航線的可能。
他們回答我:「近海的航線歸廣州海運局管」。
探聽到廣州海運局總部設在沙面,我再次聯絡對方。
海運局回答:「只要有貨源,隨時開通。」
「每月至少兩萬噸的運輸量。」我馬上神氣起來,胸有成竹,正大康地、遠東金錢各一萬噸。
玉米生意就這麼開始了。
經陸總批准,成立了飼料貿易組,獨立於貿易一科,獨立核算,由我來擔任組長。
接下來就得請個幫手了。我想到了招待所樓下那家裝配廠。找到監工,問他能否推薦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監工轉頭指向一個正在焊錫條的工人,「就他行嗎?」
看他又瘦又小,活像個童工,我心裡著實不滿,嘴上卻回答:「行!」
「你多大年紀了?」我問他。
「十八歲。」就這樣,鄧奕權成了我聘請的第一位員工。
@沒見過發票的菜鳥業務員
最先來的貨是三十噸的玉米,裝了一整個車皮,賣給深圳養雞公司(上市公司「康達爾」的前身)。
深圳養雞公司運走了玉米,我也得去收錢了。騎著單車,後座上夾著兩個塑膠編織袋,一邊騎,一邊想:「三十噸的玉米賺來現金,用單車馱回去,應該不會遇到打劫吧?我可得小心點才行。」
到了位在紅嶺路上的養雞公司。我對該公司的袁經理揚了揚袋子:「貨你都運走了,我來收錢了。」
正抽著煙的袁經理看著我:「發票呢?」
發票?我真有點傻住了。
在省外經貿委待了三年,對合約、信用狀等比較熟,卻不知道發票是何物。我又不好意思問,猜想可能是收據之類的憑證,「你要發票呀,我回去幫你拿。」
回到公司後,去找財務部要求開證明。會計是剛從暨南大學財會大專班畢業的張敏。
「小張,給我開個收款證明。」
「開什麼證明?」小張一臉疑惑地問我。
「你就寫『賣了三十噸玉米給深圳養雞公司,每噸人民幣一千三百元,共計三萬九千元,特此證明』,就行啦!」
「從來沒有開過這種證明啊!」
「你就開吧,客戶要求的。」
小張幫我開了證明,並蓋上財務章。
我騎著單車,後座依然夾著塑膠編織袋。到了養雞公司,把證明拿給袁經理:「這是給你的發票。」
袁經理接過那張證明條,瞥了一眼,樂得嗆著了,一邊咳嗽,一邊說:「來,小王跟我來。」
把我帶進財務室後,袁經理從抽屜裡拿出了一本發票:「呐,發票上有國家稅務專用章。這是專門印製的,證明不能作為發票。你回去告訴財務要發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回到公司,我對張敏說:「他們要發票。」
張敏笑了笑:「早就開好了,我還納悶怎麼不拿發票就能收到錢?」
發票送到養雞公司的財務手上,對方給了我一式二聯的銀行轉帳單。我再次敲門,進了袁經理辦公室。
「怎麼沒有給錢,卻給了兩張這樣的東西?」我徹底糊塗了。
袁經理又樂了:「小王啊,你回去把這兩張單子交給財務,其中一聯是給銀行的,銀行見了票就會把錢劃撥到特發財務。」
半信半疑地回到公司,把轉帳單交給張敏:「這就是錢嗎?」
「如果銀行把票退回來,就表示養雞公司的銀行帳號裡沒有錢。不過,這種情況很少發生。應該沒有問題。」經過張敏耐心解釋,我才終於釋然。
這兩來兩往,讓我深刻感受到自己是多麼缺乏業務常識,尤其在財務方面,我更是個十足的門外漢。於是規定自己,在下班後,無論多晚都要看兩個小時的財務相關書籍。經由自學,我學到了什麼是資產負債表,什麼是資產平衡表。為了進一步理解財務,我開始學著記帳,將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都記下來,到了下個月初,再拿去對照張敏做的財務報表。
三個月後,我已經看得懂財務報表了。
◎去闖吧!不要有後顧之憂
我賺錢買了一輛一噸半的豐田小卡車,身兼組長、推銷員、貨場搬運、司機……忙得不可開交。
隨著業務快速拓展,就算我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所以又招聘了第二個助手黃世浩,他是當地的私立學校教師。陸陸續續招聘,加上由特發介紹來的,飼料貿易組增加為七個人。
某天中午,一位省外經貿委同事來深圳出差,順便來看我。恰逢午餐時間,他表示吃過了,但可以陪我用餐。我說:「不用,很快就可以打發。」順手撕開一包泡麵,倒了杯溫開水泡一下,就咯哧咯哧嚼了起來。不過三分鐘,「瞧,午餐結束了。」
「你就這樣湊合著,會不會艱苦了點?」同事很驚訝,我卻一點不覺得苦,反而喜歡這種充滿刺激的特區節奏。雖然未來有許多不確定,但正是這種不確定,讓我對未來滿懷憧憬。
「艱苦?」我反問:「在戈壁灘上開車時,冬天零下三十幾度,夏天氣溫高達四十度,一天只吃兩頓飯,連續開車十幾個小時,有時睡著了,車子一偏,就開進了戈壁灘。呵,好在那時候路上車輛不多。」
到了深圳創業,我才感覺到當年在部隊磨練出的吃苦精神、堅忍不拔的耐性,對創業者來說,是多麼彌足珍貴。
航線開通了,遠東金錢飼料廠和正大康地的業務推展得極為順利。飼料組專項帳戶裡的資金愈滾愈多,風言風語也來了:「王石自成體系,借用特發名義,卻背著特發貿易部賺大錢」。匿名信紛紛飛向總經理辦公室。
總經辦公室主任李守芬,人長得矮矮壯壯的,黑白髮間雜。每次碰到李總,我往往只是點點頭,禮貌性也打招呼。但有一次,李主任卻把我叫進辦公室,從抽屜裡掏出一疊已撕開的信封,「你幹得很好!總辦清楚。這些信的內容就沒有必要告訴你了。」
臨走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去闖吧!不要有後顧之憂。」聽到這位老幹部的鼓勵,心裡暖融融的。
在特發,我常打交道的,除了財務部的人,還有業務秘書曾國華。曾秘書屬於老三屆*2,和他談話有種快感,我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改制問題,比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的一些觀點很值得借鑑等等。在風言風語的環境中,能遇到這麼一位談得來的同事,是件很愉快的事。
工作中,最讓我興奮的事情之一就是玉米運到了筍崗北站。我帶著鄧奕權到筍崗,指揮民工裝卸玉米包,就像個戰地指揮官。有時自己也忍不住幫忙裝卸。一百五十斤的玉米包,往肩頭一扛,來回個十幾趟。休息時,有民工問起:「一個城裡人,隨便做什麼不成,不用和我們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心裡想:燕雀焉知鴻鵠之志!
除了把玉米賣給飼料廠,飼料組也開始銷售雞隻和豬飼料。客戶分散在珠三角洲和湖南、江西、廣西等華南地區。飼料產品很受飼養戶歡迎,許多公司提著現款等貨,一包包印著「正大康地」商標的新出爐飼料正等著運到各地。
◎玉米市場在一夜間崩盤
一九八三年八月,香港出現了一則新聞報導:雞飼料裡含有致癌物質!
一夜間,香港人不再吃雞肉,改吃肉鴿。從珠三角洲出口到香港的肉雞也在瞬間失去了市場,飼主不再買飼料,飼料廠也暫時停產。再次來到正大康地,看到了觸目驚心的一幕:成千上萬剛孵化的雛雞被推進焚化爐裡!過去只在書本上看過:發生經濟危機時,上千噸賣不掉的牛奶被倒進海裡,剛出生的牛犢立刻被宰殺。眼前的場景如出一轍。細想之下,發現這看似殘酷的行為卻有其合理性,如果繼續把雛雞養大,卻又賣不掉,損失會更大。殘酷的選擇未必不是合理的選擇。
城門之火殃及池魚,原本暢銷的玉米也成了滯銷貨。
近千噸玉米陸續抵達筍崗北站。倉庫塞滿了玉米包,月台上也是滿滿的玉米堆,無處卸貨的玉米就被暫時擱在鐵路沿線……到貨的車皮數量仍不斷增加中。我開始覺得不對勁,核對相關表單,結果讓我大吃一驚,本月到達的玉米竟然多達四千噸,整整多了四倍!
怎麼會增加這麼多?我趕緊打電報問發貨單位,這才知道原來計畫內運往香港的玉米,因為香港方面不肯開信用狀,而臨時改發給了王石。如果沒有「致癌素」事件,玉米多多益善,但現在卻讓我欲哭無淚。
這下子,整個筍崗北站到處都是玉米,另外還有二十幾輛待卸貨的玉米車皮。
沒幾天後,颱風肆虐深圳。颱風一過,只見遮蓋玉米的帆布破口處冒著白色泡沫,就像大閘蟹吐泡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破口處灌進雨水,玉米受潮,加上悶熱造成發酵,於是就產生了氣泡……空氣中因而瀰漫著一股酸味。
我急忙動員全組人員,並雇了二十個民工幫忙攤開帆布,打開麻袋,曬乾受潮的玉米,剔除發黴變質的玉米。幹著幹著,突然發現麻袋口上血跡斑斑。哪來的血?張開手掌,發現自己的十指已被磨破,血淋淋的,卻沒有感到一絲疼痛。
◎雞糞再臭也得忍受
每天上午曬玉米,下午則開著小卡車,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推銷玉米,跑遍了順德、東莞、佛山、惠陽的生產大隊。但香港人不吃雞了,誰還有心思養雞?
有一次,黃世浩興沖沖介紹一位買主,是他過去任教學校的一位老師,購買一.五噸玉米,條件是還要免費幫忙運送兩噸豬飼料。我爽快答應了,送完一噸半玉米,再開車來到一處偏僻的養雞場。這位經營家庭農場的民辦老師指著一堆清理出的雞糞:「這就是餵豬的飼料,裝車吧。」我二話不說,脫掉鞋襪,挽起長褲,赤腳站到雞糞裡,屏住呼吸,掄起鐵鍬往車箱裡甩雞糞。難道這位老師是教生物的?把雞糞裡沒有被完全消化的蛋白質再送到豬的胃裡接著消化?就這麼弄,直到半夜才收工,渾身是雞糞臭味。
香港人不吃雞,珠江三角洲的人卻照吃不誤,玉米的銷售目標也隨之對準珠江三角洲的養雞場。
我電話給惠陽養雞公司的霍經理,經過我一番勸說,對方把訂單從三十噸增加到一百五十噸,條件是貨到四十五天後付款。
「下個星期我們從惠陽去深圳拉玉米,王經理,你們把貨準備好。」
「我給你送貨,明天我親自押送。」
「倉庫還沒準備好。」
「一言為定,明天下午四點前兩百噸玉米送到。」
「不是一百五十噸嗎?怎麼又加碼了?」
「啊……」
放下電話筒,我開卡車前往皇崗村。發現「牛仔」去香港了,也沒有找到發仔。打聽到村裡的翻斗車都在深南S路段運送沙石。在沙塵滾滾的工地裡找到發仔的翻斗車,追上去按喇叭,「喂!發仔,動員全村的翻斗車,明早到筍崗北站裝玉米,去趟惠陽。」
「不行啊!這裡的活得幹一個星期。」
「後天繼續幹嘛!」
「不行啊!要罰款的。」
「運輸費按雙倍價錢,去不去?」
「要多少輛?」
「多多益善。」
「什麼意思?」
「能來的全來!」
第二天,發仔帶著三十八輛卡車到了筍崗北站,其中二十一輛是八噸的翻斗車。載重量五噸的,我們裝七噸;載重量八噸的,我們裝十一至十二噸,總計裝載了三百六十噸。
身為飼料組組長,我駕駛豐田小卡車在前面引路,車隊浩浩蕩蕩殺了過去。下午四點半抵達惠陽養雞公司。霍經理嚇了一跳。我安慰他:「你不需要的算我的,暫存。」
玉米放到這裡,連路費算進去,也比堆在鐵路倉庫裡便宜。鐵路倉庫的堆場費是每三天每噸三角,三天後變成每噸六角,再過三天就漲成每噸一.二元,之後是二.四元、四.八元、九.六元……便宜貨存放一個月,其價值還不夠付倉租費。
「王經理呀!我沒有那麼大倉庫!」霍經理一付無能為力的樣子。
貨總不能再運回去吧。養雞公司旁邊是座小學校,暑假期間沒有學生。我聯絡校方,騰出三個教室當作臨時倉庫。
回深圳途中,我在車上播放《新世界交響曲》,緊繃的神經總算放鬆了些。
◎被迫流血大拍賣
沒料到,更大的打擊正等著我。
回到深圳時已經是深夜了。鄧仔一臉愁容,遞給我一張通知單,上頭寫著:鑒於貨主的積壓貨已妨礙全特區人民的糧食、煤炭的正常卸載,如不能三日內清理貨站的玉米,將視貨主藐視管理部門,沒收其貨物並重罰云云。落款的是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揮部。
「怎敢藐視啊,實在是一沒市場,二沒倉庫。」我暗自叫苦。
打聽到交通指揮部焦主任的居住地址,我抱了一顆西瓜,連夜登門賠罪。焦主任氣得質問:「我們還在納悶,這貨主是何方神聖?把地全占了,煤炭、大米、麵粉全都卸不下來。三天內把玉米清乾淨,否則重罰。」
「寬限一個星期吧!」
「沒有商量餘地,就三天,再拖延,後果自負。」
從焦經理家裡出來後,開車直奔皇崗村。村裡已經沒有燈光,只零星傳來幾聲狗吠。我咚咚咚地敲響「牛仔」家的門,睡眼惺忪的村支書(農村支部書記)應門:「什麼事,不能明天商量嗎?」
「給你賺錢機會。」
「賺錢也不能不睡覺呀!」
講明了原委,「牛仔」思索了一會,接著問:「我能做什麼?」
「港商在你們村開鑿了那麼多魚塘,玉米也可以餵魚吧?」
「這麼急,人家不殺你個血本無歸?」
「顧不了那麼多了,我現在成了破壞特區居民安定生活的禍首,看焦主任的架勢,三天不清理乾淨,要拘留我呐。」
「還是跟著我做舊輪胎生意吧!不辛苦,也沒有什麼風險。」村支書憂慮地看著我。
「呐,第一,你現在就通知魚塘老闆,明天上午十點在筍崗北站拍賣庫存玉米;第二,通知其他村的幹部,讓附近魚塘的老闆全去參加拍賣,也得現在通知。拜託啦!」
第二天十點鐘。我站在玉米堆上,下面圍著二十幾個魚塘老闆或代理人。我拉高嗓門:「這一堆三十噸,有些浸水發黴,但大部分是好的,就是發黴的,也可以餵魚。成本價四萬塊,起價兩萬,有人要嗎?」沒人投標。
「一萬八。」我只好降價。
「三千。」有人舉手應價。
我問他:「你說的是美金吧?」眾人傳來一陣笑聲。
「一萬七」,我故作鎮靜,但心口好像被捅了一刀。
「一萬六」,我仍固執地每叫價一次只降一千元。
「五千」第二個人應價。叫價、應價,幾輪下來,第一堆三十噸玉米以一萬兩千元成交,相當於每噸四百元。接著,第二堆、第三堆、第四堆……。
下午接著一堆一堆拍賣,直到夕陽染紅筍崗北站,那似乎是鮮血的顏色……。
一整天下來,拍賣出四百噸。第二天繼續淌血。無論如何,第三天一定要清空倉庫和月台。
當晚,宿舍來了幾位不速之客。自稱是深圳華僑光明農場的人,聽說這裡有大量便宜的玉米。他們自我介紹:光明農場飼養奶牛,為香港維它奶提供鮮奶。
「每噸七百元,全部掃光。怎麼樣,王經理?」
「你們是趁火打劫呀!」我一臉不情願,心裡卻盤算著:「跟魚塘佬出的價格相比,每噸多賣了三百塊,僅此一項,少損失約一百萬。問題是,沒跟光明農場打過交道,靠得住嗎?」
「OK!」我表示接受買價。
第二天,聚集在筍崗北站的魚塘老闆們得知沒了便宜玉米,心痛得不得了。
◎香港人啊,吃雞肉吧!
這場仗打下來,共賠了一百一十萬,連白手起家賺的四十萬全賠進去了。只要供貨方催逼貨款,我隨時可能破產。怎麼辦才好?
足足睡了二十四小時後,我起來打點行李,坐上往北去的火車,再從廣州搭飛機到大連,找到大連糧油進出口公司,詢問對方還有多少庫存玉米?
「一萬五千噸。」
「全收了,我派船,在當地港口交貨,付款條件是到貨一百天再付錢。」我很清楚外貿部急於出清庫存,再苛的條件也會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島,我把外貿部的庫存玉米全買下來,共三萬多噸。
我不相信香港人從此不再吃雞肉。只要吃雞肉就得養雞,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且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現貨。現在玉米沒人要,市價是最低的。問題不在香港人是否吃雞肉,答案是肯定的,而是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恢復吃雞肉?萬一玉米到了深圳一百天後,香港人仍執意「以鴿代雞」,
有一天,我坐小巴士去蛇口。在從深南路拐進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見路邊聳立著幾個巨大的白鐵罐。另外,在蛇口碼頭邊也有三座類似的金屬罐。跟附近的人打聽,才知道這是飼料廠的玉米儲藏倉。位於丁字路口的是泰國正大集團、美國大陸穀物公司與深圳養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正大康地;緊臨蛇口碼頭的飼料廠則是新加坡遠東集團投資的麵粉加工暨飼料廠――蛇口遠東金錢麵粉飼料企業。
「玉米?廣東不生產玉米啊!這些玉米打哪來的?」
「從香港來的。」
「香港也不產玉米啊?」
進一步追問,得知這些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
「為什麼廠家不直接從東北採購?」我帶著疑問前去找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盧達民先生,說起話來不急不徐,一口潮州口音:「公司也想從東北直接採購,以降低成本,只是解決不了運輸問題。」
「我來解決運輸問題,鐵路、海運都不成問題,我弄來的玉米,你們要嗎?」
「要!馬上就可以簽合約!廠裡正在試運轉,每年可處理三十萬噸,百分之七十是玉米,平均每個月的需求量在一萬七千噸左右。」
乖乖,一開始就是大生意!「正大康地能先開L/C(信用狀)嗎?」我小心翼翼地問。只要正大康地肯開信用狀賣方,我就可以背書,開給真正的賣方,「空手套白狼」*1了。
「簽合約後,就開出去。」盧先生爽快地答應。
「付的是外匯嗎?」
「對我們來講,付外匯、人民幣都一樣。」
「貨是由外貿部門提供,我要求付外匯。」
「OK!」
其實,我並不清楚東北到深圳的運輸情況,但看在龐大的商機,我必須硬著頭皮往前衝。
首先,我去赤灣碼頭詢問航線情況。碼頭經理告訴我,剛落成的赤灣港目前只有從北歐進口的散裝化肥貨源,還沒有開通各地的航線。
「碼頭能泊靠多大的貨輪?」
「萬噸輪沒有問題。」
我接著前往廣州遠洋公司,詢問有無開通大連通往赤灣航線的可能。
他們回答我:「近海的航線歸廣州海運局管」。
探聽到廣州海運局總部設在沙面,我再次聯絡對方。
海運局回答:「只要有貨源,隨時開通。」
「每月至少兩萬噸的運輸量。」我馬上神氣起來,胸有成竹,正大康地、遠東金錢各一萬噸。
玉米生意就這麼開始了。
經陸總批准,成立了飼料貿易組,獨立於貿易一科,獨立核算,由我來擔任組長。
接下來就得請個幫手了。我想到了招待所樓下那家裝配廠。找到監工,問他能否推薦一名打工仔。瘦瘦的監工轉頭指向一個正在焊錫條的工人,「就他行嗎?」
看他又瘦又小,活像個童工,我心裡著實不滿,嘴上卻回答:「行!」
「你多大年紀了?」我問他。
「十八歲。」就這樣,鄧奕權成了我聘請的第一位員工。
@沒見過發票的菜鳥業務員
最先來的貨是三十噸的玉米,裝了一整個車皮,賣給深圳養雞公司(上市公司「康達爾」的前身)。
深圳養雞公司運走了玉米,我也得去收錢了。騎著單車,後座上夾著兩個塑膠編織袋,一邊騎,一邊想:「三十噸的玉米賺來現金,用單車馱回去,應該不會遇到打劫吧?我可得小心點才行。」
到了位在紅嶺路上的養雞公司。我對該公司的袁經理揚了揚袋子:「貨你都運走了,我來收錢了。」
正抽著煙的袁經理看著我:「發票呢?」
發票?我真有點傻住了。
在省外經貿委待了三年,對合約、信用狀等比較熟,卻不知道發票是何物。我又不好意思問,猜想可能是收據之類的憑證,「你要發票呀,我回去幫你拿。」
回到公司後,去找財務部要求開證明。會計是剛從暨南大學財會大專班畢業的張敏。
「小張,給我開個收款證明。」
「開什麼證明?」小張一臉疑惑地問我。
「你就寫『賣了三十噸玉米給深圳養雞公司,每噸人民幣一千三百元,共計三萬九千元,特此證明』,就行啦!」
「從來沒有開過這種證明啊!」
「你就開吧,客戶要求的。」
小張幫我開了證明,並蓋上財務章。
我騎著單車,後座依然夾著塑膠編織袋。到了養雞公司,把證明拿給袁經理:「這是給你的發票。」
袁經理接過那張證明條,瞥了一眼,樂得嗆著了,一邊咳嗽,一邊說:「來,小王跟我來。」
把我帶進財務室後,袁經理從抽屜裡拿出了一本發票:「呐,發票上有國家稅務專用章。這是專門印製的,證明不能作為發票。你回去告訴財務要發票,她就清楚了。」
再次回到公司,我對張敏說:「他們要發票。」
張敏笑了笑:「早就開好了,我還納悶怎麼不拿發票就能收到錢?」
發票送到養雞公司的財務手上,對方給了我一式二聯的銀行轉帳單。我再次敲門,進了袁經理辦公室。
「怎麼沒有給錢,卻給了兩張這樣的東西?」我徹底糊塗了。
袁經理又樂了:「小王啊,你回去把這兩張單子交給財務,其中一聯是給銀行的,銀行見了票就會把錢劃撥到特發財務。」
半信半疑地回到公司,把轉帳單交給張敏:「這就是錢嗎?」
「如果銀行把票退回來,就表示養雞公司的銀行帳號裡沒有錢。不過,這種情況很少發生。應該沒有問題。」經過張敏耐心解釋,我才終於釋然。
這兩來兩往,讓我深刻感受到自己是多麼缺乏業務常識,尤其在財務方面,我更是個十足的門外漢。於是規定自己,在下班後,無論多晚都要看兩個小時的財務相關書籍。經由自學,我學到了什麼是資產負債表,什麼是資產平衡表。為了進一步理解財務,我開始學著記帳,將每天的交易、支出、收入都記下來,到了下個月初,再拿去對照張敏做的財務報表。
三個月後,我已經看得懂財務報表了。
◎去闖吧!不要有後顧之憂
我賺錢買了一輛一噸半的豐田小卡車,身兼組長、推銷員、貨場搬運、司機……忙得不可開交。
隨著業務快速拓展,就算我有三頭六臂,也忙不過來,所以又招聘了第二個助手黃世浩,他是當地的私立學校教師。陸陸續續招聘,加上由特發介紹來的,飼料貿易組增加為七個人。
某天中午,一位省外經貿委同事來深圳出差,順便來看我。恰逢午餐時間,他表示吃過了,但可以陪我用餐。我說:「不用,很快就可以打發。」順手撕開一包泡麵,倒了杯溫開水泡一下,就咯哧咯哧嚼了起來。不過三分鐘,「瞧,午餐結束了。」
「你就這樣湊合著,會不會艱苦了點?」同事很驚訝,我卻一點不覺得苦,反而喜歡這種充滿刺激的特區節奏。雖然未來有許多不確定,但正是這種不確定,讓我對未來滿懷憧憬。
「艱苦?」我反問:「在戈壁灘上開車時,冬天零下三十幾度,夏天氣溫高達四十度,一天只吃兩頓飯,連續開車十幾個小時,有時睡著了,車子一偏,就開進了戈壁灘。呵,好在那時候路上車輛不多。」
到了深圳創業,我才感覺到當年在部隊磨練出的吃苦精神、堅忍不拔的耐性,對創業者來說,是多麼彌足珍貴。
航線開通了,遠東金錢飼料廠和正大康地的業務推展得極為順利。飼料組專項帳戶裡的資金愈滾愈多,風言風語也來了:「王石自成體系,借用特發名義,卻背著特發貿易部賺大錢」。匿名信紛紛飛向總經理辦公室。
總經辦公室主任李守芬,人長得矮矮壯壯的,黑白髮間雜。每次碰到李總,我往往只是點點頭,禮貌性也打招呼。但有一次,李主任卻把我叫進辦公室,從抽屜裡掏出一疊已撕開的信封,「你幹得很好!總辦清楚。這些信的內容就沒有必要告訴你了。」
臨走時,他拍拍我的肩膀:「去闖吧!不要有後顧之憂。」聽到這位老幹部的鼓勵,心裡暖融融的。
在特發,我常打交道的,除了財務部的人,還有業務秘書曾國華。曾秘書屬於老三屆*2,和他談話有種快感,我們最感興趣的話題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改制問題,比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Janos Kornai)的一些觀點很值得借鑑等等。在風言風語的環境中,能遇到這麼一位談得來的同事,是件很愉快的事。
工作中,最讓我興奮的事情之一就是玉米運到了筍崗北站。我帶著鄧奕權到筍崗,指揮民工裝卸玉米包,就像個戰地指揮官。有時自己也忍不住幫忙裝卸。一百五十斤的玉米包,往肩頭一扛,來回個十幾趟。休息時,有民工問起:「一個城裡人,隨便做什麼不成,不用和我們一起扛麻袋啊!」
我淡淡一笑,心裡想:燕雀焉知鴻鵠之志!
除了把玉米賣給飼料廠,飼料組也開始銷售雞隻和豬飼料。客戶分散在珠三角洲和湖南、江西、廣西等華南地區。飼料產品很受飼養戶歡迎,許多公司提著現款等貨,一包包印著「正大康地」商標的新出爐飼料正等著運到各地。
◎玉米市場在一夜間崩盤
一九八三年八月,香港出現了一則新聞報導:雞飼料裡含有致癌物質!
一夜間,香港人不再吃雞肉,改吃肉鴿。從珠三角洲出口到香港的肉雞也在瞬間失去了市場,飼主不再買飼料,飼料廠也暫時停產。再次來到正大康地,看到了觸目驚心的一幕:成千上萬剛孵化的雛雞被推進焚化爐裡!過去只在書本上看過:發生經濟危機時,上千噸賣不掉的牛奶被倒進海裡,剛出生的牛犢立刻被宰殺。眼前的場景如出一轍。細想之下,發現這看似殘酷的行為卻有其合理性,如果繼續把雛雞養大,卻又賣不掉,損失會更大。殘酷的選擇未必不是合理的選擇。
城門之火殃及池魚,原本暢銷的玉米也成了滯銷貨。
近千噸玉米陸續抵達筍崗北站。倉庫塞滿了玉米包,月台上也是滿滿的玉米堆,無處卸貨的玉米就被暫時擱在鐵路沿線……到貨的車皮數量仍不斷增加中。我開始覺得不對勁,核對相關表單,結果讓我大吃一驚,本月到達的玉米竟然多達四千噸,整整多了四倍!
怎麼會增加這麼多?我趕緊打電報問發貨單位,這才知道原來計畫內運往香港的玉米,因為香港方面不肯開信用狀,而臨時改發給了王石。如果沒有「致癌素」事件,玉米多多益善,但現在卻讓我欲哭無淚。
這下子,整個筍崗北站到處都是玉米,另外還有二十幾輛待卸貨的玉米車皮。
沒幾天後,颱風肆虐深圳。颱風一過,只見遮蓋玉米的帆布破口處冒著白色泡沫,就像大閘蟹吐泡泡。這是怎麼回事?原來,破口處灌進雨水,玉米受潮,加上悶熱造成發酵,於是就產生了氣泡……空氣中因而瀰漫著一股酸味。
我急忙動員全組人員,並雇了二十個民工幫忙攤開帆布,打開麻袋,曬乾受潮的玉米,剔除發黴變質的玉米。幹著幹著,突然發現麻袋口上血跡斑斑。哪來的血?張開手掌,發現自己的十指已被磨破,血淋淋的,卻沒有感到一絲疼痛。
◎雞糞再臭也得忍受
每天上午曬玉米,下午則開著小卡車,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推銷玉米,跑遍了順德、東莞、佛山、惠陽的生產大隊。但香港人不吃雞了,誰還有心思養雞?
有一次,黃世浩興沖沖介紹一位買主,是他過去任教學校的一位老師,購買一.五噸玉米,條件是還要免費幫忙運送兩噸豬飼料。我爽快答應了,送完一噸半玉米,再開車來到一處偏僻的養雞場。這位經營家庭農場的民辦老師指著一堆清理出的雞糞:「這就是餵豬的飼料,裝車吧。」我二話不說,脫掉鞋襪,挽起長褲,赤腳站到雞糞裡,屏住呼吸,掄起鐵鍬往車箱裡甩雞糞。難道這位老師是教生物的?把雞糞裡沒有被完全消化的蛋白質再送到豬的胃裡接著消化?就這麼弄,直到半夜才收工,渾身是雞糞臭味。
香港人不吃雞,珠江三角洲的人卻照吃不誤,玉米的銷售目標也隨之對準珠江三角洲的養雞場。
我電話給惠陽養雞公司的霍經理,經過我一番勸說,對方把訂單從三十噸增加到一百五十噸,條件是貨到四十五天後付款。
「下個星期我們從惠陽去深圳拉玉米,王經理,你們把貨準備好。」
「我給你送貨,明天我親自押送。」
「倉庫還沒準備好。」
「一言為定,明天下午四點前兩百噸玉米送到。」
「不是一百五十噸嗎?怎麼又加碼了?」
「啊……」
放下電話筒,我開卡車前往皇崗村。發現「牛仔」去香港了,也沒有找到發仔。打聽到村裡的翻斗車都在深南S路段運送沙石。在沙塵滾滾的工地裡找到發仔的翻斗車,追上去按喇叭,「喂!發仔,動員全村的翻斗車,明早到筍崗北站裝玉米,去趟惠陽。」
「不行啊!這裡的活得幹一個星期。」
「後天繼續幹嘛!」
「不行啊!要罰款的。」
「運輸費按雙倍價錢,去不去?」
「要多少輛?」
「多多益善。」
「什麼意思?」
「能來的全來!」
第二天,發仔帶著三十八輛卡車到了筍崗北站,其中二十一輛是八噸的翻斗車。載重量五噸的,我們裝七噸;載重量八噸的,我們裝十一至十二噸,總計裝載了三百六十噸。
身為飼料組組長,我駕駛豐田小卡車在前面引路,車隊浩浩蕩蕩殺了過去。下午四點半抵達惠陽養雞公司。霍經理嚇了一跳。我安慰他:「你不需要的算我的,暫存。」
玉米放到這裡,連路費算進去,也比堆在鐵路倉庫裡便宜。鐵路倉庫的堆場費是每三天每噸三角,三天後變成每噸六角,再過三天就漲成每噸一.二元,之後是二.四元、四.八元、九.六元……便宜貨存放一個月,其價值還不夠付倉租費。
「王經理呀!我沒有那麼大倉庫!」霍經理一付無能為力的樣子。
貨總不能再運回去吧。養雞公司旁邊是座小學校,暑假期間沒有學生。我聯絡校方,騰出三個教室當作臨時倉庫。
回深圳途中,我在車上播放《新世界交響曲》,緊繃的神經總算放鬆了些。
◎被迫流血大拍賣
沒料到,更大的打擊正等著我。
回到深圳時已經是深夜了。鄧仔一臉愁容,遞給我一張通知單,上頭寫著:鑒於貨主的積壓貨已妨礙全特區人民的糧食、煤炭的正常卸載,如不能三日內清理貨站的玉米,將視貨主藐視管理部門,沒收其貨物並重罰云云。落款的是深圳市政府交通指揮部。
「怎敢藐視啊,實在是一沒市場,二沒倉庫。」我暗自叫苦。
打聽到交通指揮部焦主任的居住地址,我抱了一顆西瓜,連夜登門賠罪。焦主任氣得質問:「我們還在納悶,這貨主是何方神聖?把地全占了,煤炭、大米、麵粉全都卸不下來。三天內把玉米清乾淨,否則重罰。」
「寬限一個星期吧!」
「沒有商量餘地,就三天,再拖延,後果自負。」
從焦經理家裡出來後,開車直奔皇崗村。村裡已經沒有燈光,只零星傳來幾聲狗吠。我咚咚咚地敲響「牛仔」家的門,睡眼惺忪的村支書(農村支部書記)應門:「什麼事,不能明天商量嗎?」
「給你賺錢機會。」
「賺錢也不能不睡覺呀!」
講明了原委,「牛仔」思索了一會,接著問:「我能做什麼?」
「港商在你們村開鑿了那麼多魚塘,玉米也可以餵魚吧?」
「這麼急,人家不殺你個血本無歸?」
「顧不了那麼多了,我現在成了破壞特區居民安定生活的禍首,看焦主任的架勢,三天不清理乾淨,要拘留我呐。」
「還是跟著我做舊輪胎生意吧!不辛苦,也沒有什麼風險。」村支書憂慮地看著我。
「呐,第一,你現在就通知魚塘老闆,明天上午十點在筍崗北站拍賣庫存玉米;第二,通知其他村的幹部,讓附近魚塘的老闆全去參加拍賣,也得現在通知。拜託啦!」
第二天十點鐘。我站在玉米堆上,下面圍著二十幾個魚塘老闆或代理人。我拉高嗓門:「這一堆三十噸,有些浸水發黴,但大部分是好的,就是發黴的,也可以餵魚。成本價四萬塊,起價兩萬,有人要嗎?」沒人投標。
「一萬八。」我只好降價。
「三千。」有人舉手應價。
我問他:「你說的是美金吧?」眾人傳來一陣笑聲。
「一萬七」,我故作鎮靜,但心口好像被捅了一刀。
「一萬六」,我仍固執地每叫價一次只降一千元。
「五千」第二個人應價。叫價、應價,幾輪下來,第一堆三十噸玉米以一萬兩千元成交,相當於每噸四百元。接著,第二堆、第三堆、第四堆……。
下午接著一堆一堆拍賣,直到夕陽染紅筍崗北站,那似乎是鮮血的顏色……。
一整天下來,拍賣出四百噸。第二天繼續淌血。無論如何,第三天一定要清空倉庫和月台。
當晚,宿舍來了幾位不速之客。自稱是深圳華僑光明農場的人,聽說這裡有大量便宜的玉米。他們自我介紹:光明農場飼養奶牛,為香港維它奶提供鮮奶。
「每噸七百元,全部掃光。怎麼樣,王經理?」
「你們是趁火打劫呀!」我一臉不情願,心裡卻盤算著:「跟魚塘佬出的價格相比,每噸多賣了三百塊,僅此一項,少損失約一百萬。問題是,沒跟光明農場打過交道,靠得住嗎?」
「OK!」我表示接受買價。
第二天,聚集在筍崗北站的魚塘老闆們得知沒了便宜玉米,心痛得不得了。
◎香港人啊,吃雞肉吧!
這場仗打下來,共賠了一百一十萬,連白手起家賺的四十萬全賠進去了。只要供貨方催逼貨款,我隨時可能破產。怎麼辦才好?
足足睡了二十四小時後,我起來打點行李,坐上往北去的火車,再從廣州搭飛機到大連,找到大連糧油進出口公司,詢問對方還有多少庫存玉米?
「一萬五千噸。」
「全收了,我派船,在當地港口交貨,付款條件是到貨一百天再付錢。」我很清楚外貿部急於出清庫存,再苛的條件也會接受。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島,我把外貿部的庫存玉米全買下來,共三萬多噸。
我不相信香港人從此不再吃雞肉。只要吃雞肉就得養雞,就得消耗大量的玉米,而且只有我王石手中有現貨。現在玉米沒人要,市價是最低的。問題不在香港人是否吃雞肉,答案是肯定的,而是香港人什麼時候開始恢復吃雞肉?萬一玉米到了深圳一百天後,香港人仍執意「以鴿代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