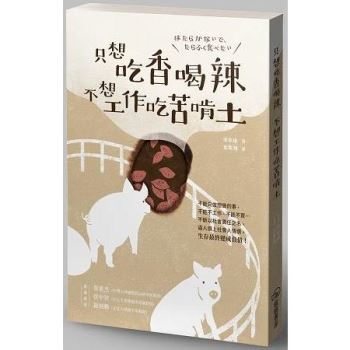推薦序
左派、牛頓定律與日本人的「日常」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給幾乎沒有左派存在的台灣
對台灣讀者來說,栗原康這本書應會帶來很不一樣的閱讀感受。
如同作者在書中不斷陳述的,他不但以「無政府主義」作為研究重點,經常參與反政府示威抗議活動(身旁還有一群人也是),字裡行間對「國家」體制的不滿更溢於言表;例如他援引了史考特(James C. Scott)的說法,指出古代國家的特徵就是要求人民從事水田稻作,支配者會先用暴力支配農民,接著再貪婪地榨取年貢稅金,甚至將奴性植入農民心中,讓他們認為自己是託了國家的福才能工作,所以一定要回報這份恩情云云。
對於當下的國家,他更直言「我討厭政治,不只是討厭而已,我甚至覺得不需要;政治指的就是人支配人這件事,還是不存在比較好;所以,一看到為了選舉之類的事便情緒激動的人,就讓我退避三舍。要把票投給某個黨的某某某,這種事我才不幹,我就是不喜歡把自己的意志委託給他人代理」,「更過份的是,利用這一點的人相當多,一下說有核彈威脅,一下說有恐怖主義的危險,不斷搧風點火,還放任警察或軍隊的違法行為,卻說是為了保護國民安全才不得已這麼做,讓那些違法的行為,變得像是遵照法令而做的行為」;甚至連看似對大家有利的年金設計,他也指出這是種「逼人們要連未來的工作都得先做,二話不說就強制要人付錢」的荒謬制度。
這些話呈現出來的畫面,是不是有點眼熟呢?
是的,不只在日本,台灣其實也差不多。差別在於,儘管這些年來,台灣的自主性公民運動成熟進步不少,對相關問題的批判能力也大幅增加,問題是類似能量還有很大的累積空間。相較世界其他國家,台灣的政治奇蹟之一是迄今仍沒有任何左派政黨的生存空間,有影響力的政黨全都屬於「中間偏右」,在學術界中左派聲音也非常有限(不像在日本,政治雖由右派佔上風,學界則是左派天下),偶爾有些激進的反政府聲浪,但領導者很快地不是跟政治力掛勾,便是讓自己在政治中體制化了。
真正的反對派,絕不能成為反對黨,而是要永遠跟政治站在對立面。如果以為只有投身政治才能改變政治,其實是有點走火入魔的嫌疑。
對一個極端矛盾之「大同」世界的反思
進一步來說,反國家或反政治也不過是「反對」的一部分罷了,這些反對者要批判的乃是「整個」體制,除了政治,經濟與社會也不能放過,更何況我們正處於某種「大同」世界中。請注意,這裡所謂大同並不是那個「大同」,而是一個由於全球化所帶來無論身處何地都「大致相同」的狀況。
從經濟面看來,就是資本主義體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以下這些話應該耳熟能詳:「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最好先去賺點錢」、「你想做的事真賺得到錢嗎?如果賺不到的話,暫時先去做其他工作賺錢比較好」、「不這麼做的話,會活不下去喔」。
栗原康一開頭便批判了「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句恐怖格言。尤其當金融海嘯逼得全球不景氣幾乎毫無止境的當下。他直言,「明明不管怎麼想,大家都深知這困境是企業搞出來的,但別說是要求企業負起責任了,反倒還強烈建議大家要為企業拚命工作」,更甚者,「圍繞在我們身邊的這個社會,姑且可稱之為認知資本主義型社會,從過去到現在,這世間的一切都是為了賺錢而運作的,……乍看之下,這個社會似乎開始活用人類的大腦,事實上它根本不在乎是否真的靠大腦思考來運作,只是在聽別人說話而已,也就是說是個只重視耳朵的社會,要求大家只要接收到資訊,便毫不考慮地照著行動」。
當這種情況瀰漫到整個社會,尤其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生存這件事最終變成欠債,也就是生存的負債化;我們明明只想到自己,言行舉止卻裝得好像擁有美麗的利他精神似的,……例如大人總認為小孩是自己的所有物,將其視為家庭的一部分,企圖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扶養長大,並施以教育,希望將來他們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但在現實狀況裡,孩子的成長方式卻非如此,他們最終沈迷在完全看不出有何重要性的事物中,忘記時間流逝,不斷重覆做同樣的事,完全不在意周遭的事,只貪婪地讓自己的力量不斷成長。」
說到這兒,大家看得出一個絕大的矛盾嗎?
沒錯,就是「自由」。
現在這個世界,看似是個「自由至上」或到處講自由的時代,可自由是甚麼呢?不就是讓自己成為人生重心的一種生活方式嗎?但事實上,無論是國家、社會、企業或家庭,比起過去那個被描述成很不自由因此應該被棄絕的時代,所有社會單位加諸於個人身上的種種「服從性」限制,卻不知大了多少;絕大多數國家的強制力早就超過歐威爾所描繪的「老大哥」,絕大多數企業以為只要符合勞基法就可以無限地役使勞工,絕大多數的父母也以為只要「為了小孩子好」就可以將他們合理地推入一個沒有自我的升學地獄中。
沒錯,這就是今天,一個既自由又毫無自由的時代。
栗原康講得直率:「如今人的言行舉止都被設定了同一種標準,讓大家以為非得照著這個標準生活不可,有夠麻煩!人的言行舉止應該要更加自由不拘才對。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不應該是照著被規定好的程序來想著該怎麼做,而是要更直接地想著是否自己真的好想要,再為此認真地發揮創意,這才叫夢想,這才是真正的魔法。」
若非如此,一生只在致力完成其他人的夢想,哪叫自由!
日本社會的矛盾日常:「絆」與「縛」
當然,沒必要以為在所謂「大同」世界中,大家的問題必然都一樣,說到底還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更甚者,當我們設法去看待瞭解這個世界時,最怕的其實就是「以為我們就代表了整個世界」,雖然這是許多研究者自然會陷入的最大盲點。就這點來說,栗原康做得還不錯。雖然他也時常不經意地流露出類似的邏輯錯誤,至少因為採取了直接面對讀者的寫法,從而讓他的描繪對象被突顯出來。
他要帶領大家審視的目標,就是日本。
眾所周知,「絆」,乃是日本社會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從某個角度看,也可說是一種「日本式的關係」。所謂絆,簡單來說就是羈絆或牽絆。他以東北大地震為例,「事實上,明明只要推廣無償的愛及憐憫之情這樣的理念就好了,卻硬是被加上稱為『羈絆』的社會道德感,現在甚至連『東北及關東地區的食物很危險,最好別吃』或『在輻射線下工作很危險,不要去比較好』等等的意見,都自我約束,不說出口;我們在精神上的負擔過於沉重,令人動彈不得。」事實確是如此。
我認為,所謂「絆」的相對面就是「縛」,也就是一種把人跟人緊緊地束縛在一起的強大能量。這麼作或這麼想的源起不難理解:生存壓力愈大,人際關係自然愈緊密,這也是「一把筷子」的自然之理。身在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嶼,日本社會的這種選擇很合理,台灣也差不多,所謂「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既表現了我們對人情味的重視,也凸顯出某種「絆」的味道。當然,兩者在程度上大有不同,由於受到制度設計(存在千年的封建體制)的強化,事實上讓日本「縛」的能量遠超過了「絆」,這便是栗原康前面指出的現象。
不過,正如經典力學對於「牛頓第三定律」的描述,當物體互相作用時,彼此施加於對方的力,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力必會成雙結對地出現:其中一道是「作用力」,另一道力則為「反作用力」或「抗力」,兩道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也就是說,隨著愈來愈強的牽絆帶來更大的束縛,尋求解放的欲望也更加強烈。以十九世紀末的近代化運動為契機,在透過維新強化國家職能,慢慢走向政治軍國主義的同時,一股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浪潮也隨之蔓延開來,至今仍在日本的文學、思想與評論界蔚為主流。
栗原康所陳述的,就是這種「主流」想法。
由於篇幅有限,對此不能談更多。總之這些對台灣來說可能有點新鮮,非常不主流的論調,在日本並不少見。尤其當所謂「絆」受到政治力加持,部分成為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後,雖看似依舊不可動搖地深植在日本社會中,想拔除它的積極或消極努力仍到處可見。畢竟很多事即便出發點良善,只要過了頭,自然會引發反彈跟矯正的聲浪,何況到了現在,強化「絆」能量的不只是政治力,還加上資本主義在「消費本位」跟「職場倫理」的調味加料,從而讓人們不禁生出為誰辛苦為誰忙的感嘆,這也就是栗原康所謂「生存負債化」的意思。
雖然全書用了非常戲謔輕鬆的字句,他在結語中說得很清楚,「衷心盼望本書能在幫助各位甩開生存負債上,盡一分微力,也希望能在將腐敗資本主義社會連根鏟除上,能有一點幫助。」說來容易,作起來當然不簡單,否則作者又何須如此叨叨絮絮呢。
更重要的,看著別人,總要想想自己。日本如此,台灣呢?
左派、牛頓定律與日本人的「日常」
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給幾乎沒有左派存在的台灣
對台灣讀者來說,栗原康這本書應會帶來很不一樣的閱讀感受。
如同作者在書中不斷陳述的,他不但以「無政府主義」作為研究重點,經常參與反政府示威抗議活動(身旁還有一群人也是),字裡行間對「國家」體制的不滿更溢於言表;例如他援引了史考特(James C. Scott)的說法,指出古代國家的特徵就是要求人民從事水田稻作,支配者會先用暴力支配農民,接著再貪婪地榨取年貢稅金,甚至將奴性植入農民心中,讓他們認為自己是託了國家的福才能工作,所以一定要回報這份恩情云云。
對於當下的國家,他更直言「我討厭政治,不只是討厭而已,我甚至覺得不需要;政治指的就是人支配人這件事,還是不存在比較好;所以,一看到為了選舉之類的事便情緒激動的人,就讓我退避三舍。要把票投給某個黨的某某某,這種事我才不幹,我就是不喜歡把自己的意志委託給他人代理」,「更過份的是,利用這一點的人相當多,一下說有核彈威脅,一下說有恐怖主義的危險,不斷搧風點火,還放任警察或軍隊的違法行為,卻說是為了保護國民安全才不得已這麼做,讓那些違法的行為,變得像是遵照法令而做的行為」;甚至連看似對大家有利的年金設計,他也指出這是種「逼人們要連未來的工作都得先做,二話不說就強制要人付錢」的荒謬制度。
這些話呈現出來的畫面,是不是有點眼熟呢?
是的,不只在日本,台灣其實也差不多。差別在於,儘管這些年來,台灣的自主性公民運動成熟進步不少,對相關問題的批判能力也大幅增加,問題是類似能量還有很大的累積空間。相較世界其他國家,台灣的政治奇蹟之一是迄今仍沒有任何左派政黨的生存空間,有影響力的政黨全都屬於「中間偏右」,在學術界中左派聲音也非常有限(不像在日本,政治雖由右派佔上風,學界則是左派天下),偶爾有些激進的反政府聲浪,但領導者很快地不是跟政治力掛勾,便是讓自己在政治中體制化了。
真正的反對派,絕不能成為反對黨,而是要永遠跟政治站在對立面。如果以為只有投身政治才能改變政治,其實是有點走火入魔的嫌疑。
對一個極端矛盾之「大同」世界的反思
進一步來說,反國家或反政治也不過是「反對」的一部分罷了,這些反對者要批判的乃是「整個」體制,除了政治,經濟與社會也不能放過,更何況我們正處於某種「大同」世界中。請注意,這裡所謂大同並不是那個「大同」,而是一個由於全球化所帶來無論身處何地都「大致相同」的狀況。
從經濟面看來,就是資本主義體系。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以下這些話應該耳熟能詳:「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最好先去賺點錢」、「你想做的事真賺得到錢嗎?如果賺不到的話,暫時先去做其他工作賺錢比較好」、「不這麼做的話,會活不下去喔」。
栗原康一開頭便批判了「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句恐怖格言。尤其當金融海嘯逼得全球不景氣幾乎毫無止境的當下。他直言,「明明不管怎麼想,大家都深知這困境是企業搞出來的,但別說是要求企業負起責任了,反倒還強烈建議大家要為企業拚命工作」,更甚者,「圍繞在我們身邊的這個社會,姑且可稱之為認知資本主義型社會,從過去到現在,這世間的一切都是為了賺錢而運作的,……乍看之下,這個社會似乎開始活用人類的大腦,事實上它根本不在乎是否真的靠大腦思考來運作,只是在聽別人說話而已,也就是說是個只重視耳朵的社會,要求大家只要接收到資訊,便毫不考慮地照著行動」。
當這種情況瀰漫到整個社會,尤其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生存這件事最終變成欠債,也就是生存的負債化;我們明明只想到自己,言行舉止卻裝得好像擁有美麗的利他精神似的,……例如大人總認為小孩是自己的所有物,將其視為家庭的一部分,企圖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扶養長大,並施以教育,希望將來他們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但在現實狀況裡,孩子的成長方式卻非如此,他們最終沈迷在完全看不出有何重要性的事物中,忘記時間流逝,不斷重覆做同樣的事,完全不在意周遭的事,只貪婪地讓自己的力量不斷成長。」
說到這兒,大家看得出一個絕大的矛盾嗎?
沒錯,就是「自由」。
現在這個世界,看似是個「自由至上」或到處講自由的時代,可自由是甚麼呢?不就是讓自己成為人生重心的一種生活方式嗎?但事實上,無論是國家、社會、企業或家庭,比起過去那個被描述成很不自由因此應該被棄絕的時代,所有社會單位加諸於個人身上的種種「服從性」限制,卻不知大了多少;絕大多數國家的強制力早就超過歐威爾所描繪的「老大哥」,絕大多數企業以為只要符合勞基法就可以無限地役使勞工,絕大多數的父母也以為只要「為了小孩子好」就可以將他們合理地推入一個沒有自我的升學地獄中。
沒錯,這就是今天,一個既自由又毫無自由的時代。
栗原康講得直率:「如今人的言行舉止都被設定了同一種標準,讓大家以為非得照著這個標準生活不可,有夠麻煩!人的言行舉止應該要更加自由不拘才對。為了得到想要的東西,不應該是照著被規定好的程序來想著該怎麼做,而是要更直接地想著是否自己真的好想要,再為此認真地發揮創意,這才叫夢想,這才是真正的魔法。」
若非如此,一生只在致力完成其他人的夢想,哪叫自由!
日本社會的矛盾日常:「絆」與「縛」
當然,沒必要以為在所謂「大同」世界中,大家的問題必然都一樣,說到底還是「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更甚者,當我們設法去看待瞭解這個世界時,最怕的其實就是「以為我們就代表了整個世界」,雖然這是許多研究者自然會陷入的最大盲點。就這點來說,栗原康做得還不錯。雖然他也時常不經意地流露出類似的邏輯錯誤,至少因為採取了直接面對讀者的寫法,從而讓他的描繪對象被突顯出來。
他要帶領大家審視的目標,就是日本。
眾所周知,「絆」,乃是日本社會中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從某個角度看,也可說是一種「日本式的關係」。所謂絆,簡單來說就是羈絆或牽絆。他以東北大地震為例,「事實上,明明只要推廣無償的愛及憐憫之情這樣的理念就好了,卻硬是被加上稱為『羈絆』的社會道德感,現在甚至連『東北及關東地區的食物很危險,最好別吃』或『在輻射線下工作很危險,不要去比較好』等等的意見,都自我約束,不說出口;我們在精神上的負擔過於沉重,令人動彈不得。」事實確是如此。
我認為,所謂「絆」的相對面就是「縛」,也就是一種把人跟人緊緊地束縛在一起的強大能量。這麼作或這麼想的源起不難理解:生存壓力愈大,人際關係自然愈緊密,這也是「一把筷子」的自然之理。身在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嶼,日本社會的這種選擇很合理,台灣也差不多,所謂「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既表現了我們對人情味的重視,也凸顯出某種「絆」的味道。當然,兩者在程度上大有不同,由於受到制度設計(存在千年的封建體制)的強化,事實上讓日本「縛」的能量遠超過了「絆」,這便是栗原康前面指出的現象。
不過,正如經典力學對於「牛頓第三定律」的描述,當物體互相作用時,彼此施加於對方的力,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力必會成雙結對地出現:其中一道是「作用力」,另一道力則為「反作用力」或「抗力」,兩道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也就是說,隨著愈來愈強的牽絆帶來更大的束縛,尋求解放的欲望也更加強烈。以十九世紀末的近代化運動為契機,在透過維新強化國家職能,慢慢走向政治軍國主義的同時,一股虛無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浪潮也隨之蔓延開來,至今仍在日本的文學、思想與評論界蔚為主流。
栗原康所陳述的,就是這種「主流」想法。
由於篇幅有限,對此不能談更多。總之這些對台灣來說可能有點新鮮,非常不主流的論調,在日本並不少見。尤其當所謂「絆」受到政治力加持,部分成為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後,雖看似依舊不可動搖地深植在日本社會中,想拔除它的積極或消極努力仍到處可見。畢竟很多事即便出發點良善,只要過了頭,自然會引發反彈跟矯正的聲浪,何況到了現在,強化「絆」能量的不只是政治力,還加上資本主義在「消費本位」跟「職場倫理」的調味加料,從而讓人們不禁生出為誰辛苦為誰忙的感嘆,這也就是栗原康所謂「生存負債化」的意思。
雖然全書用了非常戲謔輕鬆的字句,他在結語中說得很清楚,「衷心盼望本書能在幫助各位甩開生存負債上,盡一分微力,也希望能在將腐敗資本主義社會連根鏟除上,能有一點幫助。」說來容易,作起來當然不簡單,否則作者又何須如此叨叨絮絮呢。
更重要的,看著別人,總要想想自己。日本如此,台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