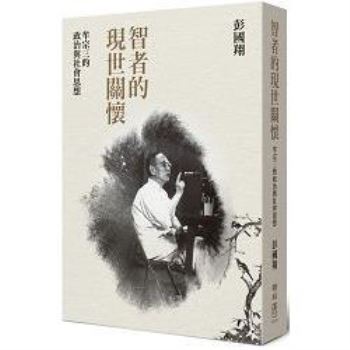第一章、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批判
一、引言
晚清以降,在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中,影響最大並切實改造了中國社會與國家的學說,莫過於馬克思主義。現代新儒學的產生自然有儒學傳統內部的原因,但無疑也是對西方思想的回應。事實上,作為當代新儒學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牟宗三一開始就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自覺地回應。這也是研究當代新儒家與西方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牟宗三與馬克思主義的專題研究。本章即專門考察牟宗三對於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牟宗三一生對於共產主義的批判,也正是建立在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理解之上。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迅速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有勢力的社會思潮。那些嚮往通過革命來使中國迅速步入現代國家的知識青年,尤其是不以純粹學術研究為然而熱中於投身社會運動者,幾乎無不對馬克思主義趨之若鶩。正如當時中國思想界的親歷者郭湛波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所謂:「近五十年中國思想之第三階段,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主要思潮,以辯證法為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同樣是見證人的孫道升(一九○八─一九五五)將當時的哲學界分為兩系八派,他在論述「新唯物論」(即辯證唯物論)時也指出:「這派哲學,一入中國,馬上就風靡全國,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實在不小,就連二十四分的老頑固受了他的薰染,馬上都會變為老時髦。平心而論,西洋各派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為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肩的。」身在時代思潮之中的牟宗三,自然也免不了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在北平念書的時候,坊間的書店,滿坑滿谷都是左傾的書。北平在當時是最左傾的。從那個時候,共產黨那一套ideology就征服了中國。」「照我個人講,當我在學校讀書時,左傾的思想滿天下。那一套ideology,我通通都讀。……那時候我把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通通都拿來讀,它有一定的講法,我也很清楚。」對於馬克思主義,牟宗三可以說是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但是,牟宗三並未像當時大部分的知識青年一樣被馬克思主義裹挾而去,而自始即對馬克思主義從學理上進行了分析考察。他生平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七、八日刊登於《北平晨報》第一六二、一六三期的〈辯證法是真理嗎?〉當時二十二歲的牟宗三正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而牟宗三在二十世紀三○年代發表的一系列批判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文章,都是他純粹從學理本身立論的嚴肅的學術論文。正如他後來回憶所說:
這些我通通讀,可是我卻沒有受它的影響,讀哲學系的人多得很,比我聰明的人多得很,但是沒有人好好考慮馬克思這些話站得住站不住。我沒有偏見,我不是資本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官僚,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也沒有身分。我只是把它們一個個衡量,就發現沒有一個站得住的。你馬克思批評邏輯,我就把邏輯仔細地讀一讀,law of contradiction(矛盾律)、law of identity(同一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排中律)這三個思想律是什麼?你唯物辯證法怎樣來批駁這三個思想律?是不是相應?三個思想律能不能反駁?你的批駁對不對?
仔細考察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之後,我們就會發現,牟宗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生拒斥,實在是基於其三○年代即已形成的理性認知和判斷。他一生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對於共產主義許多情見乎詞的批判,首先和根本的並不是一種情感性的反應,而是基於他自己對共產主義基本觀念的理解和判斷。在其離開大陸之後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幾乎隨處可見的對於共產主義的頗具情感色彩的批判,不過是他自己理性認識的感性表達而已。這一點,在本書第四章關於牟宗三批判共產主義的部分,會有進一步專門的討論。
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系統批判主要見於其二十世紀三○年代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之中。除了上述〈辯證法是真理嗎?〉這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字之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哲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牟宗三發表了〈矛盾與類型說〉。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北平民有書局出版的張東蓀主編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上卷中,牟宗三發表了兩篇文章:〈邏輯與辯證邏輯〉和〈辯證唯物論的制限〉。這幾篇文章主要都是批判唯物辯證法的。而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發表於《再生》半月刊的〈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則是牟宗三針對唯物史觀的系統和集中批判。至於張東蓀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下卷中所收牟宗三的〈唯物史觀與經濟結構〉,其實是〈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一文的前五部分。大概由於〈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最後部分是牟宗三提出了自己解析社會轉變的原則,所以〈唯物史觀與經濟結構〉一文未收。以下,我們就根據這些文字,並結合其他相關文獻,分別探討牟宗三從學理上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二、唯物辯證法批判
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自我理解還是從牟宗三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的理解來看,唯物史觀都是內在地包涵了唯物辯證法。即便是對唯物史觀的考察,也不能脫離對唯物辯證法的分析。因此,我們首先考察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的批判,再探討他對唯物史觀的批判。
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來看,唯物史觀是先於唯物辯證法的。不過,唯物辯證法被認為是超越並否定了形式邏輯的新的思想方法,同時也是貫穿於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謂:「辯證法突破了形式邏輯的狹隘界限,所以它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唯物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的批判,正是首先從邏輯的角度著手。當然,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在二十世紀三○、四○年代的中國,牟宗三在邏輯學方面的造詣堪稱一流,較金岳霖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牟宗三發表於三○年代的有關邏輯的一系列文章,都代表當時中國邏輯學者的最高水準,絕對值得在邏輯研究自身的脈絡中予以探討。不過,我們還必須看到,對於牟宗三撰寫的這些有關邏輯的文章,最重要的諸如前文提及的〈邏輯與辯證邏輯〉和〈辯證唯物論的制限〉,其目的和用意除了澄清邏輯本身的問題之外,正在於批判唯物辯證法這一當時所謂的「辯證邏輯」或「新邏輯」。
(一)以維護形式邏輯的方式批判唯物辯證法
首先,牟宗三從邏輯方面維護傳統形式邏輯的三個基本法則,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指出所謂辯證邏輯對於形式邏輯三大法則的顛覆不能成立。當時宣導唯物辯證法的陳啟修(一八八六─一九六○,又名陳豹隱)曾經在其所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一書中對形式邏輯的三大法則逐一批評,牟宗三則在其〈邏輯與辯證邏輯〉一文中逐一進行了回應。
對於同一律,陳啟修有兩點批評。他說:
從表面上看來,自同律的要求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但是他有兩種缺點。第一點,與實際上的事實不合〔……〕如說農民是農民,這一自同律的命題,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內容。農民中有地主、富農、中農、小農、佃農、貧農等〔……〕同是農民,隨時代的不同,而其性質也大有變動。又如說,我是我這一命題,我有幼年、壯年、中年、老年、衰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身體及知識都有了改變了。所以對於一個對象所反映的概念,要求永遠同一的內容,那是不可能的。第二點,依自同律,標識的總計就是概念。概念既要求永遠同一的內容,就是要求標識的不變;如此,則根本否認了發展,否認新的事像的出現。但是事實上,新的事像是常常發生的。自同律只能認識外部的標識,不能深探內部的關聯;只能認識表面的虛象,不能把握真正的本質。
針對這兩點批評,牟宗三分別予以反駁。他說:
你須知同一律並不反對農民中有富農、有中農、有小農佃農等,它也不反對同一農民可以隨時空而不同,它也不反對他有多種性質。我之有壯年老年,同一律也並非不承認,今日之我非昔日之我,同一律也決不否認,它也不否認知識自體之變化。你幾曾見過有人強不同以為同來?你幾曾見過有人這樣施用同一律來?照你這樣說,好像以前的人都不知道有富農、中農、佃農、小農、幼年、壯年、老年、衰年,等你辯證邏輯家出來才發見了這個真理似的。照你這樣反對,則物理、化學一切其他的學問皆可來反對邏輯,皆可來反對同一律。何其謬也!對象之變化與思想之進行尚且分不開,還談什麼邏輯?
同一律與標識的總計所得的概念有什麼關係?他何曾要求概念的內容永遠不變?他何曾要求對象的標識不變?他也何曾否認事物的發展與新事象的出現?你須知對象的發展與性質和同一律是兩回事,你須知解析對象的發展與性質的理論或學問與同一律也是兩回事的。你就忘記了「說話要合邏輯」這句普通的話嗎?就是你主張唯物辯證法,你作這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不也是有條有理的嗎?你如果真正能否認了邏輯否認了同一律,則不但我,就是全體人類,也早就不知你之所云了。
當然,牟宗三上述的反駁看起來還只是反問。除此之外,對於什麼是同一律,牟宗三還從正面進行了申論。他說:
同一律決不是指兩件具體東西之相似而言,它是要確定一個東西之自身同一。
同一律決不是對象本身各分子間的同一與否,也不是對象本身各時代各地方間的同一與否,它決不禁止事物的變遷與發展,它也決不禁止一個東西有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從這方面來反對同一律,完全不明白什麼是邏輯,什麼是同一律。……同一律不是解析對象諸性質諸關係的命題,它乃是理性開始發展之先在運用(antecedent function),它乃是理性的開荒之先鋒隊。它是「是」這個概念的確定,不是對象本身的性質之是此是彼、是紅是白的確定。
同一律是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證的東西,這就是他的根本處。你不能拿著事物的變化與性質來否定它。
對於矛盾律,陳啟修的批評如下:
矛盾律是自同律向反面表示,他的公式是「甲非非甲」或「甲不能同是乙又是非乙」。這個原則要求同一主辭不能有兩個相矛盾的賓辭;反過來說,他要求同一的賓辭,對於同一的主辭不能同時又被肯定又被否定。矛盾律表面上很合理,仍是不合事實。譬如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方反對帝國主義,進行世界革命,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各國相依存,如通商關係。這種事實上矛盾的存在,是形式論理所無力處理的。
針對這一點批評,牟宗三反駁說:
矛盾律何曾要求同一主辭不能有兩個相矛盾的賓辭?(其實在此所謂矛盾就是不通的,辯證邏輯家每以一物之具有數種性質、數種關係為矛盾,真是不明白矛盾為何物,不通已極!)它又何曾要求同一的賓辭?矛盾律與物體之多種性質有什麼關係?它何曾禁止物體之多種性質、多種關係?以物體之多種性質同時存在來反對矛盾律,真是荒謬絕倫。……蘇聯一方反對帝國主義,一方與帝國主義相依存,這正是它的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這與矛盾律有什麼關係?矛盾律何曾否認了它的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矛盾律是兩個命題的矛盾的禁止,並不是命題所指示的對象之多種性質的同時存在的禁止。你總不能說它是社會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吧!矛盾律就在這裡。如果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含著非社會主義的成分,這也只表示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就含有多種成分、多種性質在其內,也仍不能否認了矛盾律。
一、引言
晚清以降,在傳入中國的各種西方思想中,影響最大並切實改造了中國社會與國家的學說,莫過於馬克思主義。現代新儒學的產生自然有儒學傳統內部的原因,但無疑也是對西方思想的回應。事實上,作為當代新儒學最為重要的人物之一,牟宗三一開始就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自覺地回應。這也是研究當代新儒家與西方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迄今為止,還沒有牟宗三與馬克思主義的專題研究。本章即專門考察牟宗三對於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牟宗三一生對於共產主義的批判,也正是建立在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核心理論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理解之上。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迅速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有勢力的社會思潮。那些嚮往通過革命來使中國迅速步入現代國家的知識青年,尤其是不以純粹學術研究為然而熱中於投身社會運動者,幾乎無不對馬克思主義趨之若鶩。正如當時中國思想界的親歷者郭湛波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所謂:「近五十年中國思想之第三階段,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為主要思潮,以辯證法為方法,以辯證唯物論為基礎,以中國社會史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鎖鑰。」同樣是見證人的孫道升(一九○八─一九五五)將當時的哲學界分為兩系八派,他在論述「新唯物論」(即辯證唯物論)時也指出:「這派哲學,一入中國,馬上就風靡全國,深入人心。他的感化力實在不小,就連二十四分的老頑固受了他的薰染,馬上都會變為老時髦。平心而論,西洋各派哲學在中國社會上的勢力,要以此派為最大,別的是沒有一派能夠與他比肩的。」身在時代思潮之中的牟宗三,自然也免不了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們在北平念書的時候,坊間的書店,滿坑滿谷都是左傾的書。北平在當時是最左傾的。從那個時候,共產黨那一套ideology就征服了中國。」「照我個人講,當我在學校讀書時,左傾的思想滿天下。那一套ideology,我通通都讀。……那時候我把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通通都拿來讀,它有一定的講法,我也很清楚。」對於馬克思主義,牟宗三可以說是有相當深入的了解。但是,牟宗三並未像當時大部分的知識青年一樣被馬克思主義裹挾而去,而自始即對馬克思主義從學理上進行了分析考察。他生平第一篇發表的文章,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七、八日刊登於《北平晨報》第一六二、一六三期的〈辯證法是真理嗎?〉當時二十二歲的牟宗三正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學生。而牟宗三在二十世紀三○年代發表的一系列批判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文章,都是他純粹從學理本身立論的嚴肅的學術論文。正如他後來回憶所說:
這些我通通讀,可是我卻沒有受它的影響,讀哲學系的人多得很,比我聰明的人多得很,但是沒有人好好考慮馬克思這些話站得住站不住。我沒有偏見,我不是資本家,不是地主,也不是官僚,在社會上沒有地位,也沒有身分。我只是把它們一個個衡量,就發現沒有一個站得住的。你馬克思批評邏輯,我就把邏輯仔細地讀一讀,law of contradiction(矛盾律)、law of identity(同一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排中律)這三個思想律是什麼?你唯物辯證法怎樣來批駁這三個思想律?是不是相應?三個思想律能不能反駁?你的批駁對不對?
仔細考察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之後,我們就會發現,牟宗三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一生拒斥,實在是基於其三○年代即已形成的理性認知和判斷。他一生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之後對於共產主義許多情見乎詞的批判,首先和根本的並不是一種情感性的反應,而是基於他自己對共產主義基本觀念的理解和判斷。在其離開大陸之後公開發表的言論中幾乎隨處可見的對於共產主義的頗具情感色彩的批判,不過是他自己理性認識的感性表達而已。這一點,在本書第四章關於牟宗三批判共產主義的部分,會有進一步專門的討論。
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系統批判主要見於其二十世紀三○年代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之中。除了上述〈辯證法是真理嗎?〉這第一篇正式發表的文字之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哲學評論》第五卷第二期,牟宗三發表了〈矛盾與類型說〉。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北平民有書局出版的張東蓀主編的《唯物辯證法論戰》上卷中,牟宗三發表了兩篇文章:〈邏輯與辯證邏輯〉和〈辯證唯物論的制限〉。這幾篇文章主要都是批判唯物辯證法的。而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發表於《再生》半月刊的〈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則是牟宗三針對唯物史觀的系統和集中批判。至於張東蓀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下卷中所收牟宗三的〈唯物史觀與經濟結構〉,其實是〈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一文的前五部分。大概由於〈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最後部分是牟宗三提出了自己解析社會轉變的原則,所以〈唯物史觀與經濟結構〉一文未收。以下,我們就根據這些文字,並結合其他相關文獻,分別探討牟宗三從學理上對於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批判。二、唯物辯證法批判
無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自我理解還是從牟宗三對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的理解來看,唯物史觀都是內在地包涵了唯物辯證法。即便是對唯物史觀的考察,也不能脫離對唯物辯證法的分析。因此,我們首先考察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的批判,再探討他對唯物史觀的批判。
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來看,唯物史觀是先於唯物辯證法的。不過,唯物辯證法被認為是超越並否定了形式邏輯的新的思想方法,同時也是貫穿於唯物史觀的基本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謂:「辯證法突破了形式邏輯的狹隘界限,所以它包含著更廣的世界觀的萌芽。」「唯物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於辯證法才有可能。」牟宗三對於唯物辯證法的批判,正是首先從邏輯的角度著手。當然,之所以如此,也是因為在二十世紀三○、四○年代的中國,牟宗三在邏輯學方面的造詣堪稱一流,較金岳霖等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牟宗三發表於三○年代的有關邏輯的一系列文章,都代表當時中國邏輯學者的最高水準,絕對值得在邏輯研究自身的脈絡中予以探討。不過,我們還必須看到,對於牟宗三撰寫的這些有關邏輯的文章,最重要的諸如前文提及的〈邏輯與辯證邏輯〉和〈辯證唯物論的制限〉,其目的和用意除了澄清邏輯本身的問題之外,正在於批判唯物辯證法這一當時所謂的「辯證邏輯」或「新邏輯」。
(一)以維護形式邏輯的方式批判唯物辯證法
首先,牟宗三從邏輯方面維護傳統形式邏輯的三個基本法則,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指出所謂辯證邏輯對於形式邏輯三大法則的顛覆不能成立。當時宣導唯物辯證法的陳啟修(一八八六─一九六○,又名陳豹隱)曾經在其所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一書中對形式邏輯的三大法則逐一批評,牟宗三則在其〈邏輯與辯證邏輯〉一文中逐一進行了回應。
對於同一律,陳啟修有兩點批評。他說:
從表面上看來,自同律的要求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但是他有兩種缺點。第一點,與實際上的事實不合〔……〕如說農民是農民,這一自同律的命題,可以有種種不同的內容。農民中有地主、富農、中農、小農、佃農、貧農等〔……〕同是農民,隨時代的不同,而其性質也大有變動。又如說,我是我這一命題,我有幼年、壯年、中年、老年、衰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身體及知識都有了改變了。所以對於一個對象所反映的概念,要求永遠同一的內容,那是不可能的。第二點,依自同律,標識的總計就是概念。概念既要求永遠同一的內容,就是要求標識的不變;如此,則根本否認了發展,否認新的事像的出現。但是事實上,新的事像是常常發生的。自同律只能認識外部的標識,不能深探內部的關聯;只能認識表面的虛象,不能把握真正的本質。
針對這兩點批評,牟宗三分別予以反駁。他說:
你須知同一律並不反對農民中有富農、有中農、有小農佃農等,它也不反對同一農民可以隨時空而不同,它也不反對他有多種性質。我之有壯年老年,同一律也並非不承認,今日之我非昔日之我,同一律也決不否認,它也不否認知識自體之變化。你幾曾見過有人強不同以為同來?你幾曾見過有人這樣施用同一律來?照你這樣說,好像以前的人都不知道有富農、中農、佃農、小農、幼年、壯年、老年、衰年,等你辯證邏輯家出來才發見了這個真理似的。照你這樣反對,則物理、化學一切其他的學問皆可來反對邏輯,皆可來反對同一律。何其謬也!對象之變化與思想之進行尚且分不開,還談什麼邏輯?
同一律與標識的總計所得的概念有什麼關係?他何曾要求概念的內容永遠不變?他何曾要求對象的標識不變?他也何曾否認事物的發展與新事象的出現?你須知對象的發展與性質和同一律是兩回事,你須知解析對象的發展與性質的理論或學問與同一律也是兩回事的。你就忘記了「說話要合邏輯」這句普通的話嗎?就是你主張唯物辯證法,你作這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不也是有條有理的嗎?你如果真正能否認了邏輯否認了同一律,則不但我,就是全體人類,也早就不知你之所云了。
當然,牟宗三上述的反駁看起來還只是反問。除此之外,對於什麼是同一律,牟宗三還從正面進行了申論。他說:
同一律決不是指兩件具體東西之相似而言,它是要確定一個東西之自身同一。
同一律決不是對象本身各分子間的同一與否,也不是對象本身各時代各地方間的同一與否,它決不禁止事物的變遷與發展,它也決不禁止一個東西有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從這方面來反對同一律,完全不明白什麼是邏輯,什麼是同一律。……同一律不是解析對象諸性質諸關係的命題,它乃是理性開始發展之先在運用(antecedent function),它乃是理性的開荒之先鋒隊。它是「是」這個概念的確定,不是對象本身的性質之是此是彼、是紅是白的確定。
同一律是既不能證明也不能否證的東西,這就是他的根本處。你不能拿著事物的變化與性質來否定它。
對於矛盾律,陳啟修的批評如下:
矛盾律是自同律向反面表示,他的公式是「甲非非甲」或「甲不能同是乙又是非乙」。這個原則要求同一主辭不能有兩個相矛盾的賓辭;反過來說,他要求同一的賓辭,對於同一的主辭不能同時又被肯定又被否定。矛盾律表面上很合理,仍是不合事實。譬如社會主義的蘇聯,一方反對帝國主義,進行世界革命,同時又與帝國主義各國相依存,如通商關係。這種事實上矛盾的存在,是形式論理所無力處理的。
針對這一點批評,牟宗三反駁說:
矛盾律何曾要求同一主辭不能有兩個相矛盾的賓辭?(其實在此所謂矛盾就是不通的,辯證邏輯家每以一物之具有數種性質、數種關係為矛盾,真是不明白矛盾為何物,不通已極!)它又何曾要求同一的賓辭?矛盾律與物體之多種性質有什麼關係?它何曾禁止物體之多種性質、多種關係?以物體之多種性質同時存在來反對矛盾律,真是荒謬絕倫。……蘇聯一方反對帝國主義,一方與帝國主義相依存,這正是它的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這與矛盾律有什麼關係?矛盾律何曾否認了它的多種性質與多種關係?矛盾律是兩個命題的矛盾的禁止,並不是命題所指示的對象之多種性質的同時存在的禁止。你總不能說它是社會主義又不是社會主義吧!矛盾律就在這裡。如果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含著非社會主義的成分,這也只表示那個社會主義社會就含有多種成分、多種性質在其內,也仍不能否認了矛盾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