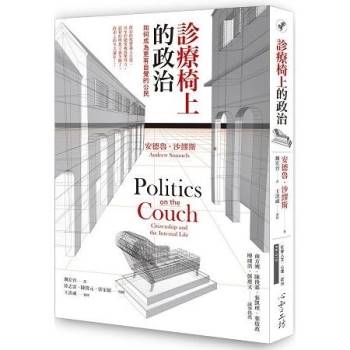前言
就某個角度而言,《診療椅上的政治》是三部曲的結語。這三部曲始於《多重心靈》(The Plural Psyche, 1989),隨後是《政治心靈》(The Political Psyche, 1993)。這系列的前兩部企圖連結我們內在與外在世界、也就是在看似對立的心理治療與政治兩個領域間建立起連結;這本書雖然延續著這樣的主旨,但還是經常挑戰自己以前的論點。而且,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是因為針對我先前提出概念的迴響所帶來的刺激而促成的。
《診療椅上的政治》為此三部曲中最具企圖心的作品,足以呈現我向來想創造一種新語言的努力。因此,正如其他兩本書的內容,我也以自己的文字能力儘可能地做到這一點。
如同所有作者一樣,我也一直好奇讀者會如何讀這本書。讀者會將這書當成一位教授還是一位心理治療師的文本來閱讀?這兩種角色尋求真理的途徑是十分不同的,看待各種情感的相對重要性和呈現在個人行為的方式也大不相同。對治療師來說,關鍵的考驗是一個人如何經驗「內在」(inside),他或她在私人領域中如何夢想、如何發展關係與言行。對學者而言,這些或許都重要,整體所強調的是──唉,沒錯,就是學術。
這書看來會像是一位百分之百就是治療師的人所寫的,還是一個剛好是治療師的公民所寫的?有時人們會跟我說,「是的,書很有趣也實用,但說那樣的東西不必通過治療師的口。你難道就不能針對這些議題提出一些治療專業的觀點嗎?」還有人說,「沒錯,專業的治療師和分析師對你的觀點會感興趣,但在政治上又有啥實用性呢?」我在1990年代工黨黨員大會組織了一些週邊的會議,同時也進行演說,就是典型例子。經由這些狀況,我已經開始熟悉如何面對這些質疑。有時,這兩種反應甚至在同一場演講裡出現。
會有這樣的情形,部分問題是出在心理治療及其思維方式並未被廣泛認同,在公眾對話中也還沒廣泛地受到歡迎的緣故。治療師經常被看成與現實社會脫節的人,因此也就是不可信任的人。然而,握有權勢的政客與名嘴,既然對我們的政治文化沒做出什麼了不起的定義或實踐,他們也就沒法拒絕這些不在他們控制內的思考方式。
而這本書會被當成「榮格學派」的文本來閱讀嗎?我曾在《政治心靈》中試著評論榮格的反猶太主義,建議當今的榮格分析師對榮格過去的言行進行修補。許多同儕不僅欣然接受了這個提議,還和我一起努力共同檢視榮格理論的整個光譜,看看有哪些是需要調整甚至該放棄的。針對榮格有關文化與心靈的概念進行批判式的分析後,現在可以自在地將這些自己真的感到相關且有用的概念組合一起。
然而,就自己的專業認同而言,我會比較喜歡被當成一位具後榮格學派(post-Jungian)訓練背景的心理治療師。在佛洛伊德派的精神分析圈子裡和在知識圈,一般還是會將「榮格學派」貼上特定的污名標籤,導致人們對他的作品有所質疑。如果「榮格學派」是這樣,那讓我直說:這本書不是一部「榮格學派」的著作,不應以這個角度閱讀。這本書應從它自有的價值來進行判讀。或者,依序言的看法來釋義的話,書中任何錯誤皆當歸咎於作者,而非卡爾‧古斯塔夫‧榮格之過。
最後,本書的經驗基礎是來自於我參與過的數個政治性組織,和最近的政治發展。我持續在英國、美國、巴西、以色列和南非為政治人物、政治組織、社運團體以及一般大眾,進行諮商工作且帶領工作坊;去探索這些源自於心理治療的觀點,在政策形成中、在思考政治歷程的新方法裡,以及在政治衝突的解決中,究竟可以發揮到怎樣地有用且有效的程度。因為要對政治進行治療性的思維是困難的,因此對主流的政治人物而言,譬如美國民主黨的參議員或是英國工黨的黨委,要他們因此而嚴肅地加以看待這些見解是困難的。至於「非主流」(alternative)政治人物或者組織,這困難也沒有比較少。但這完全不是問題。我在那些工作坊與諮商裡所體驗過、目睹過,以及發現過的東西,為《診療椅上的政治》這本書裡的論證,提供了經驗的基礎。
這本書所討論的活動,我也曾經在參與三個組織建立的過程中經歷並積極介入。「追求社會責任的治療師與諮商師」組織(Psychotherapists and Counsellor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想幫助治療師與諮商師們,如何去運用他們的知識和經驗,以專業能力進入社會與政治事務。第二個組織是「解藥」(Antidote),一個以心理治療為基礎的智庫。這個智庫採行多種領域的工作方式,尋求的連結早已不只是心理治療領域的人。「解藥」如今已著手進行金錢與經濟事務的心理態度研究,且從事將情感素養(emotional literacy)應用到政治上的嘗試。
第三個組織是「聖詹姆士連線」(St James’s Alliance)(現今已不復存在)。總部在倫敦市中心的教堂,成員來自不同的領域,包括政治學、經濟、倫理學、宗教、非政府組織、媒體,和心理治療界。這個組織試圖將倫理的、靈性的和心理的關懷,整合到英國的政治議題中,並且促進非政府組織、單一議題團體、與社會運動團體之間的對話。這是個將過去經常處於分裂與虛耗的政治能量加以結合和運用的實驗。
我希望這樣就說得夠明白了。我認為心理治療師如果想贏得搞政治的傢伙們更多的重視,心理治療的許多概念與實務就需要改變。如果要對公眾生活有所貢獻,試圖讓人聆聽到他們的意見,心理治療師也需要一些改革。
本書前面兩章是同一單元,提出以心理治療出發的方式來進行政治活動的價值開場,同時也解釋轉型政治(transformative politics)的主要原理。第三、四與五章運用性別、性與「內在家庭」(internal family)的概念,去規劃和主張如何面對政治歷程的新態度,也探討政治變遷的起源。六、七兩章討論政治中的「夠好就好」(good-enoughness),先是與領導方式有關的,其次是和父權有關。接下來的五章重點在於政治性的主題:靈性的政治、經濟、如何將心理治療的價值與實務運用到政治目的上、運用到公民與國家的關係,以及運用到國族心理學。最後,第十三章對整本書的諸主題再一次強調與延伸。
第一章
政治的私密生活
在許多西方的國家裡,政治已經是完全破碎,而且一團混亂:面對這情形,我們亟需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透過本書我將清楚地說明這主張,心理治療對政治的全面轉型/轉化(transformation)可以有一定的貢獻。身為心理治療師,他們工作上可以不管政治的敗壞,繼續僅僅聚焦在個人的轉化上。或者,他們也可以試著把對個人的關注,轉化成對社會與政治的關注,因而有助於政治的活力復甦。
當今的政客讓人民感到深深的絕望與厭惡。他們缺乏品德、沒有想像力,並且是了無新意。自西徂東,全世界都在尋求新的政治典範。而心理治療對這一點之所以能有所貢獻,是可以開啟內在現實與政治世界之間雙向的溝通。身為治療師的我們在嘗試去理解情感、個人和家庭經驗的內在世界的秘密政治時,也同時必須試著揭示強加於外在世界裡一切事務的秘密心理,像是領導權、經濟、環保以及民族主義等等,而將兩者加以平衡。
因此,這些問題要先加以回答:
•當前政治現實所提供的願景,以及幾個政黨對未來的所謂設想,可以帶給我們多少的快樂?
•我們同意政治人物所設定的目標嗎?
•我們能做得更好嗎?如果答案是對的,那麼在個體層面以及在社會層面我們又該做怎樣的改變?
•政治體系要怎樣改變,才能重新贏得包括廣泛年輕族群在內的那些已經疏離的和被排擠的團體或個人的敬重?
如果能夠將眼前這些缺乏深思熟慮的、只是直覺式的政治概念與承諾,努力變得更準確而敏銳。當人們有意願介入時,就能採取更有效的政治行動;於是,他們想這麼做的欲望也會增強。每個人的內在都有被埋葬的、關於政治智慧的源頭;我們在每個人對政治世界正發生的事所做出的個人反應裡,看到了這些政治智慧。然而,這樣的個人反應顯然是沒有出路的,因此持續處於私密狀態。本書將提出一些方法,將這些通常被認為是極度私密的事物,像是童年經驗、親密關係、幻想(包括性幻想)、夢,以及身體感覺等,透過這些私密的重新組構,而轉變成有用的、具轉型效果的政治手段。
我們的內在世界也好,我們的私密生活也好,都隨著政策的決定與既存的政治文化而顛沛受苦。然而,我們負責制定政策的各種相關委員會裡,為什麼都沒找心理治療師參與而成為其中一名專家?這不是呼籲要成立心理治療師委員會!但就如同委員會裡通常會有統計學的專家出席,儘管他的角色未必全然受到其他成員的歡迎;同樣的,這些會議桌也該留給治療師一席之地。人們將期待治療師對涉及人際關係的這些社會議題,提出意見。相反的,媒體經常深入討論男人是否能夠或怎樣才可以成為照顧他人的角色,也討論女性與男性之間政治結盟可以到怎樣的程度。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政治生活裡的傳統面向(經濟狀態、領導力、民族主義),也越來越多是以心理治療的角度檢視。而這些現象都是這本書的討論中將會逐一探討的。
這些年來我們社會如此流行「情緒智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或「情緒素養」(emotional literacy)等新名詞,其實是因為我們想要提高自我認識的內在需求。然而,這些新詞的流行不單單只是在私人的生活面。現代的社會讓我們陷入不確定的狀態,我們的感覺因此失去了可依循的軌道,而滑落到憂鬱與無助的情境。如果可以將情緒素養的概念延伸到公共領域,我們的公民意識就可以在以個人的感受和體驗作為基礎的前提下,願意去從事政治活動,並且因為可以知道彼此是一致的,而感覺是安全的。
心理治療觀點對政治生活的另一個可能的重大貢獻,就是幫助人們去面對不可避免的失望。這是心理治療最具價值的成果之一,心理治療的歷程中經由辛苦努力而體驗到的是:人們因此體會到自己擁有足夠的力量,去突破教我們絕望的障礙,而且是值得繼續奮鬥的。
許多心理專業相關工作的人經常認為政治令人作嘔,與之牽涉會有辱自己的身分,而且會失去自我尊嚴。而專業心理治療師通常也因為臨床工作的繁重,忙到無暇顧及政治。同樣地,許多政治人物,不管是主流政黨或社會運動的支持者,也經常不屑去進行自我的內在觀照與心理反思,認為這只是浪費時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種習慣性的二分法思維,將政治生活擺一旁,個人生活的創造力擺另一旁;然而這兩者真的毫不相干?有沒有可能積極投入政治而發揮影響力,卻不影響自我尊嚴?如果不這樣做,代價是很大的。如果不對政治危機做出任何回應,我們在政治生活中完全失去任何發言機會。如此一來,這種事將會留給媒體去處理。而我們是知道的,媒體對心理學的應用傾向於症狀的描述,而非提出可能的療癒。
媒體上那些明星專欄作家與自詡為專家的傢伙們,他們在討論政治人物行為時,反覆賣弄心理學的專有名詞。但他們多數只是沾點僞精神分析的方式,討論我們政治領袖人物的「個性」,企圖詮釋他們為何會那樣:美國總統柯林頓是因為有個酒鬼繼父,所以過度急於取悅所有人?英國首相邱吉爾從小不被美麗的母親所疼愛,又太清楚父親的失敗,所以渴望贏得公眾的掌聲?這全是沒啥意義的空談,就像現在的政治人物對「品德」與「遠景」極其簡化的自吹自擂。如同我們對政治領袖不再能有所期待,我們也不該依靠媒體提供政治歷程的洞察力。相反的,我們應該開始回到自身。
揣測當今政治人物心理動機的這一類解謎遊戲,總是讓人著迷。然而,真正有意義的是進行這樣的探討:如果公民開始可以啟動他們政治的自我覺察,找到每個人「內在的政治家角色」(inner politician)。這樣的話,對政治系統產生的影響又會是怎樣呢?如果可以這樣,我們將可以有一個全然不同的基礎,去質問政治人物的種種動機。(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