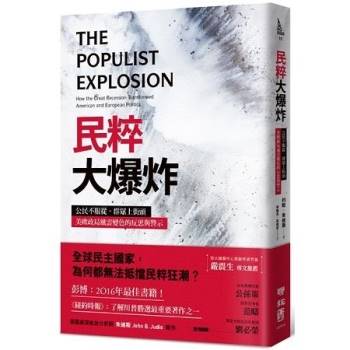民粹主義的過去和未來
川普在美國的競選活動、右翼民粹政黨在歐洲,以及甚至是左翼的五星運動,常被比作是一九二○年代的法西斯。前美國勞動部長萊克(Robert Reich)以〈川普:美國法西斯主義者〉為題寫過一篇專欄文章。史密斯(Jamil Smith)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宣稱:「是的,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Wolfgang Schaeuble)將民族陣線描繪成「不只是右翼政黨,還是……法西斯、極端主義者政黨。」荷蘭哲學學者雷曼(Rob Rieman),控訴威爾德斯的自由黨為一種「法西斯運動」。英國的《旁觀者》雜誌將格里羅(Beppe Grillo)描繪成「義大利的新墨索里尼。例子到處可見。
「法西斯主義」這個詞和「民粹主義」是相似的,也就是很難找出一組特性能夠完全用於定義法西斯運動或政黨。納粹黨讓猶太人這個外來群體成為替罪羔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最初並未針對種族或國籍。然而,在現今民粹派競選活動和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者之間,必然存在一些相似性:領袖魅力,這是很重要的(川普、雷朋、桑德斯和格里羅);對民主規範的誇耀(川普);讓外來團體當替罪羔羊(川普、雷朋、英國獨立黨的法拉吉、桑德斯和丹麥的人民黨)。但現今美國與西歐的民粹主義,和兩次大戰期間的法西斯運動之間,存在兩項重大的歷史差異。……
歐洲的右翼民粹派運動無疑反對超國家的形成。他們想要讓國家再次掌控自己的貨幣、財政政策和邊界。他們不喜歡使用「民族主義者」這個詞彙去描繪他們的目的,因為這個詞彙顯示與歐洲不名譽的過往(擴張主義曾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有所牽連;民族陣線使用主權主義者、而非民族主義者。在丹麥,人民黨發言人伯斯解釋:「民族主義讓人印象不佳,所以我們不稱自己為民族主義者,而是形容自己為國家的。」在西班牙,我們能黨使用愛國的而非民族主義的。但事實上,例如外交政策分析師弗列德曼(George Friedman)所指出,這些運動是民族主義者對抗帝國主義者或全球主義者。相對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主義,他們對歐洲和全球政治,施加了離心力、而非向心力。
川普也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他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並不包括重新占領菲律賓或發動新的征服戰爭。相反地,川普想要撤離未直接威脅美國的海外衝突,並將美國的資源轉而用在重建基礎建設和製造業。他直言批評想在中東單獨依靠美國力量維持和平的新保守主義者。在國內,川普想要建一道牆來阻止非法移民,他想要強化美國的邊境,而非擴展領土。
將這些政黨和競選活動稱為「法西斯主義的」,有別於有效的政治,也的確帶出了這些運動最毒的部分─其他種族和宗教成了他們的替罪羔羊。另以川普而言,則是對暴行的鼓勵─但對了解它們在當代歷史裡的實際角色,並沒有太大幫助。將他們稱為法西斯主義者,誇大了他們所帶來的危險─他們沒有威脅要發動戰爭或解散國會。當未來美國或歐洲的狀況改變時,這或許有可能發生,但它不是一個對他們目前狀況的準確觀點。如果他們令人厭惡,是因為他們公開宣稱某種排外的民族主義、而不是他們的全球野心。
早期預警的民粹主義
根據不正確的歷史對比,對這些競選活動和政黨的大加韃伐,讓人們難以了解為何民粹派的主張與許多民眾的想法產生共鳴,以及他們如何(儘管不完美)指向主要政黨不在乎或忽視的實際問題。基於民粹主義的天性,這些競選活動和政黨透過政見指出問題,但這些政見在目前政治環境下不太可能實現。在某些右翼民粹派的案例裡,他們的政見在某種程度上偏執或挑戰民主規範。在其他案例裡,他們的政見充斥錯誤資訊,但在既有的政治智慧結構下仍感動人心。
人民黨將銀幣自由鑄造視為萬靈丹,或建構一個複雜的國庫分庫計畫來幫助農民都可能是錯的,但公開譴責不受管制的金融和運輸、日增的經濟不平等和貪腐/不民主的政治體系,並非錯誤。龍恩的賦稅計畫並不合理,但他讓羅斯福政府注意到財富的錯誤分配。桑德斯的全民健保和免費大學或許過不了吝嗇的國會那關,且該計畫本身可能必須大幅度地修改,但它們應該是有價值的目標,因它們回應了許多美國人對自身處境所感受到的焦慮。
川普高調威脅,要對中國或將工廠移往墨西哥的製造商課徵巨額關稅,或是想要撕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因為美國與中國的貿易和自由流動的資本有許多問題。根據歐特(David Autor)、多恩(David Dorn)和韓森(Gordon H. Hanson)的資料,一九九九至二○一一年間,從中國的進口貨物讓美國喪失兩百四十萬個工作機會,特別是對底層四○%所得的勞工造成傷害。在二○○○年代,商業部的報告指出,美國跨國企業減少國內兩百九十萬個工作機會,同時在海外創造了兩百四十萬個工作。
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和西班牙我們能黨,最後可能仍將成為德國和歐元區的「模範囚犯」,但它們和民族陣線/五星運動都正確指出歐盟和歐元的機能不佳。在這樣的狀況下,三巨頭之一已改變立場,但為時已晚。在二○一六年六月,希臘已處在財政廢墟之中,國際貨幣基金的期刊《金融和發展》裡,有一篇由三位經濟學者所撰寫題為:〈新自由主義:過度應用?〉的文章,警告「某些新自由主義政策不但沒有帶來成長,還造成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接著危害可持續的經濟擴張。」
右翼民粹競選活動和團體抱持種族主義者、本土文化保護者或仇外的觀點,但他們的抱怨指向了問題的核心。華萊士要求永久隔離,他明顯是種族主義者,但關於將不同種族的學童從市內某社區用巴士強載到另一個社區這件事,他是對的,的確導致白人出於自衛而遷往郊區居住。川普、布坎南、民族陣線和丹麥人民黨,已經挑起民族主義情緒,攻擊非法和合法移民,但關於無技術移民往往拉低薪資和造成公共部門的負擔,他們是對的。
在較深層的意義上,移民下層社會的存在可能會破壞公眾對於福利國家或社會民主基石的信任。社會民主不必然要求種族的齊一性,但當種族的異質性以移民下層社會的方式存在,則可能導致公民較不願意繳稅去支持社會福利。同樣地,如法國社會學者羅伊(Olivier Roy)所警告,像法國這樣下層社會被隔離居住的狀況,可能成為政治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溫床。右翼民粹派錯誤地將伊斯蘭教看成極端主義的原因,以及鼓吹大眾壓抑伊斯蘭教,但他們至少認知到這些社區存在問題,必須加以處理。
民粹主義和新自由主義
在美國,川普和桑德斯攻擊新自由主義的共識,讓二○一六年總統大選的經濟辯論明顯轉向。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黨代表大會裡,很少談到曾經是兩黨經濟主流的供給面經濟良方。川普並未從初選時的立場退卻,而希拉蕊採取了桑德斯許多的主張。這兩位候選人在他們的演講裡都未提到財政赤字,也都沒有論述要減少新自由主義派所稱的「權利」。兩者都主張對貿易協定和外移廠商提高警覺,兩者都承諾將管制華爾街。在初選時,桑德斯是唯一要求再次實施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候選人,但兩黨黨綱都主張實施該法案的某些版本。……
然而,在不久的未來,美國不太可能出現,足以推翻新自由主義和讓政黨調整定位的政治地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已建構在內隱不顯的全球安排上─美國產生大量的貿易赤字,特別是對亞洲國家,而這些國家將從貿易盈餘獲得的美元再送返美國,以資助美國的赤字和提高消費者需求。這樣的安排讓狀況處於危機邊緣和引發危機,但它們至今仍難以撼動。美國的勞動力將持續偏離中產階級,但只要中產階級仍能找到工作,則危機不太可能發生。此外,相較於歐洲,美國處在一個較佳的位置去控制移民的流動,包括未經核准的移民。正在發生的是,對新自由主義行動方案的侵蝕、而非讓它解體。
但用經濟學家史坦(Herbert Stein)的話來說,事情不可能持續下去,絕對不會。維續新自由主義貿易的赤字循環體系、回收的美元,以及私人和政府負債,不會永遠持續下去。當它一旦停止或接近崩潰的邊緣,那麼合理猜測這將會為裴洛、布坎南、桑德斯和川普的競選創造出機會。
歐洲則是全然不同的狀況。歐盟和歐元的建立基於最大善意,但許多歐洲人沒有因此受益,特別是居住在歐元區內較不發達國家的人們。……
當然,不會有聯邦預算的存在。財政政策和所需的收入都仍掌握在國家手上,讓事情變得更糟的是,穩定和成長法案和它二○一二年後續的穩定法案,已經大幅限制使用赤字支出來減緩失業。就像希臘經濟學家瓦魯法克斯和其他左翼經濟學者的建議,歐盟轉向集權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則歐元危機將會結束,但這麼做勢必面臨巨大的阻力,特別是在包括德國、荷蘭和芬蘭等較富有的北歐國家裡。結果是,歐元區難以恢復健康。
會導致歐盟解體的其他因素─從中東和北非大量湧入的尋求庇護者,加上從歐盟本身較窮國家遷往較富裕國家的移民─對歐元危機也有影響。如果人們在某個國家找不到工作,他們可以移往其他國家尋找,這是開放邊界的部分原因。大規模移民,是北歐國家因為本身的成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英國公投脫歐的重要因素。它讓右翼民粹主義獲得成長動力,以及導致諸如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丹麥人民黨、荷蘭自由黨和德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ur Deutschland)等群體,堅定不移地反對任何的聯邦預算用於所得重分配。
歐洲政治的一些專家們,包括牛津大學政治學者杰凌卡(Jan Zielonka)認為歐盟注定解體。雖然超過我臆測的能力,但我認為以下論點是公正的:在歐洲創造出右翼和左翼民粹政黨的壓力將只會愈來愈大,直到除了英國以外的其他幾個國家也決定脫歐。果真如此,則被歐巴馬稱為「現代最偉大成就之一」的歐洲聯盟(EU),將遭遇(譯註:二戰期間由納粹德國提議的)與歐洲邦聯(European confederation)之前嘗試統合時同樣的命運。